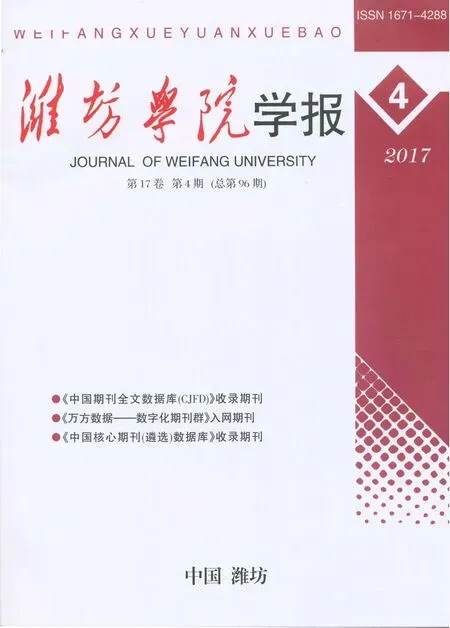《天堂蒜薹之歌》:多重视角下的现实人生
郭晴云
(潍坊学院,山东 潍坊 261061)
《天堂蒜薹之歌》:多重视角下的现实人生
郭晴云
(潍坊学院,山东 潍坊 261061)
《天堂蒜薹之歌》是一部将写实主义创作方法与现代主义表现艺术结合得比较完美的长篇小说。作品围绕着一个突发性重大事件——天堂“蒜薹事件”展开叙述,通过多重话语叙事,对这一悲剧事件进行了立体呈现,从不同侧面、不同角度全方位地反映了天堂县农民当时当下的生存状态,并融入了莫言作为一位极有社会责任感的当代作家,对农村问题深切的人文关怀和人性思考。作品还借助于时空交错、叙述视角的不断切换等叙事技巧,营造出一个多维的叙述空间,形成散点透视结构,为读者提供了文本意蕴解读的多种可能性。本文拟从“小人物”形象的塑造和多重话语叙事两个层面对其进行深入解读,以期更准确地把握这部优秀作品的主旨意蕴和艺术创新价值。
蒜薹事件;人性关怀;叙事多面体;叙述视角
《天堂蒜薹之歌》出版于1988年,是莫言的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长篇小说。作品是以1987年5月发生于山东苍山县的“蒜薹事件”为素材创作的。莫言从报纸上看到有关苍山“蒜薹事件”的报道后,立即中断了之前家族小说、先锋小说的创作实验,只用了35天时间,完成了这部具有写实风格的长篇小说。
天堂县是我国传统的大蒜出口基地,盛产优质蒜薹。上世纪80年代中期,随着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大蒜成为当地的一种主要经济作物。由于蒜薹价格不断攀升,本地政府部门受利益驱动,强行摊派,要求蒜农扩大大蒜种植面积。但是,蒜薹丰收上市后,却由于销售渠道不畅,大量滞销,卖不出去。在蒜薹购销经营和管理中,一些政府职能部门工作严重渎职:蒜薹开始上市时,抬价收购,挤走了外地客户;有的地方为了装满自己的恒温库,不准外地客户收购,甚至连一些村民委员会和蒜农与外地签订的购销合同也强令作废;县工商、税务、路政、环保等部门借机巧立名目,乱收费、滥罚款,榨取蒜农的收入,引起蒜农们的不满。天堂县委、县政府对这些混乱现象没有及时疏导、制止,致使事态不断扩大。5月26日,蒜农们集结在县政府大门外,要求政府负责人出面对话解决问题,但县政府主要负责人却躲藏了起来,只派出政府办公室逄副主任应付他们。蒜农们群情激奋,情绪失控,冲进县政府大院,最终演化成一起针对县政府办公大楼的打砸抢事件,并带来严重后果。事件发生后,虽然上级政府对事件主要责任人县委副书记、县长仲为民给以撤职处分,县委书记纪南城被停职检查,对少数违法分子也依法进行了严惩,但是这样的结果并没有让蒜农们真正接受。中国农民向来靠天靠地吃饭。他们淳朴憨厚,有极强的忍耐力,但是当生存的现实问题摆在面前的时候,他们也会以命相搏。改革开放初期,基层政府部门对市场经济规律不熟悉,对经济发展的掌控能力相对薄弱,而个别基层政府官员为了尽快出政绩,捞取政治资本,搞不切实际的一哄而起,一窝蜂,决策失察,指挥不当。到头来,为他们的渎职行为买单的,只能是普通的农村大众。莫言在《天堂蒜薹之歌·新版后记》中说:“小说家总是想远离政治,小说却自己逼近了政治,小说家总是想关心‘人的命运’,却忘了关心自己的命运。”[1]莫言作为一个有良知的当代作家,用他的直笔艺术化地再现了苍山“蒜薹事件”的全过程,通过对这个事件的叙写,对地方政府、职能部门及主要负责人的渎职行为进行了严厉抨击,对部分基层政府官员素质底下、腐败堕落,无视农民利益,以权谋私,营私舞弊,草菅人命等不法现象给予了深刻暴露;围绕着“蒜薹事件”发生的前前后后,作品还写了高马与金菊的爱情悲剧、四叔遇车祸惨死却得不到应有的赔付、金菊与四婶上吊自杀等一系列的悲剧事件,折射出了当代农村、农民的苦难和艰辛,对造成“蒜薹事件”的主要原因进行了深度挖掘,并试图通过自己的呐喊唤起全社会对当代农村现实的关注、对农民生存环境和现实命运的同情。
一
《天堂蒜薹之歌》是一部农村“小人物”的悲剧。
与莫言的其他作品浓墨重彩地渲染主要人物不同,《天堂蒜薹之歌》没有中心人物,没有高大上的正面主人公,但这丝毫不影响作品在人物塑造方面的成就。莫言曾说:“这是一部小说,小说中的事件,只不过是悬挂小说人物的钉子。”[2]作品紧紧围绕着天堂“蒜薹事件”的发生,塑造了高羊、高马、金菊、四叔、四婶、方家兄弟等一批卑微的“小人物”形象,他们没有干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业,他们都是一些生活在最凡俗的农村社会中的普通的农民,但个个形象鲜明生动。
高羊是一个顺民。他心地善良,胆小怕事,为求生存,对任何人都卑躬屈膝,却永远得不到人们的尊重。小时候,因为出身地主家庭,他处处矮人一等,被大队长的儿子王泰逼着喝尿。农村土地承包后,“狗崽子”身份逐渐被人们淡忘,但他深知人心险恶,依然事事小心谨慎,苟且偷生。在天堂“蒜薹事件”中,他被人群裹挟进县政府大院,盲目地参加了打砸抢。身体残疾的老婆头一天刚刚生下儿子,第二天他就被警察带走,家里剩下双目失明的八岁小女儿杏花和满院子因卖不出而弥漫着腐烂臭气的蒜薹。被逮捕后,看守警察逼他喝自己的尿,他却违心地装出一副兴奋的样子,说那是“高级葡萄酒”。在监狱里,与他同处一室的囚犯也逼着他喝尿,他忍辱含垢。没有人同情他,没有人怜悯他。高羊的生存法则就是“忍”。他对于不公平的事,绝不会抗争。他对方四叔说:“忍着吧,忍过来是个人,忍不过来就是个鬼。”[3]这个人物身上具有浓厚的奴性意识,他自卑到尘埃里,没有尊严,没有人格,就像一头任人宰割的“羔羊”。他只能靠阿Q式的生存本领,才可以勉强保全自己的半条狗命!透过这个卑微的小人物形象,我们不难领悟到作品那惊世骇俗的现实批判力量。辛亥革命推翻封建帝制已七十多年,农村已进行过无数次的政治、经济、社会改革,而当代农民的精神面貌、生存现状和农村的社会现实依然令人担忧!
与高羊的卑微懦弱相比,高马就是一匹桀骜不驯的烈马。高马勤苦善良,意志坚定,嫉恶如仇。他是一个复员军人,对他来说,谋生并不艰难。但由于现实社会的复杂,邪恶势力的猖獗,他遭遇了种种挫折、打击与不幸。在部队里,他因为不愿意依附权贵,得罪了团长的小姨子,所以提干不成,被逼复员;回乡后,他和金菊自由恋爱,遭到方家的嫌弃,被凶狠的方氏兄弟多次羞辱和暴打,政府杨助理员对他百般刁难;他和金菊撕毁“换亲”婚帖,双双出逃,却被杨助理员和方家兄弟抓回来,毒打一顿;他对金菊的爱执着而坚定,决不放弃,方家无奈之下向他勒索一万元钱。他起早贪黑,精心打理自家的蒜地,期望早日与金菊成婚。但丰收的蒜薹却遭遇滞销,卖不出去。他卖蒜薹的称被计量所的人没收,他们把他的秤杆踹断。这一切都让性情耿直,宁折不弯的高马无奈,愤怒,忍无可忍,他就像一个随时可能爆炸的火药桶,只需要一根导火索。高马终于在天堂“蒜薹事件”中爆发,他跳到车上高喊“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官僚主义”,把卖不出去的蒜薹抛到县政府大院里。冲进县政府大楼后,他砸电话机,放火焚烧档案,打伤打字员。跟高羊的另一点不同在于,高马是一个自觉的“暴民”。在经历多次挫折之后高马开始消极反抗,他明知犯法,却放任自己,率性而为。他对警察说:“要枪毙、要砍头、要活埋,都随你们的便,我恨不得活剥了你们这群贪官污吏的皮。”[4]他拒绝辩护律师为他辩护,对检察官说:“我求你们枪毙我!”[5]高马的悲剧在于缺乏理性与自制,他知法犯法,以暴抗恶,他虽然经受过部队生活的磨练,却没有摆脱农民的狭隘与短视,最终因越狱复仇被监狱哨兵击毙。
金菊是一个善良单纯的农村姑娘,却不幸生活在一个没有温情的家庭中。父亲性格独断,冥顽不化,对她非打即骂。大哥方一君自私阴狠,因身有残疾,四十多岁还没娶媳妇,父亲逼着金菊为大哥“换亲”,金菊却坚定地爱着健康,坚毅,“见过大世面”的高马哥。她怀了高马的孩子。方一君因担心妹妹悔婚坏了自己的好事,动辄以父母之命要挟妹妹,用虚情假意哄骗妹妹开心。二哥方一相脾气暴躁,心黑手辣,嫌弃妹妹与高马私奔丢人,时常打骂金菊,毫无手足之情。方四叔卖蒜薹回来的路上,被乡党委书记的汽车撞得车毁人亡,贪心的方家俩兄弟接受了肇事司机的财物,不仅不为父亲伸冤,还跟悲苦无告的老母亲闹分家。由于父兄的自私、狭隘、狠毒,母亲软弱糊涂,恋人高马被警方通缉逃亡,孤独无助的金菊,怀着即将出世的儿子在高马家上吊自尽。金菊死后,方家兄弟俩财迷心窍,被杨助理员说转,与曹家结为阴亲,将金菊的尸骨八百块钱卖给了曹家。四婶出狱后万念俱灰,也上吊自杀。方家人的悲剧性格,折射出的不仅是农民物质和精神的双重贫困,同时也暴露了乡村社会里人性的冷漠、现代家庭伦理的危机。
透过这些小人物的悲剧,作品对农村文化事业的落后,以及由此导致农民保守、狭隘、眼光短浅、法律意识淡漠等农村现实问题进行了深度观照,多角度、多侧面地反映了天堂县农民当时当下的生存状态,封建宗法制顽疾在当今的中国农村依然影响巨大,并且根深蒂固。莫言通过《天堂蒜薹之歌》的创作,其最深层的寓意应在于警示人们,当今中国农村的现实问题极其复杂,仅仅靠发展经济,解决农民的衣食住行问题还远远不够,唯有通过精神文化建设,引导农民提高自身的文化素质和法律意识,过滤掉物质欲望对农民精神的过度侵蚀,重塑正确的价值观念,才是最终目标。体现了莫言作为一位极有社会责任感的当代作家,对农村、农民问题深切的人文关怀和人性思考。
作品还塑造了一批自私贪婪、以权谋私的小官吏形象。乡政府杨助理员,一个不起眼的政府小职员,却在农村一手遮天。他狂妄至极:“老子们是国家干部,躺在树影里看蚂蚁上树,工资照发,一个子儿都不少,你们的蒜薹烂成酱我也照拿工资。”[6]他训斥四叔“打人犯法”,自己却知法犯法,仗势欺人。他一手制造了金菊和高马的爱情悲剧。金菊、四婶、高马三人的死无不与他相关。乡党委书记王安,纵容司机利用公车贩卖蒜薹,将四叔撞死,却以权压人,只给四婶三千五百元的赔偿金,草草了结一桩人命案。还有见风使舵的村主任高金角、草菅人命的公安警察等等。通过这些形象,作品深刻地暴露了人性的卑鄙和丑陋。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在法庭上慷慨激昂为正义辩护的青年军官形象。当“蒜薹事件”尘埃落定,参与事件的高羊、高马、四婶、郑常年等一批人被认定为“罪犯”,出庭接受公审。他们是一些法律意识淡漠,甚至根本不懂法律的人。这些弱势者没有能力为自己辩护,也没有律师为他们辩护,轮到公诉人发言时,“公诉人简单地说了几句就坐下了。”在这个代表公理和正义的庄严场所,没有人为他们说一句公道话!而就在这时候,一个身穿军服的年轻军官站出来为父亲郑常年辩护,也为在场的所有“罪犯”辩护。他的辩护词有理有据,且法理鲜明,义正词严,赢得了听众席上“疯狂的掌声”。莫言说:“这个军校政治教官,在法庭上慷慨激昂地发表的这些演说,就是我的心声。”“我自己虽然非常清醒地知道,小说应该远离政治、起码应该跟政治保持一定的距离,但是在现实生活中,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情形,使你无法控制住自己,使你无法克制自己,对社会上不公平的现象,对黑暗的政治,发出猛烈的抨击。”[7]无论这些人最后是否定罪,青年军官都以自己的一身正气维护了法律的尊严,他代表的是真理和正义。他的出场是一种象征。虽然这个形象非常单薄,但留给人们的却是对未来的希望。
二
《天堂蒜薹之歌》是一部将写实主义创作方法与现代主义表现艺术结合得非常完美的作品。从创作题材看,《天堂蒜薹之歌》以发生于当代社会的一个突发性重大事件为背景,通过写实手法真实地再现了事件的发生、原因及其影响,但艺术表现上,却深受西方现代主义,尤其是福克纳和马尔克斯的表现艺术的深刻影响。
《天堂蒜薹之歌》的整个故事围绕着天堂“蒜薹事件”展开叙述,作品没有传统小说的完整结构和情节,没有中心人物,没有中心线索,而只是围绕着天堂“蒜薹事件”塑造了一批“小人物”形象。高羊是作者用笔墨最多的一个,但他只是一个穿线式的人物。作品一方面通过叙述其微不足道的人生经历,展示他处处受挤压而扭曲变形的畸形心理,一方面借助他的所见所感,把现实中发生的诸多故事串联起来。
那么,情节、结构、线索、中心人物这些传统小说因素的淡化甚至缺失,用什么来弥补?这就为作者艺术表现的创新和探索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机会。
《天堂蒜薹之歌》是莫言小说创作的第一个叙事多面体。就叙事结构而言,作品采用了多(三)重话语叙事:一是民间话语叙事:通过瞎子艺人张扣的唱词以民间歌谣的形式进行叙事,站在民间立场上,呈现“蒜薹事件”的前因后果;二是全知全能故事叙述者的知识分子话语叙事:用传统小说叙述文体,由叙述人讲述故事;三是权利话语叙事:借助新闻媒体视角,通过新闻报道的形式,代表官方立场对“蒜薹事件”进行叙事。[8]
作品的前二十章,每章前面附有一段张扣的唱词。这些唱词并不一定完全与每一章小说的叙事内容一致,但是又紧扣“天堂蒜薹”事件展开,它独立于故事叙述人正面叙述之外,以不同于前者的话语方式,从民间立场上呈现“蒜薹事件”的前因后果、官逼民反的整个过程,对天堂县某些政府官员忽视群众的利益,导致蒜薹滞销、腐烂,给蒜农造成巨大的损失给予正面抨击。张扣的唱词酣畅淋漓且义正辞严。张扣既是叙述人,也是故事中的一个被叙述者。到第二十章,张扣的故事融入整个作品的叙事:“蒜薹事件”发生后,张扣因弹唱“天堂蒜薹之歌”而获罪,且被认定是蒜薹事件的“头号罪犯”,遭警察拘留、殴打和警棍电击,警察甚至“用透明胶带牢牢地封住了他的嘴巴”。后来,张扣因为眼瞎而得到了宽大处理,但他并没有因此闭嘴,他深知民间疾苦,民怨沸腾,广大的蒜农敢怒不敢言,他要用自己的歌谣为蒜农们伸张正义。他“还每天坐在县政府旁边的斜街上,弹着三弦,不知疲倦地唱着天堂蒜薹之歌,并把这歌越编越长。”[9]张扣因此再次受到警察的威胁,三天后遭遇暗算,惨死斜街。
作品最后在第二十一章,借助媒体视角,以新闻报道的文体形式,站在官方立场,叙述了天堂“蒜薹事件”的起因、影响、县政府对“蒜薹事件”的处理方法和处理结果,以及由此引发的思考等等。《群众日报》的通讯、事件评述、社论文章,既有对天堂县委、县政府领导严重的官僚主义、漠视群众利益的渎职行为并最终导致蒜薹事件发生的批评,也有对群众参与打、砸、抢,火烧县政府大楼的不法行为的批判,肯定了对少数不法分子惩处的必要性,并认为“不能用无政府主义反官僚主义”,从官方的角度对天堂蒜薹事件进行了评述。
作者在同一作品中,运用多种不同的话语叙事:从不同侧面、不同角度、站在不同立场,对同一事件进行立体呈现,多种叙事代表多种不同的意识形态话语,可以让读者对事件形成一个全方位的认知,更客观、更全面地了解“蒜薹事件”的经过,并不断接近“蒜薹事件”的真相。是非曲直,各自评说。三种话语叙事分别通过三种不同的文本形式,用不同的语言表达形式、感情色彩、侧重点、不同的语体风格,形成了一个众声喧哗的大合唱,颠覆了传统的小说叙事模式。通过这种不同文体的穿插、组合,突破了小说传统文体的规范,既丰富了故事内涵,又为满足读者的多重阅读期待提供了可能,使读者在多种文体的相互参照中,感受到这种全新的表达形式带来的陌生和新鲜的审美体验。如叙述者的叙述与报纸的文章都是在“蒜薹事件”发生后的叙述,是过去完成时;而张扣的唱词则是即时性的,是现在进行时。张扣的唱词,给知识分子话语叙事中的腐败官员们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压力,从而构成了激烈的矛盾冲突,增强了作品的艺术张力。另外,《群众日报》上的文章和张扣的唱词,可以与小说叙事互相印证,又可以对小说叙事起到补充作用,使读者更接近事件真相。
在《天堂蒜薹之歌》的主体部分,即全知全能的知识分子话语叙事中,作者完全打乱时间顺序,灵活运用倒叙、插叙、补叙、互文等多种手法交叉叙述,通过时空交错、叙述视角的不断切换等技巧,形成散点透视,营造出一个多维的叙述空间,追求狂欢化(复调)叙事效果,为读者提供了文本意蕴解读的多种可能性,使故事更丰满,更有张力。
作品第一章首先采用倒叙手法,从“蒜薹事件”发生后,警察抓捕高羊与高马开始写起,运用正面描述现实,侧面追述历史的手法,渐次展开高羊的灰色人生、高马和金菊的爱情悲剧两条线索,并与“蒜薹事件”的叙述交融杂糅。而“蒜薹”意象若隐若现,“腐烂的蒜薹”的臭味儿,时不时地飘荡在线索人物高羊的嗅觉范围内,令他恶心、呕吐,以此紧扣作品的主旨,将所有人物、所有事件串并在一起,并让“蒜薹事件”每时每刻萦绕在读者的脑海中,跟随叙述人的叙述,急切地去探寻事件的真相。
高羊是一个经常承担叙述任务的人物。高羊社会地位低下,人格卑贱,他只能在屈辱中求生存。高羊对生活没有任何欲望,很容易满足,他为儿子取名“守法”,他的人生愿望就是平平安安过日子,所以,他为人真诚,不虚伪,不势力;高羊性格谦和,能忍则忍,多年的卑微地位,使他养成了遇事冷静观察,善于思索的习惯。做为一个旁观者或受虐者,他一般处在事件的外围或底层,很容易被人们忽略,这就给了他更多的观察事件的机会,且收到“旁观者清”的效果。由此我们可以看出,高羊是一个故事叙述人比较信任的人物,经由他的眼和口讲述故事,真实、客观,更接近生活的本真。如果说张扣的民谣歌词主要是叙述“蒜薹事件”的经过,揭示事件的真相;那么高羊的叙述让读者找到了引发事件的多种可能性,从起因、过程接近真相;高羊同时亲眼见证了作品中几乎所有的悲剧事件:高马与金菊的爱情悲剧、高马被抓捕、高马越狱;四叔遭车祸身亡;马脸青年冤死,乡派出所警察的草菅人命;狱中犯人的凶狠,死刑犯最后一夜的歇斯底里;青年军官的出现和他在法庭上的正义辩护;四婶上吊自尽,高羊虽然没有亲眼所见,但借高羊老婆的转述传达给读者,也不失真实。
在叙述过程中,作品不停地转换叙事角度。有时候同一段叙述中,叙述人会数次转换叙述视角,通过时空交错,交叉叙述,真实地呈现出现实生活的复杂状态。如第三章写高羊被捕,警察将他锁在树上,双目失明的女儿循着声音来找他时,交叉混杂着现实、回忆、心理幻觉、迷乱的思绪和小女儿细弱的哭喊声,充分展示出高羊凄惨的现实处境和痛苦中挣扎的灵魂世界。而“很久以后,高马回忆起他随着篱笆倒下时感受到的愉悦和倒地时闻到的黄瓜味道。”则是典型的《百年孤独》式的预言式倒叙,由此也可以看出,莫言作品深受魔幻现实主义大师马尔克斯的影响。
这种随机性的自由叙述看似纷繁复杂,也可能造成严重的阅读障碍,但它呈现出来的恰恰是人类大脑活动的自然状态。人的意识飘忽不定,情绪千变万化,人类的大脑大部分时间处于无序状态,有时千头万绪,有时一团乱麻,思前想后,忽东忽西。所以,人类的思维活动不可能完全顺时发展,而是处于不断的变幻中。随机性的自由叙事,实则正是人类大脑思维方式和人类生活绵延不断的原生态呈现。频繁转换的叙述视角,造成叙事迷宫的同时,也带来叙事语言的新奇和阅读接受的愉悦,能够考验读者的阅读耐性,改造惰性阅读习惯。实际上作者也并没有为自己营造的复杂空间所局限,随机性的视点,可以使叙述者像“全知叙事”模式中的叙事者一样,比较随意的、全方位的展开叙述,没有什么他不能说的。而在整个故事的叙述过程中,叙述人很狡猾,他始终隐藏在故事的背后,冷眼旁观,不露声色,只是客观呈现故事,不做价值评判。作者把自己放到一个倾听者的位置,让故事中的人物成为真正自由的可以言说的个体,让众多的个体汇集成为一个实实在在的底层话语世界,平等地各抒己见,从而让读者去真实地接近农村的生存本相。
[1][2]莫言.天堂蒜苔之歌·新版后记[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359.
[3][4][5][6][9]莫言.天堂蒜薹之歌[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2:239,302,306,72,347.
[7]莫言.试论当代文学创作中的十大关系[J].江南,2007,(3).
[8] 陈思和.莫言近年小说创作的民间叙述——莫言论之一[J].钟山,2001,(5).
Abstract:The Garlic Balladsis a novel which perfectly combines realistic creation method with modernism performance art.In order to grasp the theme and innovation value of this excellent novel,this article has a deep-going interpretation of unimportant persons’images and multiple discourse narration.This novel narrates around an emergency‘garlic stems event’and exhibits this tragic event with the use of multiple narrations.It provides a comprehensive view of the living conditions of heaven county farmers.As a contemporary writer,Mo Yan's work shows his strongsense ofsocial responsibilityand deep concern for the humanities and human nature.With‘time and space cross’construction mode and continuous switching of narrative perspective,Mo Yan creates a multi-dimensional narrative space and forms a scatter perspective structure.He provides readers multiple possibilities ofinterpretation ofthis novel.
Key words:garlic stems event;human care;narrative polyhedron;narrative perspective
责任编辑:陈冬梅
The Garlic Ballads:Real Life from Multiple Viewpoints
GUO Qing-yun
(Weifang University,Weifang 261061,China)
I206.7
A
1671-4288(2017)04-0004-04
2017-04-11
郭晴云(1965-),女,山东寿光人,潍坊学院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