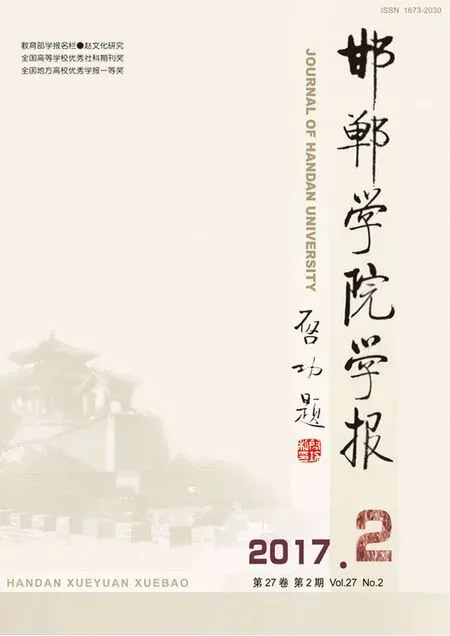从《格斯尔汗:西藏的传说》(1927)封面“TOLD BY IDA ZEITLIN”谈起
——论《格萨尔》史诗的英译
弋睿仙,马笑清,王 敏
(西藏民族大学 外语学院,陕西 咸阳 712082)
从《格斯尔汗:西藏的传说》(1927)封面“TOLD BY IDA ZEITLIN”谈起
——论《格萨尔》史诗的英译
弋睿仙,马笑清,王 敏
(西藏民族大学 外语学院,陕西 咸阳 712082)
1927年艾达·泽特林(Ida Zeitlin)的《格斯尔汗:西藏的传说》是《格萨尔》史诗早期重要英文版本,以该版本封面上的“TOLD BY IDA ZEITLIN”为出发点,对英语世界关于这部史诗的“述说”现象进行研究,认为该版本其实采用的是“译创”的翻译方法,“译创”的本质是“去史诗化”,考虑了当时英语世界对藏族史诗的接受环境和读者群体,对史诗生命在海外的拓展与延伸有重要意义。
《格萨尔》;英译;去史诗化
当前,我国少数民族典籍的外译与海外传播引起了学界的关注,全国少数民族典籍英译学术研讨会已举办了三届,研究成果颇丰。以《格萨尔》史诗为代表的藏族文化典籍的英译研究也崭露头角,不仅在少数民族典籍外译领域占有一席之地,也成为格萨尔学乃至藏学研究的组成部分和有益补充。《格萨尔》史诗代表着古代藏族文化的最高成就,在国际上享有崇高的声誉,出现了俄、法、德、英等多种外语版本。根据《格萨尔》史诗研究专家徐国琼先生关于“国外《格萨尔》的研究概述”,将这部史诗以英文展示于世的其实并非是一个英文译本,而是一个藏英结合的本子,即德国摩拉维亚传教士弗兰克(A.H.Francke)1905年在印度出版的《下拉达克本格萨尔王传》(A Lower Ladakhi Version of the Kesar Saga),该版本正文为藏文,但附有英文摘要、词汇和注释。[1]255这是目前格萨尔学界关于英文版《格萨尔》史诗的最早记录,但遗憾的是,该版本正文部分并非全英文,因此不能算作是真正意义上的英译本。后来,美国学者艾达·泽特林(Ida Zeitlin)1927年在纽约出版了英文版《格斯尔汗:西藏的传说》(GESSAR-KHAN:A LEGEND OF TIBET)。但该版本一直鲜为人知,国内关于国外《格萨尔》研究的成果中几乎无人提及,直到典籍翻译研究学者王宏印教授和王治国博士在文章中对此版本进行简要的介绍,此版本才进入国内学者的研究视野。就目前掌握的资料来看,该版本可能是《格萨尔》史诗真正意义上最早的英文版本,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但是,通过知网检索,目前关于该版本的研究成果极少,本文拟从该版本封面谈起。
一、英文版《格斯尔汗:西藏的传说》(1927)封面:“TOLD BY”
《格萨尔》史诗流传过程中出现了多种底本、抄本、刻本、铅印本等版本,除了口头和书面两种主要的传播方式外,还出现了多样化的流传方式(如电视剧、电影、歌剧、动画、游戏等),也出现了藏、蒙、土、汉、英、俄、德、法等多种语言传承的现象,但史诗在海外的传播主要采用书面形式,以英语为主要传承语言,先后出现了十几本英文版《格萨尔》。其中,艾达·泽特林的英文版《格斯尔汗:西藏的传说》1927年由纽约乔治多兰出版社出版,为布面硬精装本,彩色印刷,配有插图,共 203页。该英文本的封面上清楚地印有“TOLD BY IDA ZEITLIN”字样,却未出现“TRANSLATED BY”字样,显然艾达·泽特林以此表明该书并非真正意义上的译作。那能否认为这本书是艾达·泽特林作为作者而创作的一部作品呢?答案也是否定的。英文书籍的封面上一般都会出现书名和作者姓名,分行排列,二者之间有时使用“By”(或“BY”),有时也可省略,但译作一般都会出现“TRANSLATED BY”字样,那么1927年英文版《格斯尔汗:西藏的传说》封面上出现“TOLD BY”就值得思考了。
在该英文版的序言(Foreword)中,泽特林明确指出:在俄国的帝国科学院(Imperial Academy of Science)授意下,雅科夫·施密特(Isaac Jakob Schmidt)以1716年(康熙时期)的蒙文本《格萨尔》为基础,于1836年发行了一个新版蒙文本,1839年在圣彼得堡出版了以该版为原本的德文本《功勋卓绝的圣者格斯尔王》(Die Thaten Bogda Gesser Chan’s);1927年英文本主要以施密特的德文本为原本,并参考了本杰明·伯格曼(Benjamin Bergmann)的《少年格斯尔》(Little Gesser),伯格曼的版本译自卡尔梅克人的口传本,收录在其1804年于里加(Riga)出版的Nomadische Streifereien(第三卷)中。
根据王宏印和王志国的研究,施密特的德文本是《格萨尔》在西方最早出现的译本,[2]18泽特林的英文本源于该德文本,并将伯格曼版本的部分内容也展示于世,足见泽特林1927年版本对于《格萨尔》史诗在英语世界传播的价值与意义。从序言中可以看出,泽特林的英文本是以一主一辅两个原本为基础的,但遗憾的是她本人并未在序言中提及在英文版中对两个原本是如何取舍的,由于资料有限,目前尚无法得知。但通过序言可以理解泽特林为何采用“TOLD BY”而非“TRANSLATED BY”了,至少可以看出艾达·泽特林比较传统的翻译观,认为自己的这本书融合了两个原本,并非是对一部原作的翻译,不能算作是一部传统意义上的译作,因此采用了“TOLD BY”,笔者认为可以将其理解为“述说”。
二、史诗的“述说”“译创”及“去史诗化”
(一)泽特林对史诗的“述说”
泽特林 1927年的英文本融合了一主一辅两个原本,以自己的理解进行取舍,对史诗进行了“述说”,将一个述说本展示给英语世界的读者。该版本包括四个部分:序言、目录、正文及文末注解。正文部分共九章,内容涵盖了《格萨尔》史诗的主干部分,即降生、称王、征战和结局,各章标题依次为:英雄降生、觉如现身称王、汉地之旅、乐风山谷、十二头魔王、锡莱河三汗王、晁通背叛、锡莱河三汗王受罚、格萨尔返回。[3]该版本在形式上未采用史诗散韵结合的体例,而采用“散体化”策略,全文从头至尾没有出现一处唱词,泽特林对唱词进行了删除或将其改写为对话/描述性文字,增强了故事性;语言上采取了复古风格,即用词和句法显示古英语的特色,文中多次出现“thy”、“thou”、“wilt”、“hast”及“whence”等。该英文本短小精悍、图文并茂、情节曲折、语言流畅、古雅别致。她的“述说”是将两个原本看作素材来源,经过自己得加工,将史诗变成了一个引人入胜的东方神话故事。原作已经不是高高在上的权威了,译者的主观能动性消解了原作这个“中心”。这可能是泽特林对该版本定位时的一大困惑。
(二)史诗的“译创”
如何看待泽特林的这种“述说”说到底就是如何对定位这个本子的问题。关于泽特林的个人信息并不多,由于材料有限,目前仅知道她1902年生于纽约,长于写作与翻译,其早期作品有两部:1926年纽约乔治多兰出版社出版的英文版《斯卡兹金:俄国传奇故事》(Skazki: Tales and Legends of Old Russia)和1927年该社出版的《格斯尔汗:西藏的传说》,这两本书在排版、印刷、制作方面非常相似,并且封面上都印有“TOLD BY IDA ZEITLIN”字样。泽特林对这两本书的定位看似清晰,实则模糊,既不定位成译者的“译作”,也不定位成作者的“创作”,而采取了“述说”这种折中的方式,这既体现了泽特林严谨的学术态度,也体现了当时她对翻译的认识。显然,她认为自己所从事的这一活动并非是传统意义上的“翻译”,其活动成果也并非传统意义上的“译作”。类似这种借鉴多个版本而形成新的版本的现象在《格萨尔》史诗的口头传承和书面传承中都出现过,在近些年国内的《格萨尔》研究中也有提及,“格萨尔学界出现了吸收史诗研究成果的翻译兼创作的特殊现象,可归于编译或译创……因为它既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创作(composition proper),又与传统意义上的翻译(translation proper)不同,可以说是创作与翻译的‘杂糅体’(hybrid),是介于翻译与创作之间的一种居间状态。”[4]37虽然泽特林当时对《格萨尔》史诗的“述说”是融合了两个原本的跨语言的“述说”,那么现在看来则可以归为“译创”。
在翻译理论发展过程中,人们对“翻译”一词的定义从传统的语文学角度到现代语言学角度,再到当代的多学科研究角度已发生了较大的变化。现代译论认为,翻译“不是一种纯粹的文字活动,一种文本间话语符号的转换和替代,而是一种文化、思想、意识形态在另一种文化、思想、意识形态环境中的改造、变形或再创造。”[5]31“翻译”这一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已经与传统意义上的“翻译”有所不同,泽特林的“述说本”在当代不仅可称之为“译创”,理应视为“翻译”。
(三)“去史诗化”
1927年泽特林英译本的“译创”主要体现在内容上和形式上。该版本内容主线为格萨尔的降生、称王、征战和结局,但在具体情节上与1716年的北京木刻蒙文版(七章本)(简称“北京本”)有所不同。比如,北京本提到格萨尔爱慕马巴彦的女儿阿尔伦·高娃,趁她熟睡之际将死马驹塞入其衣群之中,戏弄她与父亲、兄弟、或奴隶等有私情,阿尔伦·高娃羞愧难耐,请求嫁给格萨尔,于是格萨尔便让其舐血订婚。格萨尔是通过戏弄、欺骗的手段迫使阿尔伦·高娃与其成婚,其后章节中也未曾出现格萨尔将真相告知给阿尔伦·高娃。[6]1960但是,这一情节在1927年版本中从未出现,该英文版中格萨尔一直是高大的英雄形象。
该英文版在形式上也进行了大胆地“译创”,并未采用七章本的体例,而是按照故事情节的需要改为九章,每章都采用长标题,旨在将本章内容概括完整。形式上最大的变化就是史诗原有的“散韵结合”完全变成散文体,整个版本从头至尾没有出现一处唱词,对史诗的唱词进行了删除或将其改写为对话或描述性文字。该译本展示给读者的完全是一个讲述格斯尔英雄事迹的故事,看不到史诗特有的庄严性、神圣性及诗性叙事特点,这种“译创”可称之为“去史诗化”。从本质上来讲,“去史诗化”是指译本以《格萨尔》史诗内容为原型,融合史诗几个版本或研究成果,采用史诗这种庄严文学体裁之外的其他体裁的“译创”。1927年英文版的“去史诗化”采用散文体,语言简洁、故事性强、印刷精致、图文并茂,呈现给英语世界一个神奇的东方故事。以“去史诗化”的方式进行“译创”,可以产生不同的版本,进一步丰富了史诗,凸显了史诗传承的包容性特点,有利于史诗走入域外普通读者的视野中。
三、1927年版本对于史诗英译的意义
1927年英译本采取了“去史诗化”的“译创”,将《格萨尔》史诗转换成一个东方神话故事,短小精悍,情节曲折,以英语读者喜闻乐见的形式“述说”异域史诗,客观上开启了史诗在英语世界的传播。史诗的翻译属于文学翻译,文学翻译与其他翻译的根本区别在于文学翻译使用的是一种艺术语言,是一种具有美学功能的艺术语言,译者的任务就是在译语中寻觅合适的语言,以如实地再现原作者所创造出来的艺术世界,因此文学翻译已经不再是一种简单的语言文字的转换,而是一种创造性的工作,但是伴随着文学翻译创造性的是它的另一面,即文学翻译中的背叛性。国际知名比较文学家与翻译家谢天振教授认为,“文学翻译创造性性质是显而易见的,它使一件作品在一个新的语言、民族、社会、历史环境里获得了新的生命……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表明了译者以自己的艺术创造才能去接近和再现原作的一种主观努力,那么文学翻译中的叛逆性,在多数情况下就是反映了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为了达到某一主观愿望而造成的一种对于原作的客观背离……它们是一个和谐的有机体……它(文学翻译的创造性叛逆——笔者注)最根本特点是:它把原作引入了一个原作者原先所没有预料到的接受环境,并且改变了原作者原先赋予作品的形式。”[7]72-75泽特林版本毫无疑问是《格萨尔》史诗最早的英文版之一,她以全新地面貌向英语世界展示了中国史诗的面貌,具有开拓性的价值。因为它在一个全新的环境中赋予史诗一个崭新的面貌,与更广泛的读者进行一次崭新的文学交流,客观上不仅延长了史诗的生命,促进了史诗在海外传播。
虽然《格萨尔》史诗是藏族历史文化的百科全书,也是中华文化的艺术奇葩,但对于英语世界乃至西方世界而言,这部史诗则是来自异域。早期西方的少数旅行家、传教士及学者对《格萨尔》史诗基本上出于探险、猎奇的心理对来自异域的史诗产生兴趣。在这种社会历史背景下,《格萨尔》史诗对英语世界读者而言是非常陌生的,但是泽特林的《格斯尔汗:西藏的传说》无论其出于何种意图,客观上都不可否认她将史诗译介到英语世界的事实。该版本作为《格萨尔》史诗早期重要英译本,虽然从形式上看不出史诗的影子,但从内容上再现了史诗记述的英雄事迹,让英语世界的读者有机会了解到格萨尔王的故事,一定程度上对史诗在英语世界的传播具有开拓性的意义。她的译创本融合了一主一辅两个原本,为英语读者呈现了一个“散体化”的异域神话故事,将古老的东方史诗以目的语读者喜闻乐见的方式引入一个崭新的语言、民族、社会、历史环境之中,正是泽特林这种创造性的“译创”不仅丰富了《格萨尔》史诗的内涵,而且使其生命在空间和时间上得以拓展和延长。
国内学者认为,虽然西方国家的读者对于中国文化的真正兴趣是从最近几十年开始的,到目前还没有形成一个成熟的接受中国文化的读者群体和接受环境,这与我国对西方文化的接受环境、接受程度及读者群体成熟程度差距太大,存在着“语言差”和“时间差”。[8]13遥想20世纪20年代,囿于当时的社会文化背景及传统译学关于“翻译”的认识,虽然艾达·泽特林将译本定位为述说本,而从现代译学的角度来看则是译创本,但是她的“述说”或“译创”方式却是提供了一种新的视野,开辟了一种新的途径,客观上将史诗译介到了英语世界,使史诗的生命在一个崭新的环境中得以拓展和延长,对于史诗在海外的译介起着重要作用,也为当前的民族典籍外译提供了借鉴。
四、启示
虽然藏族史诗《格萨尔》已经出现多种语言的译本,但是总体数量还是偏少,在已出版的十多个版本中,只有一个版本出自中国本土,其余全部出自国外,而且其中不少版本都是学术性的大部头,并且这些版本对《格萨尔》史诗的诠释也不同。因此,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大背景下,如何诠释藏族史诗《格萨尔》,如何使其真正走向世界,国内译界责无旁贷。这可能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分步走,可以灵活的方式先将其译介到国外,如缩译本、改写本,节译本等。有力例证便是莫言作品的英译,译者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连译带改”,迎合了目的语读者的语言习惯、阅读心理、审美趣味及文化心理等,虽然备受诟病,但却成功地将莫言作品推介到西方世界。在形式上可以采用故事、小说、戏剧、舞剧、音乐剧、电影、动画,甚至游戏等全方位地将其展现在世界读者面前,在传播途径上由其要注重网络传播的重要性,以现代读者乐于接受的方式进行介绍和传播。以史诗《格萨尔》为代表的民族典籍(尤其是少数民族典籍)在海外的译介与传播不是一个简单的语言转换的问题,而是受到多种因素影响和制约的复杂问题,已经超出了传统译学的范畴,要根据翻译对象和翻译语境变换视角,要随着现代译学的发展脚步在民族典籍外译的理论和实践上拓宽视野,关注译作的传播与接收问题。
[1]徐国琼. 徐国琼学术文选——《格萨尔》史诗求索[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5.
[2]王宏印,王治国. 集体记忆的千年传唱:藏蒙史诗《格萨尔》的翻译与传播研究[J]. 中国翻译,2011(2).
[3]Ida Zeitlin. Gessar Khan:A LEGEND OF TIBET[M]. New York:George H. Doran Company.,1927.
[4]王治国. 《格萨尔》史诗民译与汉译述要[J]. 民族翻译,2011(4).
[5]许钧. 翻译概论[M].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9.
[6]桑杰扎布.格斯尔传(译)[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
[7]谢天振. 译介学导论[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8]谢天振. 隐身与现身:从传统译论到现代译论[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责任编辑:李俊丹 校对:周冰毅)
Starting with “TOLD BY IDA ZEITLIN” on the Cover of GESSAR-KHAN: A LEGEND OF TIBET (1927): On Translation of Tibetan Epic Gesar
YI Rui-xian, MA Xiao-qing, WANG Min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Xizang Minzu University, Xianyang, 712082, China)
Ida Zeitlin’sGESSAR-KHAN: A LEGEND OF TIBET(1927)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early versions in English world. Starting with “TOLD BY IDA ZEITLIN” on its cover, this paper analyses the phenomenon of “TOLD BY IDA ZEITLIN” and holds that this is an English version of composition in translation. It also analyzes possible factors which have impact on Zeitlin’s choice, which is creative treason in nature in literary translation with the consideration of recipient environment and readership in English world at that time. This is significant for oversea expansion and extension of life of the epic, and also provides references for translation and dissemination of ethnic classics.
Gesar; composition in translation; creative treason
H315.9
A
1673-2030(2017)02-0113-04
2017-06-05
西藏自治区高校人文社科项目“格萨尔王史诗早期英译本研究”(项目编号:sk2015-51);西藏自治区高校青年教师创新支持计划项目“藏族典籍在英语世界的传播研究”(项目编号:QCR2016-69)
弋睿仙(1981—),女,陕西户县人,西藏民族大学外语学院副教授,硕士;马笑清(1982—),女,甘肃庆阳人,西藏民族大学外语学院讲师,硕士;王敏(1978—),女,陕西西安人,西藏民族大学外语学院讲师,硕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