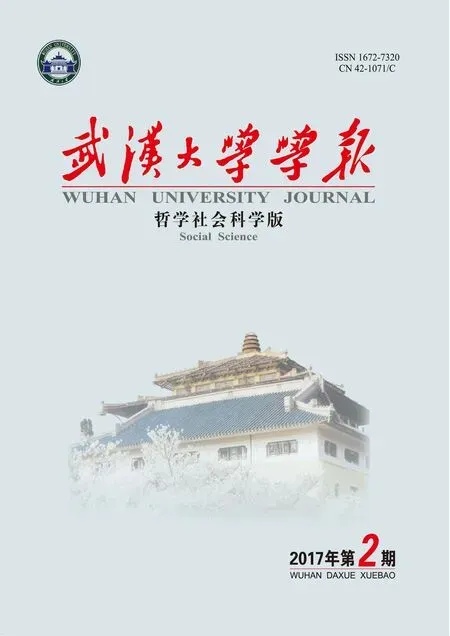网络的意识形态语言应激及其障碍解析
赵 麑 陈相光
网络的意识形态语言应激及其障碍解析
赵 麑 陈相光
网络意识形态是现实意识形态的非线性镜像。语言应激是当事人通过认知、评价而觉察到特定言语的威胁或者挑战而引起应对性的心理、生理反应。认知、情绪或者行为反应合理性程度明显弱化是语言应激障碍的具体表现。网络意识形态的语言应激障碍从现象看是语言表达冲突,事实上是语言意义冲突,本质上在于价值观冲突。
网络; 意识形态; 语言应激
语言是网络意识形态的载体。根据梳理,鲜见基于网络的意识形态语言应激及其障碍的专项研究。即使是语言应激及其障碍,作为社会交往冲突中常见多发现象,学界对其也缺乏足够的学术观察。心理学上,应激障碍不是指称应激的缺失(或者无应激),而是指称有悖于常理、常情的反应范型,包括过敏应激及低敏应激。据此,递进地澄清、厘定语言应激及其障碍、网络的语言应激及其障碍、网络的意识形态语言应激及其障碍等问题域,具有学理价值和现实社会意义。
一、语言应激及其障碍
语言应激及其障碍,作为具体的人具有切身的经验。就其概念的厘定与界说、相关特性以及发生机理等,学界对其的学术考察尚待掘进。语言应激在反应强烈程度上有强弱之分,交互语境中当事人之间可能发生强应激—强应激、强应激—弱应激、弱应激—弱应激关系。语言应激研究指向当事人对特定语言刺激的身心反应。发生于交互语境中的语言应激属于常见身心应激现象,包括心理应激和生理应激。基于交互语境的语言应激,意指语言交互进程中当事人对另一当事人的语言行为的应激性反应。限于篇幅,本文专门探讨语言的心理应激(简称语言应激)。语言应激障碍包括语言应激过强(或者称之为过敏应激)与语言应激过弱(或者称之为低敏应激,相当于发生应激阻抗)两种情形。另外,此处需要加以甄别说明的是,语言冲突研究针对的是当事人之间的语言对抗行为及其影响。语言冲突源于当事人之间在语言表达形式或者内容上存在不相容关系,即当事人之间的话语的能指、所指、意指存在立场或者意义竞争。这种冲突表现为语言交互进程中当事人反对另一当事人的言行、举止或对方的观点,继而产生话语对立,一般而言,过敏应激才会产生。
其一,语言应激概念的界说。语言应激概念的提出源于生理学、心理学上应激概念的使用。“应激”(或者“压力”)是英文“stress”的中译。蕴含三层含义:(1)代表能引发应对反应的刺激物,即“应激源”(stressor);(2)意指由刺激唤醒的身心紧张状态;(3)对应激源的生理与心理反应。研究表明,“刺激物若具备超负荷、冲突、不可控制性三个基本特点,就可能成为一种应激源”(林崇德等,2003:1575)。应激源既可以是外界物质性刺激物,又可以是个体内环境及心理社会环境中心理、社会、文化性刺激物。无论物质性应激源还是心理、社会、文化性应激源,都既可以引起生理反应,又可以引起心理反应。而且,生理反应与心理反应相伴而生。应激是一种适应性、应对性反应,大体上可分为生理反应、心理反应。其生理反应往往同交感—肾上腺髓质系统或者下丘脑—垂体—肾上腺皮质轴的积极活动相关联。心理反应则“大体上可分为情绪反应、自我心理防御反应及行为反应等”(林崇德等,2003:1577)。心理反应表征当事人被刺激后出现的解释性的、情感性的、防御性的反应以及当事人自身对应激状态的感知觉。扼要而论,应激是应激源作为刺激物与当事人的身心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刺激物与应激之间存在由诸中介因素共同决定的中介交互机制。介于刺激物与应激之间的中介因素包括应激源对当事人的意义、当事人对应激源的应对能力、环境因素、当事人的身心组成特点等。其中当事人的认知评价、认知风格、个性特征以及应激源的可预测性与可控制性等中介因素所起的调节功能是应激差异化的重要原因。有学者认为,“语言应激(language stress)是一种心理应激,主要是指人在生活交往中,由于自身的修养和心理承受能力水平低,面对各种恶性语言刺激不善于应变,导致悲剧发生以及激情犯罪的发生的心理和生理过程”(王卫平,2004:67)。一般意义上,语言应激是当事人通过认知、评价而觉察到特定言语的威胁或者挑战而引起应对性的心理、生理反应。
其二,语言应激障碍的特性。语言应激障碍是一种不良的应对反应,认知、情绪或者行为反应合理性程度明显弱化既是语言应激障碍的具体表现,也是其核心特性。扼要而论,应激对人的不良影响包括:(1)理性思维能力弱化;(2)情绪、情感波动程度扩大;(3)诱发非理性意志行为。在语言应激期间,发生的情绪反应主要包括焦虑、愤怒、恐惧、习得性无助感等;自我心理防御反应则主要表现为合理化、投射、否认等;行为反应主要表现为攻击,而且行为反应与情绪反应紧密关联。因此,即使同一当事人在面对相同的应激源时,不同时间也会发生不同的心理反应。不良语言应激发生于当事人觉察或评估应激源存在威胁或者挑战时,“语言表达策略与面临的潜在威胁程度存在密切关系”(Satoshi & Jir,2010:523)。就交互语境而论,螺旋式的循环因果语境是发生语言应激障碍的语义空间。另外,对抗性的修辞表达容易诱发语言应激障碍。在交互语境中,当事人发生语言应激障碍的理论可能性在于以下三种情形:(1)强烈不认同另一当事方语言所蕴含的意义,而且语言刺激的强度超过当事人正常的心理承受能力。(2)当语言刺激引起两种或者两种以上矛盾,当事人难以抉择。(3)当语言作为刺激物不随当事人的行为而变化与转移,即当事人对另一当事方的语言不具有控制性或者足够影响力时,最能引发当事人紧张、恐惧心理。(4)当事人受到另一当事人的语言暴力侵害。(5)当事人受到另一当事方其他成员的语言协同围攻。
其三,语言应激障碍的机理。“语言应激障碍”对应于特定语境中感性凌驾理性的情绪失控现象。根据神经学家约瑟夫·勒杜(J.Ledoux)的研究,情绪失控现象的发生源于人体内部通往新皮质的神经通路不单止存在大神经通路,人体内部还有一束小的神经元直接从丘脑通向杏仁核。通过既小又短的“捷径”,杏仁核作为激情之源可以直接获取感觉输入,并赶在新皮质完成感觉登记前抢先反应。语言作为符号性的应激源,通过神经生化系统影响人的心理和生理。当语言应激强度超出当事人的心理适应能力时,此时当事人的心理、生理处于高度唤醒状态,继而引起语言应激障碍。突破当事人的心理适应阈值的语言应激会造成强烈的心理、生理反应,乃至对人的认知功能造成即时性伤害。“当语言应激强度过大,个体原始的、自我中心的认知系统可能被激活,使其做出极端、绝对、单向的判断,使整个思维失去了意志的控制,减弱了对偏激思维的控制能力,从而出现了病态的推理和判断,进一步发生心理行为问题”(王卫平,2004:67)。
应激源与应激之间通过心理、生理的中介机制,形成基于应激源的应激关系。其中,关于生理的中介机制研究主要涉及脑与行为、心理—神经—内分泌一免疫等领域;关于心理的中介机制研究主要涉及人的意识与认知评价等问题。从心理角度看,觉察或者认知评价作为心理中介的关键决定应激源是否诱发应激及其强烈程度。“个体对应激源的认知评价可以分为积极和消极的评价。前者可适度地提高皮质的唤醒水平,调动积极的情绪反应,使个体注意力集中,积极思维,调整需要和动机;这有助于个体对传入的应激源信息进行正确评价,并启动适当的应激反应通路,获得良性应激适应;后者则导致个体过度唤起而焦虑、激动或抑郁,自我认知概念模糊,使个体难以对应激源进行客观的认知判断和选择适度的应对机制,导致应激损伤”(钱令嘉,2011:659)。应激认知评价模式由西方学者塞里(Selye)、R.S.拉扎勒斯(Lazarus)首先确立,后经武尔福克(Woolofolk)、理查逊(Richardson)等人于1979年正式提出,“应激反应是个体对情境或事件的认知评价结果,人们感知或者评价事物的方式决定着应激反应的发生和发展程度”(林崇德等,2003:1576)。从观察角度分析,当事人的应激与其外部或者内部的需求有关。当事人的心理与生理需要作为与动机关联的内部需求,以及对与情绪关联的需要的满足与否及其程度是决定人的行为的重要因素。如果当事人觉察到需求与自身满足这种需求的能力之间存在不平衡,就意味着应激的产生。应激的交互作用理论强调环境的作用,同时强调人与环境之间的反馈机制是发生应激的基础。人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相当于复杂的循环动力系统。心理活动(包括情绪、动机与认知过程)在其中起着关键性作用。另外,人与环境之间存在分时双向的循环反馈机制。人与环境之间的循环反馈机制有助于形成螺旋式上升的正向强化现象。在分时双向的循环反馈机制的作用下,一是环境的诱因功能不断得以强化或者放大;二是人的应激强度不断提升;三是环境的诱因功能与人的应激强度之间被彼此反复强化,继而诱发应激障碍。整个分时双向的循环反馈过程及其结果类似于“蝴蝶效应”。
二、网络的语言应激障碍
语言应激及其障碍现象,在网络里比比皆是。网络语言应激是当事人在网络动态交互进程中实际上或认识上的要求(或需要)与满足要求(或需要)的能力之间的不平衡而引起的心理和生理反应。网络语言应激障碍是语言应激障碍的一种,具有一般语言应激障碍的特性,其发生机理则具有一定的独特性。在澄清语言应激及其障碍概念、特性、机理的基础上,科学、合理解释网络的语言应激障碍(即过敏应激)等问题,需要进一步从语境、表征及与因果等维度廓清相关问题域。
其一,网络语言应激障碍的语境。在网络交互语境下,当事人既有社会身份、社会地位与社会角色的社会影响力被边缘化,其上下、高低或尊卑的社会权势关系明显弱化、隐性化,而网络对等关系则明显强化、显性化。继之,网络语言表达风格随人际关系的变化而变化,“在互动过程中陌生人之间因为缺乏既定的社会或者人际关系而在语言表达方面呈现冷漠或者无礼现象”(Satoshi & Jir,2010:524)。在网络语境下,美国语言哲学家格赖斯(Grice)提出的“合作原则”*“合作原则”由美国著名语言哲学家格赖斯(Grice)1967年在哈佛大学的演讲中提出。格赖斯提出,当事人在日常会话交际进程中,基于实现语言交际目的的需要,其语言表达遵循一套相互合作的基本准则,统称为“合作原则”。1975年格莱斯在Logicand Conversation一文中将“合作原则”细化为四项基本准则及其相关子准则。包括:(1)量的准则(Quantity Maxim),即会话应该满足交际所需的信息量、会话不应超出交际所需的信息量;(2)质的准则(Quality Maxim),即不说假话,不说证据不充分的话;(3)关系准则(Relevant Maxim),即会话内容具备关联性;(4)方式准则(Manner Maxim),即会话避免晦涩、会话避免歧义、会话宜简炼、会话宜有条不紊。、英国语言学家利奇(Leech)提出的“礼貌原则”*利奇认为,“礼貌原则”是充分解释语言表达过程中言外之意(implicature)、间接言语行为(indirect speech act)等现象的语用规则。语言表达的礼貌程度与其间接程度直接相关。其理论逻辑在于:(1)间接言语行为可以为受话者提供更多的选择可能性;(2)言外之意越是间接,相当于其语义集合或者空间越大,其实际含义越显得含糊,其礼貌程度也就越高。均被弱化。相反,网络交互语境中修辞表达方式更强调语言的经济性,即尊崇法国著名语言学家Martinet提出的语言的“经济原则”*语言的“经济原则”认为,当事人在确保语言的交际功能的前提下,其言语活动自觉或不自觉地体现经济性。。有学者认为,在网络交际中遵循“经济原则”的语用理据包括信息传递、人的思维、人的惰性、修辞表达等方面(柴磊,2006:38)。此观点的合理性在于:其一,与繁杂、累赘的语言表达方式相比,简约、缩略的语言表达更能迅捷地传递当事人的思想、情感信息;其二,根据心智成本理论(卿志琼、陈国富,2003:1-2)*卿志琼等认为,有限理性是心智成本存在的根据。,言语活动遵循经济原则是逻辑思维的必然结果;其三,经济性可以溯源到自然属性意义上人类的生存准则——惰性源于人类降低无谓的能量消耗需要*惰性源于人的生存本能——降低能量消耗。“自然属性所诱发的惰性是人的不自觉的生存行为。”见何剑:《浅谈人的惰性》,《第二届中国科技哲学及交叉学科研究生论坛论文集(硕士卷)》,2008年12月1日,第505页。;其四,言语的经济性缘于修辞表达的需要*Halliday(1978)在提出“篇章修辞”(textual rhetoric)的概念时指出,篇章修辞对言语表达实施“输出制约”,即影响言语的表达方式,由“可处理”、“明晰”、“经济”和“表达”四个原则加以阐明。。由于语言表达的合作原则与礼貌原则的弱化、经济原则的强化,网络语言缺乏借助冗余信息过渡的修辞表达技巧,锋芒毕露、一针见血的语言表达令网络语境缺乏回旋空间。因此,同一交互主题在网络语境下往往诱发更强烈的语言应激。
其二,网络语言应激障碍的表征。心理、社会与文化性应激源引起心理应激和应激性的心理反应。“适度的应激可以提高人的认知能力,增强思维的灵活性,有助于启动机体应对应激源的适应性反应;但长期或强烈的应激则导致机体认知功能损伤。应激所致认知功能损伤首先表现为对信息加工的影响,特别是对于记忆和注意力的影响”(钱令嘉,2011:659)。实际上,语言应激障碍所造成的伤害不限于认知功能的损伤,还包括对情绪、意志等心理因素的负性影响等。网络语言应激障碍是当事人在网络动态语言交互进程中意识或者觉察到特定言语的威胁或者挑战而发生不合理的应对性心理反应。网络语言应激障碍使当事人改变对事物、事件、问题或者观念以及自身的认知评价,引起强烈的即时性情绪波动,引致理性思维能力弱化,引发非理性意志行为。其主要表现为语言攻击或敌对。网络语言应激障碍可能令当事人在情绪、认知与行为上可能面临双趋冲突、双避冲突、趋—避冲突的选择性发生障碍。在发生网络语言应激障碍的情况下,当事人的认知与情绪及行为的相互作用可以形成一种反馈性调节机制,即对应激源的错误认知可能导致不适当的情绪和行为,而不适当的情绪和行为又可能为错误认知提供依据,进一步固化某特定认知观念。需要澄清的是,网络语言暴力可能是网络语言应激障碍,但并不必然等于网络语言应激障碍。
其三,网络语言应激障碍的因果。当事人应激过程中应对的方式受到中介因素的决定性影响。中介因素作为应激过程中的关键变量,其核心因素就是当事人对应激源的认知评价。扼要而言,认知评价与当事人所具有的内部资源、外部资源以及两者之间的平衡紧密相关。内部资源是当事人所具有的心理、生理能力,包括当事人的价值观、个性特征、行为方式与身心素质等;外部资源指当事人发生网络语言应激时可能得到的网络社会支持的多寡以及遭受网络语言伤害时所能得到的心理或者精神补偿程度,诸如当事人的人格特征、价值观、宗教信仰、健康状态和既往经历等内部资源影响其对应激源的认知评价。另外,网络上的社会支持力度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改变当事人的认知过程及其结果。内部资源与外部资源之间的权衡性平衡既表征认知评价的过程,也表征认知评价的结果。认知评价结果直接影响当事人的应对方式。也就是说,当事人的认知评价是构成应激源与应激之间因果关系的中介要件。原因指的是能引起后继现象的现象,而结果指的是由于原因的作用而引起的后继现象。“广义地讲,因果关系是原因对结果的控制”(苗东升,2006:258)。直观上,人们体验到现象之间包含了某种相互关联,而且这种相互关联的普遍特性在某种意义上,意味着每一现象是另一其他现象发生的一个因素。虽然如此,事实上,原因与结果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任何一个事件都不能是另一事件的全部的、唯一的原因。整个先前的事件一起才能引起一个新的情境,不过某一情境显著地决定了一个后起的情境的形成。”(怀特海,2010:150-151)辩证唯物主义提醒我们,客观事物之间联系的多样性决定了因果关系的复杂性。由于当事人对应激源的认知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包括个体认知模式、应激发生前的生理与心理状态、对应激源和自身应对能力变化的期望或对不完整信息的猜测性填补、受主观影响的记忆选择和重组等。归根究底,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最终决定了应对的方式。因此,科学调控当事人对网络语言应激源的认知评价,是有效控制网络语言应激障碍的重要途径。
三、网络的意识形态语言应激及其障碍
网络是诸意识形态形式及其内容的集散地,诸意识形态在网络上对话、融汇、交锋、碰撞。网络犹如哈哈镜,现实的社会意识形式及其内容,有的被放大、压缩、扭曲、拉伸、简单化、复杂化,进而形成了虚拟现实的网络意识形态。网络的与现实的意识形态之间存在循环反馈机制。在循环反馈机制作用下的社会意识形式及其内容,有的在网络里被反复强化、综合强化、累积强化。概而言之,网络意识形态是现实意识形态的非线性镜像。语言作为网络意识形态的载体,既具有语言的一般性质与功能,也具有很强的殊性及功用。网络的意识形态语言应激及其障碍现象,一定程度上诠释了网络意识形态语言的特殊性。何以认识网络的意识形态语言应激及其障碍,其相关现象、基本事实及其内在本质有待澄清。当然,就网络的意识形态语言应激障碍而言,与过敏应激不同,通常情况下低敏应激对网络社会交往不会造成直接冲突。基于网络的意识形态动态交互语境而言,探讨过弱性的语言应激,从网络的意识形态传播维度分析,意义不大。据此,下文的理论考察主要基于过敏应激。
其一,网络的意识形态语言应激障碍现象。语言的使用旨在实现人际交往目的。“语言的选择过程受语境和意图的制约,同时交际者为满足交际需求又可以调节语境因素和交际信息”(刘平,2010:28)。网络语言交互各方“搭建交际互动框架促使交际者有效坚持、加强自己的或者反对、抨击对方的观点、态度等,结果造成交际双方的对抗性升级,从而加剧冲突程度”(刘平,2010:24)。饱含社会张力的网络意识形态语境,会唤醒当事人的焦虑心理与生理上的紧张状态,这种应激状态令人感觉不舒服,当事人为了缓解或者减轻这种不适感而发生应对性反应。“应对反应是个体有意识地采取认知、情绪与行为等方式,化解环境压力或者内在不适感与潜在伤害”(Anshel et al.2012:290)。应对性反应主要包括问题取向应对(problem-focused coping)和情绪取向应对(emotion-focused coping)两大类。前者通过改变事件而不是通过调整自己的认知、情绪与行为缓解心理应激,后者通过改变自身、调整自我的认知、情绪与行为摆脱应激造成的负性影响。问题应对多见于当事人的精神压力处于中等程度以下,当事人基本能够化解自身其时面临的危机或者挑战。情绪应对则多见于当事人承受巨大的心理压力,当事人基本无力缓解或化解者相关威胁。当事人应对实际应激过程中,乐观的当事人倾向于使用直接针对应激源的问题取向应对方式,而悲观的当事人倾向于使用情绪取向应对方式。问题取向应对有助于将应激转向理性认知;情绪取向应对将可能诱发不合理的情绪性应激、非理性的意志行为,由此导致更强烈的非理性意识形态的修辞表达。问题应对和情绪应对既可以相互促进,也可能相互妨碍或者干扰。从现象看,网络的意识形态语言应激障碍是网络语言交互当事人各不相容的目的以及为达目的而发生相互之间的干预。这种语言上的相互干预是一种特殊的网络语言冲突,尤其是修辞表达冲突。网络语言冲突肇始于语言交互当事人之间对相同事物、事件、问题或者观念持有不同意见、观点、立场、视角等,因而利用相关修辞表达方式强化自己的观点,同时否定与自己相反的观点。由此发生争论、争吵、反对、反驳、异议等对抗性的言语事件或者言语行为,并体现为语言交互当事人之间相互不同意或不支持,乃至反对或者对抗。
其二,网络的意识形态语言应激障碍事实。从事实角度分析,网络的意识形态语言应激障碍是语言意义冲突。“意识形态及其相关信息是在传播过程中被人所认同的,因此,在认同特定意识形态及其相关信息的表达形式的基础上,对特定意识形态及其相关信息的认同,关键在于认同其意指,即认同意识形态及其相关信息背后的意义,简称为意义认同”(陈相光,2013:63)。语言是人类用以表达感情、传递信息、交流思想的工具,它具有丰富的社会功能。语言不等于意识形态,也不等于国家利益,但是在主导权、话语权、解释权上的语言优势可能被用来传播价值观念,谋求意识形态利益。语言的使用者可以利用其语言上的修辞表达优势获取网络上的意识形态信息传播优势,而在网络世界乃至信息社会,意识形态信息的传播优势就意味着意识形态优势。在网络中掌控意识形态的语言表达优势并形成意识形态的传播优势,就意味着特定意识形态的意义认同在网络世界占据主导地位,进而巩固特定意识形态的合法性与合理性。在网络世界,为了争抢网络意识形态的主导权、话语权、解释权,必然发生意识形态竞争。剧烈的意识形态竞争往往导致当事人之间发生语言冲突,进而可能导致当事人发生非理性的语言应激。“语言冲突的根源也在于不同语言群体间在语言利益上的差别与对立,与人们对直接的或间接的语言利益的追求密切相关”(何俊芳,2009:142)。其逻辑依据在于:第一,宏观利益目的的对立决定了冲突发生是必然的。第二,当事人的网络语言行为是维护其网络意识形态利益的思想武器。在网络世界,动态交互语境中的当事人即使在现实中具有多重身份,与其既有社会身份相比,即时的网络身份占据网络环境优越性。第三,网络动态交互语境中语言冲突的表现形式分为言语进程的表现以及信息传递的表现,前者与网络语言的修辞表达关联,后者与网络语言的意义认同关联。第四,语言应激是冲突双方采取相应策略解决冲突的可能选择之一。语言应激障碍实际上是语言冲突过程中非理性的控制-脱控-再控制反应。
这是因为:(1)在网络语言交互行为中,基于意识形态的网络语言应激障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事人对应激源的认知评价,而认知评价又取决于当事人的生活经历、个性特征、知识水平、社会地位、行为准则、期望水平等。(2)对网络交互对象的后继语言行为的不可预测性与不可控制性通常诱发更大程度的应激。Lazarus与Folkman1984年的研究证实:可预测应激源比不可预测的应激源影响小;而且同年Abbott、Sehoen与Badia的研究也证实:当应激源强度较大而且持续时间相对较短时尤其如此。如果网络交互当事人之间都相信自己可以控制或者有效影响对方的后继语言行为,那么彼此的后继网络语言行为作为应激源,对对方的影响就会小一些。(3)基于网络的意识形态语言表达的网络社会支持,与应激源影响之间的关系比较复杂:首先,网络社会支持的性质会影响当事人的应对能力,而当事人的应对能力可能决定所能得到的网络社会支持的性质;其次,网络社会支持不单指与他人的关系,还指如何识别他人的关心和帮助,即当事人主观上感受到的网络社会支持;最后,过多的网络社会支持或错误的网络社会支持与网络社会支持不足可能诱发同样的负效应,即无论受到过度保护的当事人、还是被错误支持的当事人或者网络社会支持力度不够的当事人,其应对投入可能会更少。(4)个体差异确证应激源对具有不同人格(personality)特性的当事人的影响有所不同。
其三,网络的意识形态语言应激障碍本质。语言冲突引起的心理应激凌驾当事人的应激阈值,则发生语言应激障碍。“语言交际是受目的—意图牵引的”(钱冠连,1997:166)。网络语言冲突包括非目的对立因素与目的对立因素引起的冲突。非目的对立因素引起的冲突是指语言交互各方的言语冲突不是目的原因引起的,而是由于不合理的修辞表达形式所导致。目的对立因素引起的冲突是指因语言交互各方的目的不一致而引起的语言冲突。“作为现实性的语言冲突,是冲突的双方围绕语言利益或因语言而触及到的政治、经济、文化利益而产生的冲突,冲突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重新调整利益”(何俊芳,2009:140-141)。在动态的网络语言交互进程中,交互双方或者多方之间的各自目的不是唯一的,而是存在目的体系或者目的具有层次性。目的等级系统中的最高目的,即系统中所有目的的汇集点,统摄目的等级系统中所有下位目的,下位目的是实现上位目的的方法和手段。就网络的意识形态语言行为而言,我们把目的分为两个层次:意识形态价值(利益)目的和意识形态言语目的(意图)。意识形态价值(利益)目的是决定意识形态言语目的的。从本质角度分析,如果当事人的意识形态价值(利益)目的是对立的,这种宏观利益的对立是导致网络语言交互进程中发生冲突的根本原因。
网络动态语言交互各方要达到自己的意识形态价值观的传播目的,需要借助言语交际才能完成,而言语交际的过程则是当事人对语言做出各种选择的过程,即通过选择适切的修辞表达方式达到当事人的言语意图(目的),这些浅层次的言语目的都是为了实现当事人深层次的意识形态传播目的服务的。“语言表达跟随心理模式、语言行为的目的改变而改变”(Satoshi & Jir,2010:520)。因此,在意识形态价值观冲突条件下,因观点、立场等分歧而发生对立、对抗,动态语言交互进程中出现语言冲突是必然的。网络语言交互当事人之间因为隐性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冲突而发生显性的语言冲突。从亲缘角度说,网络语言交互当事人之间因存在各不相同的亲缘关系场,具有特定的社会亲缘身份。因此,表象上网络语言行为表征人的社会关系;实际上,当事人的网络语言行为受到社会亲缘身份的制约。也就是说,归根究底,当事人网络语言行为受制于人们的社会关系。由于特定意识形态乃至表征该意识形态的特定信息具有以下几个特性:(1)价值观的排他性;(2)话语体系的相对封闭性;(3)解释权的专擅性;(4)行为的向己性;(5)符号表征的自相似性。正常的社会主体对特定意识形态及其信息都持有特定立场,而对与之相对立的其它意识形态及其信息,则往往持与之相对立的立场(陈相光,2013:62)。概而言之,网络的意识形态语言应激障碍本质在于价值观冲突。
综上,研究网络意识形态心理与行为的适切性,源于网络的意识形态实践需要。本文从概念界说、特性分析与发生机理三个角度澄清何为语言应激及其反应障碍;从语境、表征与因果三个角度厘定何为网络的语言应激障碍;从表象、事实与本质三个角度译解何为网络的意识形态语言应激及其障碍,其学理价值在于从语言应激及其障碍,到网络的语言应激及其障碍,再到网络的意识形态语言应激及其障碍,疏通其理论解释的递进路径。由此,针对网络的意识形态语言应激及其障碍现象,达致比较科学、合理的解释逻辑。此外,这一学理考察的现实社会意义在于,围绕网络的意识形态语言应激及其障碍,明确并善用语言应激及其障碍的心理与行为反应机制,实施必要的心理建设和社会建设。这既是网络意识形态研究直面现实问题的必然逻辑,也是应然价值。
[1] 柴 磊(2006).试析语言的“经济原则”在网络交际中的运行和应用.山东外语教学,4.
[2] 陈相光(2013).论意识形态及其相关信息认同的复杂性.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
[3] 何俊芳(2009).论语言冲突的若干基本理论问题.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3.
[4] [英]怀特海(2010).思维方式.北京:商务印书馆.
[5] 林崇德、杨治良、黄希庭(2003).心理学大辞典(下).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6] 刘 平(2010).会话冲突中元语用话语的语言表征及语用功能分析.外语教学,6.
[7] 苗东升(2006).系统科学精要.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8] 钱冠连(1997).汉语文化语用学.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9] 钱令嘉(2011).关于应激与认知的思考.军事医学,9.
[10] 卿志琼、陈国富(2003).心智成本理论:一个超越新古典经济学的解释框架.当代经济科学,6.
[11] 王卫平(2004).幽默在语言应激中的防御功能.医学与哲学,7.
[12] Mark H.Anshel,Toto Sutarso & Didem Sozen(2012).Relationship between Cognitive Appraisal and Coping Style Following Acute Stress among Male and Female Turkish Athletes.InternationalJournalofSportandExercisePsychology,10(4).
[13] Moriizumi Satoshi &Takai Jir(2010).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Japanese Interpersonal Conflict Styles and Their Language Expression.TheJournalofSocialPsycholog,150(5).
■责任编辑:叶娟丽
On the Language Stress and Its Disorders of Ideology in the Internet
ZhaoNi&ChenXiangguang(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The ideology on the internet is the nonlinear mirror of realistic ideology.The language stress is the litigant’s psychological and physiological responses caused by the threats or challenges of specific speech,which are perceived by the litigant’s cognition or evaluation.The reasonable degree of cognitive, emotional or behavioral stress is significantly weakened,and these are the concrete manifestation of disorders of language stress.The disorders of language-expressed stress in internet ideology look exteriorly like the conflict of language-expressed,but these are the conflict of linguistic meaning in fact and the conflict of values in essence.
internet; ideology; language stress
D64;B84
: A
: 1672-7320(2017)02-0139-07
10.14086/j.cnki.wujss.2017.02.013
2016-09-02
全国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教育部重点课题(DEA130240);广东省青少年和青少年工作研究重大课题(2016WT041);广州市哲学社会科学“十二五”规划共建课题(13G05);华南师范大学青年教师科研培育基金(16SK19)
■作者地址:赵 麑,华南师范大学化学与环境学院;广东 广州 510631。Email:21359595@qq.com。 陈相光,华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