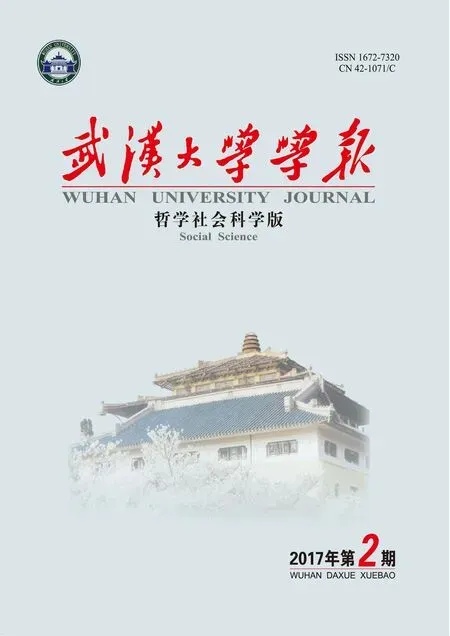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独特性及内在根据
马 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独特性及内在根据
马 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呈现鲜明的“中国特色”,从而体现出明显的独特性。从“三个独特”即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命运、独特的基本国情角度阐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有助于正确认识法治道路的唯一性与多样性的关系、中国法治道路的“独特性”与人类法治“一般性”的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独特性具体体现在三个方面:实现方式上具有强烈的顶层推动特征;方法手段上具有独特的德法互补特征;发展途径上具有明显的渐进稳健特征。其内在根据是:历史惯性和实践证明了顶层推动的必要性;中华文化为“德”“法”融合提供了深厚的土壤;现实国情要求法治建设必须渐进稳健。从中可以进一步看出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方法论问题,即要从中国的客观实际而不是抽象的理论出发;要从中国道路整体性而不是单纯的法学角度出发。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中国道路; 德法互补
十八大以来,诸如“中国梦、中国精神、中国力量”等词汇频繁地进入公众视野,体现出阐发中国“独特性”的理论诉求。同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蕴含着一系列深刻的理论问题。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独特性,目的在于挖掘“中国特色”的具体内涵,从而有助于理解我国法治道路的本土化特色。
一、“三个独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阐发维度
“三个独特”即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命运、独特的基本国情。习近平在2013年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讲道:“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命运,独特的基本国情,注定了我们必然要走适合自己特点的发展道路……宣传阐释中国特色,要讲清楚每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基本国情不同,其发展道路必然有着自己的特色。”(习近平,2013)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也应当从这个维度出发,因为中国的文化传统是独特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作为上层建筑才有其文化的根本属性;中国的历史命运是独特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才有其深厚的历史根基;中国的基本国情是独特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才有其实现的可能性。从“独特性”角度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蕴含着深刻的哲学方法,提供了深厚的立论基础,体现出中国化的思想立场和话语方式,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一) 有助于正确认识法治道路的唯一性与多样性的关系
法治道路是唯一性还是多样性?这是当前必须厘清的一个问题。因为这一问题从根本上涉及“外来化”与“本土化”的价值交锋。“本土化”自西学东渐以来就一直是中国现代化问题的一个焦点,如“旧学为体、新学为用”(张之洞,1983:427)、“全盘的西化”(胡适,2014:189)、“西体中用”(李泽厚,1994:336)等观点,都不同程度强调中国发展应借鉴西方。向别人学习无疑是十分必要的,但也要防止西方中心论。值得注意的是,目前尚存在视西方法治为唯一道路的观点,“一段时期以来,围绕宪政等问题可谓众声喧哗,甚至有人打着法治的幌子,大肆渲染西方的法治理念和法治模式……我们强调的依宪执政、依宪行政,是社会主义法治的范畴,根本不是什么西方式的‘宪政’”(溥德书,2015:39)。
纵观世界各国,法治道路具有“多样性”。“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是从该国人民的特殊性和生活中成长起来的一种有机的产物”(密尔,1982:6),可见法治并不是一个模板。即使三权分立、权力制衡的宪政原则是西方法治的普遍道路,英国有英国的法治,美国也有美国的特色。所以,我们不应将西方法治中的宪政、自由等抽象绝对化,将其作为普世的人类法治文明的唯一标准。
(二) 有助于正确认识中国法治道路的“独特性”与人类法治“一般性”的统一
另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独特性”与人类法治的“一般性”是统一的,独特性不是“另类”,而是“共性”的具体表现。实际上,“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的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列宁,1995:776),因为“马克思主义的最本质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就在于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列宁,1995:407),即“一切以条件、地点和时间为转移”(斯大林,1985:206)。所以,从“实事求是”的高度,“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固有的而不是主观臆造的规律性。”(毛泽东,1991b:801)
因此,从独特性角度论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必然性,体现了特殊性与一般性、个性与共性的统一。在强调“中国特色”这一特殊性时,并不是忽视甚至否定人类法治的历史实践已经明证的具有共性的东西,而是阐发这些共性的东西如何在中国实际中表现出来。像经济发展必然受经济规律指导和制约一样,法治也有规律可循。可以说,人类法治道路有一些内容是共同的,如民主战胜专制、平等取代特权。我们要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放在人类法治发展的宏观视野,将“中国特色”和“世界眼光”、“当前阶段”和“终极追求”统一起来。
值得强调的是,上述两对关系之间也是密切关联的。唯一性与多样性的关系意在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和西方法治道路是有区别的,不存在唯一性的法治道路,在差异中体现出多样性,着重强调的是差异。“独特性”与“一般性”的关系则在上述基础上说明这些差异的原因在于各自的独特国情,即使如此,我们也要在多样性中发现“共性”,从而为我国的法治建设提供借鉴。可见,第一层关系侧重讲区别,第二层关系侧重讲联系。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独特性的具体体现
从上述角度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独特性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 实现方式上具有强烈的顶层推动特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强调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将党的领导放在了重要地位,体现了明显的顶层推动特征,这是从我国法治建设的实现方式上讲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中14处出现“党的领导”,第七部分单列“加强和改进党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领导”,指出“党的领导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最根本的保证……把党的领导贯彻到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过程。”
在理解顶层推动作用时,要正确看待党和法的辩证关系,很多学者指出“诘问党大还是法大,是伪命题”(王文婷,2015:63)。目前理论界对于党的领导与依法治国的关系从诸多方面进行分析:如从党的作用角度,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需要党的顶层设计;从我国国情角度,认为我国需要实行“政府推进型”法治模式,不可能自发地“社会演进”;从复杂的世情角度,认为在世界格局下中国需要赶超,必然要走一条集中权力的道路,集中力量办大事,等等。这些研究是很有必要的,笔者将在上述论述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的历史与现实进一步深入分析。
(二) 方法手段上具有独特的德法互补特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突出了“以德治国”的作用。《决定》在总目标中提出“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指出“国家和社会治理需要法律和道德共同发挥作用”,并在具体内容上有诸多体现,如《决定》第五部分中指出要“加强公民道德建设,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法治的道德底蕴,强化规则意识,倡导契约精神,弘扬公序良俗”等等。
值得说明的是,作为两种社会秩序的调节手段,道德与法律具有明显区别,甚至在具体的行为裁量中存在冲突,两者作为治理方式也有着较大不同。但同样不容忽视的是,两者在一定程度上又是相通的,尤其是在方法手段上完全可以实现互补。如良好的社会道德水平可以大大降低法治成本;执法、司法主体的道德素养也可以明显提升法治质量;在我国当前法治建设尚不健全的情况下,许多(虽不是全部)在文化中长期形成的道德规范还具有积极作用和现实价值,并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转化为法律规范;法治建设应当充分继承挖掘中华文化中的有益成分,从而使法治思维逐步在民族文化心理的基础上得到培育,从而加速法治建设的进程。
但问题是,由于我国缺乏法治传统,强调法治建设迫在眉睫,人们担心,提倡德治会不会无形中弱化了法治?会不会对法治造成障碍?更有甚者认为德治易走向人治。这些问题之所以产生,笔者认为原因在于缺乏从中华文化的整体角度看待中国法治文化的构建方法,从而会产生德治优先还是法治在前这样貌似对立的问题。故从中华文化的特质出发有助于更好理解两者的关系,本文在后面从独特的文化传统角度加以论述。
(三) 发展途径上具有明显的渐进稳健特征
最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在发展途径上具有明显的渐进稳健特征。《决定》贯穿了“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的精神,指出:“必须从我国基本国情出发,同改革开放不断深化相适应……围绕社会主义法治建设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借鉴国外法治有益经验,但决不照搬外国法治理念和模式。”《决定》具有强烈的问题意识,认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一个系统工程,是国家治理领域一场广泛而深刻的革命,需要付出长期艰苦努力”。并强调从微观入手,制订并注重落实大量针对实际问题的新规定新措施,有很多亮点,体现出稳妥渐进的特点。如在实现立法和改革决策相衔接上,《决定》指出“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要及时上升为法律。实践条件还不成熟、需要先行先试的,要按照法定程序作出授权”;再如在审计制度上,指出要“探索省以下地方审计机关人财物统一管理”,等等。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独特性的内在根据
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上述独特性有其内在根据。
(一) 历史惯性和实践证明了顶层推动的必要性
首先,要正确认识“大一统”的历史惯性与顶层推动的内在联系。历史与现实是相关的,在研究中国历史时,我们不应当不加分析地贴上“封建”、“落后”的标签。在清醒认识到历史传统存在缺陷的同时,应当看到“大一统”的明显优势。自秦以来我国形成的“大一统”模式经朝代更迭,形成了巨大的惯性。历史证明,“大一统”能有效维护国家统一和社会安定,其优势是灵活反应和迅速执行,我国历史上的“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康乾盛世”等均与“大一统”具有内在联系。马克思恩格斯在论述国家时曾讲:“集权有其存在的历史的和合理的权利”、“国家集权的实质并不意味着某个孤家寡人就是国家的中心。”(马克思、恩格斯,1982:396-397)之所以“大一统”具有一定合理性,是因为其建立在社群主义这一政治文化心理基础之上而非个人主义土壤之中。“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马克思、恩格斯,1995a:585)我国在几千年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形成了强烈的文化心理惯性,强化了个体的民族归属感。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必然要遵循这一心理惯性,从中发挥集体主义精神,从而把家庭观念、集体主义、爱国主义和全球主义进行整合,建立一种新型的社群主义。这如同“东亚工业国家在儒家文化影响下,已经发展起一种现代文明,在其中,对抗主义、个人主义、利己主义的成分较少”(杜维明,2001:16)。中国的社会主义可以说是这种“新型社群主义”的发展和延伸,故“大一统”模式反映了中国社会文化的深层结构。从这个角度,中央集权制与社会主义是同源的(托克维尔,2012:136)。
其次,要看到党的顶层设计作用在法治实践中的证明。重要的是,党的顶层推动作用已经得到了实践证明。集体行动需要权威,否则就会丧失效率和秩序,没有这一作用就不可能有中国模式。“如果没有中央……各顾各,相互打架,相互拆台,统一不起来。”(邓小平,1993:278)同样,在法治建设中,不能片面强调并弱化、放弃和推翻中央的作用。可以说,把党的领导贯彻到依法治国全过程和各方面,是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一条基本经验。
具体来讲,从新中国成立前制定我党历史上的第一个土地法《井冈山土地法》开始,到新中国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到建国初期我国第一部社会主义宪法即“五四宪法”颁布,到十一届三中全会要求“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再到十三大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长远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政治体制,十四大高度重视法制建设,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十六大强调要将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得到全面落实,十七大对加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做出了全面部署,特别是十八大以来强调“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建设法治中国”,十八届四中全会更是第一次以“依法治国”为主题,在党的领导下我国法治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
最为关键的是,经过多年实践,我党在坚持改善党的领导方面取得了重大突破。习近平指出:“评价一个国家政治制度是不是民主的、有效的”,首要的是“看国家领导层能否依法有序更替”,“经过长期努力,我们在解决这些重点问题上都取得了决定性进展。我们废除了实际上存在的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习近平,2014)当前,中央高层权力交替的中国模式已基本成形。权力不是个人向个人的交接,而是中央领导集体的过渡,中国高层权力交替已走出一条符合自己文化传统和现实的路径。而西方派系政治理论在很大程度上误导人们的学术思考和公众舆论,“依靠人际关系、裙带关系、派别关系等概念为分析工具来思考中国领导人代际权力交接,缺乏准确性和可靠性。”(郭苏建,2013:27)
最后,要理解从“顶层设计”到“政府推进型法治”的必然性。由于我国的法治建设必须强调“顶层设计”的作用,因此从根本上属于“政府推进型法治”。“我们要坚持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切实防止出现群龙无首、一盘散沙的现象……切实防止出现选举时漫天许诺、选举后无人过问的现象……切实防止出现党争纷沓、相互倾轧的现象……切实防止出现人民形式上有权、实际上无权的现象……切实防止出现相互掣肘、内耗严重的现象。”(习近平,2014)这说明中国法治进程不能靠理想主义、激进主义的权利自由诉求来推进,只能确立互动平衡精神和务实策略。
其实,类似我国“政府推进型法治”的模式在国外也有很多成功例子。如“建立高度集权的政府……是战前的日本和战后的东亚NIEs(新兴工业经济体)在一代人的时间内就完成工业化或从落后农业国变成新兴工业经济体的重要原因之一”(李文,1999:32)。新加坡的经济腾飞也得益于一种集权的政治模式,形成了一种不同于西方的独特模式,可称为“共同体法治”。相反,有些国家因抛弃中央集权改革而导致分裂,如印度尼西亚因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而进行地方分权改革,诱发了民族分离和社会暴力事件。
(二) 中华文化为德法互补提供了深厚的土壤
坚持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相结合,不是将“德”与“法”简单叠加和机械替代,而是在手段层面实现两者有效互补,并非用道德理念弱化法治精神,而是使具有浓厚民族传统的中华文化在法治建设中发挥应有作用,在尽可能剔除不利于现代法治的内容后,汲取有益的文化资源,促进我国法治建设。笔者认为,中华文化能够为德法互补提供深厚土壤,最突出地体现在中华文化对社会个体的道德约束上,这为法治约束提供了正向指导。尤其体现在:
首先,士大夫精神体现出中国传统贤人治理的德性要求。在研究中国历史时,应高度重视“士大夫”这一知识官僚阶层的主体作用。在古代稳定的“辅助决策、执行、监察”的权力模式中,日理万机的“丞相”和“内阁”中均有源源不断的士大夫进入,以“给事中”为代表的决策修正人员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与之相应的是举贤使能机制,自秦以后曾出现过察举征辟制、九品中正制、科举制等,目的是“尊贤使能,俊杰在位”,有效增强了中国士大夫官僚队伍的建设。
仔细研究,中国古代贤人治理这一特色是有其“士大夫精神”的德性文化基础的。“士大夫精神”即“士志于道”中的“道”,表现为“内圣外王”的政治理念,在道德上体现为从“君子人格”到“圣人为王”的追求。所谓“君子人格”,指君子应具备仁义礼智信等品格,即宋儒提出的“圣贤气象”。按照修齐治平的逻辑路径,士大夫以“为天地立志、为生民立道、为去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张载,1978:320)为人生最高目的,在政治实践中形成了以道侍君、忠而不奸的从政信条,形成了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忧国情怀,树立了心系百姓、勤政奉公的责任意识。所以,在中国的法治建设中,不应丢掉这一传统优势。“如果中国要实行选举民主,就必须将英才主义和民主,选择和选举有机结合起来。”(郑永年,2011:17)只有这样才能超越西方民主制度,从而在集体主义的传统上成长出民主集中的现代法治,实现竞争与合作、权利和义务、自由和秩序的统一。
其次,应厘清中国古代德治、法治与人治的关系。值得说明的是,中国古代贤人治理往往被认为是人治。这样一来,中国古代“德治”很容易成为“人治”的代名词,法治也往往被认为是人治的附属品。笔者认为有以下问题需要澄清:
一是应避免将古代德治简单等同于人治。必须承认,中国古代的人治色彩十分浓厚。事实上,中国古代的德治与人治不应混为一谈,也并非德治导致了人治,相反是人治“盗用”了“德治”的名,因此德治被变形了,或者说德治没有得到很好的实现,应当反对的是人治而不是德治。剔除了人治后,德治才可能得以彰显,与法治的结合才有可能。总之,我们在深刻认识中国古代人治弊端的同时应避免将德治混同于人治,要走出人性假设的误区,即认为传统德治缺乏对性恶的反思,这是不全面的。相反我们应倍加珍惜中国古代的德治精神,如“仁政”思想对法治中“民本”理论的支撑。
二是要深入研究古代法治中的有益成分。同样,一谈到中国古代法治,往往也被简单认为法治充其量只是人治下的“法治”,粗看起来是的,但其中的逻辑误区也同前面所讲的将德治与人治混淆一样,掩盖了中国古代法治中的有益成分。其实,中国古代法治中包含的秩序理念及一定程度上的分权思想都具有借鉴性。古代法家的宏观法治思想体系均有很多合理内容,在具体的法治建设中也有很多成果,“如统一国家内不同社会制度共存、法律对权力的制约和对官员的监督、社会基层组织建设、民事纠纷和轻微刑事案件的非诉讼解决、死刑复核权由中央行使,以及录囚和大赦制度等。历史是个宝库,只要我们不懈发掘,就能找到有益的宝藏”(刘海年,2009:199)。我国历史上虽出现过秦朝“尊法弃德”和明代“刑乱国用重典”的“德”、“法”非正常关系,但也出现过西周“明德慎罚”、西汉“礼法并重”、唐代“贞观修礼”的时期。我国还创造了“中华法系”,唐律成为我国历史上最严密系统的法典。总之,我们要善于传承转化古代法治中与现代法治相通的内容,如“以民监官”的制衡智慧、“抑强助弱”的公平精神,等等。
最后,当代中国应不断开拓“道德的民主法治”。“中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单靠条条,是无法管全、管细的。线条画得再多,也有空白。”(李瑞环,2005:286)道德有利于补充法律的空白。所以,当今中国必须开拓一种具有厚重人文底蕴的“道德的民主法治”,要认真汲取德治的优秀传统内容。如中国文化中的和谐文化、和平主义、中庸精神、节制态度在很多方面和一定程度上还体现人类法治的方向。因此,“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毛泽东,1991b:707-708)特别是在人们日益看到现代性的缺陷后,由于中国文化具有明显的后现代特征,人们已更加清楚地认识到它对于解决当代社会问题的独特价值。
(三) 现实国情要求法治建设必须渐进稳健
从现实国情出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要求我们渐进稳健,走自己的路,不照抄照搬西方。“中国是一个巨人,只要稳步走,步子就是大的;只要不摔跤,就是一个了不起的成绩。最可怕的是自己折腾自己,自身先发起烧来。”(李瑞环,2005:264)这主要体现在“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和内生演化”三个方面。
首先,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性要求法治建设只能长期发展。即中国法治道路必然是漫长曲折的,法治在我国近代发展起步晚,不可一蹴而就。国情复杂性决定了我国法治发展道路的长期性,要正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客观情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订规划。”(邓小平,1993:252)
中国法治道路的长期性要求法治建设不仅仅在表层,而在于深层次的构建。如果致力于将外来法律“克隆”到本土社会中,必将与现实脱节。中国清末以来法律制度变迁大多数都是强制性的变法,清末预备立宪失败原因在于照搬照抄日本和英国等的法治,没有考虑当时中国的情况,这可以部分地说明近代法律现代化为何难以真正成功。强硬的照搬照抄西方,以外力从表层强硬干预变法,往往出现本末倒置的结果。
但长期发展绝不是缓慢发展,其机理是在量变基础上实现质变,增量的发展要以已有的存量为基础。所谓增量民主(俞可平,2003:148),就是渐进式的、积极稳妥的、有计划的、有步骤的发展民主之路。我国从古代法治到近代引进西方法治理念,直到当前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在量变之中实现质变。
其次,中国的“超大性”决定了法治建设适合渐进改进。在法治建设中,我们应渐进改进,这与国家的“超大性”有关。按照奥尔森集体行动理论,小集团的凝聚力和有效性更高(奥尔森,1995:64),因为在不同规模的集团中,小集团的人数少,利益容易达成一致。因此国家越大,越要坚持渐进改进。我国国情的“超大性”主要体现在地域规模、人口数量等方面。中国地域辽阔,人口众多,易出现矛盾复杂的情况,政策推进和更改难度较大,直接激进的改进显得不切实际。改革的实质是各种利益关系的调整,“具有非‘帕累托最优’的性质,不可能在没有人利益受损的情况下让所有人从改革中受益。”(樊纲,1996:101)需把成本和风险分摊在一个更长时段里,因此中国法治道路应有自己的风格,体现“先易后难”的务实主义。
但渐进改进并非简单的经验演进,而应是按阶段进行的理性建构。其机理是在原有的体制框架内,逐步引入新体制的因素,逐步从边缘到核心。有学者将“中国法治建设分为外围建设和核心建设两部分”(蒋立山,1995:1),前者指以维护秩序为目标的加强法制问题;后者指以保障人权和制约权力为目标的政治体制问题。
世界各国的法治建设为之提供了借鉴,日本明治维新时期明治政府视察欧美各洲之国体与法律规章,探求公法中适宜之良法,遵循了渐进发展原则。相反的例子则是泰国自1932年以来因军事政变每4年颁布一部宪法,是世界范围内法治建设严重受挫的国家之一。
最后,中国国民的法律素养决定了法治建设必须内生演化。内生演化是指法治建构应从民众对法治的需要渴望出发,以内因推动外因。《决定》指出:“法律的权威源自人民的内心拥护和真诚信仰”、“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便形同虚设。”由于中国现代法治必须与亿万中国人的价值观念和心态相联系,故当前我国国民的法治精神教育十分必要。一般而言,法治包括“精神要件、实质要件、形式要件”(徐显明,1996:37)三个层面,首要的是“法治精神”,为此必须进行法治启蒙,因为法治是人类基于自身的价值而衍生的一种制度,人文精神是深藏其后的最高精神力量和基础。现代英国法治就是在普通法基础上,在17、18世纪理性法治主义的思想启蒙和自由主义理论铺垫下逐渐形成的。人类的法治经验告诉我们,仅仅为技术问题寻找技术性的解决办法是远远不够的,必须从人的维度思考问题。
反观现实,当前我国国民的法治思维还有待提高,传统“人治”思想还根深蒂固。中国人对家族和宗族的认同大于国家,也一定程度上造成法律权威不足、崇尚法治的氛围不浓。孙中山的训政思想中包含国民训练的内容,也基于对民众政治素质的考虑。“不经训政时代,则大多数之人民久经束缚,虽骤被解放,初不瞭知其活动之方式。”(孙中山,1986:102)时至今日,这仍是我们在法治建设中须重视的问题。“经历了几千年的封建社会,缺乏民主意识与法治传统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先进文化可谓任重道远。”(习近平,2005:4)因此,我们的法治建设要在转变国民法治意识上逐步实现内生演化。
四、启发与思考: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方法论问题
一定程度上,方法就是结论。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必须理论联系实际,坚持正确的方法论原则。
(一) 要从中国的客观实际而不是抽象的理论出发
正如“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毛泽东,1991a:115)一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也需要实事求是地研究中国问题。不得不指出,在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研究中,有些观点往往从西方法理中首先提取出诸如公正自由等一般抽象原则,然后进行逻辑推理,这自然无法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独特性,甚至得出一些诸如将党与法、德与法对立的不正确的结论。这是由于没有从抽象走向具体,离开了实际。“具体之所以具体,因为它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因而是多样性的统一。”(马克思、恩格斯,1995b:23)同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逻辑起点不是抽象的概念,应是生动的中国实际。脱离实际是主观主义的做法,毛泽东曾指出:“许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者也是言必称希腊,对于自己的祖宗,则对不住,忘记了。”(毛泽东,1991c:797)这对于我们今天有很大启示。苏联解体前的“戈氏改革”就是过于依赖理论、忽略现实问题的有力证据。
(二) 要从中国道路整体性而不是单纯法学角度出发
整体和部分是一对重要的范畴,事物作为整体所呈现的特有属性,与其部分在孤立状态下所具有的属性有质的区别。显然,中国道路是整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是部分。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一些误区还来自于将视野局限在单纯的法学领域,而缺乏对中国道路的整体关注。其实“中国特色”体现在方方面面,是政治经济文化的整体体现,忽略中国道路的整体性单纯从法而谈法治道路,是片面局部地看问题。《决定》指出,“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制度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根本遵循。”实际上,“道路与制度紧密相连,道路的成功离不开制度保障。任何法治体系都必须与一国的制度相一致……只有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才能确保我国法治体系和法治道路具有‘社会主义’的制度属性和‘中国实际’的国情特色。”(夏自军,2014:37)
总之,正确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深刻内涵、基本特征和内在根据,关键在于把握其蕴含的“中国特色”。故笔者从“三个独特”角度发现其具有顶层推动、德法互补和渐进稳健特征,并分析了其内在根据,从而为深刻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提供了方法论原则,这不但有利于厘清当前诸多重大理论问题,更有助于在实践层面推进法治建设,从而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发挥积极作用。
[1] [英]奥尔森(1995).集体行动的逻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 邓小平(1993).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3] 杜维明(2001).超越启蒙心态.国外社会科学,2.
[4] 樊 纲(1996).渐进改革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
[5] 溥德书(2015).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开拓性与艰巨性.中共云南省委党校学报,1.
[6] 郭苏建(2013).西方派系理论误读中国政治.人民论坛,7.
[7] 胡 适(2014).社会与文明.广州:广东旅游出版社.
[8] 蒋立山(1995).中国民主法制(法治)改革的基本框架与实施步骤分析.中外法学,6.
[9] 李瑞环(2005).学哲学用哲学(上).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0] 李 文(1999).东亚政府主导型发展模式的形成及转换.当代亚太,7.
[11] 李泽厚(1994).中国现代思想史.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
[12] 列 宁(1995).列宁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3] 刘海年(2009).法律史学者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做出贡献责无旁贷.法学研究,2.
[14] 马克思、恩格斯(198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5] 马克思、恩格斯(1995a).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6] 马克思、恩格斯(1995b).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7] 毛泽东(1991a).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8] 毛泽东(1991b).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 毛泽东(1991c).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20] [英]密尔(1982).代议制政府.北京:商务印书馆.
[21] 斯大林(1985).斯大林文集(1934-1952年).北京:人民出版社.
[22] 孙中山(1986).孙中山全集:第11卷.北京:中华书局.
[23] [法]托克维尔(2012).旧制度与大革命.北京:九州出版社.
[24] 王文婷(2015).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理论导报,2.
[25] 习近平(2005).在(浙江)省社科联第五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浙江社会科学,1.
[26] 习近平(2013).胸怀大局把握大势着眼大事,努力把宣传思想工作做得更好.人民日报,2013-08-21.
[27] 习近平(2014).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6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09-06.
[28] 夏自军(201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核心要义与现实回应.重庆社会科学,12.
[29] 徐显明(1996).论“法治”构成要件─兼及法治的某些原则及观念.法学研究,3.
[30] 俞可平(2003).增量民主与善治.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31] 张 载(1978).张载集.北京:中华书局.
[32] 郑永年(2011).中国共产党的未来走向:挑战与机遇.当代世界,7.
[33] 张之洞(1983).中国哲学史资料选辑(近代之部).北京:中华书局.
■责任编辑:叶娟丽
The Distinctiveness and Its Inherent Basis of the Road of Socialist Rule of Law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MaZhong(Lanzhou University)
The road of socialist rule of law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has distinct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shows its apparent distinctiveness.It is very important in theory to clarify the road of socialist rule of law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reeKindsofDistinctiveness” including the distinctive cultural tradition,distinctive historical destiny and distinctive national condition.And it is very helpful to correctly understand the relation between distinctiveness and diversity in the road of rule of law,and the relation between “distinctiveness” of Chinese socialist rule of law and “generality” of rule of law in human society.The specific distinctiveness of the road of socialist rule of law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s represented in three aspects:(1)The strong top-level drive is the main manner to realize the socialist rule of law; (2)Morality and law supplement each other and (3) The obvious progressive and steady steps form the approach of development.Its inherent basis relies on following facts: (1)The historical tradition and practices have proved the necessity of the “top-level drive”. (2)Chinese culture provides a deep soil for the integration of “morality” and “law”; and (3)The real national conditions require that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rule of law must be steady and gradual.In this manner,we can further understand the methodological issue,namely,we must study the road of socialist rule of law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rom the reality of China rather than any abstract theories,and from the entirety of Chinese road rather than any simple or pure view of science of law.
the road of socialist rule of law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e road of China; complementary of morality and law
D10; DF02
: A
: 1672-7320(2017)02-0121-08
10.14086/j.cnki.wujss.2017.02.011
2016-07-05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15LZUJBWZY050)
■作者地址:马 忠,兰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甘肃 兰州 730000。Email:mazhong@lzu.edu.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