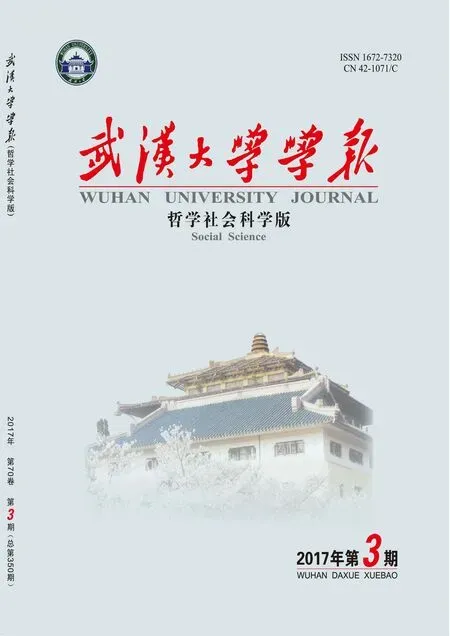关于政治与行政二分的再认识
——以澳大利亚为例
Andrew Podger[著] 韩瑞波[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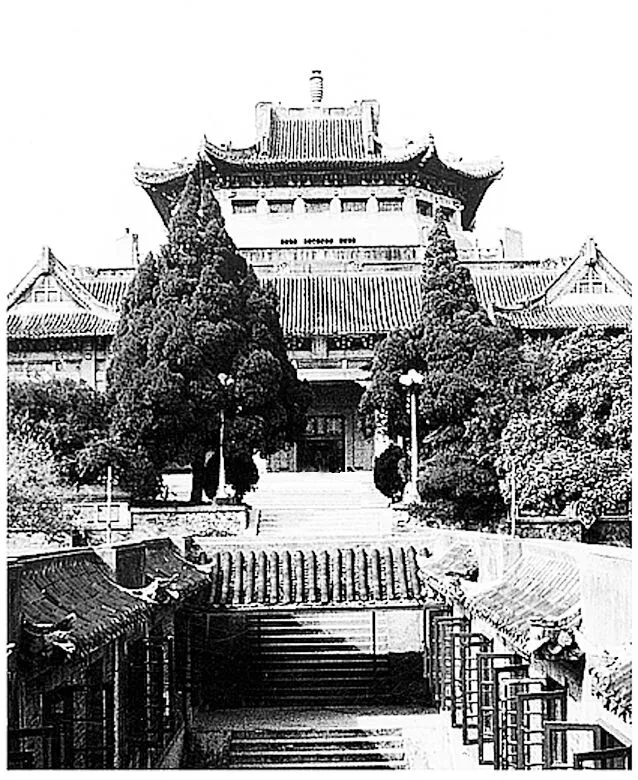
关于政治与行政二分的再认识
——以澳大利亚为例
Andrew Podger[著] 韩瑞波[译]
西方民主对政治与行政做了传统上的区分。英国于1854年通过了《诺斯科特-杜威廉报告》(Northcote-TrevelyanReport),该报告提倡构建一种基于绩效的行政部门,使之免受裙带关系和党派之争的影响。澳大利亚即依此例。美国的民主传统中政治与行政二者的界定则不那么泾渭分明,但伍德罗·威尔逊所倡导的从政治过程中分割出来的行政专业化仍具有重要意义。在任何情况下,政治与行政总是针锋相对。因为行政必须随着民主进程的变化而变动,与此同时,政客的政策必须同样得到公平、妥善且高效的执行。中国的政治与行政尚未分离,所有的政府部门都接受党的领导。然而,中国政府行政的专业性可从其值得嘉奖的官僚系统的长久历史中得以力证——执政党的每一决定都基于民众的利益,政策制定的过程也更透明。过去的40年里,澳大利亚的民主发展对政治与行政之间的互动有着重要影响,但问题依然存在。虽然中国的制度安排与澳大利亚差异巨大,但面临的问题是类似的,即确保政府行政公正(高效、有效且妥善),并且契合于中央政府、省级和地方政府对公共利益的阐释。
政治与行政的关系; 伍德罗·威尔逊的二分法; 澳大利亚;部长级顾问; 公共服务
一、 政治与行政二分:起源与核心挑战
政治与行政二分的观点出现于19世纪,因为在这一时期更多的民主政府开始掌权,特别是在英国和美国。改革,还包括法国和北美洲一些国家的革命,最初都是侧重于用代表民众及其意愿的制度性安排来取代君主的绝对权力。现如今,新的民主制度必须解决更现实的问题,即向公众提供高效和有效的服务。
在英国,1854年的报告产生了持久的影响,这种影响不仅限于英国,还包括澳大利亚、加拿大、印度、南非、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在内的英联邦国家。它是由保守的政客斯坦福德·诺斯科特(Stafford Northcote)和经验丰富的公务员杜威廉(C.E.Trevelyan)为首相威廉·格莱斯顿(William Gladstone)所准备的(Northcote & Trerelyan,1854)。众所周知,《诺斯科特-杜威廉报告》的重点是关于公务员的任命问题,建议实行绩效原则,主张通过公开考试进入公务员队伍,其目的是扭转包括政治领导人在内的裙带关系和腐败现象,进而提高行政效率。
该报告并未立即落实,也没有明确建议对政治与行政进行分离,但它真切地使人们意识到构建专业化公务员制度的重要性,并对这种专业精神意味着非党派和公正表示认同。到19、20世纪之交,一个独立于政治的专业公务员制度成为“威斯敏斯特式”的政府执政的特殊形式。自此,绩效原则获得其构建基础。
此后,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1886年的演讲是政治与行政分离的想法得以产生的关键。该演讲的主题是“行政研究”(Wilson,1887:197-222),以论文的形式于1887年发表。文中提到,“尽管政治为行政设定任务,但行政本身却是一门科学,而不是政治学的一个子集,即处于‘政治范围之外’”。现如今,它仍是一份富有魅力的文件,详细而明确地讨论了分离的情况。它阐明了政府与美国的宪法和法律以及政治和舆论的关系:
普通法……显然是处于行政之外或之上的……坚定地忠于他们所服务的政府的政策将培育善的行为。这种政策……不会是永久官员的创造,而是政客的发明,他们对舆论的责任是直接而不可避免的。
威尔逊认为,与舆论相一致的政策所依循的民主原则提高了分离政治和行政的需求和能力。这种责任框架允许行政人员拥有相当大的权力和自由裁量权,它仿效了在欧洲大陆中所看到的那些官僚程序,尽管这些程序在民主化进程方面有所欠缺。政治与行政的正式分离使美国获得了民主和良好的行政。值得注意的是,威尔逊主张整个官僚机构均是非党派的:
脱离了人们的共同政治生活,也使它和政治领导人以及普通民众都相距甚远。
这一报告比《诺斯科特-杜威廉报告》研究得更加深入,因为它提及行政的结构与实践“易于考察和监督”,此外,它还提到了绩效。
尽管美国人不断从威尔逊的演讲或文章中获得感化与参考,但美国的政治与行政分离从未像英国和其他“威斯敏斯特式”国家那样进行得如此彻底,究其原因,可能是因为美国的行政机关与立法机关的分离要求在政府行政部门任命非选举产生的政治党派领导人(议会制度的部长是立法机关中的民选成员)。但是,美国政府似乎拥有比威尔逊设想的更多的党派任命,特别是在地方政府中,还设有许多担任行政职务的民选职位。
当然,中国没有美国或议会民主国家那样的权力分离,中国共产党在所有的政府部门中都发挥着重要作用。至少在形式上,中国没有实现政治与行政的分离。然而,中国有一个古老的传统,即通过一个以绩效为特征的程序,基于儒家的哲学和教义,选择技术娴熟的顾问和管理者。此外,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共产党执政以来,官方立场是:政府是人民的代表,而不是皇帝的专制统治。近年来的改革表明,中国的政府行政越来越重视专业精神,包括改进行政程序,确保政府政策响应公众舆论。一个有趣的问题随即出现,事实上的分离是否已经开始出现?这种分离是否应当加以重视或被正式化?
将政治与行政加以分离必须同时遵循两个原则:(1)民主原则,政府代表公众及其利益进行运作(用威尔逊的话来说,就是反映民意);(2)行政原则,政府高效、有效且公平(公正和非党派)。其中,第一个原则关乎多数统治;第二个原则有助于保护人们免受多数人暴政(补充司法机关在这方面的基本作用)。由于必须遵循以上两个原则,因此行政不能完全独立于政治。由此带来的核心挑战即是确定行政应当具有的独立性的适当程度,其关键在于政治与行政的互动方式。主要表现在:行政机关在政策建议方面应当扮演什么角色?行政在多大程度上要卷入政策执行(解释和填补政客制定的政策),而不仅仅是执行政策?
二、 澳大利亚政治与行政关系的早期形态
澳大利亚于1901年1月1日成为独立联邦制国家,其宪政体制大多仿效英国和美国,政府在联邦体制内实行议会制,而上议院(参议院)由各州代表选举产生。联邦的责任是特定且有限的,其他的责任则归于联邦各州。最初,琐碎的市政工作被分配给来自各州的官员,而这些官员当时在州政府从事的工作现已归至联邦政府职责下。公务员数量以邮政、电报和海关等部门居多。某些州采纳了《诺斯科特-杜威廉报告》中创设基于绩效的专业化公务员制度的建议。新联邦政府也迅速采纳了这一观点,1902年议会通过了第一部《公共服务法》(PublicServiceAct)(该法案的颁布使澳大利亚对公共服务建立了比英国更强有力的控制,在英国,直到最近,才使政策及公约中包含公共服务安排,且还不是明确的法律条文)(Minns,2003)。
该法案建立了公共服务系统,几乎覆盖了每个人直至各部长(包括大多数机构负责人在内的四个部门的员工)。它要求任命和晋升应基于绩效,并设立了一名公共服务专员,拥有创建职位、设置机构、批准任命和晋升、确定工资和条件等实权。该系统基于一种预设:绩效会一直伴随职员的职业生涯并具有永久性,而且雇员仅限于男性员工。
在接下来的20年中,这种统一而集中的方法遭到削弱,因为一些职能和机构被分开管理,薪资和待遇受到外部监管程序的制约。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经过多次调查,行政系统的主要弱点和低效率得以明确,于是一项新公共服务法案于1922年诞生,三人公共服务委员会重申了中央控制权的重要性(Minns,2003)。1922年该法案生效,之后偶有修订,直到1999年才被废止。
最初公共服务部门不仅执行政策,还要向部长们提供政策咨询服务。直到20世纪70年代,各部长几乎完全依靠公共服务部门提供政策咨询。尽管政党论坛对如此依赖公共服务部门是否有益展开激烈辩论并在选举期间向公众提供广泛的政策平台,形成了政府的总体政策授权,但没有任何政治顾问与部长合作的情况,也很少有利益团体具有提供详细分析和咨询意见的能力;学者们有时参加政党论坛,提供影响公共服务顾问的研究成果,政府也偶尔向政府外专家咨询意见。但大多时候,公共服务部门才是那个一锤定音的力量,即使它并非是获得政策咨询的唯一渠道。
公共服务部门不仅在政策建议方面几乎处于垄断地位,它还具有涵盖多领域的政策建议能力。虽然它招聘一些专业雇员,如工程师、律师、医生等,但公共服务部门很少有社会科学领域学科背景的雇员,这种情况直到20世纪60年代才得以改善。直到20世纪30年代才开始有小型毕业生招聘,在此后的30年并未得到拓展。一个具有社会科学研究资历的小团队令人印象深刻,它在20世纪30年代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一段时期开始产生巨大影响。战后时期的“七矮人”(这一绰号基于他们的身材)仍受到广泛的尊重,他们对澳大利亚的重建和之后的经济成功做出了贡献,但该团队中某些人的名字仍然存在争议,因为他们始终处于幕后,而没有将个人形象呈现于公众面前(Furphy,2015)。
这点彰显了政治与行政分离的内涵之一,即公务员在很大程度上有匿名性,部长对政策负责且代表公众形象。至少在理论上来讲,部长的行政权要向议会负责。直到20世纪70年代,行政才主要基于公共部门内部的分层结构和完善的程序。事实上,部长很少干预行政,澳大利亚经常建立法定机构,以这种正式的途径将部长排除于行政参与之外(特别是在州政府一级)。
三、 20世纪70年代以来澳大利亚政治与行政关系的新发展
澳大利亚的发展对公共服务的影响及20世纪60年代后公共服务部门和政策制定的关系并非个例,其经济、社会和技术因素与诸多发达国家相似,如受教育水平更高的公众愿意并有能力参与政策辩论,大学生在60年代的大规模扩张起到了推动作用;公众对政府的期望不断攀升,特别是在要求政府保障提供高品质的健康、教育和福利服务方面。
在澳大利亚,大多数民众的诉求是希望联邦政府将权力从地方集中到中央;同时希望政府通过改善技术来创新行政方法,而不是执著于追求纯粹的结构和程序。此外,公众对公共服务部门存有广泛怀疑,认为它过于神秘而强大,且没有反映其服务人群的多样性。在澳大利亚,人们普遍认为,公共服务部门与过去长期存在的保守政府(1949年到1972年)靠得太近,并不是真正的非党派;日益普遍和强大的媒体更详细地披露了政策制定和计划管理中的政府内部流程,并将其影响告知公众。
20世纪70年代初期,特别是当一个新的工党政府于1972年上台时,出现了诸多变化。参议院成立了一系列委员会,旨在更为仔细地审查行政;随后,新政府介入了有史以来最坚固的政策平台,多次开展由外部专家指导的公众咨询,成立了由外部任命者领导的新机构,并雇用了自己的政治顾问,开始考虑包括《信息自由法》在内的行政法改革。
在前部门秘书(战后的“七矮人”之一)库姆斯·“金”博士(Dr.H.C.‘Nugget’ Coombs)的领导下,澳大利亚政府(Australian Government Administration)设立了一个皇家委员会,以此反思所有这些发展和活动对公共服务的影响。它于1974年由工党政府建立,于1976年向新保守党政府提交了总结报告(Coombs,1976)。根据其诸多建议,可以总结出三个关键主题:1.公共服务部门应为民选政府服务;2.政府行政应更高效;3.公共服务部门应更能代表澳大利亚社会,并允许更多的社会参与度。虽然它的建议没有直接转化为实际行动,但库姆斯报告的主题在接下来的20年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力。它们无疑重塑了政治与行政之间的关系。
在这种背景下,澳大利亚政治与行政的关系呈现出如下的新特点:
(一) 政治支持幕僚(Political Support Staff)
直到20世纪70年代部长尚未有政治支持幕僚,他们只能将公务员作为部门联络工作人员借调到他们的部门。工党政府开始采纳“部长顾问”这种形式,部长任命其拥护者以支持他们的工作。起初,即使在总理办公室里也没有很多雇员,他们在办公室里与公务员一起工作。事实上,尽管期望能在公共服务部门中做到不分党派,但有不少公务员愿意宣誓对工党忠诚。外部的部长顾问通常具备特定政策领域的专业知识,而不仅仅是纯粹的政客。1975年当选的保守党政府沿用了这种做法:少数党派部长顾问与公务员一起工作,有些部长顾问本身就是公务员。这是一个灰色地带,即没有关于各自职务角色或就业条件的明确规定。它要通过库姆斯皇家委员会的审查,直到1983年另一个工党政府上台后问题才得以解决。
1984年,议会议员法案使上述做法得以正式化,该法案不仅涉及部长级工作人员,还包括议员中的普通工作人员。它允许在绩效原则和公共服务法案之外进行党派任命。这些工作人员没有固定任期,当相关的议员在议会中失去了自己的席位,或者部长们失去部长职位时,他们会自动失去工作(但他们可以被重新任命到另一个职位)。部长除了有任命自己的部长顾问的能力,还可在不违反法案的前提下为自己所在的部门任命其他顾问。
部长顾问的数量稳步增长(Maley,1999:48-53),但多年来,他们仍是在重要决策前会首先被咨询的人,大多是借调的公务员(当他们离职时,允许回到公共服务部门或他们隶属的部门)。他们履行了许多政治职能:就部门咨询的政治后果提供咨询,就政治事务与其他部门联络,与政党和外部游说者联络,应付媒体等,但他们很少直接从党内职位直接指派或直接进入党内的职位。
随着这些带薪职位越来越吸引政治党派,上述情况逐渐转变。这些职位愈发成为政客职业道路的一部分。随着政府不断地轮流执政,在州和联邦层次的部长职位不停转移,然后寻求预选来竞选议员。顾问的政治作用得以强化,他们的专业知识往往变得不那么重要了(Maley,2015:46-55)。通过公职人员借调获得的职位更少了。
它们与公共服务的关系同样发生了变化,因为它们的互动能力不断提高,而不仅限于高层。澳大利亚公共服务委员会(Australian Public Service Commission)(以下简称APSC)主持的工作人员调查显示,在过去12个月中,超过20%的澳大利亚公共服务人员(Australian Public Service)(以下简称APS)与他们的部长或部长的工作人员有实质性的联系(APSC,2004a;APSC,2005)。如果把相关政策活动中的公务员人数纳入考虑范围,如提供社会保障金或在统计局、海关和国防部门工作的公务员等,这一结果将令人惊讶,同时公共服务的领导也会感到震惊。高级行政人员之间的互动是在意料之中的,但许多中层管理人员和某些较低级别的行政人员之间也有联系,该联系主要是关于技术问题的信息或客户在给部长的信函中提出的问题。在大多数情况下,公务员报告中提到,这些联系是合理的,这些公务员有信心保证自己与上司的交流不受自己所在党派的影响,保证公正。但有些公务员认为自己正在面临挑战,还有些公务员在保证公正方面缺乏信心(APSC,2004a)。
在过去十年中,对部长顾问的作用、行为和问责的关注越来越多(Tiernan,2007;MacDermott,2008;Scott,2012;Moran,2014;Podger,2014:47)。这表明关注侧重于公共服务领域更有力的政治控制,而不是改善部长和公务员之间的互动。他们并不反对政治顾问的存在,但建议进一步明确公务员和顾问各自的作用,以及部长、顾问和公务员的问责制。他们还建议任命更有经验的人担任部长顾问,包括像以往一样更频繁地使用借调公务员。
APSC对不同的角色做出初步解释,新的一套关于APS内部官方行为的准则扩展了法定的行为准则(APSC,2004b),随后是在与部长们的关系方面进行更加详细和具体的指导(APSC,2005)。工党政府在2007年提出了一项非法定的顾问行为准则,但2013年后保守党政府没有继续执行。最近,一位前办公室主任撰写了一篇关于顾问的作用和行为的文章,强调顾问应相互尊重且充分了解公共服务的作用和价值观,包括无党派性(Behm,2015)。
(二) 行政法规(Administrative law)
虽然对部长顾问的引入强化了要求公共服务部门对民选政府做出回应的民主原则,但行政法规增加了第二个原则的分量,特别强调了行政的公正性(或无党派性)。
《行政上诉裁判所法案》(TheAdministrativeAppealsTribunalAct)于1975年通过。它在司法机构内部设立了一个专门法庭(The Administrative Appeals Tribunal)(以下简称AAT)来审理针对行政决定的上诉。它建立在早期的行动之上,即在公共服务部门内部,有外部独立成员的申诉机制。其出发点是保护个人应当享有的权益,如社会保障金。但随着时间的推移,AAT之前的决定范围更广泛,同时行政实践受到先例的影响。高级公务员最初感到不安,但当他们认识到上诉机制在行政上的重大改进(包括更持久有效地满足公众需求)后,这种不安消失了。
《联邦行政督察专员法》(TheCommonwealthOmbudsmanAct)于1976年通过。它通过提供一个快速和低成本的行政裁决审查方案来协助AAT履行其职能。其调查结果不具有强制性,但不接受其调查结果的机构必须承认的事实是,调查报告将被公布,并记入监察员年度报告中提交给议会。此外,调查结果使公共服务部门更加开放并直接揽责,而不仅仅是让部长负责。
《行政裁决(司法审查)法》(TheAdministrativeDecisions(JudicialReview)Act)于1977年通过。它明列了可以由联邦法院审查的行政裁决范围及妥善的行政决策的要求,确定程序公正性所需的因素(或更准确地说,这就是可能产生黑幕的因素)。
《信息自由法》(TheFreedomofInformationAct)(以下简称FOI)于1982年通过。它不仅确保了人们可以获得关于他们的信息,而且提出了政府信息公开的原则,除非有明确的关于公共利益的理由解释为何信息不公开。虽然内阁文件在此基础上能够免责,但政策咨询并非总可以免责。这套法律大大加强了对行政管理的法律监督。重要的是,它还加强了公共服务中公正性和无党派性的要求。当然,这样做也突显了政治和行政之间职权交叉所面临的挑战。
这点在FOI中表现得最为明显。一些高级公务员声称FOI禁止“坦率和无畏”的建议。它也可能导致无法保存咨询和会议的书面记录(McPhee,2007)。它确实对FOI施行的管理施加了严格的政治监督,尽管决策的责任范围仅限于公共服务部门,但现在,也和部长办公室一样,需要展开定期检查。我个人的经验是,应使部长们明确,敏感文件必须公开发布是让公务员最感到有压力的责任之一。免责范围仍处于激烈的讨论之中(Shergold,2015;Gourlay,2016)。
(三) 新公共管理(New Public Management)
澳大利亚是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新公共管理(简称NPM)改革的领军者,NPM对政治与行政之间的关系以及公共部门管理公共服务的方式产生了持久的影响。在澳大利亚,NPM的主题是“结果管理”(management for results),这一主题得到以下支持:为计划设定更清晰的目标;让渡管理权威,使管理人员能够灵活地获得最佳结果;通过竞争提高效率(借助用户付款、外包、商业化和私有化等方式);解除对多种活动和行业的管制(更准确地说,重新定位监管以促进竞争);更广泛地使用私人业务管理流程,如战略规划。
与此同时,在澳大利亚,部长们制定了规划目标,更严格地审查绩效,进而加强了对行政部门的政治监督。这在部门秘书任期的变化中尤其明显。1984年,《公共服务法》修正案将秘书的头衔从“永久领导”(permanent heads)改为“部长级秘书”,并明确表示他们在“部长之下”工作。随后,他们被任命到任期为五年的特定部门;虽然这并不影响他们的总体任期,但这的确证明了他们将在工作期间定期转移,而且新的任命可能无法得到保证。
1993年,五年任期成为固定的五年合同,对失去任期的秘书进行财政赔偿。起初,其影响是有限的,因为任期在之前得不到保证。但在1996年,一个新的保守党政府利用新制度解雇了5位秘书。在政府职位更替中,有些人对新政府表示理解(秘书如果没有严格的党派观点,总理已经越来越倾向于选择那些就政策方向与其意见相一致的秘书来管理自己的部门)。秘书的流动率仍然很高,因为一些人在任期结束时没有被重新任命,许多人只签有三年合同,而不是五年合同。
1997年,政府还向部门秘书提供了绩效工资,金额是由总理在接受部门领导和公共服务专员的建议后所确定的。绩效工资已经存在于公共服务人员的其他级别之中,特别是在高级行政人员当中,只有当其从事的具体工作是在公共服务范围内的才能拿到薪资,并且要求严格基于绩效原则。
1999年通过了一项新的《公共服务法》,它反映了过去15年来新公共管理的发展,取代了以往立法对程序和投入的重视,并明确了强调绩效的“澳大利亚公共服务价值观”(APS Values)(CoA,1999)。新法案的通过使每个机构而不是公共服务委员会领导其雇员,实现了新公共管理的转移。
到21世纪初,秘书任期方面的进展由于其对“坦率和无畏”的建议和公共服务的独立性所声称的影响,受到了相当多的批评(特别是在1996年被终止之后)。针对这一问题,公众的建议往往是停止执行绩效工资,回到五年而不是三年合同制,以及加强公共服务专员在任命和免职方面的作用(Podger,2007:131-147)。这些建议在2007年被新的工党政府所采纳,随后在2013年获得两党的支持而纳入立法。尽管这一举动恢复了部门秘书这种制度安排的稳定性,但2013年新保守党政府解雇了三名现任秘书,这回应了1996年的免职,显然是因为他们认为当前的政策接近前政府的政策。
除去顾问的力量得到强化这一方面,对于自己职业未来的不确定性也在影响秘书和部长间的关系,这是政治和行政之间交锋的高潮。在对部长做出反应以及向工作人员、议会(包括将来的部长)和公众展示非党派和公正的价值观之间,什么是恰当的平衡呢?有些人认为这个问题被夸大了(Shergold,2007:367-370),但其他人担心的则是“混杂的党派之争”(Aucoin,2012:177-199),因为秘书们过分努力地去取悦任何一个当权者,对政府的政治议程过分利用,而对公共利益关注不足,他们更多地关注短期的策略事务,较少关注长期战略问题,而且显得过于规避风险。
(四) 新公共治理(New Public Governance)
“治理”一词在20世纪90年代末在澳大利亚盛行(例如,Edwards,et al,2002)。新公共管理仍是公共部门管理的哲学,其重点在于竞争和绩效,但有些方面受到更仔细的审视。新公共管理更加重视“网络”,而不仅仅是外包和客户服务。公共服务应扩大其参与范围,并使协商过程更加系统化。外包意味着“合作”,共担风险,合作伙伴和客户的贡献变得更有价值:“共同生产”和“共同设计”成为新公共治理词典的一部分(Alford,2009)。通过大幅增加对“整体政府”(whole-of-government)处理复杂问题和危机的方法的兴趣,新公共管理对规划的重视得以平衡(MAC,2004)。
与这些发展相关的是在一定程度上的再集中化,加强总理及其部门以及其他中央部长和机构(金融、财政部和APSC)的作用。它们还与通讯系统更为强硬的政治控制有关,这是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已然开始的一种趋势。因此,加强协商的努力往往是由政治顾问而不是公务员所领导,而且部长传媒顾问的作用显著增强。虽然“共同生产”和“共同设计”需要公共服务部门与合同提供者和客户之间更多的参与,但考虑到所涉及的政策(和政治)影响,对政治实施情况的政治监督仍很重要。确实,方案执行和提供服务的行政已隶属于政策领域,其中包括建立一个(部长级)人力服务部门(Department of Human Services),该部门之前由独立的法定机构加以管理,包括联邦服务部(Centrelink)和健康保险委员会(the Health Insurance Commission)。
(五) 后新公共治理(Post New Public Governance)
我们尚不明确新趋势的走向,新公共管理和新公共治理仍然得到相当多的政治和官僚支持,但是他们对二者在提供公共服务方面的能力和中立性仍有一些顾虑。
通过分析2008年关于澳大利亚政府行政报告(Moran,2008)和一系列“能力审查”(APSC,2012;APSC,2012-14)发现,尽管总体而言澳大利亚的公共服务部门是世界上最好的公共服务部门之一,但一些政府机构的能力存在严重缺陷。他们建议减少战略政策咨询能力,不要过分强调战略咨询,并指出在人力资源管理方面投资不足的问题。作为回应,新的公共服务和财务管理立法(CoA,2013;CoA,2014)加强了澳大利亚公共服务委员会的作用,强调秘书对其部门“管理”的责任,强制要求企业通过系统解决其能力问题来补充项目预算和绩效报告(Podger,2015)。
虽然新立法增强了公共服务部门的能力,但政府尚未增加对公共服务的投资预算:恰恰相反,APS自2007年以来资源持续削减,也没有证据表明部长和顾问们为了实现其政治目标而对策略咨询的需求有所减少,或为了战略政策而咨询的需求有所增加。
如上所述,尽管加强了澳大利亚公共服务委员会在秘书任命和废除绩效工资方面的作用,但是几乎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公共服务的独立性稳步下降。现任总理最近的一些任命,包括他个人办公室内的任命以及其他部长的发言都可能暗示着,对独立性更加重视,对公共服务表示担忧,对可能造成持续混杂党派的政治控制表示重视。
四、 政治与行政二分的实质
在处理政治与行政之间的关系方面总是存在挑战,要平衡以下两个原则:一方面,要求行政对民选产生的政治领导做出反应的民主原则;另一方面是高效和公平的政府行政所遵循的行政原则。
部长们往往想从公共服务中获得如下支持,如:准确的信息;专业的分析和建议;技术能力和零失误;忠诚和保密;政治意识和期望。他们不想得到的是:无正当理由的建议,或建议与政府的意识形态不一致;令人犹豫不决或感到困惑的信息;“白蚁”(澳大利亚的政治术语,指“内耗、内斗或互相拆台”)的评价,信息泄露或公开批评;行政丑闻,公共证据的错误,管理不善。
同时,公务员总想从部长那里获得的支持包括:在明确阐述其目标方面的决断;代表部门及其选区,赢得内阁,处理与议会和媒体的关系的能力和意愿;相当程度的一致性和可预测性;阅读简报的准备,参与问题讨论,了解过程信息,处理进度问题;部门质疑,勇于挑战的心态;了解当代政治,更好地调整部门及其绩效。他们最不想看到这样的部长:缺乏决断或认为自己无所不知;软弱或举棋不定;无法快速浏览简报或提出难题;过于阴暗,试图跨越法律、议会或道德规则,使公务员盲目或使行政决策“政治化”;过频地指责部门人员。
显然,从不存在一个完美的世界,自联邦政府成立以来,部长和公共服务部门都没有达到那些理想的状态。无论如何,诸多期望和不期望的行为可随意解释,且界线总是有些模糊。所以,在某种程度上,部长与公务员之间的关系总是充满挑战。
有大量证据表明政治与行政之间的关系“加深”了,政治支持幕僚的数量以及他们在公共服务中的互动都有所增加。包括提供专业化支持的利益集团和专家在内的第三方作用的增强也有助于政治和行政之间的互动。
政治也变得越来越专业化。很少有人凭借一些外部职业身份,如农民、商人、手艺人、律师或学者而直接进入政治圈:他们愈发通过政治职业路径进入政治领域,如获得部长顾问职位。他们在媒体管理和沟通方面训练有素,他们认为作为顾问或部长,公共服务部门应在其媒体管理框架内进行运作。
这种专业化在一定程度上响应了技术的变化和当前通信运行的方式,以及包括社交媒体在内媒体的力量和普遍性。有人认为问题必须立即得到回应,因此,竞选活动受到持续关注,政治已成为“超对抗”(hyper-adversarial)的结果(Wanna & Luetjens,2016)。反过来讲,这似乎正在改变部长及其顾问希望从公共服务部门中所得到的东西。
在咨询和行政方面失去垄断地位也可能改变公共服务部门的作用和文化氛围。新公共管理声称要“掌舵”而非“划桨”(Osborne & Gaebler,1992),这可能掩饰了其能力的丧失,导致它在合同双方的利益交换中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更像是“代理人”而不是“当事人”。与其他咨询来源的竞争可能不是观点的竞争,而是看谁更善于隐瞒事实,取悦部长(MacDermott,2008)。
这种鼓励会不断加剧,因为高级公务员的任期缩短,使这种服务更具风险规避性,他们不愿意提供“坦率和无畏”的建议。
政府公信力和公共服务部门的政客的信任缺失,可能导致更加强调个人的忠诚而不是正式的制度义务,以及“混杂党派”对政府当时的政策过度认同,愿意从事党派工作,并建立个人性质的友谊,而不是专业的合作伙伴关系。
可以说,高级公务员之间的匿名性丧失导致了信任的崩塌。即使在当选政府的政策语言中,公务员的公开意见被视为坚定的个人忠诚,意味着他们不能对不同的政府表示忠诚。公职人员对绩效的公共责任的增加可能允许了政客的责任转移到官僚(和相关的责任),使部长渐渐偏离公共服务。总而言之,很难接受这样的事实,即使潜在的挑战总是存在,但事情没有显著变化。
五、 政治与行政关系的未来
改善澳大利亚政治与行政之间的关系可能需要双方共同的努力,以及议会和公众的支持。
如果要重新获得部长(及未来部长)的充分信任,公共服务部门需要解决其能力问题。最近的能力审查指出了正确的方向:需要重塑研究和战略政策咨询能力,并与外部专家和有经验的利益攸关方建立更强有力的联系;且需要进一步投资于人员和制度建设。提升能力应剥夺政客没有利用公共服务部门的任何借口。有限的资源可能限制公共服务部门在没有明确的政府(部长级)支持的情况下可做的工作,但如果公共服务部门的领导重新明确其优先资源,情况则可能有一些改进。
部长们需要鼓励他们的政治顾问去支持而不是抑制政治与行政之间的合作伙伴关系。他们应澄清顾问和公务员的各自作用,根据自己的行为核准这两个组织各自的行为守则。两个组织都是为部长服务的,也不应该篡夺部长的职权。顾问应该提供专家和相关(及时)的公共服务咨询;在这样做时,他们应该提供有经验的政治观点,对建议进行评估,但不要试图改变它。他们的重点应该是合作,而不是控制,应该是提供便利,而不是把关(即使有时部长要求他们做出一定程度的控制和把关)。办公室主任可以为这种关系定下基调,包括建立与部门秘书的密切关系,巩固部长和秘书之间的关系。办公室拥有一些经验丰富的公务员,无论是作为借调顾问还是部门联络官,都有所裨益,对改进新顾问的入职培训保留余地。
尽管最近APS专员在任命咨询方面的作用有所加强,但很明显,一些高级政客继续在关于任命和解职的决定中强加政治考虑,而不是基于真正的绩效因素。澳大利亚可能参考了新西兰的做法,其中专员实际上是雇佣方或任命方,负责任命和评价绩效。这确保了决策基于绩效,同时不否认总理和部长影响决策的机会。它只是调换提供建议和实际任命的职责分工。很明显,如果证明部长和秘书不能一起工作,专员的评估将是错误的,那么就需要重新任命。这对于澳大利亚政客来说实在是太难了。较为温和的做法只是在新政府上台时需要一段时间的调整,而现任秘书在证明(或以其他方式)他们忠诚而专业地服务于新政府部长时,其职位才会被保留下来。
或者,澳大利亚可以更公开地偶尔接受的政治任命,特别是总理自己所在部门的秘书,并采用互补程序,在恰当的知识和专长方面检查任命的适当性。例如,议会可能会发挥类似于美国国会在支持行政政治任命方面的作用。
另一种情况是改善议会对公共服务和主要政党的理解。在最一般的层面上,作为真正政策辩论的审议论坛,议会可处理其作用弱化的问题。为了增强这一作用,它可能更多地涉及公共服务的专门知识。这将使更多的政治人物了解公共服务中的专门知识,并为公共服务提供展示其能力的机会,呈现问题分析,而不是提出具体政策建议。参议院还可以考虑在审查公共服务及其能力方面发挥更加积极的和无党派的作用,从而尽可能地将公共服务的政治态度从低效率和懒惰的民粹主义情绪转向对绩效和能力进行更多考虑的评估,要达到这一目的需要采取行动(包括可能的新投资)。
同样,在公共服务方面,政党可能有空间对候选人和新议员展开教育,并告知他们如何最好地利用代表政党和国家的资产。
现如今,公共服务部门领导者面临的一个艰巨的挑战是建立一个恰当的公共形象,以此来反映他们的公共责任和他们对部长的责任。一些人拥有非常明确的公共责任,他们需要引人注目的形象,例如储备银行行长(Reserve Bank Governor)、首席医疗官(Chief Medical Officer)、生产委员会(Productivity Commission)和澳大利亚竞争与消费者委员会(Australian Competition and Consumers Commission)。很少有部门秘书对公众媒体有这样明确的要求,虽然可以说,财政部长有望利用市场不时地借助其专业权威来解释部长的政策声明的背景(尤其是财政部长和总理)。
但其他秘书不可避免地拥有一种公众形象。他们出现在议会委员会之前,向部长提交年度报告,然后再提交议会。他们还经常根据法律指挥代表团,并且承担着相应的责任,还必须向媒体解释他们的决策。具有广泛和复杂责任的政策也需要利益相关者和公众的公开参与,部长们无法自己进行管理:秘书和其他高级公务员需要公开宣讲来解释政策和行政。他们还可能认为秘书有责任向媒体介绍政府政策的背景,从专家的视角对其进行解释。
从个人经验来讲,我知道部长和他们的顾问往往会对上述建议感到不太满意,并要求所有媒体通过部长办公室进行联系。他们的担忧是可以理解的,因为现如今以政治管理媒体曝光行为具有重要意义,以及偶尔不忠诚的公务员匿名发布(“泄漏”)机密信息。但是,公共部门的高级公务人员背负着强烈的公共利益,他们具有某种公众形象,有些还留下了跟政策问题背景记者有关联的记录。挑战在于,要对部长们在操作这种公众形象和媒体联系方面保持信心。当媒体的反应引起重大的政治疼痛时,这可能是特别令人担忧的。
虽然一些高级公务员担心FOI正在对他们与部长的关系造成严重损害,还减少了直白的谏言和对建议决定的存档记录,但几乎没有证据表明FOI要求向政府部长提供政府咨询,以便在公共利益保密性意义重大时得到法院的认可。更多的情形是,政治和官僚文化仍然过度关注在此情况下法院支持请求的可能性,并常常过度频繁地据此制定建议(Podger,2015)。
如果公共部门治理需要用政策回应舆论以及保证行政高效、有效和公正,那么政治与行政的分离与伍德罗·威尔逊在130年前所阐述的情形是极为相似的。这可能与第一条原则是否可以通过正式的民主化途径或其他进程来实现相契合。但是,管理这种分离的状况是一项长期的挑战。它绝不是一个有着明确答案的简单问题。澳大利亚的经验表明政治与行政分离的挑战更加艰巨,因为随着政治与行政之间的互动不断深入,政治走向专业化,媒体也变得更加普及和强大。现如今,二者之间的关系并不和谐。修复这种关系需要双方,即公共服务部门和部长的共同努力,同时还需要立法机构和媒体的帮助。
[1] John Alford(2009).EngagingPublicSectorClients:FromService-DeliverytoCo-Production.London:Palgrave MacMillan.
[2] Peter Aucoin(2012).New Political Governance in Westminster Systems:Impartial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Management Performance at Risk.Governance,25(2).
[3] Australian Public Service Commission(APSC)(2004a).StateoftheServiceReport2004.Canberra:APSC.
[4] APSC(2004b).APSValuesandCodeofConduct:AGuidetoOfficialConductforAPSEmployeesandAgencyHeads.Canberra:APSC.
[5] APSC(2005).StateoftheServiceReport2005.Canberra:APSC.
[6] APSC(2012).StateoftheServiceReport2012.Canberra:APSC.
[7] APSC(2012-14).VariousAgencyCapabilityReviews.available at http://www.apsc.gov.au/(accessed in 2014).
[8] Commonwealth of Australia(CoA)(1999).PublicServiceAct1999.Canberra:Parliament House.
[9] Commonwealth of Australia(2013).PublicService(Amendment)Act2013.Canberra:Parliament House.
[10] Commonwealth of Australia(2014).PublicGovernance,PerformanceandAccountabilityAct2014.Canberra:Parliament House.
[11] H.C.Coombs(1976).FinalReportoftheRoyalCommissionintoAustralianGovernmentAdministration,Volume 1.Canberra:AGPS.
[12] Meredith Edwards,et al(2012).PublicSectorGovernanceinAustralia.Canberra:ANU Press.
[13] Samuel Furphy(2015).TheSevenDwarvesandtheAgeoftheMandarins:AustralianGovernmentAdministrationinthePost-WarReconstructionEra. Canberra:ANU Press.
[14] Paddy Gourlay(2016).Parting Truths.CanberraTimesPublicSectorInformant,July.
[15] Kathy MacDermott(2008).WhateverHappenedtoFrankandFearless?TheImpactofNewPublicManagementontheAustralianPublicService.Canberra:ANU Press.
[16] Maria Maley(1999).Too Many or Too Few? The Increase in Federal Ministerial Advisers 1972-1999.AustralianJournalofPublicAdministration,59(4).
[17] Maria Maley(2015).The Policy Work of Australian Political Staff.InternationalJournalofPublicAdministration,38(1).
[18] Management Advisory Committee(MAC)(2004).ConnectedGovernment.Canberra:APSC.
[19] Ian McPhee(2007).An ANAO Perspective on Records in Government.Speech given on 27 June,Australian National Audit Office(available at http://www.anao.gov.au/).
[20] Bob Minns(2003).AHistoryinThreeActs:EvolutionofthePublicServiceAct1999.APSC Occasional Paper 3,Australian Public Service Commission,Canberra.
[21] Terry Moran(2008).AheadoftheGame.Final Report of the Review of Australian Government Administration,Department of Prime Minister and Cabinet,Canberra.
[22] Terry Moran(2014).SpeechtotheCrawfordSchoolofPublicPolicy’s2014LeadershipForum.Canberra:ANU Press.
[23] S.H.Northcote & C.E.Trevelyan(1854).ReportontheOrganisationofthePermanentCivilService.London:House of Commons.
[24] D.Osborne & T.Gaebler(1992).ReinventingGovernment:HowtheEntrepreneurialSpiritisTransformingthePublicSector.Massachusetts:Addison Wesley Reading.
[25] Andrew Podger(2007).What Really Happens:Departmental Secretary Appointments,Contracts and Performance Pay in the Australian Public Service.AustralianJournalofPublicAdministration,66(2).
[26] Andrew Podger(2014).Real-life Politics Is Not An Episode of Yes Minister.AustralianFinancialReview,10 September.
[27] Andrew Podger(2015).Making “Accountability for Results” Really Work?. 2015 Allan Barton Annual Lecture,CPA Australia,Canberra.
[28] Patricia Scott(2012).Our Custodial Role for the Quality of Advisory Relations at the Centre of Government.in Wanna,Vincent & Podger(eds.).WiththeBenefitofHindsight:ValedictoryReflectionsfromDepartmentalSecretaries,2004-11.Canberra:ANU Press.
[29] Pater Shergold(2007).What Really Happens in the Australian Public Service:An Alternative View.AustralianJournalofPublicAdministration,66(3).
[30] Peter Shergold(2015).LearningfromFailure:WhyLargeGovernmentPolicyInitiativesHaveGoneSoBadlyWronginthePastandHowtheChancesofSuccessintheFutureCanBeImproved.Canberra:APSC.
[31] A.Tiernan(2007).PowerWithoutResponsibility?MinisterialStaffersinAustralianGovernmentsfromWhitlamtoHoward.Sydney:UNSW Press.
[32] John Wanna & Jo Luetjens(2016).Managing and Thriving in Turbulent Times-Pro-Activism in the Face of Systemic Trends toward Hyper-Government:Key Thematic Messages from the 2016 ANZSOG Conference.Australia New Zealand School of Government,Melbourne.
[33] Woodrow Wilson(1887).The Study of Administration.PoliticalScienceQuarterly,2(2).
■作者地址:Andrew Podger,College of Arts and Social Sciences,The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13 Ellery Crescent,Canberra ACT 2601。Email:andrew.podger@anu.edu.au。
■译者地址:韩瑞波,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Email:hanruibo19920502@163.com。
■责任编辑:叶娟丽
Revisit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olitics and Administration
AndrewPodger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Western democracies have traditionally distinguished between politics and administration.Australia followed the British practice set following the Northcote-Trevelyan Report in 1854 which recommended a merit-based civil service protected from nepotism and partisanship.The US tradition has more shades of grey, but Woodrow Wilson’s advocacy of professional administration distinct from the political process remains relevant.In every case, there are challenges at the point of intersection as administration must be responsive to the democratic process but policy set by politicians must equally be implemented fairly, properly, efficiently and effectively.China does not separate politics from administration, all parts of government being under the control of the Party; yet there is strong support for greater professionalism in government administration drawing on China’s long history of a meritorious bureaucracy, loyally serving the public interest as determined by the Party, and for more open processes of policy-making.Developments in Australia over the last 40 years have had a major impact on how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politics and administration operates.Many of the developments are common to those seen elsewhere:increased community expectations, greater transparency in government, increased pervasiveness of the media, professionalization of politics and wider participation in government policy processes as well as program implementation.Specific developments include the strengthening of administrative law, new public management initiatives, the establishment and expansion of ministerial advisers, loss of tenure for top civil servants and more political involvement in appointments and terminations, and ‘network government’ widening participation in government.A number of these have contributed to a ‘thickening’ of the interface between politics and administration.The paper describes these developments and their impact. Amongst the perceived challenges associated with these developments are a loss of strategic capability in the civil service, reduced confidence in the civil service by politicians, more timid advising by civil servants, weaker deliberative processes to develop longer-term policy and a tendency towards tactical rather than strategic policy, and a more risk-averse policy environment.Some action has been taken but concerns remain.Possible further agendas are identified in the paper to ensure that administration does reflect and support the policies of the elected government, that those policies are most likely to be in the longer-term public interest including by being informed by quality, useful and timely advice from the civil service and external experts, and that management of public programs is efficient, effective, fair and proper.While China’s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are very different, the underlying issues are similar:ensuring government administration is both fair(and efficient, effective and proper) and responsive to the Central, Provincial and Local Governments’ interpretation of the public interes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olitics and administration; Woodrow Wilson’s dichotomy; Australia; ministerial advisers; public service
10.14086/j.cnki.wujss.2017.03.008
2016-10-26
D035;D733(611)
A
1672-7320(2017)03-009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