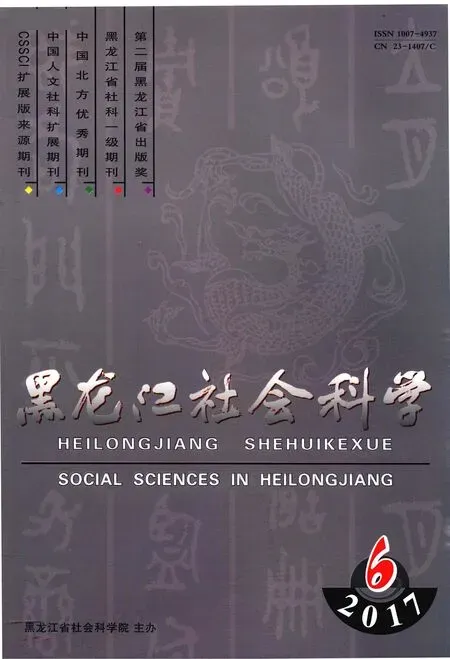卢卡奇物化意识思想研究
白 雪 晖
(内蒙古民族大学 政法与历史学院,内蒙古 通辽 028043)
·哲学问题研究·
卢卡奇物化意识思想研究
白 雪 晖
(内蒙古民族大学 政法与历史学院,内蒙古 通辽 028043)
卢卡奇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人、缔造者。他于1923年所提出的物化理论及物化意识思想与马克思于1844年所提出的异化概念具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但长期以来,由于种种原因,卢卡奇的这一观点却饱受学界争议。在当今历史时期,重新梳理卢卡奇的这一理论遗产,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
卢卡奇;物化;物化意识;理性化;现代性
格奥尔格·卢卡奇(1885—1971)在德国学习期间,受胡塞尔、李凯尔特、文德尔班、狄尔泰等著名哲学家的影响,并直接受教于齐美尔(1909—1910)、马克斯·韦伯(1912—1915),还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另一个重要代表人物布洛赫成了同学和朋友。这些人物的思想都成了卢卡奇新观点的强有力的、不可或缺的理论资源。另外,卢卡奇在其一生的学术生涯中还培养了一批理论家,如赫勒夫妇、(大)马尔库什、(小)马尔库什、瓦伊达等,后来,这些人组建形成了著名的匈牙利布达佩斯学派。同时,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也深受卢卡奇的影响,L.戈德曼在其著作《卢卡奇与海德格尔》一书中,就着重探讨了卢卡奇与海德格尔之间的关联性问题。*关于卢卡奇对海德格尔的影响,早已引起了学界的关注。L.戈德曼就强调卢卡奇与海德格尔思想之间的关联性。在他死后出版的《卢卡奇与海德格尔》(1973)一书中,讨论的就是这一问题。后来一些学者从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来讨论他与海德格尔的关系。苏联学者别诺索夫认为:“早在二十年代就在德国得到广泛的流传,在有批判意识的知识分子头脑中造成了混乱。毋庸置疑,海德格尔的许多原理,萨特的《存在与虚无》也发端于卢卡奇的这部著作(《历史和阶级意识》)。”[1]美国学者巴尔在《乔治·卢卡奇》一书中也认为,卢卡奇的这本书影响到海德格尔,他转用瓦特尼克的看法指出,海德格尔的“此在”就是从卢卡奇的思路中产生的。纵观卢卡奇的一生,我们发现他有一个不同于其他人的地方,那就是不断地受到批评和指责,同时他自己也不断地在自我批评;到头来,我们有时竟很难分清哪一个是真正的自我批评,哪一个是违心的自我批评。
卢卡奇的思想非常丰富,在这里,我们主要介绍他的总体性理论及物化意识思想。这所涉及的著作主要有《心灵与形式》《小说理论》《历史与阶级意识》。
一、物化思想的提出
《心灵与形式》和《小说理论》这两部著作是卢卡奇早期思想的代表作。《西方》杂志创刊于1908年,这个刊物是不属于任何政治党派的知识界杂志,但它反对匈牙利的民族沙文主义,赞同放眼西方。卢卡奇《心灵与形式》中的10篇文章就是他在这个杂志上发表过的文章,这部论文集于1911年出版。在这部著作中,卢卡奇提出了“一种现代社会人的存在困境的悲观世界观:即在现代社会,人处于分裂的存在状态,人被上帝抛弃,也被人抛弃。”可以说,这部著作体现了新康德主义形式先验理论对卢卡奇的影响。另外,由于卢卡奇在这部著作中深入刻画了现时代人的存在的悲剧性,因而被L.戈德曼推崇为是现代存在主义的先声。1916年出版的《小说理论》是卢卡奇在马克斯·韦伯的类型学方法的引导下完成的一部文论著作,体现了他从康德走向黑格尔的理论转换。这部著作对小说的本质和小说形式的类型进行了令人耳目一新的开创性研究,并因此被同时代人称之为“精神科学运动最重要的出版物”。
虽然晚年卢卡奇不断地号召人们忘却和批判自己的这两部早期作品,但著作本身的影响力却超出了他的主观意愿,并在20世纪20年代以后的德国思想史中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如对布洛赫、本雅明和阿多诺等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思想发展的影响。另外,值得提出的问题是,卢卡奇在这两部著作提到的对世界的批判分析和对超越物化的可能性道路的探索——这两个问题后来直接构成了他的《历史与阶级意识》中的“物化”与“总体性”主题,即这两个问题后来成了卢卡奇哲学研究的两个重要问题。
二、物化思想的展开
《历史与阶级意识》于1923年在柏林马立克出版社作为该社的“革命小丛书”第九种出版,著作包括卢卡奇1919—1922年期间在党的工作岗位上对革命运动的理论问题和组织问题进行思考而写下的8篇文章。在这里,我们着重介绍卢卡奇在这部著作中所强调的两个问题:一是总体性理论;另一个是物化及物化意识思想。
1.总体性理论
总体性是卢卡奇辩证法思想的精髓。在卢卡奇看来,马克思主义只是一种方法,而不是公式和结论;这种方法把整个人类历史看作有机的整体,实践性是其突出的特点,并强调主体性精神是其总体性的实质。我们认为,卢卡奇的这种认识和理解具有合理性,同时也正是因为这一点,卢卡奇的思想才被以后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发扬光大。“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卢卡奇是一位重要的理论奠基者,青年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构成了后来的理论尺度。”[2]也就是说,卢卡奇的总体性思想尚未背离马克思主义精神,因为在那个把马克思主义的个别原理及观点当作绝对真理的年代,卢卡奇的这一种认识和理解无疑有利于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当然,就卢卡奇的这种认识和理解,即把马克思主义仅仅当作一种方法,确实可能具有简单化的倾向,因为把马克思主义的方法与其基本原理割裂开来,就容易对马克思主义形成片面性和简单化的理解。
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卢卡奇把总体性方法当作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核心观点与列宁的认识论,即认为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法的实质思想并不矛盾。因为卢卡奇所谈的总体性方法,已内在地包含了矛盾和差异,也就是说,矛盾和差异是卢卡奇总体性方法中的题中应有之义。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他强调说明总体性——“不是把它的各个环节归结为无差别的同一性、统一性,而是把这些环节看作包含差别和矛盾的辩证同一性。对立统一强调的是微观的分析,总体性则强调宏观的综合,因此,对立统一的矛盾分析蕴含于总体性方法之中,并以总体的综合为归宿;而总体性方法又包含矛盾分析方法于自身,以矛盾分析方法为出发点。这两种思维方法相互渗透,相互补充,从而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认识过程和认识方法。”鉴于此,我们才认为,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发展史上,卢卡奇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而不是生搬照抄马克思主义。也因此,我们认同,对于马克思主义,卢卡奇开辟了一个新的理解视角或解释原则,应该说,这对于我们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具有重要的启迪作用。
2.物化理论及物化意识
卢卡奇在1919年《什么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一文中提出,并在1920年《阶级意识》及1922年的《物化和无产阶级意识》论文中详尽地论述了物化问题。卢卡奇提出的物化概念与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出的异化概念异曲同工,主要揭示和阐释了物化现象的普遍存在,并以此为依据,进一步提出了克服和消除物化的可能性路径。
马克思认为,异化的本质是以物的关系掩盖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卢卡奇对此认可,但由于他在完成《历史与阶级意识》这本著作时,并没有看到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1932年才公开发表),所以,他把这一社会现象抽象为物化而不是异化,但两者却具有惊人的相似性。卢卡奇认为,物化是现代人所面临的特有的现象,对此他曾下了一个明确的定义:“在这里最重要的是因为这种情况,人自身的活动,他自己的劳动变成了客观的、不以自己的意志为转移的某种东西,变成了依靠背离人的自律力而控制了人的某种东西。”[3]96即在发达的商品经济条件下,人的活动的结果或人的创造物变成某种自律的、并反过来统治人和支配人的力量。
物化和异化这两个概念确实具有惊人的相似性,但在存在的范围问题上,卢卡奇与马克思却有质的区别。马克思认为异化只存在于特殊领域和环节,而卢卡奇则认为物化不仅是普遍现象,而且还具有必然性,这个必然性是由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经济形式所决定的,即物化是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阶段所特有的一个问题,“一方面,资产阶级的财富越来越多;另一方面,劳动力成为商品,人的劳动同人本身相分离,成了不依赖于主体的社会劳动,即劳动的社会性质反映成劳动产品的物的性质。于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采取了物与物之间关系的虚幻的形式。”在现代社会,卢卡奇认为这种特有的物化现象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种形式:
第一,人的数字化。这源于工业社会理性化的进程,即人在这个社会化(或机器化)大生产的体系中,变成了抽象的数字,失去了主体性和能动性,其活动变成一个专门的固定动作的机械重复。他说:“如果我们遵循着劳动在它的发展过程中所采取的从手工业经过合作生产和工厂手工业到机器生产的道路加以考察,我们就会发现存在着一种不断地向着高度理性发展,逐步地在清除工人在特性、人性和个人性格上的倾向。一方面,劳动的过程逐渐地分化为抽象的、合理的、专门的操作过程,以致工人失去了同最终产品的接触,工人的工作被归为一个专门的固定动作的机械重复;另一方面,由于生产过程的机械化和合理化被加强,工人完成一件工作的必要时间期限(这是合理化计算的基础)发生了变化,开始从仅仅是一种经验水平上的数字变为一种客观的、能计算的工作定额,使它作为一种固定的和既定的现实与工人所相对。随着对工人工作过程的近代‘心理学’分析(在泰勒制中),这种合理的机械化被一直扩展到工人的‘心灵’中。”[3]97-98
第二,主体的客体化。即人由生产过程和社会历史运动的自由自觉的主体沦为被动的、消极的客体或追随者。他说:“由于工作过程的合理化原因,当主体与根据预测的正在发挥作用的那些抽象的特殊规律相比较时,工人的人的属性和特征日益表现为只是错误的源泉。人既不是在客观上也不是在同他的工作关系上表现为劳动过程的真正主人。相反,他是被结合到机械体系中的一个机械部分。他发现这个机械系统已经存在并且是自给自足的,它的作用不以他的意志为转移,无论他是否乐意,他都必须服从于它的规律。由于劳动被逐渐地理性化和机械化,随着人在这个活动中活动力的减少,他丧失的热情也越来越多。他的意志的沦丧日益加重。人们对于它自己所机械地面对着的客体采取了被动的态度,这种客体就是被固定的规律和被确定的独立于人的意识,不受人的干涉所影响的客观过程即完全被封闭的系统。”[3]99
第三,人的原子化。即指人与人的隔膜、疏离、冷漠,人与人之间丧失了统一性和有机的联系。也就是说,在现代社会,社会完全是按照物的关系和物的原则组织起来的,人的关系被物的关系所吞没和掩盖。他在著作中指出:“一方面,他们的劳动力对象化为某种跟他总的人格相反的东西,随着劳动力作为商品出卖而已完成的过程,这种东西现在已经变成了他们日常生活中永恒不变的现实。当工人自己的存在被归为一个孤立的部分并坠入了异化的系统中时,在这里人格只能袖手旁观。另一方面,生产过程被机械地分解为它的组成部分,也破坏了在生产还是‘有机’的整体时个人和社会之间的紧密联系。在这一方面,机械化也把他们分裂成孤立的、抽象的原子,他们的工作不再把他们直接地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由于禁锢他们的机械抽象规律的作用,在日益扩大的范围内,他们成了中介。”[3]100
卢卡奇关于物化的具体表现形式的分析,比马克思要走得更远或更深刻一些。其特色之处就在于他把物化同现代社会的理性化进程结合起来,从理性特别是技术理性视角观察人的负面效应来揭示现代社会的物化现象。在这里,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和卢卡奇在物化产生环节上的认识和理解是不一样的,马克思认为异化是在商品交换中产生和表现出来的,而卢卡奇则认为异化是在生产过程中产生的。这是卢卡奇与马克思在这一问题上的一个重要区别之处。另外,我们还要警醒,马克思从阶级的视角划分了物化的存在方式和非物化的存在方式,即马克思主要阐释了无产阶级的劳动异化;卢卡奇反对这样的视角,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着普遍的物化现象:不仅无产阶级存在着物化现象,而且资产阶级也存在着物化现象。
三、物化思想的危害
“物化普遍化的一个最直接的后果便是物化的内化,即物化不只是作为一种统治人、支配人的外在的力量和结构而存在,而且是内化到人的生存结构和活动方式之中,变成一种物化意识。所谓物化意识是指人自觉地或非批判地对外在的物化现象和物化结构认同的意识形态。”[4]卢卡奇认为,商品关系转变成客体性的东西必然在人们的整个意识上打上自己的印记,物化意识“正像资本主义制度不断地在更高的阶段上从经济方面生产和再生产自身一样,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物化结构越来越深入地、注定地、决定性地沉浸入人的意识里。”[3]104人自觉地或非批判地认同外在的物化现象和物化结构,并将这种物化结构当作外在的规律和人的本来命运加以遵循、服从,从而丧失了批判和超越的能力。因此,正如物化的普遍化使之成为一切人的共同命运一样,物化意识也同样支配着人的精神活动和心理活动。这意味着,物化意识的真实存在,使人失去了超越性、批判性的维度,使人的存在和社会历史进程变得支离破碎,也就是说,使人的存在和社会历史的进程丧失了内在的、有机的、具体的总体性。如何克服物化现象或扬弃物化意识呢?卢卡奇认为,必须要通过恢复总体性的原则来实现。当梳理到此,我们会不由自主地联想到马尔库塞的《单向度的人》著作。在这本著作中,马尔库塞以其特有的敏锐的理论洞察力指出了人——失去其批判性、超越性的危害性,即人会成为单向度的人、社会亦变成单向度的社会。这也使我们想起了英国学者吉登斯的“现代性与自我认同”的可怕性。因此,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认为,卢卡奇的物化理论及物化意识思想具有合理性,尤其是他对工业文明和商品经济发展所造成的人从属于物、受制于物的现象的分析,对于我们当前的社会实践仍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
[1] 关于卢卡奇哲学、美学思想论文选译[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19.
[2] 马丁·杰.法兰克福学派史[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201.
[3] 卢卡奇.历史和阶级意识[M].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
[4] 衣俊卿,等.20世纪的新马克思主义[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48.
B1
A
1007-4937(2017)06-0088-04
2017-07-10
白雪晖(1968—),男(蒙古族),内蒙古通辽人,教授,哲学博士,从事现代西方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责任编辑:张圆圆]
——回望孙伯鍨教授的《卢卡奇与马克思》
——读《卢卡奇再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