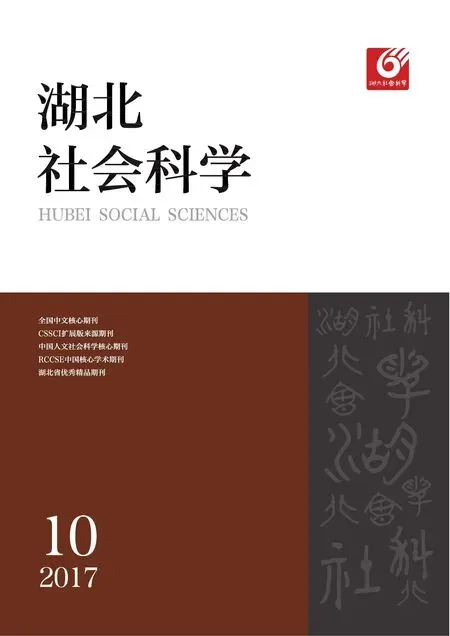腐败规范化的历史困局
——传统中国卖官现象新论
谢红星
(江西财经大学 法学院,江西 南昌 330013)
·人文视野·历史·文化
腐败规范化的历史困局
——传统中国卖官现象新论
谢红星
(江西财经大学 法学院,江西 南昌 330013)
传统社会的卖官包括制度性卖官和非制度性卖官,制度性卖官是国家根据一定标准公开向吏民出售官级、爵位、荣典、任官资格的行为,非制度性卖官是国家之外的私人或团体在法律规定之外,私下向个人出售官职,以谋取私利的行为,制度性卖官公开进行,钱入国库,非制度性卖官私下进行,钱入私门。传统王朝的国家汲取能力存在欠缺,财政收入不能随经济的增长而稳定增加,而开支却无限制膨胀,导致财政危机一再发生,政府不得不动用卖官这一政策工具来筹措经费,制度性卖官的制度化水准不断提高,同时非制度性卖官如影随形,渗入制度性卖官的体系中,冲击制度性卖官的实施,并最终淹没了制度性卖官。制度性卖官的失范及非制度性卖官的泛滥,意味着传统王朝政府将卖官规范化努力的失败。腐败本质上是反制度、反秩序、反规范和不可控的,传统王朝将卖官规范化的尝试和努力,必定陷入非制度性卖官淹没制度性卖官、反规范化趋势压倒规范化努力的历史困局。
制度性卖官;非制度性卖官;隐性腐败;潜规则
传统中国社会是一个官本位的社会,官职及随之而来的权力既是士人一展抱负成就自我的前提,也是个人锦衣玉食光宗耀祖的基础。与务农做工经商相比,做官是最划算的投资,是最佳的人生选择。人生得意时,金榜题名日,对广大寒门士子来说,金榜题名,穿上官服,是人生命运改变的开始,是家族社会地位上升的起点。
然而,“官员有数”,“而入流无限”(《唐会要》卷74《选部上·论选事》),在传统社会,“官缺有定数”和“参选之人无限膨胀”之间,存在着永远无法避免、无法克服的内在矛盾,这一矛盾使得仕途壅塞成为盛世官场之常态,同时也催发了官员铨选中经常性的大面积腐败。其中,最常见、最具有代表性的铨选腐败,就是平常说的卖官。传统中国的卖官现象包括哪些类型?有什么可以总结、可供借鉴的特点和教训?本文拟对此展开探讨。
一、制度性卖官的背后:走不出的循环
在传统社会,卖官指公开或私下地“出售”官职、品级、爵位、任官资格、晋级资格等,将官位视为商品处分的现象早在先秦就出现了,《韩非子·八奸》:“(今)父兄大臣请爵禄于上,而下卖之以收财利,及以树私党。”《五蠹》:“今世近习之请行则官爵可买,官爵可买则商工不卑也矣。”
官爵是国家公器,代表着不同于金钱财货的权力、地位、荣誉与尊严,尤其在等级社会,将官爵作为商品出售处分,势必破坏上下有别、贵贱有等的等级秩序,颠覆尊贤使能、量功授官的行政伦理,最终损害国家的政治统治与公共管理,正因为如此,韩非认为“卖官爵”是“亡国之风”,《管子·八观》也称“上卖官爵,十年而亡”,但同属法家的商鞅对出售官爵却做出了不同的判断,《商君书·去强》:“按兵而农,粟爵粟任,则国富。”《商君书·勒令》又曰:“民有余粮,使民以粟出官爵。官爵必以其力,则农不怠。”战国之世,弱肉强食,商鞅变法,农战为先,商鞅从秦国富国强兵兼并一统的眼前功利出发,将“纳粟授官”合法化、正式化,这种基于急迫的眼前功利而阶段性出售官爵的做法,为后世王朝所采用。秦王政四年(前243年)十月,“蝗虫从东方来,蔽天。天下疫。百姓内粟千石,拜爵一级”,(《史记·秦始皇本纪》)这是为救灾而卖爵。两汉时期,文帝、景帝、武帝、成帝、安帝、桓帝、灵帝都卖过官,或为募集粮食充实边防,或为筹集军费,或为赈济贫民,卖的范围从爵位逐渐扩展到低等的吏、郎职位。魏晋南北朝适逢乱世,战乱频繁,官府经常有筹集军费而卖官爵之举。之后隋代享国不长,卖官尚未制度化。唐前期基本上未实施过卖官的政策,安史之乱后,战乱迭起,国用不足,肃宗、德宗、宪宗、僖宗都颁布过卖官的诏令。五代各朝卖官制度化获得进展,制度性卖官的种类颇为繁多,有进纳官告绫纸标轴钱、光省礼钱、光台钱、尚书省礼钱、节度使代平章事纳礼钱、束脩钱、光学钱等。宋代制度性卖官通常被称为“进纳”“纳粟”“入赀”“纳赀”“献纳”“献助”,宋太宗、宋真宗、宋仁宗、宋神宗直至南宋灭亡为止,朝廷都因财政危机多次公开实施卖官,有时甚至减价卖官。元代立国后,政府为赈灾相继在成宗大德七年(1303年)、泰定二年(1325年)、文宗天历二年(1329年)、三年(1330年)实行“入粟拜官”,但此时向“入粟”者“实授”的只是属于“茶盐流官”和“钱谷官”的低级职位,到了元顺帝年间,由于国运危殆,政府向吏民开放出售“路府州县官”,然而因元王朝大势已去,应者寥寥。
明清两代是制度性卖官臻于完善的时期,其时卖官被称为捐纳。明代捐纳产生于正统、景泰之间,此后捐纳不断放开,持续实施,总的趋势是由地方化转向全国化,由临时的权宜之法转为常制,由捐纳散官冠带扩展为捐纳监生、科考资格、参选优先权、开复处分乃至实职,在制度化方面取得重要进展,成化二年(1466年),出现了目前所能看到的为时最早的捐纳则例:“在京各衙门办事官吏纳豆出身则例”和“申明办事官吏纳豆则例”。[1](p434-435)清顺治六年(1649)年清廷首开“捐监”,此后康熙、雍正年间,又多次开捐,乾隆即位后,将一部分捐纳项目固定下来,作为经常性捐纳项目,从此清代捐纳有“现行事例”和“暂行事例”之分,“现行事例”又称“常捐例”,指常年开办的捐纳,旨在筹措经常性经费,主要是职衔、封典、加级记录、取消行政处分之类,与“实授官职”无关,“暂行事例”又称“大捐”,指为筹措急需特定经费,在一定时期内开办的捐纳事项,其与“现行事例”最大的区别是,符合条件的可以捐纳郎中以下京官及道员以下外官的任职资格(含铨选、晋升时的优先资格)。清代捐纳卖官在制度化水准方面堪称历代之最,提供多种供报捐者选择的报捐流程,在印结的出具、捐升、捐复、捐纳出身者的候补与铨选等方面,也形成了一套非常完备的制度,反映出清代捐纳的常态化与规模化。
纵览传统王朝制度性卖官的历史,可以发现:(1)制度性卖官的起因基本上都是因为财政压力,制度性卖官被视为在正规财政外增加政府收入,尤其是解决紧急财政需要的最有效手段。(2)制度化水准不断提高。明清之前各朝公开卖官虽然也不少,但大多是临时性的,一旦度过财政危机,政府即结束该次卖官,自明代中期开始,卖官开始转向常态化,出现了目前可见最早的捐纳则例,清代更是将部分捐纳项目固定下来,以之为“常捐例”,各种捐纳事例种类之多,规定之详,区分之细,令人叹为观止,可以说基本实现了卖官的常态化、正规化、体系化。(3)以卖虚衔和各种资格为主,卖实官的较少。正常情况下,制度性卖官卖的大多是没有太多实际职权的爵位、官阶、官衔、出身,很少卖实官,清代虽然允许捐纳实官,但属“暂行事例”,并非常年开办。(4)出售的项目呈增加之势。自战国至两汉,国家向纳粟者提供的主要是爵位阶衔,偶尔卖低级吏职,从魏晋南北朝开始,政府开始出售任官资格和出身资格,随着科举制的确立,科举出身和参加上一级科举的资格成为出售的项目,最终发展为明清两代的“捐监”,而明清两代除了上述项目外,又增加参选资格及优先权、升职晋级资格及优先权、行政处分的减轻或解除为捐纳项目,由此,科举出身可捐而得,参选资格可捐而得,升职晋级的资格可捐而得,各种行政处分可以通过捐纳而免除。
卖官当然是有害的,统治者对此心知肚明,“捐班我总不放心,彼等将本求利,其心可知”,[2](p22)以科举正途仕进的士子更是视卖官为寇仇,痛声疾呼卖官之害,然而,所谓政事之先理财为急,财政问题不仅关乎个人的生活与命运,社会财富的分配与公平正义,更直接关系到政权的安危存亡:政府如果手里没有钱,如何维持军队司法等暴力机构,如何恩威并用、威慑怀柔不轨之徒,以及镇压叛乱,抵御外敌?历史上许多王朝的颠覆正是以财政危机为导火索,因此对统治者来说,国家财政困境是紧急而迫切需要解决的,否则就会立刻对国家施政造成重大妨碍,甚至危及统治秩序和政权生存,与此相比,卖官及其引发的腐败尽管有害于民风、士风、官风、国家治理,但这种危害是长期的、长远的,不会立刻发作。人们常批评公开卖官是饮鸩止渴,但客观来说,卖官未必毒如鸠毒,而财政危机之害甚于饥渴。
由此,制度性卖官的开办似乎是可以谅解的,而且大部分情况下,王朝政府反复申明卖官只是万不得已的权宜之举,反复强调只要财政危机度过就立即停止卖官,但问题在于,财政危机来而既去,去而复来,始终困扰着王朝政权的统治,成为历代王朝挥之不去、无法彻底治愈而间歇性发作的致命痼疾,此其一,而一旦财政危机发生,政府又总是选择公开卖官以筹措资金,此其二。易言之,财政危机发生——公开卖官——财政危机解决——停止公开卖官——财政危机发生——公开卖官—……成了一个走不出的循环,王朝政权越来越腐败,最终土崩瓦解。
“财政危机——制度性卖官”循环反复发生,反映出传统王朝国家治理能力的欠缺:(1)财政危机的一再发生,说明传统王朝国家规制能力和分配能力的欠缺。传统王朝“国家度支有常”,在“不加赋”的情况下,以田赋为主的国家财政收入每年大致不变,为了保持收支平衡,就必须“出入有经,用度有制”,然而在实践中,一则“帝王自己的奢靡无度,耗费了大量国家财政收入”,二则“皇室人口不断扩大,成为国家财政的重大负担”,三则“官吏集团及其附生人群的不断扩大”,由此,“财政供养人员的不断扩大,以及他们对生活质量的要求不断提高,必然导致固有财政收入的压力逐渐加大,加上还有可能受到外敌入侵威胁需要更多的财政支持等原因”,[3](p4)这一切使得传统王朝在事实上“用度无制”,最终必然引发财政危机。(2)制度性卖官成为应对财政危机最基本、最常用的政策手段,说明传统王朝国家汲取能力的欠缺。一般来说,汲取能力是国家能力的根本,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他国家能力,能持续、有效从社会经济生活中汲取财富的政权一般延续性也更强,[4]而“国家度支有常”某种程度上说明了传统王朝汲取能力的不足,在生产力发展、人口及财富增加的同时,国家财政收入竟不能保持同步增长,原因并不是统治者真正轻徭薄赋,爱民如子,而是政府在税收方面的无能及不作为,尤其需要指出的是,自明代中叶以降,商品经济尤其是江南地区的商品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同时,葡萄牙、西班牙、日本的白银通过贸易大量输入中国,[5](p4)社会上出现了一个拥有相当财富、渴望提升自己社会地位的商人及市民阶层,对此,政府却只求助于捐纳这一有害的政策工具,以之汲取一小部分剩余社会财富为己所用,充分说明了明清两代政府的无能。
“无能”不是明清政府的专利,“无能”某种意义上是帝制中国历代王朝的共性:首先,在一个疆域如此辽阔、受治人口如此众多、经济规模相对庞大、构造复杂的帝国,政府在有限的技术条件下要想从民间持续、有效地提取财富与资源,本非易事;其次,高度中央集权的专制政体下,帝国的可持续的良性运转以“双重控制”为前提,一是对君权及其行使者(治理主体)的控制,二是作为治理主体的君主对作为代理人的官僚机构及群体的控制,前者在制度上是缺位的,后者在实践中是失控的,“双重控制”由此变成了“双重失控”,后果是帝国可持续良性运转事实上的不可能。因此,传统王朝除少数“盛世”外,大多数时候都是以“亚健康”乃至“病态”的状态在运转,而这种“亚健康”、“病态”的直观表现就是“财政危机——制度性卖官”循环一再发生。
二、钱入私门:非制度性卖官中的博弈
传统王朝政府运用制度性卖官的政策手段,从社会各阶层汲取财富与资源,商品交换的经济原则由此加速渗入公共领域,反过来又使卖官从国家扩大到个人,从公开延伸到私下,非制度性卖官如影随形,始终存在于传统王朝的政治、社会生活中。汉代察、辟之下,官职的铨选经常成为一种私下交易。自汉初至武帝,以及东汉安帝、顺帝、桓帝时都存在很严重的权贵私下卖官现象,灵帝甚至开西园自行卖官,“私令左右卖公卿,公千万,卿五百万”(《后汉书·孝灵帝纪》)。魏晋南北朝以九品中正制选官,虽然制度上中正评品要依据家世和才德,实际上却主要看家世门第、个人爱憎、财货交情,于是,“或以货赂自通,或以计协登进。附托者必达,守道者困悴。无报于身,必见割夺;有私于己,必得其欲”(《晋书·刘毅传》)。隋朝废除九品中正制,削弱门阀政治,但私下卖官在某些时期仍较普遍,如炀帝后期内史侍郎虞世基掌选,“受纳贿赂,多者超越等伦,无者注色而已”(《资治通鉴》)。唐初,天下方定,卖官较为少见,之后太平日久,人求仕进,私下卖官现象开始涌现,“选司考练,总是假手冒名,势家嘱请。手不把笔,即送东司;眼不识文,被举南馆。正员不足,权补试、摄、检校之官。贿货纵横,赃污狼藉。流外行署,钱多即留,或帖司助曹,或员外行案。更有挽郎、辇脚、营田、当屯,无尺寸工夫,并优与处分。皆不事学问,惟求财贿”,[6](p6)中宗时的斜封卖官、安史之乱后的债帅,可谓有唐一代私下卖官之极致。宋代的非制度性卖官首先表现为中书门下、吏部等人事部门官吏私下卖官,关于宰执大臣私下卖官,北宋中前期较为少见,但从宋徽宗开始,大臣私下卖官之风就猖獗起来,蔡京、秦桧、韩侂胄、史弥远、贾似道等人当政,无不是政以贿成,官以赂得。元代私下卖官的内容不限于流内官,更扩大到一般为人所贱的吏职,甚至连监察官职也可买卖而得。
明清时期制度性卖官达到很高的水准,但这并未堵住手握实权的权贵私下卖官的门路。明武宗正德年间,刘瑾用事,贿赂公行,“百官非赀入不得迁”,“礼曹亦必二千,兵曹亦必千金”,[7](p188)自督抚至道府州县并佐贰,皆各有定价,随行就市,“某官银若干,某官银若干,至于升迁也亦然。某缺银若干,某缺银若干,群众相竞,则价值转增”。[8](p3523)康乾虽称盛世,然早在康熙年间京城就流传这样一则民谣:“要做官,问索三;要讲情,问老明;其任之暂与长,问张凤阳。”[9](p287)嘉道以降,仕途日形壅滞,官场更如市场,上下交征利,迄至晚清,上至皇帝后妃太监,下至掌握一省实缺差事分派大权的督抚布政,无不私下卖官取财,宫中以卖各色肥缺为常事,“粤、闽、海、淮、崇文门、张家口、杀虎口、山海关各监督,宁、苏、杭各织造,此皆专为应卖之品,可以名挂招牌者也;各省三品以上大员,此为帝心简在,公私不易分晰者也;学政主考,此乃清贵之官,似不致有此卑鄙,实因考差例不发榜,帝简在心;道府内放之缺,遇有素称肥缺者,部中书吏将应开列请简之名,赠予太监而招摇之,多为撞木钟,非真太后出卖也”,[10](p91)《官场现形记》描写了江西的一个盐法道署理藩台,因藩台不久就要回任,“他便利令智昏,叫他的幕友、官亲,四下里替他招揽买卖:其中以一千元起码,只能委个中等差使,顶好的缺,总得头二万银子”,[11](p30,20-25)《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也描写吴继之被藩台委了关差后,总督衙门的幕友立马送了一个折子过来,“上面开着江苏全省的县名,每一个县名底下,分注了些数目字,有注一万的,有注二三万的,也有注七八千的”,“若是想要哪一个缺,只要照开着的数目,送到里面去,包你不到十天,就可以挂牌”。[12](p23,558)
制度性卖官,卖官的是国家,钱入的是国库;非制度性卖官,卖官的是私人,钱入的是个人的腰包。卖官对政权和国家有害,统治者对此心知肚明,只是因为没有其他更有效的政策手段来化解与王朝存亡攸关的财政危机,才不得不屡屡以国家的名义“暂时”卖官鬻爵,而非制度性卖官完全无补于国家财政,完全无益于王朝政权,而且因为它卖的是实官,危害性比制度性卖官更大,因此,历代王朝于此无不立法严禁。虽然,遍览历代律典,基本找不到“卖官”之罪名,但实际上对非制度性卖官是按照其他一般性罪名来处理的,如在唐律,卖官可能构成受财枉法、受财为请求、监临势要受财为请求、受财不枉法、事后受财等罪,要言之,凡是罪状为“受财枉法”、“受财请求枉法”之类的罪名,都可以成为惩治非制度性卖官的法律依据,因为国家选官(包括卖官)自有制度,不按制度来就是“枉法”,因此卖官就是一种“枉法”,自然在律典禁止范围内。唐代史书记载的与卖官有关的案件,如李义府案、张锡案、郑愔崔缇案、元载案等,其中卖官基本上都是按受财枉法、受财为请求来处置的。《大明律》更是把非制度性卖官上升到了“奸党”的政治高度,除《刑律·受赃》“官吏受财”条的规定可以适用,《吏律·职制》“大臣专擅选官”条还规定:“凡除授官员,须从朝廷选用。若大臣专擅选者,斩。”[13](p30)这一条显然可以适用于权贵势要的私下卖官,因为私下卖官违背制度,堪称“专擅”。
律令的禁与惩,显然没有真正遏制住非制度性卖官泛滥之势;制度性卖官制度化水准的提高,也没能阻止非制度性卖官的扩张与渗入。在制度性卖官制度体系前所未有完备和法律对非制度性卖官惩治力度空前的明清两代,非制度性卖官发生的广度和深度均不逊色于前代。对于传统中国非制度性卖官的泛滥,必须从买官者、卖官者及两者间互动的角度来探讨:
其一,社会上存在着购买实官的强烈需求。虽然,捐买功名和官衔的人未必都是冲着实官去的,但在传统社会,做官、做实缺官的确是相当一部分人的人生追求,同时也是民间舆论所最认可的人生成就,想做官才是有志气,做了官、管了事、掌了权才算有出息,《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中的卜子修原来是个学徒,后突发奇想想做官,而且想做知县大老爷,请教他叔祖,他叔祖立刻就很高兴,夸他“志气不小,将来一定有出息”,“我”家境宽裕,无意功名,不小心捐了个监生和通判,家人就劝他去办引见。[12](p265)一般的制度性卖官并不能直接满足这部分人的需求,因为制度性卖官卖的是官衔和做官的资格,很少是实缺,捐官者仍须走较为正规的铨选程序,经漫长的审查、筛选、等待才能获得一缺。
其二,分利集团及其成员对卖官之利存有分润之心。美国学者奥尔森认为,“在边界不变的稳定社会中,随着时间的推移,将会出现大量的集体行动组织或集团”,这些集体行动组织或集团“极力倾向于收入或财富的分配而不是生产更多的产品”,它们是“分配联盟”(分利集团),[14](p36-47)奥尔森关注的是经济生活和经济学意义上的分利集团,实际上政治及社会生活中也存在类似的分利集团。传统中国实行高度中央集权的专制政体,国家对社会实行强控制,但所谓分利集团仍然存在,如宗室、外戚、后宫、朋党、豪强之类的小集团。卖官一本万利,人尽皆知,政府希冀垄断其利,同时尽可能缩小其危害,可分利集团及其成员岂能让政府独占其利,他们借国家卖官之东风,在制度性卖官的限度之外卖官,实际上分润了国家制度性卖官应得之利,这样做对王朝政权当然极为有害,但正如奥尔森所言,分利集团,尤其是缺乏共容性的分利集团的重要特点之一就是极端的自利性,他们没有动力使他们所在的社会更加繁荣,而是汲汲于对既有社会财富的分割与掠取,[14](p47-63)传统中国社会的分利集团,就是这样一些缺乏共容性的小集团,遍览史书,人们每每惊讶于这些人的贪婪、自私与短视,但这正是一切缺乏共容性的小集团的本性。
这里尤其要提一下作为最高统治者的君主实施的非制度性卖官。从理论上讲,在传统王朝,君主不属于任何分利集团,但事实上,君主却经常是私下卖官的主体,或者至少纵容身边亲信之人私下卖官。之所以如此,一是因为君主的个人利益并非总是与王朝政权的利益百分百重合,卖官一般不会直接、立刻导致王朝覆灭,却可以在短时间内搜刮到充足的钱财供己挥霍,二是君主并非总是理性的,他有情感、偏好、属于个人的人生经历,这一切会影响到他的性格、人生观,包括对金钱的态度,如汉灵帝少年家贫的人生经历及其生母董太后的贪欲,是其即位后疯狂卖官揽财的内在原因,《后汉书·宦者列传》:“帝本侯家,宿贫,每叹桓帝不能作家居,故聚为私藏,复寄小黄门常侍钱各数千万。”《后汉书·皇后纪下》:“及窦太后崩,(董太后)始与朝政,使帝卖官求货,自纳金钱,盈满堂室。”在帝制中国,君主是王朝政权的人格载体,但是,指望君主任何时候都能“去私曲就公法,去私行行公法”(《韩非子·有度》),显然是不现实的。
总之,非制度性卖官对有能力私下卖官的卖官者有利,对希望买官的买官者也有利,唯独对王朝政权及国家有害。对卖官者和买官者双方来说,这似乎是一场正和的博弈、双赢的交易,但如果加入王朝政权和国家为博弈方,这显然是一场零和博弈,只是零和的结局并不会立即显现,也未必由卖官者和买官者本人承担,而王朝政权和国家作为直接受害方,却没有充足的能力来制止这场博弈,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正反映出传统君主政体及国家治理机制难以克服的内在缺陷。
三、规范腐败:一个不可能的任务
从商鞅开始,人们就认识到出卖官爵是能“富国”的有效政策工具,西汉晁错全面总结了出卖官爵的功利:“所谓损有余补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顺于民心,所补者三:一曰主用足,二曰民赋少,三曰劝农功。”(《汉书·食货志上》)晁错认为出卖官爵一则不增赋而财用足,二则使天下多余的财富有一个好的去处,三则开辟由富而贵的通道,从而鼓励百姓致富。清代雍正皇帝甚至认为,科举出身未必有用,捐纳中亦有人才,他说:
朕近见科目之人苟且因循,而贪赃枉法者亦复不少。至于师友同年,夤缘请托,比比皆是。若仕途尽系科目,则彼此网结,背公营私,于国计民生为害甚巨。古圣人立贤无方,不可执一而论。且使富厚之家叨授官职,使不希冀功名,亦是肃清科场之道。[15](p417)
可见统治者不仅把出卖官爵视为解决财政问题的良策,某种程度上也把它当成了疏通仕进之途、选拔人才的一种另类方式,从这个意义上说,和科举一样,买卖官爵也是传统社会一种重要的向上流动途径。
然而,卖官终究是一种吏治腐败,无论统治者怎么为之寻找正当理由,他们终究不能否认这一点,在无法彻底舍弃这一政策工具的前提下,他们所做的,是努力使卖官这一腐败规范化,希冀能收其利而遏其害,由此,人们看到了明清时期数目众多、体例严密、内容完备的捐纳事例,但卖官真的就此规范化了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无论清代中前期还是后期,卖官这一统治者认可的“必要的腐败”从来就没如他们设想那样真正规范过,非制度性卖官的顽强存在,固然是卖官规范化努力失败的重要表现,实际上,就算是国家认可的制度性卖官如捐纳,其运行也很少严格按诸项事例文本规定的那么做,而是以另一套规则或说惯例在运作:
其一,报捐必须通过金融机构代办。依清政府的捐纳事例,捐纳允许代办,但仅限于亲戚和友人,银号、钱庄等金融机构代办报捐属于“包揽”,为例所禁,但实际上,京城的金融机构为报捐者代办报捐是清代极为普遍的现象,一则报捐者一般很难读懂各种专门化的捐纳事例和章程,二则报捐者不可能随身携带报捐所需的大量金银,所以,委托金融机构汇转、保管资金,由此发展为请其帮忙代办报捐,自然顺理成章,对金融机构来说,则不仅可以收拢资金,还可以收取手续费,自然无不乐意之理。但是,金融机构介入报捐事务之后,通过非法的利益输送,打通各种关节,与捐纳房等办理报捐事务的衙门及官吏建立起关系紧密的分肥同盟,反过来把持了北京的报捐:如果是自己报捐,即使熟知各种章程和程序,也必然遭到办事胥吏的层层刁难和需索,相反如果委托与捐纳房关系紧密的银号、钱庄办理,则一路畅通无阻。由此,委托金融机构,尤其是与中央有关衙门关系密切的金融机构代办报捐而非自己报捐,成为清代捐纳的一条潜规则,这一潜规则的背后,是京城金融机构与中央各办理捐纳事务衙门的勾结与钱权交易。
其二,印结论印计价,钱到即得。在清代,“印结”是一种保证文书,“印”指官印,“结”乃保结,清代捐纳制度规定,包括普通庶民和在职、候选候补官吏在内的报捐者在报捐时必须同时提交同乡五六品京官出具的印结,这是确认报捐者身份的必要文件,从制度上讲,出具印结的京官必须在充分了解报捐者个人情况的前提下,自愿并亲自出具印结,但实际上,由于报捐者人数越来越多以及代办报捐的普遍存在,报捐者多是将印结等报捐手续一并委托给金融机构,而由后者去找由本省籍京官组成的印结局,在交纳印结局单方规定的印结银后,再由印结局出具报捐者需要的印结,在此过程中,出结的京官与报捐者不碰面、不认识,当然更谈不上熟知情况,他们之间真正发生的关系,是以印结局为中介一手交钱、一手出结,这当然是一种权钱交易。
其三,署差、补缺任由长官意志。捐纳一般最多只能获得参选的资格,报捐者领取捐官执照,向吏部注册之后,即可参加吏部的铨选,当然,吏部的铨选则例对铨选有详细规定,有班次、花样、单双月、掣签之类,这些信息是完全公开的,捐纳出身的候选官员可以依次推算大致何时轮到自己,可由于官多缺少,即使捐纳花样,他们也很难按部就班在吏部等到官缺,基于此,大部分人选择分发指省,在京外候补,希冀获得署事、差委和补缺的机会,理论上讲,地方上的署事、差委和补缺也有一定的制度,但总体而言其决定权完全在督抚之手,加之候补官的人数远远超出了官制的规定和临时性行政事务所能容纳的人数,因此实践中,贿赂、人情等“潜规则”替代了关于署事补缺的种种公开规定,督抚藩台视贿赂的多少、人情的轻重来决定去取,《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将一省之内的候补官分为四大宗,只有前三宗人有署事补缺的机会:
第一宗,是给督抚同乡,或是世交,那不必说是一定好的了。第二宗,就是藩台的同乡世好,自然也是有照应的。第三宗,是顶了大帽子,挟了八行书来的。有了这三宗人,你想要多少差事才够安插?除了这三宗以外,腾下那一宗,自然是绝不相干的了,不要说是七八年,只要他的命尽长着,候到七八百年,只怕也没有人想着他呢。[12](p64)
此外,捐升的引见验看可以花钱找人顶替;捐复须由督抚先期向皇帝申请捐复,从而为督抚与希望捐复者之间的钱权交易提供了空间;金融机构在代办报捐的同时,又从事向资财不足的报捐者放贷的业务,由此,许多家境本不宽裕、科举又无望之人动起了举债捐官的心思,他们或向亲友熟人举债,或向金融机构借贷,打着补缺后捞钱还债的念头,成为“带肚子的官”,完全失却了捐纳“使富厚之家叨授官职”“富家子弟由捐纳一途而进”的本意,对吏治构成直接的危害;随着捐例越开越多,越开越久,仕途越发壅滞,许多捐官长年难以得缺成为普遍现实,各种报捐项目逐渐失去往日的魅力,难以聚敛到足够的钱财,对此,清政府一方面对捐项打折减价,另一方面发动地方官员向士民“劝捐”,其中自然又免不了加派、中饱与强制。
总之,清政府希望将卖官规范化,希望能尽揽卖官之利而遏其害,甚至希望捐纳能成为科举之外又一条促进社会阶层流动的有效路径,成为富家子弟、特殊人才的晋身之途,然而,看似完备的捐纳制度,根本阻挡不住捐纳实施中的私下交易、中饱私囊、弄虚作假,国家意图掌控的制度性卖官事实上被其无法掌控的非制度性卖官所渗透,对希望做官的报捐者来说,公开的捐官只是第一步,私下买缺是第二步,而且是真正关键的一步,捐官花的相对是小钱,买缺花的钱才是大头,易言之,体系化、看似规范的制度性卖官只是清代卖官的表面,非制度性卖官才是清代卖官的实质或者说主导,清政府规范卖官的努力最终被证明是失败的。
美国学者魏德安在《双重悖论》一书中提出,腐败可以分为发展性腐败和掠夺性腐败,发展性腐败是“一种有组织的犯罪形式”,在这个过程中,“政治上的黑手党从商界合法或非法所得中扣留一部分据为己有,然后出台有利于商业发展的宏观经济政策”,掠夺性腐败是“掠夺式”的,类似于“明火执仗的抢劫”,在这种腐败模式下,“腐败大多是国家组织的自体腐败,利益只是单向流动,政界打劫商界之后并没有基于长远利益的考量而出台促进商业发展的宏观经济政策”,魏德安承认,从来就没有什么“良性腐败”,但确实存在更为恶性的腐败,发展性腐败和掠夺性腐败都会造成严重的危害,但掠夺性腐败更有可能引发致命的后果,会更加迅速地暴露出恶劣影响,发展性腐败本身不会促进经济增长,但因为其有组织性、可控性,相对能遏制掠夺性腐败造成的消极影响。[16](p72,29-67)
制度性卖官使得传统社会工商阶层的游动资金“投入钱权交易的领域”,而并没有“按照商品经济的自然规律,投入商品的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增加商业资本的总量,或在商品流通领域流动”,[17](p9-10)结果是分散了商业资金,分化了工商阶层,某种程度上构成传统社会商品经济无法充分发展、难以走向成熟的原因。从这个意义上说,制度性卖官不能说是发展性腐败,但是,按魏德安的标准和逻辑,它却似乎可以说是一种有组织的、可控的、可持续的腐败,至少从统治者的初衷来看是这样。魏德安认为,如果腐败实在难以避免,那就让腐败受到某种控制甚至利用它,如朴正熙在韩国、自民党在日本、国民党在中国台湾地区做的那样,控制腐败某种程度上是可以实现的。[16](p74)然而,传统中国制度性卖官终归失败的历史实践却证明,希冀规范、控制、利用腐败,只会是政府的一厢情愿,因为从本质上讲,腐败是对规范化治理的违逆,是对法律秩序的破坏、对人之善良品质的腐蚀,对一次违法的放纵必然招来更多的违法,对某种腐败的容忍必然鼓励、创造更多的腐败,当然,在腐败积重难返、反腐败斗争长期、复杂、艰巨的情况下,将规范、控制腐败作为反腐败斗争的阶段性工作及目标,未尝不可,但是,传统王朝将卖官制度化的努力并非基于长期反腐败斗争的需要,并非反腐败建设的权宜之举,而是为了独占卖官的收益,以之为满足财政需要的稳定的政策工具,其结果由此必然是,制度性卖官的法律越来越严密,非制度性卖官却越来越泛滥,制度性卖官在非制度性卖官的冲击下难以为继,最终被非制度性卖官所淹没。
结语
在一个产权得不到充分保护、交易与投资没有足够法律保障的国家,社会资本必然流向公共领域,以公开或私下钱权交易的方式,购买足以为身份标识的官职、爵位、荣典、资格。而对缺乏更多有效税收手段的传统政府来说,卖官是一种相当见成效的提取社会财富的政策工具。由此,在传统社会,制度性卖官成为一种法律及社会观念认可的腐败,是一种看似“合法”“合理”,性质隐晦的隐性腐败。
腐败本身具有不确定性,无论它是显性腐败还是潜规则化的隐性腐败。我国有学者认为,隐性腐败的特征之一是“数量的定额化和相对稳定性”,[18](p5)但是,潜规则的约束力是“依据当事各方的造福或损害能力,在社会行为主体的互动中自发生成”,[19](p193)隐性腐败下的权钱交易,其数额、程序最终由交易双方的需求、实力及相互的博弈而定,其中就算有一定的惯例或规则,对双方的约束也只是软约束而非硬约束。由此,传统王朝将卖官规范化的尝试和努力,必定陷入非制度性卖官淹没制度性卖官、反规范化趋势压倒规范化努力的历史困局。
[1]刘海年,杨一凡.中国珍稀法律典籍集成乙编(第4册)[M].北京:科学出版社,1994.
[2](清)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1.
[3]洪振快.亚财政:制度性腐败与中国历史弈局[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
[4]张长东.税收与国家建构:发展中国家政治发展的一个研究视角[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1,(3).
[5]樊树志.晚明史(上册)[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
[6](唐)张鷟.朝野佥载[M].赵守俨,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79.
[7](明)李清.三桓笔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2.
[8](明)陈子龙.明经世文编[M].北京:中华书局,1962.
[9](清)昭梿.啸亭杂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0.
[10](清)王照.方家园杂咏记事[M].北京:中华书局,2007.
[11](清)李伯元.官场现形记[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12](清)吴趼人.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13]怀效锋点校.大明律[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
[14][美]曼瑟·奥尔森.国家的兴衰:经济增长、滞胀和社会僵化[M].李增刚,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
[15](清)萧奭.永宪录续编[M].朱南铣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59.
[16][美]魏德安.双重悖论——腐败如何影响中国的经济增长[M].蒋宗强,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
[17]宁欣.唐史识见录[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18]晏爱红.清代官场透视——以乾隆朝陋规案为中心[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2.
[19]吴思.潜规则:中国历史中的真实游戏[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
K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477(2010)10-0097-08
谢红星(1978—),男,法学博士,江西财经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法治视角下传统中国隐性腐败治理研究”(15BFX017,主持)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 唐 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