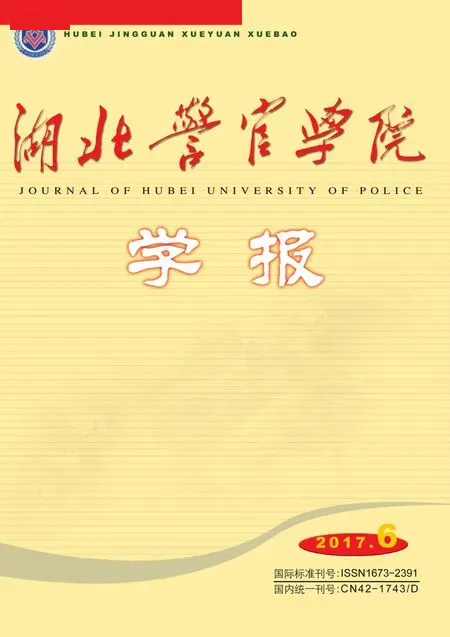“报道不应公开的案件信息罪”评析
雍自元
(安徽师范大学 法学院,安徽 芜湖241002)
“报道不应公开的案件信息罪”评析
雍自元
(安徽师范大学 法学院,安徽 芜湖241002)
自由保障与秩序维护都是刑法的机能,报道不应公开的案件信息罪的立法宗旨在于维护司法秩序,体现了立法者社会秩序优先的价值取向。该罪的构成要件比较粗疏——犯罪客观要件虚置,情节严重无标准,犯罪主体范围待划定,犯罪主观方面的认识内容不明确。为了落实罪刑法定的要求,也为了防止此罪在司法实践中被滥用,应尽快完善配套法规,界定不应公开的案件信息的范围与内容,修改罪状,明确该罪的构成要件,同时出台司法解释,明确情节严重的内涵。
新闻报道;不应公开的案件信息;构成要件明确性
《刑法修正案(九)》在刑法第308条之一第三款中增设了“报道不应公开的案件信息罪”这一新罪名,将报道依法不公开审理案件中不应公开的信息,情节严重的行为规定为犯罪。显而易见,“报道”的行为主体为新闻媒体及其工作人员,其规范的是媒体报道司法案件的行为,调整的是媒体与司法的关系。该罪名的设置有利于规范媒体报道司法的行为,但如果内容设置不科学,也可能限缩媒体关注与报道司法,影响媒体监督司法功能的发挥。《刑法修正案(九)》生效至今,学界对该罪的关注程度不高,虽然已有学者在剖析刑法第308条之一规范目的的基础上,研究本条规定在理解和适用中的疑难问题,但该研究立足于现有法条的规定,侧重于对该罪规范在理解与适用方面进行阐释,[1]属解释性研究。实际上,本罪在构成要件设置方面存在着诸多模糊之处。本文从评析的角度,拟就该罪的立法宗旨、罪状设置探讨本罪在构成要件方面的不明确性和不完备性,提出完善该罪的立法设想。
一、本罪立法价值取向——维护司法秩序
立法和司法活动都是一种价值选择活动。当立法者们为人们确定权利和义务的界限时,他们实际上就是力图通过保护、奖励和制裁等法律手段来放任、支配或反对一定的行为,从而使社会处于一种在立法者看来是正当的或理想的状态。[2]学界一般认为,自由保障和秩序维护是刑法的两大机能,刑法应兼顾公民权利和社会秩序两种价值,但《刑法修正案(九)》更倾向于优先选择秩序价值。[3]本罪的设立就是适例。
首先,在当事人信息安全与司法秩序之间,该罪优先保护的是司法秩序。从本罪的罪状设置看,报道不应公开的案件信息罪侵害的法益应该是双重的:一方面,报道依法不公开审理的案件信息妨碍了司法机关正常的诉讼秩序,具体而言是法院正常的审判秩序;另一方面,报道不应公开审理的案件信息有可能导致公民专属或隐私性信息被泄露,侵犯诉讼当事人的信息安全。近年来,公民的信息安全越来越受到刑法的关注,公民信息安全立法日趋完善。2009年《刑法修正案(七)》在刑法中增设第253条之一,将出售、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罪和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规定为犯罪。为遏制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犯罪,2013年4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下发了《关于依法惩处侵害公民个人信息犯罪活动的通知》,要求公、检、法机关对侵害公民个人信息犯罪行为统一思想、提高认识,促进社会协调发展,维护社会和谐稳定。2015年《刑法修正案(九)》对刑法第253条之一进行了修改,将“个人”增设为侵犯公民信息的主体,将单位在履行职责或者提供服务过程中获得的公民个人信息,出售或者提供给他人的行为作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从重处罚情节。可见,公民个人信息刑法保护的范围和力度都在强化。①2017年3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台了《关于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为依法惩处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提供了具体的标准。依法不公开审理的案件中涉及的当事人信息属于公民信息的一种,“报道不应公开的案件信息罪”的增设也是应时之需,是强化对公民信息保护之体现。然而,我们不难发现,虽然本罪也涉及到“个人信息”,但它并未像刑法第253条那样被设置在刑法分则第四章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中,而是被设置在刑法分则第六章“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的第二节“妨害司法罪”当中。刑法中犯罪归置的主要依据是被犯罪行为所侵害的、为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即法益。报道不应公开的案件信息既妨害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审理相关案件,也会侵犯利害关系人的合法权益,其犯罪危害的是双重法益,但从本罪的法条归置看,很显然,司法秩序才是首要的被保护价值。
其次,在新闻自由与司法秩序之间,该罪的设置同样体现了司法秩序优先。新闻自由与司法秩序、司法权威孰重孰轻?媒体报道司法是否该受刑法规制?这个问题一直存在争议。在《刑法修正案(九)(草案)》征求意见时,多位刑法学家针对此问题展开过激辩。争议的焦点之一就是第308条之一第3款会不会不当限制新闻媒体的权利,使媒体无所适从,舆论监督受损。[4]著名刑法学家高铭暄教授指出,新闻报道应有一定的自由度,即使报道有误,只要不是故意制造事端,将其入罪就要慎重。陈泽宪教授也表示,媒体的职责与诉讼参与人不同,媒体最重要的责任是向公众提供其关注的信息,只要媒体的报道符合真实情况,就尽到了职责,至于信息是否应当披露,媒体没有义务去严格核实。宋英辉教授则有不同见解,他认为不公开审理案件的所有信息都应该是保密的,不应该披露,……规定情节恶劣者入罪还是有必要的,但对入罪标准应严格限定,既不能放任,也不能打击面过大。[5]赵秉志教授也认为,有必要将造成严重后果的违法披露、报道案件情况的行为规定为犯罪。[6]虽然学界对该罪的入刑与否存在分歧,但最终全国人大常委会还是将报道依法不公开审理案件中不应公开的案件信息,情节严重的行为规定为犯罪行为。尽管法条对该罪的对象和程度作了严格的限制,体现了入罪时的谨慎,但该罪的增设无疑表明立法者社会秩序优先的价值取向。刑法是应用性极强的国家基本法律,其制定与修正都是为了面向实际,解决实际问题。该罪的设立也是官方对学界关于媒体报道自由权与司法机关独立行使司法权关系之争论的一次回应和表态。
二、本罪构成要件——粗疏、虚置
刑法是价值之法,立法者对价值权衡后增设罪名无可厚非。但是,刑法中罪刑设置应具有明确性,这是罪刑法定原则的基本要求。遗憾的是,报道不应公开的案件信息罪的构成要件要素却是模糊的。
(一)犯罪客观要件虚置
犯罪客观方面要件是犯罪构成的核心要件,是确定犯罪是否构成、厘清与其他罪界限的关键所在。细究后我们发现,报道不应公开的案件信息罪的客观方面要件实际上处于虚置状态。
1.配套法规不明确,不健全,“不应该公开的案件信息”无法确定
从法条规定看,报道不应公开的案件信息罪采用的是引用加空白罪状的立法模式。不该报道的案件信息的类型与第一款规定相同,即不公开审理案件中的信息。但和第一款一样,刑法本身并没有具体规定这一犯罪的构成特征,仅指明确定该罪构成特征需要参照其他法律、法规。因此,不应公开的案件信息实际上是由其他法律、法规规定的。这就意味着其他法律、法规中关于不应公开的案件信息之规定对确定本罪成立与否至关重要。但是,如此重要的内容却在其他法律、法规中难觅影踪。
从刑法第308条之一第3款的罪状描述逻辑看,并非不公开审理的案件中一切信息都不能报道,只是对不应该公开的案件信息进行了报道才有可能构成犯罪。规定不公开审理案件类型的是三大诉讼法,它们将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涉及隐私的案件规定为绝对不公开审理的案件,而涉及商业秘密、离婚案件则作为相对不公开审理的案件(经当事人申请,可以不公开审理)。但是,三大诉讼法都没有规定依法不公开审理的案件中哪些属于不应该公开的信息。扩大范围,将目光投向与不公开审理案件相关的法律法规,同样没有规定。
涉及国家秘密的法律主要有《宪法》《档案法》《保守国家秘密法》《国家安全法》《档案法实施办法》《保守国家秘密法实施办法》和《国家安全法实施细则》。这些法规对国家秘密的内容、密级、定密、保密、解密、保密责任主体以及纠纷救济作出了规定。但是,它们并未涉及到审理涉密案件时不应公开信息的范围与内容。我国还没有商业秘密保护法,只是在《反不正当竞争法》中规定了“商业秘密”的概念以及侵犯商业秘密的行为方式。该法仅限于“经营者与经营者之间的关系”,并没有对人民法院审理商业秘密侵权案件时,哪些信息不应公开作出规定。有关隐私权的学说林林总总,学界对隐私的核心内容仍然没有达成共识。[7]对于哪些属于个人隐私、哪些主体的隐私权应受例外保护、涉及个人隐私的案件是否全部不公开审理等问题立法中并无直接、明确的规定。这种现状必然导致法院在审理依法不公开审理的案件时,在信息公开与否上无法可依,无所适从。遗憾的是,这个问题也没有引起司法机关的重视,2015年9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联合发布了《关于依法保障律师执业权利的规定》,对律师提出了不得违反规定披露、散布案件重要信息和案卷材料的要求。但该《规定》并未对“重要”的标准做出具体说明,因而同样无法发挥指导作用。
在依法不公开审理的案件中,国家给予未成年人案件的关注最多,涉“少”案件中不应该公开信息的规定也最丰富。(1)在法律层面,全国人大常委会1991年出台了《未成年人保护法》,1999年颁布了《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这两部法律对涉少案件信息的报道主体和报道内容进行了限制。《未成年人保护法》第58条规定:对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新闻报道、影视节目、公开出版物、网络等不得披露该未成年人的姓名、住所、照片、图像以及可能推断出该未成年人的资料。《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45条第3款有类似规定。《刑事诉讼法》第275条第2款确定了对轻微犯罪(被判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未成年人犯罪记录进行封存的制度,规定除司法机关为办案需要或者有关单位根据国家规定进行查询外,该记录不得向任何单位和个人提供。(2)司法机关对涉少案件中不应公开的案件信息进行了规定。公安部1995年颁布的《公安机关办理未成年违法犯罪案件的规定》第5条指出,办理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案件,应当保护未成年人的名誉,不得公开披露涉案未成年人的姓名、住所和影像。最高人民法院2001年颁布了《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①该《规定》已被刑事诉讼法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修改,于2015年1月被废止。,其中第13条第2款规定:“未成年人的刑事案件的诉讼案卷材料,除依法查阅、摘抄、复制以外,未经本院院长批准,不得查询和摘录,并不得公开和传播。”《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469条将涉“少”案件中不得公开的信息具体化为该未成年人的姓名、住所、照片以及可能推断出该未成年人身份的其他资料,并将未成年人被害人纳入保护范围。最高人民检察院2002年颁布了《人民检察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规定》,第5条确定了检察院机关在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时,保护涉案未成年人隐私的原则,规定未成年人的姓名、住所、照片及可能推断出该未成年人的资料等信息不得公开或者传播。此后,“图像”也被列为不得公开信息,2013年再次修订该《规定》时延续了这一内容。(3)媒体也对涉“少”案件的报道比较谨慎,在行业性规范中设置了报道禁区。2004年颁布的《中国广播电视播音员主持人职业道德准则》第12条规定:报道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和性侵犯的受害者时,录音、图像应经过特殊处理,使之不可辨认;不公布其真实姓名,不描述犯罪过程。同年颁布的《中国广播电视编辑记者职业道德准则》第32条重申了上述内容。(4)一些地方性法规对涉“少”案件中不应公开的案件信息范围和内容也进行了规定。如2002年出台的《内蒙古自治区公安新闻宣传管理暂行规定》指出:未征得被害人、检举人、证人同意之前不得公开其姓名、住址、单位和正面头像(包括电视摄像和新闻图片)。由此可见,我国法律法规对媒体报道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有一定的限制,从传统媒体到网络媒体、从基本身份信息到可能推断出该未成年人的资料,从审理期间到判决前的各个环节。[8]但是,通过梳理,我们也发现,涉“少”案件中不应公开信息的规定不仅主体多元,多层次,而且范围不一致,内容也存在较大差异,如有的是案卷材料,有的是具体的个人信息。各部门单独立法不仅使法规形式凌乱,也造成各规范相互之间不匹配、不衔接,“不应当公开”的标准不统一。
除此之外,不应公开的案件信息对象范围是狭窄的,诉讼过程中还有一些人,如证人、举报人、鉴定人的信息也需要得到特别的保护,也应限制或者禁止媒体报道。
2.“情节严重”无标准
根据我国刑法第308条之一第3款的规定,报道不应公开的案件信息只有在“情节严重”时才能构成犯罪,因此,“情节是否严重”是区分罪与非罪的重要指针。但何为“情节严重”,法条并未作出规定,最高司法机关也没有出台司法解释对“情节严重”作出界定,这必然导致“情节严重”在司法实践中认定困难。是以次数,还是以后果,或是以态度、行为性质等作为“情节严重”的标准?无法知悉。
综上所述,与报道不应公开的案件信息罪直接相关的若干配套制度有的尚未确立,已有的也缺乏统一性、完整性,结果导致该罪构成要件虚置,空泛、粗疏。立法的不明确必将引发司法认定困难、适用随意等诟病。
(二)犯罪主体范围需界定
按照刑法第308条之一第3款和第4款的规定,报道不应公开的案件信息罪的主体包括自然人和单位。实践中既可能是记者、编辑,也可能是媒体和其他发布信息的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等。但是该主体是仅限于第一报道者,还是应该包括转载、转播报道和分享的主体,法条并未规定。转载、转播、分享是媒体传播信息的重要方式,媒体转载、转播之前负有审查核实的义务,但是随着新型媒体的广泛运用,人人都有可能充当记者的角色,随时会有报道出现,对转载、转播、分享的内容的审查几乎不可能,这便加大了不应公开的案件信息被公开的风险。在此情势下,报道不应公开的案件信息罪的主体是否应将转载者、转播者、分享者涵盖其中?还是仅限于第一报道者?犯罪主体范围事关犯罪圈的大小和公民切身利益,法律应明确规定本罪的主体。
(三)犯罪主观方面不明确
刑法第308条之一第3款没有对报道不应公开的案件信息罪的主观方面进行叙明,理论界对该罪的主观方面认识不一致。有学者认为,披露、报道不应公开的案件信息罪,从主观方面言之,既可能是直接故意,也可能是间接故意,还可能是疏忽大意的过失,但不可能是过于自信的过失。[9]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也认为本罪法条没有限定故意,故本罪的主观方面似应包括故意和过失。[10]赵秉志教授主张将本罪限定为“故意”,规定“明知”的主观条件,以避免本条规定处罚对象的扩大化。[11]高铭暄教授、马克昌教授共同主编的刑法学教材也认为本罪主观方面出自故意。[12]目前来看,主张故意的学者较多,但对故意的内容没有形成一致意见,是明知报道的是依法不公开审理的案件信息即可构成犯罪,还是需认识到自己报道的依法不公开审理的案件信息会损害涉案人员的权利,造成危害社会的结果才能构成犯罪?这个问题无法从法条中获得答案。
三、完善本罪的路向——罪状明确化
明确性是成文法的生命,刑法的规定应准确地确定罪与非罪的界限,使人们能够确切了解犯罪行为的内容,这是最为起码的要求。孟德斯鸠说过,在法律已经把各种观念明确地加以规定之后,就不应再回头适用含糊笼统的措辞。[13]贝卡里亚也认为,更为糟糕的是,法律是用一种人民所不了解的语言写成的,……这种语言把一部庄重的公共典籍变成了一本家用的私家书。[14]刑法乃国之大法,刑法的适用关系到公民的人身自由和政治权利等重大利益,其罪刑设置应该严谨、缜密。报道不应公开的案件信息罪的构成要件笼统、模糊,既不利于司法实践中的操作与适用,也会使公民的自由受到无形的限制。因此,对其进行完善是当务之急,笔者以为最紧迫、最重要的是增强罪状的明确性。
(一)完善配套法规,确定不应公开的案件信息的范围与内容
在《刑法修正案(九)(草案)》讨论的过程中,有学者指出:“不公开审理案件中哪些信息属于不应当公开的信息,其范围缺乏必要的界定。”[15]笔者以为,依法不公开审理案件中不应公开的信息涉及面多,内容繁杂,不宜在刑法条文中一一罗列,因而目前采用的在刑法条文中设置空白罪状,依靠其他法规具体确定的方式较为合适,只是相关配套法规应该建立健全。具体路径可以考虑如下几种:(1)制定《信息保护法》,设专章规定依法不公开审理案件中不应公开的信息范围与内容;(2)在《人民法院组织法》中增加规定不公开审理案件中不应公开的信息的具体内容;(3)在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中分别规定各类诉讼中不应公开的案件信息;(4)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严格执行公开审判制度的若干规定》或者《人民法院法庭规则》中统一确定依法不公开审理案件中不应公开的案件信息。有了配套法规支撑,刑法第308条之一第3款规定的“报道依法不公开审理的案件中不应公开的信息”中“依法”才有实质意义。
将哪些信息规定为不应公开的案件信息?我国学术界对此关注较少,域外的研究与立法或许可以为我们提供借鉴。美国法律人协会于1966年发表了雷尔顿报告,指出了6项不应该报道的事项:涉案嫌犯被指控的罪名、人格与名誉、犯罪记录、供词或者自白、证人与证词可信度、司法机关检验结果。在英国公开性犯罪受害人的身份,报道儿童作为被告、证人或者受害者的刑事案件都可能构成藐视法庭罪。法国1881年《出版自由法》规定:有关未成年犯的审判无论是文字或图片均不得发表,否则传媒将成为法院惩处的对象。结合我国已有的规定,参考域外的立法实践,不应公开的案件信息不该一概而论,应根据案件类型有所区别。(1)就涉密案件而言,无论是国家秘密还是商业秘密,不应公开的案件信息应限于秘密的具体内容和秘密知悉人员的身份信息,对其他涉案信息则无保密的必要;(2)涉及个人隐私的案件需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隐私案件的范围,由于立法没有明确规定,司法实践中一般将强奸罪、强制猥亵、侮辱罪作为隐私案件不公开审理,笔者以为除了上述两种犯罪之外,还应该包括与个人生活密切相关、可能引起被害人被歧视的其他犯罪,如重婚罪、拐卖儿童罪、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猥亵儿童罪、引诱幼女卖淫罪、引诱未成年人聚众淫乱罪等。在民事案件中,还应包含离婚案件。这些案件的审理中同样会涉及到被害人的隐私,若被公开报道,则有可能危害他们生活的安宁。二是这类案件中不应被公开报道的案件信息应该是受害人、被引诱人、无过错方和无辜者的信息,实施此类犯罪的成年犯罪人的犯罪记录和身份信息属于公共信息,并不具有隐私性[16],当然也就不属于不应公开的案件信息。三是不应报道的应该是与其身份相关的一切信息。(3)针对未成年犯罪人,其涉案信息的保护应该尽量完备。除身份信息外,其违法犯罪前科、犯罪过程、涉嫌罪名、就读学校和法庭中的陈述等可能识别出该个体的一切信息,应列为不应公开的案件信息。(4)为了鼓励报案人、控告人、举报人揭发犯罪,为了确保证人、鉴定人大胆地参与到案件审判中,客观地提供证明,作出鉴定,更为了防止他们受到打击报复,在一些特殊案件中,不应公开的案件信息也应包括上述人员的有关身份信息。
(二)修改罪状,提升构成要件科学性
1.将本罪的主体限定为第一报道者。理由有三:(1)社会危害性是犯罪的本质特征,首次报道不应公开的案件信息者是造成该信息被传播和扩散的始作俑者,侵犯了当事人的信息安全,扰乱了司法秩序,如果情节严重,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第一报道者应是首先被考虑的主体。(2)惩治已然之罪、预防未然之罪是刑罚正当化的根据。将第一报道者确定为犯罪主体,可以从源头上阻止不应公开案件信息被转载、转播、分享,防止负面影响无限扩大和局面的无法控制,能起到正本清源的功效;也可以警示其他媒体及其从业人员,不涉足依法不公开审理案件中的不应公开信息,最终实现刑罚特殊预防和一般预防的目的。(3)对犯罪主体进行限制体现了刑法的谦抑性。刑法谦抑性更多地体现在刑事立法层面[17],将第一报道者作为犯罪主体能防止犯罪圈过大,进而防止因打击面过宽而引发的人人自危和社会恐慌。因此,将第一报道者作为本罪主体是较为妥当的选择。当然,转载者、转播、分享者也应该受到警醒,对他们可以依照新闻机构的职业规范处理或者由当事人起诉追究其民事侵权责任。
2.将本罪的主观方面认识内容确定为明知报道的为“依法不应公开的案件信息”。首先,本罪的主观方面是故意而非过失,有关学者关于本罪主观方面是过失的观点是对法条的一种误解。(1)从刑法规定看,刑法第15条第2款规定:“过失犯罪,法律有规定的才负刑事责任”,在刑法中并没有出现过失犯报道不应公开的案件信息罪的条文,也没有“过失犯前款罪”的规定,因而可以得出本罪在主观方面只能是故意,即在认识因素方面是明知,在意志因素方面是希望或者放任。(2)从权利平衡的角度看,报道是媒体权利,是实现公民知情权和新闻自由权的重要手段,有些媒体抢先报道不公开案件新闻只是为了猎奇,不存在主观上的恶意。因此,对那些过失报道不应公开的案件信息的行为不应作为犯罪处理。其次,在明确本罪的主观方面为故意的基础上,对认识的具体内容,还有细化的必要。为防止媒体、从业人员以不知道报道行为有社会危害性为自己开脱,笔者以为,本罪在主观方面只要行为人明知是依法不公开审理的案件中不应公开的信息而进行报道即可,不必要求他们认识到自己的报道行为有危害社会的结果。
(三)尽快出台司法解释,明确“情节严重”的内涵
本罪属于情节犯,情节是否严重关乎罪与非罪。正因为如此,情节严重的标准确定至关重要。上海市亚太长城律师事务所陆欣律师认为,本罪中的“情节严重”,应指造成信息公开传播而给利益相关者带来的严重损失,如诉讼参与人的个人隐私为他人所知悉,导致其名誉、人格遭到贬损,甚至引发自伤、自杀等严重后果等等。[18]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认为“情节严重”主要是造成信息大量公开传播,为公众所知悉,给司法秩序和当事人合法权益造成严重损害。[19]笔者以为,针对不同的依法不公开审理案件中的信息,“情节严重”应有不同的标准,应该从报道次数、报道造成的影响、经有关部门责令停止报道是否停止等方面考虑情节是否严重。司法实践中应当根据实际情况,将行为人报道不应公开案件信息的行为认定为民事侵权行为或者治安违法行为,未必要一律追究刑事责任。无论学界意见如何,都属于不具有法律效力的学理解释。由于“情节严重”对本罪是否成立至关重要,为防止司法实践中此罪认定的随意性,最高司法机关应该尽快出台司法解释,对“情节严重”作出权威说明。
报道不应公开的案件信息罪牵涉到新闻与司法,关涉自由与秩序,它的增设是价值权衡后的选择,其适用草率不得。即使主张设立该罪的学者也建议对此罪的适用进行严格的限制,如宋英辉教授和赵秉志教授都主张对报道不应公开的案件信息的入罪标准应该严格限定,不能放任,以免扩大打击面。[20]对本罪的构成要件进行明确是立法机关的当务之急,在配套法规和司法解释作出具体规定之前,对本罪的适用也应持谨慎的态度。
[1]曹波.论不应公开的案件信息刑法保护的规范诠释[J].科学经济社会,2017(2):87-113.
[2]张文显.法的一般理论[M].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88:42.
[3]黄小亮.论我国刑法修正的秩序价值优先性[J].法学杂志,2016(3):40-47.
[4]周光权.《刑法修正案(九)》(草案)的若干争议问题[J].法学杂志,2015(5):77-84.
[5]刑法修正案报道披露不公开审理案件是否入罪存疑[EB/OL].http://news.163.com/14/1202/13/ACFCF97O0001124J.html,2017-11-24.
[6]赵秉志,商浩文.论妨害司法罪的立法完善——以《刑法修正案(九)(草案)》的相关修法为主要视角[J].法律适用,2015(1):43-49.
[7]王利明.隐私权概念的再界定[J].法学家,2012(1):108-120.
[8]张兵.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媒体报道的反思[J].新疆警察学院学报,2015(2):67-70.
[9]“披露报道不应公开的案件信息罪”及法律风险分析[EB/OL].http://blog.sina.com.cn/s/blog_3f79a3790102vy9q.html,2017-11-24.
[10]沈德咏.《刑法修正案(九)》条文及配套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15:331.
[11]赵秉志.论妨害司法罪的立法完善——以《刑法修正案(九)(草案)的相关修法为主要视角[J].法律适用,2015(1):43-49.
[12]高铭暄,马克昌.刑法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16:556.
[13]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下册)[M].张雁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297.
[14]贝卡里亚.论犯罪与刑罚[M].黄风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15.
[15]王春媛,廖素敏.性侵未成年人犯罪人与信息登记和有限公开机制研究[J].青少年犯罪问题,2016(6):92-99.
[16]林维.刑法应当如何平等规制律师[J].中国法律评论,2015(2):155-161.
[17]刘宪权.刑事立法应力戒情绪[J].法学评论,2016(1):86-97.
[18]公开披露、报道不公开审理的案件信息罪犯罪构成[EB/OL].http://blog.sina.com.cn/s/blog_491979650102wjqo.html,2017-11-24.
[19]沈德咏.《刑法修正案(九)》条文及配套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15:331.
[20]赵秉志.论妨害司法罪的立法完善——以《刑法修正案(九)(草案)的相关修法为主要视角[J].法律适用,2015(1):43-49.
Commentary and Analysis on"The Crime of Report Non-Public Cases Information"
Yong Ziyuan
(Anhui Normal University,Wuhu 241002,China)
Freedomprotectionandordermaintenanceareall related tothe functionof Criminal Law,the legislative purpose of the crime of report non-public cases information is to safeguard judicial order,it reflects the value orientation that the legislator takes into consideration the priority of social order.The constitution elements of this crime are comparatively inattentive,such as the objective elements of the crime are deficiency,the serious circumstance of no consistent standard,the scope of crime subject should be delimited,the subjective cognition of the crime is not clear.In order to implement the appropriate statutory requirements of crime and punishment,and prevent the abuse of this crime in judicial practice,we should improve the supporting laws and regulations as soon as possible,define the scope and content of non-public cases information,amend and perfect the crime,make clear the component elements of the crime,at the same time,we should introduce judicial interpretation to clear the connotation of the serious circumstance.
News Reports;Non-Public Cases Information;Clarity of Constitution Elements
D924.3
A
1673―2391(2017)06―0016―06
2017-08-20
雍自元(1972—),女,安徽无为人,安徽师范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安徽师范大学博士生,研究方向为刑法学、犯罪学。
2014年度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媒体介入刑事案件审判的时度效研究”(AHSKY2014D06)。
【责任编校:陶 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