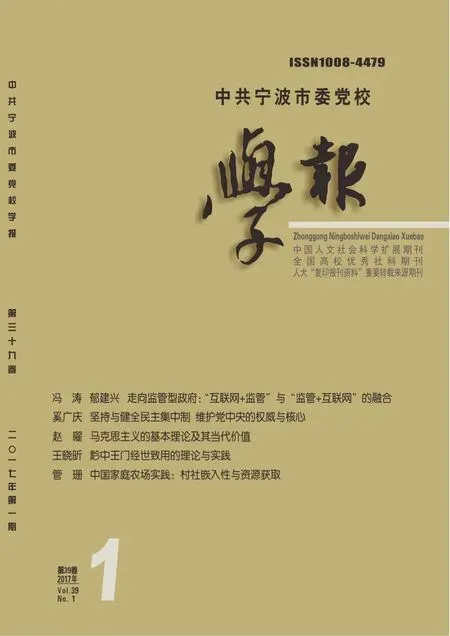社会化媒体环境下我国食品安全风险交流策略研究
——基于CERC的分析框架及运用
孙敏
(中共大连市委党校,辽宁大连116013)
社会化媒体环境下我国食品安全风险交流策略研究
——基于CERC的分析框架及运用
孙敏
(中共大连市委党校,辽宁大连116013)
随着社会化媒体的兴起,风险交流活动延伸至社会化媒体环境中。然而,在食品风险交流领域,现有文献更多关注消费者食品安全风险认知的影响因素,以及如何发展有效的风险交流策略,很少有人深入讨论风险交流媒介,尤其是社会化媒体对食品安全风险交流的影响。实际上,社会化媒体对我国食品安全风险交流带来巨大挑战的同时也蕴涵着难得的机遇,如何利用社会化媒体工具推进我国食品安全风险有效交流,培育公众风险感知,提高食品安全政策决策质量,构建食品安全社会共治体制机制,是当前食品安全领域最迫切的课题。
社会化媒体;风险沟通;食品安全
一、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伴随接连不断的食品安全事件,国家持续加大食品安全治理力度,食品安全总体态势趋好。但广大消费者却感觉食品安全问题越来越多,对政府的信任度越来越低。[1]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与媒体、消费者对食品安全的关注度、期望度都在不断提高有密切关系,[2]但更为重要的原因在于风险交流的缺失,导致科学事实与消费者认知之间,存在“信息真空”。尤其是在社会化媒体环境下,人们获取信息的方式发生了改变。在危机事件中,信息来源不再只依赖于政府或传统媒体,普通公众也能够通过各种先进信息传播媒介如微博、微信、播客、社交网站等转发风险信息,发表对危机事件的看法和意见,引起公众对食品安全这类公共事件的高度关注,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公众对食品安全及食品安全监管的认知,不能理性地看待现阶段的食品安全风险。尤其是各种以讹传讹的伪食品安全事件在社会化媒体海量传播,加之媒体为吸引眼球有意无意地夸大误导,使得食品安全风险被无限放大,引发一浪高过一浪的食品恐慌浪潮,不仅破坏产业可持续发展,引发国际贸易争端、贸易限制,还会损害公众对政府及科学家的最基本的信任。
可见,构建食品安全风险交流机制,促进食品安全风险信息有效交流,无疑是形成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新格局,增进公众对食品安全信心,提升政府公信力的有效途径。近年来,伴随食品安全风险交流压力的加大,我国政府开始重视食品安全风险交流工作,成立了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承担风险评估和风险交流工作,2015年修订实行的新《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也进一步确立了食品安全风险交流制度,标志着我国食品安全治理范式逐步走向成熟。但是在社会化媒体环境下,无论是风险交流参与者的范围,还是风险交流的媒介、方法、路径都发生了根本性改变。作为危机时刻风险交流组织者的政府(相关监管部门),需要整体把握社会化媒体信息开放环境下食品安全风险交流的内涵特征和基本规律,发挥社会化媒体在食品安全风险交流中的积极作用,否则食品安全风险交流会陷入无序、混乱状态,这对于解决当前面临的食品安全问题有害无益。本文采用危机和紧急事件风险(CERC)交流模型,分析了社会化媒体环境下我国食品安全风险交流存在的突出问题,提出了利用社会化媒体改进我国食品安全风险交流的对策建议。
二、相关文献与分析框架
(一)相关文献回顾
最早关于风险交流的研究可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之后风险交流领域得到蓬勃发展。20世纪70年代美国环保署署长威廉·卢克希斯首次提出风险交流的概念。20世纪80年代中期美国建立了一批风险交流的基础研究和应用中心,将风险交流纳入风险研究框架之中。以Covello、Slovic[2]等为代表的学者开始关注风险交流的内涵、功能,他们把风险交流视为“精英向普通公众单向地传递科学和技术信息的过程”,风险交流的功能是告知、说服和教育公众,学者将其称为“科技范式”。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学者对风险交流的关注视角开始从单向传播转到双向互动,以Heath、Witte[4~5]等为代表的学者吸收心理学对“风险认知”的研究成果,开始关注一般民众对风险的看法和认知,着重对风险交流受众开展研究。风险交流研究从“科技范式”向“民主范式”转变。20世纪90年代末,风险交流成为风险研究的重要领域,引起学者广泛关注,社会学、文化学、心理学、传播学等学科的相关理论被引入相关研究中,风险交流研究呈现出多学科交叉趋势,并被越来越多地置于具体学科领域。进入21世纪,风险交流理论获得进一步发展,Seeger(2001)[6]把风险交流分为三个阶段:即危机前(告知风险的相关知识)、危机中(紧急告知风险损害的回避)和危机后(新的风险认知形成),并将重点放在危机前的预防阶段,这一理论后经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进一步发展成为CERC模型。
食品安全风险交流研究是风险交流分析范式在具体领域的应用研究。伴随20世纪90年代末风险交流理论研究的成熟,风险交流被不断引入食品安全风险研究领域,食品安全风险交流研究文献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这些文献大致分为两大类:(1)基于管理学、传播学的食品安全风险交流策略研究。在这一领域Douglas Powell、William Leiss[7]等学者贡献巨大。(2)基于心理学、文化学的食品安全风险认知研究。国外学者对这一领域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包括食品安全风险认知内涵、度量、决定因素以及风险认知与信任、风险交流、消费者行为的相互影响等内容,研究成果颇丰。目前国外学者在这一领域的研究重点是对食品安全风险认知及相关心理与行为变量的实证研究。
近年来,伴随食品安全风险交流压力的逐步加大,国内学者也开始关注食品安全风险交流。刘鹏(2013)[8]研究了风险认知与食品安全风险沟通类别;韩蕃璠等(2013)[9]研究了我国食品安全风险网络舆情的研判和干预措施;展进涛等(2013)[10]研究了食品安全风险交流的创新机制。这些研究从风险认知、网络舆情、交流机制等角度对食品安全风险交流进行了研究,但多数研究强调自上而下的风险信息披露或政府对风险信息的监控,缺乏对互动的社会化媒体环境下风险交流的内涵特征与基本规律的把握,尤其在社会化媒体环境下,基于危机和紧急事件风险交流理论研究食品安全风险交流的新问题并从实践应用角度对解决这些新问题的方法和策略进行研究的还很少。
(二)本文分析框架
本文借用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发展的CERC模型来分析。CERC模型把风险交流大致分为5个阶段:危机前、事件初始、保持、解决和评估。本文结合Seeger(2001)提出的风险交流三阶段模型,把CERC模型中的初始、保持和解决三阶段合并为一个阶段,称为危机中;而评估阶段称为危机后。每阶段仍然推荐采用一套组合交流策略(见图1)。在危机前阶段,风险管理者(风险交流者)要使用传统的交流策略,就风险本身以及正确地避免风险的措施、知识对公众进行教育,包括行为的改变,[11]从而帮助公众形成对风险的普遍认知,对可能发生的不利事件做好准备,改变行为,降低危害发生的概率,这是风险交流的重点环节。在危机发生阶段,要及时准确地指定机构发言人以及官方的交流渠道和方法,就灾害性质的信息、官方动作、个人反应作出建议等内容及时与公众进行交流,并对受影响公众的反馈进行回应,以满足公众的风险感知需求,降低公众的情绪波动,降低危机相关的不确定性,恢复信心。随着危机事件的结束,要对回应妥善性进行讨论,对危机事件中得到的经验和教训进行总结和交流,以便就经验教训和风险认知达成一致观点,让风险交流者为下一次危机爆发做好准备。

图1 危机和紧急事件风险交流模型
三、社会化媒体环境下我国食品安全风险交流面临的突出问题
按照德国学者Andreas M.Kaplan和Michael Haenlein的定义,社会化媒体是指建立在web 2.0的思维和技术基础之上,基于互联网的应用,允许创造和交换UGC(用户生产)。[12]美国学者Antony Mayfield把社会化媒体的基本形态划分为:社交网站、博客、维基、播客、论坛、内容社区和微博7大类。[13]除了这些,本文提及的社会化媒体还包括即时通信、智能手机移动上网功能等。社会化媒体与传统媒体相比,具有传播速度快、传播方式交互性强、传播手段多媒体化、传播主体多元化等特征,这些特征恰好满足有效风险交流所需的及时性、开放性和互动性等要求。所以,利用社会化媒体进行食品安全风险交流,可以将交流内容更好地与危机事件发展进程相融合。如在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件前(危机前或和平时期),可以利用社会化媒体采用图片、视频、文字、声音等多元化方式生动地向公众进行食品安全风险警示,普及食品安全知识及宣传预防措施,让公众做好防范准备。在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件时(危机中)可以利用社会化媒体第一时间通报事件进展、政府采取的行动以及个人应采取的规避损害的措施,并就事件原因、过失、责任进行广泛、诚实、公开的讨论,回应公众的质疑,从而获取公众的支持与合作。在重大食品安全事件结束后(危机后)针对社会化媒体环境下危机事件风险交流过程中获得的经验教训进行开放式探讨,在帮助公众形成新的风险认知的同时改进风险交流策略和方法。
从理论上讲,社会化媒体应是进行食品安全风险交流的一种有效工具,但是在实践中,由于我们的食品安全风险交流理念仍然停留在传统观念上,注重自上而下的单向信息发布,交流模式、方法没有与社会化媒体的信息流动特征相结合,导致社会化媒体的信息交流优势没能在我国的食品安全风险交流中得到充分体现,在依据CERC模型划分的各个阶段都不同程度地遭遇了各种问题。
首先,危机前缺乏利用社会化媒体进行风险交流的常态化机制。依据CERC模型,风险交流的重点应放在危机前的预防阶段,贯穿于日常的风险交流工作之中。尤其是在社会化媒体环境下,媒体或个人往往先于地方政府向公众提供信息。在这种情况下,风险管理者应特别重视在危机前(和平时期)开展食品安全风险识别、防范知识和措施的宣传教育等活动,才能避免在危机到来时,缺乏食品安全常识和专业知识的公众,受到不实信息,甚至谣言的影响,导致政府公信力下降。但是,我们的风险管理者形成了风险交流就是危机公关的灭火器和维稳的思维定势,总是等待危机真正发生后匆忙应急,而没有利用社会化媒体构建常态化的食品安全风险交流机制,没有制定基于社会化媒体风险信息流动特点的食品安全风险交流计划,食品安全风险交流、科普知识普及、风险预警活动通常仍旧凭借食品安全宣传周这样的传统交流工具和平台,这种传统交流工具和平台的显著特点是交流时间集中、非持续性,且覆盖和影响的人群较窄,风险交流的预防、预警和教育的功能难以实现。而具有交流及时性、持续性、方便性、广泛性的社会化媒体平台如微信、社交网站、微博等却没有得到各级食药监部门或其他组织的推广应用。虽然个别机构利用社会化媒体搭建了交流平台,如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中国食品安全报等开通了微信公众平台,但是有些微信公众平台的使用频率非常之低,几个月甚至半年都不见其更新内容;有些微信公众平台只注重单向的发布一些相关法规、政策以及提供某些食品安全风险信息,很少主动对社会化媒体上流传的食品安全风险信息进行收集、评估和分析,使得危机前在社会化媒体中已经暴露出的一些问题食品的“蛛丝马迹”得不到应有关注,更谈不上对公众关注的食品安全问题进行及时、精准的答疑解惑,造成消费者认识的混乱或误解,甚至引发重大食品安全事故,给食品安全事件处置增加难度。
其次,危机中缺乏运用社会化媒体进行风险交流的可靠程序。在重大食品安全事件爆发时,公众往往渴望从权威部门了解事件的情形、性质、后果,以及官方行动和个人如何避免事件危害等信息。社会化媒体恰好是风险管理者及时发布这些相关重要信息,并对公众质疑进行及时回应的一种有效工具。但社会化媒体也可能过快、广泛的传播而把局部、个别的风险信息或危机信息无限放大、扩张,[14]单纯的食品安全危机可能演化为波及范围巨大的产业危机、心理危机和社会危机。因此,在发生食品安全危机事件时,风险管理者必须掌握主动,及时地利用社会化媒体就事件处理进展情况与公众进行充分地沟通和交流,避免其他信息源“先入为主”,干扰公众的认识和判断。近年来,我国政府在应对食品安全危机事件时,回应速度有所加快,应对能力有所增强。但由于没有专门针对食品安全危机事件制定风险交流的可靠程序,没有统一规定食品安全危机事件中的发言机构和交流渠道,不能在第一时间满足公众的信息需求,导致企业、政府、行业协会、媒体都有可能成为“发言人”,且一些机构,尤其是媒体的行动往往快于政府,先于政府发声。当其他声音占据主流时,不管这种声音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政府都会处于被动地位,甚至陷入“塔西佗陷阱”。此时再希望用正确的声音去纠正将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正因为如此,很多时候政府相关部门选择不理会,不发声,认为过了这个风头,就自然会风平浪静。岂不知政府在危机事件前的“躲避”“沉默”,让公众对食品安全和政府的不信任日渐增强。如前不久,有关“僵尸肉”是否存在的“口水战”在社会化媒体持续发酵,正反双方争执不休,难分胜负。而自始至终,相关管理部门要么不出面、不发声,要么前后矛盾。作为最有可能了解真相,最有可能“以正视听”的部门,任舆论汹汹而“不作为”,其结果往往让公众陷入迷雾,无所适从,政府公信力也随之日渐削弱。
最后,危机后缺乏对社会化媒体环境下的食品安全风险交流经验教训进行总结和反思。社会化媒体是一把“双刃剑”,快速海量的风险信息传递会放大风险,造成社会恐慌;但如果把社会化媒体用作风险防范知识、风险监管政策等有益内容交流的有效工具和平台,就既可以增强公众的风险防范意识和能力,也可以提高监管部门的风险决策质量。近年来,社会化媒体已经对我国的食品安全风险交流产生巨大影响,尤其是社会化媒体的使用增强了公众的食品安全风险意识,但是由于参与者绝大多数都是普通公众和新闻媒体、记者,缺乏政府部门、非政府组织(NGOs)以及专家和学者的广泛参与。社会化媒体实际上在食品安全风险交流中更多时候是担任了风险信息传播,以及公众发表对食品生产经营者和政府监管负面情绪的工具和通道,而没有真正成为食品安全科学知识、预防措施、监管法律、政策建议等有益内容交流的工具和平台,尤其是各种有关食品安全的谣言在朋友圈、微博以及一些健康网站泛滥成灾,导致公众因焦虑和担忧而陷入周期性食品恐慌。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风险管理者只注重危机中的事态控制和追责问罪,给舆论一个交代,平息民愤。一旦危机过去,他们就认为万事大吉、高枕无忧,而对于危机应对的妥善性及其经验教训则漠不关心,不对社会化媒体风险交流的有效性进行评估,不对社会化媒体环境下的风险交流经验教训进行总结反思,并在此基础上对社会化媒体环境下的风险交流策略和方法进行改进。
四、改进社会化媒体环境下的食品安全风险交流策略和方法
作为食品安全风险治理的重要手段,风险交流越来越受到各国政府的重视。我国当前应以民间的第三方机构以及相关专家学者为后盾,成立专门的权威性风险交流机构,加快制定食品安全风险交流策略和计划,尤其要利用社会化媒体搭建权威性的食品安全风险交流平台,针对食品安全危机事件的不同阶段采用差异化的风险交流策略和方法。
(一)建立基于社会化媒体的常态化食品安全风险交流机制
建立基于社会化媒体的常态化食品安全风险交流机制,加大食品安全知识的宣传教育,不仅可以改变人们的行为,从而降低危害发生的概率,而且通过日常沟通可以增强风险管理者与公众彼此间的信任,减少危机发生时谣言对社会的伤害。因此,要加强对社会化媒体的信息流动特征和基本规律的认识,顺应社会化媒体作为广大公众获取重要信息来源的趋势,利用社会化媒体如微博、微信等开设一系列官方账号,包括以国家食药监总局为名的管理者账号、以地方政府为名的区域账号、以行业协会为名的行业账号和各种特别活动账号等。在危机前(和平时期),风险管理者、专家学者等充分利用这些账号采用图片、视频、声音、文字等多种形式就风险本身以及正确地避免风险的措施对公众进行日常教育,并推送食品安全相关信息,实现风险交流的预警、预防、教育的功能。加拿大政府的“健康加拿大”(Health Canada)项目引导使用Twitter、Youtube、Facebook等社会化媒体,及时传递有关健康的建议,发布产品召回和产品安全警告信息,推广安全活动。这些有益做法值得我们在运用社会化媒体进行食品安全风险交流时参考借鉴。同时,要通过监测社会化媒体,收集来自社会公众、企业、新闻记者、NGOs等相关利益者的各种信息,包括风险预警信息、咨询信息以及对政府信息的反馈信息。同时与相关利益者建立伙伴关系,围绕风险交流与可靠信息来源开展协作和协调,对谣言或不实信息进行澄清或纠正,对公众关注的食品安全风险信息进行评估,并将评估结果和风险防范措施及时通过社会化媒体风险交流平台发布,提高公众对特定食品安全风险的认知水平和防范意识。
(二)制定基于社会化媒体的危机事件风险交流可靠程序
在社会化媒体环境下,一旦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件,如果权威部门没有利用社会化媒体及时公布事情的真相,其他信息来源就会“先入为主”,公众很容易“信息超载”,不知道该相信什么,极易陷入恐慌和无助状态。因此,需要制定一套基于社会化媒体的危机事件风险交流可靠程序,明确在食品安全危机事件中的发言机构、交流渠道等具体内容。最好把开设的一系列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作为危机事件爆发后的常规交流渠道,由主管食品安全的政府部门或第三方权威机构在危机第一时间客观地公布事件风险程度和进展情况,与公众保持实时联系,诚实回应公众关于风险事件原因、过失、责任等方面的问题,并尽快找出解决方案,向社会公布,获得公众的理解和支持。在这一过程中尤其要注重与公众的双向对话,一方面既要与受到影响的公众保持联系,通过文字、图片、视频等方式实时更新关于事件形势和防范建议的帖子;另一方面又要把公众看成是一种信息资源而非被动受众,在危机中常规性地监测社会化媒体,及时接受公众的咨询信息、求助信息,同时接受公众的反馈信息。
(三)定期总结社会化媒体环境下的食品安全风险交流经验和教训
我国在食品安全风险交流领域还处于起步阶段,尤其是非常缺乏社会化媒体环境下的食品安全风险交流经验,导致我们在鱼龙混杂的信息时代,谣言的力量常常胜于辟谣的声音,科学的声音常常淹没于漫天流言之中。这不利于培育公众食品安全风险感知,不利于形成社会共治格局,不利于食品安全问题的解决。因此,当前必须在建立基于社会化媒体的常态化食品安全风险交流机制和可靠程序的基础上,通过设定“定期回顾”和“重新修订”程序,确保社会化媒体环境下食品安全风险交流的相关经验得到及时的总结,并被吸收到新一轮食品安全风险交流机制和程序修订之中,为下一次食品安全危机事件爆发做好准备。例如在每一起重大食品安全事件之后,要对该事件交流的参与者的身份(公众、官方、NGOs、专家、媒体)、参与者的态度(积极还是消极)、行为(是转发危机信息,评论危机事件、政府行为,还是提出对策建议等)、渠道(微信、微博、社交网站等)进行量化评估,全面分析食品安全风险交流主体特征、渠道类型、交流内容等相关因素,以便整体把握社会化媒体环境下的食品安全风险交流的基本规律,让下一次风险交流有的放矢。同时,要对风险管理者的交流策略和方法进行妥善性评估,将交流中的得失、经验、教训形成书面文字,并进行交流,让新一轮的风险交流机制和程序修订充分吸收这些经验教训,并让这一过程形成统一有效的机制,乃至惯例和文化,经过一轮复一轮的总结——修订——运用——再总结——再修订过程,持续完善我国在社会化媒体环境下的食品安全风险交流策略和方法,提升食品安全风险交流的有效性,促进食品安全问题的有效解决。
[1]罗云波.食品质量安全风险交流与社会共治格局构建路径分析[J].农产品质量与安全,2015(4):3~7。
[2]王常伟、顾海英.我国食品安全态势与政策启示——基于事件统计、监测与消费者认知的对比分析[J].社会科学,2013(7):24~37。
[3]Covello,V.T.,Slovic,P.&vonWinterfeldt,D.Risk Communication:A Review of Literature[J].Risk Abstracts,1986,3(4):172~182.
[4]Heath,R.L.Corporate Environmental Risk Communication:Case and Practices along the Texas Gulf Coast. In B.R.Burelson(Ed),Communication Yearbook 18, 1995:255~277.Thousand Oaks,CA:Sage.
[5]Witte,K.Generating Effective Risk Messages:How Scary Should Your Risk Communication Be?In B.R. Burelson(Ed),Communication Yearbook 18,1995: 229~254.Thousand Oaks,CA:Sage.
[6]Seeger,M.W.,Sellow,T.L.and Ulmer,R.R.Public Relations and Crisis Communication:Organizing and Chaos[A].In:Robert Heath.Handbook of Public Relations[C].Thousand Oaks,CA.:Sage Publications,Inc, 2001:155~166.
[7]William Leiss&Douglas Powell.Mad Cows and Mother's Milk:the Perils of Poor Risk.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 Second Edition 2004.
[8]刘鹏.风险程度与公众认知:食品安全风险沟通机制分类研究[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3(3):93~97。
[9]韩蕃璠等.食品安全舆情研判与处置的思考与实践[J].中国食品卫生杂志,2013(3):279~281。
[10]展进涛等.转基因生物安全的公众隐忧与风险交流的机制创新[J].社会科学,2013(7):39~46。
[11]T.L.赛尔瑙等.食品安全风险交流方法——以信息为中心[M].李强等译.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2012:136~137.
[12]Kaplan,Andreas M.&Michael Haenlein.Users of the Word,Unite!The Changes and Opportunities of Social Media[J].Business Horizon 2010,53(1):59~68.
[13]Antony Mayfield.What is social media[EB/OL]. Icrossing.co.uk/ebooks.
[14]刘丹凌.论新媒体的风险放大机制与应对策略[J].中州学刊,2010(2):253~257。
责任编辑:路曼
D668
A
1008-4479(2017)01-0061-07
2016-01-14
辽宁社科基金项目“辽宁食品安全协同治理机制研究”(L14CGL041)阶段性成果。
孙敏(1981-),女,湖北利川人,中共大连市委党校副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政府规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