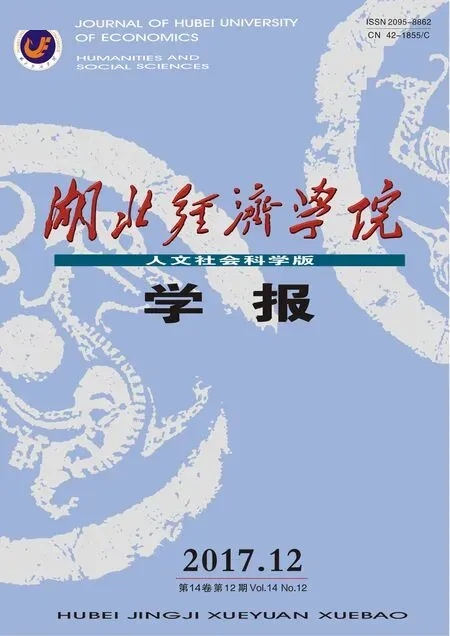从译者的适应选择看“译者中心”
——基于《易经》两英译本对比分析
(广东培正学院,广东 广州 510830)
从译者的适应选择看“译者中心”
——基于《易经》两英译本对比分析
王云坤
(广东培正学院,广东 广州 510830)
基于翻译适应选择论,在整个翻译过程之中,译者适应翻译生态环境,做出适当的选择,将适应与选择集于一身,完成翻译活动。因此,本文将理雅各(James Legge)和汪榕培的《易经》英译本进行对比,从译者对需要、能力和翻译生态环境的适应和选择三个方面进行分析,发现译品之所以产生差异是由于不同的译者为适应不同的翻译生态环境进行不同的选择,译者位于整个翻译过程中的中心。
适应;选择;译者中心;《易经》英译
一、从译者的适应选择看“译者中心”
翻译适应选择论认为,“翻译即适应与选择。”[1]译者集适应与选择一身,二者不可分割,适应中有选择,选择中有适应。选择是一种主动行为,而适应往往被认为是一种被动地接受。但是在翻译活动中,译者并不是单纯被动地“适应”,而是选择性适应,以完成翻译作品,使其能够“适者生存”。而“选择”也不是毫无章法可言,是适应性选择,并受到“译者责任”[2]的制约,从人的视角去审视文本,并实现文本的最终优化。胡庚申认为,适应和选择都是译者的本能[1],是译者为了保证译作的质量,对于译文以及翻译生态环境做出的下意识的、自然的判断,从而体现了译者在原文和译文转换过程中的中心作用。
同一部作品,译者不同,译文也各不相同,可能针对不同的读者群体,可能产生于不同的历史时代,可能不同的出版社出版,但是究其根本,都是由于译者在翻译过程中“适应”和“选择”的不同表现所致。因此,本文重点把握译者对需要、能力和翻译生态环境的适应和选择的三个方面内容,对比分析理雅各(James Legge)、汪榕培在《易经》英译过程中的适应与选择,探讨译者的适应与选择和译品差异之间的关系。
二、译者对“需要”的适应/选择
美国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曾提出需要层次,从最基本的生理需要到最高的自我实现的需要[3]。需要也可分为内部需要和外部需要,译者从自身的需要出发从事翻译活动就是适应了其内部需要。而译者作为社会成员,自我实现就体现在译者能够满足社会的需要。
理雅各被历史悠久的中华文化所吸引,曾对此作出极高评价:“他们的文明和我们的确有所不同,但却绝对不是野蛮文明…中国和其四亿子孙仍然在那里,生生不息,原因就在于人们之中存在着某些道德和社会规范。”[4]而以《易经》为首的四书五经等中国经典就是最好的规范。同时,理雅各作为一名传教士,其职责是在中国传教,向中国人民解释基督教义。理雅各钻研中国典籍,研究如何将基督教义与中华文化相结合,使民众更容易理解,如何向本国传教士介绍中华文化,消除误解,更好地传教。因此为了满足理雅各了解中国文化内涵和完成传教工作的内部需要,为了打破西方世界对于中国和中华文化的误解,理雅各选择了翻译整部《易经》,包括解释,并且还补充了他自己在翻译中的心得体会,解释了他之所以如此翻译的原因。
自从1626年第一本《易经》拉丁译本出版至新中国成立,令人遗憾的是没有一个译本是由中国人翻译。其次,《易经》历史悠久,版本众多,众说纷纭,一些问题悬而未决,影响了其理解与翻译。而近年来考古学家对于甲骨文的深入研究,使这些问题有了新的的突破口,重译《易经》在所难免。此外,《易经》中的许多生活智慧,如阴阳平衡,随遇而安等,这些都和汪榕培先生的生活哲理不谋而合,因而他能够更好地理解其精髓,表达原作的意图。
由此可以得出,不同的译作是不同时代的产物,不同的时代也赋予了其不同的历史使命。译者根据当时的时代背景做出最佳的选择。汪榕培和理雅各选择的原文并非完全相同,理雅各翻译了整本《易经》,包括其经和传,希望能够呈现出《易经》和中国文化的原貌,帮助西方读者理解和更好地传教,而汪榕培则只翻译了《易经》的核心与精髓。
三、译者对“能力”的适应/选择
胡庚申认为,“从译者对‘内’的适应的角度来看,为了提高译品的‘整合适应选择度’的目的,译者总是在可能的情况下,(以消极的方面来说)尽量不译那些自己无把握的,或把握不大的作品;(从积极的方面来说)尽量选择那些与自己的能力相适应、想匹配的作品去翻译。”[1]傅雷先生曾说,“译事…要以艺术修养为根本,无相当之社会经验,无充分之常识,(即所为杂学),势难彻底理解原作。即或理解,亦未必能深切领悟。”[5]《易经》这部儒家经典历史久远,涉及语内和语际两次转换,要求译者具有极强的双语能力,此外,国内外易学界对其的研究和诠释至今还有诸多分歧和争议,这需要译者在中西文化之间游刃有余,对《易经》有独到的见解。
理雅各长时间在中国生活,汉语素养远远高于其他汉学家。海伦·理雅各在其对父亲的传记中曾写到,理雅各曾说“对于儒家经典,我已经具有足以胜任将其翻译成英文的中文学术水平,这是二十五年以上刻苦钻研的结果。”[4]理雅各的治学态度也十分严谨。他在翻译每一本典籍之前都要反复研究不同学派的观点,认真做好记录和注释,仔细推敲,力求使译文更加准确可靠[7]。理雅各在翻译《易经》时就做了附录,解释自己的理解。同时,还有中国学者王韬的锦上添花,使理雅各对中国典籍的把握更为精确。
汪榕培从小热爱文学,所读之书贯穿古今中外。他是一名翻译家,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名作家,用语言表达心中所想。从小培养的文学素养为其日后对典籍的理解和翻译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此外,他研究生毕业于复旦大学,专业知识也十分过硬,拥有了翻译《易经》的双语能力。
译者根据其能力,包括译者的风格,气质,创造性等,选择了所翻译的文本以及翻译的策略。通过对比可以发现,理雅各主要选择异化策略,尽可能不去打扰作者,让读者向作者靠拢,使读者更加接近原文。而汪榕培则选择了归化策略,以目标语或译文读者为归宿,帮助读者更加深入地理解译文,将译文的可读性进一步提升。
四、译者对“翻译生态环境”的适应/选择
翻译生态环境由原语文本,交际意图,译语文化等多个要素构成,且每个要素本身又有不同的维度和程度,而人们又不能满足所有的维度,所以译者主要从语言维,文化维和交际维三个维度进行适应性选择转换。
(一)语言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
对整个翻译生态环境熟悉之后,译者首先应在语言形式上进行适应与选择,实现原语和译语的转换。中国典籍十分讲究遣词造句,译者在语言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可从选词和风格两个方面来探讨。语言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发展变化,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词义的发展变化更是如此,在词语的本义的基础之上,通过联想,进行词义引申。在《易经》的卦爻辞中,应选择其本义还是引申义,译者需要根据自己的理解做出合理的选择。例如:
1.枯杨生稊,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大过·九二)[8]56
James Legge:the second line,undivided,shows a decayed willow producing shoots,or an old husband in possession of his young wife.There will be advantage in everyway.[6]127
汪榕培:a withered poplar tree sprouts;an elderly man marries a wife.Nothing stands in the way.[8]57
在这两个版本中,选词差异最大的是“女”字的翻译与理解。从表面上来看,区别只在于是否强调“年轻”,在翻译中,意义的增减也十分常见,其实则不然。实际上,这关系到译者对于原义和引申义的选择是否正确。“女”字在日常生活中十分常见,根据《汉英双解新华词典》,“女”的意思为“女子,女人,妇女”(women,female)[9], 包扩了所有年龄段的女性, 无论老幼。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词义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根据《古汉语字典》,“女”的本义指未婚的年轻女子[10],在这里应取其本义。“女妻”,意为娶年轻的女子为妻,该卦爻辞用枯杨长出新芽,枯木又逢春来比喻老夫少妻,孕育着新的希望和生机,更为贴切且生动形象。理雅各选择适应中国古汉语的用词习惯,根据词的本义来进行翻译活动更为准确,而汪榕培则忽略了它在原文中的特殊含义。
译者在翻译文学作品的时候,要深入研究原作,尤其是要从整体上把握原作的风格,包括其艺术风格,文体风格和语言风格等,从而从整体上把握译文的整体基调。例如:
2.击蒙,不利为寇,利御寇。(蒙·上九)[8]8
James Legge:in the topmost line,undivided,we see one smitting the ignorant(youth).But no advantage will come from doing him an injury.Advantage would come from warding off injury from him.[6]31
汪榕培:In dealing with the ignorant,violent measures will only do harm,while proper measures will prevail.[8]9
《易经》时代久远,用文言文所书写,多倾向于书面语,和现代白话文的遣词造句的习惯有所不同。在上例中,“击”在理译本和汪译本中分别被译为“smite”和“deal with”。根据《新牛津英汉双解大词典》,“smite”为诗/文用词,意为“strike with a firm blow”[11],文学气息浓厚。 而相比之下,“deal with”只是一个常用语,无法体现古文风格,以及其原文作者深厚的文学造诣。此外,还有《讼卦》上九“或锡之鞶带,终朝三之。”中的“三”被译为“thrice”,《随卦》六二“系小子,失丈夫。 ”中的“系”被译为“cleave to”,意为“黏住”,十分形象贴切。大量古诗文词的运用增添了许多古色古香味,和原文风格更为相符。
(二)文化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
语言是文化的外在表现形式,翻译不仅是两种语言的转换,更是一种跨文化活动,需要克服不同文化之间的障碍,实现双语文化内涵的阐释和传递。《易经》是中国儒家的经典之作,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下面主要从宗教,颜色和称谓三个方面来解读。
宗教文化是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如果说西方世界是由基督教支撑起来的话,中国就是由儒教,佛教和道教所支撑起来的。此外,它极为抽象事物,更难被他人所理解,所以,在有关宗教词汇的选择上,两位译者各有不同。例如:
1.或益之,十朋之龟,弗克违,永贞吉,王用享于帝,吉。(益·六二)[8]86
James Legge:Let the king,(having the virtues thus distinguished),employ them in presenting his offerings to God,and there will be good fortune.[6]187
汪榕培:The king is making offerings to the gods;This is a sign of good omen.[8]87
在上述例子中,两个译本最大的不同在于“帝”字的翻译。理雅各将其翻译为“God”,而汪榕培则把其意为“gods”。其差别远非是否大写和单复数。根据 《新牛津英汉双解大词典》,“God”的含义为“(基督教和其他神论宗教中)宇宙的创造者和统治者,精神权威之源;上帝”,而“gods”的含义为“被崇敬的人”[11]。
与此同时,理雅各在《易经》英译本的前言中也强调,“三十几年来,根据我所掌握的资料,我认为‘帝’,也就是中国人之父,所表达的含义和我们的上帝所表达的含义是相同的,因此我一直将其如此翻译…我也非常高兴地看到许多在中国的的传教士用‘帝’或‘上帝’来代替‘God’。 ”[6]也就是说他认为所有人都是由上帝来领导的,基督教和儒教一脉相承。这并不是因为理雅各对中国文化的了解不够,而是因为宗教信仰很难改变,即使理解其他的宗教也并非一件易事,因而为了使西方读者更容易理解和接受,理雅各根据整个翻译生态环境选择了基督教词汇。
颜色术语除了用来描绘大自然中的五彩缤纷,也可用来表达丰富的感情和文化内涵。
2.龙战于野,其血玄黄。(坤·上六)[8]1
James Legge:The sixth line,divided,(shows)dragons fighting in the wild.Their blood is purple and yellow.[6]21
汪榕培:When the dragon comes to fight in the wildness,blood runs black and yellow.[8]2
其最大的差异在于对颜色“玄黄”的把握。在《坤卦》上六中,阴气太盛,阴极阳来,成为了“假阳”。“阳”象征“天”,也指龙,而“假阳”就象征“地”或“假龙”。当真假龙争斗时受伤,流出青黄色的血。同时“青”象征“天”,“黄”象征“地”,其中也含有中国古代五行中相生相克的道理。但是,由于各个民族的文化不同,其语言中的颜色体系也不同,就可能产生文化空缺,因而没有与中文的“青”这个颜色相对应的英语词汇。所以,理雅各选择适应中国文化,用“purple”这个蓝色和红色的混合体来象征“蓝天”和“红色的血液”的混合体。而汪榕培则是选择了白色和“玄”相对,却没有体现出更多的文化内涵。
(三)交际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
翻译过程中交际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指的是“译者除语言信息的转换和文化内涵的转换之外,把选择转换的侧重点放在交际的层面上,关注原文中的交际意图是否在译文中得以体现。”[1]《易经》的交际意图可分为三个方面。第一层面,《易经》本就为占卜之书,为读者提供信息占卜未来。第二层面是向读者传递语言形式之美。第三层面是通过丰富的词汇表达向读者传递文化内涵和生活哲理。
两个译本基本上都实现了《易经》的第一层交际意图,因为理雅各和汪榕培都翻译了整本《易经》,包括64卦。此外,理雅各还增加了附录,解释他的翻译过程帮助读者理解。
在第二层面,从表达语言形式之美来说,理雅各的目标读者受过良好的教育,他尽力适应原语的生态环境,重现语言规则和语言风格,即使词句晦涩难懂。而汪榕培则不希望受到行文的束缚,尽可能地简化《易经》中的词句,因为他的目标读者是普通读者。
在第三层面,从传递语言的文化内涵来看,理雅各创造性地使用宗教词汇来适应目标文化,根据原语文化来选择适当的词语翻译颜色词汇以体现其文化内涵。而从表达生活哲理来看,汪榕培选择简化句子直接向普通读者讲述生活哲理,而理雅各则向读者呈现《易经》原貌,因为读者受过良好教育,并且希望自己研究《易经》。
五、结论
译者从内部和外部来适应需要,理雅各选择翻译完整的《易经》,并融入自己的观点,而汪榕培则选择翻译其核心。同时,译者为适应自己的能力选择相应的翻译策略,理雅各选择异化策略而汪榕培则选择了归化策略,这都是译者从宏观上的选择。而从微观上来说,译者适应翻译生态环境,在语言维,文化维和交际维三个维度都进行适应性选择转换。理雅各适应了原语的语言规则和语言风格,并尽力呈现原语的文化内涵,还对宗教词汇进行了创造性处理,使目标读者更容易接受,达到交际的目的。
因此,不同的译者之所以会对同一原文创作出不同的译本,究其原因,是由于译者在适应翻译生态环境之后,选择了不同的原语文本和翻译策略,从而导致译文不尽相同,由此可见,在整个翻译过程中,译者是翻译的中心。
[1]胡庚申.翻译适应选择论[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
[2]胡庚申.从“译者中心”到“译者责任”[J].中国翻译,2014,(1):29-35.
[3]马斯洛,著.林方,编.人的潜能和价值[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
[4]Legge,H.James Legge:Missionary and Scholar[M].London:The Religious Tract Society,1905.
[5]陈福康.中国译学理论史稿[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2.
[6]理雅各英译,秦颖,秦穗校注,秦颖今译.周易[M].长沙:湖南出版社,1993.
[7]顾长声.从司马逊到司徒雷登:来华新教传教士评传[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
[8]汪榕培,任秀桦,译.英译易经[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7.
[9]姚乃强.汉英双解新华字典[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
[10]《古汉语常用字字典》编写组.古汉语常用字字典[M].北京:商务英语出版社,1998.
[11]《新牛津英汉双解大词典》编辑出版委员会.新牛津英汉双解大词典[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7.
王云坤(1986-),女,河南安阳人,广东培正学院讲师,硕士,主要从事英语教育以及翻译理论与实践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