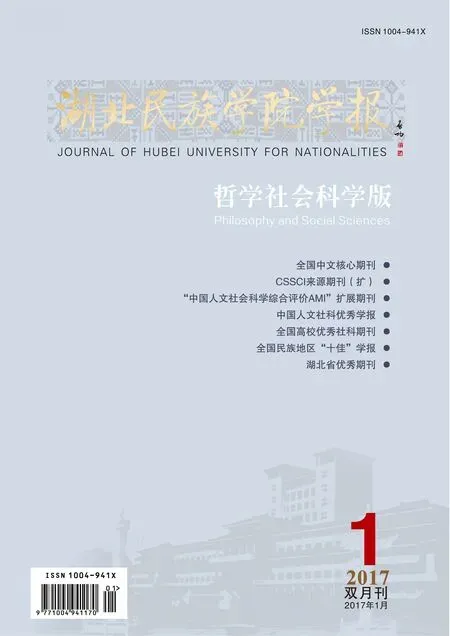西北地区“领羊”仪式的变迁与延续
刘宏涛,张陆良
(兰州大学 哲学社会学院,甘肃 兰州 730000)
西北地区“领羊”仪式的变迁与延续
刘宏涛,张陆良
(兰州大学 哲学社会学院,甘肃 兰州 730000)
学界在仪式过程与仪式变迁方面已有大量研究,但很少关注仪式变迁中的变与不变及其原因。“领羊”仪式曾广见于西北地区汉族葬礼,是葬礼过程中死者与生者进行沟通的重要环节。近年来,“领羊”仪式在部分地区日渐消失。“领羊”仪式在变迁中遗失和保留了什么?为何如此?在比较分析基于观察与访谈所获取的材料后,可以看到布迪厄提出的“现实的表征”这一概念可以较好地解释“领羊”仪式的变迁与延续。
领羊仪式;文化变迁;社会现实的表征
“领羊”仪式广泛存在于宁夏、甘肃、四川地区。[1-3]该仪式大致分为两种,或为飨神,或为祭祖,学者们从不同角度探讨了“领羊”仪式的过程和学术价值。[2-3]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领羊”仪式在甘肃某些地区或在淡出人们的生活,或已消失多年。具有丰富文化内涵的仪式何以消失?在“领羊”仪式变迁中,哪些环节发生了改变,哪些环节依然被保留?为何如此?笔者将以在甘肃靖远地区通过观察与访谈所获的民族志材料来对此加以探讨。
在甘肃靖远汉族地区流行的“领羊”仪式是葬礼上的一个环节。根据以往学者的调查,葬礼大致分为停丧、报丧、招魂、转灯、献饭、渡桥、入殓、下葬及葬后这几个阶段,而“领羊”仪式一般在献饭这一环节之中。[1]这是死者在入土为安之前与生者进行直接互动的仪式。笔者将分别从“领羊”仪式的内涵、“领羊”仪式的变迁来展开陈述,进而在“领羊”仪式的变迁中探讨社会文化的变与不变,并给出理论上的解释。
一、“领羊”仪式的内涵
“领羊”是指死者的儿子、女儿及其配偶等跪在死者的灵柩前,请死者在参加葬礼的众人面前悦纳他们向其奉献的羊。用来领羊的羊被称为“信羊”(即传递信息的羊),它须是被阉割的羯羊。“信羊”将在“领羊”仪式上表达死者对生者的态度。“领羊”仪式开始后,“信羊”会被抹上酒水。若“信羊”只是摇一下头,而并未蹬开四只蹄子,这样不叫“领”。遇此,主持仪式的总理会喊“摇头不算,开毛大领”。所谓开毛大领,是指“信羊”蹬展四蹄,用力甩干身上的酒水,浑身打颤使得毛都抖开。这才叫“领”。“信羊”在被抹上酒之后便“领”了,这叫“干领”;洒了水之后才“领”的是“湿领”。死者领了谁供奉而来的羊,便表明死者对谁满意,没有留下未了的心事或不能原谅的怨尤。死者若未领谁供奉而来的羊,则表明谁不孝或者死者对谁不满意或与他还有未了的心事。遇上“开毛大领”,参加仪式的人都很高兴:死者于他再无任何不好的牵念,可以平顺无忧地行往另一个世界了。
“领羊”仪式虽看似简单,但却包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
其一,“领羊”仪式暗含着当地社会的地域特征。羊肉是西北地区最美味的佳肴。完成仪式后的“信羊”不能再饲养,而要被做成菜肴宴请前来帮忙和吊唁的亲朋好友。由于一场葬礼需要招待上百人,如果没有足够的食物,葬礼难以进行。何况,在当地物资匮乏之时,有钱也不一定能买到食物。“养个女儿,逢年过节买两条烟,买两瓶酒就好得很了,老了还有人拉羊呢”是当地流传的话。它在表明领羊仪式中羊的重要功用。那时候羊肉是最好的食物,以羊肉款待前来帮忙的人,他们也自然会按照主人家的心意稳稳妥妥地将棺材抬送到预定的墓地。按照当地的居住习惯,儿子和父母住在一起。外嫁出去的女儿、外甥女经常是在逢年过节时回来看望老人。在葬礼上,送一只可以用来食用的羊是她们尽孝的一种方式。可见,“领羊”仪式暗含着互惠往来这一朴素的社会文化含义。
其二,“领羊”仪式表达着人们的灵魂观念。“领羊”的时候,主持人让人将“信羊”拉到孝子们围成的圈中,先用点燃的黄纸在羊身上燎一下,这叫“敬一下”,以便将死者的灵魂唤来。请死者领羊的人上前一步,跪在羊身边,给羊的耳朵、嘴巴、四蹄、背部抹上些酒,对着羊说话,请死者接受自己的心意,把羊领了。大部分人认为,“领羊”的时候,死者的灵魂会钻了羊的七窍附到羊身上,若是死者听得满意了,就会抖动羊的身体;也有一少部分人认为,死者的灵魂没有附在羊身上,而是在上房炕上坐着听大家对他所说的话。若是有人说中了他的心意,它就把羊毛一抓,羊就开始抖动了。 如果死者一直不领羊,主持人会把羊牵到灵堂里,让羊见一下死者,和死者接一下气。这样,死者就领羊了。他们认为,这是因为信羊与死者的联系太薄弱或中断了,只要加强它们的联系,死者就会领羊了。由此看到,生者无法与死者的灵魂进行沟通,只能借助工具“信羊”来对话。然而,在“工具”的工具性不足时,则需要加强死者与信羊的联系。总之,尽管“领羊”仪式的具体过程可能存在着各种变通,但一直围绕着当地人的灵魂观念来展开。
其三,“领羊”仪式还是死者表达遗愿的方式。在访谈中,村民ESZ谈到了一个她现在想起来还想哭的事例:
我叔叔死的时候领羊呢,他儿子给他领羊的时候,他死活都不领。亲戚都知道他们家情况不好。他一走,就剩下孤儿寡母了:他老婆的眼睛不好,干不了什么活,儿子年龄也不大。家里住的还是漏风漏雨的土坯房。自己走的早,一定是放心不下孩子和女人。这时候,我叔叔他们兄弟就说一定给娃把房子帮着盖好,娶上媳妇。可是羊还是不领。没办法,他们就去叫了九奶,因为她说话能算数。她到了以后,说会看着他们把说过的话都做到的,让我叔叔放心。九奶说完,羊就领了。
这个事例让我们看到了一位父亲的爱子之情以及未了的心愿。父亲牵念幼子的未来,直到获得了确切的保证后,他才肯领羊。在这个事例中,我们不仅看到了一位父亲最后的留恋,还看到了作为公开展演的“领羊”仪式是将死者的托付以及生者的承诺置于公众的见证之下。
其四,在“领羊”仪式过程中,生者请死者领羊的先后顺序也在表达着当地社会的等级规范。尽管给死者领羊的人有娘家人代表、女儿、儿子,以及他们的子女和配偶等,但是参与的顺序必须先是娘家人代表,然后是女儿、儿子、孙女、外甥女等,按照辈分、年龄大小的顺序进行。娘家人在先,意在表示对娘家人的尊重。然而,娘家人不一定要带一只羊过来,如果没带,主人家还要给娘家人准备好“信羊”。足见舅权在汉族社会的地位。娘家人参与领羊仪式也是在观测死者是否有不为娘家人所知的事。这与报丧时首先通知娘家人是相同的道理。可见,“领羊”仪式不只是给死者领羊,也在展示生者在特定场合的仪式等级。
“领羊”仪式不仅维护着当地社会规范,还是基于人情的对残破家庭的救助途径。相比之下,另外一个事例则从反面表达着这一含义。
64岁的村民KME说,以前有一个老婆子,她的女婿家底特别丰厚,山里放着两群羊,羊都很肥。有一次这个女婿捉了六只羊羔放在骡子拉的车上驮着,顺道看望岳母。岳母招待女婿的时候就想着应该会给自己留下一只羊羔。结果女婿走的时候直接把六只都拉走了,没有留下一只。岳母就十分生气,说:“要是我死了以后他来领羊,我一定要把羊攥死。让他不能上场合”。等到了老婆子死了以后,女婿就拉着一个大羯羊来领羊。结果羊刚拉到大门口就叫了一声跳了三下死了。应验了他岳母生前说的话。人们都说这个女婿平时太小气,六个羊羔子给岳母一个都舍不得给。等岳母死了再拉个羊能有什么用。这个女婿就生气了,问谁家还有羊,要再买一个重新领。别人都劝他算了,太过丢人现眼。你要买我们也不卖给你。她不领羊是有原因的或是你不孝顺,或是对你不满意。旁观的人都谴责这个女婿,认为要是他在岳母生前给她吃一次羊肉也不至于会变成现在这样,白白让人看了笑话。
吝啬的女婿在“领羊”仪式中被记仇的岳母捉弄,女婿在乡亲们面前名声扫地。可见,“领羊”不但有关于死者与生者、过去与现在,再加上一旁看热闹的乡邻,即刻就变成了评判和规范个人行为的标准。
其五,由于死者领羊与否,不在生者的掌控之中,而且“领羊”仪式中死者的意愿是通过生者猜测出来的,这还可能引发出“皮薄人”*这个当地词汇的意思是令人尴尬、难堪,不给人面子。的议论。请死者领羊的人在给羊撒酒之后,就开始说“我是谁,我平时对你挺好的,你给我领吧”之类的话,但羊可能无动于衷。人们一般会接着叙说自己的功劳,希望能感动死者。如果死者还是不领,就说一些自己的过失,让死者知道自己知错了。例如,有的人会说“您看,哪一次我没有来看您。那是因为家里有事,或是娃生病了。你也不要太记挂。” 或者,说自己以后要好好做什么之类的话,希望得到死者的谅解和认可。由于领羊时,还有仪式主持人、其他孝子、旁观的人在一旁围观。他们大多与死者熟悉,也可能听过死者生前念叨过的心愿。在死者一直不肯领羊的时候,他们也会帮忙猜。比如,人们会说:“你看咱们给娘家人先领羊。你老人家领的好,娘家人也高兴。今天你这个事情办的也好。来的人多也红火。现在给女儿领羊呢,女儿的羊一定没有问题。女儿平时把你伺候的又周到又好。不论有多忙,回来首先要把你老人家看一下呢。所以我觉得你老人家也没有什么不满意的。女儿不但在你活着的时候把你伺候的周到。现在你过世了,女儿也拿着很阔绰的东西来送你。你就给这个女儿领一下羊吧”。若还是不领,旁观的人们会猜是死者还有什么事没有嘱咐,或是还有什么放心不下的,或是还有一个家庭困难的小儿子,别的兄弟过得好些,希望他们能多照顾一下这个小儿子。在场的人希望能猜到死者的心意,如果有谁猜对了的话,死者才领羊了。然而,在靖远县朝阳村调查时,村民Z告诉笔者,他爷爷领羊的时候领了大女儿的羊,却无论如何不领二女儿的羊。二女儿就哭坐在地上两三个小时。相邻的人都知道,他二女儿嫁得近,平日里二女儿“一天看个八十遍”,而大女儿嫁在远处,一个月也就来看望一两趟,但结果却是死者不领二女儿的羊。绝大多数村民认为,死者不领谁的羊就说明谁不孝顺,或让死者不满意。在这个事例中,当地人觉得“领羊”也有有违常理、令人难堪的一面。
当然,为了不在众人面前丢脸,人们也想出了多种应对办法。死者若是一时不“领羊”,孝子可以重新敬一下再领,或者孝子再请妻子来做这个仪式。还可以给羊身上洒水,让羊变的易于抖动。有的羊,洒水也不领,酒洒上也不领。主持人就让两个小伙子捉住羊的四蹄,往羊身上洒上水,再把羊放在地上让土粘在它身上。一般来说,羊身上粘了土,它为了抖掉尘土也会抖动身体。如果是女儿“领羊”的话,死者给女儿不“领羊”,就换女婿来敬,若还是不领,就换外孙女来敬。若死者执意不领,仪式主持人就把羊牵到灵堂,把房门一关,说是让羊见一下死者,和死者接一下气。实际上,一进屋,总理就喊“领了”,以便为当事人圆一下面子。
总之,“领羊”仪式不仅是人们通过诉说功劳、忏悔过错、许下承诺等方式猜到死者的心意,以便让死者满意接受献祭,它还是人情的自在表达、社会规范的宣告,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与社会意义。
二、“领羊”仪式的变迁
近年来,具有丰富文化内涵与社会意义的领羊仪式却在甘肃靖远地区慢慢地蜕变和消逝。
“领羊”仪式由原来女儿、儿子等一一请死者领羊,变成了现今的集体领羊。在访谈时,很多村民告诉笔者,虽然需要请死者领羊的人都带来自己的羊,但在“领羊”时只从中选一只羊,所有的人都用那一只羊。因为死者后代的家庭条件不尽相同,孝子们带来的羊也各有大小,有了对比就容易产生一些闲言碎语。然而,在靖远县平堡乡,笔者从当地村民那里得知,当地“领羊”时,主持人会让人把所有的“信羊”都赶到死者的灵前。敬过之后,这群羊中只要有一只羊抖动了身体,就算死者领了所有人的羊。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村民觉得逐个“领羊”的方法不但费时间,而且经常有死者不领的情况出现,最后落得不愉快。现在改为一起领,既快又好。
不唯如此,原来的“开毛大领”也变为即便“信羊”不抖动身体也被认为是“领”。笔者去做调查的时候遇到一场葬礼。在“领羊”时,所有孝男孝女们在灵棚前跪着成一个圈。在主持人喊“领娘家人的羊!”之后,两个小伙子抓着羊角和羊蹄把羊拉到了孝子围成的圈里,主持人点燃黄纸燎过羊,又在羊的耳朵等地方倒了些酒。之后,便说“羊领了,请下一个的羊”。所有人的羊都是这样领过。期间,孝子也没有和羊交流。在此,我们看到,当地人甚至将生者与死者沟通这一核心的环节也省略了。还有的一些乡镇,“领羊”仪式省略的更多。葬礼时,死者的儿女们都会拉羊过来,但却不再举行领羊仪式了。这样,领羊仪式原初的两个意义(带来食用的羊和与死者沟通)只剩下了一半。
然而,尽管领羊仪式在消逝,但“羊背子”却在很多地区出现和流行。“羊背子”即用来代替“信羊”的钱财。如果送了羊就不用送“羊背子”,送了“羊背子”也就不用再送羊了。羊背子和礼钱在主人家的账簿上是两个项目,这也说明尽管它们都是钱财,却代表着不同的含义。女儿、外甥和侄子之类的人,要么带来“信羊”要么带来“羊背子”,二者必选其一,同时还要随上礼钱。在物资短缺的时候,有钱也不一定能买上羊。现在只要有钱,就能买到需要的物品。直接给钱不但方便,而且钱的数目一样,不会引起旁人的议论。当地人认为,用“羊背子”代替羊,说明物质丰富了,是社会进步的表现。
相比之下,甘肃靖远地区的三滩乡是靖远几个乡镇中最彻底不领羊的。当地人说,这三十多年来很少看到领羊了。绝大多数家庭都不做了,只是零星听到有葬礼“领羊”的事。六七十岁的老人回忆说,自己还是十几岁孩子的时候经常跑去看领羊,但是之后就很少有了。随着领羊仪式日渐消逝,追悼会却开始悄然流行。
追悼会在葬礼上出现,并在一定意义上替代了“领羊”仪式的结构性功能。甘肃靖远的有些地方“领羊”仪式和追悼会一起举行,有的地方则只举办追悼会。从当地文化角度来看,追悼会和“领羊”仪式明显不同。追悼会仅仅是生者缅怀死者的仪式,而“领羊”仪式则是生者和死者进行沟通的场合。追悼会是单向的,死者只是被动地参与其中。相比之下,在“领羊”仪式上,不但生者与死者借助“信羊”相互沟通,而且更是死者借助“信羊”在仪式上占主导地位。追悼会令人缅怀死者的成就和功绩,可以顺利地展开;“领羊”仪式中则可能出现甚至激化已有的矛盾、带来尴尬,甚至迫使人们想象死者的忧虑乃至死者家属的困窘。
可见,领羊仪式在靖远地区各个乡镇里日渐变化,它的作用也在不断消弱甚至逝去。为何原本具有丰富文化内涵的仪式会日渐消逝?在变迁的仪式中,有一直在延续的文化内容吗?
三、“领羊”仪式在变迁中的延续
从“领羊”仪式的内涵来看,该仪式主要满足了两个需要:为葬礼提供美味的食物和了解死者最后的心愿。当然,仪式的公开举行,还衍生了社会评价功能以及激发人们参与的热闹场合。
然而,尽管这些因素在变迁的社会文化中日趋衰微,但是西北地区葬礼中“领羊”环节中的变化亦透露着一些不变的社会文化规则。即便与十几年前相比,当今的经济繁荣与资源丰盛已经远远超过了人们的想象。市场经济的发展已经使得人们不再为食品匮乏而烦恼。尽管羊肉依然是西北地区最受欢迎的美食,但经济的发展已经使人们从纯物质的交换中解脱出来,只要有足够的金钱,所有的物质产品皆可在市场中获得。现今的葬礼已经不需要人们用来宰杀的“信羊”了。“羊背子”的出现便表明了这一点。同时,“羊背子”虽然替代了“信羊”,但它们都是乡村社会互助的形式。这一点并未改变。
在“领羊”的先后顺序方面,“领羊”仪式强调按照娘家人的代表、女儿、儿子、孙女、外甥女等姻亲与血亲以及辈分的次序一一请死者领羊,变成了现今的集体领羊。几乎在中国的所有地区,娘家人都会在葬礼上被视为贵宾,而外嫁的女儿也因死者女婿是外人而具有较高的仪式地位。作为葬礼所属家族的姻亲成员,他们比葬礼所在家族的血亲成员的地位更高。这几乎是葬礼仪式中的一种普遍的规则。也因此,作为死者血亲成员的孝子排在他们之后请死者“领羊”。在他之后,又是死者的孙女。死者的孙女虽为死者的血亲成员,但她却同样代表了她所嫁入的家族,即死者的孙女也是姻亲的代表。这样看来,“领羊”的先后顺序分别按照姻亲与血亲的分别以及辈分高低来进行。在“领羊”仪式变为集体进行后,这些顺序的分别被掩盖了。从葬礼所耗费的时间来看,按照先后顺序一一领羊需耗费近半天的时间,而在村民因打工或工作而无法付出那么多时间时,“领羊”仪式被简化了。然而,领羊仪式的简化并未消除血亲与姻亲的差别以及辈分的高低,这些社会文化规则依然表现在葬礼中礼金的数额、礼物的种类、吊唁的顺序等方面。
在如何界定死者是否“领羊”这个问题上,村民将原来认可的“开毛大领”也变为即便“信羊”不抖动身体也被认为是“领”。这即是省去了死者与生者交流的环节,也不再将死者与生者的关系置于公众评议之下。在传统的乡村社会,交通和通信皆难与今日相比。尽管在老人垂危时,晚辈们都会前来照料,但不可能所有晚辈都能陪在身旁。死者的遗愿也可能因此而不为人知。“领羊”仪式恰是在亲人去世之后的又一个相互沟通的契机。然而,今日便捷的交通与发达的通讯已经使得彼此沟通非常简便及时,死者的遗愿也变得更易为人所知。与这一变化具有相同含义的是追悼会的出现。追悼会仅仅是生者表达对死者的哀悼,而将死者的态度排斥在外。这两个细节的变化共同反映了村民将死者与生者的关系从公开变为私密,这与中国社会的个体化遥相呼应。
从当地文化来看,“领羊”仪式是死者在一个公开的场合在众人的见证之下表达自己的遗愿。如果说在安土重迁亲友毗邻而居的乡土社会共同体中[4],人们的隐私观念淡泊,这为公开的表达个人遗愿乃至家庭困窘提供了文化土壤,那么,在现今中国社会的个体化时代[5],人们不再愿意将自己的家事曝光于众目睽睽之下。其实,“领羊”仪式衰微并不是因为人们失去了灵魂信仰,恰恰相反,是人们依然相信灵魂存在,只是不愿意将自己的家事公之于众。在调查中,村民KMR说,当地有一家老人过世,死者的女儿拉着羊来领羊,但死者的长子却坚决不同意。因为死者的长子知道自己的妻子对去世的亲人不好,他担心在请去世的亲人领羊时,先人不领他的羊,以致落人话柄、名声扫地。还有,在“领羊”仪式中可能出现“皮薄人”的情形,这也是个体主义社会所不愿接受的事。“领羊”仪式被追悼会所取代,这也在表明,人们逐渐将由死者主导的仪式转向由生者可控的仪式。可见,在现今日渐个体化的社会,人们更多地关注自身,他们的生活重心已转向家庭之中,而日渐从村落共同体中退出。
由此可见,“领羊”仪式原本的内涵并未完全消逝:奉献“信羊”以为食物的交换功能被同样具有交换含义的“羊背子”所取代;“领羊”仪式的信仰根基——灵魂信仰——依然在人们的生活中发挥着作用。变化的是乡村生活的社会情景,村民从村落共同体的一员日渐成了个体主义的一员。公开展演家庭事务的“领羊”仪式因个体主义在乡村社会的发展而失去了社会条件。
四、小结
在讨论仪式变迁时,有的研究要么是仅仅呈现变化却未分析原因[6],有的提出仪式是根据需要变迁的[7],有的则探讨外来力量对当地文化的改变[8]。其中,有研究者看到生产方式、交换方式等社会基础的变化引发了仪式的变化[9],但却未能说明社会基础如何导致了仪式变迁。
在对其关于区隔的研究进行总结时,布迪厄提出“现实的表征”[10]这一概念。他认为,物品本身转化成了具有区分性的符号。通过此类符号,我们可以看到个体和群体不可避免地在他们的实践中展现出来的表征,而此一表征(representation)又是社会现实(social reality)不可或缺的一部分。[11]更宽泛地说,除了“物品”之外,行为也是具有区分性的符号。作为表征的行为本身也不可避免地展现着社会现实。在“领羊”仪式中,我们看到,作为物品的羊和“羊背子”一样具有区分的作用,它们将那些与死者具有特定关系的人们区分了出来。在这一点上,羊被“羊背子”所取代这的确是一种变化,但不变的是,羊和“羊背子”都表达了相同的社会现实,即死者与生者之间的特定亲属关系与互惠关系。尽管当地人依然存留着灵魂观念,但在“领羊”仪式中省去死者与生者交流的环节、以追悼会取代葬礼等,这些变化反映着社会现实的变化:注重公共生活的无隐私的社会日趋变为个体化的注重隐私的社会。
总之,“领羊”仪式是传统乡土社会现实的表征。“领羊”仪式的衰退与追悼会的兴起恰是在表征着一种正在发生的社会现实:作为共同体的乡土村落在日益衰微,中国乡村社会正在经受着个体化的冲击[5]。尽管社会流动和经济发展为乡村社会文化的变迁提供了条件,文化的变迁却并不直接来源于社会经济的变化,而是村民基于自身对社会经济发展的理解而引发的行为调试。正是在乡村共同体变为个体化的村民所生活的村落时,“领羊”仪式才在社会条件和个体动力的合力下发生了行为细节上的变化。“领羊”仪式中的具体行为虽然在日渐变化,但“领羊”仪式依然受制于经济互惠、亲属等级等社会文化规则。
[1] 董湘漪,孙振玉.山远水长:西北汉族地方性丧葬仪式的个案研究——来自南长滩的田野报告[J].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4).
[2] 马向阳,孙月梅. 酬神仪式:人神间的祭祀“互动”——以西高山乡“领羊”仪式为例[J].四川民族学院学报,2013(4).
[3] 宗喀·漾正冈布,巨浪.甘肃兰州、天水等地“领羊”祭祀仪式的人类学解读[J].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2).
[4] 费孝通.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5] 阎云翔.中国社会的个体化[M].陆洋,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10-24.
[6] 明跃玲.文化互动与仪式变迁:“武陵民族走廊”跳香仪式的田野调查[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2).
[7] 谭志满.从祭祀到生活:对土家族撒尔嗬仪式变迁的宗教人类学考察[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9(10).
[8] 赵孟雄,杨鸿荣.纳西族丧葬仪式变迁及文化象征意义分析[J].思想战线(人文社会科学专辑),2010(S1).
[9] 邢莉.成吉思汗祭祀仪式的变迁[J].民族研究,2008(6).
[10] 王明珂.羌在汉藏之间:一个华夏边缘的历史人类学研究[M].台北:联经,2003:133.
[11] Pierre Bourdieu.Distinction: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ement of Taste[M].Translated by Richard Nic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4:482-484.
责任编辑:刘伦文
2016-12-15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自由探索项目“西部地区社会人类学调查研究基地选点调查”(项目编号:14LZUJBWZY055)。
刘宏涛(1980-),男,河北邢台人,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亲属关系和民间信仰;张陆良(1993- ),女,甘肃靖远人,主要研究方向为民间信仰与社会心理。
C953
A
1004-941(2017)01-0042-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