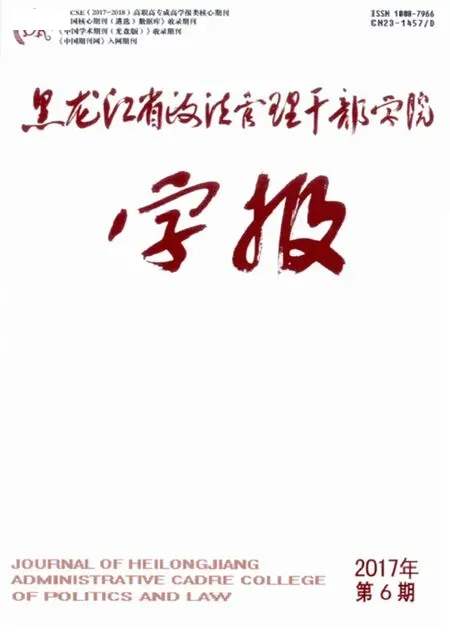论故意在犯罪论体系中的位置
王 珏
(黑龙江大学 法学院,哈尔滨 150080)
论故意在犯罪论体系中的位置
王 珏
(黑龙江大学 法学院,哈尔滨 150080)
在三阶层犯罪论体系的发展历程中,故意经历了由罪责要素到构成要件要素,再由构成要件要素分裂出罪责要素的过程。在三阶层犯罪论体系下,将故意纳入到构成要件阶层可以说已经成为德日刑法理论的多数说。这不仅是行为无价值论的当然结论,而且从修正的旧过失论出发,即使是结果无价值论也与构成要件故意不冲突。相比从构成要件的犯罪个别化机能、目的与故意的关系以及未遂犯的故意等角度入手,从构成要件过失推导出构成要件故意的做法更具有说服力。而责任故意概念的提出导致故意具有双重的机能,使得在解决假想防卫等问题时,理论之间更加的协调。
构成要件故意;责任故意;修正的旧过失论
德国三阶层的犯罪论从贝林——李斯特的古典体系到迈耶、麦兹格的新古典体系的一个重要变化,就是例外地使主观构成要件要素得到承认,而在韦尔策尔的目的论体系下,故意作为一般的构成要件要素得到认可。受结果无价值论的影响,我国学者对主观构成要件要素一直持保守态度,大都仅承认目的犯中的目的和未遂犯中的既遂意思,而将故意与过失仅看作是责任要素。但是,故意与过失作为最重要的主观要素,其体系位置必须要做到精准定位。尤其是故意,其能否被纳入到构成要件中将影响构成要件的机能以及构成要件与罪刑法定原则的关系。另外,如果故意被纳入到构成要件中,其在责任阶段是否还有继续存在的意义,责任故意与构成要件故意分别承担着怎样的功能,这些问题都必须要仔细讨论。
一、肯定构成要件故意的现有依据
将行为无价值二元论作为通说的德国刑法理论很早就将故意前移到了构成要件之中,这毋宁说是肯定行为不法的应有结论。我国一些继受德国刑法理论的学者也开始承认构成要件故意,并且除了逻辑演绎二元论的思路外,还主要提出了以下三点理由:
首先,将故意纳入构成要件阶层有利于区分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实现构成要件的犯罪个别化机能。刑法分则各构成要件规定了各种各样的禁止规范和命令规范(纯正不作为犯),故意也是禁止素材的一部分。这样,故意杀人罪的构成要件所禁止的便是“不得故意致人死亡”,而过失致人死亡罪的构成要件所禁止的是“不得过失致人死亡”。因此,若行为人在行为时没有故意,就不会被卷入故意杀人罪的构成要件之中,如果连过失也没有,则会因不符合构成要件而直接被认定为无罪。罗克辛教授指出,将故意、过失放在构成要件符合性阶层,可以有效地限制行为的不法范围,使构成要件具有了“眼睛”[1]。另外,在日本,始自小野清一郎博士,将构成要件理解为违法有责类型的观点也提出构成要件故意的概念。小野博士指出:“从理论上将构成要件看成是客观的,责任看成是主观的,这样的区别是错误的。道义责任本来就是规范性的东西,应当以被类型化的形式体现在构成要件中。”[2]另外,对于主观的违法要素,小野博士持怀疑态度,然而其认为否定主观的违法要素并不等于直接否定主观的构成要件要素。总之,在该说看来,故意等主观的事情终归不属于违法要素,而承认其作为主观的构成要件与责任要素,于是构成要件的犯罪个别化机能就得以发挥。虽然小野博士没有将故意纳入到行为不法的范畴(主观违法要素),但是从其认为故意属于构成要件要素这一点来看,与罗克辛教授的观点具有一定的相似性。
其次,既然例外承认了目的这样的主观构成要件要素,那么故意也不应被排除在外,因为故意是认定目的的前提条件。我国有学者以我国刑法第265条为例,“以牟利为目的,盗接他人通信线路而使用的,以盗窃罪论处”,如果行为人在使用通信线路时根本不知道自己盗接了他人线路,那么又如何去讨论牟利目的呢?比如说,如果是行为人误接了他人的线路,就没有盗窃的故意,也就根本不存在什么牟利的目的。目的是建立在故意的基础之上的,这样,故意作为目的等主观要素的必要条件,它本身就必须属于构成要件阶层。承认目的犯中的目的属于构成要件却否认故意也属于该阶层,这在逻辑上难以说通[3]。
再次,既然结果无价值论也承认未遂犯的“故意”能够影响法益侵害的危险性,认可了其属于主观违法要素的地位,那么对未遂而言系妥当的见解,也应认为对既遂而言同样妥当。如果某罪的未遂是可罚的,则故意就应当属于其构成要件的内容,因为若没有故意,未遂的客观构成要件(着手以实现所计划的犯罪行为)就会悬在半空中,即当行为人都不知道自己的行为决意时,人们无法判断行为人是直接着手实施行为了还是没有着手。既然如此,就难以理解为什么当未遂发展为既遂后,故意就要失去它作为主观构成要件要素的意义,仅依结果是否发生而对故意做不同的体系评价,是非常奇怪之事[4]。刑法教科书上经常举的例子是,在摆出用手枪瞄准他人的姿势的场合,要是存在实施射杀行为的意思的话,较之于不具有这种意思的场合,杀害的危险要明显高得多,杀害意思是未遂犯成立的不可缺少的条件。据此,根据逻辑上的当然理解,在既遂犯场合只有具有杀人故意才能够符合故意杀人罪的构成要件。
然而,对于肯定构成要件的故意来说,上述理由是没有说服力的。就第一点理由而言,构成要件失去犯罪个别化机能并不是致命的缺陷,在持结果无价值论和违法类型说的山口厚教授看来,犯罪个别化机能可以由构成要件符合性加上故意、过失而形成的犯罪类型这样的另外概念来承担[5]33。罪刑法定原则要求分则各个罪名的内容明确,但这项任务并不一定要由构成要件来单独完成,构成要件具有犯罪个别化机能只能说是锦上添花。而主张第二点和第三点理由的学者,可能存在理解上的错误。首先,故意并不是目的的前提。故意的成立并不只是要求行为人认识到单纯的客观事实,还要对行为的社会意义有所认识[6]。就符合记述的构成要件要素的事实而言,行为人在认识到单纯事实的同时,就能认识到行为的社会意义,但就符合规范的构成要件要素的事实而言,则情况可能会有所不同。以我国刑法第152条的走私淫秽物品罪为例,即便肯定行为人客观上存在走私淫秽物品并且具有牟利或传播的目的,也不能当然地得出其存在故意。这是因为行为人的价值观可能不同于法律法规以及一般人的价值取向,行为人可能不认为其贩卖的是淫秽物品,也不是通常所说的色情物品,甚至认为一般人也不会将这些物品认定为淫秽物品。据此,即使肯定行为人有牟利或传播的目的,也不能肯定其具有走私淫秽物品的故意。其次,所谓未遂犯的“故意”其实说的是既遂意思或行为意思,不能将其与刑法上的故意概念相混淆。举例来说,甲从乙的手中接过一把手枪,以为手枪中没有子弹。如果甲没有扣动扳机的行为意志,致人死亡的危险就比较小,反之则危险会增大甚至产生伤亡结果。但是本例中,甲始终不存在刑法上的故意,即使甲存在瞄准他人的意思,也并不明知自己将要实施的是杀人行为(因为甲以为枪里没有子弹),这样就不存在对杀人罪构成要件的认识。故在未遂犯的场合,是行为意思影响着法益侵害的危险大小,而非故意。
二、以过失的体系地位重新审视故意
故意与过失是犯罪论体系中最主要的主观要素,二者具有相当的亲和力以至于有的学者如张明楷教授认为二者之间存在位阶关系而非对立关系。故意与过失在犯罪论体系上的位置应当是相同的,这一点应当不会有过多疑问。过失犯与故意犯的构成要件不同,其属于开放的构成要件,仅仅什么都不做并不能回答法律对行为人的期待。过失犯必须要关注,为了回避法益侵害结果的发生,需要行为人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即结果回避义务内容的设定问题。这里拟通过以结果无价值论为基础的修正的旧过失论的见解,首先来说明过失属于构成要件要素。
与新过失论主张大量树立行为基准并将其类型化的做法不同,日本旧过失论的代表学者平野龙一博士从重视过失的行为侧面出发,认为过失行为必须包含引起结果发生的“实质的不被容许的危险”,只有当结果的发生是此种行为的危险现实化时,才可以处罚[7]。其进一步指出,当结果已经发生时,再说行为不包含危险已经是不可能的了,重要的是,在行为当时这个危险对行为人来说是不是可以认识得到的,这才是决定有无“实质的不被容许的危险”的关键。而且,行为是否包含“实质的不被容许的危险”,本来也不是可以脱离主观的行为人本人的认识可能性纯粹客观地衡量的。以交通事故为例,A深夜回家途经一条小巷时没有减速慢行,与街口突然冲出的摩托车相撞,导致摩托车驾驶员死亡。按常理来说,事故发生地属于住宅区且已经深更半夜,路上几乎没有人,这样说来A以正常速度行驶的行为本来算不上实质的不被容许的危险。但是如果A知道小巷里开有多家歌厅网吧,每天夜里都有年轻人在此出没,那么A的上述行为就存在实质的不被容许的危险了。而造成这种差异的只是行为人主观认识上内容的不同,客观方面没有发生任何变化。总之,平野博士及其他持修正的旧过失论的学者认为,新过失论基准行为的确立只能回答法的一般期待,结果回避义务的确定不能脱离行为人本人的预见可能性。
但是如果仅仅发展到这一层面,旧过失论还是不能很好地解决现实中的情况。以日本上世纪60年代发生的森永奶粉案为例①该案案情如下,森永乳业公司德岛工厂一直从有信用的药店购买一种提高乳粉溶解度的安定剂“磷酸氢二钠”。但是后来的一段时间,工厂购进了一批与平常购买的品牌不同的,含有砷的“松野制剂”,这种制剂也叫作磷酸氢二钠。加入这种制剂所制造的乳粉后来造成许多婴儿死伤。参见张明楷著《外国刑法纲要》,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40页。,能否认定工厂厂长对“购买其他牌子的同种制剂存在危险”具有预见可能性是存疑的,因为厂长对这种危险只存在危惧感,远远达不到具体的预见,也就难说存在实质的不被允许的危险。我们可以与交通事故做一下类比。只要人们开车出门,就会有发生事故的危惧感,这不可避免,但是认定正常行驶的驾驶者具有过失责任显然是不合理的,不能将其行为认定为具有实质的不被允许的危险。但是森永奶粉案与普通的交通肇事不同,已经属于公害犯罪,受害人众多且社会反响非常大。这就使理论与现实产生了一个矛盾,定罪有违反责任主义之嫌,而由于本案属于公害案件牵涉甚广,不定罪显然不利于社会的稳定。
面对上述这样的情况,井田良教授提出了“预见可能性的结果回避义务关联性”理论。预见可能性不是有或者没有这样抽象地谈论,而必须与所应采取的结果回避措施结合起来确定。要求行为人承担高度的结果回避义务需要具备高度的预见可能性,而为低度的结果回避义务奠定基础的,只需要低度的预见可能性就够了。即使结果发生的可能性极低,但是如果与之相对的,需要行为人采取的也只是极其基础的结果回避措施,就不存在任何问题[8]。旧过失论对这种思考方法是赞同的,但是认为该理论颠倒了结果预见可能性与结果回避义务这二者间谁决定谁的关系。从结果无价值论出发,既然是对结果、对法益侵害的惹起追究责任,那么仅存在对行为和义务违反的认识是不够的,行为人对一定构成要件事实的认识可能性是要求他采取结果回避措施的前提,只能就行为人能够认识到的内容与程度去划定结果回避义务的内容,而不能相反。回到森永奶粉案来,即使认为厂长对购买其他品牌的制剂所可能造成的危险只有危惧感,也不妨碍其要采取极为基本的回避措施,如向制剂厂家询问两种制剂是否完全相同或对用新制剂生产的奶粉样品先行进行卫生安全检测等等。厂长连这种极其基本的回避措施都没有实施,就不能说其不存在过失。
如果将旧过失论上述的思路极端化,在行为人对行为的危险没有任何预见可能的场合,就不能对行为人课以任何的结果回避义务。也即,在无过失的场合,应当认为行为人没有违反结果回避义务或者说行为所创出的危险是被允许的,因此就不符合过失犯的(开放)构成要件,进而不违法。以此逻辑来看,过失的有无影响着行为的违法性,无过失则不违法。而作为与过失存在位阶关系的故意则是另一头的极端表现,也即行为人对行为可能造成的危险与结果存在极高的预见可能性,导致法律对其课以的回避义务也非常之高,即要求其不为或停止为正在实施的行为。只是“不为”在故意犯中是必然的、固定的,是实行行为的反面,没有特别检讨回避义务内容的必要。但正是行为人没有“不为”(实施了实行行为),才导致故意行为的危险转化为实害或紧迫的威胁。可以说,人们在考察故意犯的成立时,更多的是关注结果或危险的发生以及因果关系,而忽视故意犯既定的结果回避义务(不为)这一行为侧面。这也无可厚非,因为既然实施了分则构成要件规定的实行行为,就表示行为人确实没有履行“不为”的结果回避义务。而且这导致故意与过失的行为侧面的功能不同,故意犯的结果回避义务是确定的,并且其没有履行义务也是确定的,故起不到限制故意犯成立的作用。但是不能因为结论的必然性就否定结果回避义务在故意犯中的位置。可以说,上述情形产生了“聚光灯”效应,故意的结果回避义务始终处于阴影之中,不容易被发现,但绝不是自“舞台”消失。即使是故意犯,也不能认为行为人缺乏期待可能性,法律仍然期待行为人规避结果的发生,中止犯的规定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故在笔者看来,过失犯中,由于行为人对行为的危险性具有预见可能性,就应当采取相适应的结果回避措施,行为人未采取措施导致法益侵害结果的发生,在罪刑法定的范围内要受到处罚;故意犯中,由于行为人明知行为可能导致结果的发生,故应采取高度的结果回避措施,行为人未采取任何措施导致法益侵害结果的发生,应按照分则的规定受到处罚。
总之,通过类比过失的构造来推及故意的构造,进而推出故意属于构成要件要素的结论,这种思路应当比前述的几点理由更具有说服力。
三、对构成要件故意的批判与回应
在我国,学者们专门针对置于构成要件中的故意进行了批判,这种批判主要来自于结果无价值论者的体系性结论。但是通过上文的分析,应当认为即使是结果无价值论也可以包容构成要件的故意。
首先,如张明楷教授批判道,如果将故意、过失作为主观的违法要素进而成为构成要件要素,那么就必然陷入犯罪的整体考察,从而损害构成要件的罪刑法定主义机能。换言之,犯罪论体系基本上就会演变为“构成要件符合性——违法阻却——责任阻却”。这种体系将成立犯罪所需要的绝大部分积极要素全部纳入构成要件这一个阶层之中,将导致对犯罪的综合整体的考察,不利于约束法官裁断[9]92。如果将故意、过失这种需要积极判断的主观要素纳入到构成要件之中,确实会使得构成要件阶层承担更多的内容,而使违法和责任阶层所要讨论的内容变少。我国的四要件犯罪构成就因为是平面地考察各个要件而受到了整体性考察的诟病,导致犯罪构成的限制机能不佳,从而引起了阶层式犯罪论体系的主张与提倡。故将故意和过失再次纳入构成要件阶层,在我国学者中引起是否接近于四要件论的忧虑,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笔者认为之所以担心主观构成要件会引起整体的考察,出现主观不够客观补、客观不够主观补的危险,乃是因为担心主观要素置于客观要素之前或二者缺乏明确的判断顺序。即便将故意、过失纳入到构成要件阶层,也要严格遵循客观先于主观的判断顺序。这个审查顺序是符合逻辑要求的,因为只有存在了客观构成要件,主观构成要件尤其是故意才能有所指。另外,阶层式犯罪论体系较之四要件理论最大的不同在于明确区分了违法与责任(而不是在不同阶层限定主观与客观),正是因为如此才导致在处理赃物犯罪、犯罪参与等疑难案件中,二者会得出不同的结论。即便将故意过失纳入构成要件阶层,构成要件符合性、违法性、责任这样的三阶层也并没有崩溃,故只要明确构成要件阶层中的主客观判断顺序,就不会影响对案件定性的精准性。
其次,张明楷教授认为,将故意、过失作为构成要件要素,意味着只有故意、过失实施的行为才具有违法性,这显然不利于国民行使防卫等权利。例如,当甲面对精神病人乙正在杀害自己时,因为乙缺乏构成要件故意,不具杀人罪的构成要件符合性,甲不得防卫[9]93。受侵害者能否针对精神病人实施正当防卫,这一问题确实具有实务意义,应当分情况考察。第一,我们应当明确的是,即使精神病人属于无责任能力人,也并不意味着就一定没有故意。责任能力包括辨认能力和控制能力,只有在丧失辨认能力的场合才不可能存在故意,而在有辨认能力但丧失控制能力的场合,是有可能肯定故意的存在的,此时也就存在行为不法。第二,在精神病人缺乏故意(或过失)的场合,应首先考察是否属于原因自由的情况。在原因行为时存在故意或过失而在结果行为时丧失对法益侵害的认识可能性时,按照山口厚教授的看法,可以认为结果行为尚不足以阻断原因行为与结果之间的因果性,原因行为即便介入了结果行为仍对构成要件结果存在支配,从而具有正犯性,而事实上引起了构成要件结果的结果行为,是被作为来自于原因行为的因果经过的一个情形来把握的[5]258。也就是说,精神病人所实施的无故意的侵害可以被视为是有故意或过失时的原因自由行为所导致的因果经过历程,对此应认为可以进行正当防卫①举一个极端的例子,即便行为人在开枪对他人实施射杀行为后瞬间丧失责任能力和故意,也不妨碍他人可以在子弹飞行过程中将其截住。。第三,即便精神病人既无故意也无过失,也不属于原因自由行为,其侵害行为不能被认定为违法时,人们也可以通过(防御型)紧急避险来规避危险。从我国刑法第21条第一款关于紧急避险的规定来看,其并没有对避险的对象做出明确的规定,完全可以将防御型紧急避险的情况纳入进来。行为人因非违法行为而客观上造成侵害的情形同样属于“危险正在发生”。虽然适用紧急避险会招致其适用要件要严于正当防卫的谴责,但是在面对不法侵害与合法侵害时采取不同的措施毋宁说是理所当然的。而且,即使是正当防卫,也要受到必要性和相当性的限制而不能采取过激的防卫措施,所以在面对精神病人的侵害时,正当防卫和紧急避险的实际效果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大。
再次,存在对客观构成要件该当事实的认识与容认的话就存在构成要件的故意,由于对违法性阻却事由该当事实的误信并不影响构成要件故意的存在,但为了否定故意犯的成立,就会进一步要求作为责任要件的故意,在假想防卫的场合,责任故意会被阻却。而在行为人存在过失时,在阻却责任故意后还得重新进行过失犯的构成要件该当性的判断。这就意味着在经过了构成要件、违法性和责任的评价之后,再次回到了构成要件的评价,这被学者们称为回飞镖现象[10]。如果采取严格责任说,认为违法性阻却事由的认识属于违法性认识,那么对违法性阻却事由该当事实的误信就与故意无关,而是在违法性意识这一责任要素中解决,从而避免了上述问题。但是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判例中出发,严格责任说都是存在问题,应当将违法性该当事实纳入到故意的认识对象中。对此,就像上文所提到的,应当认为故意与过失是位阶关系,构成要件的故意实质上包含着构成要件的过失。虽然这样做仍会产生回飞镖现象,但是大体上能够说明何以肯定过失犯的构成要件该当性。笔者认为,回飞镖现象并不是重要的问题,重要的是构成要件故意与责任故意的关系,对此有必要予以详细说明。
四、责任故意的独立化
原来的刑法理论在采取不法与责任区分的体系下,通常认为违法性意识属于责任的内容,亦即持限制责任说。这固然没有错,但是因为需要处理假想防卫的问题,主流见解在限制责任说的基础上作了修正,将违法性意识与责任故意都在责任阶层讨论,这被称之为法律效果转用之责任说[11]。原本,限制责任说就将事实意义上的、作为心理要素的故意,与责难意义上的、作为评价要素的不法意识相区分。而该说对故意进一步做了区分,分为构成要件的故意与责任故意。大塚仁教授对此解释道,不属于直接对具体行为人施加责难而属于对事实的反映的描述性要素,应列入构成要素的范围内;而关于违法性事实的表象,作为关于规范性事实的心情,考虑到其接近于违法性意识,将其作为责任故意的要素是妥当的[12]。
在现今的德国,故意具有双重机能已经成为主流的见解。将故意理解为主观的构成要件要素并不必然导致故意在责任领域就没有任何意义。毋宁说,故意在犯罪体系中需作为举止形式和责任形式来实现双重的功能。责任故意在责任领域是犯罪行为的思想非难的载体,作为责任的形式,其体现为行为人针对法律中举止规范的法敌对态度和法冷漠态度。而构成要件故意只是为责任故意这一责任类型提供可被反驳的征表,当行为人行为时误以为存在正当化事由的事实,这个征表即消失[13]。也就是说,事实性故意的存在,是推定责任故意存在的前提,但这种推定是一种可被反驳的推定,就好比构成要件可以推定违法性但二者属于不同的阶层一样,构成要件故意与责任故意也分属在不同的阶层。
总之,法律效果转用之责任说之所以区分构成要件故意与责任故意,并使构成要件故意先于责任故意,实际上是区分了事实性故意与价值性故意。在正当化前提事实认识错误的情况下,尽管存在事实性故意,但因为不成立价值性故意,故应当予以减轻或免除责难,不应承担故意的罪责和刑罚。至此,我们可以看到,随着犯罪论从(新)古典体系发展到目的论体系又演变为新古典与目的论相结合的体系,故意也从单纯的责任要素发展为构成要件要素进而又演变为具有双重地位,并与违法性意识划清了界限。
我国刑法第14条规定:“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并且希望或放任这种结果的发生,因而构成犯罪的,是故意犯罪。”对此,有学者认为,该条中规定的是一元化的故意,与德日学者将构成要件故意仅理解为对事实的认识的做法冲突,故我国没有划分构成要件故意和责任故意的余地[14]。还有学者认为,该条规定的是一种实质的故意,已经包括了非难可能性的要素[15]。首先,不论是在我国还是在德日刑法中,故意都是由认识因素和意志因素构成的,不能将构成要件中的意志因素等同于责任故意,二者分别是对事实和价值的判断。就以假想防卫来说,在事实层面,防卫者认识到自己在实施杀人或伤害行为,对此也存在容认,也即不得不说防卫者就是想杀死或打伤“不法侵害者”,只是以为自己是在正当防卫。况且,即便是正当防卫,也不能否定防卫者的认识因素和意志因素,即不能否定防卫者存在事实上的故意。其次,至于张明楷教授的观点,则代表了古典犯罪论体系的理念,即故意包括“对构成要件的认识(知)、实现构成要件的愿望(欲)、认识到实现构成要件将与社会敌对(不法认识)”。虽然我国刑法第14条可以按上述这样理解,但是陈兴良教授合理地指出该条其实规定的是“故意犯罪”而非“犯罪故意”[16]。故意犯罪和其他犯罪类型一样,必须要具备全部的犯罪成立要件,当然也包括违法性意识,而犯罪故意只是犯罪成立的主观要件。况且将违法性意识纳入到故意中,认为其等于责任故意也是有问题的。责任故意针对的是违法性事实的表象,是行为人对规范性事实的心情,属于规范评价的范畴,这虽然与违法性意识相似,但是后者与事实二字完全没有关系,是全然的规范的产物。“我知道我在杀人,也知道杀人违法,但认为我所实施的杀人是正当防卫”与“我知道我在杀人,但认为杀人本来就是合法的”。将两者相进行直观的比较,就能够看出责任故意所对应的违法性该当事实与违法性意识所对应的法律规定存在质的差异。违法性该当事实的认识错误要视场合才能发生,只有在特定的事实背景下才可能出现此种认识错误,只不过这种事实受到了法律评价的洗礼,具有一定的规范色彩。而违法性的错误则与具体案件事实无关,可以说理论上在任何案件中都可能发生违法性错误。
在笔者看来,我国刑法就故意的概念问题也应当向德日刑法的观点看齐,这在法条上没有任何障碍,也没有必要一定要坚持实质故意的概念,毋宁说是现有学理的执拗导致我们还处于18世纪古典犯罪论体系阶段。并且在我国还处于四要件犯罪构成模式主导下的现在,承认故意的双重机能也是向着阶层式犯罪论体系前进的一大步,有助于培养公民的法律规则意识,况且多出一项责任故意,也有利于罪责范畴的限制机能的发挥。
五、结语
我国刑法学者虽然已经接受三阶层的犯罪构成体系,但一部分人仍将故意、过失作为单纯的责任要素,忽视了故意、过失的行为侧面,而另一部分认为故意属于构成要件要素的学者大都是从行为无价值论出发,以故意、过失会影响行为不法为由,将其认定为主观违法要素继而进入到构成要件阶层。在笔者看来,从修正的旧过失论出发,可以推导出,即使是结果无价值论也不应将故意、过失排除在构成要件阶层之外的结论。肯定构成要件的故意会强化构成要件的诸多机能如保障机能、犯罪个别化机能,并无碍于故意规制机能的发挥,也并不会导致犯罪的整体评价以及诸如减损正当防卫范围这样的问题的出现。另外,考虑到故意的事实侧面和规范层面,以及实务中合理处理假想防卫的需要,区分构成要件故意与责任故意是必要的。责任故意是对行为人进行非难的要素,其以构成要件故意为前提,并且与认识因素和意志因素无关,其关注的是行为人的法敌对意思或法冷漠意思。将故意进行如此的剖析后,将使得三阶层犯罪论体系的内部结构更加清晰明了,使理论与理论之间更加协调,也使得实际案件能够得到更合理的解决。
[1][德]克劳斯·罗克辛.刑事政策与刑法体系[M].蔡桂生,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65.
[2][日]小野清一郎.犯罪构成要件理论[M].王泰,译.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4:15.
[3]蔡桂生.构成要件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227.
[4][日]前田雅英.刑法总论讲义[M].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1988:113.
[5][日]山口厚.刑法总论[M].付立庆,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6]张明楷.刑法分则的解释原理(下册)[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830.
[7][日]平野龙一.刑法总论Ⅰ[M].东京:有斐阁,1972:193.
[8][日]井田良.変革の時代における理論刑法学[M].东京:庆应义塾大学出版会,2007:150-151.
[9]张明楷.犯罪构成体系与构成要件要素[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10][日]西田典之.日本刑法总论[M].王邵武,刘明祥,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13:184.
[11][德]乌尔斯·金德霍伊泽尔.刑法总论教科书[M].蔡桂生,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281.
[12][日]大塚仁.论故意在犯罪论体系中的地位[M]∥陈泽宪.刑事法前沿(第6卷). 李世阳,译. 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12:139.
[13][德]约翰内斯·韦塞尔斯.德国刑法总论[M].李昌珂,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230.
[14]彭文华.德日犯罪构成体系与我国刑法规范的内在冲突[J].法学,2010,(5).
[15]张明楷.刑法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208.
[16]陈兴良.规范刑法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160.
[责任编辑:范禹宁]
D914.1
A
1008-7966(2017)06-0024-05
2017-05-05
王珏(1990-),男,黑龙江哈尔滨人,2015级刑法学专业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