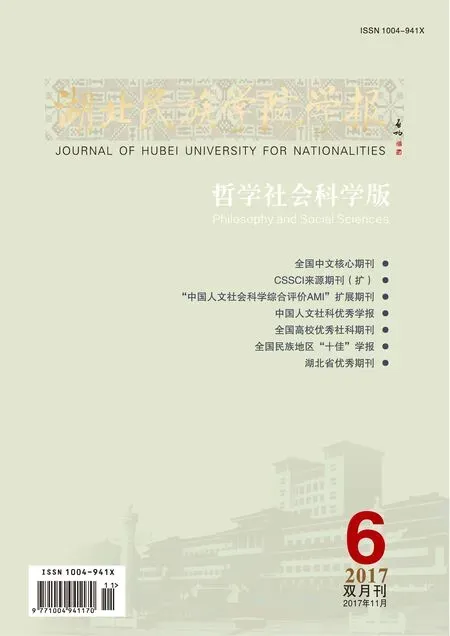苗族银饰的文化生态与传统工艺的保护
——基于湘黔苗族地区的案例比较
李若慧
(中南民族大学 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4)
苗族银饰的文化生态与传统工艺的保护
——基于湘黔苗族地区的案例比较
李若慧
(中南民族大学 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4)
苗族银饰成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以湘西与黔东南苗族的银饰制作加工工艺为代表。随着改革开放以来发生的社会变迁,这两个地区银饰工艺的保护和传承表现出“本土自觉中的文化保护”与“政府推动下的文化保护”两种模式。由银匠的生存境况与当地人的银饰观念构成的文化生态是促成这两种模式的原因。而文化生态受制于特定地区的社会历史条件,结合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来思考如何在不同的文化生态环境中进行银饰工艺保护,可以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提供新的思路。
湘黔苗族;银饰工艺;文化生态;文化保护
一、引言
苗族银饰是苗族文化的象征,其中尤以湘西苗族银饰与黔东南苗族银饰为代表。2006年,苗族银饰锻制技艺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就银饰锻制技艺的保护和传承方面,很多学者对它进行了研究。曾任贵州省博物馆馆长的苗族学者李黔滨,基于省博物馆收藏的苗族银饰做了较详细的梳理介绍,就文物保护而言具有一定的意义。[1]另有学者以湘西或者黔东南为固定区域作为其研究对象,或者关注银饰文化[2],亦或关注银饰锻制技艺本身[3][4],而缺乏对这两个区域进行比较的视角。同时,这些研究还缺乏将银饰工艺置于作为制造者的银匠与作为使用者的当地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中来考察。银饰工艺的保护与传承直接由银匠的生存处境决定,而银匠的生存处境主要受当地人的银饰观念所影响。
苗族银饰的工艺保护和传承情况在湘西和黔东南这两个地区有什么异同?如果银饰有生命,它所处的文化生态*张建世在《黔东南苗族传统银饰工艺变迁及成因分析——以贵州台江塘龙寨、雷山控拜村为例》一文中试图证明传统银饰工艺在现代社会存在“兴盛”和“变异与延续并存”两大变迁模式,并认为不同的变迁模式均由各自的文化生态所决定。该文化生态在其文中包括银饰的佩戴习俗以及社会文化环境要素。参见张建世.黔东南苗族传统银饰工艺变迁及成因分析——以贵州台江塘龙寨、雷山控拜村为例[J].民族研究,2011(1). 笔者希望在本文指出,文化生态受制于特定地区的社会历史条件,该社会历史条件不能被简单地囊括在“社会文化环境要素”中。有何不同?换句话说,生活在这两处区域的苗族银饰制造者——银匠的生存处境有何不同?购买和使用银饰的当地人的银饰观念有何不同?根据前期对于这两个地区的长期调查,笔者发现这两个区域的案例具有很强的可比性。笔者认为,对这些问题的关注将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银饰锻制技艺保护中保护的是什么,并思考下一步应该如何进行保护。
湘西和黔东南两片苗族聚居区分散着一些著名的银匠聚集村镇,主要有贵州雷山县西江镇和台江县施洞镇,以及湖南湘西凤凰县山江镇和禾库镇的德榜村等。随着社会的变化,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变迁,这两个地区银匠们的生存处境以及当地人佩戴银饰呈现出不同的境况,银饰工艺的保护和传承现状表现出不同的模式。其中主要表现为“本土自觉中的文化保护”与“政府推动下的文化保护”两种模式。
二、本土自觉中的文化保护
施洞位于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台江县境内,在历史上,施洞苗族并不属于人类学惯常研究的“无国家社会”的部落形态。雍正年间“改土归流”之后,伴随着“清水江疏浚”,清水江流域与外界产生了以“木材流动”为主要形式的大量贸易往来[5],这标志着清水江流域沿岸苗寨与内地的中央王朝发生了某种联系,也标志着此处苗族被逐渐纳入到中央王朝的直接管理体系当中。[6]施洞作为清水江干流上的贸易重镇,“台拱辖境。后倚高山,前临清水江,中饶平衍,周数里”[7]。苗语称之为“展响”,意为贸易集市,可以想象当时外来的汉人客商与走出邻近大山的苗人通过白银进行贸易的杂处场景。而在当代,施洞银饰被黔东南银饰加工界公认其银饰“造型最为华丽、工艺最为精湛”。与黔东南西江镇控拜村的苗族银饰相比,施洞苗族银饰仍延续使用传统工艺与纯正的原材料。[4]1994年贵州省文化厅将施洞命名为“刺绣银饰剪纸艺术之乡”。2013年它被列为贵州省“5个100工程”的21个重点建设的旅游景区和30个重点建设的省级示范小城镇。
塘龙寨是施洞镇的一个自然村,也是有名的银匠村,均为吴姓。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这个村只有五户银匠。据施洞镇的人说,塘龙现在家家户户都会打银饰,是施洞镇最富有的村寨。除了塘龙寨,其他寨子也有银匠,但是没有塘龙那么集中。施洞镇有两名年纪最长的银匠——塘龙的吴通云与方寨的刘永贵*两位银匠现已年近八旬,刘永贵于2017年夏天突发脑溢血不幸去世。。吴通云精于钻工,刘永贵精于花丝工艺。*钻工和花丝工艺是苗族银饰工艺的特色。两位银匠均不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甚至不是州级非遗传承人,*施洞镇塘龙有一个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吴水根,是吴通云的侄子也是他的徒弟。据笔者调查,施洞当地人普遍不找吴水根打制银饰,吴水根的主要社会活动是对外宣传和展演苗族银饰工艺。但他们在当地家喻户晓,并经常被外界作为施洞银匠的代表。笔者从2011年开始,对两位银匠以及他们的后代有持续地跟踪调查。银匠从事银饰工艺的生命历程体现了他们对苗族银饰以及银饰工艺的态度,从银饰锻制工艺保护与传承的角度出发,笔者认为,探寻两位银匠对苗族银饰以及银饰工艺的态度,即追溯两位银匠制作银饰技艺的个人经历,可以为我们展现出改革开放以来黔东南施洞银匠的生存处境。
由于“四清”和“文革”期间,制作银饰即他们所谓的“打银子*施洞人将银饰称为银子,因此“打银饰”也被称为“打银子”。”被认为是“投机倒把”的行为,两位银匠不得不表面停止了这项手艺*虽然“四清”和“文革”期间不允许公开打制银饰,但刘永贵和吴通云在采访中告诉笔者,他们也有私下偷偷地打。。改革开放之后,据他们口述,“打银子”这项活计至今就从未间断过。
1983年,贵州省博物馆准备陈列一组苗族服饰展,考虑到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雷山县西江镇与台江县施洞镇两个地方的银饰工艺最有代表性,博物馆工作人员在这两个地方邀请了几位当地有名的银匠到省博物馆制作“苗族银饰”。刘永贵与吴通云作为施洞银饰手工艺者的代表,为省博物馆打制了 “具有施洞特色的苗族银饰”*贵州省博物馆退休工作人员吴仕忠在采访中对笔者回忆1983年他从西江与施洞各邀请几位银匠的经历时所言。,其中包括银牛角、龙纹银项圈、浮雕双狮戏球纹银挂牌(也称为银压领)、S型绞丝银项圈等。
两位银匠一直钻研于银饰技艺,对银饰技艺赋予极大的热情,坚持每天加工,笔者多次采访都在二位银匠的制作过程中进行。二位银匠由于年龄相仿,有着相似的经历:1983年同时被省博物馆请去制作具有施洞特色的银饰、同时被评为“贵州省十大民间工艺大师”,均被清华大学工艺美术学院邀请给该院学生上课,还受北京服装学院邀请去北京学习交流。在刘永贵看来,1983年在贵州省博物馆做的工艺并不是最好的,好的工艺是在他们去北京服装学院学习交流之后。自这次学习交流后,他开始思索,“以前做的都是平面的图案*苗族银饰的特点是只能做平面图案,即将花丝镶在一个个银片上。,”这次的学习交流让看到了故宫里陈列的“皇宫贵族”使用的金银器。这些金银器采用的镂空雕琢工艺,让他开了眼界。回到施洞后,他开始尝试制作錾花镂空工艺品。
即便錾花镂空工艺不能用于苗族女人身上佩戴的银饰上,只能将其用于摆放的装饰品中,他仍然坚持用这种工艺制作。与很多游离于商业与艺术之间的艺术家一样,经过他劳动创造的产品最终需要投向市场。他自己很清晰地认识到,机器制作的银饰无法替代手工制作,因为手工制作的银饰更值得“收藏”。
刘永贵大部分时候还是制作苗族银饰,在做苗族银饰时,他坚持慢工出细活。因此在施洞当地,村民们都称赞他做的银饰工艺非常精致。他有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儿子在凯里开银饰加工坊,女儿在施洞开了个店铺,名为“大刘银饰店*刘永贵有两个弟弟也在施洞做银饰生意,他在家中排行老大,所以将银饰店取名为“大刘银饰店”。”。作为银匠的父亲对银饰的态度会感染后代,刘永贵的女儿告诉笔者:“我父亲总是告诉我做银饰要有耐心,以前我不懂事耐不住,现在做起来经常会忘记时间,有时候做到半夜。”
吴通云未追求新的工艺,而是在苗族银饰技艺基础上对银饰本身进行改造,在他看来,苗族银饰即苗族文化。以下这段话来自2013年笔者对吴通云的采访,这段话很好地解释了施洞苗族人为何要戴银饰,换句话说,他道出了苗族银饰在苗族文化中的意义以及施洞苗族人的银饰观:
苗族用银饰来代替文化,并且在服饰上体现,一整套银饰是多件的组合,体现出苗族人爱热闹的性格。而汉族则喜欢做单件饰品,并且是立体的。而苗族银饰都是平面的。汉族有龙凤冠,苗族有银帽,而且银帽上多是动物图案,像蝴蝶、龙、凤,银帽也是看这家人有没有钱的标志。苗族有句话叫:这姑娘长得丑点,有套银饰也能嫁出去。银饰还是象征着富贵。银饰多少决定了是否能嫁一个好人家。女儿带出去,媳妇带进来。苗家都是这样,家里有儿子也有女儿,这样才能有进有出。苗族人的家产观念与汉族人不一样。国家为什么支持苗族银饰呢?因为苗族没有文化,弄点银饰可以戴着去踩鼓场*施洞每逢节日期间,便有苗族姑娘穿着银饰盛装到踩鼓场围着木鼓,跟着鼓点跳舞。玩,心里痛快些。像文化大革命时期,不给戴银饰,觉得干活都没劲,完全磨时间。
施洞苗族婚姻继承习俗中规定,女儿出嫁只能从娘家带走银饰与苗服,房子田地归儿子继承。就如吴通云所说,“银饰多少决定了是否能嫁一个好人家。”银饰象征着财富的观念在施洞苗族人心里根深蒂固,因此,但凡谁家里生了女儿,母亲便要开始为女儿购置银饰,随着女儿年龄增长,银饰也越积越多,待出嫁时便有了一套完整的银饰。之所以母亲在女儿小的时候就开始购置银饰,是因为施洞节日繁多,节日期间要踩鼓,逢年过节亲戚之间需要走客*逢年过节亲戚之间串门送礼在施洞被称为“走客”。,走客和节日时小女孩也需要穿戴银饰。如果小女孩没有穿戴银饰和绣衣,村民便会指责其母亲。虽然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施洞外出务工人数激增,但人们并未因为接受了城市文化而改变他们购买银饰的理念。
外出务工给当地人带来的直接变化是,他们开始有钱购置越来越多的银饰,也因此施洞的银匠变得越来越多,当地的银饰加工行业得到进一步繁盛。这样的变化同时刺激了银匠们的创作激情。
在吴通云看来,老一辈的银饰工艺很糟糕,“龙不像龙,人不像人”不该在新的银饰中复制,所以他将龙钻得更加活灵活现。同时,在纹样上复杂化,比如头上的马带里有人骑马的纹样,以前的人骑马图案中没有马缰绳,他加上了一个马缰绳,觉得这样更逼真。
吴通云在访谈中说道,以前施洞盛装中不戴牛角,走客装*施洞苗族服饰分为盛装与走客装,盛装较走客装更繁琐,只在姊妹节、龙舟节以及结婚时穿,而走客装是在走客期间穿的。的牛角造型纹样都比较简单。上世纪八十年代他在盛装服饰上添加了造型复杂的牛角,为了姊妹节*姊妹节与龙舟节是施洞最大的两个节日,通常在这两个节日期间,从几岁的小女孩到二十多岁未出嫁的姑娘都会身着盛装去踩鼓场上围着木鼓跳舞。时戴着进踩鼓场显得更加辉武和美观。从这时候开始,施洞的银饰造型从视觉效果上变得更张扬和夸张,银饰部件的数量变多了。而单件银饰的质量却从“重”变“轻”。吴通云谈道:“说去说来,银饰为什么要安排在姑娘身上戴?以前有些人要重的耳柱*一对耳柱通常有5-6两左右。,把耳朵都掉断了,但还是喜欢重的,出嫁的时候银子多表示家里越有钱。我后来都帮她们改了,改成里面是空的,以前是实的。有些妇女来我这打银饰,说实的太重了,要改成轻的。”
这些新的图案、新的造型被年轻一代的女人们接受,她们不再喜欢戴“重”的银链和耳柱,而是喜欢轻巧但纹样精致的银饰。老一辈苗族妇女喜好的耳柱开始成为“古董”,只有少数老人继续佩戴。“耳柱”由于过重,导致很多女人的耳朵破裂,但不少女人去医院缝了后又继续戴。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粗重的实心项链与耳柱是当时女人最喜爱的饰物,吴通云说道:“我老太以前做家务事的时候也戴着。”老一辈妇女愿意承受其重,认为“重”才是好的,它代表着财富的多少。老一辈女人愿意承受银饰之重的“身体”习惯不被当代苗族青年女人接受,但“银饰象征着财富”的观念并未随着社会变化而被年轻人遗弃。吴通云告诉笔者,他听老人们说,民国年间施洞只有四户人家有全套银饰,所以姊妹节只有他们四户人家的女人有全套银饰去踩鼓。随着九十年代以后施洞外出务工人数的增多,不少年轻一代的女人可以通过打工挣来的钱为自己添置整套银饰。姊妹节不再像吴通云说的只有四户人家有全套银饰踩鼓,而是大多数人家的女儿都能穿全套盛装参加。
吴通云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大儿子分家后也在塘龙打银饰,生意做得如火如荼,是施洞有名的富硕家户。小儿子也跟随父亲制作银饰,在台江县开了家银饰店。
施洞的例子证明了银匠的生存处境主要受当地人的银饰观念影响。历史上“清水江疏浚”给当地人带来的白银繁盛形塑了当地的苗族银饰文化[8],使得“银饰象征着财富”的观念就如涂尔干所说的“社会力”[9]一样弥散在施洞苗族人的心中,因此,施洞的银饰佩戴和继承习俗并未因外出务工现象而消失,反而表现得更兴盛。如吴通云的大儿子吴国政在访谈中说道,他生意兴起主要得益于改革开放后外部环境的改变,一方面是国家支持少数民族银饰加工,银匠们可以无息贷款,同时,九十年代施洞外出务工的人数激增,就如他所说:“赚的钱都是回家来买银子,百分之八十的人都拿来买银子。”施洞的例子代表着黔东南传统银饰工艺保护中的重要类型——本土自觉中的文化保护。
与施洞相比,在改革开放以后社会变迁的背景下,无论是银匠的生存处境还是当地人对银饰的态度,湘西凤凰县的山江镇与德榜村都是另一番景象。
三、政府推动下的文化保护
苗族银饰锻制技艺于2006年申请非遗成功后,山江镇的银饰锻制技艺开始受到外界重视。 但在此之前,当地银匠几乎没有受到外界关注。德榜村的银饰工艺开始引起外界关注甚至晚于山江镇,德榜村隶属的柳薄乡*2015年12月柳薄乡经行政区划调整与原禾库镇、米良乡合并为新禾库镇。成功入选2011-2013年度“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德榜村的银饰工艺资源受到挖掘,德榜村也因此成为凤凰县有名的银匠村。
明清时期中央王朝曾在湘西地区修筑“边墙”,通过“边墙”对当地苗人社会实行封锁政策来加以管理。山江、禾库以及腊尔山地区在当时都位于边墙外,生活于此的苗人被当时的中央王朝视为“化外之民”[10]。因此山江、腊尔山和禾库地区的苗族文化(包括服装、银饰)被当地学者认为更淳朴和原汁原味。[2]德榜东邻米良乡,南接禾库镇和两林乡,其西部和北部分别与花垣县雅酉镇、补抽乡接壤,地势较高,属纯苗族聚居区。村里共有11户银匠。目前德榜从事银饰加工的有上寨的龙建杨、龙吉堂、龙玉生、龙玉春、龙玉先、龙玉成、龙先虎、龙文汉、龙绍兵,以及下寨的隆自荣等。这个村寨锻制技艺的传承主要以龙建杨和龙吉堂为中心。他们两位银匠是目前该村最年长的两位银匠。该村没有国家级非遗传承人,龙吉堂是德榜唯一一个于2015年成为州级非遗传承人的银匠。
禾库镇作为苗族聚居区重要贸易集市,每逢农历初一、初六赶集,德榜村与雅酉镇的银匠都会赶来摆摊。与黔东南施洞镇一样,德榜和山江银匠的销售渠道主要有两种,一种是逢赶集时去集市上售卖,一种是接受村民来自己家里订购。因此,口碑信誉好的银匠更容易接到订单。比如施洞吴通云的大儿子吴国政,为人和善,定价合理,而且接受客户赊账*施洞很多年轻人和中年人都外出打工,到年底才能拿到工钱,针对这种情况,吴国政让他们提前拿银饰,拿到一年工钱后再结账。,施洞镇上不少村民都选择到他家里购全套银饰。龙吉堂和龙建杨属于德榜口碑信誉不错的银匠,因此找他们定制银饰的客户较多。
虽然德榜村主要是在2013-2015年间龙吉堂等人被评为州级以及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之后,在县政府部门的政策推动下而受到重视,但龙建杨家里的银饰加工技艺系谱可以追溯到清末。1950年代临近的其他村还没有银匠,但德榜村已经有两三户。德榜村经济状况较落后,在那个年代全村没有一户人家有全套银饰。据龙建杨说,他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打制的一整套银饰才一斤左右,而现在随便一套银饰都有十多斤。虽然现在全套银饰的重量增加了,但购买量并没有那么大,就如他所言:“现在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谁会天天戴啊,只是走客、结婚的时候戴。”
龙建杨现年75岁,他在1958-1959年间开始学习银饰制作,1963-1964年“四清”期间,银匠们不允许私自从事银饰加工,那个时候他在拖拉机站和电站工作,改革开放后再拾起这门手艺。由于生意不错,龙建杨家里不仅有不少银饰加工器械,还常年雇着两名帮工。龙建杨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均会打制银饰,都各自分家从事银饰加工生意。龙吉堂比龙建杨稍年长几岁,1939年出生,15岁跟随其爷爷学习制作银饰。2014年,龙吉堂与其小儿子龙先虎成立了“吉虎手工银饰厂”,被县文化局授予“德榜村苗族银饰锻制技艺生产性保护基地示范户”的荣誉称号。在县文化局等相关部门的帮持下,将其在德榜村的老宅改造成银饰加工坊的形式,并配以宣传板介绍“苗族银饰锻制技艺”及龙吉堂的生平,以供外地来的游客参观。
在德榜村作为一个银匠村被外界知晓之前,由于当地村民对银饰的购买量不大,即便龙建杨和龙吉堂的生意是当地最好的,但他们的收入与施洞生意最好的银匠相比,差距仍然较大。吴通云的大儿子吴国政作为施洞生意兴盛的银匠,他对笔者说,在正月间生意好的时候一天就能收到十几万。施洞的年轻银匠基本月收入也在三四千左右。而龙吉堂家里在几年前的年均收入在十万左右。在他评为州级传承人之后,有不少外来游客购买,年均收入有所增长。德榜其他银匠每户年收入在三到四万之间。
正因为银饰在当地销售量不大,有些年轻银匠在学银饰工艺的中途便选择出去打工了。也有银匠由于近年生意不好而选择出去打工,比如龙建杨的女儿和女婿因抱怨生意不好,今年去浙江打工了。同时,由于销售量不大,德榜银匠不会一次性购入大量银料,因此他们不可能囤银子,一般都按照需求量购买。但施洞银匠会囤积银子,一方面与施洞银饰需求量大有关,一方面也在于,施洞银匠认为,银子可以储值,比人民币更能保值。*银子比人民币更能保值的观念在施洞深入人心,因此,施洞当地人在购买银饰时,会计算在银子价格低的时候购买。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前,无论是施洞还是德榜、山江,村民购买银饰时都主要是来料加工;但九十年代以后,外出打工人数激增,这些外出打工的人更愿意购买成品。禾库地区的苗族年轻女人大多在结婚前才会购置全套银饰,用于出嫁时穿,平时仅会购置一些小件饰物(如手镯、项链、耳环、银簪等)作为日常穿戴。
虽然禾库、腊尔山以及山江五十岁以上的苗族女人仍有坚持佩戴苗族银饰的习惯,尤其银项圈(绳项圈)是当地女人常佩饰物,但年轻一代的苗族女人因为外出务工而受到“汉化”影响,日常佩戴银项圈的习惯几乎消失。当地苗族女人对待银饰态度的代际差异在某种程度上对银匠也是一种打击。这种打击直接削弱了银匠们钻研于此种技艺的激情。如果可以用机械替代,则尽量不用手工。在德榜,不仅龙建杨大量使用现代器械加工,其他银匠也普遍使用现代器械。笔者从德榜几位银匠处得知,这里的银饰纹样在过去几十年没有发生变化。他们也没有有意对其进行改造,由于过去银料少,银饰普遍较小,因此,唯一的改造是将过去小件的银饰改成大件,但图案本身没发生变化。
与禾库类似,山江镇也是重要的苗族聚居区贸易集市,每逢农历初三、初八赶集。但由于德榜村与山江距离太远,德榜村的银匠一般不会来山江镇集市上摆摊。山江镇有龙米谷、麻文芳、麻恩佩、麻忠君、麻茂庭、龙喜平、吴云表、吴求表、吴金竹、吴平安、吴兵云等13位银匠师傅,与德榜村一样,山江镇的银匠均为男性。
2017年笔者去山江做调查时,龙米谷已去世,山江镇还有龙喜平与麻茂庭两位师傅继续采取传统的手工方式制作银饰,其他银匠师傅均引进了现代工艺。与施洞银饰工艺国家级非遗传承人不一样的地方在于,山江镇的两位国家级非遗传承人麻茂庭与龙米谷制作的银饰主要受当地人欢迎,甚至有腊尔山的村民听闻他们的口碑后来山江找他们打制银饰。他们被选为非遗传承人,也是得益于当地村民的推介。麻茂庭在与笔者访谈中说到他被评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经历:“大致在2008年左右,县政府工作人员来到我们这里到处打听谁打银饰打得好,他们都说我打得好,县政府工作人员就找到我了。”
以下是他对其学习银饰加工工艺经历的回忆:
我1953年出生,1977年进入“银饰加工厂”(加工厂具体名字不记得),加工厂大致有十个银匠,其中包括我父亲,我刚进加工厂时是做保管和管理工作的,在这一年做保管工作的同时,我开始学习制作银饰,直到1982年加工厂解散,这时候开始允许私人打制银饰。有的银匠从加工厂出来后就不做银饰了,但因为我有一个同学在工商所工作,他提前给我信息说可以允许“私人制造”,所以我是第一个从加工厂跳出来的,然后开始回到家里做,当时的银料来源主要来自我在市场上回收的光洋,或者顾客带来的银子。
麻茂庭认为自己学习银饰工艺非常偶然,主要出于兴趣而学。与德榜村银匠不同,麻茂庭坚持用纯银加工,且家里没有现代加工器械,主要靠手工制作,因为在他看来,制作银饰就如同创造一件艺术品一样,需要耐心地钻研。在访谈中,他说到一个重要的事实:在1995年以前,他几乎每天都在打制银饰,来找他打制银饰的人很多,所以很忙碌。但在1995年以后,由于越来越多的村民选择外出打工,打工回来后都“汉化了”,他也变得没有那么忙碌了。如今虽然他已成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但他坦言:“现在大部分时候都比较清闲。”偶尔有村民来找他打制银饰时,他也会做,但他已很少去集市售卖银饰了,家里的银饰加工器具也处于闲置状。
麻茂庭有一个哥哥,两个弟弟。他们兄弟四人在九十年代以前都做银饰,但当地村民开始外出打工后,除了他还坚持在做,其他三兄弟都不做了。后来他陆陆续续收了一些徒弟,但有些徒弟因为看到银饰加工生意不好做,也改行了。麻茂庭有一个儿子,两个女儿,均未从事银饰加工行业。
麻茂庭叙述他的个人经历时带有些许凄凉,对于当下银饰的商品化,他更是感到无奈。他在访谈中谈到了当下银饰商品化后银匠们使用银料的变化。在山江以及德榜,许多银匠更愿意购买被机器配比好了的银饰半成品,这类半成品通常含银量很低。直接购买这类半成品来加工,可以大大缩减苗族银饰制作的成本,但制作好的成品也失去了其保值功能。麻茂庭虽然在2008年被评为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其技艺也受到当地人的推崇,但他陈述了一个事实,即山江与德榜的银匠受到当地销售量降低的影响后有不少人选择退出这个行业,他自己的事业也因此有了“转折点”。
山江和德榜的银匠们的经历再次证明了银匠的生存处境与当地人的银饰观念密切相关。明清时期“边墙”的修筑使得处于湘西苗疆腹地的山江与德榜两地的苗人与外界少有联系,历史上并非像位于清水江畔的施洞出现过大量的白银涌入,这导致了当地苗族人并未形成以银饰为主要载体的财富观念,山江与德榜的银饰文化并未如施洞地区深深根植于当地人的心中。就如德榜银匠龙建杨所说,“以前这里的银饰非常少。”笔者在调查中了解到,虽然在继承习俗上,母亲的银饰是传给女儿,但由于这里以前银饰非常少,所以在继承习惯中并没有形成自女儿出生后母亲就开始为女儿备置银饰的习俗。尤其外出务工带来当地苗人的“汉化”后,当地人穿戴银饰的观念更加薄弱。在当代,穿戴银饰主要为了美观,而未像施洞苗人一样将其作为“财富的象征”,也没有储值的功能。九十年代外出务工潮进一步冲淡了当地人穿戴银饰的观念,银匠的生存处境也受到冲击,当地人淡化的银饰穿戴观念与银匠的生存处境形成的僵局,使得当地的银饰工艺保护只能成为政府推动下的文化保护。
苗族银饰锻制技艺于2006年申请非遗成功后,山江镇的银匠开始受到外界关注。德榜村也是在其隶属的柳薄乡成功入选2011-2013年度“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之后,尤其是龙吉堂被选为州级非遗传承人之后,德榜村的银饰工艺资源开始受到外界的挖掘。但结合银匠的现实生存处境以及当地人对银饰的态度来看,这里的银饰锻制技艺的保护与传承主要是由政府推动下进行,而似乎还不是发源于当地人自身的苗族文化自觉。
四、结语
贵州施洞与湖南德榜、山江多地的历史过程形塑了当地苗人不同的银饰文化生态。湘黔两处苗区的苗族银饰文化生态与银饰工艺传承的经验案例较为充分地说明了银匠的生存处境与当地人的银饰观念息息相关。如果将上述各地代表的湘黔苗族地区的经验加以对比,可以更为清晰地辨析出两地模式的不同之处。
从比较可以看出,银饰文化生态浓厚的苗区不容易受当代剧烈的社会文化变迁所影响,因此,湘黔两地银匠的生存处境以及当地人的银饰观念反差较大。施洞人银饰的穿戴和传承习俗并未因为九十年代当地人的外出务工潮而变淡,而德榜与山江地区的老一辈妇女与年轻一代存在很大的差异,老一辈妇女还坚持穿戴银饰,年轻一代的女人仅仅在节日与结婚时穿戴,且平时的购买量也不大,穿戴银饰仅为了美观,不是为了储值。而施洞人购买银饰不仅为了美观,还为了储值。银饰象征财富的观念在施洞人心里根深蒂固,因此,施洞人用苗语“Niongs Nix Niongs Gad(银多米多)*Nix即银子或银饰。”指代富有。当地人对于银饰的态度影响了银匠的生存处境以及银匠对待银饰工艺的态度,因此在银饰加工工艺上,德榜村银饰加工工艺主要采用现代化器械,德榜与山江的银匠们普遍采用配对好后含银量不够高的半成品银子。而施洞的银匠普遍采用99纯银,且老一辈银匠仍坚持手工制作。在银饰工艺传承方面,德榜与山江的老一辈银匠的后代不一定继承其父亲的工艺,且老一辈银匠收取的徒弟也会因为市场不好而选择改行。因此银匠数量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后并未增多。而施洞老一辈银匠的后代几乎都在从事银饰加工行业,并以此为生。新一代银匠数量在九十年代后有所递增。
近年来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我国传统文化重要瑰宝的保护传承问题受到人们的重视,基于这样的背景,由银匠的生存境况与当地人的银饰观念构成的文化生态促成了这两种文化保护模式——本土自觉中的文化保护与政府推动下的文化保护。国务院办公厅在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中明确指出:“随着全球化趋势的加强和现代化进程的加快,我国的文化生态发生了巨大变化,非物质文化遗产受到越来越大的冲击。”[11]笔者希望指出,在当代社会,非遗保护主要针对的是对文化生态的保护,而文化生态受制于特定地区的社会历史条件。将施洞与德榜、山江对比,银饰所处的文化生态呈现出两种完全不同的境况,出现这两种境况不仅与改革开放以后的社会变迁有关,也与他们各自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有关。在不同的文化生态环境中,需要采取什么措施和方法对该工艺进行保护,是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的问题。
[1] 李黔滨.苗族银饰[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0.
[2] 石群勇.凤凰山江苗族银饰探析[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2).
[3] 毛家艳.非物质文化保护语境下的控拜苗族银匠调查[J].原生态民族文化学刊,2010(2).
[4] 张建世.黔东南苗族传统银饰工艺变迁及成因分析——以贵州台江塘龙寨、雷山控拜村为例[J].民族研究,2011(1).
[5] 张应强.木材之流动——清代清水江下游地区的市场、权力与社会[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
[6] 张中奎.改土归流与苗疆再造——清代“新疆六厅”的王化进程及其社会文化变迁[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
[7] (清)田雯.黔书. 黔书·续黔书·黔记·黔语[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75.
[8] 杨正文.清水江流域的白银流动与苗族银饰文化的成因[J].民族研究,2015(5).
[9] (法)爱弥尔·涂尔干.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10] 张应强.边墙兴废与明清苗疆社会[J].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2).
[11] 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国家中心.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普查工作手册[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5:171.
责任编辑:陈沛照
C912.5
A
1004-941(2017)06-0092-07
2017-08-15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黔东南苗族银饰手工艺人的代际传承调查研究——以黔东南台江县施洞镇为例”(项目编号:CSQ17004)。
李若慧(1986-),女,苗族,湖南吉首人,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西南少数民族物质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