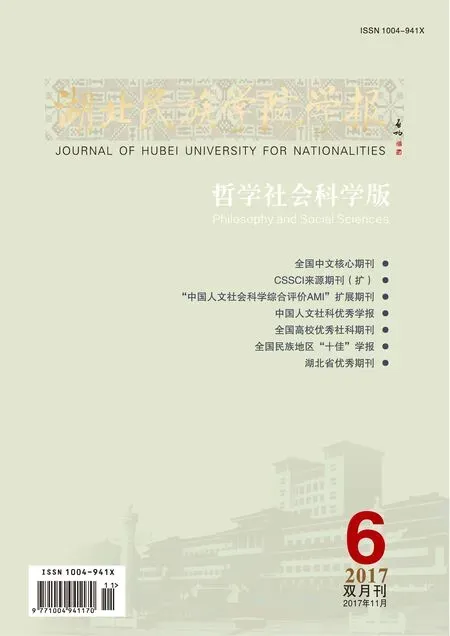政治统一与文化多元:民国时期西南少数民族的民族共生诉求
刘波儿
(南京中医药大学 人文与政治教育学院,江苏 南京 210023)
政治统一与文化多元:民国时期西南少数民族的民族共生诉求
刘波儿
(南京中医药大学 人文与政治教育学院,江苏 南京 210023)
在近代中国由王朝天下向现代国家转变的过程中,汉族知识精英们长期围绕西方“一族一国”的民族建国模式探讨新型国家的组织结构问题,形成了“夷汉同源说”、“中华民族是一个”等旨在构建一个“中华民族”以因应民族国家理论的思考路径。事实上,当时已经产生民族意识觉醒的西南少数民族精英们自有一套实现多民族凝聚于一个政治共同体的逻辑,他们提出的统一国家认同与文化多元诉求,揭示了民族共生理论的另一种思路。
政治统一;文化多元;西南少数民族精英;民族共生
19世纪下半叶以后,作为统一帝国存在的传统中国面临着越来越严重的外部侵扰,在严重的边疆危机面前,必须最大程度地在内部寻求一致性,构建“一体化”的现代国家遂成为贯穿整个近代中国的政治理想。王柯认为“孙中山以来的中国历代政府,都将在多民族的中国实现国民国家的形式,即实现超民族的广泛的国民整合设定为一个重要的政治目标;尽管具体方式各自不同,基本方向都是朝着实现‘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即建设一个与国家等身大的民族”[1]。
1935年,傅斯年发表《中华民族是整个的》一文,指出:“我们中华民族,说一种话,写一种字,据同一的文化,行同一的伦理,俨然是一个家族……‘中华民族是整个的’一句话,是历史的事实,更是现在的事实”[1]。在傅斯年的影响和要求下,顾颉刚提出了“中华民族是一个”的主张,他的观点可以归纳为,中国经过几千年的融合与同化,各族类群体或已经相融,或正在相融,“中华民族”已经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不存在单一纯粹的汉满蒙回藏群体,而在遭受日本侵略的现实条件下,为避免国家被肢解,必须承认只有“中华民族”这一个民族。[2]“中华民族是一个”的主张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尽管得到了较多的赞同,但也有反对的声音。苗民鲁格夫尔以“蛮夷之民三苗子孙”的名义致信顾颉刚抗议道:“苗夷历史虽无专书记载,但苗夷自己决不承认是与汉族同源的”,“值此全面抗战之际,宣传固应以认清国家、提高民族意识为主,然负责宣传的人们不甚注意及‘民族’之宣传。凡有关国内民族团结之言论应慎重从事,不能随便抬出来乱喊一阵”[3]。刚刚留学归国的费孝通以民族学视角发文质疑,他认为:“我们不必否认中国境内有不同的文化、语言、体质的团体”,因为各个民族“在政治上的合作,共谋国家的安全和强盛,决不是取消了几个名词就能达到”[4]。傅斯年、顾颉刚二人关于中华民族整体性的阐述引发了一场大讨论,被称为“20世纪历史学和民族学的初次交锋”。[5]需要指出的是,这场讨论主要是基于清末民初以来,北方民族中始终存在的民族分离情绪而进行的,正如顾颉刚所说,“若不急急创立一种理论把这谬说挡住,竟让它渐渐深入民间,那么我们的国土和人民便不是我们的了”[6],却没有关注到其时已渐渐萌发自我身份意识的西南少数民族。有人曾提出:“汉苗风习不同 ,语言迥异 ,数千年来彼此争战 ,虽一胜一败 ,而今犹未被同化 ,焉得谓无族可分 ?”[7]那么,在国家与民族之间,西南少数民族精英又如何选择自己的位置?
一、同化抵拒与多元文化诉求
学界关于中华民族问题的讨论也影响了政界,“民国朝野大致分享着共同的观念,那就是要建设一个民族国家,要促成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中华民族的统一性和整体性即使不是历史的事实,也必然是未来的目标”[8]。1943年,蒋介石在《中国之命运》一书中正式提出了宗族论,他说:“我们中华民族是多数宗族融和而成的……融和的方法是同化而不是征服。”[9]此后,构建统一思想文化成为边政实践中的重要内容。
1945年,杨森主政贵州后,认为贵州之贫弱“盖本省边胞特多,率不明国族同源共同进化之理”。因此,必须推行统一的语言,改用汉语汉文,“逐渐统一其语言服装,并奖励各族通婚,则大一统制中华民族”[10]。他要求儿童上学必须先学国语,苗区的保长必须由能说国语的人担当,并在苗区举办国语比赛,千方百计在苗民中推行语言同化。[11]在文化统一的政策下,原本独立办学的边疆学校逐渐与普通国民教育合并,独立筹设的边教经费也依附于国民教育经费项目之中,为边疆教育举办的研究、设计与师资训练机构逐渐消失,民俗研究会和方言讲习所停止办理,一切边疆教育事务均以苗汉一体化为圭臬。这激起了西南少数民族知识精英的强烈不满。1945年7月,杨森的秘书长李寰拟好同化方案后,找来梁聚五(苗族)、吴修勤(僮族)、伍文正(布依族)和张斐然(苗族)四人讨论,提出停止使用石门坎的苗文,一律改用汉文,在生活上也必须逐渐使用汉语等要求,“整个会场的空气顿时就凝固了,每个人的面容上表现出极端愤慨而难以抑制的心情”。张斐然第一个表示了强烈的反对,他认为石门坎的苗文属于世界上最进步的拼音文字,只要掌握了声韵母就可读可写,而书写要求极高的汉文却不便传播,所以苗文绝不应取消,反而汉文应效仿苗文采用拼音文字的形式。至于语言,张斐然认为,语言是人类在生产劳动的过程中,自然形成的表达感情的工具,只要它还能在生产生活中起着交换思想,沟通联系的作用,就无法强行用刺刀和命令取消。[12]面对张斐然的慷慨陈词,李寰面红耳赤,表态“石门坎的苗文我们不取消了,以后再说”。省训团秘书白敦厚劝张斐然说,这是“杨主席在贵州的施政方针,不能反对,只能善意的建议”,张斐然毫不示弱地指出:“你请我参加讨论的是民族问题,参加讨论的各个民族,都得以同等地位表示自己的态度,如果讨论民族问题,你们硬要采取高压手段的话,那样就会形成一个民族支配另一个民族。”[12]58张斐然认为,文字,语言和服饰是构成民族的基本要素,而杨森的同化政策正是意欲消灭少数民族,因此少数民族知识分子必须旗帜鲜明地表示反对。
梁聚五也表示了强烈的异议,在他看来,高唱“同化”主义的人根本不了解民族问题,意图禁穿少数民族服装,禁用少数民族语言的行为从根本上违背了孙中山先生的民族平等主张。况且,建国大纲早已明示要“扶持国内弱小民族,使之自决自治”,“自决自治尚且要推行,哪里还容许人来干涉少数民数的服装语言呢?”[13]他强调:“一个民族的构成,依据国父孙中山先生的遗志,是有着血统,语言,文字,宗教,生活习惯之不同。今以不同而强同,是不啻以帝国主义自居,而把国内各弱小民族当作殖民地来看待,如此,只有分划中国民族的团结力。”[13]
不仅推行汉语的做法受到苗族精英的抵制,杨森的民族通婚政策也激起他们的反感。1946年,白敦厚娶蒋介石夫妇义女、花溪把火寨苗族保长陈伯光之女陈为瑾为妻。订婚仪式上,陈父回溯了苗族的发展,肯定了苗汉同源说和苗族的宣化史。杨森率数十位省府重要官员亲自证婚,并发表讲话,称“这(苗汉通婚——笔者注)都是(为)我们整个中华国族共同进化着想,希望各位边胞,对此能够深切的了解才好”[14]。闻二人婚讯,蒋介石夫妇更赐寄照片,并将把火寨改名为中正村,以示对苗汉通婚的褒奖与重视。这段婚姻成为宣传民族同化的样板与工具,也引发了少数民族人士的反感。1947年,陈为瑾得到贵州省政府和部分县国民党党部的支持,当选为“行宪国大”代表候选人,激起苗族知识人士的愤怒,痛斥:“陈为瑾(原文中误为“陈文瑾”——笔者注)列于前名,而我全省边民素景仰之朱焕章、梁聚五、张斐然、陆宗棠、王玉玺等列于最后,此种之记分、列名,竟依何法,据何理”,“此辈不肖之徒实有意破坏宪法,扰乱宪政,愚弄边民,强奸民意,剥夺我边民之权利,欲置边民族于死地。凡我边民,莫不痛心切齿,誓死抗议,誓与死争,不达不休。”同时,他们向行政院、内政部、中央党部、选举总事务所上书要求法办,废除此次会报记分,“否则,凡我边民,为整个国家民族之统一团结计,绝对当仁不让,一致否认到底”[15]。
显然,以文化同化的方式构建一个“中华民族”的思路无法得到少数民族的认可。那么,他们又是怎样看待自己在国家中的位置呢?
二、参政心愿与统一国家认同
近代中国的现代国家构建运动不仅唤起了汉族社会的民族自觉,也唤醒了“非汉”民族精英的民族意识,30年代中期至整个40年代,西南少数民族精英的政治诉求运动蓬勃兴起,争取参政权正是贯穿其中的主调。1936年,彝民高玉柱和纳西族青年喻杰才作为西南夷族沿边土司代表和西南夷族民众代表从昆明赶赴南京,向国民政府请愿*关于高玉柱、喻杰才赴宁请愿一事,目前已有伊利贵的《民国时期西南“夷苗”的政治承认诉求:以高玉柱的事迹为主线》(中央民族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1年)、娄贵品的《1937 年西南夷苗民族请愿代表在沪活动述论——以《申报》为中心的考察》(《民国档案》,2010年第2期)及《1936-1937年西南夷苗代表在南京的请愿活动及其意义》(《西南边疆民族研究》第9辑)做过较全面的研究。。在请愿书中,他们明确提出了参与管理自身事务的愿望:
其一,请求中央指拨相当经费,补助西南夷族文化促进会,健全其组织,促进其发展。即有该会,立即联合各机关及学术团体,共同组织西南夷族调查团,深入西南沿边一带,宣扬中央德意,实地考察夷务;其二,请求政府在中央特设夷务机关,指导夷苗民族之教养卫等事务;其三,请求政府准许各土司夷苗民众,在沿边一带,组织夷务整理委员会,负责办理夷苗民族之一切事务。[16]
从职能上看,在高玉柱的设想中,“负责办理夷苗民族之一切事务”的“夷务整理委员会”类似于一个民族自治机构,而从内政部的批复:“夷苗散居各地,与蒙藏情形不同,其处理事项,应由该管省政府筹改进办法,自未特设机关致涉分歧”,“俟各省统筹办理后,再行酌量办理,目前无设置必要”[17]来看,这个请求没有得到批准。第二次请愿时,高、喻二人改变了措辞,“请援照待遇蒙藏办法,准予成立西南夷苗代表办事处协助开发”[18]。这里将原有的“办理一切事务”改为“协助开发”,显然淡化了民族自治的意蕴。第三次请愿时,两人再次作出了让步,只说“请中央特设夷苗管理机构,或在蒙藏委员会,增设夷苗办事处”。从开始充满民族自治意味的夷务整理委员会,到仿蒙藏例的西南夷苗代表办事处,再到在蒙藏委员会下设置夷苗办事处,高、喻二人的诉求显示出一定的弹性,但其底线始终未变,即坚持参与本民族事务管理。二人的请愿不能算成功,但却开启了西南少数民族人群争取自身政治权利的先河。
1945年,梁聚五在《贵州民意月刊》上发文批评参议员选举忽视了乡镇中的少数民族,他质疑:“以占百分之六十以上之苗夷,仅得一两个参议员,怎能够代表大多数民意呢?”[19]提出破除对苗夷代表的歧视心理,充分考虑苗夷人群的实际文化水平,降低资历要求,并指出县参议会应该以苗夷问题为主要议题。[20]
1946年召开的制宪国大引起了西南少数民族代表争取参政权情绪的集中爆发。由于会议将少数民族代表划入各区域代表团,未单独成团,湘西苗族知识分子石启贵遂联合贵州代表杨砥中、西康代表麻倾翁提出抗议,以“西南土著人口达二千五百余万,呼吁大会应遵奉国父遗教,扶助弱小民族”为由,建议“西南土著民族应自成为选举单位,加选主席团候选人一人”,杨砥中甚至“做狮子吼”,高呼“蒙藏代表为什么有位置?难道苗族不是中国国民么”[21]?国民大会临时主席孙科只得宣布“张代表道藩放弃为主席团候选人,并贵州土著代表杨砥中递补”,大会主席团选举才得以顺利进行。[22]尽管递补出任的杨砥中正式当选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但其获得候选人资格本身即显示了一种来自国家层面,对少数民族政治地位的确认,而这种认可恰恰是石启贵等人的主诉。
除了在中央政权机构争取参政席位,西南民族知识精英也很看重地方政权组织中少数民族代表的位置。1948年4月,曾在国民党中央党校学习的彝族土司岭光电和其他土著民族委员联合在立法会议上提出在《省县自治通则草案》中加入“凡有土著民族居住的省县参议会,应订出土著民族之参议员名额”条款的要求,一番据理力争后,终于获得了其它委员的认可,将这一条加入了自治草案中。5月,他又借晋见蒋介石之机,提出蒙藏委员会应改为“边政部”,并推荐杨砥中和孙子文参与事务管理。[23]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西南少数民族精英不断以索求政治身份的方式来彰显本民族的存在与价值,但他们的参政与自治诉求同时体现出依归于国家格局的特点。不仅高玉柱、喻杰才在请愿书中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态度表达了认同于统一国家,共赴国难的心愿,彝族土司岭光电也自觉国家复兴为少数民族之责任,他指出:“今日大中华民族已于生存之意识下醒觉,正奋其潜藏之伟力,挥其无穷丰富之生命向世界以谋其出路,我西南夷族为大中华民族构成份子之一,自当奋发追踪,完成民族之复兴。”[24]抗战的全面爆发更加强了少数民族精英对国家的向心力。国民政府文官处官员刘曼卿、格桑泽仁等一批在南京的康藏籍人士组织了“康藏民众抗敌赴难宣传团”,赴前后藏、西康各地宣传,唤起边民共赴国难,并募捐西藏毛织氆氇及金银饰物数百件贡献国家,支援抗战。而在国大代表选举中遭遇不平等待遇的石启贵仍以苗民对国家的高度忠诚为荣,他说:
西南边疆民族虽在中央腐败官吏暴政之下,然对国家仍最具赤诚心,敢向诸位声言,抗战期间,边疆民族无一为汉奸者,其时日人曾多方企图引诱吾人与之合作,吾人即以赤手空拳,或原始武器,答复其阴谋。[25]
民族学家江应樑曾感叹西南民族是被“五族共和”遗忘的人群[26],但在民族危亡的时刻,少数民族知识精英表现出明确的国家认同,他们的参政与自治心愿不同于基于分离情绪提出的自决要求,其最终目标是在国家框架下获得民族位置的确认,也就是说,“他们的目标不是成为与更大社会并列的单独的和自治的群体,而是希望改变主流社会的制度和法律,使主流社会更好地接受文化差别”[27]。正如梁聚五所说,他们需要的是“把各民族的地位,不管是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都提到‘一律平等’的线上,互助互谅,以发展大家的新生命”,真正做到“中华一家民族平等,大同进化,适者生存”[28],他们所认同的国家整合道路不是以汉族社会为模板的同质化洗涤,而是各民族在自有道路上,互助式的前进。这也正是他们在多元文化与统一国家双重诉求背后隐藏的共生智慧。
三、意义与启示
晚清以来,蒙、藏、新疆等北方少数民族中不断出现分离情绪,形成了空前严重的边疆危机,抗战爆发以后,将各民族留在中国团结抗战,更成为时势所需,包括“中华民族是一个”在内的多次讨论都是围绕着这一需要展开的,这些讨论暗含了这样的逻辑:文化多元=多民族=国家分裂,所以只有“文化一元”才能“一族一国”,从而达成团结。然而,对那些本来就认同“一国”的西南边缘群体而言,这样的逻辑并不能让他们服膺,在此逻辑之下,以文化同化为目的推行的种种民族政策更是不能接受。在他们看来,文化多元与国家统一并不矛盾,鲁格夫尔曾说:“今日要团结苗夷共赴国难,并不须学究们来大唱同源论”[3],高玉柱甚至认为,“参加抗战是我们的义务,同时也是我们的权利,争取大中华民族的自由与解放,同时也是取得了我们夷苗民族的自由与解放”[29]!
西南少数民族精英关于各民族各有文化特点且同时具有整体性和共同利益的主张更多是一种来源于丰富民族实践的朴素感知,难称为理论,但这种认识既符合当时的政治需要,也能被边缘群体接受,在“中华民族是一个”主张遭遇学理困境之时,不失为一种将多民族凝聚于一个政治共同体国家的思路,这一思路不以“建设一个与国家等身大的民族”[30]为国家整合方式,不通过构建“中华民族”这样一个民族符号来解决西方民族国家理论与中国社会实际之间的适配性问题,跳脱出了“一族一国”的理论窠臼。
政治统一,文化多元的思路并不全然是乡野之音,当时较为接近民族社会的民族学家也曾在这一方向上进行理论思考。就在“中华民族是一个”讨论如火如荼之时,杨成志提出“提高和普及中华国民教育到国内各族去”,“陶化山族部族大众得具有中华国家之意识,及国民之义务”,从而将西南地区二三千万的“浅化大众”变为“中华公民与卫国战士”[31]的想法,指出国家意识是多民族国家的凝聚核心。1942年,徐益棠使用了“公民责任”的提法,他指出:“我辈治边疆教育者,当努力设法消灭各民族隔阂之成见,而为大中华民族唯一单元之团结。此种团结,当从‘公民’责任一观念培植之。”[32]同年,凌纯声指出,边疆教育的内容除了应有史地知识之外,还应包含“中国国民应有的公民常识”,他所构想的多元文化社会不仅“对边疆民族予以国家教育,使边民接受现代的文化,同时又能保存其固有的文化”[33]。1943年,吴泽霖沿着这一思路做了具体阐释,他认为,民族工作的要义在于使各族产生一种同类意识,在国家民族大义面前同心同德,统一步调,而社会生活中的种种风俗习惯则不必强求统一,也就是统一但不划一,求大同而存小异,如此不仅可以保留各族的族性,减少民族间的矛盾而且丰富了国家文化。[34]应该说,这时的民族学家在处理国家整合问题上已经有了一些不同于西方民族国家建国模式的思考,他们开始探索建立一个既容括多民族、多文化又具有高度政治认同的统一国家之理论可能,试图用一个建立在“中华公民”意识之上的文明体系更新传统的“天下”统治机制,使具有历史延续性的少数民族在新的国家体系中找到位置。
但是,在那个民族危机空前剧烈的时代,西方民族国家模式展现出强大的规界力,几乎成为“政治正确”的唯一范式。1943年,蒋介石“宗族论”正式发表,意味着主流政、学界将继续在实现“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思路上谋求广泛的国民整合,中国民族关系理论也丧失了重要的发展契机。
尽管没有作出更深入的理论探索,但可以看到,在近代国家整合的历史潮流中,西南少数民族并非简单地呈现出或接受同化,或抵御同化,寻求独立的二元对立状态,而是主动探索、提出自己的民族身份愿景。政治统一,文化多元的民族共生思路源于中国实际,迥异于主流政、学界所遵循的西方民族国家建国模式。它不仅仅反映了当时西南少数民族精英的诉求,也为今天民族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启发,是中国民族理论发展的一条暗线。
[1] 傅斯年.中华民族是整个的[J].独立评论,1935年第181号.
[2] 顾颉刚.中华民族是一个[A]//顾颉刚.顾颉刚全集[C].北京:中华书局,2010:105-106.
[3] 顾颉刚.答鲁格夫尔君[N].益世报(边疆周刊),1939-05-15.
[4] 费孝通.关于民族问题的讨论[A]//顾颉刚.顾颉刚全集[C].北京:中华书局,2010:136-137.
[5] 郑善庆.爱国的逾越与压力——略论抗战时期中国史家的民族观与节操观[J].西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2).
[6] 顾颉刚.我为什么要写“中华民族是一个”[A]//顾颉刚.顾颉刚全集[C].北京:中华书局,2010:116.
[7] 佚名.方召来信[J].禹贡,1937(10).
[8] 汪洪亮.民国时期的边政与边政学(1931-1948)[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81.
[9] 蒋介石.中国之命运[M].南京:正中书局,1943:184.
[10] 贵州省政府秘书处.三年来黔政之检讨[G].1948.
[11] 梁瓯第.西南边疆教育的几个类型[J].边铎,1946(2-3).
[12] 杨忠德.张斐然同志反抗民族压迫和争取民族民主斗争的轶事[A]//政协会议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威宁文史资料[G].1986:60-61.
[13] 梁聚五.我们需要什么民主[J].贵州民意月刊,1944(1-2).
[14] 白敦厚.蒋主席关怀边胞:巡视花溪把火寨[J].边铎,1946(39).
[15] 贵州旅蓉吴善祥等揭发贵州省府暨省参议会等联合主持选举通同舞弊情形致行政院呈 [A]//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G].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750-751.
[16] 高玉柱.喻杰才.西南沿边土司夷苗民众代表请愿意见书[J].新夷族,1936(1).
[17] 贺伯烈.夷苗概况及夷苗代表来京请愿活动(续)[J].边事研究,1937(5).
[18] 高玉柱,喻杰才.西南夷族代表第二次请愿意见文[J].新夷族,1937(2).
[19] 梁聚五.论贵州政治应以苗夷问题为中心[A]//张兆和,李廷贵.梁聚五文集——民族·民主·政论(下)[C].香港:香港科技大学华南研究中心,2010:4.
[20] 梁聚五.贵州苗夷选举问题[A]//张兆和,李廷贵.梁聚五文集——民族·民主·政论(下)[C].香港:香港科技大学华南研究中心,2010:11.
[21] 杨成志.民族问题的透释[J].边政公论,1947(1).
[22] 主席团名单昨揭晓 蒋中正孙科等当选[N].民国日报,1946-11-22(1).
[23] 岭光电.忆往昔:一个彝族土司的自述[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8:200.
[24] 西南夷族文化促进会宣言[J].新夷族,1936(1).
[25] 国大继续讨论宪草 少数民族要求自治[N].民国日报,1946-12-04(1).
[26] 江应樑.抗战中的西南民族问题[M].广州:中山文化教育馆,1938:26.
[27] (加)威尔·金利卡.多元文化的公民身份——一种自由主义的少数群体权利理论[M].马莉,张昌耀,译.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9:3.
[28] 梁聚五.历代中华各族纷争与团结之研究[J].边铎,1946(1).
[29] 高玉柱.动员夷苗民族与抗战前途[J].西南导报,1938(4).
[30] (日)王柯.国民国家与民族问题——关于中国近代以来民族问题的历史思考[EB/OL].(2013-07-11) [2016-05-12].http://www.docin.com/p-286374507.html.
[31] 杨成志.西南边疆文化建设之三个建议[J].青年中国季刊,1939(1).
[32] 徐益棠.边疆教育的几个原则[J].学思,1942(3).
[33] 凌纯声.中国边疆文化(下)[J].边政公论,1942(11-12).
[34] 吴泽霖.边疆的社会建设[J].边政公论,1943(1-2).
责任编辑:陈沛照
C952
A
1004-941(2017)06-0062-04
2016-09-23
刘波儿(1981-),女,江苏南京人,博士,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民族史与边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