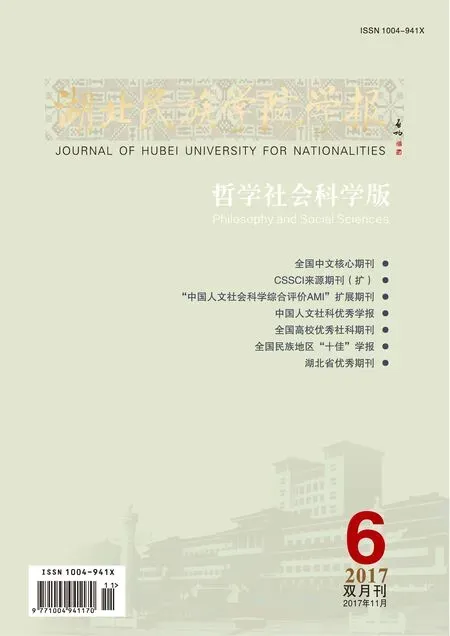中国少数民族戏班研究的政治学考量
杨天保,张强伟
(广西民族大学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广西 南宁 530000)
中国少数民族戏班研究的政治学考量
杨天保,张强伟
(广西民族大学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广西 南宁 530000)
民族戏班是一个政治性较强的社会组织。以往研究主要集中于戏剧学、人类学等领域,视角较单一。基于政治学的新考量,更可发现它与汉族戏班的诸多差异性:首先,明清帝国时期的边疆带,为其生成发展设置了独特的自然空间、制度空间和历史时段;其次,南传儒学“内卷化”与少数民族坚守民族文化的两种进程,同构了民族戏班生成发展的政治文化总背景;再次,戏师权威地位的建构、民族戏班的权力分配与运行机制等,营建了别具一格的权力结构和政治体系;最后,在重构本土“社会资本”、开展“高台教化”、完善地方“自治”以及实现政治整合等方面功能显著。
地方戏;戏班;社会组织;民族政治;政治学
戏班亦称戏曲班社或戏剧团。作为一个传统民族社会组织,少数民族戏班相较汉族戏班而言有较大的差异性。据不完全统计,中国少数民族戏曲剧种约有30个。[1]3这些戏剧反映着不同民族的历史状况、社会形态、政治文化及宗教信仰等,戏班则是少数民族戏剧、戏曲的承载者。但少数民族有戏剧、戏曲等艺术形态,却并不意味着一定有戏班。作为一种社会组织的戏班,它是少数民族社会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目前对少数民族戏班的研究,关注度虽较以往有所增加,但研究的视角与深度均还有所欠缺,从政治学视角进行研究考量更能彰显其独特之处。
一、少数民族戏班生成发展的独特政治时空
少数民族戏班主要分布于我国的边疆民族地区,且大都诞生于明清以后。而学界普遍认为,汉族戏班诞生于宋朝,主要流传分布于中原地区。二者相比,少数民族戏班在生成发展的时间与空间上都独具特色,从政治学视角对其分析如下:
(一)“中间圈”:兼容并蓄的自然空间
少数民族戏班大多分布于我国的西北、西南等边疆地区,这一区域被王铭铭称为“中间圈”。所谓“中间圈”是王铭铭站在“世界性的空间定位”角度对古代“夷夏”之间一个宽阔的过渡地带所下的定义。[2]53-55他的“三圈说”看法认为,古代“华夏”王朝将其统治的核心区域称为“中国”,是帝国的“内圈”。而真正的“夷”则是在中华帝国大一统时代称臣于朝廷,并与之构成“朝贡关系”的外围政权,是帝国的“外圈”。那些处于二者之间,“似夷非夷”、“半文半野”的中间地带,就是“中间圈”。[2]179
这一区域的独特之处在于,它既是“华夷”政权之间政治或军事上的拉锯地带,又是古代华夏王朝对外进行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节点。许多地区更是形成了古代中国对外交流的“黄金走廊”,著名的如通向中亚、西亚和地中海沿岸的陆上“丝绸之路”,通向尼泊尔、印度的“唐番古道”、通向缅甸、印度的西南“马帮驮道”等。欧洲的古希腊、古罗马文明,西亚、中亚的伊斯兰文明,南亚印度文明,北非古埃及文明,再加上中原华夏文明等多元复杂的政治形态及文化形态,共同作用于边疆少数民族戏剧、戏班的形成发展过程。
从西域传入中国的戏剧主要有印度梵剧,波斯戏剧,希腊、罗马的悲剧以及毗邻地区的原始民族歌舞戏剧等。王文章(2013)研究指出,新疆很早就存在戏剧活动,主要是受印度梵剧的影响。梵剧随着大乘佛教从“罽宾弋山离道”传入新疆。经过长时间的孕育形成了维吾尔剧这一地方剧种。[1]543李强、柯琳(2003)也指出,西域民族戏剧的形成和发展……经历了“外国题材中国化,非现实的题材世俗化”的演变过程……是我国少数民族戏剧中形成历史较早,内容与形式较为成熟的一个特殊戏剧品种,是汉唐以来中西宗教与世俗文化交流的光辉结晶。[3]544-545
少数民族在吸收借鉴多种戏剧文化形态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本民族的戏剧,之后创造出了具有本民族特色的戏班组织形式。如王文章(2013)书中所载,青海民间藏戏队特别是寺院藏戏队不断发展增加……而且在果洛地区还有一种特别的藏戏——骑马演出的“马背藏戏”。[1]137由此可见,少数民族依托其独特的自然空间,通过长时间的吸收借鉴孕育了戏剧这种艺术形态,并于成熟后组建了具有本民族特色的戏班对其民族戏剧进行传播与传承。
(二)“中心—边缘”:基于地缘政治的制度空间
边疆少数民族戏班的生成往往受汉传戏班的影响,其大背景则是中央王权逐渐将边疆民族地区纳入统一“制度化”管理的过程。中国古代统治者将“天下”由中心到边缘划分为五种或九种空间层次,称为“五服之制”或“九服之制”,少数民族聚居区通常处于古代政治空间安排的最外围。伴随着专制制度的逐渐稳固,中央政权逐渐对外扩张,并加强了对边疆民族地区的管控与治理。少数民族文化在与中原文化碰撞交流的过程中,产生了新的文化形式及组织载体,民族戏剧及戏班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帝制后期,随着专制制度逐渐发展到顶峰,中央政权加大了对边疆民族地区的管辖和治理,一系列经济、政治、文化政策的颁布施行有效推动了中原地区与边疆民族地区的互动交流。王文章(2013)指出,我国少数民族戏曲古老剧种的诞生与明朝实行“土司制度”“军屯制度”,清朝实行“改土归流”制度,从而推动了南方各民族经济繁荣、社会安宁、文化发展密切相关。[1]7
但中央政权对边疆民族地区的管控与开发,有时也会因精神文化或物质利益等方面的不合而发生冲突。因而,民族戏班作为民族戏剧这一文化交融产物的承载者,其组织结构、组织策略、分布范围中多蕴含着中央政权与边疆民族之间权力交锋的影子。如张应华(2011)在研究湘黔交界处的石阡木偶戏班时发现,其组织方式、剧目分类等策略是当地少数民族文化和“沅湘”地区民族文化混成的结果,是在政府权力扩张的过程中,夷汉文化共谋协商的结果。[4]肖可(2011)在对布依族地戏戏班考察时也发现,它的地理分布状况及其剧目内容和特征,背后蕴含的是“布依—汉”之间文化的交流与碰撞。[5]
(三)明清:边疆地区的开发与民族戏班的诞生
汉戏班成型于于两宋时期,而少数民族戏班的生成时间则相对较晚。如王文章(2013)指出,我国少数民族戏曲的古老剧种,几乎都诞生于明清两代,尤其是清中叶以后。[1]7《中国戏曲志·广西卷》也记载到,流传于桂西隆林、百色等地的北路壮剧传说最早形成于乾隆三十年(1765)年。[6]72其他诞生于明清时期的少数民族戏班还有藏戏班、白族吹吹腔等。
汉戏班成型主要是受商品经济、市民社会发展的影响,而少数民族戏班的诞生则与明清时期的“改土归流”有着密切的关系。明清政府一系列政策的颁布施行使得西南民族地区政治、经济、文化得到了长足的发展。随着大量汉民涌入少数民族居住区,少数民族因此有机会吸收、消化外来文化,从而丰富本民族文化。如《布依族简史》(1984)中记载到,自明洪武后,黔西南州八个县均在不同时间、不同规模地建造了一些寺庙、书院、戏台等。随着汉族移民带来的汉文化的渗透,注入了布依戏形成的因素。[7]23另外,吴炳升、陆中午(2006)在研究侗戏的形成发展时也指出,明末清初时期,中原的政治、经济、文化逐渐向侗族地区渗透,刺激了侗族文化的发展。[8]6而早在两宋时期成型的汉戏班无疑也会随着中原汉移民迁移至侗族地区。傅安辉(2013)认为,侗戏创始人吴文彩通晓汉话,29岁外出到许多交通、商业发达的地方。因对汉族地方戏曲的浓厚兴趣,从而产生了编排侗族戏剧的强烈想法……吴文彩创作侗戏后就开始收徒授艺,成立侗戏班。[9]由此可见,部分少数民族在明清时期流传过来的汉戏班影响下,组建了本民族的戏班。
综上所述,民族戏班的生成发展与其所处的政治时空有着密切的关系。因而,将现有民族戏班研究置于古代地缘政治及边疆治理等政治学视角进行考察,既可以凸显民族戏班这一社会组织生成发展的独特性,又可丰富现有戏班研究的方法与视角。
二、少数民族戏班生成的政治文化背景——冲突与整合并构
伴随着中央权力的不断扩张及对边疆民族地区开发力度的加大,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原文化得以在边疆民族地区广泛传播,而民族戏班组织就是在吸收借鉴中原文化并主动进行民族文化再造的过程中逐步诞生发展的。
(一)“他者” 的渗透与本土化——以明清儒学为主
自程朱理学之后,中原地区儒学的发展逐渐僵化,但其在边疆民族地区的渗透却不断加深,并演化出了新的形态,这一过程被称为儒学的“内卷化”。“内卷化”这一概念最初源于美国人类学家戈登·威泽的研究。他将“内卷化”描述为一种文化现象发展到一定形态后,既无法趋于稳定也无法突破至新的形态,只能不断重复内向的复杂化过程。如周帆、黄守斌(2011)指出,明清时期侗族地区儒学化进程加快,侗戏始祖吴文彩就是以“廪生”身份创建的侗戏。[10]结合明清“改土归流”以后,府学、县学、义学在民族地区的的广泛设立可知,湘黔贵边区侗戏班的形成过程与清代官方正统政治文化——儒学的“内卷化”过程有着密切的关系。
且民族戏身上的“儒学”因子,从部分民族戏班所演的反应儒家道德伦理的经典剧目也可得到进一步的佐证。李强、柯琳(2003)在研究受汉族戏曲影响的少数民族戏剧时指出,壮、侗、布依、傣等少数民族的许多剧目就直接取材于汉戏或传奇小说,诸如《三国演义》《杨家将》《水浒传》《说岳全传》《梁山伯与祝英台》《孟姜女》等。[8]694-695这些剧目传达了忠、义、节的观念思想。郝广霖(2005)在研究戏曲与儒学的关系时就指出,儒学思想常居于封建社会意识形态的主流,给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留下了深刻的烙印……所以古代戏剧以忠孝节义为主要题旨……自然成为最突出的内容特色。[11]少数民族戏班在引进改编汉传剧本的过程中,有意无意就会将儒家之“忠孝节义”思想融入到自己的民族文化基因之中。
(二)少数民族文化的坚守与再造
虽然“儒学”伴随中央政权权力的扩张得以在民族地区强势传播,但少数民族对其也并非全盘接受,将自己的民族传统文化与新来的中原文化进行有机结合并再创造是少数民族的普遍选择。如周帆、黄守斌认为(2011)侗戏是清嘉庆至道光年间处于弱势的侗族文化主动接受并学习汉文化的产物。从汉戏到侗戏是一个本土化、民族化的过程,展示了侗族人直面强势文化冲击,善于吸收先进文化并结合本民族文化创造发展的内在力量。[10]
少数民族戏剧剧本也最能反映他们进行文化再造的努力。如李贵恩(1989)研究发现,壮剧的原始剧本《弄三色》演唱的是梁山伯,《弄送兄》演唱的则是英台送山伯。除改编汉戏剧本外,借用汉剧的形式将本民族英雄故事改编为剧本的也有很多,如《弄娅汪》讴歌的是宋景佑年间(1035-1037)的岭南壮族农民起义领袖扬梅(杨妹),“娅汪”就是女王的意思,《弄侬智高》歌颂的则是宋皇佑四年(1052)的壮族领袖侬智高。[12]再如吴炳升、陆中午(2006)《侗戏大观》中所载的传统侗戏《珠郎娘美》最初是由“侗戏鼻祖”吴文彩受汉族小说《二度梅》的启发而改编的。[8]21由此可见,少数民族在间接吸收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原文化基础上实现了民族文化的再造。
(三)中华民族文化“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的逻辑推演,是以中国地域文化的多元特征为起点,并在多元地域文化的交融和汇集过程中逐渐形成的。[13]民族戏班是中国各类戏曲戏剧得以相互借鉴融合的重要载体之一。正所谓“合则生物,同则不继”,各民族以戏班为载体进行的戏剧文化交流不仅促使中国戏剧文化推陈出新,更有效推动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
学者就汉族与少数民族相互之间的戏剧文化交流均做过研究。如原凯敏(2015)研究指出,盛唐时期云南爨国人(爨族)向中原王朝进贡了一支“爨戏班”,并认为爨戏集曲、唱、舞、歌为一体的表演形式促进了中原戏曲表演形式的形成。[14]这说明,边疆地区的独特民族文化为中原地区文化的发展注入了新的元素。王文章(2013)还指出,五世达赖阿旺洛桑嘉措于清顺治九年(1652)赴京觐见顺治皇帝时,观看了汉、满、蒙等民族的戏曲,回去之后就组织了自己的宫廷歌舞队,以及藏戏班。[1]2由此可见,民族地区戏班的生成往往是中国各民族文化协商共谋的结果,且这一文化交流协商的过程是双向的,边疆少数民族的文化也能为中原文化的推陈出新注入新的生机与活力。而民族戏班交流与发展的过程也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过程。
综上所述,少数民族戏班的生成发展与汉族戏班一样,均受到了“儒学”等中原文化的影响,但“儒学”作为文化“他者”借助戏班组织这一载体传播到少数民族地区之后,被少数民族吸收借鉴,并与其本土文化融合交流后实现了“自身”文化的再造。这一过程也为中国各民族注入了相同的“文化基因”,从而推动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
三、别具一格的权力体系——以藏、侗戏班为例
许多少数民族的戏班及其成员在其族群当中拥有较高的声望及地位,这从侗族俗语“讼师千人恨,戏师万人尊”就可见一般,而汉族戏班及成员被蔑称为“倡优乐户”或“下九流”,并通过“乐籍制”进行管制。二者同样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一)戏师与戏班的权威建构
对于权威的来源与建构方式,马克思·韦伯提出了三种正式的形式,即传统型权威、魅力型权威与法理型权威。传统型权威来自于已经确立的习俗或习惯,魅力型权威来源于领袖个人的非凡人格或超凡感召力,法理型权威则基于合理的规则和程序。少数民族戏师与戏班的权威主要为传统与魅力的混合型。
民族戏班作为少数民族社会“新兴”的社会组织,被少数民族纳入其传统政治体系当中,并借助戏班宣传他们的传统政治思想,这一地位帮助戏班构建了传统型权威。如严福昌(2007)研究发现,藏戏团演出演奏时所用的器乐,大部分是寺庙法器。演出前,必举行隆重的“烟祭”和供神仪式,并在诵经祈福后才开始戏剧演出。演出的剧目也以歌颂法王(土司本人自称法王)和狮王的善行。其宗旨是宣扬佛法无边、王者尊严,通过演出对群众进行“高台教化”。以强化其土司制度下的统治。[15]5而且,藏戏师在组织、排练戏班的过程中也因其丰富的知识、优秀的组织能力得到了普遍的敬仰,从而还获得了魅力型权威。
侗戏班也是如此。陈国凡等人(1986)指出,戏班组织是侗族村寨共同的集体事业,其最高领导权力机关是全寨的父老,机构设在鼓楼……戏师能力高,应变能力强,很受人尊敬[16]17且因侗族没有自己的文字,他们的文化传统只能口口相传,因而戏师的身份就显得愈加尊贵,并受到了族人的普遍敬仰。由上可见,藏、侗戏班及戏师均依托于本民族传统文化和个人才识建构了传统、魅力相结合的混合型权威。
(二)与汉人“家班”相异的权力分配与运行机制
民族戏班作为一个社会组织,它并不是一个自足的体系,其人员构成与组织方式与它所处的社会环境、政治体系有着密切的关系。严福昌(2007)发现,在嘉绒藏戏的发展过程中曾经涌现出不少的名僧艺师。[15]50王文章(2013)在研究藏戏班时也指出,18世纪中叶,西藏设立一僧三俗的噶厦政府 ,职派管理布达拉宫内务的官员,直接负责组织、管理藏戏的演出。藏戏班有由头人、施主或寺院高僧扶持组织的,还有僧兵或藏兵自己组织的。[1]21可见,藏戏班的组织人、参与人均具有较高的地位,其组织方式也反映了藏族“政教合一”政治体系的特点。
另外,吴炳升、陆中午(2006)在《侗戏大观》中写到,侗戏班由戏师、主管以及村寨中的年轻人自愿组成。主管是村里有很高的权威性和组织能力的老者,由他协助戏师组建戏班。[9]16而侗族社会的管理方式,有学者将其称为“准公民社会”,其政治体系则被称为“地方性的原始民权政治”[17]22-25。可见,侗戏班的组成人员及全凭自愿的组织方式,类似于侗族原始村社式的民主政治体系。
综上所述,少数民族戏师与戏班的权威建构,戏班组织内部的权力分配、运行机制与本民族的传统政治体系、政治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无论是藏戏班“政教合一”的组织方式还是侗戏班“民主式”的组织方式,均与汉族戏班“宗法制”下的家班有着本质的区别。
四、少数民族戏班独到的政治功能
在“王权不下县治”的时期,少数民族村社大都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治理体系与治理方式。少数民族戏班作为民族地区的重要社会组织之一,拥有着较高的权威,这就使其有条件参与到民族地区的治理当中,发挥着独到的政治功能。
(一)有效重构本土的“社会资本”
“社会资本”产生于组织网络之中。包括普遍信任在内的公民参与、共享的规范及价值观等特点,是社会资本的理论内涵。[18]而村社治理的难点就在于普遍信任、社群观念与公共精神,这些是村民之间能够相互合作,良性互动所必须具备的“社会资本”。民族戏班的组织及活动过程能够生产这些“社会资本”,并促使这些“社会资本”得以增值。
首先,从戏班组织层面来说。戏班组织通过在节庆日期间为村民提供文化产品的方式,得到人们的赞赏、尊敬和信任,使得组织整体的社会资本量得以增值。陈国凡等人(1986)在《侗戏志》中还写道:侗戏班的演出,特别是“月也戏”活动的举行不仅丰富了侗家的文化生活,同时,还促进了侗乡人民寨与寨之间的团结与友谊,是侗乡人民通向团结和友谊的桥梁。[17]18可见,民族村社之间的社会资本量也通过戏班的走访表演得到了增值。
其次,从戏班成员个体来说,不少少数民族戏班的成员利用戏班组织产生的“社会资本”使自己在民族村社中拥有较高的地位,建构了自己的政治权威。如李强、柯琳(2003)通过研究发现,戏曲文学被少数民族视为“强宗旺族”的标志。[18]694严福昌(2007)在对嘉绒藏戏的艺人与戏班进行研究时也指出,人们藏戏艺人十分尊敬。[16]51因而,参与戏班组织的族民以及戏师傅能够获得一定的声望,从而提升个人的社会资本量,许多戏师也因此获得了新的政治身份,成为维护村寨秩序的权威人物。
(二)“高台教化”与政治社会化
戏班通过戏剧表演这一“柔性的力量”能有效推动民族地区的政治社会化。很多少数民族戏班所演剧目多取材于本民族的历史传说或生活故事,其中蕴含着本民族的传统政治文化,且很多少数民族还将现实生活中的道德观、伦理观编成耳熟能详的歌曲、戏词进行传唱。
如严福昌(2007)通过统计整理发现,嘉绒藏戏的内容有历史故事、佛经故事、人物传记、生活趣事等。[16]32藏民视藏戏为神戏,看藏戏为接受“高台教化”。朱恒夫(2009)也指出,羌族释比戏、傣族的傣剧等,均在表演汉族剧本时将本民族的传说故事、道德伦理融入其中,观众每看一次,就接受一次心灵的洗礼,并且常年多次的接受教育。[19]
民族戏班的政治社会化功能通过民族戏剧的表演来实现。戏班通过表演戏剧,在戏台上使民族历史空间得以再现,族民通过参加或观看戏剧表演逐步获取了本民族的传统政治知识与能力,形成了自己的政治意识与政治立场,实现了民族政治文化的继承与发展。此外,族民通过观看本民族戏剧还能产生情感共鸣,这进一步增强了村民之间的认同感与归属感,从而达到了团结村寨、维持秩序的目的。
(三)地方“有序化”与“自治”
民族戏班的组织也有利于地方秩序的维护。廖君湘(2005)认为,侗族传统社会外在控制方式有社会组织控制、社会舆论控制、风俗习惯控制和习惯法控制四种。侗戏班正是社会组织控制的一部分,承担着规范社会舆论、传承风俗习惯等功能。[18]53彭庆军(2013)通过个案研究也发现,侗戏班等文化表演团队经常性地造访湖南通道县坪坦村,结果使得该村的社会治安、社会风气明显高于其他村寨。[20]
笔者在对湘黔桂边区的现代侗戏班进行调查时发现,在三江县出现了一种新的戏班组织形式——农民工戏班,它打破了侗戏班以村寨、鼓楼为单位进行组织的惯例,由各个乡镇进城打工的农民工出于自愿组成,通过一起学戏、唱戏的方式来遏制赌博现象,并且还排练关于戒毒的剧目进行宣传,有效地对进城务工人员进行了组织管理,维护了城市社会秩序。而且,三江县司法局也借助侗戏班编演法治剧本来进行法治宣传,这种方式极大地提升了村民的法律意识。
(四)政治整合:从政治认同到国家认同
民族戏班还具有强化政治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功能。如严福昌(2007)研究发现,嘉绒藏戏在历史上除为土司、奴隶主、王公贵族演出外,20世纪30年代红军长征时,亦为欢送工农红军北上抗日演出过。1935年,当红军路过阿坝州卓克基地区时,卓克基戏班为红军演出了《格冬特青》中的“英雄战胜降妖魔”(军士舞)片段。[16]31可见,在战争时期,藏戏班通过为红军演出戏曲的方式表达了藏民对红军的拥护和认同。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国的执政党,许多民族戏班进一步为党和国家的政策宣传服务。如吴永华(2010)撰写的新闻中写道,广西三江良口的侗戏艺人杨开远同时也是村里的党支书,他成立的戏班将党委政府的各项惠民政策编成侗戏剧本,使村民通过这一方式了解党和政府政策,掌握了脱贫致富的信息和技能。[21]通过这一方式,使少数民族群众加强了对党和国家的认同感。
综上所述,民族戏班组织作为民族地区的重要社会组织,基于其较高的权威与地位,发挥了独到的政治功能,不仅成为了民族村社秩序的有力维护者,更是现代国家对民族村社进行政治整合的有效组织载体。
五、余论
据上文知,民族戏班组织的差异性主要就在于,它既是特殊政治时空下的历史产物,又能独立发展出全新的政治个性,以新的身份和组织能力,营造新的政治参与路径和政治生态。所以,其价值当不仅仅只是一种文化遗产,而更是一份厚重的政治遗产,对于探讨边疆民族区、省际交界区的治理秩序极具意义。
当然,差异性也是多样性,在呈现中华民族多元的政治智慧和政治创新的同时,又会因民族戏班的繁富活跃,终让此项研究更显复杂艰难。甚至于,即使是同一少数民族,也会因其居地空间、时代际遇、社会关系等方面的不同而自成一格。为此,民族戏班既是政治学开拓研究新域的对象,也将是坚守和发展政治学实践原则的一个理想场域。
最值得警醒的是,在日趋深入的城镇化进程中,民族戏、民族戏班组织皆显式微,陷入了无人传继、行将归逝的宿命,也许正如诸多学者所断言,这就是历史发展优胜劣汰规律的本来反映。但是,这一粗率简单的历史决定论,显然忽视了民族戏班组织与当代基层政治发展的逻辑关系。
[1] 王文章.中国少数民族戏曲剧种发展史(上、下)[M].北京:学苑出版社,2013.
[2] 王铭铭.中心圈:“藏彝走廊”与人类学的再构思[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
[3] 李强,柯琳.民族戏剧学[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3.
[4] 张应华.湘黔交界少数民族社区的汉传戏班[J].艺术探索,2011(12).
[5] 肖可.从布依族地戏的分布看布依—汉的文化接触[J].贵州民族学院学报,2011(4).
[6] 中国戏曲志编委会.中国戏曲志·广西卷[M].北京:中国ISBN中心,1995:72.
[7] 《布依族简史》编写组.布依族简史[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4:23.
[8] 吴炳升,陆中午.侗戏大观[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6.
[9] 傅安辉.吴文彩创立侗戏对侗族文化艺术的影响[J].原生态民族文化学刊,2013(5).
[10] 周帆,黄守斌.侗戏:柔性的力量[J].文艺研究,2011(11).
[11] 郝广霖.戏曲与儒学[D].济南:山东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5.
[12] 李贵恩.壮剧史源再探[J]民族艺术,1989(3).
[13] 陈建樾.多元一体:多民族国家内部的族际整合与合法性[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5).
[14] 原凯敏.云南少数民族爨文化与中原戏曲艺术[D].西安:陕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5.
[15] 严福昌.四川少数民族戏剧[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7.
[16] 三江侗族自治县文化馆编纂组.侗戏志[G](内部资料),1986:17.
[17] 廖君湘.侗族传统社会过程与社会生活[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9:22-25.
[18] 吴军,夏建中.国外社会资本理论:历史脉络与前沿动态[J].学术界,2012(8).
[19] 朱恒夫.论中国少数民族戏剧的特征[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5).
[20] 彭庆军.论民族地区传统社会组织的创造性转化——以湖南省通道侗族自治县为例[J].华中科技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5).
[21] 吴永华.侗戏村支书唱富穷乡村[J].农友之家,2010(6).
责任编辑:陈沛照
C912.4
A
1004-941(2017)06-0015-05
2017-01-04
广西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广西民族大学中国南方与东南亚民族研究中心资助 “广西三江侗戏师的历史沿革与生存现状”(项目编号:2016ZXS010);2017年广西研究生教育创新计划项目“湘黔桂边区侗族戏班组织及其政治功能研究”(项目编号:YCSW2017125);广西民族文化保护与传承研究中心研究生创新项目“湘黔桂交界处侗戏的公共资源化及认同建构研究”(项目编号:2017CXYB08)。
杨天保(1971-),男,湖北黄冈人,博士,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政治人类系、思想史;张强伟(1992-),男,山西吕梁人,主要研究方向为政治学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