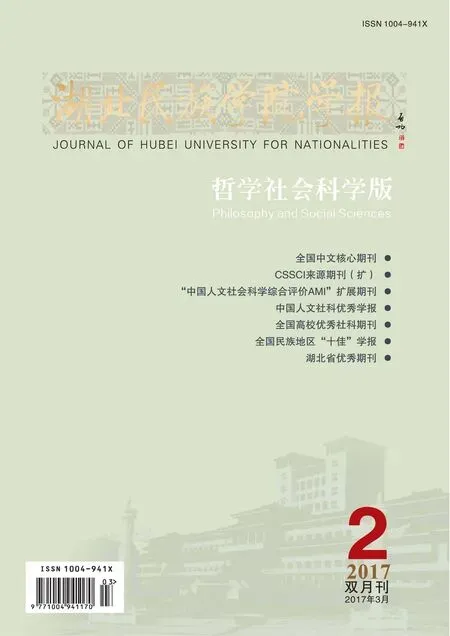初唐传奇中的第一人称叙述视角作品探析
江中云
(信阳师范学院 文学院,河南 信阳 464000)
初唐传奇中的第一人称叙述视角作品探析
江中云
(信阳师范学院 文学院,河南 信阳 464000)
中国古代小说特别是文言小说作品一般都采用第三人称全知叙事的叙述视角,而很少有第一人称限知叙述视角作品的出现。难能可贵的是初唐传奇作品中已开始呈现较为成功的第一人称叙述视角的作品,如《古镜记》、《游仙窟》,尽管作品数量寥若晨星,但它们在展示人物心理的曲折、提升故事的真实性等方面较第三人称叙述视角有着明显的优势,探究它们的特点和价值也具有小说史的意义。
初唐传奇;第一人称叙述视角;人物心理;真实性
叙事体文学作品诸如小说、戏曲等类型的核心内容便是叙述,叙述即是记叙和述说,它是一种记人叙事并陈述其来龙去脉的表述方法。这种表述的过程中涉及到一个由“谁”站在什么“位置”来叙述的问题,也就是作品中对故事内容进行观察和讲述的角度问题,这就是叙述视角问题。作家正是通过他所选定的叙述视角将人物、事件也就是故事的一切告诉读者的。
一、叙述视角的类型及特征
叙述视角也称叙述聚焦,是叙述语言中对故事内容进行观察和讲述的特定角度。叙述视角的特征通常由叙述人称决定的,而叙述人称一般来说也就是第三人称叙述、第一人称叙述、第二人称叙述、人称或视角变换叙述四种类型。其中的第二人称叙述视角较为罕见,而人称或视角转换的叙述视角也相当特殊。比较常见的便是前两种。
第三人称叙述是从与故事无关的旁观者立场进行的叙述,传统的叙事作品通常采用这种叙述。由于叙述者是身份不确定的旁观者,由此造成这种叙述的显著特点便是无视角,叙述者可以在同一时间出现在各个不同的地点,他知晓过去、了解现在、预知未来。一句话,第三人称叙述的叙述视点可以任意游移,叙述者无所不知、无所不晓。这种叙述视角因为没有视角限制而使作家获得了充分的自由。
第一人称叙述的作品中叙述者同时又是故事中的一个角色,叙述视角由此也就移入作品内部,成为内在式焦点叙述,也就是叙述者所知道的同故事中的人物知道的一样多。叙述者借助某个人物的感觉和意识,从他的视觉、听觉及感受的角度去传达一切。由于叙述者直接进入故事和场景之中,或讲述经历,或转述见闻,其话语的可信度、亲切性自然超过第三人称全知视角叙事。一如《叙事学导论》所言:“叙述者存在于虚构的小说世界中。第一人称叙述者就像其他人物一样,也是这个虚构的小说世界中的一个人物,人物的世界与叙述者的世界完全是统一的。”[1]第一人称叙述视角中的叙述者虽不能像第三人称叙述视角那样全知全能,且无法提供人物尚未知晓的东西,但拉近了作者与读者之间的距离,易为读者接受和相信。
当然,不同的叙述视角决定了作品不同的构成方式,并且也决定了接受者不同的感受方式。第三人称全知全能的叙述,可以使阅读者感到轻松,只管看下去,叙述者会把一切都告诉读者。但是,这种方式迫使读者被动地跟着叙事跑,留给读者再创造的的空间特别有限,且容易遭致读者对叙事真实性的怀疑。第一人称限知叙述可以使阅读者共同进入角色,有一种身临其境的真实感,也便于揭示人物内心世界的隐微。但它难以用来叙述背景深厚、头绪繁杂、题材重大的故事。
二、古代小说中第一人称叙述视角少见的原因
提起用第一人称叙述视角创作的小说,很多人会想到西方的莫泊桑、狄更斯、契诃夫,也会想到中国的鲁迅。也有人认为中国小说运用第一人称叙事的模式是从国外引进的,但事实并非如此。中国的第一人称小说既不是来自外国,也不是鲁迅首创,而是在我国古已有之。
从叙述视角上纵观中国古代小说发展史,第三人称全知叙述视角的作品比比皆是,而第一人称叙述视角的作品不仅出现甚晚,且少之又少。汉魏六朝时期的小说作品尽管只是“粗陈梗概[2],”也均是第三人称全知叙述视角。直到唐传奇才开始出现第一人称叙述视角的作品,但数量很少。最早出现的则是初唐时期的单篇传奇作品《古镜记》和《游仙窟》,稍后的则是中唐时期的《古岳渎经》和《周秦行纪》。究其原因,不难看出,深受传统史传文学影响的古代小说在叙事模式上完全承袭了史传文学的第三人称叙述视角。
史传是我国最早成熟的叙事体作品,史官在对过往历史进行记写时,不可能采用第一人称叙述视角将自身移入作品之中。再加之第一人称叙述视角仅将叙事范畴局限在“我”的视野中,这就不利于全方位全视角地叙述宏阔复杂的历史画面和具体而微的历史事件,且第一人称叙述极易蕴涵作者的主观感情色彩自然不符合史传作品秉笔直书的实录精神。因此,第三人称全知叙述视角也就成为史传文学的首选和最佳方式。依附于史传文学而产生的小说在叙述的视角与方式上也是长期受其影响,这就导致了我国古代小说作品在第一人称叙述视角上的极度匮乏现象的发生。
其次,我国古代小说观念的演变经历了曲折的过程。唐传奇出现以前,古典小说一直被视为“小道”“末流”,以史传的附庸身份存在着,在我国文学史上长期处于被轻贱的地位,这也限制了第一人称叙事在小说中的出现。在小说和小说家被歧视的社会环境下,作者是不敢毫无顾忌地采用具有个性色彩的第一人称视角进行叙事的。而在古典小说较为繁荣的明清时期,统治者大兴文字狱,小说作家迫于政治环境和文化氛围的双重压力,大多数人在创作小说时都避免采用容易流露自己主观情绪的第一人称叙事视角,甚至出现小说家在作品中不愿署名或另用别名、化名的异常文化现象。小说家们不肯在自己的作品出现任何自我暴露的痕迹,不愿让小说中描写的故事与自己沾上关系,这也直接导致了第一人称叙述视角小说的罕见。
另外,中国古典小说具有强烈的教化色彩,几乎无一部无一篇不蕴含着劝戒说教的意图。为了使小说摆脱“小道”“末流”的文学地位,作家们便尽力把小说向经史靠拢。小说和经史的形式虽然不同,但二者反映的内容却是相近的,而且小说比经文更容易吸引读者而达到劝善惩恶的目的。如果小说可以劝善惩恶,那么小说家们便可以理直气壮地将其提升到文学正宗之位,同时,深受儒家伦理文化影响的古代小说家们也多抱有劝善惩恶的创作目的,小说重在写理,向读者宣扬儒家伦理意识,其教化的实质多是宣扬儒家思想的忠孝节义的内容。而第一人称叙述视角是最具个性和个人化的叙事,古典小说本身所蕴含的教化色彩就制约了个性化叙事的出现。小说家们常常采用全知全能的第三人称叙事方式,忽视对自我情感的抒发,仅靠讲述别人的故事以达到说教目的,而不是运用第一人称限知视角将自己的经历和思想情感融入小说,让读者发现和了解“我”的性格个性。
正是上述的种种原因才造成了中国古代小说史中以第一人称叙述视角创作的小说作品寥寥可数,而且这些第一人称叙述视角的作品诞生较晚。
如前所述,魏晋六朝以前,我国古代小说完全继承了史传的第三人称叙事方式,直到唐传奇,才开始真正出现了第一人称叙述视角的小说作品。著名的如《古镜记》《游仙窟》《周秦行纪》等。此后的明清小说中也有少量作品是采用第一人称叙述视角进行创作的,如明代的寓言小说《东游记异》、艳情小说《痴婆子传》,明末清初有神怪小说《吕祖全传》、短篇小说集《虞初新志》中的一篇《看花述异记》,清代有文言小说集《聊斋志异》中的几篇故事、自叙性散文体小说《浮生六记》等。这些作品在中国古代小说的漫漫长河里尤为稀少,但它们的存在说明在中国古典传统小说里可以寻找到第一人称叙述视角的“根”。尽管中国现当代小说拥有大批以第一人称叙述视角进行叙事的作品,其固然有近代西方翻译小说影响的因素,但更是中国古代小说自身发展演变的结果。也就是说,小说中第一人称叙述视角的“根”是深植于中国传统古典小说之中。
三、强化故事真实性的《古镜记》
法国结构主义文艺批评家杰拉尔·热奈特曾说过:“叙述者的叙述功能有五种:叙述功能,组织功能,评价功能,见证功能,交流功能。”[3]第一人称叙述视角的小说作品里,作者既是叙述者,又是故事的见证者,也可以是小说中的一个重要人物,诸如主人公之类。依照热奈特的理论来说,第一人称叙述视角的作者具有叙述功能、见证功能、评价功能,还同时具有人物角色的多重功能。作者去讲述故事,同时又是故事中的一个重要角色,他既可以见证或参与故事发生的过程,也可以离开故事的环境而向读者进行描述和评价故事本身。要知道,在小说作品中,以第一人称向读者讲述自己亲眼见证或亲身经历的故事,很容易给读者一种真实存在或真正发生过此事的感觉,一下子也就拉近了作者和读者之间的距离,从而在读者的内心深处造成一种身临其境的真实感。初唐时期王度的传奇小说《古镜记》就属于充分体现见证功能的第一人称叙述视角的作品。
作为唐人传奇的开山之作,王度的《古镜记》采用第一人称限知叙述视角,以“度”也就是“我”的所见所闻,依次记叙了古镜一生所发生的十二件灵异之事。故事中的古镜是中心,也可称为“主人公”,而发生在古镜身上的一系列奇异之事,则由次要人物也就是目击者、见证者王度一一道出。王度在长乐坡程雄家亲手用古镜降服了狸精鹦鹉;王度见证了古镜与当时发生的日食相呼应;月圆之夜,王度亲眼目睹了古镜竟让闪闪发光的铜剑黯然失色;在芮城任职期间,王度用古镜制服了蛇妖,消除了疫病;即便是王度的弟弟王绩携古镜远游,也同样是降妖伏魔,屡立奇功。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借助于王度的亲身经历、亲眼所见、亲耳所闻,重点突出了古镜的珍贵而奇异,也强化了古镜灵异的真实存在。最后,又专门交代古镜失去之日正是隋朝灭亡之时。
显然,小说中的“我”是“主人公”古镜一系列灵异故事的见证者和转述者,全部故事均在“我”这个次要角色的叙述视角下有条不紊地进行着。“我”的叙述功能、见证功能和人物角色的功能均已具备。故事中的王度与古镜有着密切的关联,他亲身经历或亲眼目睹了古镜的神奇,除了“度”,故事中还有侯生、胡僧以及王度的弟弟王绩,这些人物在故事中与古镜相关的言行也都是被“度”一一转述的。因此,王度亲身经历、亲眼所见古镜的奇异,以及转述他人所言古镜的神奇,也就共同构成了“主人公”古镜的来龙去脉、富有传奇色彩的完整一生。读者跟随着亲切自然的第一人称叙述视角,仿佛置身其间,自觉不自觉间也就消除了横亘在读者与作者之间的理解障碍,使读者从内心深处产生一种身临其境的认同感、真实感。其可信度与亲切感自然要大大超过第三人称全知全能的叙述视角。其提升故事真实性的效果显而易见,“读者往往深受叙事者的感染,不知不觉地沉浸于叙事者‘我’营造的虚构的艺术世界中不能自拔,丧失应有的警惕性,从应保持的怀疑态度转而完全相信‘我’的故事。相信所读到的故事,可以进一步延伸相信叙事人,从而接受其情感、思想、道德观念等等。”[4]
另外,小说中的“度”又可以随时离开故事的环境对所叙古镜之事做出感情反映和道德评价,意味深长地抒发了作者内心深处的人生感慨。这点突出表现在小说的开首和结尾对古镜得而又失的呼应上:
虽岁祀悠远,图书寂寞,而高人所述,不可诬矣。昔杨氏纳环,累代延庆,张公丧剑,其身亦终。今度遭世扰攘,居常郁怏,王室如毁,生涯何地?宝镜复去,哀哉!今具其异迹,列之于后。数千载之下,倘有得者,知其所由耳。[5]1761
大业十三年七月十五日,匣中悲鸣,其声纤远。俄而渐大,若龙咆虎吼,良久乃定。开匣视之,即失镜也。[5]1767
“王室如毁,生涯何地?宝镜复去,哀哉!”隋朝大业十三年(公元617年)正是隋军战败、隋炀帝决定迁都江都的日子,作者将古镜的失去与隋王朝的灭亡相对应,也就意味深长地表达出救世无术的悲愤与绝望之情。
与此同时,小说始终将古镜的得失、神奇与作者身处的隋王朝的兴亡联系在一起,古镜的一桩桩奇异故事均发生在隋炀帝大业七年(公元611年)至大业十三年之间。诸如:
大业七年五月,度自御史罢官归河东。适遇侯生卒,而得此镜。
大业八年四月一日,太阳亏。度时在台直,昼卧厅阁,觉日渐昏。诸吏告度以日蚀甚。整衣时,引镜出,自觉镜亦昏昧,无复光色。
大业九年正月朔旦,有一胡僧行乞而至度家。弟出见之。觉其神采不俗,更邀入室,而为具食,坐语良久,胡僧谓曰:“檀越家似有绝世宝镜也,可得见耶?[5]1763
要知道,大业七年正是山东人王薄首揭义旗、号召起义之年,之后,起义烈火燃遍了黄河南北,逐渐向江淮推进。生活在隋朝末年的王度亲身经历了隋王朝迅速走向衰亡的日日夜夜,眷恋故国、无力回天的惋惜与悲痛之情充溢胸间。作者笔下的古镜神通广大,降妖伏魔,劫富济贫,普惠众生,王度曾希望用它来造福于百姓,但镜精却表明自己不能够“反天救物”,甚至王度本人也不能够长期拥有这面古镜。作者借古镜的灵异反映了隋末社会的动乱与黑暗,抒发了内心深处无可奈何的怜惜与悲痛之情。从这一点来讲,小说的主旨超越了六朝志怪小说的搜奇记异,而上升至抒发情感、寄寓怀抱上,初步呈现了与六朝志怪小说的不同,充分体现了小说作家创作主体意识的自觉。这在文言小说发展史上也是一种质的飞跃。
四、展示人物心理曲折的《游仙窟》
程毅中先生曾言:“《游仙窟》是唐代小说中最特殊的一篇作品。”[6]陈文新先生也说:“《游仙窟》是唐人传奇的一篇特殊作品。”[7]的确,在唐传奇中《游仙窟》比较特殊,这种特殊性既体现在题材内容的转变方面,又表现在艺术上的发展与创新上,且均具有着小说史的意义。就其内容而言,《游仙窟》由六朝志怪小说写鬼怪神异成功转变为写人世间的悲欢离合。《游仙窟》在艺术技巧上的发展与创新更是体现在多种层面上:一是人物形象的成功塑造;二是描叙的细腻完整;三是文辞华艳,骈散结合;四是第一人称叙述视角的出色运用。《游仙窟》从内容到形式上的发展与创新也就铸就了它在文言小说发展史上的非同凡响,一如《中国文言小说史》所言:“《游仙窟》基本上完成了由志怪小说向唐代小说的过渡。”[8]
张文成的《游仙窟》以第一人称叙述视角,用骈散相间的一万余字铺陈了作者本人“历访风流,遍游天下”的一次风流艳遇。作者以“余”、“仆”、“下官”等称谓,自叙奉使河源,日晚途遥,马疲人乏,寻至神仙窟投宿,与女主人崔十娘、五嫂以诗相会,三人宴饮歌舞,调情作乐,由五嫂做媒,“余”和十娘做的一夜夫妻,一宿而别,依依不舍,惆怅不已。
“余”既是故事的叙述者,更是故事的男主人公,整个故事情节的发展与推进、人物形象的出场与塑造、场景的更迭与转换,全都在“余”的视野与掌控之中。主人公叙述自己的故事,自然而然地就带有一种亲切感和真实感,相比《古镜记》中的叙述者、见证者的王度而言,他给读者的感觉也就更加真实可信。
这种主人公视角的最大优势则在于从容地走进主人公自己的内心世界。要知道,人物形象的塑造固然离不开叙述者对其行为、言语、相貌等的描写,同时更要借助于细腻丰富的内心披沥,才能真正地完成。而这种第一人称叙述视角特别便于揭示和剖析主人公自己的深层心理,且对于其他人物,也可以通过外貌、言行等外部描写的方式走进人物的内心世界。在第三人称全知全能叙述视角的作品中,只要叙述者想办到的事,都能办到。想听、想看、想走进人物的内心、想知道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发生的任何事情,均不难做到。这种方式固然有着视野开阔、时空穿越、全方位地描述人物和事件的优势,但也正是这种全知全能、无所不晓,才受到读者的挑剔与怀疑:他是怎么知道某地发生了什么事的?他是如何清楚某人内心是怎么想的?他为何不向读者作出解释?种种疑问自然生出。相比之下,读者对第一人称叙述视角也就是主人公视角的挑剔与质疑也就不存在了。在第一人称叙述视角的作品中,叙述者也就是主人公只要自己愿意,他就可以袒露内心深处的隐秘,即便他的话语有些夸张或谦恭,读者也会认同其性格的外现而置之不理。
《游仙窟》一开始叙述时就直率地道出“余”的所思所想与所为:
余乃端仰一心,洁斋三日。
余乃问曰:“承闻此处有神仙之窟宅,故来祗候。山川阻隔,疲顿异常,欲投娘子,片时停歇;赐惠交情,幸垂听许。”女子答曰:“儿家堂舍贱陋,供给单疏,只恐不堪,终无吝惜。”[9]78
原来“余”也就是作者寻觅住所并不仅仅因为日晚途遥,人困马疲,而是有探寻神仙窟之究竟的意图。“端仰一心,洁斋三日”、“承闻此处有神仙之窟宅,故来祗候”,直白地袒露了“余”的好奇猎异、率性、风流的内心世界。
《游仙窟》中,“余”是一个风流放荡、搜奇猎异、文才出众的士子;崔十娘则是一位气度优雅、美丽多情、内敛腼腆的才女;五嫂是一个雍容华贵、艳冶妖媚、能说会道的少妇。在“余”的眼里,十娘与五嫂不仅容颜姣美,且是才思敏捷、出口成章、“足使班婕妤扶轮,曹大家搁笔”的才女。“余”与十娘、五嫂的诗歌唱和,不仅推进了情节的发展,塑造了个性鲜明的形象,更是细致入微地剖析了主人公、十娘、五嫂的心理轨迹。“余”与崔十娘初会时的诗歌互答即可明显地见出风流大胆的“余”,以及娇羞腼腆的十娘、善于言辞的五嫂的个性。
余读诗讫,举头门中,忽见十娘半面,余即咏曰:“敛笑偷残靥,含羞露半唇;一眉犹叵耐,双眼定伤人。”
又遣婢桂心报余诗曰:“好是他家好,人非著意人;何须漫相弄,几许费精神。”[9]97
文中“余”所咏“敛笑偷残靥,含羞露半唇”之句,很好地刻画了十娘欲拒还迎、欲语还休的娇羞之态与佯羞假嗔的心理。当十娘意欲出来会见作者“余”时,竟是“匣中取镜,箱里拈衣。袨服靓妆,当阶正履”,这一系列精心妆扮的动作也就生动形象地把年轻孀居的崔十娘的腼腆、迟疑、犹豫,最终做出会面决定的心路历程和盘托出。尔后,作品中的“余”又是用诗句一步步试探十娘,并最终与十娘缠绵缱绻一宿;离别之时,双方又有一系列的赠别诗,也都很好地表达了一对难舍难分的情人内心深处的生离之痛。尤其是十娘所咏的离别诗更是痛彻心扉:
别时终是别,春心不值春。羞见孤鸾影,悲看一骑尘。翠柳开眉色,红桃乱脸新。此时君不在,娇莺弄杀人。[9]237
整篇小说的情节发展和场景转换都没有逾越主人公也就是“余”的视野范畴,这种第一人称叙述视角在描摹人物丰富的内心世界方面比第三人称全知叙述视角有着更加便利且不被读者质疑的优势。“余”的性格得到了形象的展示,“余”的心理描写也更加真实贴切:“余”与两位女性调笑戏谑时的酣畅肆意,与十娘缠绵缱绻时的欢悦欣喜,以及离别时的惆怅难舍等。这些隐微深沉的内心活动都使“余”的性格得到了更加丰满、生动的体现,且使读者对小说的内容产生一种强烈的认同感与真实感。还有前述的十娘的个性特征与心理活动也有形象的刻画与展示。
由上可见,我国小说史上第一人称叙述视角的“根”深植于传统古典小说特别是唐传奇之中。因此,探究最早出现第一人称叙述视角的初唐传奇作品的文学价值和艺术魅力,对于系统了解中国古典小说的叙事格局和创作手法,以及第一人称叙述视角对近现代小说叙事技巧和表现形式的丰富创新,具有着积极深刻的小说史的意义和价值。
[1] 罗纲.叙事学导论[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163.
[2]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32.
[3] (法)杰拉尔·热奈特.叙事话语[M].王文融,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257.
[4] 顾建新,孙艳秋.小说第一人称叙事再探[J].写作,2006(5):30-32.
[5] (宋)李昉.太平广记(第五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1.
[6] 程毅中.唐代小说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107.
[7] 陈文新.文言小说审美发展史[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200.
[8] 吴志达.中国文言小说史[M].济南:齐鲁书社,1994:275.
[9] (唐)张文成.《游仙窟》校注[M].李时人,詹旭左,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0.
责任编辑:毕 曼
2016-10-28
江中云(1965-),女,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传统文化与古代文学。
I207.41
A
1004-941(2017)02-0138-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