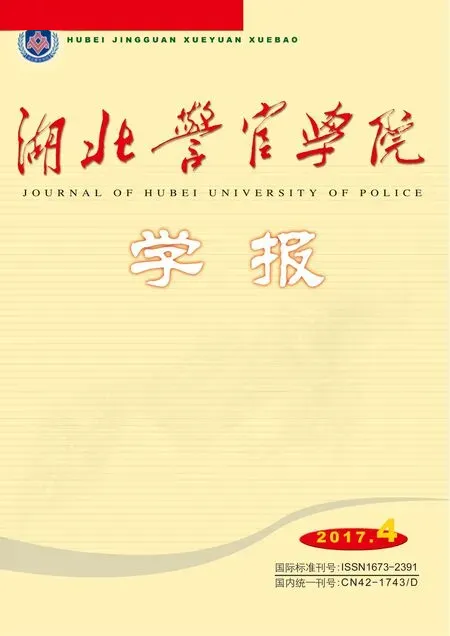口供证据补强规则研究
王瑞恒,姜文捷
(辽宁师范大学 法学院,辽宁 大连116000)
口供证据补强规则研究
王瑞恒,姜文捷
(辽宁师范大学 法学院,辽宁 大连116000)
口供证据补强规则是指对证明力明显薄弱的、能够证明案件全部事实或主要事实的有罪口供,要求有其他证据予以证实才可以作为定案依据的规则。口供证据补强规则由被补强的口供范围和对象、用以补强口供的证据、补强证据的证明程度四个方面构成,当内在构成达到完善的程度时,口供证据补强规则就能够发挥保障口供真实性、防止误判和防止过分倚重口供、保障人权的功能。但是,我国的口供证据补强规则存在很多问题。在理论上,对被补强的口供范围和对象、用以补强口供的证据、补强证据的证明程度等规定不明确。在实践中,缺乏适用口供证据补强规则的指导和标准。基于口供证据补强规则存在的问题,应当从明确被补强口供的范围、明确口供补强的对象、明确用以补强口供的证据、明确补强证据的证明程度四个方面完善口供证据补强规则的内在构成。
口供证据;补强规则;证明程度;证据条件;口供范围;补强对象
口供作为证据的法定种类,对证明案件事实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了两种情况:一种是有些案件没有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口供,其他证据确实充分,可以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定罪并予以处罚。另一种是运用已经获取的口供,结合其他证据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定罪量刑,这种情况在刑事诉讼程序中比较常见。但是,在这一过程中有时存在错误运用口供、侵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权利的情形。2012年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体现了我国的刑事诉讼理念从惩罚犯罪为主向更加注重保障人权转变的趋势,这一转变对运用口供的过程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即要求司法人员更谨慎地运用口供。因此,应当在刑事诉讼过程中限制和规范对口供的适用,口供证据补强规则正是可以实现这一要求的重要规则。
一、口供证据补强规则的涵义、缘起及内在构成
补强证据规则(corroborationrequirement),是指为了防止错误认定案件事实,对某些证明力明显薄弱的证据,要求有其他证据予以证实才可以作为定案依据的规则。[1]在英美法中,补强证据规则的对象是言词证据,不仅包括自白也包括证人证言等证据。但是,补强证据规则在大陆法发展的过程中,逐渐演化为主要适用于口供,口供证据补强规则由此而来。
(一)口供证据补强规则的涵义及缘起
对于该规则的内涵,有的学者认为:口供证据补强规则是基于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合法权利的目的而存在的,应当用其他符合法律规定的证据对其所作口供加以佐证,才能将口供作为定案依据予以采纳。有的学者认为:口供证据补强规则是针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口供作为定案的唯一依据的情况,当这份口供是承认犯罪事实的口供时,必须用法律明确规定的其他证据加以印证,否则不可以以此口供作为定罪的唯一根据。[2]以上两种观点,实际上是对什么样的口供需要补强存在分歧,即能够被作为定案依据的所有口供都需要补强,还是只有能够证明案件全部事实或主要事实的有罪口供才需要补强。
口供证据补强规则是防止因错判而侵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合法权利的一项规则。一方面,只有当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承认全部或主要犯罪事实的口供作为认定其有罪的唯一根据时,直接使用才会产生比较大的误判可能性;当口供只能证明部分犯罪事实时,其本身就需要其他证据的支持才能认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在这种情形下,谈补强没有实质意义。[3]另一方面,对于能够证明案件全部事实或主要事实的有罪口供加以补强,是各国普遍的做法,也是理论界大多数学者比较认可的观点。因此,本文将口供证据补强规则限定为:对证明力明显薄弱的、能够证明案件全部事实或主要事实的有罪口供,要求有其他证据予以证实才可以作为定案依据的规则。
口供证据补强规则起源于17世纪中期的英国。当时发生了一起抢劫杀人案,经过审判,被告人被判死刑并且被执行了死刑,这之后的某一天,这起案件的被害人突然出现在人们面前,人们因此开始反思当时的口供规则以及仅依据一个证人的证言就定罪的弊端,逐渐形成了现今的口供证据补强规则。我国1979年制定的《刑事诉讼法》将补强证据规则引入,其第三十五条明确规定:“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没有被告人供述,证据确实充分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这被公认为是我国的口供证据补强规则。口供证据补强规则可以说是吸取了刑讯逼供制造无数冤假错案的沉痛教训的基础上得以确立的。
(二)口供证据补强规则的内在构成
设置口供证据补强规则的目的,就是对能够证明案件全部事实或主要事实的有罪口供用其他证据加以印证来达到证据确实、充分的程度,进而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定罪量刑。我国对于“证据确实、充分”的规定必须符合以下三个条件:一是定罪量刑的事实都有证据证明;二是据以定案的证据均经过法定程序查证属实;三是综合全案证据,对所认定事实已排除合理怀疑。结合口供证据补强规则的定义、性质来看,这项规则应涵盖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1.被补强口供的范围和对象
被补强口供的范围是指包括何种内容或哪个诉讼阶段做出的口供需要用其他证据加以补强。从口供的内容来看,被补强口供的范围包括能够证明案件全部事实或主要事实作为定案依据的有罪口供;从不同诉讼阶段做出的口供来看,包括法庭上的口供和法庭外的口供两类。
被补强口供的对象是指能够证明案件全部事实或主要事实的有罪口供,包括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做出的对犯罪主观方面、犯罪客观要素等的陈述。被补强口供的对象就是指对哪部分陈述需要其他证据来补强。对于口供补强的对象这个问题,国外学者持有不同的观点,比较有名的是“实质说”和“罪体说”。“实质说”认为,补强证据只要能担保自白的真实性即可,没有对罪体进行补强之必要。[4]“罪体说”则认为,犯罪罪体需要补强,这里的犯罪罪体包括犯罪事实、犯罪客观方面、犯罪主体方面、犯罪主观方面、非犯罪构成事实。
2.用以补强口供的证据
补强证据是用来肯定、支持待证证据的证据。口供的补强证据是指可以用来增加和确认口供证明力的证据。口供证据补强规则中应当规定用以补强口供的证据种类与应当具备的条件,即补强证据本身的品质。[5]
3.补强证据的证明程度
补强证据的证明程度,是指用证据对口供进行补强后,应该达到的对案件事实的证明程度。口供证据补强规则的存在就是为了用其他证据对口供加以佐证,以增强口供的证明力,从而使案件的证据达到确实、充分的程度,所以应当对补强证据的证明程度加以规定。
应用口供证据补强规则的第一步是确定被补强的口供范围,第二步是通过对此范围内的口供进行分析,确定应补强的对象,第三步是寻找适格的证据作为补强证据使用,第四步是通过证明程度来验证口供是否得到了补强,是否可以据此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定罪量刑。作为口供证据补强规则应然层面上的内在构成,它们之间的联系是非常紧密的。其中每个要件既有其独立的意义,又相互影响,缺一不可,缺少了任何一个要件都会使口供证据补强规则不完整,导致其无法正确地发挥作用。
(三)口供证据补强规则的功能
在我国司法实践过程中,对口供一直比较倚重,基于口供的特有属性在获取口供的过程中非法或者不规范获取口供的行为时有发生,这导致取得的口供存在瑕疵。对口供证据补强规则来说,一方面,通过口供以外的证据验证口供是否具有真实性。当这些证据与口供相吻合时,就是对口供真实性的支持,从而使口供证明力得到确认。因此,口供证据补强规则的功能首先在于担保诉讼中运用的口供的真实性。另一方面,口供证据补强规则在保障口供真实性的同时,削弱了口供的效用。当司法工作人员意识到即使获取了有罪口供,审判主体也不会单凭它判案,这就会降低司法人员对口供的倚重程度,从而将工作重点转移到收集其他证据上去。相应地,司法工作人员就不会因为要千方百计地获取口供而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施暴力、引诱等非法行为,这在很大程度上保障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利。
二、口供证据补强规则的立法与司法现状
一个法律规则的现状,不仅仅只是立法现状,更重要的是其实践应用。立法是司法的基础,司法是检验立法是否理性的程序,促进着立法更加科学理性。口供证据补强规则的法律规定和在司法实践中的运用,就是立法与司法关系的具体表现。
1.口供证据补强规则的立法现状
1979年我国正式出台了《刑事诉讼法》,运行过程中,分别在1996年和2012年进行了修订,但对口供证据补强规则的规定除了条文的序号外并没有变化,现行的《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三条规定:“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没有被告人供述,证据确实充分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
2013年最高人民法院印发的《关于建立健全防范刑事冤假错案工作机制的意见》第七条规定:“重证据,重调查研究,切实改变口供至上的观念和做法,注重实物证据的审查和运用。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这条规定的进步之处在于从观念上进行了引导。从立案、侦查、审查、起诉到审判阶段都会涉及到非法取证、非法运用证据,其根本原因就是人们根深蒂固的口供中心主义的观念。这条规定也是对口供证据补强规则的重申,体现了司法机关对证据运用的慎重。
由此可见,我国对口供证据补强规则的规定粗疏且不系统,从而导致司法实践中对立法初衷的悖离,使得对口供证据补强规则的规定如同虚设。因此,将口供证据补强规则细化,提高可操作性、实用性是很有必要的。
2.口供证据补强规则的司法现状
上述对于口供证据补强规则的立法规定,具体到刑事案件中,如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承认犯罪事实的口供是唯一能认定该被告人实施了公诉机关指控的犯罪行为时,那么就不应该认定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施了犯罪行为而对其定罪量刑。虽然在绝大多数案件中都正确地适用了这一规则,但是在实践中运用口供证据补强规则遇到了一些问题,这些出现的问题也不应当视而不见。
三、我国口供证据补强规则存在的问题
口供证据补强规则立法的粗疏导致司法实践中法官大量使用自由裁量权,法官裁量权的滥用和错用给司法的公平正义带来不可弥补的伤害。究其原因,一方面,我国口供证据补强规则理论不够成熟,立法没有对其内在构成作出具体规定,无法为实践提供确切的指导;另一方面,没有确立相关制度来支撑口供证据补强规则,使得其在孤立无缘的环境下更加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
(一)应当被补强的口供范围不明确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三条规定:“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没有被告人供述,证据确实充分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从该规定可以看出,立法上没有从口供内容上对口供范围进行划分。从字面上分析“被告人供述”,就是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就犯罪事实向侦查、检察、审判人员做出的陈述,并没有具体说明“陈述”的内容是全部或主要犯罪事实还是部分的犯罪事实。
立法上也没有从口供做出的不同阶段对口供范围进行划分。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口供可分为庭前口供和庭内口供,我国《刑事诉讼法》只是笼统地规定为“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并没有对口供的空间范围进行具体划分。如果不区分庭内口供和庭外口供,那么就会不加区分地对所有口供都进行补强,这是非常不明智的,因为这会造成司法资源的浪费,有违现代司法效率的要求。
(二)口供补强的对象不明确
立法上没有明确规定口供中具体哪些对象需要补强,导致理论界对此争论不休,形成了不同观点。有的学者赞成“实质说”,认为只要对犯罪构成事实一部分进行补强就可以了。有的学者赞成“罪体说”,认为支持“实质说”的学者没有想明白的问题是,该说实质上是通过保障其中一小部分犯罪事实的真实性,推导判断全部犯罪事实也是真实的,有些“以偏概全”的意味,由此导致误判的可能性变大,这是“实质说”固有的缺陷。如果对犯罪罪体一一进行补强,就能更全面地反映出案件事实。所以,笔者认为,应采纳“罪体说”来确定口供补强的对象。
(三)用以补强口供的证据条件不明确
用来增强口供证明力的补强证据的品质,是影响一个证据能否具备补强口供的资格的重要因素,因此,在选择补强证据的时候应该持谨慎的态度。那么究竟具备什么条件的证据可以作为补强证据使用呢?补强证据能够发挥增强口供证明力作用的基本前提是这个证据自身必须具有作为证据的资格。因为补强证据本身也是证据,如果是通过非正当手段取得的证据,那么就算这个证据的内容是符合真实情况的,也不能作为法律意义上的补强证据。我国刑诉法并没有具体规定用以补强口供的证据应具备什么条件,虽然规定了要和法定证据一样,必须符合证据的基本属性,即具备合法性、客观性和关联性,但是是否具备了这三种属性就可以了呢,法律并没有作出详细的规定。
(四)口供补强证据的证明程度不明确
对于补强证据需要达到证明程度,理论界针主要有“绝对说”“相对说”“折中说”三种学说。[6]“绝对说”认为,用来补强口供的证据,应当单独达到证明案件事实的程度,法官可以不需要再结合口供对案件进行判定;“相对说”认为,用来补强口供的证据结合口供之后能够达到证明案件事实的程度就可以了。在这两个观点的基础上,日本有学者还提出了一种折中的观点,认为对于犯罪嫌疑人在进入审判阶段之前做出的口供进行补强适用“绝对说”,对于被告人在审判时做出的口供进行补强适用“相对说”,这种观点被称为“折中说”。我国在立法上对于证据证明标准的规定一直是“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不仅缺少可依据的操作标准,而且规定过于单一,在实践中,补强证据的应当达到怎样的证明程度,对口供与补强证据之间的证明力的分配有着很大的影响。
四、完善我国口供证据补强规则的构想
(一)明确被补强口供的范围
根据口供内容对口供范围进行明确。明确规定只有反映案件全部事实或主要事实的有罪口供作为唯一定案依据时,才需要适用口供证据补强规则对该口供进行补强。
根据口供做出的不同阶段对口供范围进行明确。法律规定通常会有内容模糊之处,这个时候正确的做法是从立法本意去理解并灵活运用,而不是穿凿附会。所以,在明确被补强口供的范围时首先不应狭义地将《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三条规定的“被告人供述”解释为法庭审判时做出的口供,因为在侦查阶段取得的虚假口供的可能性更大,如果不对庭外口供进行补强而直接采信,那无疑是对“刑讯逼供”等非法取供行为的漠视。
在普通诉讼程序中应包括当庭供述的补强和庭外供述的补强,因为被告人当庭做出的口供也会因为一些原因具有虚假性,比如担心一旦做出的口供不正确,又要被刑讯等。同时,为了限制法官的自由心证,制约法官的自由裁量行为,法庭上的口供也应在补强的范围之内。
(二)明确口供补强的对象
口供需要被补强的具体对象,应当是能够反映案件所有或重要事实的部分。口供证据补强规则的设置,是为了在运用口供的过程中对其进行规制,防止审判人员误用口供而产生错误认定案件事实的风险。如果口供只能片段化地还原案件事实,并且这些片段无法拼凑完整,无法呈现一个清晰的案件全貌,审判人员就必须通过其他证据而不是仅仅凭借口供来认定案件事实。那么究竟对口供哪些部分进行补强才能够使犯罪事实的全部或主要部分得到证实呢?部分“罪体说”是最为合适的观点,即对犯罪的客观要素进行补强。如实施犯罪的人、实施犯罪的具体行为、犯罪行为导致的结果等要素,必须要用独立于口供的其他证据来补强。“口供补强规则的实质就是遏制法官仅依据口供就认定被告人有罪的现象发生。而组成犯罪的要素中,客观要素是客观存在的,不以主观意识为转移的,属于最重要的部分,因此为了防止脱离客观事实而以主观为主对犯罪进行认定,对于客观事实的认定必须要求具备补强证据。”[7]当然,对只有犯罪行为而没有导致损害结果的行为犯和未遂犯来说,在对口供进行补强时理所应当地不用考虑损害结果,只需要对存在犯罪行为进行补强就可以。对实施犯罪的人与被告人是否具有同一性这个问题,也需要进行补强。因为,冤案、错案的产生多是由于抓错了犯罪嫌疑人,冤案、错案得以纠正也多是由于真凶出现,迟到的正义不是正义,即使最后抓获真凶,对无辜者的伤害也不能被抹灭。因此,对于案件的被告人与犯罪行为人的同一性进行补强是很有必要的,这也得到了我国各界的一致认可。
我国各级法院“案多人少”,如果对每一个案件都要对犯罪客观要素不加选择地严格适用口供证据补强规则,那么将会导致刑事诉讼效率低下。如果将很多时间耗费在对普通案件特别是轻微刑事案件上,那么就会占用重大案件的审判时间。在权衡利弊之后,从原则上来说对于普通案件特别是轻微刑事案件,并不需要像处理重罪案件一样,对口供或者口供中涉及的犯罪客体进行一一补强,而应该由法官通过对案件的实际情况作出分析后,根据不同案件类型进行区分处理,在更大的程度上赋予法官自由裁量的权利。
(三)明确口供补强证据的条件
必须具备证据能力和证明力。补强证据也属于证据,首先应符合证据的基本属性,即证据能力和证明力。从这个角度出发,补强证据可以是除了口供外的其他七种证据的任意一种或多种,但是如果不具备证据能力,将不能作为证据使用,也就不具备对口供进行补强的资格。再者,要想增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案件联系的紧密度,补强证据和被补强的口供必须要有关联性,即补强证据一定要对需证明的案件事实有实质的意义和确切的帮助。反之,则不能被作为补强证据使用。例如,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作案行为没有实质性联系的品格证据,一般情况下不能作为口供的补强证据。再如,案后犯罪人的悔罪表现、和解协议,因其与犯罪行为联系并不紧密,既不能当作口供补强证据来用,又不能当作量刑证据来用。
必须具备可靠性。“证据事实必须是伴随着案件的发生、发展的过程而遗留下来的、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而存在的事实。”[8]作为补强证据也应当具备这样的条件,应当保证来源真实可靠。不能查明准确来源的材料不能作为补强口供的证据使用。
必须具备独立性。独立性要求用来补强口供的证据应当是有独立来源的,必须独立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口供。因此,其在不同阶段做出的口供不能互为补强证据;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己写的书面口供也不可以作为补强证据使用。在司法实践中,经常有公诉机关利用侦查机关的讯问笔录来补强被告人在审判时做出的有罪口供的情形,但是讯问笔录只是口供的载体而已,它仅是对口供和获取口供过程的记录,不具有独立性,将讯问笔录作为补强证据,这必定是与补强规则独立性要求背道而驰的。因此,对被告人当庭认罪案件,公诉人示证的正确方法应是略过被告人的供述,通过出示其他证据来证实犯罪。[9]
(四)明确口供补强证据的证明程度
“绝对说”认为,用来补强口供的证据应当单独达到证明案件事实的程度,法官可以不需要再结合口供对案件进行判定。此说存在不妥之处。若是如此,法院则不需要利用这些补强证据来补强被告人的口供,而直接将补强证据当作有罪判决的依据。因此,“绝对说”在事实上并没有涉及口供,这样口供则在案件审理中起不到任何作用,这很不科学。
“相对说”更合理一些,因为“相对说”认为用来补强口供的证据结合口供之后能够达到证明案件事实的程度就可以了。问题在于,实践中如何平衡口供和其他补强证据的证明力?在此问题上应该注意对不同情形的案件,分类对待。一方面,口供证据补强规则并不是作为一个硬性规则存在的,在实践中应当灵活使用。这样既可以限制口供的证明力,又能发挥裁判者的自由裁量权,但前提是裁判者可以合理行使自由裁量权。另一方面,虽然证据的证明力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一个事实问题,但是无法避免在事实的发展过程中掺杂主观性,面对不同的情况,必须对口供的证明力加以限制和规制,这是为了避免虚假的口供对裁判者造成干扰而滥用自由裁量权。
在实践中,普遍的做法是在对犯罪情况的严重性进行客观分析后,结合上述文中的观点,针对不同的案件类型设定不同证明程度,但在原则上我们应要求口供和其他补强证据的证明力之和能够满足合理排除怀疑的标准。在严重的、可能判处无期徒刑以上的案件中,如杀人、强奸致死、绑架并杀害被绑架人等,补强证据应达到“绝对说”要求的标准,即抛开口供,补强证据能够单独证明犯罪事实。在比较严重的犯罪中,如可能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的犯罪案件,补强证据应达到“相对说”的标准,即在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口供的证明力进行补强后,将补强证据和口供结合使用来达到刑事案件的证明标准。即补强证据虽然不需要能够独立证明犯罪事实的存在,但大体要满足和口供相结合后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在轻微犯罪案件中,口供补强证据与口供共同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标准低于重罪的要求,仅对案件的主要事实予以补强,对其他事实不作严格要求。[10]
五、结语
完善的口供证据补强规则对于实现实体和程序两方面的公正,有着双重的促进作用,更深层次的意义是对我国刑事诉讼追求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理念的宣示。我国在构建口供证据补强规则时,应当在借鉴西方国家优秀成果的基础上,在明确自身所处背景的情况下,从观念、立法、制度三个层面采取措施,促使这一规则发挥最大作用。口供证据补强规则的完善和落实需要立法机关、司法机关以及社会各界从不同的层面共同努力,尽管在这一过程中会经历挫折,新的法律规定会遭受质疑,但一定会在不断摸索的过程中愈加丰富和完善。口供证据补强规则不单是简单的口供运用规则,而且涉及到侦查、起诉及审判等环节,与之相关的理论和制度十分庞杂,尤其是对于共犯口供作为补强证据的研究还有很多方面需要深入探讨,只有全面深入的研究,才能为我国相应立法提供更深的理论支撑。
[1]陈光中.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证据法专家拟制稿(条文、释义与论证)[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4:168.
[2][3]周颖.口供制度研究[D].上海:复旦大学,2013:67.
[4][日]田口守一.刑事诉讼法[M].刘迪,张凌,穆津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254.
[5]牟军.自白制度研究——以西方学说为线索的理论展开[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6:337.
[6]周颖.口供制度研究[D].上海:复旦大学,2013:75.
[7][日]石井一正.日本实用刑事证据法[M].陈浩然译.台北:五南图书出版公司,2000:311.
[8]徐美君.口供证据补强规则的基础与构成[J].中国法学,2003(6).
[9]肖巍鹏.论口供补强规则的具体运用[J].人民检察,2012(24).
[10]李海明.口供补强证据规则研究[J].宁波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0(1).
【责任编校:陶 范】
Research on the Rule of Oral Confession Reinforcement
Wang Ruiheng,Jiang Wenjie
(Liaoning Normal University,Dalian 116000,China)
Theruleof oralconfession reinforcementrefersthatthe oralconfession ofguiltis obviouslyweak,which can prove thatall thefacts ormain facts of the case,and requireother evidence toprove that it can be used as thebasis fora final decision.The rule of oral confession reinforcement consists of four aspects:Firstly,the scope of the supplementary confession.Secondly,the object of the supplementary confession.Thirdly,the corroborative evidence.Fourthly,the degree of corroborative evidence.When the internal structure reaches the perfect degree,the rule of oral confession reinforcement is able to guarantee the authenticity of oral confession,prevent the miscarriage of Justice,prevent the excessive reliance on oral confession,and protect the human rights.However,the rule of oral confession reinforcement encounters varieties of problems in China.In theory,the provisions of the supplementary confession's scope and object,the corroborative evidence,the degreeofcorroborativeevidencearenotclear.Inpractice,theruleoforalconfessionreinforcement'sguidanceandstandards are lacking.In view of the rule of oral confession reinforcement's problems,we should improve the internal structure of the rule of oral confession reinforcement from four aspects:Firstly,clearly defining the scope of the supplementary confession.Secondly,clearly defining the object of the oral confession reinforcement.Thirdly,clearly defining the corroborative evidence.Fourthly,clearly defining the degree of corroborative evidence.
Evidence of Oral Confession;Reinforcement Rule;Degree of Proof;Evidence Condition;Scope of Oral Confession;Reinforcement Object
D915.3
A
1673―2391(2017)04―0003―06
2016-09-21
王瑞恒(1968—),男,内蒙古集宁市人,辽宁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证据法学、诉讼法学;姜文捷(1991—),女,辽宁省大连市人,辽宁师范大学2013级硕士研究生。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我国司法鉴定立法疑难问题研究”(14YJAZH079);2015年辽宁省教育厅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辽宁省司法鉴定立法研究”(W2015244)。
——以“被告人会见权”为切入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