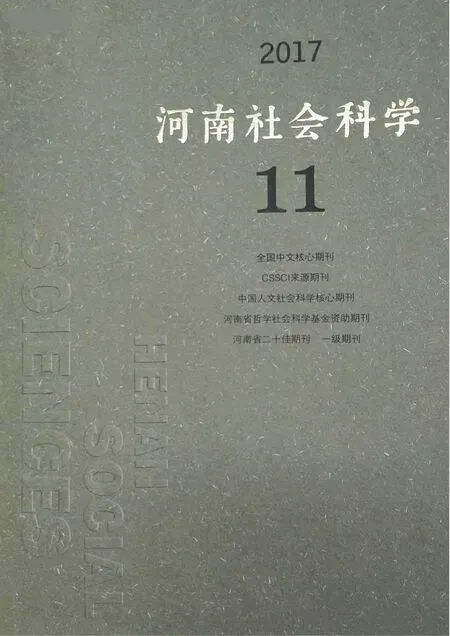“微时代”文化批判
张红翠
(大连大学 文学院,辽宁 大连 116622)
“微时代”文化批判
张红翠
(大连大学 文学院,辽宁 大连 116622)
“微时代”的现实发生是当代文化资本逻辑不断向前推进并持续加剧的必然结果,被这一时代网罗的人们无一不受着“微时代”潜在文化逻辑的暗示乃至训示。揭开这一资本-文化逻辑发生的具体过程,捕捉“微时代”文化表征的现实痕迹,展现这一时代的文化机理,进而勾画“微时代”下人类心灵的结构地图,索解这一时代隐在的文化训示,应该是有关“微时代”跨学科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
微时代;资本;技术;机器;文化逻辑
今天,以智能手机为代表的智能电子产品(在本文中,我们主要以智能手机为研究对象)已经很难只是简单意义上的信息传播媒介和通信工具,它不仅为“微时代”的文化实现提供现实的物质基础,还具体地改变着现代人们日常生活场域的时空形态。甚至,智能手机俨然已经成为“微时代”的“代言人”和时代意志的执行者,对生活主体的生活方式、意识习惯以及价值系统进行一整套的引导、改造和重塑。借助于智能手机时空现场的日常介入,微时代对它的子民进行一系列的文化训示。判断微时代文化训示的内在意图,需要在梳理智能手机的来龙去脉及其在时代中地位作用的基础上进行,也即描述微时代具体的文化表征,方能进入对微时代暗含文化意旨的辨析。
一、微时代的智能手机:时代意志的机器装置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是由掌上电脑(PocketPC)演变而来的,与传统的键盘式手机不同,智能手机像个人电脑一样,具有独立的操作系统、独立的运行空间,可以由用户自行安装软件、游戏、导航等第三方服务商提供的程序,并可以通过移动通信网络来实现无线网络接入手机的功能拓展。而且,智能手机出现的意义在于,它借助网络技术实现了一个立体而全方位的生活世界场的展示、转换和自由生成,所以,自IBM公司在1993年推出世界上第一款智能手机——Simon之后,智能手机的使用范围便布满全世界,时代之“微”的文化情境也开始迅速向人们围拢。
每一部智能手机都是一个世界,一个独立的时空存在,它涵盖了多种功能,集合了多样的主题信息。这些主题有新闻资讯、视频音乐、网上商城、游戏中心、旅行票务、地图天气等,涵盖了购物、阅读、娱乐、社交、学习、吃喝玩乐等日常生活的几乎所有方面。这些主题软件作为手机原始配送软件与手机一起进入微民的日常生活。作为微时代生活主要的“日常之物”,智能手机与微时代的人们整日耳鬓厮磨,一起生活、不离不弃,正在成为微民生活最重要的生活现场,致使微民们的生活几乎都在智能手机中完成。在手机的方寸界面内,使用者可以完成生活的各个方面而几乎不需要借助如纸质媒介等传统媒介或者实体店铺,不需要现实的奔波,比如乘坐交通工具去到售票点或商场等,也不需要和工作人员进行直接的对话和面对面的接触就可以迅速无声地完成“交换”。除却这些新的快捷生活方式的改变之外,这些并列在手机开启后井字界面中的主题,还构成只对手机主人单独开放的私人空间,它延伸出隐秘幽暗的时空隧道将社会意识的价值和信息一起输送给微时代的子民们。
在深入了解智能手机内藏的神秘世界时,我们还需要对智能手机中独立主题的运作进行观察,看看它是如何生产和运行的。以信息网站服务为例,其主要功能是向手机用户提供主题推送服务。它把完全不同时空的生活故事捆绑并置在一起,持续推向客户端,使之海量而快速地拥入用户的生活意识。比如,同一时间中,我们可以同时收到叙利亚难民困境与浙江渔民保存3米长鱼刺等这些发生于不同时空中完全不同性质的故事信息,诸如此类的信息在滚动的推送服务中快速更替刷新;与此同时,微信聊天信息与QQ聊天信息交替弹出;同时还有朋友圈中完全不同内容信息的共时分享;等等。每一条信息都意味着一个时空的延展,而每一种时空的启用,又意味着对另一种时空的干扰入侵和中断。而且,这些信息主要以图片形式被推送,强化着微时代的视觉主义趣味。尼尔·波兹曼在上世纪讨论图片信息的文化本质的时候指出:“照片把世界再现为一系列支离破碎的事件。在照片的世界里,没有开始,没有中间,也没有结束……世界被割裂了,存在的只是现在,而不是任何一个故事的一部分。”①这就是图片的美学本质,也是视觉主义趣味的美学本质。
智能手机中时空异质的不同主题之间彼此独立又共同分有手机空间,相互交叉、驳杂喧闹、多声部混杂,它们与生活个体捆绑在一起,随时在场,随时等待随时召唤,随时启动,呼唤着微民们的点击、浏览和阅读。这些缺乏历史关联和背景的信息拥挤在一条条信息通道上,通过不断拼挤、刷新的方式抢夺资源,形成了一个令人无法抗拒又令人疲惫不堪的纷扰世界。这个世界中,不仅本雅明所谓的艺术品的“灵光”不再,即便信息本身的意义也消失了,因为,信息不再具有促成现实行动的价值作用,这种作用已经在娱乐的名义下稀释冲淡。
这种信息爆炸的世界状态在媒介理论家尼尔·波兹曼的时代早已出现,只不过那个时代是电视的时代,今天是智能手机的时代,时代的更迭并没有改变事情的本质:“掩藏在电视新闻节目(今天应该将之替换为‘智能手机’——本文作者注)超现实外壳下的是反交流的理论,这种理论以一种抛弃逻辑、理性和秩序的话语为特点。在美学中,这种理论被称为‘达达主义’;在哲学中,它被称为‘虚无主义’;在精神病学中,它被称为‘精神分裂症’;如果用舞台术语来说,它可以被称为‘杂耍’。”②
尤其重要的是,智能手机中驳杂凌乱的时空秩序迎合了这个时代文化时空结构的内在需求。因而,智能手机所展现的不是空间的重组而是空间的分裂,它以即时性、零碎性的方式刺激和吸附它的“主人”。当生活主体的时空体验经常被打断、被插入、被截取、被干扰和频繁置换的时候,传统社会中人的整体性时空生存经验随即被切割分解为断断续续的不连贯的单体粒子——碎片感和断裂感随之产生,浮躁的文化基因也被埋下伏笔。智能手机生活主题的生产、传播和接收,形成了微时代信息生活的拓扑学景观,它展示了微时代信息如何以多次幂的方式被繁衍拓殖,如何以不容抗拒之势压向每一个生活主体。因而,同样无可避免的是,智能手机的功能设定和程序实现正在改写着时代生活主体的时空程序、时空经验,这种时空的重新编排加强了时代对生存个体的内在控制——手机控、低头族越来越疏离了生存个体之间的交互联系,日益陷入多重奇幻信息的黑洞中无法自拔。
利益附加。作为与“微时代”的内在文化逻辑相适应的智能电子产品,智能手机将微时代的时空表述凝缩在方寸之间,正在以娱乐化和信息化的外观,利用任何时间和空间的可能,将消费信息、欲望观念、物质关切等价值倾向和意识观念组合叠加、批量输出和传播,制造各种炫惑的需求让人们不断追求。然而,海量信息通过智能手机信息通道源源不断流入接收者的眼睛、耳朵,这些背后是什么,它的驱动力在哪里,它以什么样的目的远程遥控着我们并塑造着我们,并最终导致一种迷恋症和强迫症呢?手机智能程序的随机推送,到底是一种用户额外得到的福利,还是另有图谋,这样的一种文化景象是智能手机所能期许给我们的“美好世界”吗?在诸多疑问中我们看到的是,智能手机各类主题的信息空间并不纯粹是信息本身,其背后还附加着更为重要的东西,一起通过信息通道传播给生活主体。它是什么?是智能手机界面中每一个主题背后网站的期求:对用户点击率的期求。因为,点击率决定广告定制量以及广告收益,要提高收益就要提高点击率。所以,推送主题信息的关键不是信息本身,而是如何唤起和培养用户的点击欲望。于是,网络信息日益趋向猎奇性、偷窥性和夸张性,这样才能吸引人们的眼球提高点击率;于是微时代再一次重申了它夸大、奇酷美学趣味的合法性。也因此,碎片化是微时代叙事形式的必然选择,因为碎片化才能使信息得到不断更新、大量定时推送,碎片化才能保证手机用户随时点击进入,随时在线,随时保持对信息阅读的兴趣。这也就是为什么微时代需要以更加无微不至、更加频繁,更加无时不有、无处不在、无孔不入的方式,对人们日常生活进行更加持续深入的牵引和介入的原因。信息的碎片化才能保证隐藏的附加利益得以实现,而生活主体内在时空经验的碎片化和思维意识中的难以弥合的断裂性状态只是它的副产品而已。
机器的意志。智能手机主题功能软件运行背后,是一套套运行的程序指令、数据、编解码语言和装载这些程序指令的机械处理器。也就是说,当我们经常下意识地开启手机主题功能进入各种空间,进行聊天发帖、阅读浏览新闻等手机生活时,不仅潜在地受着信息程序操作系统的远程控制,还被网站的终端处理器记录和分析,我们手指的每一个选择和点触都被写进了智能手机技术装置的隐形意志。这种意志正在改变人类的大脑程序。瑞士一项最新研究称,经常使用智能手机会在大脑处理触觉的部分留下强烈“印记”。研究人员对26名触屏手机用户和11名传统手机用户的拇指、食指和中指进行1250次刺激,并记录他们的脑电图,随后将测试结果与近10天内的手机使用记录进行比对分析,结果显示,与没有使用触屏技术的用户相比,智能手机用户与体感相关的脑皮质活动增强,即处理手指触摸动作大脑区域的活动增强。研究负责人阿尔克·高希表示,智能手机使用越频繁,大脑体感皮层的活动越强烈,而这种频繁触摸的动作最终可能会重塑大脑指挥手指工作的方式。这种改变对人类到底有什么样的影响,高希说,可能不全是好消息,如有证据表明,过度使用智能手机可能与运动功能障碍及慢性疼痛有关。也有研究人员认为,频繁使用智能手机可能导致记忆力下降、注意力不集中等问题③。这便是机器意志的作用,它似乎正在重新设计微时代人们的生活和理智活动,并且正在塑造十分鲜明的“一体化”的经验模式,从而在最深层次上制约微时代人们对当代世界的了解。在这一现实中,文化的多样性生态已经开始瓦解。
二、微时代的文化表征
微时代通过智能手机这样的机器装置为时代中的人们提供无微不至的生活“关怀”,致使人们越来越依赖这个机器。生活主体每天都在训练自己与智能手机长时间“联网挂机”的智能生活,通过对这种生活行为的选择和实践,微民们接受着微时代的文化训示,配合着微时代的文化趣味和倾向。这些趣味和倾向被生活主体理解为生活的内在规则,引导、规定并重塑着微时代生活主体对自身的理解、表述和自我显形。而这些都以具体而微的文化表征方式展现着。
微时代很“宅”。20世纪60年代,在现代政治经济形势下,消费文化的发展催生了一种在全球化发展形势下出现的亚文化现象——宅文化。宅文化专注于私人空间的精神追求方式和生活方式,其精神内核是趋于封闭的心理状态和不拘泥于形式的文化方式。实际上,现代化开始之后,消费文化在全球资本的推动下进入日常生活领域,全球文化中“宅”的现象也日益普遍乃至加剧。微时代的文化方式便带有强烈的“宅”的特征。因为,智能手机的时空场域为生活主体“宅”在一个独立的私人空间提供了现实的可能,这个私人空间已经分割了传统的家庭空间,拦截了人与人之间交流的热望,切断了人与外在世界的关联性意愿。借助智能手机,微时代的人们将宅在智能时空中的自我想象理解为令人赞美的时尚和与众不同、个性和自由,这种高度自我中心的文化倾向不断强化生活主体对私人空间的强烈关注和自我迷恋,而它的另一面则是对周围世界的屏蔽。常见同事的女儿,平时的习惯是晚睡晚起,白天也拉着窗帘、开着台灯,反锁着门;和人在一起时也大多是低头沉浸在刷屏的世界中。在“90后”“00后”年轻人的生活方式中,这种“宅”的现象既普遍又突出,这就是微时代之“宅”对年青一代心灵和行为的“养成”。这种“宅”自然也显现于微民们再熟悉不过的朋友圈中充斥着的各种生活瞬间的各种“晒”——那可能是一顿看起来不错的午餐,一次家庭的远足,一个女儿的发夹……微时代的粉丝们在对影像化个人生活空间的沉醉和迷恋中获得奇异的存在感。
微时代很“琐碎”。微时代的时空技术正在催生和培植生活主体对细末事物的狂热,它将人们的视野牢牢地吸引并且固定在吃喝玩乐这些生活的细枝末节上。智能手机中的新闻资讯除了娱乐和猎奇之外,绝大多数是有关吃喝玩乐的商业广告。这些网络信息紧紧跟随都市人日常生活的各个环节,如影随形,以各种技术方式和营销手段千方百计地刺激人的感官欲望,使这部分神经异常敏感和兴奋,从而强化人们对世界中物质一面的迷恋、关注和获取的意念。它不断唤醒和激发微时代人们内心深处的原始欲望——千万次呼唤与千万次狂购练习,正在使这种集体无意识变得日益强大,促使生活主体将物质表象放置于价值系统结构的最顶端。于是正如热衷于这个时代的叙事者们惯常使用的方式那样:“抢”(“同事都在抢”“双11你买了吗”“终于降价了”“快来抢半价”……)成了大街小巷的口号和微时代的大景观。诸如此类的叙事,通过街头广告、车身广告、公交车车载视频不断写入人们的思维程序,逐渐改写人们的价值观基础、世界观基础。它将物质占有、欲望实现认定为时代最重要甚至唯一的价值,无数次,它把我们的幸福许诺给了物欲的满足。在关注这些微末生活的同时,人们正在遗忘传统宏大叙事对生活的意义,失去对伦理大义乃至宏大理想的兴趣和信任,这必然导致时代主体精神的内在空虚。于是,微时代又在拼命书写另一种宏大,它是我们随处可见的商业宏大叙事的召唤:盛大开幕、炫彩盛装启幕,闪亮登场;“全民抢占”“全民淘宝”“限时抢购”,势动全城;购物狂欢、店庆嘉年华、买别墅做英雄老爸等。对于物质生活不遗余力、不顾一切地占有成为时代的价值、理想和追求,似乎用此掩盖传统宏大叙事消弭后留下来的不安、恐惧和空虚。
微时代很“酷”。微时代人群中流行对外在形象的迷恋和颜值的投资,追求炫酷、前卫和另类的视觉形象和个性装备,符合这种表现会被赞为“酷”。在被“酷”文化所强调的时尚和个性中,“冷峻”是一种令人赞美的品质。于是“酷”和冷以及冷漠也必然被接受为时代文化的基本品质——正如人们所呼唤的那样,微时代文化越来越“酷”。此间,无限放大个体形象价值与原子化个人主义互为表里,“原子化的个人主义,否认了个体与其他人之间的联系,否定了社区与家庭的意义”④,也否定了个体与赖以生存的生存环境之间的共同体意义,从而导致对环境的极度冷漠:人们越是对自我的生活利益过度关注,就越是对身边的生活环境、生存家园视而不见。这种冷漠在文化生活的各个层面蔓延弥散,例如今天社会中有一个极为普遍的现象,那就是很多公共场所(以我所熟悉和走访到的学校、研究机构为例)都有长明灯现象。各类会议习惯于大白天拉窗帘开灯开会,公共管理部门办公室、教室上课习惯于白天拉窗帘开灯——尽管阳光正好……这足见我们对生活环境的漠视已经到了随处可见、极为普遍的程度。这种不约而同的冷漠和浪费表现了这个时代的偏执意志——拒绝自然、拒绝阳光和世界(这也是“宅”的一种隐喻);只顾“低头”生活在自己的欲求和利益中,丝毫不在意环境和资源;只见个人眼前利益,不见社会长久利益。于是,雾霾成为微时代意涵最丰富的隐喻:微时代的人们拒绝理解个人的奢侈浪费与能源消耗以及与雾霾之间的关系,拒绝理解生活环境各个要素之间的关联性和共同体关系,拒绝理解中国青少年在美国凌虐同伴事件中人性关怀的极度缺乏和绿地消失以及环境危机之间的内在关联,也拒绝理解诸如此类社会现象与社会事件之间的相互关联性正在侵蚀着人类生存的整体性利益。人性关怀与环境关怀的缺失正在塑造一种恶劣的生活习气和文化偏执。更可怕的是,人们对这种冷漠无动于衷,视之为自然。这无疑是对事实的回避,而“对事实的回避就是心灵的腐化”⑤。
微时代很“饕餮”。在城市的公交车上、人行道上、商场中、地铁上、校园中甚至家里的沙发上,我们随处可见那些甚至不能将眼睛从手机屏幕上转移开来哪怕一分钟的人,人群中搜索不到可以和他们相遇和交流的目光,身外的世界在他们的意识中似乎已经不复存在。人们开始只关注于以自己为中心的三米以内的事情。该如何命名这些与我们同城的、擦肩而过甚至共同生活的人呢?西安大雁塔所在的大慈恩寺门前广场的西南面是一条美食街,街头入口处有两个高耸的石柱子,柱子高处赫然耸立着两个大字——饕餮,用这两个字描述微时代特征似乎再贴切不过了。饕餮以贪婪为天性,而那些迷恋智能手机世界不能自拔也无意自拔的人,亦如饕餮般扑向虚拟世界的巨大黑洞。而智能手机则像一个有着巨大吸附力的黑洞正在吸食它的子民——吞噬他们的双眼、双手,他们的身体和灵魂。此时,人们热恋的智能手机作为“某种不依赖于人的东西,某种通过易于人的自律性来控制人的东西,同人相对立”⑥。
微时代还很“致命”。微时代是一个“迷恋过度”的时代:与智能手机长时间的“联网挂机”在客观上会导致身体的不适,颈椎病、腰椎病、头晕心悸等手机症是手机时代的常见病症。网上曾有关于5岁孩童因长时间玩手机,颈椎老化如50岁的报道。微时代还是一个“致命”的时代:有人通宵淘宝猝死床上;有母亲路上玩手机疏忽孩子,致使孩子遭遇车祸死亡。笔者并不认为这只是发生在一个个看起来不可理喻的人身上的个体行为,我们看到的是强大的时代意志对主体生活意志的替代、重写乃至挟持。微时代通过它的智能机器正在夺走人们的鲜活的表情、珍贵的对他人的关注和热情,并使我们变得魂不守舍,心不在焉,不可理喻。在这背后,我们还隐约看到一个更为深远的预示,那就是,微时代的资本在攫取了现实的最大利益的同时,也可能带来人类进化链条的退化,这种退化既是肢体的,也是精神的;既是情感的,也是思想的。微时代把人们的生活变得华丽、丰富、精致而忙碌,也把人们变得更加无聊和空洞,人类是否会失去宝贵的精神生活?这种“杞人忧天”已经不止一次出现在人文学者的质疑声中。正如美国大学教授鲍尔莱恩在《最愚蠢的一代》一书中所指出的那样:“数码时代正在使美国的年轻一代成为知识最贫乏的一代人。”⑦当信息不再是一种自我成长的资源,而变成催生主体欲望的一种商业手段和“社会结构”时,技术的进步和信息的丰富就必然淹没和侵蚀生活主体的心灵判断。
三、微时代的文化训示
微时代文化的诸种表征足以证明,商业主义和技术主义的信念与精神正在形成一种合力,对微时代人们的生活方式、心理和行为的习惯性表现以及深层的价值认知系统的影响何其深远。微时代正在以各种方式向它的子民发出召唤,给出训示,引导社会按照它的训示去感受、需要、理解和行动,而这一切的主要动力则在于商业主义和技术主义的价值信念。
(一)去消费——商业主义价值信念的训示
中国互联网先锋马云2015年在纽约经济学会演讲时提出了一个世界互联网经济蓝图,并且以“阿里巴巴上面有成千上万的‘饥渴’的消费者在等待”来表达互联网时代潜在的全球化商机。作为一个经济设想,这或许是动人的商业游说,但它同时也道出了以互联网为支撑的微时代背后隐藏的“叙事”逻辑:消费者的“饥渴”很大一部分来自商业的暗示,消费者的“饥渴”正是各种商业信息喂养起来的,是商业的“饥渴”需要消费者“饥渴”。为了使这种“饥渴”成为人们日常的心理必需和群体的无意识冲动,智能手机迅速被包装成时代意志的代言人,以最快的速度调动和满足着消费者的“饥渴”,因为,只有消费者的“饥渴”得到满足才能满足商业资本的“饥渴”,才能保证资本增值的最后完成。于是,微时代的生活主体被改写为商业链条中必须无限“饥渴”的消费者。所以,这个时代才会出现年轻人卖肾买苹果手机、大学生用父母的钱分期付款买名牌手机以及对这个时代无限忠诚的人们“刷屏致死”的奇特现象。这便是一个“技术主义+商业主义”文化价值模式对人内在价值观念以及思维程序深度改写的写照——人正在变成一架不顾一切去消费的机器。对生存个体操控力的不断加强,体现了这个时代典型的强迫症倾向。
不仅如此,当机器意志持续在微时代人们的生活中发生作用的时候,微时代还进行着一套文化价值程序的编码和书写。在这套书写中,最重要的是对价值信念的重构。微时代协同它的生活主体正在形成这样一种信念——“满足等同于消费”。这种信念似乎已经成为这个时代中生存主体的集体无意识。任何一种文化,都要向文化中的个体提供一种实现幸福的方案,而微时代提供的方案是用物质来填充欲望的沟壑。这就将人的幸福的实现替换为人的欲望的满足,认为物质和欲望的满足就是人生的目的和幸福的内容,生活质量就是对外在物质的占有,就是幸福本身。这种认知降低了文化的理想,使之变得简单,甚至缺乏教养。“强大的商业主义标志着退化和根本的不道德。为了满足自己,我们正在破坏地球和它上面的一切。”⑧
(二)去打开手机——技术主义价值信念的训示
对于微时代的人们来说,每天早晨醒来的第一件事恐怕就是打开手机看朋友圈信息、浏览天气网页等,这是微民们几乎一致的生活程序。智能手机的召唤随时都在,回应它的召唤是那样的自然和义不容辞,其背后起作用的还有深远的技术主义价值信念。在有关智能手机的文件资料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描述:“××手机也已在中国形成了大笔粉丝。”我们很难把这种表述仅仅理解为纯粹的商业修辞,其背后隐藏的其实是关于“崇拜”的信念,人类崇拜从图腾、“上帝”、伟人、明星,进化到对机器的崇拜。或许这就是南帆先生所说的今天社会中流行的“机器之瘾”吧。微时代人们在利用智能手机这样的机器装置进行日常生活的时候也在把自己变成机器装置,以至于人们的自我显呈、自我表述、自我理解都必须或者不由自主地通过机器技术的方式来完成。今天,当微民们想要抒发心情的时候,不是拿起笔和纸,写下只有自己才知道的心情日记,而是打开手机微信或微博,放到朋友圈去晒,甚至自己的身体和隐私也会晒出去。
有国外学者在批判“汽车社会”时提出,“汽车化已经成为人们的一种消费方式,并且在‘自我再生产’中挟持了人们的意志”⑨。像塑料袋一样,汽车是最糟糕的发明,也许今天我们还应该加上智能手机。汽车社会中,汽车成为改变世界的机器,今天智能手机以更加难以抗拒的方式扮演着这样的时代角色。手机以及无处不在、无微不至的网络用爆炸的信息将人的精神空间拥堵直至无路可走,这是否会带来人类精神空间无路可走的困境呢?美国IT专家Nicholas Carr在《Google把我们变愚蠢?》的文章中指出,网络本身就是一个机器,它“是一个以效率、自动收集、传播和处理信息为目的而设计出的机器”。工业机器已经成为新体制宰控人的日常生活和精神世界⑩。智能手机可以说是工业机器在今天最常见的形态,它让这种新体制无孔不入地深入人们的日常生活。这个机器时刻不停地运转,时刻不停地向它的接受者发出号令。接受训示的人们无暇他顾,他们专注、认真,沉迷于网络的搜索、链接和连自己也不清楚意义的无休止的漫游,以至于通宵淘宝猝死床上。他们又那样地麻木迟钝,以至于被痛恨者戏称为“行尸走肉”。智能机器正在成为新的体制规训着人们的生活行为,它们在塑造人们的生活方式的同时也在挟持人们的头脑思想,重新改造人们的日常生活和精神心理,改变着人类自身,构建着人类生活新的价值系统。这不仅改变了人与人之间尤其是亲人之间的日常关系,也重新定义了人与机器之间的交互关系——“手机成了人身上的一个器官”——一个新的体制正在像芯片一样植入人的内心。这个机器“芯片”似乎已经具有了阿尔杜塞理论中的“意识形态”的意义,它似乎已经是一个先于个体的“社会结构”,深深地揳入人们的潜意识当中,时刻包围着时代中的人们,人们却毫无觉察并依赖它去体验和行动。
四、重返文化轴心
微时代中,我们每个人都是这个时代文化的表征者。也许我的花甲之年的母亲已经不在这个文化编码中,但是当她召唤沉浸在手机世界中、无视她存在的女儿却迟迟得不到回应的时候,她又是这个时代文化深刻的体验者。每一个人都逃不脱这个时代的逻辑,只有应对它的问题。这个时代的问题在于它对基本的社会文化价值系统基础的替换、改写乃至颠覆。文化意志和个体选择不约而同地把幸福以及终极意义的基础放置在外在的物质存在而不是内在的精神生活,此间,每个生命个体都必须面对的基本的存在问题被极力遮蔽或者延宕。所以今天的文化才有种种的危机,有种种深层的不安和焦虑。作为单个的生命存在,每一个人都需要为自己的生命寻找一个出口,一种文化也一样,也需要为自身的发展寻找一个出口。微时代文化要重建生活主体的心灵中心,应对碎片化、欲望化和原子化的文化病症,需要一场持久的“文化心理”疏导,其根本在于对现实文化价值系统的辨析和重建。在这一场文化理解的过程中,我们需要重新思考和追问这样几个基本的文化命题:欲望是什么?身体是什么?人如何才能幸福?技术和机器的本质是什么?它们对于人类生活的终极作用是什么?在重新理解这些问题的时候,西方的思想资源可资借鉴,但中国古老的思想智慧同样也为我们提供了优秀而有效的方案,这些方案中有非常清晰的理论方法,可以帮助我们研判微时代文化深层的哲学症结。它或许会为我们指示下一个出口,告诉我们如何从信息、消费和欲望的黑洞里重新浮出水面,回归生命与存在内在的宁静、安详与平和。
注释:
①②[美]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章艳译,中信出版社2016年版,第91、125—126页。
③http://baike.baidu.com/link?url=kRmPIxxoAiz6OJom 1cpaaCK4tiWMuWwr9aAGfne5Ty9WD9A5545JaJK zhHBnrR09QFKZTiiJG_-0jfwZUq-cza.
④⑨陈永森、蔡华杰:《汽车的福与祸——国外学者对汽车社会的批判性思考及其启示》,《国外社会科学》2015年第4期,第104—111页。
⑤⑧[印度]克里希那穆提:《教育就是解放心灵》,张春城、唐超权译,九州出版社2015年版,第34、24页。
⑥卢卡契:《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任立、燕宏远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150页。
⑦⑩许知远:《最愚蠢的一代》,凤凰出版社2009年版,第14、13—25页。
Cultural Criticism in Micro Era
ZhangHongcui
Micro era is an inevitable outcome of the improving of the modern capital logic.Everyone in this age accept the instructions from the micro era’s culture logic.To overcome the particular process that how the capital-cultrue occurs,and to catch the cultrue trace of the micro era,should be an important subject of the study about the micro era.
Micro Era;Capital;Technology;Apparatus;Culture Logic
G24
A
1007-905X(2017)11-0099-06
2017-07-10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项目(10YJCZH216)
张红翠,女,文艺学博士,大连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文学理论与批评研究、文化研究。
编辑 王秀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