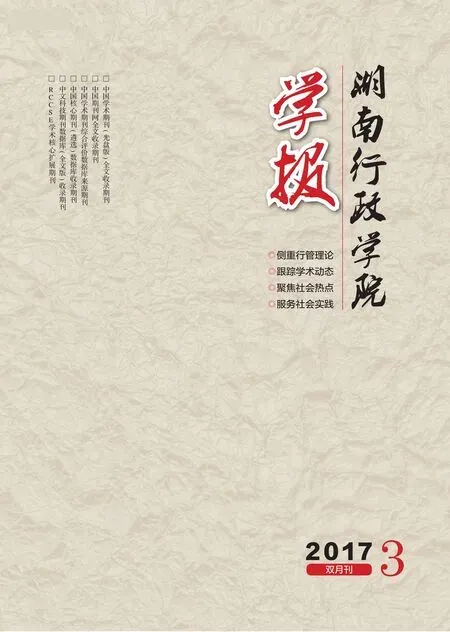哥斯达黎加境内圣胡安河沿岸的道路修建案法律评论
蹇 潇
(中国政法大学,北京 海淀 100088)
哥斯达黎加境内圣胡安河沿岸的道路修建案法律评论
蹇 潇
(中国政法大学,北京 海淀 100088)
哥斯达黎加境内圣胡安河沿岸的道路修建案是国际法院已判决的最新的涉及跨界环境损害和跨界环境影响评价的争端,国际法院对于本案的裁判对跨界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在国际法中的演进起到了一定的推进作用。本文首先对该案的背景进行了简要的介绍,对案件的主要争议点和国际法院的裁判进行了归纳和分析。随后对本案中所涉及的跨界环境影响评价问题进行分析,对该制度的起源和发展进行了简要的介绍,并总结了本案对跨界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的推进。
环境影响评价;跨界损害;一般国际法
一、案件概述
圣胡安河是一条长约205公里,从尼加拉瓜湖流向加勒比海的国际河流,其中下游为尼加拉瓜和哥斯达黎加的界河。两国在对于水资源的利用、在河流及其沿岸开展工程等一系列围绕该国际河流的问题上一向存在较多争议,其中不乏向国际法院提交的争端。
由于哥斯达黎加有些领土仅能通过圣胡安河与哥斯达黎加的主要领土相联系,而尼加拉瓜的一些行为被哥斯达黎加认为属于入侵行为,因此哥斯达黎加想通过在圣胡安河沿岸修建道路的方式,与这部分地区加强联系。2010年12月,哥斯达黎加开始在该河流沿岸属于其本国境内的区域开展1856号公路(以下简称“公路”)的建设。哥斯达黎加于2011年2月21日通过一项行政法令免除了自身在修建道路前应进行跨界环境影响评价的义务。尼加拉瓜于2011年12月21日向国际法院提交诉状,将争端提交国际法院以寻求司法解决。
2013年4月17日,国际法院发布一项命令,将尼加拉瓜诉哥斯达黎加“圣胡安河沿线修建道路案”的诉讼程序和哥斯达黎加诉尼加拉瓜“尼加拉瓜在边界地区进行的某些活动案”的诉讼程序合并。在经过多次书面和口头的审理程序后,国际法院于2015年12月16日对本案做出了判决。
二、主要争议和法院的裁判
(一)哥斯达黎加是否违反其应承担的程序义务
1.哥斯达黎加是否违反了进行环境影响评价的义务
尼加拉瓜认为,哥斯达黎加违反了其根据一般国际法应承担的在公路建设开始前,尤其是对公路的长度和选址,进行环境影响评价的义务。而哥斯达黎加则认为,建设公路并不会使圣胡安河受到实质损害。哥斯达黎加还认为,由于尼加拉瓜对伊斯拉波蒂略(IslaPortillos)的占领所造成的紧急状态,它被免除了进行环境影响评价的义务,即使根据国际法其负有义务采取环境影响评价,哥斯达黎加也已经通过开展一些包括2013年的“环境诊断评估”在内的环境影响研究履行了该义务。
经过审查,法庭认为根据一般国际法,哥斯达黎加负有进行环境影响评价的义务,且该义务不因其宣称的紧急情况而被豁免,其开展的环境影响研究也不构成对该义务的履行。因此,法庭认为哥斯达黎加没有遵守一般国际法赋予它的针对道路建设工程进行环境影响评价的义务。
2.哥斯达黎加是否违反了《生物多样性公约》第14条
尼加拉瓜认为,根据《生物多样性公约》第14条,哥斯达黎加应当进行环境影响评价。而哥斯达黎加则认为该条款涉及的是对可能对生物多样性产生重大不利影响的项目采取适当的程序,而该公路修建工程不可能对生物多样性产生严重的不利影响。
法院认为,有关法规没有规定在开展可能对生物多样性产生重大不利影响的活动之前进行环境影响评价的义务。因此,不认为哥斯达黎加违反“生物多样性公约”第14条。
3.哥斯达黎加是否违反其通知和咨询义务
尼加拉瓜认为,根据习惯国际法、《1858年公约》和《湿地公约》,哥斯达黎加都负有就该建设项目通知和咨询尼加拉瓜的义务。
法庭认为,如果环境影响评价确认存在重大跨界损害的危险,则计划实施该可能造成重大跨界损害的活动的国家为了履行其在防止重大跨界损害方面的审慎义务,应当向潜在的受影响国通知并咨询。但在本案中,并不需要查明是否存在通知和咨询义务,因为哥斯达黎加并没有履行其一般国际法下的采取环境影响评价义务。但法院同时也认为《1858年公约》和《湿地公约》并没有规定哥斯达黎加负有就公路建设工程向尼加拉瓜通知和咨询的义务。
(二)哥斯达黎加是否违反其应承担的实体义务
1.哥斯达黎加是否违反其不对尼加拉瓜造成严重跨界损害的义务
尼加拉瓜声称,建筑工程对其造成了严重的跨界损害。法庭通过调查发现尼加拉瓜对于其声称的损害均没有提供足够的证据加以证明。因此,法庭得出了结论,即尼加拉瓜声称哥斯达黎加违反了习惯国际法下关于跨界损害的实质性义务,这一说法必须予以驳回。
2.哥斯达黎加是否违反了相关的条约义务
尼加拉瓜认为哥斯达黎加违反了相关条约义务,包括:《湿地公约》第3条第1款;《尼加拉瓜和哥斯达黎加之间关于边境保护区域的协定》的目标和宗旨;《生物多样性公约》第3条和第8条等规定的条约义务。
法庭认为,由于尼加拉瓜仅口头认定哥斯达黎加违反了这些条约中的相关规定,但并没有解释哥斯达黎加是如何违反了这些条约的目的或条款,尤其是在缺乏证据证明产生了重大环境损害的情况下。因此,法庭认为尼加拉瓜认为哥斯达黎加违反上述条约义务的观点不能得到支持。
3.哥斯达黎加是否违反了尊重尼加拉瓜领土完整和对圣胡安河主权的义务
尼加拉瓜声称,由道路侵蚀的泥沙造成的三角洲是物理入侵,因此哥斯达黎加侵入了尼加拉瓜的主权领土,而且哥斯达黎加将沉积物、土壤、连根拔起的植被和砍伐的树木倒入河流,对尼加拉瓜在圣胡安河行使权利构成了严重威胁。
法院认为,无论是否由于建设道路而产生沉积三角洲,尼加拉瓜所认为的通过沉积物侵犯其领土完整的理论是不可信的。因为,没有证据表明哥斯达黎加在尼加拉瓜领土上行使任何权力或在尼加拉瓜境内进行任何活动。而且,由于建设公路所产生的沉积物量至多占河流总载荷的2%,不能证明公路建设削弱了尼加拉瓜在圣胡安河上的航行权。因此,尼加拉瓜关于侵犯其领土完整和主权的要求必须予以驳回。
(三)判决结果
尼加拉瓜请求法院判决并宣布,哥斯达黎加的行为违反了它依据国际法所应承担的不得违反尼加拉瓜领土完整的义务;不损害尼加拉瓜领土的义务;及其根据一般国际法和有关环境条约承担的义务。其次,尼加拉瓜还要求法院命令哥斯达黎加停止继续进行任何影响或可能影响尼加拉瓜权利的国际不法行为。第三,尼加拉瓜请求法院命令哥斯达黎加尽可能恢复公路修建前的状态,并对因恢复原状而造成的损害提供赔偿。
最终,法院以全票通过,哥斯达黎加违反了其进行环境影响评估的义务;13票对3票通过,驳回争端双方其他各项请求。因为法庭认为,哥斯达黎加未能进行环境影响评估目前不会对尼加拉瓜的权利产生不利影响,也不可能进一步影响它们,没有理由批准尼加拉瓜所要求的停止继续采取行为的补救办法。且法庭认为恢复原状和赔偿是对物质损害的赔偿形式,虽然哥斯达黎加没有遵守进行环境影响评价的义务,但尚未确定道路的建设对尼加拉瓜造成重大损害或违反国际法规定的其他实质性义务。
三、对进行环境影响评价义务的裁判及其评论
(一)国际法院在本案中对环境影响评价义务的分析
法庭在分析本案中哥斯达黎加是否负有进行环境影响评价的义务时回顾了其在乌拉圭河纸浆厂案中的判决,认为一国在防止重大跨界损害上的审慎义务要求该国在进行可能会影响他国环境的活动前应确定是否存在重大跨界损害的风险。如果存在这种风险,该国必须进行环境影响评价,而这项义务属于进行该项活动的国家,即在本案中,哥斯达黎加应当在建设公路之前评估是否存在重大跨界损害的风险。法院认为,对活动造成的风险进行初步评估是一个国家可以确定拟议活动是否具有重大跨界损害风险的方式之一。然而,哥斯达黎加没有提出任何证据表明它实际进行了这样的初步评估。法庭通过对该项目的规模,以及执行该项目的背景进行考虑,得出了哥斯达黎加建筑公路有造成重大跨界损害的危险的结论,因此,哥斯达黎加负有对该公路建设项目进行环境影响评价的义务。
接着,法庭对哥斯达黎加是否因为紧急情况而被免除进行环境影响评价的义务进行了审查。法庭认为,一国有权在其国内立法或项目授权过程中,在考虑到各种因素的情况下,确定每种情况所需的环境影响评估的具体内容,但这与是否应进行环境影响评估的问题无关。而且哥斯达黎加没有表明存在一个紧急情况,以使其没有进行环境影响评估的行为正当化。因此,在本案中,哥斯达黎加并不能援引紧急情况作为豁免其依据一般国际法进行环境影响评价义务的理由。
对于哥斯达黎加进行环境影响评价的义务是否得到遵守的问题。法庭援引了其在乌拉圭和纸浆厂案中的观点,认为进行环境影响评价是一项连续的义务,并且在整个项目持续期间,必要时都应对项目对环境的影响进行监测。而且,进行环境影响评价的义务需要事先评估重大跨界损害的风险,因此必须在项目实施之前进行环境影响评价。在本案中,哥斯达黎加有义务在开始建设公路之前进行这种评估,以确保项目的设计和执行将使发生重大跨界损害的风险最小化。法庭认为,哥斯达黎加虽然进行了多次环境影响研究,但都是对已经建成的公路的环境影响的事后评估。这些研究没有评估未来可能发生的跨界损害的风险。
通过以上三方面的分析,法庭最终得出结论:哥斯达黎加没有遵守一般国际法规定的对公路建设进行环境影响评价的义务。
(二)评论
1.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的兴起和相关国际环境立法
环境影响评价制度最早于1969年由美国通过《国家环境政策法》率先纳入其国内法中。经过半个世纪的发展,已有百余个国家在其国内法中建立起了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基于这一现状,Birnie和Boyle推测:“各国的国内实践很好地确认了根据1992年《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所表达的共识进行的环境影响评价,可能会被视作一项一般法律原则甚至是习惯法的必然要求。”[1]268
除了各国在其国内法中制定相关规定,将环境影响评价制度适用于跨界环境影响外,诸多国际条约中也包含着在特定情况,尤其是存在重大跨界环境损害风险的情况下,进行环境影响评价的条款。例如:《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206条,规定了缔约国在实施可能对海洋环境造成重大污染的活动时,应对该活动可能对海洋环境造成的影响作出评价;《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4条第1款(f)项要求各缔约方通过环境影响评价程序,减少为了缓解或适应气候变化而进行的项目或采取的措施对经济、公共健康和环境质量产生的不利影响;《生物多样性公约》第14条第1款(a)项,要求各缔约国就可能对生物多样性产生严重不利影响的拟议项目进行环境影响评估;《关于在跨界背景下环境影响评价的埃斯波公约》(以下简称《埃斯波公约》)更是关于跨界环境影响评价的综合性公约。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2001年《预防危险活动造成跨界损害的条款草案》第7条中明确规定了,对存在造成跨界损害危险的活动应当进行环境影响评价。该草案是对习惯或一般国际法的编纂,产生了长期的和深远的影响。[2]251-256
环境影响评价制度还体现在很多关于环境问题的国际宣言与决议中。例如,1972年《联合国人类环境大会宣言》第21条原则今天已被公认为是国际环境法的习惯法规则的基本表述。[3]17该原则虽然没有直接规定有关环境影响评价的相关内容,但从逻辑上看,该原则暗含着进行环境影响评价的要求,因为如果一国不知道其正在或将要实施的某项行为是否可能造成跨界损害,也就无法采取行动以预防这种损害的发生,如果没有环境影响评价程序,禁止跨界损害的实质性规定除了作为对受影响国赔偿的依据外将毫无意义。1992年《里约热内卢环境与发展宣言》原则2基本是对《联合国人类环境大会宣言》原则21的重申,但在此基础上增加了“发展”一词,且该宣言原则17直接规定了环境影响评价义务。《21世纪议程》第8章题为将环境与发展问题纳入决策过程,该章节中多次体现了进行环境影响评价的要求。虽然这些国际宣言本身并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但这类文件往往有助于国际习惯的形成或条约的产生,对各国的行为具有一定的影响力。[3]137
2.本案判决和审理过程对于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
虽然从多国国内实践和诸多条约、国际宣言等法律文件来看,环境影响评价制度早已在国际环境法领域占据了一席之地。但一方面,由于国内法仅具有域内效力,而条约又仅对缔约方具有约束力,国际宣言更是缺乏基本的法律拘束力,因此在实际发生相关国际争端时,如果争端各方之间并不存在共同签署的有关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的条约,则很难确定应以何渊源作为适用该制度的依据。另一方面,关于在什么情况下应进行环境影响评价,以及环境影响评价的内容和范围等有关该制度具体实施的相关问题尚不存在一个十分明确且被国际社会普遍接受的标准。基于以上原因,对于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在国际司法机构争端解决实践中的适用的研究就显得尤为重要。
本案作为国际法院已判决的最新的涉及跨界环境损害和跨界环境影响评价的争端,对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第一,本案中国际法院确认了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的一般国际法地位。在本案中,作为原告的尼加拉瓜的诉求之一就是宣告哥斯达黎加违反了其在一般国际法下应承担的进行环境影响评价的义务。而在原被告双方的辩论中,哥斯达黎加也并未否认该义务,而是从该义务产生的前提、该义务的豁免和该义务的履行方面对尼加拉瓜的观点进行反驳。而法庭在2013年12月13日作出的有关临时措施的指令中也提到了,如果拟议的工业活动存在可能产生重大跨界影响的风险,一国即在一般国际法下负有进行环境影响评价的义务,且这一点已经得到了许多国家的认可。法庭最终以全票通过,哥斯达黎加违反了其在一般国际法下的进行环境影响评估的义务,毫无疑问地确认了对具有重大跨界损害风险的活动进行环境影响评价是一项由一般国际法确立的规则。
第二,明确了跨界环境影响评价的前提,即活动具有产生重大跨界环境损害的风险,且是否存在这种风险由拟采取行动的国家基于对所有相关情况进行客观评价的基础上进行判断。这种一般国际法下的环境影响评价义务并不要求一国对其所有行为都进行环境影响评价,而仅要求对那些存在造成重大跨界损害风险的活动进行环境影响评价,对于那些并没有造成重大跨界损害风险的活动则无需进行环境影响评价。因此,是否需要进行跨界环境影响评价,首先要对活动是否存在重大跨界损害的风险进行一个预判,而这种预判则是由拟采取这种活动的国家做出。目前,关于如何判断一项活动是否存在造成重大跨界损害的风险还没有一个国际通行的标准。除《埃斯波公约》在其附件3中规定了确定重大不利影响的一般指导标准,判断标准包括:规模、地点、影响外,一般相关的国际条约仅规定了进行环境影响评价的必要性,而对进行环境影响评价的前置条件并未加以明确规定。本案中,法院在审查公路修建项目是否存在造成重大跨界损害风险时,对项目的性质和规模以及执行该项目的背景这几个要素进行了考虑。
第三,具体的环境影响评价的内容由一国在其国内法或授权该活动时依据个案的具体情况决定,但国内法对环境影响评价的规定不能免除一国在一般国际法下进行环境影响评价的义务。一般环境保护协定中,即使规定了环境影响评价的必要性标准,对于其具体内容却少有提及,仅在《埃斯波公约》中,其附件3专门对环境影响评价报告的内容进行了规定。但受到该公约缔约国数量的限制,这一关于环境影响评价报告内容的规定的适用范围也十分有限。在本案中,国际法院继续援引乌拉圭河纸浆厂案判决中关于该问题的观点,即“每个国家在其国内立法或项目授权过程中确定每种情况下所需的环境影响评价的具体内容”。因此,不同的国家,甚至同一国家针对不同的活动所进行的环境影响评价的内容可能都是不同的,但拟采取行动国仍应尽到其审慎义务。
第四,环境影响评价应在活动开始前即做出,且该义务在活动进行的全过程中是持续存在的。本案中,法庭在否认哥斯达黎称其多次环境影响研究即对进行环境影响评价义务的履行的观点时,指出由于这些环境影响研究均是在公路修建工程开始后作出的,因此没有满足环境影响评价应在活动开始前做出这一基本要件,这一要求与环境影响评价的目的是一致的。进行环境影响评价的最主要目的是为了评估和预测活动可能造成的重大跨界损害,并提出用来最大限度减少不利环境影响的措施,从而达到尽量避免造成重大跨界损害的目标。基于这一目的,环境影响评价必须在活动开始实施前就做出。而在活动进行的整个过程中,为了达到根据活动的进程,即时预测新的风险并加以避免的效果,环境影响评价还应贯穿于活动的全过程。
四、总结
总的来看,国际法院对本案中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的分析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该制度在国际法中的演进。环境影响评价制度至少是一项一般国际法下的制度,这一点已得到国际法院和大多数国家的一致认可。结合国际条约、国家实践和国际法院及其他国际争端解决机构的裁判实践来看,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甚至已经发展成了一项习惯国际法上的法定义务。只要一国拟进行的活动具有产生重大跨界损害的风险,该国就应当遵守该规则,严格履行进行环境影响评价的义务,且在正式开始活动之前就应作出,在活动进行的过程中,必要时也应对项目对于环境的影响进行监测。其次,环境影响评价不仅是一项程序义务,它还包含了实质内容,具体的环境影响评价报告的内容由各国国内法或授权该活动时依据个案的具体情况决定。
[1]欧文·麦克因泰里.国际法视野下国际水道的环境保护[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4.
[2]欧文·麦克因泰里.跨界水道环境影响评价的法律与实践[J].江西社会科学,2012,(02).
[3]林灿铃.国际环境法(修订版)[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
责任编辑:肖 琴
D9
A
1009-3605(2017)03-0088-05
2017-03-10
蹇潇,女,湖南安乡人,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国际环境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