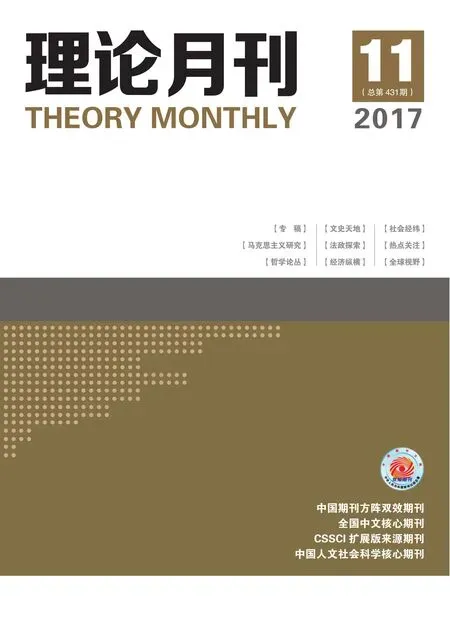民族性与时代性的统一
——话语建构视阈下中国共产党的话语逻辑
□黄 斐
(北京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0871)
民族性与时代性的统一
——话语建构视阈下中国共产党的话语逻辑
□黄 斐
(北京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0871)
话语是一种与社会、道德、秩序相交织的隐蔽又普遍存在的权力关系,话语权即掌控话语的基本规则和语言规范,从而拥有制定规则的权力,控制观念、思想、文化等,话语的建构实质上是为了掌握话语权,形成自身赖以支撑的话语体系,实现文化自信与文化自觉。从话语建构的视阈出发,中国共产党的话语逻辑突出展现了两个维度:民族性与时代性。其中对外话语逻辑突出了民族性维度,经历了依赖—探索—自主—自觉的过程,从俄式马克思主义话语的接受者转变为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话语的积极开拓者;对内话语逻辑突出了时代性维度,经历了革命—建设—改革—深化改革的过程,体现了理论创新和实践发展的良性互动。
中国共产党;话语;建构;民族性;时代性
中国共产党逾今已走过96年历程,期间实现了理论体系的两大历史性飞跃,产生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习近平总书记在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决策,并在2015年提出发展 “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标志党在理论创新之路上又向前跨越了一步。中国共产党在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诠释中建构了自身的独特话语,理论体系发展史同时也是一部话语体系的建构史。理论是话语的媒介,话语能力通过理论传播来彰显。在党的历史中,如何处理好信仰与实践的关系一直是核心问题之一,即如何将源于欧洲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与建设实际相结合,在信仰与实践的博弈中掌握“中国话语”的主动权,寻求“中国道路”的发展路径,话语体系的建构因而成为党的重要任务。
1 话语及后殖民语境下的话语霸权
话语一词源自拉丁语“diseusrus”,最初具有“到处跑动”的意蕴,发展为英语“discourse”后,有“言谈、言说”的意思。对话语的研究最早起源于语言学领域,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开创了结构主义语言学研究,巴赫金(Бахтинг,Михаил МихаЙлович)则使话语成为与思想信仰、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相交织的术语。20世纪60年代,西方哲学领域出现了“语言学转向”,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分析哲学、现象学、解释学、西方马克思主义、后现代主义、后马克思主义等都十分关注语言问题,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伽达默尔 (Hans-Georg Gadamer)、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 德里达 (Jacques Derrida)、利奥塔(Jean-Francois Lyotard)、罗蒂(Richard Rorty)、拉克劳(Ernesto Laclau)和墨菲(Chantal Mouffe)、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等都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探讨。此后“话语”研究大大超出了语言学的范畴,在不同领域不同学科中都出现了,因此,“话语”的含义在不同领域内有众多说法,至今没有形成统一共识。其中对于话语的分析最为系统、影响最大的福柯(Michel Foucault)创立了“话语分析”范式,将话语与权力相结合,运用“知识谱系学”和“权力分析法”对处于边缘的话语进行权力分析,将权力建立在支配技术的微型权力的分析上,以一种局部的微小话语分析反抗科学整体性的、知识等级性的知识[1]。
本文所使用的话语,借鉴福柯的话语权力概念,认为话语是一种与社会、道德、秩序相交织的隐蔽又普遍存在的权力关系,人们的思想和生活都与话语紧密相连。话语权即掌控话语的基本规则和语言规范,从而拥有制定规则的权力,控制观念、思想、文化等。掌握话语权才有可能居于中心文化地位,反抗话语霸权,成为主流话语主体。
在话语研究中,对话语霸权的研究占有重要地位,而后殖民语境下的话语霸权又是话语权研究中的主流。后殖民主义是二战后流行起来的一种哲学思潮。战后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纷纷摆脱帝国主义的殖民,取得民族独立,但在文化上依然依赖原宗主国,处于话语边缘地位。后殖民主义主要指在殖民时期之后,原宗主国对原殖民地从文化、语言、知识等方面进行干涉和渗透。因此后殖民主义研究主要侧重于分析殖民话语与被殖民话语之间的文化话语权力关系,延伸开来还包括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之间的话语霸权现象以及在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帝国主义研究,旨在解构建构在不平等话语上的权力——知识体系。
一般认为,后殖民主义话语研究的先驱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葛兰西(Antonio Gramsci)。葛兰西提出了“文化领导权”理论,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产阶级通过文化生活实现对人的思想形式的控制。资产阶级不是通过强制性的国家机器,比如军队、警察、法院等,而是通过宣扬主导价值观念,使人们形成世界观、价值观、方法论上的统一,实现文化上的认同,从而使资产阶级的统治具备合法性[2]。福柯的“权力话语”则使“话语权”理论系统化,成为话语霸权研究的重要范式。美国后殖民主义学者萨义德(Edward Said)将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与福柯的“权力话语”相结合,创立了“东方学”,揭示了语言如何通过社会机构和知识生产发挥其政治力量。“东方学”,又称 “东方主义”,是一种思维方式和权力话语方式,即西方通过做出与东方有关的描述,对东方作出权威裁断,进行描述、教授、殖民、统治,成为西方用以控制、重建和君临东方的一种方式。“东方主义”对东方的表述,使东方丧失了自我意识,自然也不会实现文化身份的认证,从而完全成为“他者”身份[3]。在《文化与帝国主义》一书中,萨义德扩充了《东方学》的观点,从文化的角度分析了当今帝国主义对第三世界进行的意识形态和文化殖民[4]。同样从后殖民主义的角度对资本主义国家的话语霸权进行分析的还有汤林森(John Tomlinson)和詹明信(Fredric Jameson)。汤林森在《文化帝国主义》一书中对后殖民主义语境下的话语进行了多层次分析[5]。詹明信用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分析方法深入分析了全球化时代资本主义的文化霸权,试图在第一世界(中心文化)和第三世界(边缘文化)的二元对立关系中,找到第三世界把握自身文化语境和话语权的出路,为理解后资本主义时代的文化逻辑提供了重要的分析范式[6]。
2 话语的建构
“建构”一词在哲学层面上表示一种价值论上的转向,即世界从一个与人无涉的自在世界转变为人创造的世界。苏格拉底(Socrates)与柏拉图(Plato)被认为是最早的建构主义者。维柯(Giovanni Battista Vico)与康德(Immanuel Kant)被奉为近代建构主义的先驱。胡塞尔(Husserl)的“构成性概念”、海德格尔与伽达默尔的现代解释学、萨特(Jean-Paul Sartre)“存在主义”等思想都体现了建构痕迹。瑞士心理学家和哲学家皮亚杰(Jean Piaget)创立“发生认识论”原理,被认为是当代建构主义的创立者。维果茨基(Lev Vygotsky)、曼海姆(Karl Mannheim)、默顿(R.K.Robert King Merton)、维特根斯坦(Ludwig Josef Johann Wittgenstein)、库恩(Thomas Sammual Kuhn)等均为当代社会建构主义的代表人物。此外,福柯的理论也体现了建构思想,他认为身体、性别都是话语的产物,是被人为建构的,被一系列社会的、权力的、宗教的、习俗的因素所规范和限制。在福柯的理论中,话语不再是封闭的结构,而是与复杂变化的现实环境、社会和历史等诸多因素勾连的符号系统,具有多重功能。话语与权力交织在一起,使人受到规训[7]。
从某种程度上说,马克思(Karl Marx)也是建构论的支持者。马克思强调“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8]。“不是处在某种虚幻的离群索居和固定不变状态中的人,而是处在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中的人”[9]。他从社会实践和社会关系出发来考察人的存在和人的本质,把人置于真实的客观境遇中,通过人与人的相互交往,人与社会的互动来实现人的发展。在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中,意识形态与经济基础、上层建筑之间存在着“结构功能”关系。葛兰西、詹明信、拉克劳和墨菲等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和后马克思主义者的话语霸权思想本质上仍在马克思的分析框架内。
从建构主义的视角看,话语本身就是建构的产物,是主体与客体即人与社会互动的结果。处于强势地位的主体可以通过掌握主流话语场以实现话语殖民,并使位居边缘话语场的一方逐步丧失自主性,最终实现价值认同。对话语进行有意识的建构,将观念、价值、文化等融合进符码系统中,形成同一语言规则体系和话语框架,对于掌握支配性话语从而在国家与社会的“霍布斯丛林”中站在话语高地而言,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对民族和国家而言,话语的建构实质上是为了掌握话语权,形成自身赖以支撑的话语体系,在所处的权力体系内寻得一席之地,反对话语霸权,在思想交锋中占据主动地位,在此基础上实现文化自信与文化自觉。
话语的建构体现出两大特性。其一,由于话语本身受到内外部因素影响较大且具有易变性,在多元性与异质性并存的话语场内建立一套稳定的叙事体系绝非易事,因此话语的建构需要在内部协调与外部协调中保持均衡,在内在张力与外在张力之间不断进行自我调节与重新组合,必要时进行重构与重释,以实现有效的话语规范。其二,话语建构的复杂性同时也表现为多向度多维度的发展特性,面对不同的主体与境遇表现出不同立场,在不同环境中不断发展变化,在遇到失衡与混乱状态时保证稳定的内在发展逻辑,尤其是当处于边缘文化地位时,能在与中心文化的交锋中保证自身独立性。如此,使本民族形成同一观念模式和同一价值倾向的话语体系,在国际国内话语场域内实现文化认同与身份认同。
3 民族性与时代性的统一:中国共产党的话语逻辑
中国共产党在90多年的历史中不断致力于建构自身话语体系,掌握话语权以争取中国革命的胜利和实现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虽然中国未曾经历完全意义的殖民阶段,但在革命与建设的过程中,时常面临他者的话语霸权,需要不断进行话语博弈,避免成为后殖民主义语境下的边缘话语主体。这期间,中国共产党的话语体系实现了两次历史性飞跃,产生了两大历史性成果,即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1938年毛泽东同志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中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开启了中国的原创性革命话语。1945年党的七大将“毛泽东思想”列入党章,“毛泽东思想”的形成标志着话语建构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第二次飞跃发生在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改革开放新时期,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逐步形成为代表。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建构“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将党的话语推入新的发展阶段。
从话语建构的复杂性和多维度的发展特性来看,党的话语建构逻辑体现了两个突出维度:民族性维度与时代性维度。对外话语逻辑主要表现为民族性维度,目的为反对俄共和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国家的话语霸权,实现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对内话语逻辑主要表现为时代性维度,目的为因应国内环境变化转变话语以适应时代发展。
3.1 民族性维度
从民族性维度来说,党的话语建构依次经历了依赖、探索、自主、自觉的过程。具体而言,从依赖俄共和共产国际,以俄式话语为主导到反对俄共话语霸权,争夺中国革命与建设以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路线的话语权,从以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为唯一正统的社会主义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的形成,并在改革开放之后与资本主义国家争夺社会主义话语权,直至在全球化体系中积极建构“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力图在全球化体系中形成中国话语一极,从而实现更广泛的国际影响力。在此过程中,党的话语经历了从防御性建构到主动建构的变化,从俄式马克思主义话语的接受者转变为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话语的积极开拓者。
1921 年中国共产党成立至1935年遵义会议期间“俄式话语”在党内居于领导地位,党内话语的主要特征是“以俄为师”,普遍将俄式马列主义视为唯一正统的马克思主义,以俄共和共产国际的指示和经验来指导中国革命。从上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前期,党的思想、组织、革命策略等多以俄共和共产国际为纲。党之所以在早年高度依赖“俄式话语”离不开俄共对马克思主义的独占性话语解释。十月革命给中国带来了马克思主义,然而当时传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已被深深打上了列宁主义的烙印。十月革命的胜利使之后成立的各国共产党纷纷以马列主义为唯一正统的指导思想。斯大林主义的形成进一步强化了俄共的话语权威地位,俄共凭借强大的知识传输能力和宣传优势将带有列宁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烙印的马克思主义熔铸进中国共产党人的血液中,造成了党内早期对俄式马克思主义的高度依赖。而革命经验的缺乏,使第一个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苏俄自然而然地成为效仿的模板。直到1935年遵义会议毛泽东同志取得党的实际领导权,党的原创性革命话语才真正走上历史舞台,并被用来指导中国革命。
遵义会议以后,党开始了漫长的话语探索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以“毛泽东思想”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逐渐成为党的话语主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的产生是在革命遭遇挫折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人努力摆脱联共(布)和共产国际话语霸权、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必然结果。毛泽东同志早年就十分注重联系中国具体实际开展革命事业,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文中毛泽东同志通过对中国社会各个阶级的深入分析,指出中国无产阶级的最广大和最忠实的同盟军是农民,反击了党内的左倾和右倾倾向,对党内外对农民革命斗争的责难进行了坚决回击[10]。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毛泽东同志率先开辟了“工农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相继发表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等著名文章,对中国农村革命根据地存在的必然性和根据地的军事、组织等问题进行了详细探讨[11]。在1938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提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说来,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12]明确提出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任务。1945年党的七大召开,“毛泽东思想”被写入党章。此后,以“毛泽东思想”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逐渐取代“俄式话语”成为党内的支配性话语,被用于指导党的革命和建设工作。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从确立到巩固并非一帆风顺,期间因中国革命与建设状况、中苏关系的变化以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经历了起起伏伏。1958年以后中苏关系恶化,爆发了公开论战,围绕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和社会主义建设等问题进行了激烈争论,党积极争夺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话语权,在社会主义阵营乃至全世界发出了自己的声音。但在那时,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仍然被视作正统的社会主义,尽管苏共二十大以后中国共产党开始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但由于对“社会主义”的理解没有取得实质突破,导致之后中国的社会主义探索遭遇挫折。
毛泽东同志逝世后,经过两年的徘徊期,党做出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以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为开端,创造性地突出了“中国主体”意识,以区别于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在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中,邓小平同志提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13],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概念,逐步开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建构。此前,党主要是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与苏共争夺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以及国际共运路线的话语权。改革开放以后,中国进入全球化体系,直面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竞争,西方国家凭借独占性话语优势建构了“中国形象”。在后俄式话语时代进行话语转型,不仅旨在区别于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也是为了与资本主义国家的话语霸权相抗衡,实现“社会主义的中国化”,建构中国独特的社会主义话语体系,旨在用“中国特色”武装“社会主义”,用“社会主义”支撑“中国特色”,在二者的双重论证中构筑属于中国人的文化认同和文化自信。由“毛泽东思想”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的转变,是党迫于国内外严峻危机作出的历史性选择,标志党的话语自主意识的觉醒。
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国际化程度的加深,西方诸多思潮纷纷涌入中国,社会思潮纷纭激荡,马克思主义在国内面临严峻的认同危机,在国际上遭遇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话语霸权挑战。为进一步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寻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强大的话语张力,“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话语应运而生。2015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次集体学习时指出,要根据时代变化和实践发展,不断深化认识,不断总结经验,不断实现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良性互动,在这种统一和互动中发展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14]。发展“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在高度全球化的背景下提出的,表现出党在21世纪新阶段建构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的高度理论自觉。建构“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一方面突出了21世纪的时代背景,强调新时期新阶段新理论的建构,另一方面进一步突出“中国特色”,彰显了中国意识,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力图实现“民族性”与“全球性”的融合。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到“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党从被动接受到主动融合、发展、创新马克思主义,使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从二元调和到一元统一,在中国实现了由“客体”向“主体”的转变,这是建构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的重大突破。
3.2 时代性维度
从时代性角度而言,党的话语逻辑依次经历了革命、建设、改革、深化改革的过程。具体而言,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党的对内话语主要是围绕“革命”,以“新民主主义革命话语”为代表。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党积极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经验,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依据国内外环境变化积极调整政策和话语,作出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2013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以适应国家新发展。
新中国建立以前,党的主要任务是实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不论是遵义会议前的“俄式话语”还是之后以“毛泽东思想”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体系的建构,均以实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为目标,其中以“新民主主义革命话语”为代表。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毛泽东同志率先在实践上开创了“工农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新道路,并在遵义会议以后逐渐形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话语”。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共产党人〉发刊词》《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论著中,毛泽东同志详细阐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思想,分析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任务、动力、领导阶级,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两步走发展战略,并制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纲领。“新民主主义革命话语”融合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民族文化因素,对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进行了延伸和发展,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原创性革命话语尝试,建立了党的革命叙事体系,解决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进行什么样的革命、怎样进行革命这一问题,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建构的重要成果。
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党继续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并在1956年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社会主义的建设成为新时期的主要任务,毛泽东同志提出要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进行 “第二次结合”,在《论十大关系》《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等文中,毛泽东同志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积极探索。党的八大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提出,“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党和全国人民的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15],作出了将党的工作重点转向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体系的形成过程中,党一直面临着将源于欧洲和俄国的理论和经验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问题。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正统,又要满足中国实际的需求,在理论和环境方面都面临很大差异,而中国的革命和建设又在不断发展、变化,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必须在实践中不断与时俱进。另一方面,“文革”结束后,党面临后“文革”时代的话语重建问题,需要打破“两个凡是”的教条思想,因此“改革”话语应运而生。1978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扫清了“两个凡是”等教条主义思想,为改革开放吹响了前奏。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的主要任务从 “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作出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确立了“改革”的话语基调。“改革”话语不仅指导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也给中国的思想领域带来颠覆性转变,影响深远。
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了飞速发展,也产生了一系列突出矛盾和挑战,如经济上发展方式依然粗放,产业结构不合理,科技创新能力不强,城乡区域发展不协调,社会贫富差距较大,教育、就业、医疗、住房、社会保障和生态环境等方面矛盾增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解决这些问题, 关键在于深化改革”[16],“改革开放中的矛盾只能用改革开放的办法来解决”[17],“改革是由问题倒逼而产生,又在不断解决问题中得以深化”[18]。在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作出了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决策,使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步入新的历史阶段,党的对内话语也因应实践要求转变为“深化改革”。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是为了解决我国发展中面临的矛盾和挑战,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和发展。“深化改革话语”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出的,目的是在理论层面诠释党的方针政策,丰富党的理论资源,使其更具话语张力。当下,中国依然在全面深化改革的道路上前进,实践发展永无止境,解放思想永无止境,中国的话语体系建构还需进一步冲破思想观念的障碍和利益固化的藩篱,凝聚思想共识和行动智慧,在实践中实现理论的创新。
4 结语
中国共产党的话语建构逻辑体现了三大明显特征:第一,党的话语体系是在理论与实践的互动中生成的,在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中得以不断发展和完善。理论是对现实过程的描述,是对事实作出的抽象或概括。《共产党宣言》中提出共产党人的理论原理,“绝不是以这个或那个世界改革家所发明或发现的思想、原则为根据的”,而是“我们眼前的历史运动的真实关系的一般表述”[19]。党的话语体系是在探索中国革命与建设道路、解决中国问题的过程中生成的,是对这个过程的理论表述。离开中国的实践道路,就不可能深刻理解中国理论,更不能理解以此理论为基础的话语体系。第二,党的话语建构经历了从防御性应对到主动性建构的变化。在从话语的被殖民到话语的自觉建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从舶来思想内化为内在自觉,在中国实现了话语革命,产生了更强大的生命力,也使党的话语具有更宽广的全球视野和更深厚的历史视野。第三,党在话语建构的过程中重视对中国传统资源的利用。从毛泽东时代将农民革命经验与农民文化融入马克思主义,到邓小平时代对“中国特色”的强调,再到如今从中华文明史角度对中国道路进行自觉的知识论话语建构,中华传统历史与文化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
中国共产党的话语体系是一个持续发展的动态建构过程,在过去的96年历史中,党的话语内核和外延不断深化、扩展,在对时代特点的深刻把握中融合了民族性与世界性、多样性与统一性,成为具有宽广视域和强大效应的话语引力场,开拓了马克思主义新境界,增强了中国人的文化自觉和理论认同。“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不可能找到现成的教科书。”[20]中国道路必须依托于中国实际,用“中国话语”诠释“中国道路”,以“中国道路”完善“中国话语”,建构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话语体系。
[1]米歇尔·福柯.知识考古学[M].谢强,马月,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M].刘北成,杨远婴,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
[2]安东尼·葛兰西.狱中札记[M].田时纲,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3]爱德华·W·萨义德.东方学[M].王宇根,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
[4]爱德华·W·萨义德.文化与帝国主义[M].李琨,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
[5]汤林森.文化帝国主义[M].冯建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6]詹明信.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M].张旭东编,陈清桥,严锋,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
[7]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M].刘北成,杨远婴,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
[8][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01,525.
[10][11]毛泽东选集:第 1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3-44,47-84.
[12]毛泽东选集:第 2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534.
[13]邓小平文选:第 3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
[14]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方法论 提高解决我国改革发展基本问题本领[N].人民日报,2015-01-25(1).
[15]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二十四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248.
[16][17][18]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71-72,69,74.
[1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2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44-45.
[20]习近平主持召开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强调 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 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N].人民日报.,2016-05-18(1).
10.14180/j.cnki.1004-0544.2017.11.019
D26
A
1004-0544(2017)11-0116-6
黄斐(1990-),女,福建宁德人,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
责任编辑 赵继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