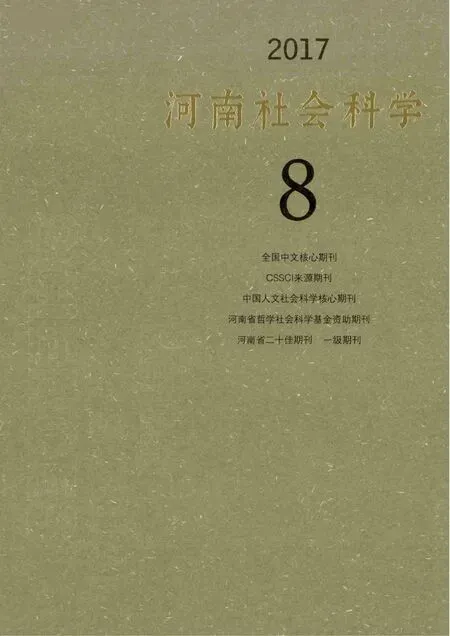第四次工业革命经济观念变革与企业战略调整
李 曼
(广东财经大学 信息学院,广东 广州 510320)
第四次工业革命经济观念变革与企业战略调整
李 曼
(广东财经大学 信息学院,广东 广州 510320)
在云计算技术和物联网技术的推动下,第四次工业革命的主导性成果是大规模定制化智能制造。应对巨大的时代变迁,要求人们的经济观念从大规模批量生产转向大规模个性化定制生产,从“1到n”的竞争主导转向“0到1”的协同创新,从等级、服从、大一统转向平等、自主、多元化,从纵向供应链转向纵合横联供应链。要求企业将差异化战略逐渐提升到首要地位,将创新作为自身发展的根本动力,加速向新型组织模式、生产模式和商业模式转变,从谋求供应链环节优势转向谋求供应链整合优势。
第四次工业革命;经济观念;企业战略
由蒸汽机的使用所触发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引领人类社会从手工生产时代跨入机械生产时代。伴随电力被利用和福特流水生产线的出现而发生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大批量规模化生产方式应运而生。由半导体技术、大型计算机、个人计算机和互联网技术催生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基本标志是“工业自动化”。正在拉开序幕的基于云计算技术和物联网技术的第四次工业革命,主导性成果则是大规模个性化定制的“智能制造”。第四次工业革命,正以惊人的速度拓展开来,不仅极大地改变着人类的生产方式,而且极大地改变着人类的观念、行为、生活方式与交往方式。
一、第四次工业革命与经济观念变革
设备智能化、能源管理智能化、生产智能化与供应链管理智能化的“智能制造”,带给人类社会的变化是巨大的。这种剧烈的时代变迁,要求人们的经济观念必须发生相应的变化。而经济观念的变化,无疑是中国制造业抢占先机、获得竞争优势的前提条件。
(一)大规模批量生产观念向大规模个性化定制生产观念转变
“智能制造”的基本内涵,就是基于数字化的机械、知识、管理和技能等多种要素的有机结合,借助物联网的资源、信息、物品、设备、人的互联互通,通过生产设备自动化层与生产制造管理层的无缝对接,实现合乎消费者个性化定制要求的生产计划的自动生成及其生产要素的自动优化配置,进而自动完成产品的全部生产过程,实现以产品为中心的同质大批量生产方式向以用户个性化需求为中心的大规模定制生产方式转变。
伴随生产方式的上述变化,人们的观念也要发生相应的变化。这就是要从大规模批量生产观念转向大规模个性化定制生产观念。“批量”与“定制”不仅是字面的差异,更包含着本质的不同。大规模批量生产观念,基于企业的立场,注重的是生产成本水平的降低,追逐的是企业利润的最大化;大规模个性化定制生产,基于消费者的立场,注重的是服务质量的提升,追求的是消费者差异化需求的满足。正因为两种观念存在本质的不同,所以前者向后者的转化过程不可能一帆风顺,难免要伴随一系列矛盾,甚至要遭遇种种阻力与冲突。
现今,我国一批富有远见的企业已经捕捉到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发展机遇,快速反应、付诸行动,成为大规模个性化定制生产方式的践行者;还有一批企业,已经感受到第四次工业革命的脉动,正在摩拳擦掌、跃跃欲试、整装待发;而相当多的企业则对社会的急剧变动没有察觉,仍然因循守旧,抱着既往的观念,循着传统的轨道,对新一次工业革命没有丝毫敏感。
(二)“1到n”的竞争主导观念向“0到1”的协同创新观念转变
硅谷创投教父、Paypal创始人、Facebook首位外部投资者彼得·蒂尔在其所著的《从0到1》一书中,率先向竞争主导的市场观念发难。在彼得·蒂尔看来,传统的市场就是“从1到n”的宿命。走在这条路上的企业厮杀在红海里,它们从竞争对手那里抢夺市场,以便在惨烈的竞争中赢得生存。然而,这种局限于此消彼长的零和博弈,充其量只是“从1到n”的同质化复制与扩张,并未给世界增添任何新的发展可能性与价值。彼得·蒂尔推崇的是“从0到1”,也就是“从无到有”或“道生一”的智慧。这种“从0到1”的非零和博弈,意味着创新,意味着赋予世界新的发展元素,意味着给世界增添新的发展价值。
人们不禁要问,这种变化缘何产生?为什么人们视为至理名言的“竞争图存”的观念竟然会失去它往日的光辉,逐渐被日渐高涨的“协同创新、共荣共存”的观念所取代?在笔者看来,这种变化无疑是信息网络技术高度发达的产物,无疑是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亦即大数据与智能制造时代转变的前奏。
数据的使用价值与物质性产品使用价值存在较大差异,后者的使用价值不能共享,其使用具有排他性。不止如此,物质性产品的使用过程,也是其被消耗亦即丧失使用价值的过程。数据的使用价值则不仅可被共享,共享的人越多,使用价值越大;而且数据被使用的过程,也是新数据产生的过程,数据使用的人越多,产生的新数据也越多,派生的效用也越广。
工业时代,是以大规模物质性要素投入和大批量物质性产品生产为基本特征,由于信息技术水平的局限,数据源的开发困难重重,人类所能获得的信息数据资源比较贫乏。工业时代的企业,面对有限甚至是无法再生的物质资源,只能进行零和博弈,使尽浑身解数去占有更大市场份额。显然,工业时代的最高法则只能是“适者生存”,工业时代的主导性观念只能是“竞争图存”。
跨入大数据与智能制造时代门槛之后,与以往的工业社会不同,信息数据资源投入已经取代物质性要素投入的地位,开始成为制造业中居主导地位的、发挥着决定性作用的资源。与这种变化相伴随,“创新”开始成为制造业的主旋律,成为推动制造业发展的基本动力,图存图强的最佳选择不再是“虎口夺食”,而是如何避其锋芒、另辟蹊径。
既然作为主导型投入的信息数据资源的特有本质是共享、共创,共享的规模越大,信息数据资源发挥的作用就越大;共创的范围越广,共创成果的数量就越多,质量就越高。至此,零和博弈就必然让位于非零和博弈,竞争就必然让位于协同,垄断独享就必然让位于合作共赢,协同创新也就必然成为大数据时代的主导性观念,合作共赢也就必然成为新时代的主旋律、最强音。
(三)等级、服从、大一统观念向平等、自主、多元化观念转变
工业时代向大数据与智能制造时代过渡派生的另一重大的观念变化,就是等级、服从、大一统观念转向平等、自主、多元化观念。
工业时代,金字塔状的层级组织结构是制造企业的基本组织形态。在这种组织形态下,信息主要通过纵向通道而非横向通道来传递。这种传递方式,与工业时代的信息技术水平、信息数据的采集存储处理能力是相适应的,前者不过是后者派生的必然结果。说得更明确一点,工业时代的信息技术与处理能力,还不足以使密如蛛网的横向信息得到充分的挖掘与高度的利用,绝大多数信息处于潜在的、沉睡的状态。至于自下而上纵向传递的信息,则由于遭遇叠加层级的一次次过滤,大量表征事物个性、特性的信息损失了,留下的只是反映事物一般性、共性的信息。基于该类信息所做的决策,无疑不具有个性化只能是同质化的批量生产。
工业社会的金字塔状的企业组织形态,必然派生并强化等级观念、服从观念和大一统观念,致使企业处于刚性有余、弹性不足,统一有余、机动不足,服从有余、自主不足的发展状态。这种状态与工业社会所要求的基本经济秩序是彼此呼应、相互匹配的。然而,一旦跨入智能制造时代,上述观念的局限性、弊端、危害便会显露出来,固化的思想状态无法满足创新发展的需要。
大数据与智能制造时代企业组织形态最为显著的变化,就是一反金字塔层级结构的常态,转而向扁平化、网络状结构发展。由于大数据与智能制造时代的信息网络技术已经发展到如此的高度,使人们可以凭借触角无所不及的有线无线网络,用极低廉的成本采集、存储、处理海量的信息,因而使工业时代客观存在着却不得不处于沉睡状态的部门与部门之间、生产系统与生产系统之间、劳动者与劳动者之间、机器设备与机器设备之间、原材料与原材料之间、不同生产要素之间的海量信息得到挖掘和利用,进而建立起纵横交错、密如蛛网的多维联系。换言之,第四次工业革命时代的企业,其内部的大量信息完全可以通过横向的、直接的渠道得到沟通、交流与处理,只有那些事关全局战略决策的信息才仍需通过纵向的渠道来传输。在这种情况下,借助纵向信息传递方式建立起来的金字塔状的企业组织形态,便必然丧失其存在的价值与意义,而代之以扁平化、网络状的新型企业组织形态。
如果说金字塔式的高度集权的企业组织形态必定滋生等级、服从、大一统观念的话,那么,扁平化、网络状的企业组织形态则会淡化等级观念、强化平等观念,淡化服从观念、强化自主观念,淡化大一统观念、强化多元化观念。新型企业组织形态在使企业保持政令畅通、令行禁止、秩序井然、高度统一的同时,让每个层级、每个局部、每个单元的自主性、积极性、创造性都得到充分发挥,从而具有更强的弹性、多样性,具有更高的效率和更大的活力。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扁平化、网络状的企业组织形态,是与大规模定制生产方式、商品差异化发展相匹配、相统一的企业组织形态。
(四)纵向供应链观念向纵合横联供应链观念转变
伴随着工业时代向大数据与智能制造时代推移,商品供应链及其相关的观念也在发生着变化。
在工业社会前期,商品供应链大致由生产要素的供应、商品的生产与商品的消费三大环节组成,供应链三大环节分别对应的是生产要素供应商、商品生产商和消费者三大主体。工业社会前期商品的研发设计、流通、销售等功能尚未与商品的生产功能分离开来,均由生产商来承担,商品的研发设计、流通、销售等功能的分工,体现为企业内部的部门与部门之间的分工,而不是企业与企业之间的社会分工。这表明工业社会前期围绕商品供应链所展开的纵向分工还不够发达,其水平还处于相对低下的状态。
到了工业社会中后期,当生产能力扩张到商品的研发设计、流通、销售等功能可以由独立的企业来承担的时候,这些功能便逐渐从生产企业中分离出来。围绕商品供应链所展开的纵向分工不再主要体现为生产型企业的内部分工,而是主要体现为生产型企业与生产服务型企业的外部分工。这表明社会分工达到了更高的水平。
大数据与智能制造时代,展现在人们面前的则是并行不悖的双重趋势:一方面,商品供应链的纵向社会分工越来越深、越来越细,以至越来越多的服务性、配套性业务从生产商中分离出来,成为生产服务型企业的经营对象,成为第三产业的有机组成部分;另一方面,不同商品供应链之间的横向整合趋势越来越强,诸如信息平台商、融资平台商、物流平台商、交易平台商、展示平台商和集多种功能于一体的综合平台商等雨后春笋般成长起来。这些平台商不是面向单一的商品供应链提供服务,而是面向众多的商品供应链提供服务。“平台”已经成为当下最时髦、使用频率最高的词语;“平台经济”已经成为众多厂商所追捧、最具发展潜力的新型经济形态。
上述双重变动趋势必然派生新的经济观念。具体说来,在工业时代,人们关注的是如何通过与处于供应链不同环节的厂商的协调、配合、对接,以实现供应链的优化和提升供应链的运行效率,或者说,居于支配地位的是一种纵向的供应链观念。而在第四次工业革命背景下:一方面开始转向生产性服务企业如何通过整合众多供应链的同类环节亦即平台经济的发展,以降低全社会商品生产的成本水平,进而获得更大的生产性服务规模经济效益;另一方面开始转向制造业企业如何通过全方位获取、整合各种平台所提供的生产性服务资源,以缩短自身内部的供应链条,实现与消费者差异化、个性化需求及其变动最紧密、最快捷的对接。简言之,不同企业供应链之间“横联”和企业内部供应链“纵合”的迅速产生与发展,必将推动纵向供应链观念向纵合横联供应链观念转变。
二、第四次工业革命与企业战略调整
工业社会向大数据与智能制造时代的转变,不仅要求人们的经济观念发生相应的变化,而且也要求企业对自身的发展战略做出相应的调整。
(一)将差异化战略逐渐提升到首要地位
被管理学界誉为“竞争战略之父”的迈克尔·波特,基于产业竞争优势及“五竞争力模型”对产业内企业竞争地位进行了研究,他指出:企业可依靠成本领先、差异化和目标集中三大基本竞争战略获得持久的竞争优势。
成本领先战略目标,是企业争取成为产业内低成本生产的厂商。在企业成本略低于或接近产品平均定价标准的场合,成本领先战略将帮助企业获得高于产业平均利润水平的经营业绩。进一步地,该战略可通过追求规模经济、专有技术创新、垄断价格优惠的原材料等方式实现差异化战略目标,争取创造和保持产品或服务的独特性,以满足客户的个性化需求。客户通常愿意为满足自身的个性化需求而支付高于购买普通商品价格的价格,在差异化商品的价格溢价大于研发和生产差异化商品所附加的额外成本的场合,企业同样可获得高于产业平均利润水平的经营业绩。差异化战略可依靠产品创新、售后服务优化、营销渠道拓展、品牌建设等方式实现。目标集中战略则是成本领先战略与差异化战略在特定条件下的综合。
就我国企业而言,目前成本领先战略仍重于差异化战略无疑有其必然性,差异化战略得以全面推行并充分发挥作用的技术基础与条件尚不完备,企业之间的竞争仍普遍表现为以降低成本水平为主要手段的价格竞争,而不是以满足差异化需求为主要手段的提高产品附加值的竞争,这也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动因之一。
第四次工业革命时代的企业,差异化战略必定会优于成本领先战略。因为在信息网络技术高度发达的大数据与智能制造时代,大规模定制生产将成为一种普遍的生产方式。在此背景下,企业之间围绕降低成本水平展开的价格竞争必将退居次要地位,代之以提高服务满意度为目标的错位发展、差异发展的互利共赢的格局。
对正在或即将发生的变化,我国企业务必要有清醒认识,并身体力行、未雨绸缪,提前做好战略调整的准备,积极创造条件,逐渐将差异化战略提升到首要地位。
(二)将创新作为自身发展的根本动力
伴随着工业时代向大数据与智能制造时代迈进,企业之间的较量,将会从零和博弈转向非零和博弈。
在零和博弈的场合,企业面对的是一个同质化的市场。也就是说,企业提供给市场的产品不存在大的差异,企业之间比拼的是成本,争夺的是本企业产品的个别成本低于市场平均成本的优势地位,追逐的是自身产品市场份额量的扩张。面对这样一个市场,企业关注的显然不是产品的差异化与独特性,而是如何以更小的成本去复制更多的相同产品,“创新”并不在企业的视野之中。
在非零和博弈的场合,企业面对的是一个非同质化的市场。也就是说,企业提供给市场的产品,其间存在显著的差异,甚至是个性化差异。企业之间比拼的是与消费者差异化需求的吻合度,争夺的是自身产品的附加值高于市场产品平均附加值的优势地位,追逐的是需求变动与产品发展的前沿。面对这样一个市场,企业尽管仍然会关注成本,但关注的重点是如何推陈出新、以特取胜,“创新”无疑会成为企业发展的原动力、主旋律与生命线。
零和博弈市场向非零和博弈市场的转变,必然要求企业从沿袭低成本复制战略转向奉行崇尚创新、注重创新、致力创新的战略。
我国现今仍有相当多的企业,在这一重大的转变面前,因为种种原因不愿改变或不知怎样改变企业发展战略。在笔者看来,面对巨浪般席卷而来的创新大潮,大企业也好、中小企业也好,财力雄厚的企业也好、财力单薄的企业也好,老牌的企业也好、新生的企业也好,都必须勇敢应对、从容应对、设法应对、创造条件应对,这是求得生存、发展的唯一道路,低成本复制发展战略在第四次工业革命背景下已是明日黄花。
(三)加速向新型组织模式、生产模式和商业模式转变
扁平化网络状组织模式、大规模定制生产模式和纵合横联的商业模式是第四次工业革命时代组织与发展模式变革的主要方向。
在我国现实的条件下,制造业企业的扁平化网络状组织模式、大规模定制生产模式和纵合横联的商业模式,尽管“小荷才露尖尖角”,尚未充分展现其强大的生命力,但其代表的发展方向和广阔的发展前景却毋庸置疑。
伴随着第四次工业革命时代的到来,传统的企业组织模式、生产模式与商业模式正在被颠覆,新型的企业组织模式、生产模式与商业模式正在迅速生长。传统的金字塔式、习惯于发号施令的管理模式,传统的热衷于产品市场规模量的扩张而漠视消费者差异化需求及其变化的经营思路,传统的商业模式亦步亦趋而不思如何创新求变的经营战略,已经无法适应新一次工业革命变迁的要求。企业必须认清自身的差距,紧跟时代的潮流,加速向扁平化网络状组织模式、大规模个性化定制生产模式和纵合横联的商业模式转变。
(四)从谋求供应链的环节优势转向谋求供应链的整合优势
如前所述,在工业社会的中后期,当生产能力扩张到商品的研发设计、流通、销售等功能可由独立企业承担且具有经济合理性的时候,这些功能便会逐渐从生产企业中分离出来,围绕商品供应链所展开的分工不再主要以生产型企业内部分工的形式存在,而是主要以生产型企业与生产服务型企业的外部分工的形式存在。
这一时期位于供应链不同环节的企业,由于所处市场环境的差异,在整条供应链利益分配格局中所处位置不同。比如,处于供应链高端——创意设计环节的企业,凭借着对创意设计服务产品市场的垄断,往往可以获得稳定的超额利润;处于供应链低端——制造环节的企业,由于所处的市场通常竞争激烈,充其量只能获得平均利润。面对如此的供应链利益分配格局,企业要想从根本上改变不利的境况,显然必须实行向供应链高端发展的战略。
第四次工业革命开启的不同供应链之间的“横联”和同一供应链内部的“纵合”,则使位于供应链不同环节的企业相互关系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在大数据与智能制造时代,由于面向众多制造企业提供生产性服务的平台经济的高度发展,创意设计服务等稀缺资源不再被那些位于供应链高端的企业所垄断。企业无论大小强弱,都能以较低的成本,从相关平台获得所需的生产性服务资源。在这种情况下,决定同一供应链不同位置企业利益分配格局的,就不再是所处供应链的环节优势,而是对接生产服务性资源的能力。也就是说,企业不分大小、不分强弱,都被推上同一起跑线,能否善用大数据带来的各类生产服务性资源,直接关系一个企业的强弱与成败。
面对新的发展格局,企业无疑应从谋求供应链环节优势的战略转向谋求供应链整合优势的战略。
(五)加速“互联网+”的进程
大数据与智能制造时代,最基础的变化是以云计算技术为标志的信息网络技术的高度发展;最根本的支撑是触角无所不及的互联网和浩瀚无垠的信息数据云。企业要想紧跟社会变迁的步伐,合乎第四次工业革命发展的节拍,就必须跨上“互联网+”这趟“高速列车”,进而充分利用正在赋予人类极其广阔的发展可能性空间的“信息数据云”。企业要实现成本领先战略向差异化战略转移,要实现低成本复制状态向创新驱动状态转变,要加速向扁平化网络状组织模式、大规模定制生产模式和与消费者无缝对接的商业模式转化,要从谋求供应链环节优势转向谋求供应链整合优势,都离不开“互联网+”,都离不开“信息数据云”,它们是基础、是前提、是条件。
要加速企业“互联网+”的进程,企业自身的觉悟与努力固然不可或缺,但外部的环境与条件同样非常重要。比如,互联网基础设施的空间延展与运行效率的提升,公共数据库的系统构建与信息孤岛的全面贯通,应用信息系统的加速开发与整合配套,信息服务产业发展的兴盛与深化,“互联网+”全民宣传教育与普及,信息安全防线的打造与保障,凡此种种,均需要国家从总体上予以规划,从财力上予以支持,从政策上予以引导,从实施上予以促进。
三、结语
以大数据和智能制造为典型表现形式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正在全球范围内得到越来越多国家,尤其是发达工业国家的极力推行。我国目前正处于工业化中期向后工业化时代过渡阶段,内部存在供给侧结构性问题,外部又面临新一次工业革命的冲击。能否抓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有利时机,借助第四次工业革命的东风,在制造业创新发展与标准制定方面领跑世界,决定了未来长周期内中国制造业在全球范围内的竞争力与影响力。
第四次工业革命一方面给我国制造业带来巨大的发展压力,国际上以美国、德国、日本为代表的传统制造业强国纷纷提出了新的工业化发展方向,比如美国再工业化、德国工业4.0,日本机器人制造强国等。它们依据各自在制造业中的优势资源和有利地位,通过创新、整合与推动,进一步促进自身制造业的转型升级,通过在各类新兴产业中制定有利于自身发展的标准,意图在第四次工业革命中占据先发位置,继续垄断它们在世界制造业中的高端地位,固化世界制造业既有的版图。另一方面第四次工业革命也为我国制造业提供了难得的发展机遇。当前,第四次工业革命方兴未艾,大数据、智能制造、人工智能、物联网等从概念到实体在各个国家发展程度不一,我国在上述方面保持着良好的发展势头,存在领跑和占据标准制定高地的机遇。
为实现中国制造业在全球范围内的突围与崛起,中央从战略高度制定了《中国制造2025》,提出创新驱动、质量为先、绿色发展、结构优化、人才为本的基本方针,要求市场主导、政府引导,立足当前、着眼长远,整体推进、重点突破,自主发展、开放合作的推进原则,到2025年使我国迈入制造强国行列,到2035年我国制造业整体达到世界制造强国阵营中等水平,到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综合实力进入世界制造强国前列。《中国制造2025》为我国制造业确立了明确的中长期发展目标。为了实现上述目标,我国制造业企业在经济观念上要树立从大规模批量生产向大规模个性化定制生产转变、零和博弈向合作共赢转变、等级化管理向平等多元化观念转变;在企业战略制定上将差异化战略提升到首要位置,将创新作为自身发展的根本动力,加速向新型组织模式、生产模式和商业模式转变,从谋求供应链的环节优势转向谋求供应链的整合优势。通过观念的转变与战略的转型,站在推动与引领第四次工业革命发展的高度,有力地促进我国制造业企业转型、创新与升级,有力地促进我国经济在未来保持长期向好的发展势头。
[1]王喜文.工业4.0:最后一次工业革命[M].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15.
[2][德]克劳斯·施瓦布.第四次工业革命[M].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6.
[3][美]彼得·蒂尔,布莱克·马斯特斯.从0到1——开启商业与未来的秘密[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5.
[4][英]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肯尼斯·库克耶.大数据时代[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
[5]荣鹏飞,苏勇.组织结构扁平化下高层管理者的机遇、挑战及对策[J].现代管理科学,2015,25(11):12—14.
[6]迈克尔·波特.竞争优势[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6.
[7]李勇坚.高端服务业与流通产业价值链控制力——基于中国本土零售企业的研究[J].中国流通经济,2012,31(8):14—24.
[8]原磊.人民日报国际视野:私人定制,引领商业模式 创 新 [N/OL].http://opinion.people.com.cn/n/2014/0618/c1003-25164935.html/2014-06-18.
A Change Economic Concept Coping with the Fourth Industrial Revolution and Corporate Strategic Realignment
Li Man
Mass customization of“intelligent manufacturin”is the major outcome of the fourth industrial revoluion based on cloud computing techno1ogy and Internet of Things techno1ogy.To cope with the great changes,it is necessary to change the economic concept from the mass production concept to the mass customization concept, from the competitive expansion concept based on“1 to n”to the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concept based on“0 to 1”,from the hierarchical,obey,and standardization concept to the equality,autonomy,and diversification concept,from the verticalsupply chain concept to the cross-linked supply chain concept. The primary role of differentiation strategy cannot be overemphasiezed. Innovation as the fundamental driving force is needed.The tranformation to new organizational model,production model,and business model shall be welcomcd,Supply chain advantages based on integration rather than on linkage shall be achieved.The“Internet+”process shall be accelerated.
the Fourth lndustrial Revolution;Economic Concept;Corporate Strategy
F40
A
1007-905X(2017)08-0080-06
2017-04-22
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二五”规划项目(GD13HYJ01)
李曼,女,广东财经大学信息学院副教授,广东省商业经济学会秘书长,华南商业智库副秘书长,广东财经大学流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编辑 凌 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