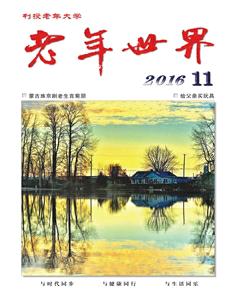我与蒙古袍
阿斯娜
今年春天,因为要完成一篇毕业论文,我读了一些追寻蒙古族历史的书籍,日本作者江上波夫写的《蒙古高原行纪》中的一段文字几乎让我落泪:“我们站在草原上的雨中,又冷又饿。突然有位蒙古人骑马向我们这里飞奔而来,从外表判断她是女的——仅限于她梳了两条辫子,从她的肤色和所穿的蒙古族服装上根本看不出来性别。”
读到此处,我的心,痛如刀割。一直以来,我们心中的蒙古族姑娘都是穿着浅粉的、彤红的、洁白的蒙古袍,像五彩的花一样绽放在辽阔的草原上,书中的描写残酷地揭示了战争期间草原人民悲惨的生活状况。就是这位穿着褴褛的看不出性别的蒙古袍的姑娘,为这群打着考古旗号在草原上迷路的入侵者,端来了热腾腾的奶茶……
历史已经翻过很多年了,书中那位蒙古族姑娘,她孙女的孩子也应该像我这么大了吧?我想象着她的衣橱里,一定会有很多彩虹一样美丽的蒙古袍……
叹息着合上书,我一件一件地轻抚着自己从小到大那些美丽的蒙古袍,也抚过被蒙古袍包裹着的温暖的成长岁月。
从记事起,我看到的蒙古袍就是闪着漂亮光泽、镶着彩色花边的华贵的衣裳。但那些年,很多人只有一件蒙古袍,逢年过节、婚宴庆典时,人们才会小心翼翼地从叠放整齐的布包里拿出来,扎好腰带,戴上礼帽,穿上马靴,男人们喝酒拉琴,女人们跳舞唱歌……那个时候,穿着蒙古袍的每个人都会在歌声中回到辽阔的草原。
鲜花有苞衣,鸟雀有彩翎,连草原上的小羊羔也都披着云朵般的白衣裳。出生3个月的我,就有了第一件蒙古袍。面料光滑柔软,浅浅的杏花一样的粉色衣襟上,缀着几粒小小的紧实的银色盘扣。蒙古袍里包裹着的我,如粉嫩的花朵儿一样绽放在盛夏的季节里。后来才知道,因为这件蒙古袍太小,买不到合适的盘扣,奶奶就自己动手去做。那些精致美丽的盘扣,是奶奶用银色的缎子剪好缝成细细的窄条,再一点点盘成的。小小的盘扣,对年纪已大、眼睛不好的奶奶来说,该是多么巨大的一个工程啊!
那时候会做蒙古袍的裁缝不多,家里人的蒙古袍都是奶奶亲自做的。记忆中,总有一幕温暖着我:奶奶用那双粗糙、灵巧、布满褐色老人斑的手握着细细的银针,在昏暗的灯光下缝缝补补,一台不知年龄的旧缝纫机在寂静的夜里不停地转动,“嗡嗡嗡嗡”,无论秋冬春夏,仿佛一直不停……而那低低柔柔的声音,就是我童年里最悦耳的音响;奶奶耳边的碎发投下柔润的阴影,是我眼里最动人的影像。
我能像小马驹一样撒欢的时候,奶奶给我做了第二件蒙古袍。比量一下,它还没有我现在的腿长,做工却是一丝不苟。玫红色的绸缎上绣着具有蒙古族风情的云纹,领口袖口腰带均用金色的丝线缝缀着波浪形金边;连小小的立领上,也滚动着一圈浅浅的细密的金边。黑色的盘扣别致、讲究,而那顶帽子就像一座小塔——黑绒布的帽檐上,镶着银边,银边上又轻俏地点缀着几粒红色的碎珠子似的玛瑙。已经不记得当时穿着它的感觉了,但那个小小的我,一定也和这件小小的蒙古袍一样,一直包裹在奶奶慈爱的凝望中。
挂蒙古袍的第三个衣架是空的。我的第三件蒙古袍在爸爸的画中。
喜欢画画的爸爸还有很多其他的本事:唱歌、跳舞、拉四胡、写文章……而画画应该是融在爸爸生命里的天赋。只要有一支笔,无论是毛笔、钢笔、圆珠笔或者我写字的铅笔,我们生活中的每一个镜头就会跃然纸上。小时候的我总爱和爸爸一起伏在书桌上,看他画我的每一天。我们一起去公园,一起捉蝴蝶;我乖乖地坐在爸爸自行车后座的小筐里,去幼儿园;爸爸接我回家,我举着雪糕或糖葫芦坐在他的肩头……每一张白纸上,都印记着我的成长。
爸爸的画里也有草原。无垠的天空,辽阔的草原,静立的牛羊……画里也总有一个秀颀的身影,梳着长长的发辫,瘦肩窄腰的蒙古袍随风舞动。我伸出胖胖的小手,问爸爸:她是谁啊?爸爸摸摸我的头发,吻一下我的额头,笑一笑,说:这是我的姑娘——等你长大了,爸爸送给你这样的蒙古袍!我好奇地盯着画中的人,又看看自己穿的小小的蒙古袍,总也想不明白,画中那个仙女一样的身影,怎么会是我呢?
草原上的草绿了又黄,黄了又绿。现在,我终于长成爸爸画里的姑娘,却永远也穿不上爸爸送我的蒙古袍了……爸爸的画忘了涂颜色,我不知道他是想让我穿什么颜色的蒙古袍呢?于是这个衣架就空了下来,一直空着。
小孩子都长得很快,好像就那么一眨眼,我就磕磕绊绊地上了高中。高二那年,学校组织新年演出会,要求同学们穿着民族服装登台表演节目。我们这些正在埋头苦读、备战高考的学生娃,似乎没有谁适时准备着一件合身的蒙古袍,所以一下子都慌了手脚,东凑西借乱成一团。
这个时候,姑姑把一件蒙古袍递给了我。我接过来却愣住了——这可是她结婚时要穿的礼服啊!看到我手足无措,姑姑大大咧咧地說:拿去!别耽误了演出!姑姑的蒙古袍是淡蓝淡蓝的颜色,干净,素雅,大方而又美丽。我穿在身上,想:姑姑心底里的爱情一定就是这样的清澈纯净吧。
衣橱里那些浅紫的、深粉的、大红的、嫩绿的蒙古袍,一件件从短到长,嫣然绚丽……若说记忆是温润的细雨,这些蒙古袍就是细雨中静放的花朵,缤纷着我成长的每一个日子。
摘自《半月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