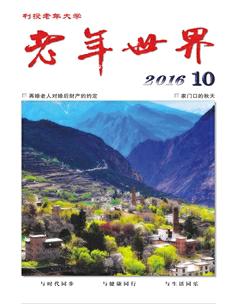算盘人生
钟芳
我家里珍藏着一把红木算盘,十三档,梁上两颗珠、梁下五颗珠,算珠和算框都是枣红色的,四角用铜片箍住。这个算盘是母亲的心爱之物,也是我家的传家之宝。
早年,母亲读过几年小学,写得一手好字,又打得一手好算盘。从我记事起,母亲就一直是生产队会计,家里经常放着一把算盘,一年到头响个不停。我经常看到她在煤油灯下拿着本子,然后在算盘上拨拉得“叭叭”作响。当时是按人头分口粮、按实得工分计收入。比如秋季分稻谷,先算出生产队年产总产量,除去公粮、种子,余者按一个工分能分到多少斤粮食,一家人一年分得多少斤谷子。无论多麻烦的账目,母亲都一笔笔地记账、过账,一把算盘,手指上下舞动,噼里啪啦地响着,数字毫厘不差。所以,她常常自豪地说:“我的算盘,打出的都是明白账。”
每到年底,是母亲最忙碌的时候,不只算本队的账,还不时地有邻近生产队邀请她去帮忙核实账目,更有甚者,亲自拿着账本找上门来的。在寒风呼啸的冬夜,我们全家人蜷缩在被窝里,而母亲在煤油灯下聚精会神打算盘的情景,是我一生中永远抹不掉的记忆。
那时,我还不懂什么账本,也不知道她在做什么工作,只是对算盘很感兴趣。我会把母亲的算盘翻过来,当火车在桌子上滚动。“哗啦啦哗啦啦”珠盘响动的节奏中,我把桌子上的碗筷、糖盒,还有水果之类的东西,装在算盘“火车”上,从桌子的这头开到桌子的那一头。同时,我也学着母亲的模样,用手指打响算盘。母亲见我对算盘爱不释手,于是就教我算算术、打算盘。“一上一,二上二,一下五除四,四去六进一……”边念口诀边敲打,从“三遍九”开始,学会后,又打“九遍九”。
上小学四年级时,学校开始学习珠算。我背着母亲的算盘和小伙伴们上学,大家你追我赶,算盘发出的响声非常悦耳。数学课时,老师用大算盤,我们用小算盘,满教室里全是打算盘的声音。由于母亲教过我简单的加减运算,学起来一点都不费力,每次考试,我总能得满分,那时候在我眼中,不论多么复杂的题目,算盘都能算出来。学习珠算以后,我算盘打得不仅速度快,结果也精准,母亲会让我在放学后帮忙记账。得到了大人的肯定,我学算盘的劲头更足了。
“算盘一响,黄金万两。”每到家里要算账什么的,也都由母亲来完成。在我们儿时的记忆里,那时候的物质生活虽然贫乏,可有着母亲的这把算盘,一家人的生活有条不紊,其乐融融。每天晚上,父亲和母亲总会坐在一起,将那些小圆鼓似的算珠拨来拨去,嘴里念念有词,脸上洋溢着一种幸福的微笑。算珠在母亲轻快的拨动中如跳动的音符,演绎出一曲曲动听的乐曲,弹奏着人生的酸甜苦辣。
——珠算系列介绍 新中国珠算
——珠算系列介绍 清代珠算
——珠算系列介绍珠算与《数术记遗》
——珠算系列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