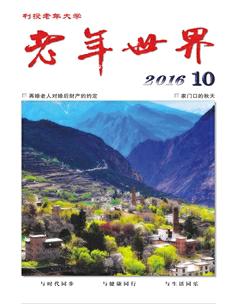我和我的小梳妆台
从我记事起,我的家就没有一件完整的家具,真是“穷家破业一条被,老少倒着睡。”就在这饥寒交迫的日子里,我仅十四岁就在戏班里唱了主演。因为这,父亲为我买了一架日本式的小梳妆台。那一天,父亲兴冲冲地抱来了它,一路上街坊邻居都抢着看啊,问啊……
小梳妆台是父亲对女儿的一片心意,也是我艺术生涯的第一个伙伴。爸爸对我说:“这是鬼市上最讲究的梳妆台了,五块多钱呢,比买张抽屉桌还贵,你唱戏唱成了主演,该用这最时髦的镜台。贵人吃贵物,大院子栽大树。”从那开始,演戏时候我总是随身带着这面镜台,1945年日本投降后,我从青岛坐轮船回家,因为只能坐大通舱人挤人,为了保护这个小梳妆台,我一夜抱着它没敢躺下。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天地变了样,我也结束了流浪卖艺生活,由唐山来到北京,进天桥小戏园子里唱戏。头一天扮戏,就先把小梳妆台摆放在化妆桌上了,它随着我有了房子,结了婚,成了我唯一的陪嫁品。
“十年浩劫”时,我们家经过多次抄家,记得那是1966年8月,红卫兵上街大扫四旧,剪短发、手持皮鞭的造反小将们,横冲直撞地打门进来,我们全家人眼看着一车车的东西被拉走。
我那时天天劳动改造,每天都能看见我家被抄的东西,全堆放在排演场。小白玉霜、魏荣元、喜彩莲等人的东西也都横七竖八地堆放在排演场,好乱哪!9月间,造反派们忽然通知我们去领回抄家物品,红卫兵的头是一位三花脸演员的儿子,他是舞台工作人员,平时我对他很好,他在我们各自领东西时,偷偷对我说:“你今天一定把东西拉走,以后就不许再领了。”我走进那个乱堆里,一眼看见了那个小梳妆台。我把东西认好了,但因为自己是“黑帮”,谁肯帮忙往家运啊!好心的炊事员师傅见我实在为难,便弄来了一个平板车帮助我往回运,他蹬车我跟着推,跑得满头大汗。走了一段路,炊事员师傅因有事不能帮我蹬车了,他说:“凤霞,我只能到此了,你得自力更生呵!”
我骑着平板车走了一点路,就满脸流汗气喘了。两位副食店的中年同志认出我是新凤霞,就偷着端来一碗凉水让我喝,当时我流着眼泪喝下了这碗水。
一路上,我还碰上了好几位这样的好心人。骑到北海的时候,因为上坡,我累得筋疲力尽,头趴在车板上,感觉起不来了。一位工人同志走过来叫醒我,说:“我帮助你推一下。”他主动帮助我推了一段路,我们在树荫下停了车。他仔细一看认出了我:“你是新凤霞同志吧,不用说我明白这是劳动改造。”他说着摇摇头,“哎,这不是糟害人吗?一个演员,唱戏有什么罪!”他看看周围,小声对我说:“新凤霞同志,你忍着点,不能总这样无法无天的。天上有神,地下有人,人是有良心的,沙里能澄金哪,你还得上台,我们要看你的戏。”我听了这番话,又感动又害怕,真是时刻都有好心人啊!
我的家多次被抄,很多家具都丢失了,大屋搬小屋。記得1968年搬进和平里不久,一个街道的所谓积极分子,以势欺人硬要占去我的一间住房,勒令一夜之间搬出。我丈夫在干校不许回来,婆婆89岁了,孩子还小,屋里家具摞家具,连站脚地方都没有,我借了平板车后,连推带骑卖了一些家具,给仨瓜俩枣的钱就卖了,那些红木硬木黄花梨木的好家具都遭了难,离开了我,唯有这件小梳妆台一直守在我的家。粉碎“四人帮”后,我的家具全换新了,唯有我这艺术的伴侣——小梳妆台仍保留着。
摘自《人生如戏——新凤霞回忆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