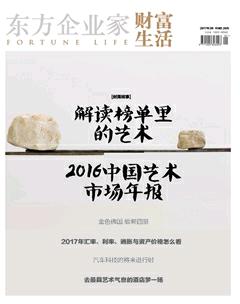年喜的“桂冠”
吴晓波
陈年喜站在大观舞台“年終秀”的后台,与身旁的舞者们格格不入。
他的脖子有点僵硬,就在一年前,他动了一场颈椎手术,三块金属被植入到颈椎的第4、5、6节处。
我第一次见年喜是2015年1月寒冷的皮村,那天,他和其他十八位工人诗人各自朗诵了一首自己的诗。我记得那天的皮村很冷,破败不堪的街道上,孩童们追逐着乱飞的枯叶和烟壳。“工友之家”的玻璃有一半是破裂的,里面积满了新鲜的灰尘。
后来,读到了年喜写皮村的诗。“跑过皮村坑洼街道的孩子/穷人的孩子 他们/肠胃里盛着粗食和白薯/他们多么快乐/快乐得像一块新抹布/擦过秋天的旧桌子/他们还不知道这个世界/有多大 与多少流水正失去速度。”
皮村是北京郊区最大的外来打工者聚集地。就在“年终秀”的前一夜,2016年12月29日,皮村进入综合整治期,“工友之家”的两台取暖锅炉被砸毁,那天,皮村的气温是零下七度。
“他们还不知道这个世界/有多大 与多少流水正失去速度。”
年喜是穷人的孩子,他的孩子也是穷人的孩子。诗人杨炼又把他称为“游民知识分子”,因为他写诗。在过去的十六年里,他是一个命悬一线的矿洞爆破工,同时是中国最优秀的工人诗人之一。
如果不是亲历,你一生也想象不出矿洞的模样,它高不过一米七八,宽不过一米四五,而深度常达千米万米,内部布满了子洞、天井、斜井,像一座巨大的谜宫。在这样的环境下,身高1米85的陈年喜开始了他的打工与诗歌生涯。
年喜的工种是巷道爆破,这可能是世界上最危险的工作之一,与雷管、炸药、死神纠缠在一起。这么些年,经他手使用的炸药雷管大概要用火车皮来计算。他的妻弟也是爆破工,几年前,炸药炸响之前,他跑错了方向,于是粉身碎骨。
年喜家乡那个只有八户人家的村子,就有三人死于矿难。如今的年喜,疾病缠身,风钻已经令他的耳朵几乎失聪,颈椎也错位了。
要评选“桂冠工人诗人”,是我跟秦晓宇商量的结果。一年一度,一度一人,它微不足道得像一声叹息,只是为了拒绝遗忘。只是为了让那些真实的诗歌,像年喜开采的矿石一样,有得见天日的一刻。
给年喜的颁奖词是杨炼写的,“陈年喜很像传统中国的游民知识分子,离开乡村外出打工,辗转于社会底层,饱经世态炎凉。不同于普通游民,他有一种自觉的文学书写意识;不同于传统士大夫或现代知识分子,他是以矿山爆破这样一种后者绝不可能从事的危险工种来谋生,具有顽强的生命活力。作为一名有着十六年从业经验的爆破工,他把在洞穴深处打眼放炮、炸裂岩石的工作场景第一次带入中国诗歌,这既是大工业时代的经验,又是能够唤起人类原始生存场景的经验。”
站在台上,年喜的答词更加的简洁:“现在,我站在这里,既慌恐又高兴。我知道,这个诗歌奖,不仅是颁给我的,也是颁给那些逝者和生者,奖给劳动、创造、和生活的意义。我会继续写下去,努力让自己的写作对得起这个时代,对得起这片土地和土地上的人民。”
他讲这些话的时候,空气凝固成一块粗劣的矿石,大观舞台安静得像五千米深的坑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