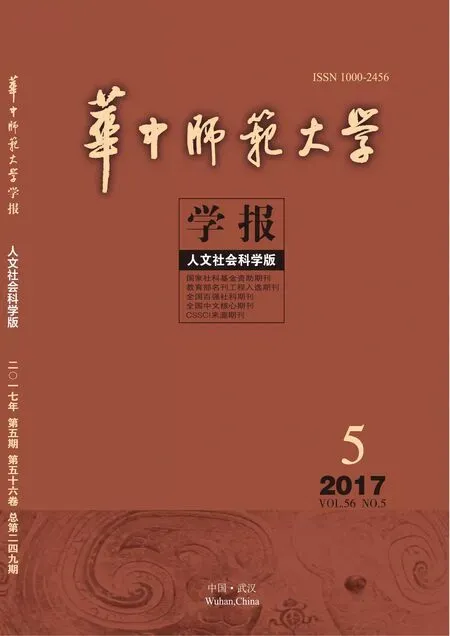先秦的君子威仪与“周文”之关系
付林鹏 张 菡
(1.华中师范大学 文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9; 2.华中师范大学 音乐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9;3.湖北文学理论与批评研究中心, 湖北 武汉 430079)
先秦的君子威仪与“周文”之关系
付林鹏1,3张 菡2
(1.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湖北武汉430079; 2.华中师范大学音乐学院,湖北武汉430079;3.湖北文学理论与批评研究中心,湖北武汉430079)
威仪是先秦贵族所追求的一种理想的人格状态,其着眼点在于区分君臣之名分,内容则不止于仪容举止和精神面貌一面,还包括君子的德政行为。因而在西周至春秋时期,威仪作为一种政治礼仪形式,成为“周文”的外在呈现方式。周人正是通过对君子威仪的观察,来反思“周文”所蕴含的价值系统,以实现其在政治文化中的实际效用。
先秦; 威仪; 君子人格; 周文
威仪是先秦贵族所追求的一种理想的人格状态,由两部分组成,一是威,二是仪。前者是由内而外的精神状态,具有阶层和身份的意义;后者是由外而内的修养手段,具有文化和教养的意义。两者相互作用,才成就了文质彬彬的君子人格。可以说,威仪是“周文”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周代的政治生活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以往之研究,对先秦的威仪观念有所关注①,但对其政治功能及与“周文”之关系,研究得却并不充分。有鉴于此,本文试论之。
一、君子威仪之内涵及养成
在先秦文献中,威仪有两义,一是指人的仪容举止和精神面貌,二是指典礼中的各种动作仪节。至于其间的分别和联系,我们已有专文探讨,兹不重述②。这里着重讨论前者的未尽之处。
关于威仪的具体内涵,春秋时的北宫文子曾做过全面而深刻的论述,据《左传·襄公三十一年》载:
有威而可畏谓之威,有仪而可象谓之仪。君有君之威仪,其臣畏而爱之,则而象之,故能有其国家,令闻长世。臣有臣之威仪,其下畏而爱之,故能守其官职,保族宜家。顺是以下皆如是,是以上下能相固也。《卫诗》曰:“威仪棣棣,不可选也。”言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内外、大小皆有威仪也。《周诗》曰:“朋友攸摄,摄以威仪。”言朋友之道,必相教训以威仪也。《周书》数文王之德曰:“大国畏其力,小国怀其德。”言畏而爱之也。《诗》云:“不识不知,顺帝之则。”言则而象之也。纣囚文王七年,诸侯皆从之囚,纣于是乎惧而归之,可谓爱之。文王伐崇,再驾而降为臣,蛮夷帅服,可谓畏之。文王之功,天下诵而歌舞之,可谓则之。文王之行,至今为法,可谓象之。有威仪也。故君子在位可畏,施舍可爱,进退可度,周旋可则,容止可观,作事可法,德行可象,声气可乐,动作有文,言语有章,以临其下,谓之有威仪也。③
北宫文子之所以有这番言论,是他随卫襄公如楚,观楚令尹公子围之威仪,认为“令尹似君矣,将有他志。虽获其志,不能终也”,即预言其作乱虽能成功,却不得善终——“令尹其将不免”④。基于此,北宫文子向卫襄公阐述了威仪的内涵及重要性,是从三个方面展开的:
首先,威仪是有其阶层性的,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内外、大小皆有威仪”。在北宫文子看来,各阶层能够谨守威仪,是社会结构稳定的基础。所谓“君有君之威仪”、“臣有臣之威仪”是也。其中,国君保持威仪,能够“有其国家,令闻长世”;臣子保持威仪,能够“守其官职,保族宜家”。两者之间不能随意僭越。令尹围本为臣子,却在威仪动作上“似君矣”,故而招致了北宫文子的批评。这说明,北宫文子论威仪之初衷,本就是为了维护阶层的稳固性,目的在于使“上下能相固”也。同样,《左传·隐公五年》载臧僖伯谏隐公“如棠观鱼”,也提到“昭文章、明贵贱、辨等列、顺少长,习威仪也”。“文章”者,据杨伯峻解释是“车服旌旗也”⑤,故“昭文章”即通过车服旌旗文采的不同,昭明身份的差异。其余“明贵贱”、“辨等列”、“顺少长”三者,无不是为了区分等级上下贵贱之不同。而从感情上讲,在下位者面对上位者之威仪,要既畏且爱。畏者,畏其威也。爱者,爱其仪也。故不管是春秋前期的臧僖伯,还是春秋中后期的北宫文子,都将维护阶层的稳定性,作为“习威仪”的首要内容。
其次,威仪是有其理想原型的。在讨论完威仪对社会结构的巩固之后,北宫文子又提到了作为威仪典范的周文王。可以说,威仪观念的提出,是在反思殷鉴的基础上,以周文王的德行举止为理想原型的。《尚书·酒诰》就提到商纣王“诞惟厥纵,淫泆于非彝,用燕丧威仪,民罔不衋伤心”⑥,因耽于逸乐,丧失威仪,最终失去了民心。而文王却恰恰相反,其所作所为无不恪守威仪。北宫文子认为,周文王之威仪体现在四个方面:其一,以德抚诸侯,受到诸侯臣民的拥戴,是为“爱之”;其二,闻崇之乱而以兵伐之,让蛮夷宾服,是为“畏之”;其三,因其功而被天下歌颂,是为“则之”;其四,其行为举止被后世所效法,是为“象之”。这说明除了被“畏而爱之”两种感情外,能否被“则而象之”,也是天子威仪的重要内容。因此,后代周王一直把模仿文王的德行,作为威仪培养的目标⑦。如《诗经·大雅·文王》载:“仪刑文王,万邦作孚。”⑧《周颂·我将》也载:“仪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⑨同样,士大夫也通过模仿祖先的样子,来培养自己的威仪。西周中晚期的叔向父禹簋铭文就载:“余小子嗣朕皇考,肇帅型先文祖,恭明德,秉威仪,用申恪,奠保我邦我家。”⑩故威仪的理想形态,就是能够继承先王、先祖的德行,治理好邦家。
最后,威仪是君子人格的总体呈现。用王齐洲的话来说,就是“个人按照社会结构和秩序的要求而做出的行为及其所获得的社会认可”。王齐洲所言之“个人”,主要指的是士以上之贵族,也即北宫文子所言之“君臣”。至于君臣威仪的具体呈现,可用“八可”来概括,共分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在位可畏,施舍可爱”,两者皆与身份相关。“在位可畏”者,是下之仰上,言君子在位,望之俨然;“施舍可爱”者,是上之惠下,言君子抚民,有如慈母。盖“施舍”一词,在先秦语境下有两种含义,一是免除徭役,《周礼·天官·小宰》载:“治其施舍,听其治讼。”郑玄注:“施舍,不给役者。”二是布德惠,如《左传·宣公十二年》:“老有加惠,旅有施舍。”《襄公九年》:“魏绛请施舍,输积聚以贷。”皆统治者之施政行为。第二个层次是“进退可度,周旋可则,容止可观”,三者皆与礼容有关。《礼记·乐记》:“升降上下,周还裼袭,礼之文也。”“进退”,即行礼时的升降上下;“周旋”又作“周还”,谓行礼时之周曲回旋;容止,谓行礼时之仪容举止。第三个层次是“作事可法,德行可象,声气可乐”,三者皆与行事相关。《左氏会笺》释曰:“作事者,君子所作之事功,即政事也。德行就其身言之。有行事必有言,故以声气辖之。”此与孔门四科颇为相似,除文学外,其余德行、政事、言语,莫不是君子威仪的重要内涵。“八可”之后,还有“二有”,即“动作有文,言语有章”,用以呼应前文并作为小结。“动作”呼应“进退”、“周旋”,两者有文,故容止可观;“言语”呼应“声气”,“言语”文雅而有次序,故声气可乐。
故北宫文子之语,看似无章,实则有其内在的逻辑性,是先秦时人对威仪所下的最权威,也是最全面的定义。其威仪观,着眼点在于君臣之名分,内容则不止于仪容举止和精神面貌一面,还包括君子的德政行为。不过,周人在培养国子之威仪时,更偏重于仪容举止和精神面貌的一面,这就将北宫文子所说的君臣威仪,变成了我们所说的君子威仪。
那么,先秦的君子威仪,是如何养成的呢?这可以从贵族君子的先天地位和后天修养两方面来讨论:
第一,先天之地位,这对于“威”的形成有着重要作用。我们知道,周公制礼的一大目的,就在于区分上下等级。周代官制中的“内爵称”,将贵族分为公、卿、大夫、士四等。而身份的不同,预示了各自威仪的差异。《礼记》中就记载了处于各身份层次的贵族,所具有的不同威仪。如行走时的仪态,是君子威仪的重要表现。《曲礼下》载:“天子穆穆,诸侯皇皇,大夫济济,士跄跄。”郑玄注云:“凡行容,尊者体盘,卑者体蹙。”是说身份越高,行走时越舒展;身份越低,行走时越局促。之所以如此,是与威仪的多少有关:“天子尊贵,故穆穆,威仪多也。诸侯皇皇,庄盛不及穆穆也。大夫济济,徐行有节,不得庄盛也。士跄跄,容貌舒扬,不得济济也。”又如外在的修饰,也是君子威仪的重要内容。《礼器》载:“礼有以文为贵者:天子龙衮,诸侯黼,大夫黻,士玄衣纁裳。天子之冕,朱绿藻,十有二旒,诸侯九,上大夫七,下大夫五,士三。此以文为贵也。”也是身份越尊贵,装饰越繁盛。总之,按照周礼的规定,威仪往往与跟个人身份有关,地位越高者,威仪越盛,而且只能是“下不得兼上,上得兼下”。
第二,后天之修养。仅有地位,并非就有威仪,春秋时就有很多反面例证,如上文的令尹围,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其威仪却不被北宫文子所认可。因此,威仪之养成,还需要后天的修养。后天之养成,也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帅型祖考”。帅者,循也;型者,本义为模,引申为法,即后代子孙要遵循效法先祖之威仪。这在先秦的铜器铭文中颇有记述,如上引叔向父禹簋铭文“肇帅型先文祖,恭明德,秉威仪”之语。又如西周晚期梁其钟铭云:“梁其曰:‘丕显皇祖考,穆穆翼翼,克哲厥德,农臣先王,得纯亡愍,梁其肇帅型皇祖考,秉明德,虔夙夕,辟天子。’”其中,“穆穆翼翼”者,庄重谨慎貌也,是梁其褒美皇祖考品格气质之语。罗新慧就通过对周代铜器铭文的考察发现,周人在描述其祖先形象时,十分专注于仪容的描摹,这与周人十分重视威仪有关。故周代之铜器铭文,通过对祖先威仪的追摹,为自己树立了一个可兹效法的典型,这对于培养自己的威仪,起到了榜样的作用。
二是“得之师保”,即由师保类职官所直接教授的容礼。《国语·楚语上》载申叔时论述教育太子的道理,提到“诵诗以辅相之,威仪以先后之,体貌以左右之”,说明威仪是培养贵族君子的重要手段。而君子威仪的培养,是从容礼的教授开始的,由师保类职官负责。《周礼·地官司徒》载保氏有“教六仪”之职:“一曰祭祀之容,二曰宾客之容,三曰朝廷之容,四曰丧纪之容,五曰军旅之容,六曰车马之容。”《大戴礼记·保傅》也载,天子“不闲于威仪之数”,是“太师之任”,而“处位不端,受业不敬,言语不序,声音不中律,进退节度无礼,升降揖让无容,周旋俯仰视瞻无仪,安顾咳唾趋行不得,色不比顺,隐琴瑟,凡此其属,太保之任也”。可见,师保在培养国子时,主要从“仪”的角度展开:“威”之形成,必须经过“仪”的规范;“仪”之动作,也需以“威”为前提。故容礼之教,有明确的培养目标。《礼记·玉藻》就有“九容”之说:“君子之容舒迟,见所尊者齐遫,足容重,手容恭,目容端,口容止,声容静,头容直,气容肃,立容德,色容庄,坐如尸。”朱熹就认为“九容”与《论语》的“九思”,是“一同本原之地,固欲存养。于容貌之间,又欲随事省察”。即通过群体和人际之间的互动,由外而内,达到涵养个体的作用。
二、“观威仪”与“周文”之政治呈现
周人尚“文”,是古往今来历代学者的共识。相关论述如《论语·八佾》:“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礼记·表记》:“殷周之文,至矣。”《史记·梁孝王世家》:“周道文。”现代学者也做出了有益的探讨。据李春青的研究,在先秦的文化语境中,“文”大致有两方面的基本含义,一是形式方面,凡属人为创造及自然之物而有光彩者,皆可归为“文”之范畴;二是道德规范和人格理想方面。换句话说,“周文”至少也应包括形式系统和价值观念两个方面。其中,形式系统主要指西周贵族创造的典章制度、礼仪规范以及与之配套的文化符号体系等,价值观念则是“周文”背后所体现出来的伦理道德观念。故从这一意义上来讲,威仪属于“周文”的形式系统,是“周文”的呈现方式。
可以说,君子威仪与“周文”之关系,主要体现在容貌、登降、兴俯、献酬、裼袭等具体仪节上,所谓“动作有文”是也。贾谊《新书·容经》就将北宫文子之言改为“有威而可畏谓之威,有仪而可象谓之文”,司马光《答司户孔文仲书》也说:“古之所谓文者,乃诗书礼乐之文,升降进退之容,弦歌雅颂之声,非今之所谓文也。”说明古人将“仪”之本身就视为“文”。在先秦文献中,威仪除指人的仪容举止外,还可专门指各类典礼中的动作仪节。如《礼记·中庸》有“礼仪三百,威仪三千”的说法,孔颖达疏曰:“‘威仪三千’者,即《仪礼》行事之威仪。《仪礼》虽十七篇,其中事有三千。”这里的威仪,更多表现为外在的礼仪规范,是“周文”的重要组成部分。
周代的“尚文”传统,从一开始就蕴含着深厚的政治教化特质,牟宗三就说:“周之文只是周公之政治运用以及政治形式(礼)之涌现。”故作为“周文”中的呈现方式,威仪在西周乃至于春秋的政治生活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有学者就认为:“威仪的核心是强调政治中的美学形式。”换句话说,威仪是一种政治礼仪行为。无怪乎周成王在临终前,就反复告诫太子钊要“自乱于威仪”,将之作为重要的统治手段。在《诗经·大雅》中,就屡见成王重视威仪的描述,如《假乐》有“威仪抑抑”之语,据郑笺:“抑抑,密也。……成王立朝之威仪致密无所失。”《既醉》有“威仪孔时”之语,据郑笺:“孔,甚也,言成王之臣威仪甚得其宜。”所谓“致密无所失”、“甚得其宜”,其着眼点都是威仪的阶层性,是说成王君臣立朝之威仪符合规范,各得其宜。这也符合章太炎对“文”所下的定义:“盖君臣朝廷尊卑贵贱之序,车舆衣服宫室饮食嫁娶丧祭之分,谓之文。”可以说,正是成王对威仪的重视,才成就了周初的“成康之治”。
至此之后,“敬慎威仪”和“敬尔威仪”等,也成为“周文”体系中的核心话语。如《仪礼·士冠礼》载先秦士人行冠礼时的祝辞有“敬尔威仪,淑慎尔德”语,是作为长辈的宾对贵族子弟的祝愿和要求;又如春秋晚期王孙遗者钟铭提到:“余……惠于政德,淑于威仪。”是贵族王孙的自我评价;《诗经·大雅·既醉》还提到即便在宴饮时刻,仍然要“朋友攸摄,摄以威仪”,是朋友间的相互劝勉。及至春秋晚期,能不能“慎吾威仪”,仍然是外交斡旋,保持国家尊严的重要手段。《左传·昭公五年》载:
晋韩宣子如楚送女,叔向为介。郑子皮、子大叔劳诸索氏。大叔谓叔向曰:“楚王汏侈已甚,子其戒之!”叔向曰:“汏侈已甚,身之灾也,焉能及人?若奉吾币帛,慎吾威仪;守之以信,行之以礼;敬始而思终,终无不复。从而不失仪,敬而不失威;道之以训辞,奉之以旧法,考之以先王,度之以二国,虽汏侈,若我何?”
此“楚王”即楚灵王,以骄奢无礼著称。因此,子大叔才提醒出使楚国叔向多加小心。叔向认为,骄奢无礼只能导致自身的灾祸,不能危及他人,而且只要自己能保持威仪,“从而不失仪,敬而不失威”,就不会存在祸患。其后果然,“王欲敖叔向以其所不知,而不能,亦厚其礼”。此即先秦君子恪守威仪,战胜于朝廷的典型例证。这说明,威仪不但是贵族君子所自觉遵守的公共价值标准,也是贵族君子修养自身人格的主要手段。
故在“周文”的价值系统中,威仪又成为贵族君子间相互评鉴的重要标准。《诗经》里就很多以威仪对贵族君子进行评价的诗篇。其中,敬慎威仪者,美之;违反威仪者,刺之。前者如赞扬仲山甫,称其“古训是式,威仪是力”(《大雅·烝民》);夸耀鲁僖公,则称其“敬慎威仪,维民之则”(《鲁颂·泮水》)。后者如批评周厉王,就说他“威仪卒迷,善人载尸”(《大雅·板》);控诉周幽王,则说他“不吊不祥,威仪不类”(《大雅·瞻卬》)。更甚者,能不能恪守威仪,还成为当时攻击政敌的重要理由。如鲁昭公二十六年(前516年),周王室的王子朝作乱失败,逃亡楚国。在逃亡之后,他仍然攻击自己的政敌“傲很威仪,矫诬先王”,这也从侧面反映了威仪在时人心目中的重要地位。
另外,在“周文”的制度设计中,还有“观威仪”以“省祸福”的说法,可谓是最早的观人之法。此说见《左传·成公十四年》:“卫侯飨苦成叔,宁惠子相。苦成叔傲。宁子曰:‘苦成叔家其亡乎!古之为享食也,以观威仪省祸福也。……今夫子傲,取祸之道也。’”宁惠子提出,古代享、食之礼的设立,就是为了观察参与者的威仪,并以之预判参与者将来的祸福结局。其实,不独享、食之礼,祭祀、朝聘等礼仪,也是如此。《诗经·小雅·采菽》载诸侯朝见天子之礼:“君子来朝,言观其旂。其旂淠淠,鸾声嘒嘒。载骖载驷,君子所届。”据郑玄笺,诸侯来朝,周王要派人迎接,在迎接时,还要“观其衣服车乘之威仪,所以为敬,且省祸福也”。“观威仪”之目的,就是为了观察诸侯贵族之“敬”与“不敬”。盖“敬”是周礼得以实行的精神保障,《左传·僖公十一年》载内史过曰:“礼,国之干也;敬,礼之舆也。不敬,则礼不行。”即“礼”是立国的骨干,而“敬”则是行礼的乘舆。人如果无“敬”,“礼”只能流于形式,无法实行。在《左传》和《国语》中,就有大量因“不敬”而导致覆灭的例证。而“敬”之与否,又可以从威仪上体现出来,如上文的楚令尹围,就因威仪“似君矣”,而招致北宫文子的批评。
除此外,还有类似例子:如《国语·周语上》载,周襄王派邵公过及内史过赐晋惠公命,在行礼时,“吕甥、郤芮相晋侯不敬,晋侯执玉卑,拜不稽首”。按照周礼的规定,执天子所赐之器应平正适中,并行最重的稽首礼。然而晋惠公在行礼时却有所怠慢,故内史过回王室复命时,对襄王预言说:“晋不亡,其君必无后。且吕、郤将不免。”其原因是:
夫执玉卑,替其贽也;拜不稽首,诬其王也。替贽无镇,诬王无民。夫天事恒象,任重享大者必速及,故晋侯诬王,人亦将诬之;欲替其镇,人亦将替之。大臣享其禄,弗谏而阿之,亦必及焉。
故晋惠公之过,一在于废礼,即“替其贽”;二在于不敬,即“诬其王”。废礼则无以自重,不敬则人亦诬之。最终内史过的预言成真,惠公的儿子被晋人所杀,而吕甥、郤芮则被秦人所杀。其结局,固然非仅惠公君臣不敬周王所致。但不重威仪,却从细节方面反映了晋惠公对待国政的态度,招此结果,也非无因。
又如《国语·周语下》载晋厉公合诸侯于柯陵,在会上,单襄公“见晋厉公视远步高。晋郤锜见,其语犯。郤犨见,其语迂。郤至见,其语伐。齐国佐见,其语尽”,做出预言,认为“晋将有乱,其君与三郤其当之乎”,其原因:
吾见晋君之容,而听三郤之语矣,殆必祸者也。夫君子目以定体,足以从之,是以观其容而知其心矣。目以处义,足以步目,今晋侯视远而足高,目不在体,而足不步目,其心必异矣。目体不相从,何以能久?夫合诸侯,民之大事也,于是乎观存亡。故国将无咎,其君在会,步言视听,必皆无谪,则可以知德矣。视远,日绝其义;足高,日弃其德;言爽,日反其信;听淫,日离其名。夫目以处义,足以践德,口以庇信,耳以听名者也,故不可不慎也。偏丧有咎,既丧则国从之。晋侯爽二,吾是以云。……今郤伯之语犯,叔迂,季伐,犯则陵人,迂则诬人,伐则掩人。有是宠也,而益之以三怨,其谁能忍之!虽齐国子亦将与焉。立于淫乱之国,而好尽言,以招人过,怨之本也。
据单襄公的说法,霸主合诸侯,步、言、视、听四者皆应无可指摘,而观厉公之容,“视远步高”,违背其二,是行为的不得体;而作为大臣,三郤和国佐是言语的不得体。前者是容止不可观,后者是言语无章,都是君子威仪的重要组成部分。后来果不其然,三郤和国佐被杀,厉公被弑。
再如据《左传》载,定公十五年(前495)春,邾隐公朝见鲁君,子贡前往观礼,“邾子执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对此,子贡评价曰:
“以礼观之,二君者,皆有死亡焉。夫礼,死生存亡之体也,将左右、周旋,进退、俯仰,于是乎取之;朝、祀、丧、戎,于是乎观之。今正月相朝,而皆不度,心已亡矣。嘉事不体,何以能久?高、仰,骄也。卑、俯,替也。骄近乱,替近疾,君为主,其先亡乎。”
鲁为大国,邾为小国,结果在行礼时,邾隐公其容仰,有骄态;鲁定公其容俯,有忧色,均为失仪之举。故子贡预言,两君皆有死亡之相,但因为鲁定公是主人,所以会先去世。其后,子贡预言,也都成真。
以上例证,均发生在“周文疲敝”时代,晋惠公、晋厉公、邾隐公三人之威仪,都违背了“周文”系统中的“朝廷尊卑贵贱之序”,故而为贤人君子所指责。而三公之结局,也被贤人君子所预言,其后也无不应验。
不过,这些预言,颇近于鬼神之说,或有道德决定论的因素在内,可能经过史官的事后加工。但不可否认,这些说法也并非毫无道理。对此,前人也有过研究,如明人戴仔《〈非国语〉辩》说:“夫古之为享祀朝聘以观威仪,省祸福也。故古之观人也,受玉而惰,受赈而不敬,或视远而步高,或视下而言徐,与夫言之偷惰、手之高下、容之俯仰,皆有以见其祸福。何者,其民气素治,故其乱者可得而察也。”认为当时民气素朴,故一有无礼作乱者,都无所遁形。清人阎若璩引游氏曰:
古之观人者,于一指顾,一瞻视,一謦欬之间,其人之贤不肖、是非、祸福皆可得而分。盖古人以礼为常,一失其节,则为改常,则人之祸福,宜可得而知也。……圣人为礼,以制天下之心;威仪之中否,以验其神明精爽之存亡。讵可指登降、兴俯、献酬、裼袭以为末节,而不之察乎?先王盛时礼教达于天下,士无贤不肖,皆周旋于礼文之中,其节奏、度数、耳目习焉,手足安焉,不得而少差也。于安且习之中,而忽乖其度,是必其神明精爽之不在是也。三代之衰,列国公侯卿大夫犹知奉礼以从事,一不中节,则有死生祸福之说。……盖先王所以制人心之意,犹未冺灭,而秉礼君子既能以自检其身,故能以身察乎人也。
“礼文”作为一种传统的文化秩序,完全地落实到西周的社会生活之中。即便到了春秋时期,仍然得到普遍的认同。贵族君子时时所习,早已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故稍有差池,就被秉礼君子所察,并能准确预判其吉凶祸福。惟其如此,威仪才成为“周文”的呈现方式。贤人君子,由“观威仪”以验“周文”,将“周文”之价值范畴作为衡量贵族君子的重要标准。
三、君子威仪与“周文”之内在关联
归结到具体人格方面,周人所尚之“文”,是以德行及知识修养为内涵,外现文雅、雍容、裕如的气度与风范。对此,《荀子·不苟》言:“君子宽而不僈,廉而不刿,辩而不争,察而不激,直立而不胜,坚强而不暴,柔从而不流,恭敬谨慎而容。夫是之谓至文。”荀子眼中的君子人格,就是“至文”的具体表现,这一人格既包括“宽而不僈”等价值观念或道德规范,又包括威仪这一外在表现形式,据郑玄注:“容,威仪也。”
不过,作为一种总体性君子人格,威仪并不局限于外在的行,更注重背后的德。《礼记·表记》说圣人“制行”,要“容貌以文之,衣服以移之……君子服其服,则文以君子之容;有其容,则文以君子之辞;遂其辞,则实以君子之德。是故君子耻服其服而无其容,耻有其容而无其辞,耻有其辞而无其德,耻有其德而无其行”。作为君子威仪,服、容、言、行四者缺一不可,而四者又必须以德为依托。因为光有其服、容、言、行而无德,往往流于形式。而修于外者,又可及于内,通过外在的文饰,又能涵养内在的德性。只有内外合一,才是“周文”的最高体现。
据现存文献,在威仪方面,能将内外合一贯彻最好的,莫过于周文王,因为“文王质文,故天胙之以天下”。而另一典型例子,则是春秋时晋孙谈之子周(即晋悼公),《国语·周语下》曾载其“适周,事单襄公,立无跛,视无还,听无耸,言无远。言敬必及天,言忠必及意,言信必及身,言仁必及人,言义必及利,言智必及事,言勇必及制,言教必及辩,言孝必及神,言惠必及和,言让必及敌。晋国有忧未尝不戚,有庆未尝不怡”。相较于晋厉公的“视远步高”,晋悼公的言行举止无不恪守威仪。故单襄公评价他“其行也文”,并预言其“将得晋国”,所以在病重时嘱托儿子单顷公要善待他。单襄公对晋悼公之评价,是观其威仪而来,包括四“无”之行和十一“言”之德,由其外而知其内,认为其所言所行莫不契合“文”之特征:
夫敬,文之恭也;忠,文之实也;信,文之孚也;仁,文之爱也;义,文之制也;智,文之舆也;勇,文之帅也;教,文之施也;孝,文之本也;惠,文之慈也;让,文之材也。……此十一者,夫子皆有焉。……且夫立无跛,正也;视无还,端也;听无耸,成也;言无远,慎也。夫正,德之道也;端,德之信也;成,德之终也;慎,德之守也。
十一“言”之德,包括敬、忠、信、仁、义、智、勇、教、孝、惠、让等德目,体现了“文”的各个方面,故韦昭注曰:“文者,德之总名也。”四“无”之行,反映出的德行则是正、端、成、慎四方面。前者是所言为“德”,内涵为“文”,是“与他人和社会直接关联的德行”;后者是所行为“文”,内涵为“德”,是“贵族的‘礼’文化中所要求的个人人格的一部分”。换句话说,“周文”是德、行的统一体。
那么,“周文”是如何通过威仪这一中枢,达到内外合一的?《礼记·乐记》中的一段记载,为我们提供了答案:
致礼以治躬则庄敬,庄敬则严威。心中斯须不和不乐,而鄙诈之心入之矣。外貌斯须不庄不敬,而易慢之心入之矣。故乐也者,动于内者也;礼也者,动于外者也。乐极和,礼极顺,内和而外顺,则民瞻其颜色而弗与争也;望其容貌,而民不生易慢焉。故德煇动于内,而民莫不承听;理发诸外,而民莫不承顺。
这虽然是说礼、乐之别,但却明确提出,以礼治身,固然可以使人庄敬威严,但内心若不和乐,也达不到相应效果。只有做到“内和而外顺”,才能威仪棣棣,成为民之表率。也难怪,在培养君子威仪时,要做到礼、乐兼顾,以礼治其外,以乐和其内。所以,乐仪才成为培养君子威仪的重要手段。
可以说,在西周至春秋前期,威仪作为一个综合性概念,往往言其外就知其内,看到外在的文饰,就能了解其背后的象征意义,正如单襄公所言“观其容而知其心矣”,“步言视听,必皆无谪,则可以知德矣”是也。然而到了春秋中后期,人们对“威仪”的认识发生了偏移,这一方面与时人屡屡违背礼仪,导致“威仪不类”有关,上节所列诸例,皆是如此;另一方面也与时人只重形式,不重内在的德性有关。如据《左传》载,昭公五年(前537)鲁公如晋,“自郊劳至于赠贿,无失礼”,晋平公夸其善于礼,女叔齐却说:“是仪也,不可谓礼。”同样,昭公二十五年(前517),子太叔见赵简子,赵简子问“揖让周旋之礼焉”,子太叔明确告诉赵简子,其所问“是仪也,非礼也”。两例虽是言礼、仪之别,却也说明时人对威仪概念的理解,也是只重外在的形式而忽略其内涵。换句话说,时人是将“周文”的形式系统和价值观念分成两橛来加以讨论的。
到了孔子的时代,也呈现出这一趋势。如《论语》就屡次通过“文”与“质”这对范畴,来品评君子的人格特征。如《颜渊》载:
棘子成曰:“君子质而已矣,何以文为?”子贡曰:“惜乎!夫子之说,君子也。驷不及舌。文犹质也,质犹文也。虎豹之鞟犹犬羊之鞟。”
据赵辉的研究,“质”是指人内在的伦理道德,而“文”是指人外在的行为表现。换句话说,在原来的“周文”体系中,“质”属于其中的价值观念,而“文”属于其中的形式系统。这一说法是正确的,因为《论语·卫灵公》载孔子曰:“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其中,“义”说的就是内在的价值观念;“礼”则是与“质”相对应的“文”。尽管子贡强调理想的君子人格是“文犹质也,质犹文也”,孔子也强调“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试图恢复作为总体性人格的威仪观念。但不可否认的是,他们也意识到其中“文”与“质”的分别。
综而言之,“周文”虽然体现为西周贵族所创造的礼乐制度及其相配的文化符号等,但其本身又蕴含着相关的德性观念,是形式系统和价值观念的统一体。所谓的威仪,就是“周文”的形式系统,也就是说“周文”必须借助于威仪这一外在形式,才能得以呈现。周人正是通过对君子威仪的观察,来反思“周文”所蕴含的价值系统,以实现其在政治文化中的实际效用。
注释
①代表性成果有王齐洲:《“威仪”与“气志”:孔子〈诗〉教的人格取向》,《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1期;李雷东:《历史语境下的西周“威仪”观》,《甘肃社会科学》2013年第6期;付林鹏《乐仪之教与周代的君子威仪》,《中国文化研究》2014年秋之卷,等等。
⑥孔安国传、孔颖达疏:《尚书正义》,十三经注疏本,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07页。
⑦学者也意识到文王的政治行为是春秋贵族认识威仪的重要维度,而《诗经》又是考察文王的历史政治行为的重要文献依据。参见李雷东:《历史语境下的西周“威仪”观》,《甘肃社会科学》2013年第6期。
责任编辑王雪松
On the Nobleman’s Dignity in Pre-Qin Period and Its Linkage with “Zhou Wen”
Fu Linpeng1Zhang Han2
(1.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Literary Theory and Criticism Research Center of Hubei Province,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430079;2.School of Music,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430079)
Dignity was the pursuit of an ideal personality state of the aristocrats in pre-Qin period. It focused on distinguishing the status of the monarch and his subjects, which contained not only a nobleman’s appearance, manners and mental outlook, but also a nobleman’s benevolent conduct. Thus “dignity” as a political etiquette behavior became the external presentation of “Zhou Wen” from the Western Zhou Dynasty to 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Through observing dignity people in the Zhou Dynasty reflected the value system in Zhou Wen, to get access to the actual application in the politics and culture.
pre-Qin period; dignity; nobleman’s personality; Zhou Wen
2017-07-10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两周乐政与乐官的文学活动研究”(15CZW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