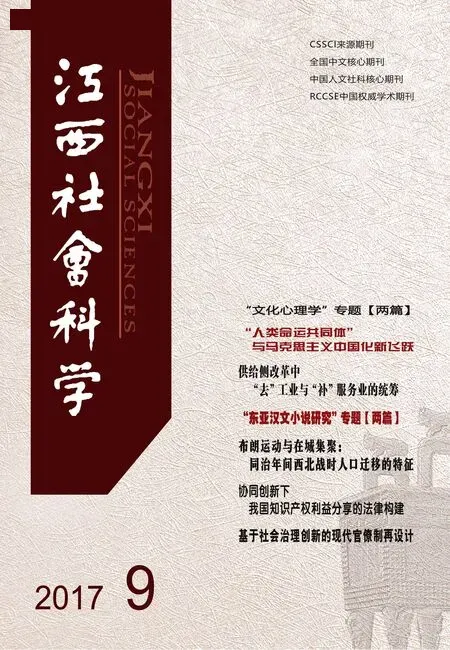明清闽浙赣毗邻地区的山区开发与流民控制
■廖 涵
明清闽浙赣毗邻地区的山区开发与流民控制
■廖 涵
明清时期,流民是山区开发伴生的社会问题之一。在闽浙赣毗邻山区,为防范流民滋事,明清两代长期奉行封禁政策。然而,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山区开发的形式不同,流民各具特点,封禁实践亦相距甚远。明前期,从事坑冶的矿徒极具流动性和危险性,封禁执行严格。明中后期,从事造纸的槽工流动性相对较弱,官府允许其在封禁外缘地区进行毛竹种植和纸张生产等活动,封禁政策出现了松动。清雍正以后,从事土地开垦和农业种植的棚民,与山外的农民无实质差异,官府默认其开垦禁山,封禁饬令如一纸具文。这表明,明清两代应对流民问题的侧重点并不相同,明代为防范叛乱而严禁人口流动;清朝害怕“天下有事”,但施政时颇注意贫民生计,以致封禁徒有虚名。
山区开发;流民控制;封禁政策;明清
明清时期,南方山区的资源开发引起了全国经济结构的深刻变化,甚至出现了新的生产方式,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的起点。[1](P156-159)与此同时,聚集于山区的流民一度成为地方社会秩序,乃至王朝统治的威胁,秦岭—大巴山区[2](P85-145)、南岭山区[3](P171-239)等地无不如此。为巩固统治秩序,明清朝廷往往因地宜制,推行不同的治理政策,或镇压,或驱遣,或附籍,或新置州县,力图将流民置于国家权力的控制之下。事实上,山区资源开发的具体形式因时而异,山区流民各具特点,同一项政策在不同时期的历史实践亦相去甚远。
闽浙赣三省毗邻地区纳入国家行政体系的时间较早,州县设置在北宋已趋成熟。明清时期,凭借优越的地理位置和发达的河流网络,这一地区交通便捷,经济繁荣,人才辈出,蔚为东南要地。但是,临界三省的武夷山区,“重山复岭,迭嶂层岩”,交通闭塞,“有岩峒溪壑之阻”,又有“擅铅矿材木之饶”,又因三省官府“本自秦越,不相为谋”,以致境内流民杂处,为“盗所垂涎”[4](卷二百四十六《为请专勅严经略疏》,P2578),俨然是帝国统治的“隙地”[5]。明正统间(1436—1449),浙江处州府矿徒叶宗留等率众入山,在江西永丰(清雍正间更名广丰)、上饶等处盗采银矿,后抢掠毗邻州县,为害一方。平乱后,明廷将临界的方圆数百里山区严加封禁,限制流民入山,这一政策沿袭至晚清同治间,跨时400余年,是中国历史上封禁时间最长的地区。本文拟在前人的基础上①,通过梳理方志、文集、档案等历史文献,围绕闽浙赣毗邻地区的封禁政策,考察明清两代应对山区开发与流民问题的基本策略。
一、明前期的矿徒与封禁政策
明代前期,商品经济尚不发达,出入闽浙赣毗邻山区的流民主要是来自浙江处州府的矿徒,他们试图进山开采金银矿产,是为山区资源开发的早期形式。
三省毗邻地区的矿产资源开发很早。在两宋时期,浙江处州、福建建州和江南东道信州三处均设有大规模矿场,是当时全国铜铁产量最多的地区之一。[6]入明后,建州、信州各处矿场早已废弃,唯处州府有矿场还在营运。在当时技术条件下,易开采的矿产也日益减少,处州贫民无以为生,转而“相习盗矿以自糊其口”。明廷严禁民间开矿,四处缉捕盗采矿产之人,并称之为“矿徒”[7](P351)。
相传,江西广信府下辖之永丰、上饶二县临界的南部山区藏有大量金银矿产。自永乐间(1403—1424)起,处州矿徒便入山盗矿,直至“矿乏山崩,没死者甚众”[8](卷三《封禁考略》)。宣徳七年(1432),浙江豪民项三等聚众于永丰县四十二都的包公尖、上饶县五十都的横山头、五十三都的洪水坑等处,“起立垆场一十三座”,盗采银矿,后流窜江西、福建各处,打家劫舍。经福建行都司派兵镇压,项三等人伏法,官府曾将盗矿之处略加封禁,后世称之为“封禁内山之门户”[8](卷三《封禁考略》)。
遗憾的是,三省地方并未对入山盗矿的行为予以重视。正统七年(1442),处州矿徒王能、郑祥、叶宗留等人再次“聚众千余,入山盗矿”,在永丰境内肆意采挖。由于山内矿产储量有限,矿徒“所获甚微”,入不敷出。于是,叶宗留向众人提出,“与我取于山,既无所得,孰若与尔取于人,一撑而有余矣”。随之,众矿徒拥立王能、叶宗留为首领,劫掠永丰、上饶等地,成为“矿盗”。官府闻讯,调集南昌前卫、广信所、铅山所的兵士前往弹压。结果,官军大败,“被杀者甚众”。正统十年,因官军无力镇压矿盗,江西府县官员改行招抚之策。永丰知县邓颙偕同当地老人余斌等人,深入永丰县南之铜塘山深处,招抚王能等35人,将县内二十四都的瘠荒田地予之耕种。随后,邓颙又以招抚之名,诱骗郑祥、四苍、大头等300余人下山,“悉斩于永丰之十五都”,仅叶宗留等数人不愿投降,逃往福建。[9](卷九十九,正统七年十二月辛亥条,P2004)
叶宗留等人潜回处州后,经一年多休整,又于正统十二年聚集大量匪众,攻掠处州政和诸县,矿盗之势日炽。次年,叶宗留率众进入闽北,破浦城、陷崇安,“所过焚掠”,掐断了沟通闽赣的分水关一线。适时,佃农邓茂七在福建沙县倡乱,与叶宗留“互为声援,此入彼岀,官兵首尾不能相应”。是年冬,都御史张楷受命率部前往闽中镇压邓茂七叛乱。行至广信府,道路为矿盗所阻,官军无法入闽,故暂驻上饶、铅山等处。浙江官员见状,遂恳请张氏先灭近在咫尺的矿盗,再图佃变,张楷应请。于是,遣部将陈荣、戴礼等率兵至铅山县南弹压矿盗,对阵于石塘镇附近。战乱中,矿盗首领叶宗留中箭身亡。随即,叶希八被拥立为新首领,率众乘夜偷袭官军,大胜而归。迫于官军的压力,叶希八等返回处州府,并以龙泉县云和山为据点,占山为寇,“兼水杨希、鲍村陶得二各率众数千人归之”,肆意抢掠,气焰更甚。乘此空隙,张楷取道闽中,镇压了邓茂七叛乱。正统十四年夏,张楷率兵驻于福州,浙江官员再遣使请之对付矿盗。张氏率军行至处州,设计击溃了前来索战的矿徒,而扭转战局。于是,张楷派阵中处州籍士兵前往云和山传话,“反复譬晓”官军的招抚之意,并成功说服矿盗首领陶得二。如此再三,叶仁八、杨希、陶秉伦等人相继投降,张楷“给帖合复业”,叛乱才得平定。[10](卷十《平处州寇》,P125-126)
在处理善后事宜时,户部尚书金濂(1392—1454)和三省守臣一致认为,要让三省边界山区安靖,非“悉加封禁”不可。为此,明廷下令严加封禁以铜塘山为中心的数百里山区,其范围东至永丰县拓阳关、西至铅山县分水关,包括江西上饶、永丰、铅山和福建建宁府浦城、崇安诸县临界地区。具体措施如下:
上饶五十二都三堡至八堡,民田粮七十八石,及五十三四等都,东至永丰十五等都,西至铅山十三等都,山塘地皆不得耕种。录居民通贼者,尽行诛戮,家产入官。被寇者量行给复,徙之他所。浦城、崇安视此例。凡诸洞向通往来之路,悉甼石为障。于上饶设高洲、枫林、张湾,永丰设谹山、军潭、港头,凡六隘。择素有恒业居民,充为老人,添设快手,月给口粮,令各分守信地,统以寨官,随军操演。禁不许停插异郡商民,及于隘内往来,以月之朔望申报,违者籍没戍边。[8](卷三《封禁考略》)
据上文可知,明正统间的封禁措施主要有:第一,禁止山外人等进入,用瓮石堵住往来通路;第二,封禁区内原有居民悉数外迁,山内田地亦不得耕种;第三,在上饶县的高洲、枫林、张湾,永丰县的谹山、军潭、港头等六处设置关隘,添设快手驻防;第四,选择六隘附近有恒产之人充当“老人”,协助管理;五,外地商民来往隘内,每月需要申报两次,不守法者抄家充军。这些措施有效地限制了山外民众潜入封禁山区,维护了周边地区的社会秩序。
封禁政策一度得到有效执行,且有不断加强的趋势。据载,正徳十年(1515),一伙奸民佯装在禁山外缘采伐木材,后潜入禁山内采挖铁矿,妄图邀集铅山县民人倡乱,被官府迅速镇压。事后,广信府衙在封禁旧界立石示禁,又于六个隘口新设“寨官”,增添士兵和快手。在此情形下,嘉靖末年江西广信府、饶州府与浙江衢州府三府交界的云雾山地区矿盗迭起,波及闽、浙、赣、南直隶数省,但铜塘山附近安然无恙。一个名叫祝十八的浙江龙游人,“聚矿徒数百”,从浙江江山县前往福建浦城县,妄图乘乱“邀众分劫平洋、铜塘”等处,因当地兵士有准备充分,而被拒于山外[8](卷三《封禁考略》)。不过,江西副都御史胡松(1503—1566)并不放心,向朝廷要求仿“汀州武平之属岭北、潮州程乡之属漳南故事”,加强封禁。内容如下:
请乞以福建浦城、浙江之常山、江山三县,与三县所属之盆亭、溪源、高泉、仙霞、小竿诸巡检司,悉听江西分守湖东道管辖提调,责令盘诘探报,可以先期为备。如遇各贼盛聚,一体召集乡兵,首尾应援,阻截遮邀。最盛则移文建宁兵道,严、金、衢、温、处守巡各道,速发援兵,协力驱逐。违期者,听臣等江西抚按参论。仍乞敕下兵部查议,果于事体可行,请赐不坐名敕书一道,专令分守湖东道参议驻扎广永丰县治,训练营乡等兵,控扼禁缉,逆折潜消。[4](卷二百四十六《为请专勅严经略疏》,P2578)
引文显示,为防范三省毗邻地区的流民滋事,分守湖东道参议移驻于永丰县治,并获得了调配邻近巡检司的权力;形势危急之时,还可要求严州、金华、衢州、温州、处州等地兵力迅速增援。
二、明中后期的槽工与封禁松动
明代中后期,南方山区的经济迅速发展,闽浙赣三省亦不例外[11]。江西广信府的造纸业兴起,大量业纸槽工聚集在封禁界线附近,从事毛竹种植和纸张生产,成为三省边界山区新的安全隐患。
据万历《江西省大志》记载,江西玉山县曾是南方数省的造纸中心,“各纸原行江、浙、福、湖四省,色数相同,造解顿殊,而彼三省俱各差官赍捧现银前来玉山县收买”。嘉靖间,原集中于玉山一县的官营纸槽逐渐向私营转变,散布于武夷山北麓的丘陵地带。
自嘉靖以来,始有永丰、铅山、上饶三县续告官司,亦各起立槽房。玉山槽坐峡口等处,永丰槽坐柘杨[阳]等处,铅山槽坐石塘、石垄等处,上饶槽坐黄坑、周村、高洲、铁山等处。[12](卷八《楮书》,P196-196)
结合前文,纸槽分布的永丰、上饶和铅山三县,也是正统间封禁的边界所在,而永丰之拓阳、上饶之高洲二处则是把守封禁山入口的据点。查照地名志资料可知,铅山之石垅,在分水关东北;上饶之周村、铁山,在高洲之东北,三者均处于封禁的边缘处。晚明广信府的造纸非常繁荣,铅山县尤甚,纸槽密集之处,需提供大量的嫩竹作为造纸的原料。据此推断,铅山、上饶等造纸之处,势必广泛地种植了毛竹,说明封禁边缘之区得到一定程度的开发。
与此同时,封禁界内的树木蓄养已久,为外地商人觊觎。据载,隆庆三年(1569),“有徽人者疏请开荒以济国用”;隆庆五年,又有商人“合谋奏部行勘报如前”。因朝臣举证封禁故事,“诚恐有徒突之患”,均被拒绝。万历九年(1581)前后,江西等地施行“一条鞭法”,重新丈量土地,又有商人“建议垦荒”,亦未获得准许。[8](卷三《封禁考略》)不过,随着内臣向皇帝贡献杂货税银之风渐盛,江西矿税使潘相于万历二十八年鼓动江西矿税窑木腾骧左卫百户赵应璧,向朝廷奏请弛禁饶、信二府边界的云雾山,开采山内银矿,以征缴矿税。明神宗闻知,下旨命潘相前往查实,遭浙江衢州、江西饶州等地官员强烈抵制。次年三月,潘相报称,“江福永丰、浦城官山(封禁山)内产大木”,请朝廷开放采伐。[13](卷三十《征榷考·杂课》,P445)明神宗又命潘相前往勘察,上饶地方闻讯,群情激动,官员亦强烈反对,并设计阻挠潘相的勘察事宜。万历三十年正月,前往禁山调查的潘相片木未见,踉跄返回饶州,采木之议遂寝。又有上饶民人刘鉴报告,封禁界内的铜塘山有银矿可采。潘相闻之,遂派人招揽匠工直接入山采挖银矿,匠工“日恣其挖掘”,侵害地方利益。于是,广信知府陈九韶向朝廷要求罢矿,愿以“采青”替之,获得皇帝批准。未曾料到的是,采青之害,甚于开矿。匠工采挖土青,“波及民间坟墓者,十之七八”,“法令所不能禁,约束所不能施”,以致民怨沸腾。[14](卷八《封禁考》)为停罢采青,陈九韶再次上奏,“情原包纳山价三千两,认买此山”,“续议加增土产折价银一千两,一并解进助工”,“岁以为常”,弛禁一事才算了结。[8](卷三《封禁考略》)
广信府官员如此强烈地抵制开发封禁山,一方面是矿税使等人行为不端,危害民众利益;另一方面,则是担心聚集在封禁边缘的大量槽工滋事。据知府陈九韶言:
查得铅山石塘纸厂槽户不下三十余槽,各槽帮工不下一二千人。近因税额太重,远商鲜至,槽户亦渐罢槽,而趋他业。其帮工人流散各邑,群聚为奸,昼则募化,夜则穿逾。封禁之开,如开采果行,此必乱之道也。[14](卷八《封禁考》)
石塘镇位于铅山县东南,属十二都,与正统间属封禁范围的十三都仅一山之隔。据万历《铅书》记载,石塘地方“多宜于竹,水极清冽,纸货所出,商贾往来贩卖,以给天下之用”[15](卷四《街市》,P500),是广信府专业化造纸和纸张贸易的著名市镇。倘如陈九韶所言,石塘有纸槽30余座、槽工三五万人,加上其他造纸之处,封禁边缘恐怕聚集了数以十万计的槽工。若遇市场不畅、槽户歇槽,这些槽工失业,即使不开禁山,也是严重的社会问题。
不过,官府并未关闭或驱赶各处纸槽,而是允许槽工在封禁界线附近从事纸张生产。万历末年,广信府造纸业已十分繁荣,仅铅山一县的纸张便可供“天下之所取足”[16](卷一《食货书》,P406),原属封禁范围的铅山县十三都竟出产“独连”“小表”“黄白”等多个品种。[16](卷一《食货书》,P406-408)不止如此,天启七年(1627),明廷将封禁碑立于上饶县南的岑阳关,[17]岑阳关是沟通福建崇安和上饶县交通要道。清顺治间,江西巡抚蔡士英(?-1675)也称,“封禁山界连上饶、永丰二县之界”,只字未提及原属铅山县境的封禁地区。[18](卷三《行查山场出产木植疏》,P272)这些迹象表明,封禁政策在晚明出现了松动,临界上饶、铅山、崇安三县的造纸地区已不在封禁范围之内。
三、清代的棚民与封禁沿袭
清代初年,历经清初征服战争和“三藩之乱”的兵燹,闽浙赣毗邻地区经济凋零,人口骤减。为恢复经济发展,江西广信府大肆招揽流民,赣南、闽西、闽南等处流民随之涌入,进一步促进了山区资源的开发。[19]
江西战乱初靖,便有人提议开发封禁山,顺治间巡抚蔡士英奉旨前去勘察有无木材可采。顺治十年(1653),蔡氏奏请维持对上饶、永丰二县临界山区的封禁,“若此幽深崇峻、夙称盗薮之处,今日一启其衅,将来必至从乱而不可收拾”[18](卷三《行查山场出产木植疏》,P272-273)。实际上,顺治间的封禁政策仅制止了封禁山区的开发,而无法阻挡武装势力入山。据载,“三藩之乱”时,广信府境内盗贼四起,“前者甫平,后者复乱,今日败走,明日重来”,“逆贼所踞为巢穴者,如上、永之高洲、周村”等处。这些盗贼“既不耕种,又无馈饷”,只有“于诸山隘口,四面堵截,绝其打粮之路径”,才能“翦其通线之奸徒”,将之一一剪除。叛乱平定后,广信知府曹鼎望提议,在“各属险要之区,设立重汛,或建造木城,或垒筑石寨,每汛拨兵二三百名,镇守其地,申明纪律,剿寇安民”,严格控制边界山区的流动人口。[20](卷十一《咨询地方利弊条陈》,P1448-1449)从现存宫廷档案资料看,康熙间广信知府限制流民的政策具有一定的效果,封禁范围内长期未有流民进入。据雍正间江西巡抚裴率度(1667—1740)报称,雍正三年(1725)广信府境内查获有不少以种靛、种烟为生的棚民,但他们均生活在封禁界线之外,且已编入户籍,禁山内并未发现棚民。鉴于“现在地方宁谧”,裴氏建议“一动不如一静,似又无可开增也”[21](P529-530)。故清廷于雍正四年下令沿袭旧例,维持封禁政策。[22](P381-382)
社会承平日久,广信府人口渐增,抛荒土地开垦殆尽,雍正末年贫民逐渐向山区移动。据福建崇安知县刘埥称,因江南总督赵弘恩(?-1758)拿获数名江西“奸匪”,匪首供出封禁山内尚聚有众多余党,故奏请江西、浙江、福建三省邻近官府联合入山搜查,刘埥便是受命随同勘察的成员之一。事后,刘氏写成《会勘封禁山纪事》一文,详载当时的封禁情形。刘埥认为,封禁山内的山地“开垦难于为力”,山木“皆不堪适用”,更无铜矿可采,故“禁则并无弃利,开则必有遗害”,建议增派兵员严加把守,但文辞间呈现出封禁山区的开发情况。据载,刘氏于雍正十二年六月从福建崇安出发,经岑阳关进入上饶境内,“两日而抵高洲”,次日入山。其文曰:
雇土人十余名为引导,且挑负米盐。自高洲行三十里,住范家坳,系上饶地方,即入山入口六处之一。危岩怪石中茅屋六七家,奇零勺土杂种芋靛等物。其人多黑面深目如鬼形,树根、蛇皮叠如堆。……入禁山口,一路皆丛林密菁,唯松最多,大者可五六围,其余杂树,每有各种攒簇并生,合之可数十围者。深草过顶,碍路处以长刀劈开方可着步,而其下多湿秽难行,盖积年旧草萎而复生,重叠糜烂于其中也。……纡曲经行,虽非正路,然土人犹能约略其径、指目其名者,缘山中多草药,如柴胡、土连、泽泻等物,附近穷民往往结伴带短刃、小枪潜入采取,夜则宿于大树之上。其汛兵皆熟识,知其无他意而不深问也。[23](P410-427)
引文显示,在封禁外围地区,有“黑面深目”的贫民,他们搭茅屋而居,开垦田地种植芋、靛等农作物,并砍伐树木、抓捕野生动物。这些人就是所谓的“棚民”。不过,进入封禁界内后,“丛林密菁”“深草过顶”,尚处于未开发的状态。值得注意的是,有不少“土人”携带短刀、小枪等利器入山采药,留宿山中,而且“其汛兵皆熟识,知其无他意而不深问”。此时,封禁已不是前朝严格限制流民出入,为日后棚民开发禁山打开了突破口。
在乾隆至道光的百余年间,清廷不断饬令强化对铜塘山的封禁,实际情况却与之大相径庭。乾隆八年(1743),江西巡抚陈宏谋(1696—1771)鉴于江西生齿日繁,向朝廷奏请弛禁赣东铜塘山和云雾山两处官山,认为山内有土地可垦,有木植可采,有野物可猎,“利于穷民”者甚多。更何况,铜塘山经“附近居民渐于四围垦殖”,封禁范围“较诸从前已窄,非复旧时广阔”,山内“树艺已蕃,渐成村落”。[24](卷三十四《请开广信封禁山并玉山铅矿疏》,P43)。对此,户部尚书海望(?-1755)指出,陈氏所言与雍正间朝臣意见相左,提议遴选官员前去“再行详细确勘”,“铜塘山荒弃地亩果否可以开垦,并有无滋事扰民之处”。新任江西巡抚受命前往封禁山确查,结果认为弛禁不利地方治安,建议维持封禁。[25]乾隆二十年,江西巡抚胡宝(1694—1763)受命派员巡查封禁山。据广信知府五诺玺等人回报,封禁范围不过百里,山内已有不少耕地,上饶县仅有零星耕地一亩余,广丰县则有“不成片段”的“零开田地”二百余亩。但胡宝对业已开垦土地和居住山内的棚民视而不见,坚持认为,“弛禁一道,有损无益”,建议增添兵汛,永行封禁。[26]嘉庆十五年(1810),广信知府王赓言勘察封禁山区,发现六个隘口的驻守汛兵仅72名,平时不仅无人认真缉捕,还私招棚民垦荒,封禁徒有其名。[20](卷一《拟陈封禁利弊禀》,P98)道光元年(1821)夏,河南道监察御史朱为弼(1770—1840)奏称封禁山内有无籍之徒盘踞,请朝廷令三省督抚筹议驱逐。于是,两江总督、闽浙总督随同三省巡抚前往探查情况。次年,两江总督孙玉庭(1741—1824)等人回报称,封禁山内并无流民,建议新定巡防稽查章程,增加原有六汛的兵员,再于临界四县各添一汛,各派巡检司按月分巡;另由广信府和建宁府每季入山会查一次、建宁镇总兵与江西九江镇总兵每年会哨一次。[27]道光十五年,两江总督陶澍(1779—1839)按例巡察封禁山,发现“禁山内古木无几,山坡多有开种,尚遗包谷、粟米根植,并搭有茅篷”,向清廷建议弛禁,“虽有封禁之名,并无封禁之实”,“似不若因时弛禁,以安穷民”。恰逢江西按察使陈继昌(1791—1849)赴任,受命前往封禁山确查。陈氏回奏,“封禁为要”,并重申道光二年之巡防章程。[28](《江西封禁山山场委勘仍应封禁,并筹议稽查办理章程折子》,P19-44)清廷罔顾封禁山不断被棚民开发的事实,而沿袭数百年的旧制,维持对铜塘山施行封禁政策。
清同治五年(1866)春,福建崇安县有“斋匪”作乱。经江西、福建两省官军合力围剿,匪首相继伏法,却传言有匪党匿于封禁山内。于是,江西巡抚刘坤一(1830—1902)请兵入山搜捕,并“选贤能地方官,编查保甲,随时晓谕该处百姓,以靖盗源”。不久,江西督粮道道员段起前往封禁山内勘察,发现禁山内并无匪类,“惟有在山耕种棚民”,“悉系附近各县人民,因咸丰间屡被贼扰,贫苦无依,入山垦地,借以糊口,并未吃斋为匪,亦无外来吃斋匪徒”。于是,刘坤一向朝廷奏请:“查封禁山内棚民耕种度日,迄今已经数载或十数载。原隰悉成田园,户口居然村落。……该棚民等作苦食力,各得尺寸之土,视为恒产,断不至于为非,亦不容外匪入山,自干株累。今于该棚民强之使出,正难保异日无复入者,徒扰穷黎,无益事实,似不若弛禁为便。”[29](《封禁山内查无斋匪并各府举行保甲折》,P91-94)随之,广信府知府钟世帧、广丰县知县王恩溥等人受命前往禁山,查勘“界址、村落、户口、田亩、林木、溪沟、道途远近”等项,并称:“乡愚避寇入山,耕种年久,户口既盛,原隰已成田园。”[20](卷一《禀复禁山弛禁经制事宜》,P98)同治八年,清廷“奏准弛禁”,两江总督马新贻(1821—1870)协同广信府官员前往山内查办保甲、清查户口等事宜,[20](卷一《奏铜塘山弛禁折》,P100)终将持续数百年的封禁政策废除。
四、结 语
明清时期,流民问题是山区开发伴生的社会问题之一。在闽浙赣毗邻山区,延续四百余年的封禁政策,无不以防范开发山区的流民滋事为目的。然而,不同历史时期山区资源的开发与利用形式各异,官府试图控制的流民并不一致,封禁政策的具体实践也各具特点。明中前期,山区开发以金银矿产开采为主,从事坑冶的矿徒四处觅矿,易聚难散,具有极强的流动性和危险性。为制止矿徒开矿和防范叛乱,地方官府和驻守汛兵较为严格地执行各项封禁措施,将山外流民拒于封禁界线之外。明中后期,山区开发以种植毛竹、生产竹纸为主,从事造纸的槽工活动范围比较固定,流动性和危险性大大降低,官府虽担心其滋事,却也允许他们在封禁外缘地区从事生产活动,致使封禁政策松动,封禁范围大为缩小。清雍正以后,山区开发以种山垦地为主,从事土地开垦和农林作物种植的棚民,与山外的农民并无实质差异,其流动性高,但危险性低,故驻防汛兵“知其无他意而不深问”,甚至私招棚民开垦,地方官亦常向朝廷奏请弛禁,“听民耕种”,封禁政策委实徒有虚名。
明清封禁政策的内容不断强化,具体实践却与之相距甚远,既是受到山区开发形式和流民类型差异的影响,也是明清两代应对山区问题之不同策略的体现。雍正三年,清世宗在裴率度的奏折上批示:“当开,因循不得;当禁,轻动不得。若不存贪利图功之念,为地方兴利除弊,何事而不可为也。全在卿等秉公相度事宜,斟酌而为之。”[21](《江西巡抚裴率度等奏陈封禁山始末情形折》,P530)就封禁政策而言,所谓“秉公相度”的公,主要有两方面内容:一是防范流民滋事,稳定社会秩序;二是开发利用,获取经济效益。比较而言,明朝试图通过里甲体系将民人控制在土地上,限制人口频繁的流动。[30]流民进入山区从事经济开发,已属不法之徒,封禁以防乱为重,故地方官较为严格地执行封禁措施。清朝虽亦害怕“天下有事”,但面对日益严峻的人口压力,施政过程中颇注意贫民生计,往往鼓励民人前往山区开发山林资源,自糊其口,甚至免除新垦、畸零土地的赋税,[31]地方官屡次奏请弛禁亦多虑及于此。同治间,面对封禁山区“户口既盛,原隰已成田园”的现实,清廷应允弛禁,将山内棚民的权益合法化,编排保甲以控制棚民,则是对“以靖盗源”和“以利穷民”的双重考虑。
注释:
①目前,关于闽浙赣边界山区封禁政策的研究尚不系统。唐立宗《坑冶竞利:明代矿政、矿盗与地方社会》(台湾政治大学历史学系2011年版)论及正统间的封禁情况;日本学者日野康一郎《明末民变与山地开发问题——江西上饶县的场合》(《东洋学报》2005年第3期)论及万历间的情况;熊秉真的《清政府对江西的经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18期,1989年)和陈支平 《对于清代雍正年间政府官员考察闽浙赣边区生态环境的解读》(载张建民主编:《10世纪以来长江中游区域的环境、经济与社会变迁》,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8-16页)论及雍正间的情况。
[1]傅衣凌.明清社会经济史论文集[M].北京:中华书局,2008.
[2]张建民.明清长江流域山区资源开发与环境演变——以秦巴山区为中心[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
[3]黄志繁.“贼”、“民”之间:12-18世纪赣南地域社会[M].北京:三联书店,2006.
[4](明)陈子龙.明经世文编.第三册[M].北京:中华书局,1962.
[5]鲁西奇.内地的边缘:传统中国内部的“化外之区”[J].学术月刊,2010,(5).
[6]王菱菱.宋代矿冶业研究[M].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5.
[7]唐立宗.坑冶竞利:明代矿政、矿盗与地方社会[M].台北:台湾政治大学历史学系,2011.
[8](康熙)新修上饶县志[M].清康熙刊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9]明英宗实录[M].上海:上海古籍书店,1983.
[10](明)高岱.鸿猷录[M].济南:齐鲁书社,1996.
[11]徐晓望.明清东南山区社会经济转型——以闽浙赣边为中心[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4.
[12](万历)江西省大志[M].台北:成文出版社,1989.
[13](明)王圻.续文献通考[M].北京:现代出版社,1986.
[14](乾隆)上饶县志[M].乾隆九年刊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15](万历)铅书[M].北京大学图书馆藏稀见方志丛刊.第一六七册,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3.
[16](万历)铅书[M].北京大学图书馆藏稀见方志丛刊.第一六六册,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3.
[17](清)崔应阶.奏报查办汀州逆匪傅元禧案搜查封禁山折(乾隆三十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Z].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朱批奏折,档号:04-01-38-0045-034.
[18](清)蔡士英.抚江集[M].四库未收书辑刊七辑二十一册,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
[19]曹树基.明清时期的流民与赣北山区的开发[J].中国农史,1986,(2).
[20](同治)广信府志[M].台北:成文出版社,1979.
[21]第一历史档案馆.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四册[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
[22]第一历史档案馆.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七册[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
[23](清)刘埥.片刻余闲集[M].北京:九州出版社,2004.
[24](清)贺长龄,魏源.皇朝经世文编[M].北京:中华书局,1992.
[25](清)海望.题为遵旨查议江西奏请开垦上饶广丰二县铜塘山田地事(乾隆九年二月)[Z].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户科题本,档号:02-01-04-13783-008.
[27](清)孙玉庭.奏为遵旨查明江西浙江福建连界地方封禁山并无流民潜匿居住并筹议巡稽章程事(道光二年三月)[Z].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朱批奏折,档号:04-01-01-083-0376.
[28](清)陶澍.陶澍全集.第四册[M].长沙:岳麓书社,2010.
[29](清)刘坤一:刘坤一遗集[M].北京:中华书局,1959.
[30]刘志伟.在国家与社会之间:明清广东地区里甲赋役制度与乡村社会[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31]彭雨新.清代土地开垦史[M].北京:农业出版社,1990.
【责任编辑:姜庆刚】
K207
A
1004-518X(2017)09-0148-08
重庆市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清代内地的封禁问题研究”(2016BS066)
廖 涵,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讲师,博士。(重庆 4000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