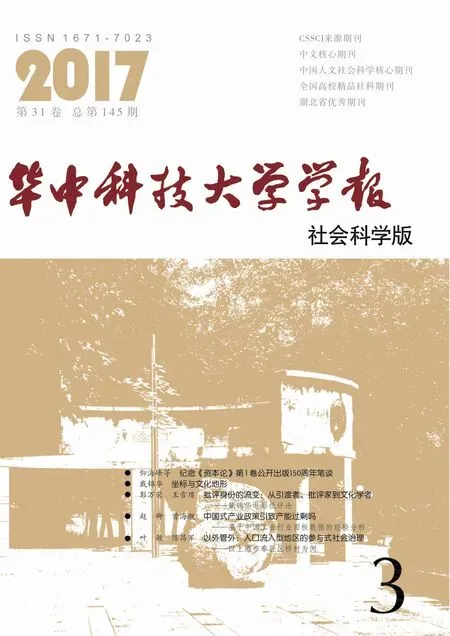坐标与文化地形
□戴锦华
坐标与文化地形
□戴锦华
本文选择三部生产机制、接受层面迥异的文本:话剧《北京法源寺》、电视连续剧/网络小说《琅琊榜》、国际获奖艺术电影《刺客聂隐娘》为细读与思考对象,尝试借重文本之表述与症候群勾勒其显现的文化地形。笔者由伦理主体对政治主体的置换、能指游戏与非行动及镜中女侠等议题的展开,尝试探讨面对全球化的今日世界,面对中国崛起,我们该如何重新确定或创造新的社会文化坐标。笔者认为,今日文化研究的首要挑战,不仅是通过文化、文本事实形绘社会,而且是质询并挑战既有的坐标系统与思维惯性。
《北京法源寺》; 《琅琊榜》; 《刺客聂隐娘》; 坐标系统; 文化地形
一、引 言
2015年,法国戛纳国际电影节上,两部华语片:侯孝贤的《刺客聂隐娘》和贾樟柯的《山河故人》入围了竞赛片名单。今天,甚至在中国电影圈,这已不能构成耸动性新闻,最多只能称为“好消息”。两位入围者均为备受欧洲、尤其是法国国际电影节钟爱的电影艺术家,最终,以侯孝贤再获最佳导演、贾樟柯获金马车/终身成就奖而曲终奏雅。
然而,这两部在戛纳获奖、在中国电影院线隆重上映(尽管票房战绩不佳)并斩获了无数华语电影奖项的影片,却间或在不期然间展露了某种文化政治的症候:“中国时间”的重归与悬疑。于《刺客聂隐娘》——这部主要借重中国大陆资本的台湾电影大师侯孝贤的作品,是“梦回唐朝”,中国古代史脉络的再度显影和接续;于《山河故人》——这部几乎成为中国(大陆)艺术电影代名词的贾樟柯的新作,则是未来,三段故事的最后一段设定为2025年。甚至影片的一、二部分(20世纪90年代与新世纪之初的中国山西汾阳故事)都似乎置身在出自未来的怅然回望中。对于一个曾丧失或曰抹除了自己的历史的国度、对于一个百年来焦虑于时间的再度启动或曰时间的获得的文化说来,两部影片不期然展示的悠长、久远的历史维度与未来纵深,似乎以有别于经济学统计数据的方式,印证着中国的激变或曰国际视野中的中国崛起。有趣的是,这两部被述年代相距1 500年的故事,却在其结局时刻,采取了某种结构相类的时间再现。影片的结局或许也正是《刺客聂隐娘》中最动人的段落:女主角放弃了印证“道心”的刺杀使命,履约护送来自东瀛(日本)的工匠返乡。伴着苍凉辽远的苏格兰风笛与非洲乐器演奏出的法国民谣Rohan,一行人马在漫天枯草间渐行渐远。朝向大唐/中国版图之外,朝向中国历史之外,朝向无名而未知的时间。而《山河故人》的第三段、2025的故事则远移到澳大利亚某地,女主角的儿子、那个被名之为到乐/Dollar的孩子已长成为一个中国游离民,遗忘了母语、遗忘了母亲和母国,在青春的无助间躁动,空余母亲赠予的一串归家的钥匙。似乎是往昔梁小斌著名的朦胧诗句“中国,我的钥匙丢了”的反转,不是我们在红色的岁月、“红色的大街上”遗失了开启中国的钥匙,而是我们紧贴心口珍藏着钥匙,却遗忘或曰遗失了家/国、或得以进入的大门。此间显影了另一处与今日中国有关的症候:不约而同地,两部影片在脚注了中国时间重启的同时,溢出了中国故事。加入世界时间?还是规避或悬置了对未来与方向的确认?进步?或前行?朝向何方?
二、坐标与文本
中国近200年的国族创伤记忆与100余年的曲折的现代化进程,不仅将欧美资本主义作为榜样与敌手深深地植入了中国社会与文化的内部,而且令表达为“赶超(欧美发达国家)”的现代主义逻辑成为20世纪百年中国的社会动力与政治文化坐标。若说21世纪之初,危机与纷争的底景显影了作为世界性事实的中国崛起,那么,今日中国所面临的是重新为自己选择并确定方向,进而为世界演示不同的可能。一度中国持续高速增长的GDP,因幅员和发展的不平衡而展示的巨大的资本纵深,中国巨大的人口基数之上的潜在市场,间或令中国显现出充当全球资本主义发动机的潜能。然而,21世纪之初的十余年间,中国不仅迅速地挥洒着其资本纵深,而且快速步入(如果不说是加剧)了全球资本主义困局。
颇具意味的是,21世纪,作为唯一一个介入“环球逐鹿”的非西方大国,资本主义的高速发展背书了“中国道路”,而曲折经历了20世纪的中国道路则无疑是中国革命之路。然而,居于今日的世界高地之上,中国却是在20世纪最后20年间,最为深刻地将革命书写为创伤记忆、以“告别革命”为内在共识的国度(之一)。曾经,在20 世纪的终结处,卡尔·马克思与汉娜·阿伦特或许并不对称的遭遇与对话,似乎以某种理论的表达总结、终了20世纪。这或可视为对世纪之交中国主流知识界社会共识的一种描述:站在后者的角度上,对贫穷这一社会经济问题的、“不当的”政治解决,非但未能创造社会进步,相反酿造了社会灾难及无穷后患[1]。如果说,在全球思想史的视域之间,这意味着美国革命取代了法国革命成了君临性的现代范式,那么在世纪之交的中国,它同时意味一份有效的“告别革命”的政治实践。在某种隐形的社会常识系统中,这不仅是对“革命”、而且是对一切政治实践之为社会解决方案的拒绝。然而,冷战终结20年、新自由主义主宰30年,资本主义已经快速“返璞归真”,急剧的贫富分化再度形构陡峭的金字塔形的全球结构——不仅是富国与穷国,更是富国与穷国中的富人与穷人。全球金融海啸固然一度撼动了金融帝国的主建筑,但最终只是消融了欧美国家“纺锤形”社会的中段与底端。在中国,即使忽略(尽管难于忽略)收入的巨大的灰色地带,在统计学可能触及的范围内,基尼系数早已拉响警报。于是,看似猝不及防地,汉娜·阿伦特遭遇了皮克提[2]。对后者——这位不断声明自己绝非左派、对社会主义毫无同情之意的主流经济学家说来,他面对这再度固化的、承袭型资本主义世界可能提出的解决、缓解方案都只能是政治性的,或者说必须以政治方案为前提或保障。但是,急需却未曾出现答案的是:姑且不论革命,各类政治方案如何得以达成或实践?这无疑内在联系着中国如何选择自己的方向与坐标。然而,如果警醒到法国革命作为唯一现代范式所携带的问题,直面“后冷战之后”的世界,冷战造就的全球结构已全然改观,那么,即使不论及革命,我们该如何定义,至少是想象政治选择中的左与右?依据多数/99%或少数/1%的利益?仍然依据激进变革或现实秩序?后者看似自明:即参照着已然发生过的欧美世界的现代历史,问题便再度出现,在中国巨大的人口基数与资源状态之下,我们可否复制任何西方模式?对于前者,问题则在于,激进变革向何方?如果说,20世纪终结处的“大失败”*1989年-1990年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延续40年的全球冷战对峙以西方阵营的不战而胜宣告结束。国际左翼观点将其称为“(全球共产主义运动的)大失败”。尚未耗竭共产主义构想*21世纪之初,欧美左翼思想家开始重提“共产主义”议题。颇为著名的是法国理论家阿兰·巴迪乌(Alain Badiou)2008年1-2月号发表在《新左派评论》上的文章《共产主义构想》(The Communist Hypothesis),后发行单行本。,且不论20世纪世界革命的实践对这一构想的玷污与冷战胜利这对这一构想的妖魔化,20世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遗留给我们的遗产尚阻断在巨大的历史债务与创伤之下,20世纪遗留的历史谜题:关于新的历史主体、关于阶级与政党、关于民族国家与新国际……尚未有新的推演、清理与更新。当关于社会的未来的愿景尚在暮霭重重的迷茫中,激进变革便不时成为不服从的呐喊和种种符号学的反叛展演形式。
不错,冷战终结,资本主义全球化成了唯一的世界事实;片刻之后,资本主义不再拥有其外部(并因此而丧失了其潜能与活力),资本主义也开始失去其内部差异性;社会问题与苦难极速加剧。但更为深刻的问题接踵而至。即使我们暂且搁置自2001年9.11袭击、美国的反恐意识形态及战争、到ISIS的全球扰动,搁置2008年迸发自华尔街的金融海啸、金融帝国的倾斜与未绝余震,搁置自1994年墨西哥恰帕斯玛雅原住民打响了“反全球化的第一枪”到占领华尔街运动及晚近发生的、法国的“黑夜站立”,搁置继政治犬儒主义的全球弥散之后,右翼民粹主义的世界性蔓延和践行,今日资本主义所遭遇的,不仅是危机与乱象,而且是以能源危机与生态灾难显影出的现代文明遭遇、碰触着的玻璃穹顶。颇具反讽的是,这阻断了现代主义无穷上升之承诺与愿景的玻璃穹顶,正遭遇以生物学技术和数码媒介为代表的又一度技术革命。此番,新的生物技术在全面入侵、改造人类身体和自然秩序同时,首度问鼎死亡;而数码技术——互联网、数据库尤其是移动终端/移动通讯平台,不仅整体地改变着通讯、传播,改写了知识生产、生活方式,而且改变着人类社会的组织方式与社会生态。两者确乎将现代世界带到了某种临界点或突破点上。于是,一边是新技术奇异而充满魅惑的后人类邀请,一边是阻断了未来视野,将今日世界定位于“末日生存”[3]。因此,甚至在好莱坞科幻类型的主屏上,不仅技术进步推进的未来场景不约而同地成了彼此截然分立的双重世界:光洁美丽、青春永驻的富人、统治者的顶层世界与劳动者和弃民们的底层社会的穷街陋巷,而且末日想象以颇为宽广的光谱再度覆盖了银幕空间。如果说19 世纪终结资本主义的旗帜扬起,基奠于资本主义的掠夺、帝国主义的暴行与深重的社会苦难,那么,它同时立足于资本主义所激发和释放出的巨大的生产力潜能与社会能量,马克思主义的表述及展望因此盈溢着巨大的激情与欣悦。今天,当20世纪的历史创伤令“终结资本主义”几乎成了集体缄口的禁忌,资本主义的终结却以现代主义逻辑的反噬开启了现在进行时。置身于全球资本主义前沿,中国正迸发着惊人的后发优势,因此而多少颠倒着曾经欧洲中心的“历史进步”坐标;但是,当资本主义的终结意味着现代文明必须在野蛮主义与未来间重新选择方向,那么,中国是否应该或必须为自己和世界提供不同的可能以赢得未来?在持续百年的中国文化的古、今、中、西的四项坐标之间,我们将如何定位中国时间?如何形绘今日中国的文化地形?
2015年-2016年间的一组文化文本似乎显现了丰富的文化症候。那便是作为全新的天桥剧场揭幕式、与百老汇经典音乐剧《剧场魅影》“并肩”上演古装政论剧《北京法源寺》的演出与热议,一演再演;还有2015年间风靡中国大陆,一时间达成老少咸宜、雅俗共赏、官民同乐的古装电视连续剧《琅琊榜》——此剧改编自未见经传的作者的网络长篇小说,经由民间影视制作商业机构斥重金制作,电视剧在全国热播,达到“现象级”的同时,获得国家与政府各类官方、民间电视奖项并通过商业渠道成功地全球发行。迥异其趣的,则是亚洲艺术电影第一人的侯孝贤的新作《刺客聂隐娘》。三部文本除了有着覆有共同的“古装”——其间间隔着千余年的光阴,文化生产机制各异,资本来源与文化动力不同,传播与接受层面天差地别,却似乎怪诞而有趣地共同勾勒出这坐标漂移的文化地形的一隅。
三、伦理与主体的意味
当今中国最重要的舞台剧导演、也是近乎唯一的重量级女性导演田沁鑫的剧作《北京法源寺》*话剧《北京法源寺》,改编自台湾作家、政治异见者李敖的同名长篇小说,田沁鑫编导,2015年12月在北京新天桥剧场首演,2016年与全国各地巡演,2017年将重返国家话剧院舞台。选取了中国历史转折点的重要历史事件:戊戌变法为被述事件。在版本各异的主流历史叙述中,戊戌变法事实上被视做现代中国历史的起点之一。当然,这一仅只百天、以当事人身首异处、血洒法场为终结的历史事件,与其说是一个明确的终结与开端,不如说是一个历史的岔路口:在帝国主义列强的环伺下尝试延续封建帝国,其政治制度或变法维新——采取相对温和的改良路线以君主立宪的形态完成近代中国的现代化“跃迁”——其间昔日中华帝国的朝贡国日本便是一个切近的成功的例证(于是,在彼时的历史现场与此后的历史追述中便形成了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与中国戊戌变法的失败间的平行比照,由此形成了一系列关于古中国的社会、政治、文化的历史与价值判断。尽管这一比较中太多的省略项造成了诸多历史与现实的盲区);或戊戌变法的失败印证了中华古文明的老迈不堪、衰朽无力与积重难返,因此只有革命一途。由此开启了20世纪之为革命世纪的、极端、酷烈而波澜壮阔的100年。
21世纪之初,话剧《北京法源寺》作为某种意义上的、当下中国的新“主旋律”之作,作为对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的《文艺座谈会讲话》的自觉实践,该剧与其说是为某种政治立场和理念所统御的文本,不如说更像是为多种政治与社会潜意识所穿透的独特文本。事实上,剧作的编剧、导演田沁鑫对戊戌变法这一被述时间的选择:所谓以“盛世之音”演绎“末世之危”的组合,其自身已充满了社会文化意味。我们固然可以在中国文化的“盛世危言”的传统中寻找文化逻辑与依凭,亦可在扣访历史的特殊关头的以重述国家政权之合法性的文化惯例间去确立阐释路径,但在笔者看来,这一时间点的有趣重合,可以或可能服务于某种现实的意识形态效果:中国正争取着近乎无穷的历史/未来纵深。戊戌变法之际,昔日中国/清王朝尽管面临着帝国主义列强亡国灭种的威胁,但近旁有日本效法欧美、维新成功、富国强兵的榜样,远方有欧美发达国家的目标,且英国的工业革命,正激发出现代资本主义的巨大活力与生机,但事实上,剧目或许在政治潜意识的驱动下,在这个有趣的时间点的重合上,再现了今日中国、也是今日世界胶着的社会议题——“告别革命”。在剧中,当变法尝试触及既有的政治制度,保守派开始反扑,光绪帝密诏维新派,维新派最终读懂了密诏的真意——年轻的皇帝在求救。此时,这一逻辑而怪诞的情景得以显影:在“忠君”的首要信条中,维新派必须即刻行动,救驾/勤王,这是维系既存秩序的底线与必需;但在彼时的历史情势下,这同时不仅意味着帝党颠覆后党,“围园劫后”则意味着“谋反”,甚至革命。这一历史时刻的张力,不仅出自高层权力内部的自我倾轧,而且是再度抉择方向的历史时刻:救驾亦即谋反,维新是否演化为革命?而在剧情结构中,痛切的是,即使搁置包藏在这段历史中的诸多谜团,此时的维新派即使果决行动,他们也只是极端脆弱、激进的异端,全无政治/军事力量的支撑与加盟。换言之,权力高端的危机情势并不始终意味着革命情势。于是,剧情的重心,便由中国历史的政治抉择,转向了个人命运的道德抉择:在历史回望的视点中,登场伊始便确认了“中国英雄”*2015年4-5月间,田沁鑫监制的话剧《英雄24小时》上演,相对西方价值和表述,寻找和追问“中国英雄何在”,“何谓中国英雄”。该剧无疑成了《北京法源寺》的热身和垫场。谭嗣同的意涵:殉。若说这正是此剧的重心所在:再度启动、更新中国文化主体与核心价值,借重佛教言说激活个人与家国间的连接(“大慈悲”、“救众生而引刀一快”),那么,此间不期然间显露的社会症候,则是道德主体对政治主体的置换,个人生命的伦理抉择取代并悬置了政治选择与政治困境。一旦伦理评判取代了政治论述,那么这部政论剧自觉不自觉地令角色、也是历史形象的对照组:康有为(“去留肝胆两昆仑”)因道德底色的含混而黯然。同时黯然乃至消隐或放逐的,不仅是康有为代表的激进政治选择,也是他激进的政治思想:《大同书》。正是后者,不仅溢出了戊戌变法的政治构想,而且溢出了以欧洲为楷模和模板的资产阶级革命或启蒙思想的对“人类公理”的大胆设想。相对于今日与当下,所谓“讲述神话的年代”,不仅参照着“中国崛起”,更参照着“危机中的资本主义”,康有为的政治理想原本更具思想资源与文化价值的意义,但这确乎可能再度开启中国时间、也许也是人类时间/未来的历史角色与表述却如此“逻辑地”消弭于一部以思考中国价值为其自觉的文本中。因为剧作的社会前文本,正是“告别革命”的深刻共识与另类选择的彻底缺席。
于是,《北京法源寺》中,其被述的历史事件已然决定了“谋反”/“革命”/激进变革曾是(并最终成为)真切的现实选择与历史时刻,只是在饱满的戏剧张力迸发之际悄然转换为个人与伦理命题。类似时刻与选项在《琅琊榜》与《刺客聂隐娘》中则全无踪影,而道德主体对政治主体的置换,却成为文本意义确立的不约而同。颇为有趣的是,在《琅琊榜》中,这并非绝对与唯一主角的生命意义与价值的确认,而是他呼风唤雨、运筹帷幄地推进与执行的政治规划:重整朝纲——在既存的政治制度内部重建道德秩序,即以明君替换昏君,以清官替换贪吏;而确保明君不会再度堕落为昏王的依据,是其人的人格特质与道德高度;确认清官不复贪腐的理由,则不仅是其人品而且是其职业伦理:兢兢业业、克勤克俭的自觉。这一政治规划的达成,则不仅以多重道德主体置换了政治主体,而且完成了主角自身作为政治主体的自我否认与抹除。而在《刺客聂隐娘》里,主角之为意义与道德主体的获取,正在放弃颠覆性的政治行动:刺杀暴君,以达成其政治选择,即维系岌岌可危、不尽如人意、或甚不如人意的既存秩序。尽管有着艺术的高下与文化定位的巨大落差,《刺客聂隐娘》却的确再现了2003年张艺谋的另一部古装巨制《英雄》的叙事主题:刺客的故事最终落锤于放弃使命、选择不刺的结局,中国电影史上唯一的成熟类型:功夫或曰神怪武侠片作为中国动作片却终了于非行动。但不同之处在于,无名之不刺,出自对权力逻辑的了悟和认同:唯有将未来托付强权和暴力,才有和平与秩序的可能;而聂隐娘之不刺,则瞩目于维系秩序的别无选择:“死田季安,嗣子年幼,魏博必乱,弟子不杀。”而这一政治选择与承担同样在令聂隐娘获得了道德主体(“与圣人同忧”)的高度的同时自我抹除,她弃置刺客的指令与使命,飘然远逝。
或需赘言,类似文本无疑继续推进着社会文化的非政治化进程,并以其变奏形态再度形绘这一坐标错位或曰丧失了坐标的文化地形:事实上,不仅出自笔者的文本选择,亦无关乎古装/时装,几乎所有略具政治性的文化文本,都集中于高层权力集团内部的对决与选择,所谓“殿堂高耸,人间戏场”,全然无关于民众、民间或人民。事实上,在新世代的网络文化中,“宫斗”一词,已成为英文politics的“标准”中译。考虑20世纪中国曾有过普及历史唯物主义教育的时代,农民起义、人民革命曾取代王朝更迭而成为历史教科书中的主线——“把颠倒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对这一颠倒的颠倒,其意义便昭然若揭。或许更为有趣的是,《琅琊榜》与《刺客聂隐娘》这两部事实上“风马牛不相及”的文化文本,却再度不约而同地选用了类似美国西部片式的结构形态:神秘无名的外来者进入了文本中的元社会,最终以法外执法捍卫或修复了社会秩序,而后悄然消失/自我放逐至文本世界之外。当然,取代了“荒原”与“田园”之二项对立式的,是中国文化想象中的“江湖”与“朝廷”。且不论汉代以降,所谓“江湖”已不复,朝廷权力不及的真实地理空间,而略类于公民社会之于现代国家,但是,甚至这一作为皇权补充物的“江湖”,也并未在任何意义上成为故事中的想象空间,而只是某种子虚乌有的悬置,或曰空洞的能指。不同于西部片的结构设定——外来的牛仔相对于白人/殖民者的定居点具有充分的(尽管无疑是意识形态性的)异质性,这两部文本中的外来人则具有十足的内部性——不仅高度内在于权力结构,甚至极端繁复和紧密地置身于中国式的亲属关系的密网之中。
换言之,在大众文化与公众想象中,与另类政治解决方案同时丧失的,是想象权力之外部空间的愿望或能力。如果权力结构没有其外部,那么也就没有政治意义上的革命或变革,没有搁置另类愿景的所在,甚至没有希望的空间;有的只能是“改朝换代”——当权者的更迭,而民众——尽管渐次从大众文化中褪色、消失,其命运只能是永恒地在“兴亦苦、亡亦苦”间辗转。
四、能指之戏与非行动
在类似文本中,这些来自内部、回归内部的“外人”/他者同时症候性地遭遇着“命名”困境。影片《刺客聂隐娘》尽管以主角为片名,但在影片中,除了一处例外,她从未被称做聂隐娘或隐娘,相反在影片中她拥有一连串本名、别称、乳名或爱称。如果说,聂隐娘这一流传千年的能指对应的正是女侠客/女刺客的传奇,那么在影片中,对这一称谓的避讳或搁置(固然有其中国传统文化的依据)间或正是在意识与潜意识之间表达了对激进政治与行动的拒绝或规避。唯一一处例外,是影片的尾声处,来自日本的负镜少年喊出了“隐娘”,而此时的聂隐娘已绝恩于师,放弃自己的刺客身份。而《琅琊榜》这部最终以四卷实体书和52集电视连续剧形式确定的浩繁篇幅,或可视为一个能指互译游戏。以“琅琊榜”榜首之人的身份登场的,是梅长苏/“江左梅郎”,他初入京城化名苏哲,这个毫不用心、甚至欲盖弥彰的化名当然很快得到破解,但追索到此人即“江左梅郎”,并未终止一个贯穿始终的追问——他是谁?在剧情中,这份谜底看似清晰:他便是十二年前惊人冤案的罹难者、传统中国叙事中的典型角色、幸免于灭门九族之祸的忠臣之后、亦为“天纵奇才”之“白衣小将”林殊。然而,林殊这一能指除了为角色提供了行为动机并预设了他的内部身份外,并未构成任何结构性所指的意涵。主角拒绝也不曾以林殊的身份出现(故事中的玄幻成分 “合理”地抹除了梅长苏身为林殊的全部依凭),惟一充当了角色之意义或曰所指的,是一块牌位——一个死者或亡灵。有趣的是,《北京法源寺》亦开始于生者与牌位/亡灵的对话,但其主旨是最终令死者在场;而《琅琊榜》则最终令其缺席:梅长苏或林殊最终将自己“还原”为一个死者/一块牌位,一个在既存秩序与法理中占有了位置的牌位。而梅长苏得以自外部进入的“名片”/能指出自琅琊阁:“得麒麟才子者得天下”。然而,这预设给定了破解路径的谜语,很快便锁定于梅长苏,“麒麟才子”由是成了主角的另一个能指。此能指远比其他能指更为重要的是,它界定了主角相对于权力核心的功能意义。这也正是梅长苏给自己的定位:一个“权臣”,而非林殊这一能指所指向的“复仇者”。他因此必须被否认、最终被抹除,缘于他负载着剧中作为“宫斗”的全部政治行为与意义:权谋、厚黑、夺嫡、构陷……。他存在的意义,便是以其“政治”主体的行动令未来的、理想的“政治”领袖不遭“政治”的玷污,仅仅作为道德主体而确立。
可以说,正是这围绕着人物命名的能指的游戏,令《琅琊榜》的主角成了某种“空洞”,一处为行动和“意义”所充满的空洞。用齐泽克的说法,便是“以‘空洞的姿态’(帮助靖王夺嫡)悄然完成了‘精神无声的编织’”[4]。不仅其行动意义是所谓“回溯性的标记”(昭雪冤案),而且其叙事便是主角逆行性地抹除自己的政治行动及其自身存在的痕迹。其政治诉求不是颠覆,甚至不是重建,而只是恢复——对旧有的/理想的(亦即曾寄托于蒙冤而死的前皇太子的)政治秩序的恢复。全剧的大团圆结局中:明君清官、母慈子孝、夫唱妇随——中国伦理秩序的再度确立,梅长苏似乎从未到过,从未存在;或者说早已作为林殊而长眠。如果说,主角原本来自一道结构性的裂隙(历史冤案),那么他也正是在裂隙的弥合中消失。
也正是在这里,《北京法源寺》《琅琊榜》和《刺客聂隐娘》作为在不同社会层面、不同接受路径上大获成功的文化文本,显露出内在的差异与更为深刻的社会症候或曰政治潜意识。《北京法源寺》以谭嗣同之名成功地再度命名了“中国英雄”,以佛教蕴含支撑或曰刷新了其伦理意味和高度。同时颇具症候性地重叠了一个激进行动与非行动的选择:请袁世凯发兵与“谭嗣同不求救援”。于前者,尽管充满了历史的偶然,但在回望的视野之中,此举不论成败,都无异于行动所成就的非行动;于后者,舍生取义——以一己之躯承担历史命运,同时成就了(政治)非行动之(伦理)行动。在那一历史时刻,也是在舞台的再现之中,谭嗣同正是在自觉与不自觉之间将自己成就为一个可以填充多义的能指。如果考虑到今日,在后冷战之后的世界上,几乎所有包含群众动员于其中的社会运动(左翼之如反全球化抗争,右翼之如各种民粹集结)都带有符号学展演的性质,那么,此文本间的行动与非行动、政治与伦理意义及诉求的叠加与相互消解,便十分意味深长。与之相对,则是《琅琊榜》中充满了时间/情节链上的(政治,毋宁说权术)行动和实践。然而这行动却是名副其实的置换/“对倒”,其行动所成就的是对既存制度的保全与加固。由《琅琊榜》这部多层面上的流行文化文本显现的保守主义选择,或许更为真切地表达了在文化想象中社会性政治动能的萎缩或消失。
五、镜中女侠
文化政治表达更繁复、更曲折的或许正是电影《刺客聂隐娘》。片名主角聂隐娘无疑是影片的视觉与意义中心。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她的“形体和视线轮番占据着影片的主导位置”[5]89。然而,在影片的叙事结构中,聂隐娘却始终是某种结构性的冗余,是一系列三角关系中“多余”的一角。在影片角色的情感关系中,首先是田元氏/田季安/聂隐娘(窈娘)的关系式,而聂隐娘显然在前史中已然出局。而在剧情的展开中,则是胡姬/田季安/田元氏与胡姬/田季安/聂隐娘(窈七)间的交错、重叠;于前者——宠妃与主母之争,聂隐娘无疑是十足的局外人,于后者,胡姬与聂隐娘(窈七)间的相互认同,无疑是自怜性的投射与错认。在此,或许真正占据意义中心三角关系的是王后嘉诚公主/聂隐娘(窈娘)/道姑嘉信公主。如果说,“青鸾舞镜”(“罽宾国王得一鸾,三年不鸣,夫人曰:‘尝闻鸾见类则鸣,何不悬镜照之。’王从其言。鸾见影悲鸣,终宵奋舞而绝……”)令孤绝遗世、形影相吊这一关于孤独与镜像的主题潜在地贯穿了整部影片,那么,有趣的是,这一隐喻或曰意象却先在地隐含裂隙。因为在剧本的设置中,嘉诚、嘉信是一对孪生姐妹、且由同一位演员扮演——这在影片的视觉呈现中必然形成完美的镜像表达,然而,这组镜像性人物的设定,却不仅内在地抹除了孤独的主题,而且将政治潜意识里的冲突与选择内置于剧情核心:嘉诚/王后/殿堂之高映照着嘉信/道姑/江湖之远;嘉诚,对既存秩序的尊重与护卫,映照着嘉信,对现世统治秩序的蔑视与“剑道无亲”。而剧中聂隐娘所置身的意义张力,正在于作为两姐妹间争夺的价值客体与主人公认同选择间的主体位置。此间,更为有趣的是,嘉诚、嘉信尽管分置殿堂与江湖,尽管选择成为秩序卫士或世外高人,但她们的意义与位置的确立,却同样参照着影片之元社会的秩序,只是路径不同:前者倾心维护,后者暴力修订。也可以说,前者维护的是现实中的统治逻辑;后者捍卫的则是理想秩序。毋庸赘言,或许这正是“侠”这一前现代中国社会与文化中独特的功能角色的位置与意义。如果重提与美国西部片的类比,两者间或对应着一组经典角色设置:警官与牛仔,既是对手,更是互补:前者苦心经营,后者法外执法,其症候性的意义正隐现着美国历史的双重真相与叙述:移民的历史,白人垦殖者的故事与殖民的历史,殖民者暴力杀戮与掠夺的纪录。而“侠”——某种前现代中国文化想象中近乎独一无二的个体独行而神秘(尽管无疑仍隶属于江湖社会、门派、师徒秩序),事实上则充当着某种王权秩序之裂隙的填充物。影片中,准确地说,是在影片的前史中,聂隐娘是一个在嘉诚与嘉信的意义位置间流动或传递的主体/客体。前史中,聂隐娘无疑曾深深认同嘉诚公主,后者曾承诺与期盼聂隐娘成为她的继任者,但终在权力利益原则下将其抛弃,因而为嘉信掠去。故事开启便是嘉信将其还回,由外部重归内部。在唐传奇的原作里,“师傅”及其掳人行为并无阐释或出处,归来的聂隐娘始终是个外人或异类;而在电影中,她却最终皈依正统,以不尽人意的现实秩序为上,成就了嘉诚的遗志,背叛并自绝于嘉信。剧情的逆转,令主角最终在文本中获取了意义的结构位置:聂隐娘才是对镜起舞之青鸾,而嘉诚是她的镜中像,或者说,因剧情中聂隐娘的最终抉择,嘉诚与嘉信间的对称镜像关系被阻断,维护秩序与法外之法的互补功能被扬弃或搁置,聂隐娘终于成了嘉诚期盼的、自己的镜中之像。对应着聂隐娘/阿窈之为剧中人物关系中的冗余,嘉信及其指称的社会功能位置,则由此成为意义结构中被弃的冗余。在这一意义指向上,尽管聂隐娘最终叛出师门,却仍将自己重叠于嘉信的结构位置上:以自我放逐成就了社会性的放逐。
或许是在不期然间,《刺客聂隐娘》回归了中国电影独有的亚类型电影:神怪武侠片的源头,重现了曾占据银幕与叙事中心的功能角色:女侠。不同的是,在中国电影史之初——女侠形象占据绝对中心和压倒优势之际,那个自天外仗剑而来、锄强扶弱、匡扶正义,而后飘然仗剑而去的女侠,其社会文化的功能意义在于创生现代意义上的个人;而女侠作为巾帼英雄/刀马旦的变奏,却在这一叙事模式间,实践着历史性的后撤:以基督教为底色的现代性别秩序开始曲折地替代、置换前现代中国的阴阳/权力秩序。而在此,聂隐娘的自我放逐/遭社会放逐,所逐出的却是侠/刺客/法外执法的内在威胁,同时也自我放逐/放逐了现实秩序之下或之内的、对理想秩序与正义的执着。甚至,聂隐娘作为剧情结构中的绝对冗余,间或在社会潜意识的层面上,意味着类似社会位置或想象位置的消失。
六、结语
于笔者,这组文类各异、生产与接受层面不同的文本,间或显现为一组重要而有趣的社会文化症候群,其中突出的文化症候:无论是伦理主体/主题置换政治主体/主题,还是“动作片”的非行动化,抑或主人公的“匿名”与能指的漂移之舞,与其说勾勒出某种坐标参照下的文化地形,不如说显影了某种张力下的悬置与漂浮。这幅文化地形图,与其说是再度标识了今日中国、今日世界的坐标,不如说,其症候意义所在显影了既有坐标系的失效、含混或错位。或需再次提及的是,于笔者,此间的张力不仅是出自文本自身的叙述逻辑所显现的诸多变形、扭结甚或悖谬,而且无疑出自全球化时代的世界情势与中国的国际角色及内部情境的结构性投影。于是,有无尽奢靡间的低回,有似纵深深广的闭锁,有快节奏“剪辑”间的“呆照”,有大步前行时的离散和迷失。
当新技术革命再度赋予现代文明冲顶的动能,能源危机与生态灾难所标识的此期文明的透明穹顶却同时迫近;当中国开始在赢回“中国时间”并开始参与主导世界时间,种种历史目的论的时间却正纷纷碎裂,我们必须再度确认方向与方位,我们必须去获取或创生新的坐标。200年来,中国社会变革与社会革命的动力及目标正是“赶超”已创生或赢回世界意义上的“中国时间”。如今,彼岸已至、未来亦临,新的中国动力与目标是否已经确认?且不论,承诺了无穷发展的欧美现代主义,早已遭到了全面的挑战,多重危机中泥足深陷;即使现代世界仍拥有着深远的未来纵深,中国,作为第一个跻身全球资本主义前沿的非西方大国,作为一个被20世纪多重革命所更生、所造就的国家,加入对世界未来的构想、规划,我们原本可以、也必须为自己、为世界提供别样的路径、别样的可能。
[1](美)汉娜·阿伦特:《论革命》,陈周旺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
[2](法)托马斯·皮克提:《21世纪资本论》,巴曙松等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年版。
[3]Slavoj Zizek.LivingintheEndTimes,Verso: Rev Upd edition , April 18, 2011.
[4] 网友的译文:《齐泽克论<美人鱼>、<琅琊榜>和<疯狂动物城>》,http://www.wtoutiao.com/p/14cz548.htmlhttp://www.wtoutiao.com/p/14cz548.html.
[5] Nick Brown.TheRhetoricofFilmicNarration, Umi Research Pr , March 1982.
责任编辑 吴兰丽
特邀栏目编辑 王 庆
Reference System and Cultural Topography
DAI Jin-hua,
BeijingUniversity
The aim of this paper is to scrutinize and reflect on the symptoms and cultural topography represented by three particular texts, stage play?Martyrs' Shrine: The Story of the Reform Movement of 1898 in China(directed by Tian Qinxin, 2015), TV series & Online Novel?Nirvana in fire?(2015), and the award-winning film The Assassin?(directed by Hsiao-hsien Hou, 2015), although these texts stand against different mechanisms of production and reception. Starting from the replacement of political subjects by ethical subjects, games of signifiers and non-action, and the mirror images of swordswoman, we will redefine or even rebuild the social-cultural reference system, in the new context of globalization and the rise of China. In addition, this paper will acclaim that nowadays the primary challenge of cultural studies is not only mapping societies from reading realities in cultural texts, but also inquiring and challenging the established reference system and conventional thinking.
reference system; cultural topography; martyrs’ shrine; nirvana in fire; the assassin
戴锦华,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2017-04-10
I06
A
1671-7023(2017)03-0000-08
主持人语:本期为戴锦华新近思想和系统把握戴锦华思想的专题研究。一篇为戴锦华最新撰写的关于全球化时代,我们该如何重新确定新的社会文化坐标的文章;另一篇是对戴锦华电影、文化批评思想发展脉络进行系统评述的文章。前者选取了三个迥异的文本:话剧《北京法源寺》、电视剧/网络小说《琅琊榜》和电影《刺客聂隐娘》,分析了文本突出的文化症候:伦理主体/主题置换政治主体/主题、“动作片”的非动作化、主人公的“匿名”与能指漂移,并指出该症候的意义与其说再度标识了今日中国、今日世界的坐标,不如说显彰了既有坐标的失效或错位。因而提出今日文化研究面临的挑战是,不仅是通过文化、文本事实形绘社会,而且是质询并挑战既有的坐标系统与思维惯性。后一篇论文作者是彭万荣和王雪璞,他们从西方电影思想的引渡人、关注电影文本的批评家和以电影为媒介反思历史与当下的文化学者三重身份出发,评析了戴锦华的电影批评思想转换的内在逻辑。
栏目主持人:蒋济永,华中科技大学中文系/中国当代写作研究中心教授;王均江,华中科技大学中文系/中国当代写作研究中心副教授
——论女性主义视域下电影《刺客聂隐娘》的改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