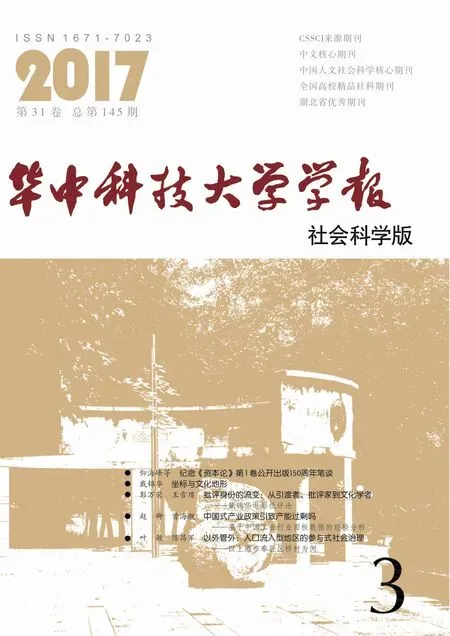《资本论》如何证明了唯物史观
□白刚
《资本论》如何证明了唯物史观
□白刚
作为“政治经济学批判”,《资本论》揭示了唯物史观所“唯”之“物”不再是旧唯物主义抽象的“自在之物”,而是具体的商品、货币和资本等“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物及其背后所掩盖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绝不是天然的、普遍的、永恒的和非历史的,它必然会随着生产方式的变革而逐渐走向消亡。正是《资本论》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发现“剩余价值”而揭开了资产阶级压迫和剥削无产阶级的“历史秘密”,真正把“唯物主义”和“历史”结合了起来,既历史性地解释了资本主义的历史命运,又历史性地解释了共产主义的历史前途,从而实现了对“历史之谜”的“政治经济学解答”。
《资本论》; 唯物史观; 政治经济学批判;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剩余价值
自马克思主义问世以来,一直争论不休的就是马克思创立的“唯物史观”问题。对此,美国的悉尼·胡克曾明确指出:“在马克思的全部理论中,最受人误解的,要算是唯物主义的历史观了。”[1]97而作为马克思主义的伟大继承人,列宁也曾指出:《资本论》的问世表明,唯物史观不再是一种假设,而是转化为一种被科学证明了的原理;如果认真阅读了《资本论》,还说找不到唯物主义,那将是十分“可笑的怪事”[2]163。那么,到底该如何理解马克思的唯物史观?《资本论》与唯物史观又是何关系?特别是《资本论》究竟如何“证明了”唯物史观?这些正是本文尝试回答的问题。
一、《资本论》何以是“唯物的”
唯物主义是和唯心主义相区别而言的。表面上看,唯物主义关心的是“物质”,唯心主义关心的是“精神”,二者是根本对立的,但实际上,这里的“物质”和“精神”都是抽象的概念范畴,二者在思维方式却是根本一致的,都是一种非此即彼的本体论思维方式。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作为一种“新唯物主义”,反对的就是这种“旧唯物主义”。所以,《资本论》作为唯物史观的体现和证明,它所关注和研究的“物”,决不再是从前的旧唯物主义只是从客体的或直观的形式去理解的与人的感性活动无关的“抽象物”,而是与人的现实生活实践密切相关的“具体物”,也即铺天盖地、无处不在地游荡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商品、货币和资本。但在古典经济学这里,商品、货币和资本都是天然的“自在之物”,而《资本论》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却是要把它们变成人为的“为我之物”:“当物按人的方式同人发生关系时,我才能在实践上按人的方式同物发生关系。”[3]190所以,《资本论》绝不是就物而言物,而是要揭示使物成为“物”——商品、货币和资本——“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物”的背后所掩盖的人与人之间的真实社会关系。这才是《资本论》作为“新唯物主义”之“新”所在。其实,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作为一种“新唯物主义”,并不是最早在《资本论》中提出和论证的。早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及其《导言》中,马克思通过批判黑格尔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关系的颠倒问题,就初步提出了唯物史观的问题;后来又在《神圣家族》中通过“对法国唯物主义的批判的战斗”而得到了进一步阐述;而真正第一次明确地提出和阐释唯物史观的,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论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和唯心主义的观点的对立”。但正如恩格斯所言:这部著作“已写好的部分是阐述唯物主义历史观的;这种阐述只是表明当时我们在经济史方面的知识还多么不够。”[4]266在此意义上,正是由于“经济史方面的知识”的欠缺,马克思此时对唯物史观的阐释还是相对抽象而不具体、不深刻和不彻底。弥补这一缺陷的,正是马克思后来为之牺牲了健康、家庭和幸福的作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巨著《资本论》。这也正实现了马克思自己所主张的到政治经济学中去解剖“市民社会”的夙愿。为此罗素指出:马克思的唯物主义是一种特殊的唯物主义,和18世纪的唯物主义毫无共同之处;当他谈到“唯物主义历史观”时,他只是强调产生社会现象的“经济原因”,而从不强调“哲学的唯物主义”[5]7。
由此可见,在《资本论》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视野里,唯物主义的“物”不再是17和18世纪启蒙主义者对物理学或生理学的规定性上的“物质”,其本质内容必然是作为最广义的社会范畴出现的“商品”——充满了形而上学的微妙和神学的怪诞的“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物”:“商品形式在人们面前把人们本身劳动的社会性质,反映成这些物的天然的社会属性”,而实际上,它们只不过是人们之间社会关系的外在反映[6]89-90。因此,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借以伪装成为物或者物与物之间联系的过程,这是导致人们不能认识我们生活于其中的社会真面目及产生“拜物教”的根本原因。如果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还像从前的唯物主义一样,只是作为一种抽象的世界观的表白的话,那么它就和唯心主义并无二致了。所以说,作为马克思唯物史观的真正对象和出发点的,绝不是所谓的“物质”这一抽象实体,而是作为社会关系体现和表征的“商品”及其完成形态的“货币”和“资本”。对于这一问题,恩格斯早在为马克思1859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写的评论中,就曾明确指出:归根到底,经济学研究的绝不是物与物之间的关系,而是人与人、特别是阶级与阶级之间的社会关系;由于这些关系是一种看不见的抽象存在,因此,它们必须借助于物的载体表现出来。虽然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有时也会意识到这种联系,但在整体上他们并没有克服这种外在表象及其束缚,而是陷入到拜物教的漩涡之中。这种联系对于整个经济学的伟大意义,正是马克思第一次揭示出来的,从而使这个最难的问题变得如此简单明了,甚至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现在也能理解了[7]604。这才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本质意义和他实现的“政治经济学革命”之所在。
关于唯物史观的本义,恩格斯曾明确指出,唯物史观始终强调,物质生产以及与其相适应的交换方式,是划分阶级和区分不同社会制度的根本基础,因此,要真正揭示社会演变和政治变革的最终原因,就必须到生产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以及特定时代的经济活动中去寻找,而不应当到人们对永恒的正义和真理的日益增进的认识和头脑以及有关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8]547。在此意义上,《资本论》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就是唯物史观的具体运用和体现,而《资本论》也就是凝缩和精华版的唯物史观。通过《资本论》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而对资本主义经济问题的分析,马克思发现资本主义是社会关系“整体物化”的社会,物化不仅产生于头脑中,更产生于真实的社会关系中。这是一个被普遍化的商品拜物教所控制和折磨的人与物颠倒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人们看到的只有“物”而没有“人”。所以,只要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还存在着,物化和拜物教即使被揭穿,也不会被消灭;而只有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这一物化和拜物教得以产生的温床,才能彻底消灭物化和拜物教。
作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资本论》,力求用唯物史观这一客观、科学的方式在政治经济学中分析和解剖资本主义。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中对资本主义的解剖,并不是出于革命热情和对被蹂躏、被压迫者的同情,简单地对一种特殊形式的经济组织发泄他的义愤;他也不是被个人恩怨、物质匮乏或精神创伤所驱使。马克思力求发现资本主义的客观运动规律——《资本论》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而要找到这一规律,就必须把握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一“物质总体”[9]9。这才是《资本论》作为唯物史观所“唯”之“物”的独特的根本意义所在——“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7]591更进一步说,作为唯物史观的《资本论》所“唯”之“物”,就是马克思自己在《资本论》第一版的序言中所强调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
二、《资本论》何以是“历史的”
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奠基人的卢卡奇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就是“从历史的角度”科学地考察时代,不仅看到时代的外在现象,而且也看到那些比较深层的实际推动事件的“历史的动力”[10]306。但资本主义的总体和推动力不能被资产阶级科学粗糙的、抽象的、非历史的和肤浅的范畴所考察和把握,因此,“历史唯物主义首先是资产阶级社会及其经济结构的一种理论”[10]312。也就是说,历史唯物主义就是从历史的角度考察资产阶级社会及其经济结构,而这正是《资本论》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所做的工作,即《资本论》作为唯物史观的“历史性”之所在。在《资本论》这里,生产方式既是马克思建构历史唯物主义的支架,也是揭开历史之谜的钥匙。马克思认为,决定社会历史前进的真正力量,既不是神,也不是自然,而是人类的生产方式。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断然地批判了以往的旧唯物主义,指责它们忽视了自己所提出的唯物主义观点同历史过程的关系:过去的自然唯物主义排除了客观的历史过程,每当它们从自然领域进入到社会领域之后,那种潜在的和抽象的意识形态就充分地暴露了出来[6]429。以此来看,一切旧唯物主义的“唯物”都缺乏历史性视野,在它们那里,“唯物主义”和“历史”是彼此分离的,作为旧唯物主义的集大成者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代表。而《资本论》正是由于使唯物主义和人类历史有了新的关联,所以才科学地阐释和证明了唯物史观。
事实上,早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就指出和责难所谓的“批判的批判”——黑格尔左派无视物质生产而错误地解释历史:“批判的批判”以为,只要它把工业和自然科学以及人对自然界的实践关系和理论关系排除在历史运动之外,它就能——哪怕只是初步达到对历史现实的认识;同时,它也以为不需要把某一历史时期的生活本身的直接的生产方式认识清楚,它就能真正地认清这个历史时期。在他们看来,历史的诞生地是“天上的迷蒙的云兴雾聚之处”,而不是地上的“粗糙的物质生产”[3]350。它们虽然反对黑格尔对历史所做的思辨阐述,但在本质上,它们与黑格尔哲学又是一致的,都是物质生产与历史的脱离,都是一种马克思所批判的非批判的唯心主义和非批判的实证主义。
同样,正是由于物质生产与历史的这种脱离,古典经济学家往往把商品、货币、资本、分工、工资等资产阶级的社会关系的体现说成是永恒不变的范畴,而根本没有、也无法向我们解释这些社会关系得以产生、运动和发展的历史过程[3]598。但在《资本论》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视野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作为创建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基石,绝不是永恒的、普遍的,而是历史的、发展的。在马克思看来,与手推磨相适应的是封建社会,而与蒸汽磨相适应的是工业资本家社会,所以人类社会必定会随着生产方式的改变而改变。人类社会的生产方式大体可分为原始的、奴隶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这几种“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而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就是这一“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中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不过在马克思看来,由于资本自身所固有的内在矛盾,它在大力发展生产力的同时,又将遇到自身不可克服的内在界限,从而推动自身走向瓦解和灭亡,届时,人类社会将会进入到一个更高阶段[7]592。也是基于此,在《资本论》的序言中,马克思强调: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史的过程。但在古典经济学和庸俗经济学这里,它们却认为只有两种生产方式:一种是人为的、暂时的,如封建社会的生产方式;而另一种是自然的、永恒的,如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方式。于是,以前是有历史的,现在再也没有历史了[3]612。在这里,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们实际上是不自觉地在现实经济领域中坚持和论证了黑格尔思辨哲学在概念领域关于“历史终结论”的观点。但在《资本论》这里,马克思却深刻地揭示出“劳动产品的价值形式”绝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社会发展到特定阶段的产物,因此,建立在这种特殊形式上的资产阶级生产方式也必然是一种特殊的、具体的、历史的生产方式,如果将其指认为一种永恒的自然形式,必将抹杀价值形式、商品形式以及与其相适应的资本关系的特殊本质[6]99。以此来看,正是《资本论》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才把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基本形式,表述为社会关系的一种特殊形式,这种形式只是在物质生产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上出现,而绝不是人类社会普遍永恒存在的自然形式,它必将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最终走向灭亡。如马克思所言,这种关系本身是许多次经济变革和一系列陈旧的社会生产形态灭亡的产物,它既不是一切历史时期所共有的社会关系,也不是自然史上的关系,而是已往历史发展的结果,因此,它也必将随着历史的发展而走向终结[6]197。所以说,正是《资本论》的“历史”唯物主义才真正实现了对资本主义历史的终结。也正是在此意义上,卢卡奇才一针见血地指出:“承认历史唯物主义,对资产阶级来说简直就意味着是自杀。”[10]307
在《资本论》这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性和非自然性体现为自身的局限性和矛盾性:在生产力的发展中,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必定会遇到一种同财富生产本身无关却相伴而行的限制,这种特有的限制证明了它在一定阶段上同财富的进一步发展发生冲突,证明了它不是财富生产的绝对的生产方式,反而是它的局限性以及它的仅仅过渡的和历史的性质[11]270。为此,马克思才会指出“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它必将为新的社会生产方式——共产主义所取代。因此,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科学分析,是《资本论》证明唯物史观的柱石。正是《资本论》才能深入物与物背后的社会关系,探明作为社会历史之根本体现的“社会经济形态”——一定生产关系总和——这个概念及其发展是“自然历史过程”,否定和推翻了那种把社会历史看做“机械的个人结合体”,可按政府意志或者说按长官意志和社会意志发展的,甚至可以随便改变和偶然产生的观点,从而第一次把社会学(历史唯物主义)放在科学的基础之上[2]163。所以说,《资本论》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直率而鲜明地提醒资产阶级及其辩护士们,资本主义本身就是历史的产物,就像它过去产生一样,将来终有一天会走向灭亡。它要表明资本主义为什么和怎样通过它自己的发展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的社会创造了经济的、物质的和社会的前提。《资本论》就是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历史命运和共产主义历史前途的科学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
三、《资本论》:历史之谜的“政治经济学解答”
《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作为马克思终生战友的恩格斯曾盖棺定论地指出,马克思一生有“两大发现”: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而《资本论》正是这“两大发现”的最完美结合和体现。一方面,在《资本论》中,“实际的经济关系,是以一种完全新的方式,即用唯物主义方法进行考察的”[12]244,因此“马克思的经济学说,是把历史唯物主义应用于价值、价格和利润这些‘神秘东西’的产物”[1]154;另一方面,正是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其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批判性分析,《资本论》才揭示出了“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从而证明了唯物史观的真理性和现实性。实际上,这是一个“双向”的建构过程,唯物史观的原则与方法成为马克思《资本论》的经济学革命话语的中轴,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具体深入又使唯物史观发生了巨大飞跃[13]554。在根本而重要的意义上,《资本论》运用唯物史观对资本主义经济运动规律的揭示和把握,并不是为了赚钱和发家致富,而是为了否定和批判古典哲学家和古典经济学家共同坚持的“历史终结论”,进而揭示和回答“历史之谜”,为无产阶级的觉醒和解放开辟可能性道路,从而为以每一个“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更高级的社会形式——共产主义建立现实基础[6]683。所以说,正是《资本论》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所实现的唯物史观的伟大“哥白尼式革命”,使经济学研究由“物”转向了“人”,才揭开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神秘面纱而回答了“历史之谜”,证明了唯物史观是科学的原理。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阐发的经济学理论,直接继承和受益于古典政治经济学:“我的价值、货币和资本的理论就其要点来说是斯密-李嘉图学说的必然发展。”[6]19但这一发展却不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的直接延伸和变形,而是借助唯物史观对其进行的彻底的批判性超越。这一超越的根本标志,就是在古典经济学“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对“剩余价值”的揭示和发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主要功绩之一,就是在劳动价值学说的基础上,探讨了利润、地租等价值的分割,并把价值的起源问题从流通领域转到生产领域。但是,古典政治经济学家都没有也无法提出“剩余价值”这一完整的独立范畴,他们都只是对剩余价值的各种具体转化形式,如利润、利息、地租等进行了不同程度的研究,根本不能揭示剩余价值的实质及来源,而这是一切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都犯的错误。正如马克思批评的:李嘉图从来没有考虑剩余价值的起源,在他看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天然合理的社会生产的“自然形式”,而剩余价值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自带的、固有的东西;他只是在劳动生产率中寻找决定剩余价值量的原因,而不是在其中寻找剩余价值产生和存在的根本原因;不过对这个问题,李嘉图学派也只是回避,而没有解决;因为他们实际上具有“正确的本能”,懂得过于深入地研究剩余价值的起源是非常危险的“爆炸性问题”[6]590。但对于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回避的这个非常危险的“爆炸性问题”,却成了马克思的《资本论》最为关注和竭力解决的核心问题——通过剩余价值的发现揭露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殊运动规律和资本自我增殖的全部秘密。为此,在《资本论》第一卷出版前夕(1867年8月24日)致恩格斯的信中,马克思就曾强调自己的《资本论》一书“最好的地方”有两点:一是提出了“劳动的二重性”,二是研究了作为一般形态的“剩余价值”[12]225。而“劳动的二重性”被马克思称为“批判地理解问题的全部秘密”,《资本论》正是抓住了这一“秘密”,才发现和揭示了“剩余价值”的秘密。在《资本论》第一卷出版后(1868年1月8日)致恩格斯的一封信中,马克思又明确指出:与过去的一切经济学一开始就把表现为利息、利润、地租等固定形式的剩余价值特殊部分当做已知的东西来加以研究相反,自己首先研究剩余价值的一般形式[12]250。正是通过对剩余价值的发现,马克思揭示出了资产阶级赚钱的秘密和工人阶级被剥削、被奴役的原因,从而使无产阶级第一次意识到自身的地位和需要,唤醒了无产阶级争取自身自由解放的革命斗志。为此,恩格斯也曾强调剩余价值的发现是马克思《资本论》“划时代的功绩”——像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一样,从前的社会主义者在经济学的领域中也曾在深沉的黑暗中摸索,但剩余价值问题的解决,使明亮的阳光照进了经济学的各个领域[14]212。可以说,正是剩余价值的发现,标志着《资本论》真正实现了“政治经济学”和“唯物史观”的“双重革命”。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通过对“劳动二重性”的揭示,发现和论证了剩余价值产生的具体来源。但剩余价值得以实现的真正机制,却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以,《资本论》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并不是为了分割财产,重新分配剩余价值,而是从根本上改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也即废除资产阶级财产权,彻底消灭私有制。“对我们说来,问题不在于改变私有制,而只在于消灭私有制,不在于掩盖阶级对立,而在于消灭阶级,不在于改良现存社会,而在于建立新社会。”[7]192对此,恩格斯在《论住宅问题》时也明确指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还存在的前提下,企图单独解决任何同工人命运有关的社会问题,包括住宅问题都是愚蠢的,解决办法只能是彻底消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最终由工人阶级自己占有全部劳动资料和生活资料[8]307。所谓由工人阶级自己占有“全部劳动资料和生活资料”,也就是实现财产权由资产阶级向工人阶级的变更——在联合起来的个人共同占有生产资料的基础上进行“合作生产”,以此最终消灭私有制、取消剩余价值。这种财产权的变更是一种新的生产方式的创建,而不仅是简单的“移交”。因此,只有当物质生产过程的形态,即社会生活过程作为自由联合的人之产物,处于人的有计划、有意识的控制之下的时候,它才会揭掉伪装和神化自己的神秘纱幕。但是,做到这一点却需要一定的社会物质基础或物质生存条件,而这些条件本身又是艰难的、漫长的发展史的自然产物[6]97。这一系列物质生存条件或一定的社会物质基础,实际上就是资本主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矛盾的不可调和:当劳动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的集中,发展到了同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当资本的垄断成了在这种垄断之下繁盛起来的生产方式的桎梏的时候;资本主义的外壳就要炸毁了,它的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6]874。正是《资本论》敲响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而在《资本论》这里,丧钟的敲响和“剥夺剥夺者”实际上就是在扬弃和超越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基础上“重建个人所有制”: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是对个人的私有制的第一个否定;但资本主义生产又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这种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否定的否定,是在对土地及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和协作的基础上,也即在资本主义时代的生产成就的基础上“重建个人所有制”[6]874。正是通过这种在资本主义时代的生产成就基础上“重建个人所有制”,作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资本论》才能在批判资本主义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彻底消灭私有制和剩余价值,为作为新社会的共产主义创造条件,唯物史观也才能得到科学的和现实的证明。所以,《资本论》通向的是自由之路,而绝不是奴役之路。
由此可见,《资本论》为理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提供了一个完全不同于古典哲学和古典经济学的彻底的、批判的历史唯物主义标准,它把隐藏在物与物背后的人与人之间的生产关系转化为现实的社会结构,正是这一“社会结构”为唯物史观的确立奠定了科学的基础:无论何时,我们总是要在直接生产者同生产条件的所有者的直接关系当中,为任何当时的独特的国家形式,为主权关系和依附关系的政治形式,从而也为整个社会结构,发现最隐蔽的秘密和隐藏着的基础[11]894。因此,我们只有根据这一结构和基础,才使人有可能以严格的科学态度去记载、分析和评价社会现象。在此基础上,列宁强调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就是《资本论》确证和建构唯物史观的“骨骼”:马克思完全用生产关系来说明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构成和发展,并又对与这种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上层建筑进行随时随地地探究,从而使唯物史观的“骨骼”有血有肉[2]162。所以说,正是《资本论》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和规律的揭示,才使唯物史观的实质内容得以真正完成。而一切唯心主义者,特别是黑格尔的历史哲学,虽然承认并揭示了历史现象发展的规律性,但它们不把这些现象的发展和演进看做是客观的自然历史过程,而是看做“无人身的理性”的自我演变过程。这是因为它们不善于把人类历史的形成和发展归结于物质资料的生产关系,却只限于从观念层面指出人类历史的思想和目的。而《资本论》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却由于把社会关系归结于生产关系,把生产关系归结于生产力的水平,才在现实的社会物质生产的基础上把社会形态的演进看做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进而揭示出了社会历史的真实客观本质。在此意义上,《资本论》作为唯物史观的任务不是要“描述真理”,而是要引导一项不知疲倦地揭露经济的真相、法律的真相、国家的真相和历史的真相的工作[15]187。《资本论》实际上就是通过揭示“资本之谜”而对“历史之谜”的“政治经济学解答”。在此基础上,作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资本论》把物质生产和“历史”有机结合了起来,它既超越了唯心主义,也超越了旧唯物主义,因而是真正的新唯物主义。《资本论》才是唯物史观的具体运用和真正完成。也惟此,我们才能理解列宁为什么强调《资本论》科学地证明了唯物史观。
[1]悉尼·胡克:《对卡尔·马克思的理解》,徐崇温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
[2]《列宁专题文集: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5]吴晓明:《当代学者视野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西方学者卷》上,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6]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9]欧内斯特·孟德尔:《〈资本论〉新英译本导言》,仇启华等译,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
[10]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
[11]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12]《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
[13]张一兵:《回到马克思》,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
[1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15]丹尼尔·本赛德:《马克思主义使用说明书》,李纬文译,北京:红旗出版社2013年版。
责任编辑 吴兰丽
How doesDasKapitalDemonstrate the Historical Materialism
BAI Gang,
JilinUniversity
As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Marx reveals inDasKapitalthat the “thing”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s “the new materialism” is rather the abstract thing in the traditional materialism than the things that are sensible and supersensory such as concrete commodity, money and capital, as well as the social relationship between individuals behind it. The capitalist social relationship is by no means natural, general, eternal or historical. In contrast, it will head for its doom gradually with the change of mode of production. InDasKapital, Marx has uncovered the secret of the oppression and exploitation of the proletariat by the bourgeoisie through “surplus value”, and claimed to “eliminate private ownership” by “reconstructing the personal ownership” in order to advance the proletariat’s liberation. InDasKapital, Marx has truly combined the materialism and history, which historically explained the historical destiny of capitalism and the future prospect of communism and unveiled “the answer in political economy” to the “riddle of history”. Therefore,DasKapitalhas not only made use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but also demonstrated it.
DasKapital; historical materialism;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capitalist code of production; surplus value
白刚,吉林大学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心暨哲学社会学院教授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资本论》哲学思想的当代阐释”(12&ZD107);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资本与自由:马克思政治哲学研究”(14BZX021)阶段性成果
2017-03-01
A714
A
1671-7023(2017)03-0008-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