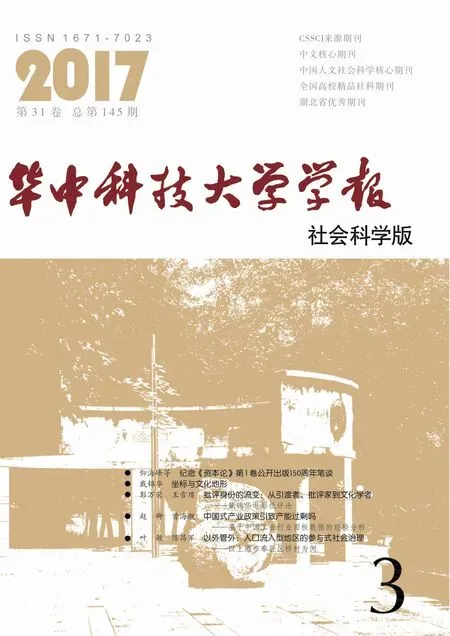《资本论》哲学思想研究:反思与重构
□仰海峰
《资本论》哲学思想研究:反思与重构
□仰海峰
自《资本论》出版以来,在国内外形成了诸多解释构架。或者把《资本论》看做经济学著作,或者将之看作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运用与证明,或者从劳动辩证法出发,对之进行主体性的解释。从历史与思想史的内在关系视角来重新解读《资本论》,可以看出《资本论》体现了马克思资本逻辑批判的哲学思路,这既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简单运用,也不是劳动辩证法所能涵盖的内容,更不是结构主义所理解的多元决定论。《资本论》虽然是一种带有“理想型”的理论构架,但它是对社会历史生活的抽象,在理论抽象的背后,是马克思对社会历史生活的批判理解。
生产逻辑; 资本逻辑; 历史性; 结构化
自《资本论》出版以来,对其哲学思想的研究一直是国内外学界关注的重要主题。在一百多年来的解读中,形成了各种不同的解释路径与不同成果。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的视角对这些成果加以清理,反思其深层的理论前提,这对于进一步推进《资本论》哲学思想的研究,无疑是非常重要的。
一、国外《资本论》研究的主要思路
1.马克思恩格斯晚年对《资本论》经济决定论解释的批评。自《资本论》产生之后,对它的解读就形成了一种带有经济决定论的解释框架。在这一研究中,一方面《资本论》中的哲学思想被简单地理解为一种经济主义或简单的经济决定论,另一方面《资本论》中的哲学又被理解为简单的利益决定论。在此基础上,结合马克思恩格斯相关论著,如《〈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序言》《哲学的贫困》《反杜林论》《费尔巴哈论》等著作,形成了对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框架的探索与研究。对这一解释模式的批评,是晚年马克思恩格斯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为了摆脱这一经济决定论的解释,恩格斯晚年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进行了众多的阐发,对把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奠基在利益观基础上的看法进行了批判。
当然,经济决定论的思路并没有因此而完全消解,并在第二国际时期得到了再现。但即使在那时,对《资本论》的讨论也是沿着不同的向度展开的,有些学者关注的是《资本论》中的经济决定论及其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确证,有些学者即从马克思的经济学思考出发,提出了对当时社会发展的新解释。
2.第二国际时期《资本论》研究的不同理论路径。在第二国际时期,对《资本论》哲学思想的研究体现出不同的关注点。一是经济决定论的解读思路继续得到张扬。将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相关论著中的哲学思想看做是经济决定论,这在以伯恩施坦为主导的一些学者中较为流行。在《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等著作中,伯恩施坦就认为马克思的观点已经过时,特别是缺乏有关道德的理论,这使得马克思主义已经无法解释当前的历史。正是根据这一判定,他提出要以康德的道德学说来补充马克思。与此相似的是,第二国际时期的一些学者虽然也认为马克思哲学具有经济决定论的特性,但并不是简单的机械决定论。在这方面的讨论中,拉法格的《思想起源论》、考茨基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库诺的《马克思的历史、社会与国家学说》等,都进行了深入的讨论。比如在拉法格的《思想起源论》中,他认为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就是经济决定论,但并不是简单的机械决定论,这种决定论关注经济与思想之间的联系;他力图以上述理论为指导,考察正义、善、神等观念是如何与当时的经济生活有着内在关联的。考茨基的《唯物主义历史观》以《资本论》和“序言”为基础,系统论述了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基本框架,“技术”“机器”等《资本论》中的许多问题,都被提炼为唯物主义历史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探索历史唯物主义基本理论构架的同时,这些学者还对将马克思还原为简单的机械决定论的观点进行了批判。如库诺就认为,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具有丰富的内容,他以“社会”与“国家”理论为基础,对马克思的思想进行了新的阐述,并指出马克思以科学的社会历史理论超越了思想史上的抽象的历史哲学理论。
二是关注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相关论著中体现出来的辩证方法。在《资本论》第二版“跋”中,针对当时德国学界完全无视黑格尔辩证法的状况,马克思说:“我公开承认我是这位大思想家的学生,并且在关于价值理论的第一章,有些地方我甚至卖弄起黑格尔特有的表达方式。辩证法在黑格尔手中神秘化了,但这决没有妨碍他第一个全面地、有意识地叙述了辩证法的一般运动形式。”[1]22受此影响,一些学者,如拉布里奥拉在《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等论著中就指出,马克思批判继承了黑格尔的辩证法,强调从事物自身的自我批判中来揭示事物的发展过程。在面对资本主义社会时,就是从资本主义社会的自我批判中论证社会主义的合理性。除了关注马克思思想中的批判性方法之外,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总体性考察方法也被诸多学者所强调。库诺就强调马克思关注的是对社会整体结构的考察。拉布里奥拉指出,历史唯物主义是要完整地考察历史及其总和。这些探索对丰富马克思哲学思想的方法论有其重要的意义。
三是揭示《资本论》的时代意义。在这方面的研究中,卢森堡与希法亭具有代表性。在《资本积累论》中,卢森堡结合马克思的资本生产理论,揭示出资本主义社会资本生产中内部市场(即资本主义市场)和外部市场(非资本主义市场)的内在矛盾,特别是消费不足的矛盾,指出资本主义生产的最终崩溃是不可避免的,帝国主义只是缓解危机的一种方式。虽然卢森堡的研究更具经济学的内容,但她对资本生产的空间区分,对后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空间理论起到了重要的影响;而其消费不足理论,不仅影响人们关于1929年经济危机的看法,而且直接影响到保罗·斯威齐的资本积累理论。另外,希法亭《金融资本》中关于金融资本的形成及其意义、金融资本与帝国主义的关系的论述,对于展现《资本论》的时代意义,也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
四是从资本主义历史发展出发,以《资本论》为指导,得出科学的帝国主义理论,实现了《资本论》的时代发展。在这方面的研究中,代表作是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及相关论述。在列宁的论述中,需要注意的是,他将马克思关于西欧资本主义理论,发展为以俄国为主要参照系的、带有本土特征的帝国主义批判理论,从而实现了理论研究与革命实践的有机统一。
3.前苏联、东欧《资本论》研究中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和辩证方法。前苏联、东欧关于《资本论》的研究,基于三个立足点:一是将《资本论》看做历史唯物主义在经济领域的运用所得出的结果。随着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模式的形成,学界普遍将《资本论》看做是历史唯物主义在经济领域的推广与运用,在这一层面,学界关注的是《资本论》中所包含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理论与方法。二是以晚年恩格斯关于马克思的两大发现的论述为依据,以剩余价值的发现为核心来论述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思想进程及《资本论》的创作史,揭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关系。三是探讨《资本论》中的辩证法思想。在《哲学笔记》中,列宁在研读了黑格尔之后曾感慨地说:“不钻研和不理解黑格尔的全部逻辑学,就不能完全理解马克思的《资本论》,特别是它的第1章。因此,半个世纪以来,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是理解马克思的!”[2]200列宁的这一论断直接影响了后来者的研究。这些研究中,出现了一些有分量的研究成果,国外学者如卢森贝的《十九世纪四十年代马克思恩格斯经济学说发展概论》和《政治经济学说史》、维戈斯基的《<资本论>创作史》和《马克思的一个伟大发现的历史》、罗森塔尔的《马克思<资本论>中的辩证法问题》、伊利延科夫的《马克思<资本论>中抽象和具体的方法》、缪勒的《通向<资本论>的道路》、罗斯多尔斯基的《马克思<资本论>的形成》、图舒诺夫的《<剩余价值理论>及其在马克思的经济学说中的地位》、巴加图利亚与维戈斯基的《马克思的经济学遗产》、阿法纳西耶夫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产生》等一批重要著作。虽然在总体思路上,这些研究并没有突破传统教科书的束缚,但在一些思想史问题的探讨上,却较为精细,并具有较强的文献资料价值。
4.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与《资本论》时代意义的阐发。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卢卡奇、柯尔施和葛兰西那里,都注重从哲学、政治经济学与科学社会主义的结合中来重新讨论马克思的思想,也是在这种结合中重新讨论《资本论》。在柯尔施的《卡尔·马克思》以及葛兰西的《狱中札记》中,他们都关注上述学科间的内在关系,并以之作为讨论《资本论》的方法论基础。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更是深入到哲学与政治经济学的内在关系之中,重新讨论马克思的哲学思想及其方法论意义。他关于“物化”、“资产阶级思想二律背反”的哲学讨论,都与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学分析相关联,并提出了马克思思想中的“总体性”方法、以历史辩证法超越物化意识的思路。在其后期思想中,卢卡奇以《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为哲学基础,通过解读《资本论》,形成了以劳动本体论为基础的哲学思考。
卢卡奇与柯尔施的研究直接影响了法兰克福学派。法兰克福学派虽然以批判理论闻名,但实际上早期的批判理论是以政治经济学研究为基础的。格罗斯曼关于帝国主义的研究、波洛克关于晚期资本主义的研究就是批判理论的经济学前提。在他们的讨论中,关注的不再是马克思时代的自由资本主义,而是列宁称之为“帝国主义”的资本主义,波洛克以“晚期资本主义”来称谓这一资本主义新阶段。在这个阶段,国家的组织与计划功能以及生产的技术化、组织化日益明显,并直接影响人们的意识与心理结构[3]。这是以社会生产与消费的组织化为新特征的资本主义,批判理论正是以这一社会历史为基础的。在《启蒙辩证法》中,正是对以现代科学技术为基础的、日益组织化的资本主义的批判,构成了重新审视西方启蒙哲学的历史基础。阿多诺在《否定的辩证法》中,在批判西方哲学的同一性时指出:这种同一性的基础正是普遍化的商品交换。另外,波洛克关于“晚期资本主义”的论断,经过曼德尔的《晚期资本主义》一书的中介,成为杰姆逊在《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中论述后现代主义的理论前提。
在20世纪50-60年代,随着《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研究日益热化,人本主义也成为当时研究的主导模式。在这一新的思潮下,《资本论》在一些学者眼中一改过去的经济决定论的解释,成为马克思的人本主义哲学的思想宝库。比如弗洛姆在《马克思关于人的概念》的著作中,《资本论》就是以人本主义为主要理念的。作为对此的反思,阿尔都塞通过重新解读《资本论》,出版了《读<资本论>》一书,对人本主义的解释框架提出批评,并指出马克思的哲学是一种科学的历史理论,在这一理论视野中,历史是一个无主体的过程。这些研究进一步打开了《资本论》的哲学空间。
20世纪70年代之后,沃勒斯坦的“世界历史体系”理论、阿明等人的“依附理论”、哈特与奈格里等审视全球化的“帝国”理论相继登台。虽然这些理论并不直接研究《资本论》,但对《资本论》的判定与思考仍然成为这些思想家的理论基础。他们都承继了马克思的生产理论,并将之作为讨论世界历史与全球化的理论基础,从资本生产的空间布局中揭示其统摄力。有的学者将《资本论》与当代思想结合起来,重新建构批判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理论武器,如德鲁兹与瓜塔里的《反俄狄浦斯: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症》[4]就将生产劳动理论与精神分析理论结合起来,揭示资本主义生产与精神分裂的内在关系;齐泽克在《意识形态的崇高对象》中则将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批判与拉康的精神分析理论相结合,重新讨论资本主义社会的压抑问题。有的学者如哈维,通过重新研究《资本论》中资本生产的空间结构,并结合现代社会与思想的变迁,提出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空间理论,对现代性提出了批评,其《希望的空间》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作。与此相近,杰姆逊以劳动为基础,通过对劳动与时间、空间的建构关系,来展现《资本论》的哲学。也有一些学者批评《资本论》中的生产劳动理论,认为以生产劳动为基础的历史唯物主义并没有摆脱资本主义社会的意识形态。鲍德里亚的《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生产之镜》就是沿着这一思路展开的。他认为,现代资本主义是以消费社会为主要特征的社会,符号消费已经成为资本主义社会合法性的基础,这正是《资本论》的生产劳动理论所无法解释的内容。
与上述思路同时展开的,还有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对《资本论》的重新研究,如爱尔斯特的《理解马克思》、罗默的《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分析基础》[5]和《剥削和阶级的一般理论》[6]、柯亨的《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个辩护》等,力图将现代经济学的微观分析方法引入到对马克思《资本论》等著作的研究中,对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阶级理论、社会主义等思想重新展开讨论,尤其是对正义思想展开分析。另外,一些生态学者如福斯特、奥康纳等,也从《资本论》等著作出发,重新揭示《资本论》的生态学意义。法国的调节学派则从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区分出发,即从福特主义与后福特主义的区分出发,通过分析雇佣劳动关系的变化,揭示资本主义弹性生产的自我调节能力,阿格里塔的《资本主义调节理论》[7]就是这一学派的奠基之作。这些研究从不同的方面,进一步拓展了《资本论》的哲学理论空间,同时也需要我们从理论深层上做出回应。金融危机之后,《资本论》研究再度兴起,《21世纪资本论》虽然与《资本论》已经大相径庭,但对于推进《资本论》的研究,还是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即MEGA2)的编辑出版,为《资本论》研究提供了新的材料。MEGA2的第二部分“《资本论》及其手稿卷”15卷24册即将全部出版,加上第三部分第8-35卷有关《资本论》的书信及第四部分第2-9卷有关《资本论》四个笔记的手稿的相继出版,为进一步研究《资本论》提供了文献基础。在西方学界,随着MEGA2的出版,一些学者提出了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对立问题,日本学者还专门列出恩格斯在编辑《资本论》第二卷、第三卷时是如何采用马克思的手稿、又如何改动马克思的手稿的,根据他们的统计,这种改动有近5 000多处,马克思与恩格斯对立的思想正是以此为文献支撑的。这些考证丰富了《资本论》的研究图景,但在国内外学界也产生了一些问题,这主要表现在:一是过分强调马克思《资本论》原稿与恩格斯修改稿差异,并由此提出马克思恩格斯对立论,对《资本论》的哲学思想的研究,并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二是在一些学者那里,形成了一种较为极端的看法,似乎过去出版的所有版本的《资本论》都已经失效了,有的甚至完全否定现有中文版的研究价值,从而以文献上的比较取代对《资本论》哲学思想的阐释,形成了一定程度上的MEGA2崇拜。这就需要我们对MEGA2的文献进行合理评价,防止陷入到无思想的文献复述中。
二、国内《资本论》哲学思想研究的内在逻辑
自1938年王亚南、郭大力合译的《资本论》出版后,国内的《资本论》研究拉开了序幕。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其研究的重点也存在着一定的变化。
1.新中国成立到20世纪80年代,主要是对《资本论》的结构、范畴、辩证法思想展开研究。1963年,王亚南、袁镇岳合作出版了《<资本论>讲座》,对《资本论》的结构、经济学理论及主要范畴进行阐释。1973年王亚南的《<资本论>研究》则较为详细地论述了《资本论》的结构及其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同时涉及历史唯物主义的主要思想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内容,且提到了列宁《哲学笔记》中关于《资本论》与辩证法关系的思想的影响以及前苏联相关研究的影响。国内的《资本论》研究同样非常关注其中的辩证法问题。如吴传启的《<资本论>的辩证法问题》(三联书店1963年版),力图揭示商品发展过程中的辩证法、资本主义社会产生过程中的辩证法,对《资本论》中的从抽象到具体的方法进行了深入的讨论。
2.20世纪80年代至今,《资本论》哲学思想研究的内在逻辑。这一内在逻辑体现在以下进程中。在上世纪80年代,人们开始突破传统教科书的框架,拓展《资本论》的理论空间。这包括对社会存在问题的重新探讨、社会有机体理论的提出与论证、生产力内涵的丰富与突破、科学技术对于社会生产的意义与作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法的重新思考、社会经济形态的再探讨、人的价值等。这些讨论极大地丰富了《资本论》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而不是简单地将《资本论》看做历史唯物主义的确证。这些讨论不仅体现为《资本论》研究的成果,也体现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层面的成果,同时也使学界意识到,基础理论研究与经典文献研究是无法分割的。
自上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到90年代,随着实践唯物主义的展开,对《资本论》的研究也随之发生了重要的变化。第一,学界开始将《资本论》看做一部“自洽性”的哲学著作,并开始从经济学与哲学的内在关系中去理解《资本论》。这是一个重要的视角转变和方法变更。在这一转变中,人们开始从经济学-哲学内在关系这一总体的视角去考察《资本论》,以展现《资本论》本身的哲学思想,而不是简单地将之理解为对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应用与证明。第二,从实践唯物主义与主体性出发重新理解《资本论》。在过去的研究中,人们关注得更多的是《资本论》中物质生产理论,以及物质生产过程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导致的社会革命。在新的视野中,上述思想虽然还处于背景之中,但学界已经关注到《资本论》中人的主体性思想、人的价值等内容,并从实践主体性出发,对商品社会、社会存在、社会形态、人的发展、社会发展等问题进行了新的探讨,形成了一批研究成果。这些成果虽然也受到国外相关研究的影响,但从问题意识来看,这些成果已经内含本土逻辑,是对中国社会发展过程的反思与前瞻。因为,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改革开放,推动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得人的主体性等问题走上了哲学的前台,在这个意义上对《资本论》展开研究,已经打上了本土的印记。
2000年之后,《资本论》哲学思想的研究再次成为热点问题。与实践主体性思路不同,新的研究更多从人的存在入手,更为关注人的存在状态的异化、沉沦,关注社会生活的拜物教,关注资本与现代性的共谋,从而对资本统治下的人的存在状态的物化提出批评。或者说,随着对资本理解的深入,人们已经意识到,原来所弘扬的主体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异化了,如何摆脱这种状态,真正实现自由王国,成为新的主题。可以说,这是对实践主体性理论的再思考,并力图通过重新阅读《资本论》建构一种新的构架。正是在这样的语境中,在21世纪之后,对《资本论》的存在论解读,成为许多学者关注的问题。
这些研究,从不同视角展现了对《资本论》哲学的不同理解,推动着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研究。这些成果,既有国外学术的影响,也有国内学者的努力。但从总体上来看,笔者更倾向于将这一思路理解为本土马克思主义哲学逻辑的建构。当然,这并不是说这些研究已经穷尽了《资本论》的哲学,学术的进展,总是存在于对前人成果的反思中,存在于新的探索中,以便打开《资本论》哲学的新的理论空间。
三、重构《资本论》哲学研究的理论前提
对《资本论》哲学思想的现有研究,形成了四种不同的解释构架:一是历史唯物主义扩展论,形成了经济决定论的解释模型,《资本论》被看成是历史唯物主义一般原理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应用与证明,这是自第二国际以来一直占据主导地位的解释思路。二是将《资本论》与《逻辑学》进行比较研究,揭示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及差异,从而陷入黑格尔的哲学逻辑中。三是以劳动本体论为基础的主体性解释构架以及对这种主体性进行再批评的存在论框架,这是自卢卡奇到国外马克思主义学者的主导解释构架,关注的是对人的异化的批判以及人的潜能的自由实现。四是阿尔都塞的“断裂说”,强调自《德意志意识形态》到《资本论》与早期人本主义著作之间的认识论断裂,强调《资本论》与主体性思想(阿尔都塞称之为人本主义)的对立,认为马克思以《资本论》中的成熟的科学历史理论取代了其早期的意识形态思想。这些解读模式展现了不同历史时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对《资本论》的不同理解,揭示了《资本论》中的丰富内涵,对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这些模式并没能从深层上揭示马克思思想的内在转变。从共同点上来说,这些模式都是以《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确立的物质生产理论为前提,或者拘泥于从物质生产出发的经济决定论意义,或者从物质生产的主体层面出发,形成了劳动本体论,强调人的主体性,并以此作为《资本论》研究的基础。在这些模式中,如果以《德意志意识形态》为界,几乎所有的模式都强调这一文本与《资本论》的连续性,这也成为马克思思想研究中的“共识”。
在笔者看来,1845-1846年马克思的哲学变革体现在两个层面:一是就哲学本身的逻辑来批判传统哲学;二是从社会历史生活出发来展示哲学的逻辑建构及其现实含义。比如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讨论意识形态的颠倒性时,马克思不仅揭示了青年黑格尔派在哲学理念上对社会历史生活的颠倒性理解,而且还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历史生活建构中的颠倒性,正是后者才是意识形态颠倒性的根源。这是《德意志意识形态》之后马克思的基本理念。正是上述两点才将马克思的哲学与传统哲学区别开来。传统哲学主要关注观念之间的逻辑关系,关注概念之间的运思过程,而对马克思来说,这种逻辑关系虽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揭示哲学与历史之间的内在关系,揭示哲学理念与社会生活之间的内在联系,将对传统哲学形而上学的批判,推进到对社会历史生活的批判,并从这种批判中反思形而上学,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要揭示哲学与社会历史之间的内在关系,揭示哲学的历史生成过程,就需要深入社会历史生活之中,在马克思的时代,就需要深入到对资本的结构、资本的运行过程及其特征的批判分析中。因此,《资本论》虽然是一种带有“理想型”的理论构架,但它是对社会历史生活的抽象,在理论抽象的背后,是马克思对社会历史生活的批判理解。正是在这个过程中,马克思揭示出资本主义社会的颠倒性存在,这种颠倒性存在,才是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资本拜物教的最终根源。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资本论》成为马克思哲学的代表性文本。
从马克思的思想发展过程来看,历史唯物主义的形成离不开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历史唯物主义体现为双重逻辑:即传统历史唯物主义所强调的生产逻辑与面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资本逻辑。《德意志意识形态》确立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生产逻辑,经过《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又称《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和《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等中介,在《资本论》中确立了资本逻辑。按照传统的研究,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是将历史唯物主义的物质生产逻辑推广应用到历史领域的结果,在这个意义上,《资本论》只是历史唯物主义应用于特定社会历史领域的结果,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证明,不具有独特的哲学意义。实际上,随着《哲学的贫困》中“历史性”思想的确立,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开始形成了面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双重逻辑,即生产逻辑与资本逻辑,前者以劳动本体论为基础,后者以资本的形式化结构为基础。经过《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等阶段,马克思逐渐意识到从物质生产出发并不能真正地剖析资本主义社会,只有从生产逻辑进入到资本逻辑,才能批判地考察资本主义社会,从而确立了资本逻辑,认识到在资本主义社会,虽然生产逻辑仍然是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重要内容,但它并不占据主导地位,不是生产逻辑决定资本逻辑,而是资本逻辑统摄生产逻辑。这也意味着,我们需要重新辨识生产逻辑与资本逻辑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的作用,并从资本逻辑出发重新展示《资本论》的哲学。
在马克思的论述中,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与再生产具有人类学的意义,它是一切社会存在的基础,资本主义社会也不例外。在这一维度上,任何能够促进物质生活资料生产的社会结构与社会关系形式,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与历史意义。这也是马克思评价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性标准。理解了这一点,我们就能理解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在讨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时,马克思常常先讨论物质生产的一般模式,并由此肯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意义。这正是生产逻辑在马克思理论中的具体表现。但需要引起我们注意的是,人类学意义上的物质生产逻辑并不足以说明资本主义生产的特性。如果说物质生产逻辑具有人类学的意义,那么这是就生产的一般抽象意义来说的,在这种抽象中,物质生产的具体社会形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构成物质生产的一般要素和条件,物质生产的结果体现为以有用性为取向的产品。物质生产的这些要素、条件与结果是一切社会物质生产都具有的特征,资本主义社会也不例外。但正如马克思所分析的,如果按照一般物质生产逻辑来理解资本逻辑,那么资本就会被还原为具体的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这时,劳动资料与劳动对象就成为剩余价值的来源,工人的劳动反而与剩余价值的生产没有关系。更为重要的是,当资本被还原为物质生产要素时,物质生产过程就离不开资本,如果没有作为资本具体化形态的劳动对象与劳动资料,生产还如何进行呢?按照这一逻辑,只要生产存在,资本就无法消除,斯密、李嘉图甚至将这一逻辑延伸到了原始社会,从而赋予资本以超历史的意义。李嘉图式的社会主义者也是根据这一逻辑,得出了不能消灭资本,但可以消灭资本家的结论。因此,面对资本主义社会,并不能简单地认为将历史唯物主义加以推广与运用,就可以得出《资本论》中的思想,而是要重新提炼出新的理论逻辑,以此作为理解《资本论》的枢纽,这正是资本逻辑批判的意义。
虽然生产逻辑具有人类学的意义,资本逻辑只是针对特定社会而提出的,但在资本主义社会,它们之间的关系却发生了颠倒,即不是生产逻辑统摄资本逻辑,而是资本逻辑在统摄生产逻辑。可以说,如果不理解资本逻辑支配下的生产过程,也就不理解人类学意义上的物质生产过程。因此,从生产逻辑到资本逻辑并不是历史唯物主义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应用与推广,而是历史唯物主义新的理论发展。1845年哲学变革只是发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第一重逻辑,即人类学意义上的物质生产逻辑及其哲学意义。这一变革的确是非常重要的,这是哲学视野的根本转变,没有这一转变,马克思就不可能真正地将视野投向社会历史领域。但对于马克思来说,其理论的根本主题是要批判分析资本主义社会,而一般生产逻辑并不能达及这一目标。从生产逻辑到资本逻辑的思想进展,不是一种理论的应用与推广,而是马克思理论发展过程中的新的质变。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不仅要关注生产逻辑及其相应的理论构架,更要关注资本逻辑以其对生产逻辑的统摄作用,以及从资本逻辑出发的哲学构架,这是我们今天重新探讨历史唯物主义时需要着力解决的问题。
在厘清了《资本论》的理论前提后,根据文章前半部分的讨论,从资本逻辑出发,对《资本论》中的哲学理念展开分析,这构成了后半部分的主要内容。资本逻辑体现为一个抽象化、形式化与结构化的过程,从而将资本主义社会结构化为一个不断更新的总体。对于马克思来说,一方面需要揭示这一逻辑的展开环节,另一方面需要对这一逻辑的总体进程及其在各个环节上的表现进行批判。对于马克思哲学的新的探索,需要同时在这两个方面展开,并从资本逻辑与生产逻辑的统一中进行历史性的分析。这要求我们,必须将《资本论》中的一些经济学范畴重新上升到哲学的高度,成为重新探讨马克思哲学的基本范畴,并通过这些范畴建构新的解释框架。对于马克思哲学思想研究来说,这是一个全新的课题。
[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宁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2]列宁:《哲学笔记》,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1990年版。
[3]Pollock. “State Capitalism: Its Possibilities and Limitation”, inTheEssentialFrankfurtSchoolReade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4]Deleuze, Guattari.Anti-Oedipus:CapitalismandSchizophrenia, Minnesota, 1983.
[5]Romer.AnalyticalFoundationsofMarxianEconomicTheor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6] Romer.AGeneralTheoryofExploitationandCl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7] Michel Aglietta.ATheoryofCapitalistRegulation, NLB, 1979.
责任编辑 吴兰丽
Contemporary Reflections and Reconstruction of the Studies onDasCapital’sPhilosophical Thoughts
YANG Hai-feng,
PekingUniversity
Lots of scholars at home and abroad have constructed many interpretation modes onDasCapital’sphilosophical thoughts since it was published. In these modes,DasCapitalis interpreted as either economic work or the application and justification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moreover, it is constructed as a work of subjectivity in terms of labor dialectic in contemporary western academia. In fact, these interpretations are fully one-sided. According to Marx’s definition,DasCapital, in essence, reflects the philosophical approach of the critique of capital logic. Although bearing an ideal theoretical framework,DasCapitalindeed embodies Marx’s method of “real abstract” based on the critical interpretations of social history.
production logic; capital logic; historicity; structuralization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重大基础理论问题研究”;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问题研究”(16AZX002)阶段性成果
2017-03-01
A714
A
1671-7023(2017)03-0001-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