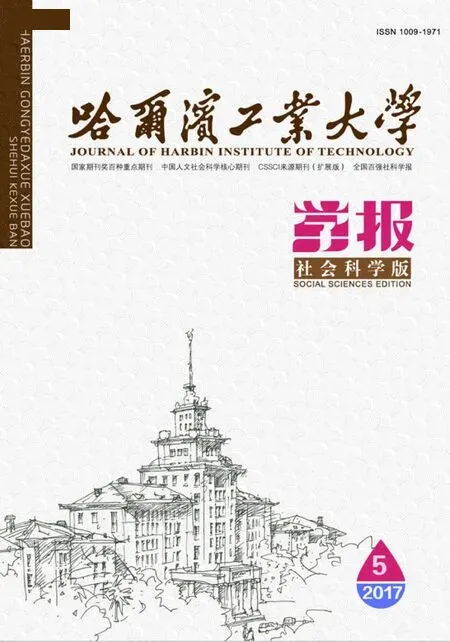接受与认同:琼瑶文学作品对两岸共通意义空间的建构
陈 致 烽
(1.福建师范大学 文学院 ,福州350007;2.福建师范大福清分校 文法学院 ,福州 350300)
接受与认同:琼瑶文学作品对两岸共通意义空间的建构
陈 致 烽1,2
(1.福建师范大学 文学院 ,福州350007;2.福建师范大福清分校 文法学院 ,福州 350300)
文学活动本质上也是一种传播活动,作家通过一定的媒介把文学作品内容所包含的信息、观念、态度或情感,传递给接受者。文学作品作为一种沟通的方式,具有跨越制度鸿沟、修复历史创痕的重要意义和功能。琼瑶文学作品蕴含的传统中华文化元素,契合两岸人民深层次的共同接受心理。从报纸刊物到电影电视,琼瑶文学作品因应媒介的变迁,在海峡两岸长时间大范围地传播,培育着广大的接受群体,进而构筑了一个共通意义空间,利于巩固两岸人民的文化认同。
琼瑶文学作品;海峡两岸;文学传播;文化接受与认同;共通意义空间
我国幅员辽阔,生活习俗、文化、血缘、语言等都有较大的差异,尤其是海峡对岸的台湾同胞,由于长时间的分治及社会制度的差异,在交流沟通中存在一定隔阂。尽管如此,两岸人民源远流长血脉文脉相连的事实是任何人都无法改变的,但只有持续的交流和沟通才能增进沟通和了解,求同存异。以文学作品为中介进行沟通交流也是一种可行的方式。文学作品作为一种沟通的方式,具有跨越制度鸿沟、修复历史创痕的重要意义和功能。20世纪后半期兴起的文化消费主义带动文化产业化、商品化,通俗文化和大众文化高歌猛进,使传统精英文化逐步退守边缘,海峡两岸皆如此。面对这种现状,本文选取那些在两岸都有广泛受众群体的通俗文学作品作为我们研究的切入点,从接受美学和传播学视角出发,将研究聚焦在两岸都有巨大阅读群体的琼瑶作品,说明琼瑶作品因应媒介的变迁,长时间在两岸传播和为广大读者所接受,探索其在构筑两岸共通意义空间的作用。
一、从小说到影视:琼瑶文学作品存在方式的变迁
传播学者麦克卢汉提出:媒介即讯息。意为真正改变人们行为和思想的,并非是媒介所承载的内容,而是媒介本身,一种新媒介的出现,是促成社会变革的重大甚至是决定性力量。任何文学作品都需要借助媒介传播给接受者,传播方式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文学生产方式和接受方式,进而改变人们对文学要素构成的认识。一般认为,现代意义上的文学出现于17世纪的西欧,印刷术应用和纸质媒介在这一时期开始普及,印刷术的出现,加快了文学作品的传播,因此传统意义上的文学传播载体主要为书籍、刊物、报纸等纸质媒介。在电子传媒时代,鉴于传播媒介对文学活动的重要影响,有学者对艾布拉姆斯以来的围绕文学四要素提出了质疑,进而提出了文学研究“五要素”的新研究范式,即认为“文学活动范式由作品、世界、作家、传媒、读者五个基本要素的整体结构和它们之间的动态关系构成。”[1]尽管该文学研究的范式还不大成熟,但传播媒介对文学的重大影响是毋庸置疑的,学者王一川认为:没有媒介就没有文学[2]。琼瑶的作品之所以能够持续近半个世纪在两岸流传,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是其文学作品的存在方式始终与媒介变迁密切相关。
琼瑶早期的作品都发表在文学刊物和报纸副刊等纸质媒介,后期的影视作品大都由其小说改编,它们之间存在着紧密的关系。基于电子媒介的影视作品可以说是纸质印刷作品的延伸,是小说在新的媒介载体的呈现。学者南帆说过:“不言而喻,今天的文学是生存于报纸、电影、电视以及互联网之中的文学。”[3]“这些新的媒体——电影、电视、因特网不只是原封不动地传播意识形态或者真实内容的被动的母体……它们都会以自己的方式打造被‘发送’的对象,把其内容改变成该媒体特有的表达方式。”[4]包括电视、电影、网络在内的新媒介,使文学形态的边界越来越模糊,2016年的诺贝尔文学奖颁发给美国民谣艺术家鲍勃·迪伦,也印证了文学存在形态的丰富性,琼瑶创作历经半个世纪,以各种不同的媒介形态呈现给受众。鉴于琼瑶及其文学改编作品的密切关联性,本文所提到的文学作品包括纸质印刷形态的作品和以电子形态呈现的影视作品。
在创作初期,琼瑶作品大都以纸质媒介呈现。20世纪60年代,琼瑶小说都是在《皇冠》杂志和联合报副刊上连载,前者为当时台湾地区影响力最大的流行文学刊物之一,后者为当时台湾文学的重要引领者,而身兼《皇冠》社长和“联副”主编的平鑫涛(两人于1979年结婚)对琼瑶非常赏识,积极地为琼瑶作品进行量身定制,安排策划了琼瑶几乎所有的作品在《皇冠》和“联副”出版发行,由此奠定了琼瑶长盛不衰的文学创作生涯。到1960年代后期,电影开始在台湾地区盛行,于是两人共同创立了电影公司,专门负责把琼瑶的小说作品翻拍成电影。自1965的《婉君妹妹》到1983年的《昨夜之灯》,总共近50部琼瑶小说改编为电影,在台湾的电影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台湾爱情文艺片的主流,成为当时少数能与风行的武侠片抗衡的电影,如1968年《第六个梦》在台北首映时,第二天,联合报以《第六个梦昨天首映受观众欢迎 每场都爆满》为题,报道了琼瑶电影受欢迎的盛况。1975年《一帘幽梦》创下台湾自产片三个月内上档两次的辉煌记录。进入80年代,电影行业普遍不景气,台湾地区自产片80%是亏损,但琼瑶改编的电影依然受到观众的欢迎,1981年上映的《聚散两依依》在春节第一档排第二名,《梦的衣裳》在青年档则是一枝独秀,高居自产片票房榜首,这两部电影在当时不景气的自产片票房中创造了一个神话。随后,她的改编电影也开始在华语地区热播。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电影行业不景气和电视机开始进入普通家庭,琼瑶的文学作品被改编拍摄成电视剧,其自制或授权拍摄的电视剧有24部。由于前期拥有广大的读者群,加上精良的制作团队,琼瑶小说改编的电视剧几乎都拥有超高的收视率。
进入21世纪,随着互联网的普及,网络逐渐代替了电视等传统媒介,成为年轻人最常用的交流空间。琼瑶也在网上设立了官方网站,在大陆用户众多的新浪网开通了博客,积极主动地在网络空间与读者互动沟通。尽管琼瑶于2007年关闭了博客,但随后琼瑶的读者专门开设了“琼瑶小筑”等专门供琼瑶作品爱好者交流沟通的空间,读者们在空间里分享对琼瑶作品的心得体会,网站又成为传播琼瑶作品的新渠道。
“现代传媒改造了我们的文学,全方位地改变文学的生产、传播与消费以及文学的再生产与再消费……传媒对文学的干预有了自觉意识。而这种自觉干预且生成,就会倚靠话语权、媒介法则等文化霸权迫使文学做出适媒性的改变。”[5]从纸质印刷媒介到电影再到电视剧,包括在网络空间流传,琼瑶作品始终与各种新媒介的变迁保持着密切的互动,以受众最欢迎的方式进行传播,让作品深入接受者的内心世界,不断延续着其作品的生命力。同时,琼瑶的创作从主题、情节结构到语言风格也在不断地变革。特别是90年代进入创作生涯的后期,她的作品大都为影视剧量身定制,影像化倾向极为明显,部分作品甚至是先由剧本拍成电视剧热播之后,再发行纸质印刷小说。如果从传统的文学批评视角来看,其文学价值大大不如前期,但这些不妨碍其作品在市场的接受度。
尼克·布朗认为:“电影和电视作为再现社会的主要传播媒介,对创造和确立各种社会成规与性别成规来说,是十分重要的。”[6]我国著名的导演、编导张骏祥更进一步说:“电影就是文学——用电影表现手段完成的文学。”[7]从印刷媒介到电子媒介再到网络空间,从台湾地区到祖国大陆再从祖国大陆回传台湾,近半个世纪以来,琼瑶的作品超越“浅浅的海峡”,在两岸中国人中回传穿荡,在琼瑶作品所构筑的爱情王国中产生了共鸣,拉近了不同地域的读者彼此的距离。
二、传播与接受:琼瑶作品在两岸的流传
文学活动本质上也是一种传播活动,其生产和传递的基本信息就是文学信息。“传播就是个人或集团主要通过符号向其个人或团体传递信息、观念、态度或情感。”[8]文学活动是人类的一种高级的特殊精神活动,作家通过一定的媒介把文学作品内容所包含着的信息、观念、态度或情感,传递给接受者。接受者并非被动地接受,而是对所接受到的文学信息做出相应的反应,从而影响作家的创作。姚斯指出:“在作家、作品和读者的三角关系中,后者并不是被动的因素,不是单纯的做出反应的环节,它本身就是一种创造历史的力量。”[9]
琼瑶1938年出生于祖国大陆,1949年迁居台湾,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琼瑶的创作一直持续到21世纪初,总共创作了60多部有影响力的作品。1963年7月琼瑶小说《窗外》发表,这部约20万字的小说在《皇冠》杂志一次性刊完,读者反应极为热烈,于是紧接着出单行本,单行本小说依然畅销,成为当时出版界罕见的现象。此后,《窗外》多次在台湾重印出版,在台湾地区销量超过百万,成为皇冠出版社50多年来最畅销的书籍。此后琼瑶推出的小说在台湾地区持续畅销,如1964年《烟雨蒙蒙》在联合报连载后,出现了每天大清早一大批背着书包的女中学生聚集在联合报社门口,迫不及待地要在上学前等到当天的小说,可见,琼瑶小说当时畅销的盛景。其作品《烟雨蒙蒙》和《庭院深深》在1986年被评为台湾地区十大畅销书,琼瑶本人也名列“最畅销的十大女作家”。
琼瑶作品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在台湾地区及海外地区受到读者广泛欢迎,但两岸交流始终处于隔绝的状态,直到1976年大陆“文化大革命”结束,大陆实行改革开放政策,1979年元旦,全国人大发表《告台湾同胞书》,表达了希望两岸和平统一的愿景,提议两岸开展学术文化等方面交流。随后,两岸开始了沟通交流,两岸文学的交流也得到恢复,台湾的文学作品也逐步被引入祖国大陆,其中琼瑶小说迅速在大陆受到读者的喜爱,1982年《海峡》杂志刊载了琼瑶小说《我是一片云》,之后几年里,从边远的云南到最北的黑龙江,有多达20个以上的出版社出版了琼瑶的作品,加之猖獗的盗版书籍,琼瑶的小说迅速红遍大陆。1986年,上海电视台与书店联合举办的“我最喜爱的十本书”评选活动,1985年出版的三本琼瑶小说《我是一片云》、《船》、《几度夕阳红》竟全部入选[10]。根据1986年11月13日《文学报》报道,广州地区约有70%的学生读过琼瑶小说。在2001年“全国国民阅读与购买倾向抽样调查分析”中,琼瑶在最受读者喜欢的作家中名列第四。
不仅仅琼瑶的小说在海峡两岸广受欢迎,20世纪80年代后,由其小说改编的电影电视剧也受到了受众的欢迎。1986年播出的《烟雨蒙蒙》收视率高达42%,到1986年10月上旬落幕后,整体收视率高达48.7%,这种收视盛况是空前的,在台湾地区至少有800万的观众观看了该剧。1987年推出的《庭院深深》可称为琼瑶电视剧的巅峰之作,在台湾地区的收视率超过六成。
1989年,台湾当局开放影视业赴大陆取景拍摄,琼瑶立刻召集剧组前往大陆拍摄电视剧,开启了两岸合拍剧时代,之后琼瑶几乎所有的电视剧都在大陆拍摄完成。20世纪90年代开始,两岸开始合拍电视剧,以拍古装剧为主,如1993年的《梅花三弄》,就同时在两岸热播,接着是1998年的《还珠格格(一)》,在海峡两岸都创下了极高的收视率,在大陆该剧的全国平均收视率47%,最高62.8%,成为史上收视率最高的电视剧。在台湾岛内的收视率达到17.%,排名首位。之后的《还珠格格》第二部,在此创下了收视新高。2007年推出的《又见一帘幽梦》,初期在台湾的收视不是很理想,但在大陆却屡创新高,在18个城市的总收视率突破30%,在结束的当日,创下了约8.2亿名观众收看的记录。随着电视剧的播出,在台湾的收视率也在稳步地提高,最后也获得破2%的不俗成绩。2013年,琼瑶再次推出了《花非花雾非雾》,仍然在两岸取得不俗的收视成绩。笔者利用在校开讲座的机会,对2016级(大都出生在1996年)来自不同专业的学生进行调查,调查显示8成以上的学生看过琼瑶的电视剧,可见其在号称“网路原住民”(1995年后出生)的年轻人群中仍然具有极高的认知度。
无论是初期在台湾还是后期在大陆,琼瑶作品的接受都经历了曲折的历程,20世纪60年代,琼瑶作品在台湾受到了文学界的严厉批判,其中以李敖的批判最为尖锐。他认为《窗外》不健康,是背着“孝顺服从”这个沉重的文化包裹,对中国青年为害甚大。家长和学校也把她的作品当作“毒草”来严防死守,不让青少年看她的作品。同样的情景发生在大陆的80年代,家长、老师们觉得琼瑶言情小说没文化,没有教育意义,会耽误孩子的功课,要加以封杀。相对于台湾,大陆批评界显得包容,但在肯定之余,大都认为其作品存在着“肤浅”、“公式化”等局限。尽管如此,一个不争的事实是:琼瑶作品以爱情为主题,深受读者的欢迎,她的读者群遍布华语世界,同时也被翻译成韩、日、泰、越、英、荷等多国语言,琼瑶开创了一个属于她的时代,其作品在两岸持续几十年受到接受者的欢迎,培育着广大的接受群体,影响着海峡两岸几代人,被称为“爱情教母”。其所产生的影响已经超越了其文学本身,更是成为一种社会现象,台湾学者林芳玫就主张从文学社会学的角度对琼瑶作品进行研究,透过琼瑶作品的传播与接收,我们可以从一个侧面把握两岸社会的发展演变和交流互动。
三、从接受到认同:琼瑶作品传播构筑共通的意义空间
传播是一种信息共享活动,传播成立的主要前提之一,是传受双方必须要有共通的意义空间,即传受双方对传播中所使用的语言、文字等符号含义的共通的理解和大体一致或接近的生活经验和文化背景[11]。同样,“文学场域和传播场域一样,都依靠共同的语言和游戏规则来决定游戏权利的存在与否、传播的可能与否。”[12]在文学作品中,作家常常运用语言通过某种具体的形象来表现与之相似或相近的观念和思想,或寄托某种特定的情感。
琼瑶在大陆出生,在颠沛流离中度过了童年,后移居台湾,其对中国人和中华文化有着深深的认同,如琼瑶所言:“中国人爱自己的祖宗,爱自己的土地,爱自己的故乡,爱自己的家园,有强烈的‘山河之恋,故国之思’”[13]。 值得关注的是,尽管琼瑶作品也被翻译成多国语言,但琼瑶作品的流传区域主要是在以海峡两岸为核心的华人圈,对于琼瑶作品在两岸长时间地持续地为两岸民众所欢迎,我们仅仅从文学的价值层面很难解释这一现象,如伊格尔顿所言:“文学犹如‘杂草’,它的存在取决于‘园丁’的喜好;‘园丁’的喜好不是完全任意的,制约文学‘园丁’做出判断的是居于‘深层’的‘那些感觉、评价、认识和信仰模式’即意识形态。”[14],这里的“深层”,就是琼瑶作品中无论是小说还是影视都呈现出来的浓厚的中华文化根脉和两岸受众的深层次心理认同。
琼瑶作品中传统中华文化元素利于两岸人民接受和认同。琼瑶说过:“我喜欢中国的古代文化,我是在唐诗中长大的,我写书常借鉴诗词的形式和意境,常常不露痕迹地把中国的‘根’的东西,借现代语言传达出来。”[15]出生于书香门第的琼瑶,受过正统的中华传统文化教育,有着深厚的中国古典文学修养,对于通俗言情小说家而言,其古典文化的基础知识尤为突显。且不说其小说的题目很多都有古典意蕴,如《在水一方》出自《诗经·蒹葭》、《碧云天》和《寒烟翠》都出自范仲淹的《苏幕遮》、《秋歌》与李白的浪漫情怀有关。而更加引人关注的是琼瑶作品源流自传统中国小说的表现手法,以古典诗意的呈现方式,追求故事的完整性。《烟雨蒙蒙》以女主角陆依萍作为小说的叙述者,文本开头写“细雨”“水珠”“街灯”“芭蕉树”等物象,在这烟雨蒙蒙的景象中人物出场了,也为全文奠定了沉郁阴冷的格调。小说的结尾依然是回归到这些景物,尽管物是人非,但首尾相照,强调故事情节整体性的表现手法与传统小说如《水浒传》《红楼梦》《金瓶梅》等一致。同时,琼瑶对于这些景物是予以诗意呈现的。如“细雨”是绵绵密密的,“水珠”是晶莹而透明的、“芭蕉树”上的水滴是“一滴又一滴地”从那阔大的叶片上滚下来,“街灯”是在细雨里高高站着的、“光线”是孤高骄傲而又昏黄的……小说最后,女主人公听着“雨滴打着芭蕉的声音,那样潇潇的、飒飒的,由夜滴到明”,一夜无眠追忆着破碎了的梦……“碧潭上小舟一叶,舞厅里耳鬓厮磨”,想起何书桓爱唱的那首歌:“最怕春归百卉零,风风雨雨劫残英。君记取,青春易逝,莫负良辰美景,蜜意幽情!”此境与汤显祖《牡丹亭》中的“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相似,也可看到唐诗《金缕衣》“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之影。琼瑶把古典诗歌与小说中创造意境的手法相融洽,营造一个诗情画意的纯净情调,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很容易被此情境所吸引,从而进入这一婉转清丽的意境之中。
琼瑶作品为两岸民众共同接受的根本原因是两岸人民内在的深层次心理认同。在其带有自传性质的处女作《窗外》第十一章中,写女主角江雁容落榜后对于生命的探求,“我从何处来,没有人知道!我往何处去,没有人明了!”此语出处虽与西方文化的起源有关,却应合了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大陆对于西方文论中提出问题的思索,也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无”与“有”、关于“常”与“无常”的思想命题相契合,或者可用佛教“从来处来,到去处去”的用语来解释这一命题。琼瑶紧接着写江雁容突然想起其父说的话,中国最后一个王朝——清朝的顺治皇帝曾当过和尚,当时写的一个偈语中——“生我之前谁是我,生我之后我是谁?”江雁容奇怪着“谁是她,她是谁?”她紊乱的思绪想到李白的“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可自己又不是李白,“我”却等于“无用”,她的不稳定的思想又跳跃到《圣经》中的“虚空的虚空,一切都是虚空”……这一长串有关自我的追问与寻求,中西方文化自然的衔接与融合,在西学东渐的过程中,与此期受传统文化熏陶的中国读者对于宇宙恒常问题的思索相应合,达到与中国大陆民众共同深层的心理文化认同,因而受到两岸民众的欢迎。
余 论
当今全球化时代,一个民族的成员往往分居各地,流动性增大,覆盖全球的大众媒介就成为维系各个成员之间关系、保持民族身份认同的重要途径。美国学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认为:民族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是由特定的文化所建构的。他认为小说、报纸、收音机和电视这些大众媒介能传播将民族成员相互联结的共同意象和共同想象,尽管这些民族成员散布在不同地区,相互之间从未谋面,素不相识,而共同的想象和共同的意象像一根纽带,将他们形成一个共同体。利奥·洛文塔尔指出:“文学是基本象征和价值观的特别恰当的载体,能够对不同的社会团体——从不同的民族、时代到特殊的社会亚群体和关键时刻——产生凝聚力。”[16]文学作品是文化的重要载体,作为想象的一种重要方式对构建民族共同体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琼瑶的文学作品,历经半个世纪,借助各种媒介进行传播,在海峡两岸长盛不衰,构筑一个可行的共通交流话语空间,利于两岸的交流互动,巩固两岸的文化认同。
进入20世纪末期,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大陆经济不断发展壮大,市场经济体制逐步确立,普通大众对文艺作品的需求也日趋多元化,大众文化市场也不断地壮大,仅仅从港台引入的电视剧已不能满足大陆人民的消费需求。同时,政府也对文化体制进行改革,文化生产也逐步走向市场化,随着文化生产能力的不断加强,大陆的文化机构、企业也具备了生产和创新能力,在影视制作方面,大陆的电视剧生产不仅数量大大增加,质量也在不断提高。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期,琼瑶通过与湖南卫视合作,把影视拍摄制作的重心放在大陆,陆续推出了《还珠格格》(共三部)、《又见一帘幽梦》、《花非花雾非雾》等作品,这些作品大都由琼瑶亲自参与,两岸演员共同出演,在两岸同时上映。两岸源远流长的一致的语言、文字和大体相同的文化背景,为两岸人民的交流搭建了便利之桥。传播既是一种过程,也是一种系统,传播活动是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制约,海峡两岸打破了人为的制度性藩篱和不断缩小的经济差异之后,由单向输出到双向交流,文学作品得以其本真的艺术品质开始在两岸流传回荡,引起两岸读者的共鸣,构筑共通的意义空间。
传播是双向的交流和沟通,有效的传播是受到各种因素制约的。尽管琼瑶文学作品几十年来在海峡两岸拥有广泛的接受群体,但进入21世纪,同样是琼瑶的作品,在大陆仍然能够取得较高收视率的电视剧,在台湾地区却不甚理想。如2003年暑期同时在两岸三地上映的《还珠格格Ⅲ天上人间》,在大陆,收视率虽然不如前两部那样火爆,但仍然占据各中心城市同时段收视第一;而在台湾地区,却遭遇惨败,据AC尼尔森的数据,《还珠3》在台湾地区的收视率是1.98,开播的八天时间内每天都有不同情况的下降。对此,琼瑶发出“台湾已经不要我了”的感叹。可见,因为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制度的差异,两岸人民之间对中华传统文化的接受和理解都有相当大的差异。我们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文化传播交流随着社会环境的变迁而改变,要实现两岸人民的文化认同,还需及时把握台湾民众的心理需求,跟随时代的发展变化,审时度势,有效地开展两岸人民的交流,才能取得积极的成效。
[1]单小曦.论五要素文学活动范式的建构[J].社会科学研究,2009,(1):166.
[2]王一川.文学理论[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111.
[3]南帆.理论的紧张[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3:95.
[4][美]J.希利斯·米勒.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还会继续存在吗? [J]国荣,译.文学评论,2001,(1):135.
[5]张邦卫.媒介诗学:传媒视野下的文学与文学理论[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176-177.
[6][美]尼克·布朗.电影理论史评[M].徐建生,译.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94:149.
[7]张骏祥.电影的文学性讨论文选[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85:63.
[8][美]丹尼斯·麦奎尔,斯文·温德尔.大众传播模式论[M].祝建华,武伟,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5.
[9][德]H.R.姚斯,[美]R.C.霍拉勃.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M].周宁,金元浦,译.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24.
[10]周振东.中学生何以“热”琼瑶[J].社会,1986,(6):25.
[11]郭庆光.传播学教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44.
[12]林淇瀁.场域与景观——台湾文学传播现象再探[M].台北:印刻文学生活杂志出版有限公司,2014:133.
[13]琼瑶.剪不断的乡愁[M].北京:作家出版社,1988:198-200.
[14][英]特雷·伊格尔顿.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M].伍晓明,译.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19.
[15]覃贤茂.琼瑶传奇[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340.
[16][美]利奥·洛文塔尔.文学、通俗文化和社会[M].甘锋,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2.
Abstract:Literary activity is essentially a kind of activity of dissemination that the writer conveys the information, ideas, attitudes or emotions contained in the content of literature to the receiver through a certain media.As a way of communication, literary works are of great significance and function in bridging the system gap and repairing the scars of history.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elements behind Qiong Yao's literary works meet the psychology of deep common acceptance of people on both sides of the Strait.With the changes of media, from newspapers and magazines to film and television, Qiong Yao's literary works achieve large-scale dissemination for a long time in the Cross-Strait, which cultivates awide accepting group, then construct common meaning space, and finally strengthen the cultural identity of people on both sides of the Strait.
Key words: Qiong Yao's literary works; Cross-Strait; literary dissemination; culture Acceptance and identification;common meaning space
[责任编辑:郑红翠]
Acceptance and Identification:Qiong Yao's Literary W orks on Construction of the Cross-Strait Common M eaning Space
CHEN Zhi-feng1,2
(1.College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Fuzhou 350007,China; 2.College of Cultural Media and Law, Fuqing Branch of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Fuzhou 350300,China)
G206.3
A
1009-1971(2017)05-0088-06
2017-06-28
福建省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影视传播与民族共同体研究”(2013B163)
陈致烽(1973—),男,福建永泰人,副教授,博士研究生,从事影视传播、文学传播、华文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