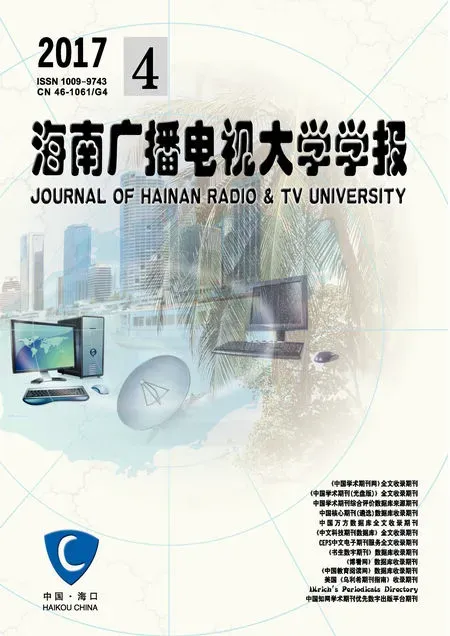对刑法实质解释与形式解释的批判性分析
童云峰
(华东政法大学 法律学院,上海 200042)
对刑法实质解释与形式解释的批判性分析
童云峰
(华东政法大学 法律学院,上海 200042)
刑法条文的规定不可能是完全明确和具体的。所以,就需要对刑法条文进行解释。对于刑法条文的解释我国刑法学界有不同的观点并形成较大争议。以实质解释论和形式解释论的争锋最为激烈。实质解释论过度强调社会危害性,在解释刑法之前就已经存在主观判断和目的,导致解释的结论具有较大恣意性。形式解释论过分拘泥于刑法条文的字面含义,不能适用客观社会变化,结论的合理性易被人质疑和诟病。因此,无论实质解释或形式解释都不应该被完全提倡。故有必要对实质解释和形式解释的不足和合理性进行系统的批判性分析,以期完善我国刑法解释观。
实质解释论;形式解释论;解释位阶;罪刑法定
最近几年形式解释论和实质解释论在我国刑法学界产生激烈的交锋,双方学者粉墨登场,互相撰文批驳争相亮出自己观点,但遗憾的是我国这种形式解释论和实质解释论的争端并没有形成学派之争,往往是一种观点的输出和口舌之争,这种现象对我国刑法学发展并没有起到积极作用,甚至会产生某些负面效应。不可否认,我国形式解释论和实质解释论的观点重合部分是相当多,一些所谓的争论可能是由于个人的立场或误解所导致。形式解释论和实质解释论的争论往往会被学者上升到形式刑法观和实质刑法观的对立中来,不免让人感觉是扩大了矛盾范围,也是夸大形式解释论和实质解释论的差别,缺乏发现它们之间共同点的眼光。形式解释论主张忠诚于罪状的核心意义,有时候甚至仅仅是自己熟悉的法条含义*陈兴良:《形式解释论的再宣示》,《中国法学》2010年第4期,第28页。。实质的解释论则重视情势的变化与法律适用的目的,主张根据变化了的情势与目的考量来发现法律规范的意义、目的*[德]阿图尔·考夫曼,温佛里德·哈斯默尔著:《当代法哲学和法律理论导论》,郑永流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158页。。两者最起码都坚持罪刑法定原则。任何一方的学者都在试图告诉大众己方观点之合理性与贬低对方观点一文不值。不可否认,从哲学角度来看形式和实质根本就不是一对范畴,形式和内容是一对范畴,现象和本质是一对范畴,所以从这一角度而言,形式解释和实质解释的争论根本就是伪命题。
一、对实质解释论的认识及思考
(一)实质解释论者总是坚持刑法解释以保护所谓的法益为指导
首先,对于法益这一概念,理论界还存在不同观点。法益理论是德国学者李斯特所大力弘扬的,李斯特认为,法律所保护的利益即法益,法益就是合法的利益*李斯特:《德国刑法学教科书》(修订译本),徐久生译,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6页。。笔者认为:法益不过是我国学者照搬其他国家刑法学说所运用的概念或范畴,其存在比较玄乎,不具体不明确,容易被解释者所利用以达到其想要的法律效果。而且法益和我国传统的客体区别又有多大呢?笔者认为:法益不过是一些学者用来博人眼球的舶来品。
其次,有些学者认为“任何一个用语都可能有两种以上含义,对任何一个法条都可能作两种以上解释,如果没有解释方向和目的,就不可能对构成要件作解释*张明楷:《实质解释论的再提倡》,《中国法学》2010年第4期,第50页。。”笔者不禁想问,你在解释之前都已经存在方向和目的,那你的解释还会不朝着你的方向和目的吗?也就是说解释之前存在主观判断最终就代替了真正意义上的刑法解释。而这主观判断就来自于实质解释论所坚持的所谓法益概念。因为他们认为刑法的目的就是保护法益,将法益视为犯罪构成中的核心要素,是刑法条文中客观要素与主观要素所描述的中心概念。毫无疑问,法益就变成实质解释论进行任意解释的挡箭牌。似乎让人以为没有法益的目的就不能对刑法条文的含义进行合理阐述和解释,无论是坚持四要件的实质解释论者还是坚持三阶层的实质解释论者,对构成要件的解释都是以保护法益为指导的解释。2016年5月3日,知名网络写手“水木然”发表《比承包医院更黑:莆田人承包了中国90%的寺庙!》一文,在互联网引起轩然大波。该文发布后4小时,阅读量突破10万次,一天后,上千个微信公众号转载该文章。在相关机构撰文驳斥后,5月18日,杭州市警方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将“水木然”刑事拘留。此消息一出,部分网民表示不解:为何认定“水木然”构成寻衅滋事罪?笔者不禁想问,为了维护社会稳定和网络秩序将网络上一些传播、转载、语言暴力等行为定为寻衅滋事罪真的恰当吗?难道不违背我们对寻衅滋事罪根据罪刑法定原则所进行的理解吗?固然,该行为具有社会危害性,但以寻衅滋事罪追责的这种实质解释不可避免的让人将其与类推解释相联系。法益目的论者认为同一法律条文如果其所保护的法益发生了变化则对其解释也必将发生变化,笔者认为:如果将该原理作为一项解释的原则则可能违背刑法条文的安定性和国民的可预测性。
(二)实质解释论者始终坚持社会危害性、处罚必要性、合理性理论
实质解释论者认为对违法构成要件的解释,必须使得行为的违法性达到值得科处刑罚的程度;对责任构成要件的解释,必须使行为的有责性达到值得科处刑罚的程度*张明楷:《实质解释论的再提倡》,《中国法学》2010年第4期,第50页。。笔者不禁想问这里的“值得”是怎样得出的?很明显,这里的值得是经过主观的价值判断,是脱离了罪刑法定原则的形式侧面的主观判断,易言之,对具体的行为在没有寻找与其相一致的刑法条文之前就已经对其进行了价值判断,主观判断优于罪刑法定,这是罪刑擅断思想的残留。实质解释论者认为如果进行形式解释会不当地扩大刑罚处罚范围将本不具有社会危害性或处罚必要性但却被刑法条文规定的行为纳入刑罚处罚范围,并且列举了将向多人借款用于生产经营的行为,认定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将乘坐交通工具携带用于自己吸食的少量毒品的行为认定为运输毒品罪;将3人以上秘密的淫乱行为认定为聚众淫乱罪等例子来支持进行实质解释的必要性,笔者认为上述案件如果严格按照罪刑法定原则本身就不构成犯罪,之所以定罪是由于司法工作者在办理案件时候本身就没有严格遵循罪刑法定原则,对犯罪构成存在认识错误或者对刑法第13条的但书规定没有认识清楚,有权力滥用嫌疑。
实质解释论者认为当某种行为并不处于刑法用语的核心含义之内,但具有处罚必要性和合理性时,应当在符合罪刑法定原则的前提下,对刑法用语作扩大解释。这里实质解释论者还是先从主观判断出发,主观上先入为主,先认为具有处罚必要性,然后再去刑法条文中寻找是否有对应条文,如果没有完全一致对应条文再去寻找相近条文,为了避免滑入类推解释的泥沼,实质解释论者就必须要对相近条文中的法律名词进行所谓的扩大解释,这样就是他们所说的既坚持了罪刑法定原则又克服了类推的魔咒,一个完整的犯罪解释链就这样形成,很难让人认为这样会缩小刑罚处罚范围。实质解释论者用前田雅英的公式来证实自己的观点,即解释的实质的容许范围,与实质的正当性(处罚的必要性)成正比,与法文通常语义成反比*前田雅英:《刑法总论讲义》,东京:东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78-79页。。笔者个人比较反感学者拿外国人的学说来证实自己的观点。第一,外国学者的学说也只是他们自己的观点并不代表普遍真理;第二,外国学者的学说适用于该国的法治环境,而中国的法治有自己的特点,外国学说不一定适用;第三,用外国学者的学说来证明自己的观点恰恰证明自己的观点没有创新是照搬照抄罢了,更体现了对自己观点的不自信。总之,中国学者应该拥有自己独立的价值判断。实质解释论者总是强调单纯运用罪刑法定主义的形式侧面是不充分的,形式判断也是不足够,而是强调“值得”科处刑罚,即处罚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值得”的标准来自何处?这个标准本身是形式的还是实质的?这个“值得”是由司法者来判断,还是由立法者在立法时决定?笔者认为:这几个问题恰恰是实质解释论者所不好回答的,因为所谓的合理性和必要性本身就是主观的,既然是主观的就可能因人而异,你认为有处罚的必要性,而我却认为用刑罚处罚没有任何意义,所以主观判断就导致实质解释具有随意性。以天津的赵春华案为例,2016年10月12日晚,经营了两个月气球射击摊的51岁赵春华,连同另外12名“同行”被警方带走。12月27日,天津河北区法院以“非法持有枪支罪”,率先判决赵春华有期徒刑3年6个月。如果实质解释论者认为赵春华的行为根本不值得处罚,就会通过对枪支作缩小解释认为该气枪根本不属于刑法上的枪支而予以处罪。如果有实质解释论者认为赵春华的行为值得处罚,并以具有社会危害性为理由,对该枪支作扩大解释,认为属于刑法上的枪支,构成非法持有枪支罪。可以看出实质解释具有较大恣意性。
(三)实质解释论者很难摆脱与类推解释的关系
罪刑法定原则已经深入我国刑法之中,类推解释已经被明确禁止,虽然某些学者依旧坚持有利于被告人的类推解释但也不能改变类推解释被我国刑法所摒弃的命运。大多实质解释论者之所以坚持实质解释就是认为刑法的规定不可避免地存在漏洞,因此需要通过实质解释来填补漏洞。有的学者认为可以通过类推以外的解释方法填补的漏洞都不是真正的漏洞,只有通过类推解释才能填补的漏洞才是真正的漏洞。笔者认为,我国刑法作为成文法存在漏洞是不可避免的,如果实质解释都可以填补这些漏洞那实质解释不就是万能工具了吗?很明显,实质解释并非能够解决所有刑法漏洞问题,否则万能的实质解释就不可避免地包含类推解释。这里又回到类推解释与扩大解释的区别,两者的区分界限至今还没有一个明确定论,是刑法学永恒的课题。所以,实质解释论者主张通过扩大解释来填补漏洞就一定可以与类推解释划分界限吗?显然这是非常困难的。我国刑法第247条规定了暴力取证罪,刑法条文规定的本罪对象只能是证人,对于暴力逼取被害人陈述的行为,能否适用本规定理论界存在争议,形式解释论者主张通过新的立法予以补充,实质解释论者认为完全可以通过扩大解释将被害人的陈述解释为证人证言,这难道就很容易摆脱类推解释的嫌疑吗?将抢劫国有档案的行为解释为抢夺国有档案罪也能轻易说服形式解释论者吗?显然并非如此。如果抢劫行为可以解释成抢夺行为,那刑法直接就规定一个抢夺罪就好了,何必又多加一个抢劫罪?实质解释论者坚持对违法构成要件的解释,必须使行为的违法性达到值得科处刑罚的程度;对责任构成要件的解释,必须使行为的有责性达到科处刑罚程度。这正如杨兴培教授所认为的:“这是把行为先套进来后,再作创造性的解释使该行为符合法律的规定,这种理论与实质解释论倡导者曾经倡导学习的大陆法系三阶层构成模式应该以该当性为第一要件的原理发生了严重冲突,从中我们也看到了倡导者在这里所表现出来的无规则思维轨迹*杨兴培:《刑法实质解释论与形式解释论的透析和批评》,《法学家》2013年第1期,第36页。。”实质解释论者对构成要件进行解释和判断时总是脱离行为本身而侧重于从社会危害性角度来进行解释;在进行实质解释时,每一个解释者不可避免地受到其所处的社会地位、生活命运、政治地位等影响,往往不能进行价值中立的判断。
(四)实质解释论的处罚范围
实质解释论者指责形式解释会不当扩大刑罚处罚范围,形式解释论者则指责实质解释会不当扩大刑罚处罚范围。至于哪一种解释会真正扩大处罚范围呢?笔者认为,每一种解释都会有扩大处罚范围和缩小处罚范围的情形,不能一概而论地认为某种解释就会完全扩大处罚范围,而且对于绝大多数案件而言形式解释论和实质解释论的处罚范围是一致的。以抢劫罪中的冒充军警抢劫为例,实质解释论者认为军警人员显示自己真实抢劫比非军警人员冒充军警抢劫的社会危害性有过之而不及。故从实质角度将冒充进行扩大解释为“假冒或充当”,从而把军警显示真实身份抢劫作为抢劫罪的加重处罚情节。但实质解释这一解释明显违背了国民预测可能性,扩大了处罚范围。再以王力军案为例,王力军于2014年11月至2015年1月期间买卖玉米未办理粮食经营许可证和工商营业执照,严格按照法律规定则具有违法性,但不具备社会危害性和刑事处罚必要性,若按照形式解释则会不当扩大处罚范围。
我们不能将限制处罚范围作为基本原则,也不能将存在疑问时一概作出有利于被告人的解释作为原则。易言之,刑法解释和处罚范围之间没有必然联系。很明显,刑法解释在前处罚范围在后,不能为了扩大或缩小处罚范围而再去解释刑法,这就会造成本末倒置和以刑制罪。刑事立法时已经限制了刑罚处罚范围后,刑法解释就不应该再突破这一界限,否则无论你是扩大解释还是类推解释都是违背立法原意。虽然当今社会犯罪猖獗,社会秩序也不太稳定但不能依赖刑罚的处罚范围扩大来整顿社会,如果我们的社会需要完全依赖刑罚来维稳的话,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悲哀!
处罚范围的妥当性和处罚程度的妥当性不应该成为进行实质解释的借口。因为这里的妥当性是由谁来界定?这完全又是一个主观判断。这种主观判断就会导致解释的恣意性。而且限制处罚范围和限制国家机关的权力之间就有必然联系吗?刑罚处罚范围的确定是由国家权力机关立法时所决定的,刑罚处罚范围确定后司法机关的权力范围就必然会被限制。易言之,刑罚处罚范围只能限制司法机关的权限。实质解释论者通常认为形式解释会被国家机关所利用从而去滥用权力。形式解释论者则认为通过实质解释去滥用权力的情形会更多。笔者认为,根据刑法条文字面含义去迫害他人的难度较大,毕竟会受到罪刑法定原则限制,除非是立法本身就存在缺陷;而实质解释首先进行了主观价值判断然后再去寻找刑法条文,这种先入为主的主观性更容易迫害他人。
(五)实质解释论的其他相关理论
目前,很多学者认为:实质解释和形式解释的对立其实是形式犯罪论和实质犯罪论对立的延伸。实质犯罪论者主张在刑罚法规的解释特别是构成要件的解释上,应当从处罚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出发。按照这种观点,刑法是行为规范,但更应当是以法官为主体的裁判规范,是导入了实质的当罚性判断的裁判规范。因此,罪刑法定原则中的明确性或刑法的严格解释原则并不重要,应当从处罚的必要性和合理性的立场出发,对刑罚规范或构成要件进行实质性的解释*前田雅英:《刑法的基础-总论》,东京:东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84-89页。。形式犯罪论者认为应该进行定型的、形式的判断,在这一点上,不同于作为非定型的、实质的价值判断的违法性判断和责任的判断*刘艳红:《实质刑法观》,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第163页。。笔者认为,我们对实质解释和形式解释研究过程中不应该扩大矛盾范围,不应该将形式解释与实质解释的对立上升到形式犯罪论与实质犯罪论的对立,我们的研究应该是就事论事,不应该将刑法学问题延伸至犯罪学。
对于所谓实际不值得科处刑罚但符合刑法规定的行为,形式解释和实质解释的出罪路径是完全不同的,实质解释论者认为该类行为没有处罚的必要性和合理性,不值得处罚所以予以出罪;形式解释论者认为虽然形式上符合刑法规定的构成要件但根据刑法第13条的但书规定宣告无罪。笔者认为这两种不同的出罪方式站在各自学派立场都似乎有一定道理,但实质解释论的这种方式具有较大恣意性。与形式解释论相比,实质解释论更早地得出了有利于被告人的无罪结论。这种更早地得出的结论是先入为主、无法律依据的价值判断,当然这也是实质解释的通病。
有实质解释论者提出形式的刑法解释能更好地贯彻罪刑法定原则、体现依法治国之实践?实质的刑法解释必然与罪刑法定原则相冲突、必然不利于保障人权吗*苏彩霞:《实质的刑法解释论之确定与展开》,《法学研究》2007年第2期,第40页。?笔者很肯定的回答:无论是形式解释还是实质解释都不能完全很好地贯彻罪刑法定原则,都不可避免地存在缺陷,无论实质解释还是形式解释,最终目的都是为了更好地贯彻罪刑法定原则和最大程度上保障人权。无论哪种解释只要与这种初衷背道而驰的话我们都需要将其抛弃,但不可否认的是两种解释都有一定合理性。我们所要做的就是取两者之精华,去两者之糟粕。
实质解释论者认为:从法律解释与适用方法的一般理论上看,实质解释论具有方法论意义上的合理性。并提出以下论据:第一,他们认为刑法作为制定法本身的局限性,决定了仅对刑法进行字面解释与机械适用是行不通;第二,认为刑法规范本身的结构决定了对其的理解与适用不能是字面的和无价值的;第三,认为刑法的适用具有复杂性,决定了对具体的案件事实适用不可能是简单的逻辑推理过程。笔者认为,作为成文法的刑法具有其本身的缺陷是正常的,这种缺陷可以通过立法的推进来逐渐完善并不必须通过恣意性的主观解释来填补。刑法规范的本身结构就是罪刑法定原则的体现,不能因为坚持了罪刑法定原则就说明是无价值的和机械的。刑法作为成文法对其进行适用当然是机械逻辑推理的过程,不能因为成文法有缺陷和适用比较复杂就放弃逻辑推理。
任何法律规范都包含了立法者的“利益评价”,也就是“价值判断”,所以,法律适用就意味着在具体的案件中实现法定的价值判断*[德]魏德士:《法理学》,丁小春、吴越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61页。。实质解释论者认为必须对法律规范作实质的考察与解释,使经过解释后的法律规范能切实地反映出立法者的价值评价。立法者做价值判断不代表司法者也必须做价值判断;不能把立法者的价值判断强加于司法者,不能将立法者的价值观当作司法者进行罪行擅断的借口。实质解释论者又认为:从我国刑事法治目标、罪刑法定原则的涵义、犯罪概念与犯罪构成体系特点来看,实质解释具有优越的合理性。并坚持认为实质解释契合了刑法的安定性与追求实质正义的实现。并拿纳粹德国推行形式法治,法官只坚持形式的三段论推理来决定案件导致压制民主和法律的局面作为论据,据此认为我们不能再搞形式解释。笔者认为,纳粹德国的现象是由希特勒的恐怖主义统治所导致的,无论当时是坚持实质解释还是进行形式的机械解释都不能避免残暴的局面,本来就是立法本身和司法过程出现了问题,不能完全怪罪于形式解释。所以究其缘由还是要限制立法权,立法者在立法时就应该进行实质的价值判断和衡量,将根本不值得判处刑罚的行为直接排除在刑法规范当中。实质解释论者也主张犯罪构成是我国认定犯罪的唯一标准,并不需要在犯罪构成以外还寻找其他的定罪标准,但实质解释论者的论据却又反复重申刑罚的合理性、必要性、“值得”等,这些完全是在犯罪构成外进行考虑,是一种脱离罪刑法定原则的形而上学,难道不是自相矛盾吗?而且实质解释论者的论据总是在反复重复没有任何新意。此外,实质解释论者主张通过解释使犯罪构成所反映的社会危害性达到应受刑事责任追究的程度*张明楷:《刑法的基本立场》,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147页。。笔者不禁想说:这种解释的功能也太强大了吧,直接就可以通过解释把人的行为解释成有罪。实质解释论还认为,一般的危害行为尚不足以应受刑事责任追究的,立法者通过‘情节严重’来限制是以实质解释的方式来限制刑罚处罚范围。笔者认为这里的“情节严重”的限制是刑法的明文规定和任何解释没有关系。即使是司法解释中规定的数额限制也是司法解释的明文规定并非是实质解释的功劳。
二、对形式解释的认识和思考
形式解释论者认为,形式解释论是基于罪刑法定原则所倡导的形式理性,通过形式要件,将实质上值得科处刑罚但缺乏刑法规定的行为排除在刑法范围之外。并且,认为己方是坚持罪刑法定原则,而实质解释论是完全的社会危害性论。因此双方的争论也就变成了罪刑法定原则和社会危害性的争论。笔者认为,这种看法存在一定误解,因实质解释论者也是坚持罪刑法定原则的,不过他们硬把罪刑法定原则分为形式侧面和实质侧面。某些形式解释论者认为关于刑罚法规,也并非否定一切的自由解释。特别是在对有利于行为人的方向进行解释,不受罪刑法定主义限制,实际上也可以从超法规观点广泛地承认违法阻却事由和责任阻却事由*〔日〕大塚仁:《刑法概说(总论)》第3版,冯军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78-79页。。如果承认这种理念则变成一切有利于被告人的解释都会被允许,存在疑问时以有利于被告人解释作为原则。显然这种观点是不能被接受的,无论实质解释论者还是形式解释论者都是反对这一原则的。实质解释论者认为形式解释论者只是坚持机械和形式的判断,形式解释论者则反驳道他们反对实质解释但不反对实质判断,并提出了形式判断和实质判断的一种逻辑位阶关系,即先进行形式判断再进行实质判断。笔者认为,这是形式解释论在争论过程中的一种妥协,因为这和实质解释论者所主张的罪刑法定原则的实质侧面和形式侧面的关系之间又有多大区别呢?至于实质上具有科处刑罚必要性但形式上缺乏刑法的明文规定的行为的处理方面,形式解释论当然持反对意见,但形式解释论者认为实质解释论者对此持肯定意见的观点笔者对此不敢苟同。因为笔者通读相关实质解释论者的文章对此也是持否定观点,只不过他们认为能否根据刑法条文所可能具有的含义进行扩大解释将该行为纳入刑罚规范中来。所以双方的某些争议来自于误解。
形式解释论者提出法内解释和法外解释概念来证明己方是坚持法内解释,而实质解释会进行法外解释从而滑入类推解释的泥沼,形式解释论者也主张不能认为只要依据法律文本所作的解释就一定符合罪刑法定原则。这难道不是和形式解释论所主张的文义解释所矛盾吗?如果不符合罪刑法定原则的话该怎么处理?莫非要再进行实质解释吗?总感觉形式解释论者为了达到争论的上风一再退步、一再妥协自己的观点。无论你怎么演绎自己的实质判断和形式判断都不能摆脱和罪刑法定原则的形式侧面以及实质侧面重合的嫌疑。当然,这种罪刑法定原则的形式侧面和实质侧面本身的划分就存在问题,这些概念源于陈忠林教授在翻译意大利学者的著作时进行阐述的。其实意大利实质的合法性原则与罪刑法定原则之间本身就没有关系,但陈忠林教授却把这种实质合法性演绎成罪刑法定原则的实质侧面,把原本的罪刑法定原则称为罪刑法定原则的形式侧面,这样就不当地扩大了罪刑法定原则的范围。理论根源就是错误,那么两派依据这样的理论得出的结论必然是不科学的。而且,我们为什么要拿外国的理论来验证自己的学说?本身的目的和用意就是不理性。*参见陈忠林:《从外在形式到内在实质的追求-罪刑法定原则蕴涵的价值冲突与我国应有的立法选择》,载《现代法学》,1997年第1期。形式解释论还对常识、常理、常情应该区分立法和司法两个层面:在立法层面,常识、常理、常情作为设置制刑的依据完全是正确的。但是如果在司法层面将常识、常理、常情作为实质正义凌驾于刑法之上,这将是十分危险的。笔者认为:在司法过程中如果法官不考虑常识、常理、常情,那么法官不就完全变成机器了吗?这样法官的内心确信就完全不能起到作用。发生在河南省的一起父亲杀子案,黎二某是黎某之子,多年来叛逆不逊,对父母非打即骂,相当凶恶。在外也是坏事做尽,先后因奸淫幼女和盗窃被判刑6年和6个月,实在是穷凶极恶之徒。最终其亲生父亲终于忍不住了,有一天儿子醉酒后,用菜刀将其杀害,还把尸体掩埋在自家鸡场。但黎某这一行为,却得到了全村人的谅解和支持,并且获得117人联名求情。如果法官对该案中的常识、常理、常情不考虑,完全按照形式解释必然会加重对被告人的处罚。面对这类问题的结论,正是形式解释论者的通病,因为他们会牺牲处罚必要性来保障国民基于预测可能性所进行行为的自由。因此形式解释论者会将实质解释论者所主张的扩大解释直接归位于类推解释。
形式解释论在许多具体问题上的解释是有问题的。首先以重婚案件为例,广东湛江市陈某先与海南姑娘叶某恋爱同居,后又与另一名姑娘戴某恋爱同居,后来出现三人同居情形。2001年5月16日,陈某举办婚宴同时迎娶叶某和戴某。很明显,陈某和叶某、戴某的婚姻只是办了酒席并未登记,都是属于事实婚姻。形式解释论者认为,重婚罪是有配偶而重婚,或者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之结婚的,其中的有配偶必须理解为有法定婚的存在,即行为人之前必须有法定婚,或者明知他人之前存在法定婚而与之结婚的情形。对于行为人之前有事实婚姻而与他人登记结婚或者行为人与他人存在事实婚后又和其他人有事实婚的情形则认为不构成重婚罪。所以,形式解释论者认为陈某等人的行为均不构成重婚罪。对此,笔者不能赞同。很明显,此处形式解释论者对重婚罪侵害的客体已经存在认识错误,重婚罪侵犯的是一夫一妻制而并非是婚姻登记制度,这也是民法不承认事实婚姻而刑法对事实婚姻予以考虑的原因。形式解释论一味强调之前必须存在法定婚,侧重点是对之前婚姻登记的保护,则似乎背离了重婚罪设立的初衷。笔者认为,无论行为人之前是事实婚或法定婚还是之后是事实婚或法定婚都构成重婚罪,因为这几种情形都对一夫一妻制度存在侵害。
关于故意毁坏财物犯罪方面,形式解释论者的解释过于机械,将故意毁坏理解为仅限于物理上的损毁,主要是指使财物严重变形,丧失完整性,或者使财物灭失和流失。将他人的戒指扔入大海或者将他人的鸟笼打开放走笼子中的鸟儿的行为都不构成故意毁坏财物罪。实质解释论者认为故意毁坏不应该仅限于物理上的损毁还应该包括效用上的侵害,因此上述两种情形已经完全使得权利人的戒指不能再使用,鸟儿不能再观赏,效用被严重侵害。笔者认为,在故意毁坏财物的问题上实质解释论者的解释更具有合理性。关于虚拟财产问题,形式解释论者一方面承认虚拟财产属于刑法上财物,盗窃虚拟财产构成盗窃罪不存在疑问。但另一方面,对于行为人为了报复侵入他人股票交易账户,在账户内高价买入股票低价卖出造成财产损失的行为又不构成故意毁坏财物罪,前后理论明显存在矛盾*陈兴良:《判例刑法学》(下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53页-388页。。说明形式解释论的解释根本没有形成完整的逻辑体系。
再以许霆案为例,2006年4月21日晚10时,被告人许霆来到天河区黄埔大道某银行的ATM取款机取款。结果取出1000元后,他惊讶地发现银行卡账户里只被扣了1元,狂喜之下,许霆连续取款5.4万元。当晚,许霆回到住处,将此事告诉了同伴郭安山。两人随即再次前往提款,之后反复操作多次。后经警方查实,许霆先后取款171笔,合计17.5万元;郭安山则取款1.8万元。事后,2人各携赃款潜逃。类似于许霆的行为,在不同国家有不同的处理结论,英国直接将钱款判给行为人,作为对银行自身行为出错的处罚,其他国家则作为民事案件处理,行为人将钱款退还给银行即可。在中国该案存在重大争议,有的学者认为应该按民事案件处理,没有必要上升到刑事案件;有的学者认为该行为具有较大的恶性有必要通过刑罚来处罚。形式解释论者不深入讨论条文的实质含义和案件争议焦点的实质之处,仅是从是否违反罪刑法定原则来得出自己结论。大多形式解释论者认为许霆的行为完全符合盗窃罪的构成要件,应当以盗窃罪进行处罚,也不去讨论以重刑去处罚是否适当。而实质解释论者则基于是否具有处罚必要性或是否“值得”处罚而得出不同结论,有的认为应该用刑罚来处置,有的认为没必要采取刑罚方式,具有较大恣意性。笔者认为,形式解释论和实质解释论对本案的解释都不具有合理性,本案涉及刑法的谦抑性问题,不能什么问题都希望通过刑法来解决,为何不放手以其他方式来解决。例如“大学生掏鸟窝获刑10年”、“深圳鹦鹉案”等都涉及刑法的谦抑性,形式解释论和实质解释论似乎都不能很好地解决。
再以偷越国边境罪为例,被告人何某、刘某等人,在北京租房作为窝点,与全国多地犯罪团伙相互勾结,以湖北及其他省农民工为偷渡对象,私刻假印章,以组团出国旅游名义向外国驻华大使馆骗取签证,使这些农民工出境至荷兰、罗马尼亚等国,集体失踪从事非法劳务。形式解释论者认为,骗取的出境证件,无论护照还是签证都是合法的,将持有形式上合法的出境证件认定为偷越国边境罪,不符合偷越的意思。笔者对此不敢苟同,虽然证件的形式是合法的,但是通过不合法方式骗取而来,本质上属于不合法,再以该证件组织人员出境的,应该构成偷越国边境罪。法院的判决也对该行为构成偷越国边境罪予以确认。
形式解释论者认为,虽然作为成文法的刑法本身可能存在规定的漏洞,但罪刑法定原则的形式侧面本身没有缺陷,因为刑法没有明文规定的部分也是以另外一种方式规定,因为刑法没有禁止的就不是犯罪;并主张罪刑法定原则的形式侧面与实质侧面的冲突就是刑法中形式与实质的矛盾,也就是法律形式主义与法律实质正义的矛盾。前者笔者予以赞同,但对于矛盾的类比与扩大,笔者不以为然,因为我们在讨论一个问题的时候应该就事论事,而不能偷换概念。罪刑法定原则的形式侧面本身具有实质的价值这是立法者立法时考虑到的,不意味着罪刑法定原则不需要实质侧面来限制,如果承认实质侧面存在的话,还必须考虑实质侧面。形式侧面和实质侧面的存在不意味着一方必须否定另一方,两者是相辅相成协力进步。形式解释论者认为对于法无明文规定但实质上值得科处刑罚的行为不予处罚是实行罪刑法定原则的必要代价,而并非罪刑法定原则的缺陷,笔者想问,那对于刑法明文规定但实质上不值得处罚的行为也不是罪刑法定原则的缺陷吗?这种法律不可避免牺牲的代价其实就是法律的缺陷,不能因为为自己的主张辩护而忽视这种缺陷。形式解释论者误认为,形式解释论与实质解释论的根本对立在于对刑法没有明文规定的情况下能否将实质有处罚必要性的行为通过扩大解释予以入罪。笔者认为两者根本对立在于刑法解释有没有位阶?是先进行形式判断还是先进行实质判断?因为两者在很多方面是趋同的,形式解释论者已经让步提出有实质判断的存在,并且认为可能的语义并非实质解释论的专利,认为在任何情况下必须将可能的词义视为最宽的界限*[德]汉斯海因里希·耶塞克,托马斯·魏根特:《德国刑法教科书》,徐久生译,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第197页。。实质解释论同样主张以可能的语义作为解释边界,而且可能的语义刚好是实现处罚必要性的手段。很明显,形式解释论者的让步是非常大的,可以看出他们也是可以接受扩大解释的,所以两者的对立范围已经越来越窄变得趋同。总之,实质解释论者总是站在道德制高点以社会卫道士角色自居,形式解释论者总让人感觉是拘泥于字面含义不会变通。
三、对完善刑法解释观的建议
德国学者按照文义解释、历史解释、系统解释、客观解释、目的解释这样一个顺序为刑法的各种解释方法提供了一个价值位阶,给解释者在解释时提供了一个指引,对解释位阶进行修正后的形式解释论者主张将文义解释放在首位,这也就是形式解释论者所极力提倡的形式判断,那其他几种解释方法应该就是他们所主张的实质判断。当然实质解释论者也提倡解释位阶,认为刑法解释方法的位阶关系对于解决刑法解释的争端,保证刑法解释的客观性具有重要意义,承认解释方法的位阶关系,是与我们的思维特点相吻合的*苏彩霞:《刑法解释方法的位阶与运用》,《中国法学》,2008年第5期,第97-98页。。关于刑法解释方法的位阶关系已经在实质解释论和形式解释论之间几乎达成了共识,至于这种位阶关系如何,以及是否受到刑法的公平、正义等价值影响存在一些分歧,但毫无疑问,根据罪刑法定原则和法的安定性,要求文义解释是必须首先要坚持的。这种解释位阶不仅是运用时的先后考虑,而且还包括在发生冲突时何种解释得出的结论效力优先问题,关于效力优先问题是两派不可能达成共识的地方,也是争议焦点。我国学者在德国学者基础上提出了最后位阶即合宪性解释,就是由宪法来做最后检验,以免得出的结论违宪。而且这样的解释符合由客观到主观、由表及里、由部分到整体的哲学规律,最后再由宪法来兜底。
关于刑法的解释,从解释效力角度划分,包括有权解释(包括立法解释、司法解释)、学理解释(文义解释、扩大解释、缩小解释、当然解释);有实质解释论者对其划分为解释技巧(平义解释、扩大解释、缩小解释、反对解释、补正解释等)、解释理由(文理解释、体系解释、历史解释、比较解释、目的解释等)*张明楷:《刑法学》(上)第五版,北京:法律出版社,2016年,第34页。。前一种是我国刑法学的通说,后一种已经逐渐产生影响,但笔者不赞成,因为对司法实践没有实际指导意义。
笔者认为,存疑时有利于被告不能适用于刑法的解释过程中,只能用于在案情确实难以查明时,存在难以排除的合理疑问时,应该作出有利于被告人的推定,但对于刑法解释存在疑问是很正常的,而且在解释时提出疑问和质疑也是非常轻易的,如果这样就作出有利于被告人的解释的话,那么所有案件都必须作出有利于被告人的解释,这显然是与罪刑法定原则相违背的,而且导致刑法的许多条文将成为废条,这时法官应该选择最合理、最正确的解释方法而不是最有利于被告人的解释方法。
笔者赞成解释方法存在位阶关系,不过笔者主张文义解释→体系解释→合宪性解释,不太赞成历史解释和目的解释,因为这两种解释方法归根到底是主观解释,而主观解释带有较大恣意性,容易被司法者所利用。笔者的主张既保证了刑法的安定性,也限制了实质解释的过度运用。
从哲学角度而言,哲学范畴是哲学里概括与抽象程度较高的概念,包括物质与精神、信息与能量、运动与静止、必然与偶然、规律与混沌、对立与统一、系统与要素、结构与建构、理性与信仰、利己与利他、现象与本质、形式与内容等。所以形式和实质根本不是一对哲学范畴,所以二者根本不存在对立,所谓形式解释与实质解释对立根本就是伪命题。当下学者研究具体学科时根本不从哲学角度考虑问题,所以产生许多的学术或争论是根本没有逻辑体系的。所以对形式解释与实质解释的争论如果要是选队站的话就是陷入了这种哲学圈套,赞成哪一种观点无论你的学术论据是多么扎实也不过是没有哲学根基的无病呻吟。作为一个理性的法律人,我们要避免这种没有意义的争论,而且要发现这种争论背后的本质问题,不能被表面的争论所误导从而迷失了学术方向。所以笔者既不赞成形式解释也不赞成实质解释,而是主张脱离这种无谓争论去寻找解决具体案件争议的最好解释方法,更何况两种解释没有哪一个是十全十美的,都存在缺陷,笔者在前文已经叙述,此处不再赘述。
笔者认为,我们在解释刑法时首先要立足刑法的文理规定,进行严格解释。严格解释是第一位阶的解释,是进行其他解释的基础,在进行严格解释时,要特别注意刑法第13条但书条款的应用,属于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认为是犯罪的情形,要严格进行出罪。当下各种解释观都忽视了该条款的运用,一旦运用该条款对相关行为进行出罪,既可以保持刑法的谦抑性也不会产生相关无意义的解释争论。例如对于深圳王鹏鹦鹉案,王鹏3年前在工厂里捡到1只鹦鹉,带回家小心饲养,后又买回1只配对。3年来他细心钻研,花费大量时间与精力,自学养殖鹦鹉技术,竟然无师自通,孵化出四十多只鹦鹉。2016年4月他出售过两只鹦鹉。但没多久买者(贩鹦鹉者)被抓,供出了王鹏。王鹏被抓1年后1审被判了5年徒刑。王鹏孵化鹦鹉的行为促进了鹦鹉的繁殖,可以说其行为符合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完全可以按照第13条但书条款予以出罪。大多形式解释论者和实质解释论者忽视了严格解释,对但书条款视若罔闻,才会有后面的争论。福建刘大蔚等仿真枪案、大学生掏鸟窝案、卢氏农民采3株野草获刑案、杂戏团运输动物案与本案处理路径一样,本不应该有争议。
如果严格解释不能解决案件争议,再进行体系解释。体系解释处于第二位阶,联系整个刑法体系或法律体系进行解释。体系解释包括两方面内容。第一,排除性体系解释。即刑法条文中同一概念并不具有完全一致含义。比如,抢劫罪中的暴力和强奸罪中暴力不能做一致的解释,抢劫罪中的暴力可以致被害人死亡,强奸罪中的暴力不包括致被害人死亡情形。强奸罪中胁迫范围比较广,而抢劫罪中的胁迫仅限于暴力胁迫。第二,一致性体系解释。即刑法中某一概念若不能明晰,从联系整个刑法条文或者整个法律体系进行解释以明晰。如刑法中没有关于恐怖主义或恐怖活动的明确定义,对此可以联系《反恐怖主义法》对恐怖主义或恐怖活动范围进行确定。
最后由宪法进行最终的检验。合宪性解释是最后位阶或者说是兜底位阶。对严格解释和体系解释的结论进行检验,如果违宪直接排除,合宪则是合理的解释。如在日本司法实践中出现过的一个案例,行为人散发“主张实施内乱罪的正当性和必要性的文书”而被提起犯罪诉讼。法院认为,被告人尽管实施散布上述文书行为,但该行为客观上不可能引起内乱,因此宣告被告人无罪*黎宏:《日本刑法精义》,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4年,第51-52页。。
结 语
刑法的解释是必须的,我们不要再拘泥于是要采纳形式解释还是实质解释,逐步淡化这种无谓的争论,而是要安心学术去追寻最合法又合理的解释。寻找一种既合乎于理论研究又合乎于司法实践的解释,不能让理论和实践有较大脱节,如果这种脱节障碍还迟迟不能清除,其实就是我们的刑法理论研究的失败。易言之,一种理论都不能运用于实践则说明这种理论就是废话。
[1] 陈兴良.形式解释论的再宣示[J].中国法学,2010(4):27-28.
[2] [德]阿图尔·考夫曼,温佛里德·哈斯默尔.当代法哲学和法律理论导论[M].郑永流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158.
[3] 李斯特.德国刑法学教科书(修订译本)[M].徐久生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
[4] 张明楷.实质解释论的再提倡[J].中国法学,2010(21):77.
[5] [日]前田雅英.刑法总论讲义[M].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2006:78-79.
[6] 杨兴培.刑法实质解释论与形式解释论的透析和批评[J]法学家,2013(1):36.
[7] [日]前田雅英.刑法的基础-总论[M].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84-89.
[8] 刘艳红.实质刑法观[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9] 苏彩霞.实质的刑法解释论之确定与展开[J]法学研究,2007(2):38-52.
[10] [德]魏德士.法理学[M].丁小,吴越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61.
[11] 张明楷.刑法的基本立场[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147.
[12] [日]大塚仁:刑法概说(总论)[M].冯军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78-79.
[13] 陈忠林.从外在形式到内在价值的追求——论罪刑法定原则蕴涵的价值冲突与我国刑法应有的立法选择[J].现代法学,1997(1):30-40.
[14] [德]汉斯海因里希·耶塞克,托马斯·魏根特.德国刑法教科书[M].徐久生译.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197.
[15] 苏彩霞.刑法解释方法的位阶与运用[J].中国法学,2008(5):97-108.
[16] 张明楷.刑法学(上)第五版[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6:34.
[17] [日]大谷实.刑法讲义各论[M].东京:成文堂,2007:343.
[18] [日]内藤谦.刑法讲义总论(上)[M].东京:有斐阁,1983:36.
[19] [日]前田雅英.现代社会实质的犯罪论[M].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1992:24.
[20] [日]山中敬一.刑法各论[M].东京:成文堂,2009:730.
CriticalAnalysisofSubstantiveInterpretationandFormalInterpretationofCriminalLaw
TONG Yun-feng
(School of law,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s and law,Shanghai 200042,China)
The criminal law provisions are not completely clear and concrete. Therefore,it is necessary to interpret the provisions of the criminal law. The criminal law for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provisions of China's criminal law scholars have different views and the formation of a larger controversy. The substantial interpretation and formal interpretation over the most intense substantive Interpretation on excessive. Emphasize the social harmfulness,subjective judgment and objective existence already in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criminal law before the conclusion in interpreting has great arbitrariness. Explanation on the form of literal meaning rigidly adhere to the provisions of the criminal law,not for changes in the objective of the society,the validity of the conclusion is questioned and criticized. Therefore,whether substantive interpretation or Formal interpretation should not be fully promoted. Therefore,it is necessary to make a systematic and critical analysis of the inadequacy and rationality of substantive interpretation and formal interpretation in order to perfect our interpretation of criminal law
substantive explanation theory;formal interpretation theory; interpretation order; legal principle of crime and punishment
D914
A
1009-9743(2017)04-0116-10
2017-05-07
童云峰,男,汉族,安徽无为人。华东政法大学2016级刑法学在读硕士。主要研究方向:刑法学。
10.13803/j.cnki.issn1009-9743.2017.04.021
张玉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