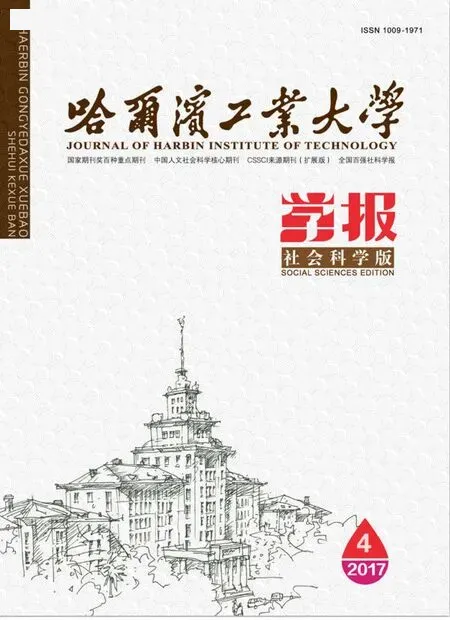基层政权的公共性建构:一个历史制度主义视角
周庆智
基层政权的公共性建构:一个历史制度主义视角
周庆智
(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北京100028)
公共性贯穿于基层政权建设,有两层含义:一是关系政权存在的合法性,二是关系政权性质的社会基础。历史上看,现代政权建设和公共性建构未必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因为:把公共性作为实现国力强盛的手段,基层政权建设可以着眼于资源汲取和社会动员及控制能力,这必然构建与社会的支配和庇护关系;把公共性作为实现平等公民权的目的,基层政权建设只能着眼于社会公正和社会福祉的公共性质。所以,如何建构基层政权的公共性,涉及政治逻辑和权力性质的转变。换言之,关于基层政权建设的讨论,需要置于其公共性建构的历史发展逻辑和现实发展基础之上。
基层政权建设;政府公共性;历史制度主义
当前,基层政府的公共性成为一个需要讨论的问题,有复杂的历史原因和现实约束条件。因此,阐释基层政府的公共性,需要回到基层政权建设的历史发展逻辑上。从历史制度主义视角看,以其“历史性因果关系”和“结构性因果关系”分析性概念①这两个分析性概念是历史制度主义理论的核心含义。所谓“历史性因果关系”,即通过“追寻历史”,深入了解一个国家的政治和政策发展史,在追寻历史的过程中,可以看到某种政策方案的选择和实施往往受制于既定的政策制度模式,而既定政策模式的形成又是一个历史的过程,引出即所谓的“路径依赖”——一旦制度固定下来之后,学习效应、协同效应、适应性预期和退出成本的增大将使得制度的改变会越来越困难。所谓“结构性因果关系”,有两层含义:既定的制度是如何构成政治生活中的互动关系的,即强调政治制度的重要作用;影响政治结果的各政治变量之间的结构关系。详见何俊志《结构、历史与行为: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范式》,载于《国外社会科学》2002年第5期。来辩明基层政权建设的影响因素,需要解释是什么样的“结构性架构”主导着基层政权建设的政治进程、制度发展路径和方向,进而分析是什么样既定的制度结构决定了基层政府的权力功能和公共政策指向。换言之,关于基层政权建设的公共性问题的讨论,需要从历史的视野和制度结构性因素来展开,不仅要作历史分析,还要分析“制度之间的链接”。这样,才能恰当地进入当前基层政权建设公共性问题的实质性讨论当中。
一、传统基层政权的功能和组织形式
有一个主流性的认识,认为皇权不下县,基层政权设在县一级,县下的乡村社会是一种(乡绅主导)自治形态。换句话说,王朝时期县以下不存在“基层政权建设问题”。但深入的历史研究也表明,皇权控制基层社会有非常复杂的结构体系,也就是说,王朝时期的基层权力由代表皇权的胥吏群体、地方精英如乡绅和宗族等势力分割。换言之,在基层的权力是由正式结构或准正式结构、制度形式与非制度形式构成的一个基层组织体系。
胥吏群体是传统基层政权衍生出来的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①胥吏内部分两个层次:上层为有一定文化、遵照官员命令、处理具体政务特别是经办各类文书的人员;下层为从事杂务、厮役的一般小吏。详见祝总斌《略论中国封建政权的运行机制》,载马克垚主编《中西封建社会比较研究》,学林出版社1997年版,第308—309页。本文所论胥吏,乃指下层,关注的重点在于吏民之间的关系。它掌握着基层政权的实质性权力。胥吏不在官僚体系内,而是由官僚体系内官员如县官“辟召”的职役人员。以乾隆年间吴江县为例,知县之下仅11名佐杂官,但各类吏役多达300~400人[1]。从制度史的角度看,胥吏属于官僚制度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只是非正式制度的一部分,虽不在国家行政编制内,但却具体运作行政活动,与基层百姓打交道,代表官方的权力。
把皇权与基层社会联系在一起、支持帝国运行的胥吏群体担负着税收和治安这两项“公共事务”,亦即发挥着基层政府(县衙)税赋征缴和维持地方秩序的作用。《文献通考》卷35《选举八》引苏轼语:“胥吏行文书,治刑狱、钱谷。”县官做出决断之后,各种来往文牒的起草、赋税的催征、盗贼的捕获等事宜,均由胥吏按照分工具体承办。概言之,基层胥吏在土地丈量、清理财政、赋税摊款中扮演重要角色,因此胥吏的擅权行为也多发生在上述方面,包括操纵赋役,欺压百姓,与地方势力如商人、军人勾连合流等乱政扰民之行径[2]。但胥吏之所以能够成为皇权的基层行政操控者,是因为:其一,帝国的基层官员如县官的任用体制弊端,如顾炎武认为“胥史之权所以日重而不可拔者,任法之弊使之然也”[3][4]。结果是,一方面,县官任上不得不倚重本地人出身的胥吏,所谓“寄命于吏”;另一方面,“官无常任而吏有常任”的状况,导致胥吏支配某一部门或某一区域的行政管理事务。其二,胥吏凭借谙熟律例、掌控文书的机会获得了部分官员的权力,且以惯例胥吏由本地人担任,与地方有实质性联系。其三,帝国财力有限,不足以对基层社会贯彻“官治化”或制度化。由于以上原因,胥吏成为官与民之间“交接之枢纽”,官与民之间要打交道,必须通过他们,这使他们成为一种不可或缺的角色[5]。胥吏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政治群体,构成了皇权在基层社会秩序中将官治秩序规则与民治秩序规则贯通的角色位置,基层政府如州县衙门事务必须依仗庞大的胥吏队伍配合才能完成,对皇权治理的成败及其在基层社会秩序的维持上,胥吏发挥着基础性的功能和作用。
所以,传统的基层吏治问题,就是胥吏擅权问题。顾炎武说“今夺百官之权,而一切归之吏胥,是所谓百官者虚名,而柄国者吏胥而已”[6],指出的就是胥吏操控基层行政问题。唐宋以来的士人曾经反思讨论解决之道,但终不能有所改进。这部分原因受制于论者的历史局限性,比如,南宋叶适认为,胥吏擅权以至吏弊丛生,是由于在科举制下官员对行政法规多有隔膜,对法规条例的熟悉却又正是胥吏的特长。官、吏之间知识结构的差别以及官员行政能力的不足,是胥吏能够僭越官员权力的重要原因,再加之胥吏对当地风土人情的熟悉以及在当地人脉的深厚,这又放大了官吏之间知识结构和行政能力的差距。解决之道是以士人为吏,即“使新进士及任子之应仕者更迭为之”[7]。此后直至清代,对胥吏问题的思考,基本上不出叶适所论问题之外,观点也多有近似之处。明末清初的顾炎武提出的对策与叶适等略有不同,叶适等以士人为吏的关注点在于“吏”,而顾炎武则把重点置于“官”,他认为解决吏弊的方法是让地方官皆由本地人来担任,而且不设任期,终身为之,如此“上下辨而民志定矣,文法除而吏事简矣。官之力足以御吏而有余,吏无所以把持其官而自循其法”[8]。文献所见清人对胥吏的专论更多,内容仍然集中于对吏弊原因的分析及其解决策略上。
二、近现代以来的基层政权现代化
近现代以来的基层政权建设是国家政权建设的一部分,它具备两个特征:一是国家权力向基层扩张;二是将基层社会纳入国家管制体系中。它的目的是强化国家汲取资源的能力和提升社会控制及动员能力。从基层社会看,这一过程乃是官治化和去自治化的过程,即政治整合代替社会整合,社会与国家一体化。
对传统基层政权进行现代化的改造和思考,始于近代以来的民族国家建构和现代化。但深入的历史分析之后,我们发现,清末民初关于基层政权建设包括所谓地方自治的论争及其实践,其实针对的仍然是一个老问题:从帝制一直延续过来的基层吏治(针对胥吏)擅权和腐败问题。以“地方自治”为名重构基层权威的各种改制主张和实践,最终无不以加强中央集权体制为目的,亦即有关地方自治的设想并不是带有根本性质的改变,更不是革命,它的目标指向是“一个更具有活力、也更为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9],为此诉求的是一个中央集权体制下吏治清明的基层社会秩序。因此,我们需要追问的是:对传统基层权力结构的如此“现代化”思考和改制设计包含多少以建构公共性社会关系为基本任务的公共政权建设含义。
比如,晚清至民国期间的基层政权建设,是依靠“乡村经纪体制”来征收赋税并实现对乡村社会的统治。所谓“乡村经纪体制”,就是国家利用非官僚化的机构及人员代行政府的正式职能。但这些寄生于国家与乡村社会罅隙之间的类似于“中间人”的“国家经纪”(state brokerage),往往借用国家的名义巧取豪夺以中饱私囊,使乡村社会陷入国家和乡村经纪人的双重盘剥之下,导致国家权威在乡村社会的缺失和地方精英的退化,从而造成所谓“国家政权建设内卷化”①杜赞奇认为,开始于清末新政的政权现代化建设到民国时期没能实现各级政府机构和人员的正规化与官僚化,而是走向了全面的“经纪化”,从而导致“国家政权建设内卷化”。参见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66-68页。。
再比如,国民政府时期,县级吏役官僚化,其行政任务已不限于收税、收粮以及处理民间诉讼等项公务,而且,乡镇实现了行政官僚化,这极大地加强了国家的施政能力和税收汲取能力。但总的来说,国民政府的基层政权政治现代化努力并没有取得成功,“一方面,乡镇政权的行政效率十分低下,难以真正承担起国家进行乡村政治经济动员的责任;另一方面,乡镇低层官僚及其在乡村的代理人的‘经济人’行为越来越明显,并逐渐形成了经纪体制,国家又缺乏对其有效的约束,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对农民的剥夺也就越来越重,乡村社会各利益主体之间的冲突也就越来越尖锐”[10]。概言之,国民政府凭借国家权力对基层的强制介入,并没有把乡村社会整合进以国家权威为中心的统一的政治体系当中。
在推进基层权力官治化的同时,以“地方自治”为主张的社会改造运动也在论述和实践中。也就是说,对传统基层吏治问题的思考和讨论不同以往,主要因为外来观念和势力的进入,有了一个外部参照体系,即西方宪政体制及附着其体制的观念。仿效西方宪政民主的“地方自治”,引发了关于国家体制及扩大统治基础(如政治参与)的讨论并印证在现代国家建构的历史实践进程上。梁启超认为集权体制的尾大不掉问题,出在地方官任用制,“以数千里外渺不相属之人,而代人理其饮食讼狱之事,虽不世出之才,其所能及者几何矣”。这是从集权体制看问题,与地方自治没有多大关系,至于他提出要“复古意,秉西法,重乡权”,②《戊戌政变记》,载《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一,第133页。以及设立地方议会,以地方之人治其他之事,实行“地方自治政体”的地方政制改革之议,与顾炎武的应对胥吏弊病之策比较,也并无新见,所不同者似援“西法”为参照,但他最终将自治的原义——自我治理(selfrule)、自我统治(self-government),转变为自我限制(self-mastery)、自我克制(self-control),亦即将政治意义上的个人自治,本土化地解读为伦理上的个人自治(自制)[11]。虽然对地方自治的界定含有限制皇权的变法意味,与“封建”(对抗集权)之意有相似之处(之前唐宋以来已多有讨论),但这个自治含义与外来观念的“自治”一词,本质上不同,它不是现代国家建构意义上的自治含义。以西方关于“地方自治”的肤浅认知不能解决中国积千年难解的胥吏擅权基层问题,比如,有学者指出从清末民初“尽管税收体制发生了巨大的改革,但在最下层却无实质性变化,那些税收人仍然逍遥于国家控制之外”[12]。最后的结果只能是重新回到加强中央集权体制官僚体制和再造传统基层权力结构的旧路径上。
所以,自近代以来随着皇权体系的胥吏阶层瓦解和乡绅的没落,国家政权向下渗透,比如乡镇组织正规化等,建构没有了皇权体系、胥吏阶层和乡绅阶层的基层社会秩序,这成为基层政权建设的头等大事。一系列社会改造运动的主线,为从乡村社会提取尽可能多的资源和强化社会动员能力,重构基层社会秩序,借机构设置确定地方权威在官僚体系中的位置,从而促进基层政权官僚化与合理化。随着国家权力逐步深入乡村社会,传统乡村治理的治理结构与运作逻辑开始改变。但尽管基层政治已经发生改变,基层社会的制度型权力依然没有建构起来,“代表国家权力的管辖权和规则既没有建立,也没有通过机构的设置贯彻下去,国家并没有改造地方权威的管制原则或取代它的管制权力,从而将地方社会纳入国家规则的治理范围中”[13]31。也就是说,旧的制度和旧的秩序原则并没有改变,不仅如此,还要通过复制旧制度和新的代理人来重构基层社会秩序。这导致两个直接的后果:一是国家政权建设发生“内卷化”①杜赞奇提出的概念,即正式的国家政权虽然可以依靠非正式机构来推行自己的政策,但它无法控制这些机构。这种情形被称作“国家政权的内卷化”。参见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66-68页。;二是旧的基层社会秩序愈发陷入失序形态。
三、当代基层政权公共性含义
对当代基层政权公共性展开分析,要明确的前提是:(如上所述)近代以来的基层政权现代化是官僚制度向基层社会扩张,传统基层权力性质并没有得到根本性改变,只是因国家权力范围延展而获得制度化或“正规化”(乡镇行政的设置)的支持从而得到进一步强化。要辨明的问题是:基层政权建设和公共规则变化的本质是什么,是新的基层社会公共性关系的现代建构形式,抑或是旧的基层控制方式和社会关系结构的传统再造形式。这是思考和讨论当代基层政权公共性建构的前提条件和必要条件。
20世纪50年代发生的政治变革及其伴随而来的一系列社会改造运动,使国家在基层社会实现了有史以来的彻底改革——社会结构的重组。国家通过人民公社体制重新建构了当代中国村庄,所以这一时期的村庄之所以能够作为一个社区或单位存在,主要靠的不是传统社会中村庄共同体意义上的“集体表象”,而是村庄即当时的生产队所具有的由国家力量建构的一种新型权力,这种新型权力由生产资料的集体所有、工分制度、统购统销制度以及户籍制度等一系列制度所维系,这种制度型权力重塑了村民与村民之间的联结方式,并且对村民具有强有力的支配能力[14]。通过政治整合实现社会整合,国家权力实行了对全社会包括城乡社区的全覆盖。可以说,社会结构重组的结果是城乡社区成为国家政权统治的一个基础单位,附属于国家权威管制体系的现代再造过程当中。
改革开放以后,基层社会秩序再次进入一个围绕(党政)权威重建秩序的过程。第一,国家改变了对基层社会的控制方式,从政社合一体制到政社分离体制,体制性权力从村社收缩至乡镇一级,国家与基层社会的关系发生了变化。第二,乡村社会组织形式发生了改变,即实行村民自治组织形式。村民自治是与集体土地产权相连的成员身份共同体,其自治更多地体现在经济意义上。第三,国家权力的退出和村组制度性权力的弱化。虽然农村的传统势力有所抬头[15],但从全国看,这种情况还不至于对基层社会秩序产生实质性的影响。与过去不同,现在的基层社会是一个国家直接面对个体民众的官—民(干群)结构关系。基层社会组织形式重构的秩序特征:一方面,在国家正式权力的运作过程中,引入了基层社会规则或地方性知识,展现了国家与农民关系的实践形态[16];另一方面,国家权力将村民自治组织作为控制和影响基层社会秩序的新的组织形式,后者成为乡镇基层政权对基层社会控制和动员能力的组织形式。概言之,改革开放以后,国家权力改变了过去的控制和动员方式,从由国家力量构建起来的基层社会秩序结构转变为以国家规范性权力为主与以乡村社会(村民自治)非规范性权力以及基层社会规范为辅的秩序形态和组织形式。
当今的基层社会秩序运行由党政权力系统、派生系统和吏役系统构成:第一,党政系统,即指由两个权力系统即党的组织系统和国家的行政系统构成。前者代表政治权力,后者代表行政权力。党政统合体系的治理意义在于:执政党通过政党组织系统将其政治意图贯彻于各级行政治理体系中,将党的实质性领导这一原则嵌入政府治理模式中。党政统合体系之精髓所在:这种制度的基本特征就在于政治控制成为完整行政机器的一部分。社会整合在行政体系中达成,并且政治博弈进入行政体系当中。第二,派生系统,即由企事业单位组成,这些治理主体与基层政府不是上下级行政隶属关系,它们负责某一个社会领域的事务,与基层政府构成既竞争又合作的复杂关系。这些治理主体包括党政系统的“外围组织”如工、青、妇,(包括辖区外的)企事业单位。挂靠行政部门的社团组织也在其中,但这类社团组织基本上不是具有独立性、自主性和促进性的社会组织,类似于“封闭性自治组织”(close corpora⁃tion),亦即依附于权威授权的社会自治组织[17]。党政系统外的治理主体主要起到宣传政策、处理诸如福利、卫生等社会事务,发挥政府助手的作用。第三,吏役系统,即体制外的官治与民治相结合的组织形式,主要由三个部分构成:一是村民自治组织。村(居)干部群体由村支书、村主任以及村会计所谓三职干部及其他两委干部组成。二是公安系统辅助力量。由辅警群体组成,因基层社会的利益分化、社会流动的扩大化、职业群体的多元化等,基层警务力量难以应对,因此雇佣人员——“辅警”成为重要的补充力量。三是雇佣群体,即完全依靠市场化机制构建起来的雇佣群体。他们居于国家与社会的交汇点上,承载着行政机构分配下来的任务。
上述治理体系具有如下政治和行政特性:首先,党政双重权威体制治理逻辑、官僚群体的治理规则和依据与标准的(韦伯)科层制形似但质不同,它具有政治嵌入行政的体制特性,官僚群体是一个负有“政治使命”的特殊群体。其次,党政系统外围组织及企事业单位,乃是政府治理的延伸部分,具有派生群体的特征,但实质上是党政权力的代理部分,由国家治理体制特性所决定,既是被纳入治理体系中的对象,又是实现有效治理的组织形式。再次,吏役体系是在基层治理结构中起到连接政府与社会、政府与市场的中介组织形式,包括村民自治组织、官办或半官半民的社会组织,包括市场组织,以及政府强力部门的力量补充——辅警力量。
基层秩序体系由政治动员型体制和行政压力型体制的特性,形成比较完整的政权权威秩序整合体系。第一,政府权威。建构在自上而下的政治与行政授权关系之上,基层政府是国家政权代理人,是基层社会权威性资源与配置性资源的中心。第二,代理治理模式。典型运作形式是自上而下的行政任务下派方式,比如上下级政府之间签订的“行政目标管理责任书”,这使它与韦伯式的基于对正式制定的规则和法令的信赖基础上的官僚组织区别开来,前者造成大量的“非正式”制度和“变通”实践成为基层政府治理行为中的“均衡”常态,与此互为表里,代理治理的运作逻辑造成基于不同的控制权基础上的多重权威中心治理结构。第三,社会原子化。集权化与行政化的后果是社会自主支配空间日益萎缩,社会自组织的缺位,政府与公民之间缺乏整合机制,彼此沟通管道不顺畅。总之,基层社会秩序就确立在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并存、象征性权力与实质性权力互为转化的结构形式上。
结 论
基层政权的现代转型即以建构公共性社会关系为基本任务的公共政权建设含义。在王权时代,基层政权为皇权服务,代表基层政权的是县衙及其衍生群体和雇佣群体,后者属于直接与民众打交道的官制授权系统的基层权力形式。始于近代民族国家建构(state-making),基层政权转而为国家服务,并且它的治理能力因国家权力范围延展而获得制度化或“正规化”(乡镇行政的设置)的支持从而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
一个主流性的看法,认为近代以来的基层政权建设改变了“皇权不下县”的权力结构,是现代国家官僚体制正规化和合理化的必然趋势。表面的意思不错,但实质上(如前所述)国家权力——传统称皇权,现代称国家——从来就没有离开过基层社会,“皇权不下县”,并非是历史的真实情况,而此时国家权力表现为大规模的下移,部分原因是传统基层社会秩序的瓦解,而国家权力需要重新集中和强化;部分原因是国家现代化需要从乡村社会提取更多的资源和提升社会动员能力。所以,基层政权现代化表明的只是基层秩序的权威再造和重塑政权代理人的变化。
也就是说,基层政权建设的紧要问题并非要明确民众权利以及与国家的权利关系(这是“国家政权建设”完整内涵的一个方面),或者说,现代治理原则——公共性或公共规则——既没有历史的基础,也没有现实的条件。在此,所谓“国家政权建设”乃是国家主义主导的现代化过程。在这个意思上讲,不是基层政权建设未能完成政府公共性问题的逻辑论证——社会相对于国家来说才具有基础性意义,而是传统国家向现代国家转型的“历史的惯性”的政治逻辑展开形式而已。
但现代政权与历史的关联却不能成为对传统治理与现代治理做出无差别比附的理由,因为现代治理的特征与传统治理具有本质的不同,比如现代政治国家的特性、利益分殊的社会结构、基于规则和契约上的市场秩序、组织化的现代社会联系方式,等等。从国家政权建设上看,政权的现代化是一个基层政权建设和基层社会“去自治化”(相对于传统自发秩序)的过程,与帝制时期建立在皇权、绅权、族权统一的基层社会秩序不同,现代基层社会秩序的最大变化,是党政系统双重权威几乎嵌入基层社会的所有方面。换言之,当今中国基层社会秩序建立在自上而下的基层政权组织的权威支配关系上,并没有建立在自下而上的,以习惯、习俗、惯例、自治权为基础的公共性社会关系上。
也就是说,从基层政权组织的功能性权力配置和治理原则上,与旧的政治权力格局比较,还有很大的改变空间。“在实质性的管辖权方面,基本的权力格局还是旧的,统一的行动规则——法律和税制体系并没有确立,农民仍然处于分割化政治单位的统治中。”[18]在这样的原则和功能配置下,基层政权承担着基层社会管理和经济建设的基本任务,比如,它的最重要的经济功能是把农村公共资源由下向上集中,以完成国家现代化的目标要求,国家与社会的一体化是达成目标的必要的条件。惟其如此,基层行政权力几乎被扩大到基层经济和社会的所有公共领域之中。
概括地讲,当前基层政权公共性缺失所针对的是一个体制问题,集中体现在集权与分权的矛盾、压力型体制、“政权经营者”[13]52、晋升锦标赛治理模式和行政发包制[19]、政府制度异化[20]等结构性特征上。因此,建构基层政权的公共性,更本质的含义是:基层政权除了为公众服务、为公民自身的利益而存在,没有任何自身的目的,这是基层政权存在的合法性所在,也是基层政权完成现代转型的完整含义。
[1]周保明.清代地方吏役制度研究[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115-117.
[2]张建斌.略论唐代县级政权中的胥吏[J].理论月刊,2005,(9):103-104.
[3]顾炎武.日知录集释:卷八·吏胥[M].黄汝成,集释.秦克诚,点校.长沙:岳麓书社,1994:292.
[4]顾炎武.日知录集释:卷八·都令史[M].黄汝成,集释.秦克诚,点校.长沙:岳麓书社,1994:292.
[5]赵世瑜.吏与中国社会[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4:2.
[6]顾炎武.日知录[M].陈垣,校注.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7:470.
[7]叶适.水心别集:卷一四·吏胥[M]//叶适集:第3册.刘公纯,王孝鱼,李哲夫,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61:808-809.
[8]顾炎武.顾亭林诗文集:卷一·郡县论八[M].华忱之,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3:16.
[9]孔飞力.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43.
[10]于建嵘.国家政权建设与基层治理方式变迁[J/OL].求是理论网,2011-11-03.http://www.qstheory.cn.
[11]杨贞德.自由与自治:梁启超政治思想中的“个人”[J].二十一世纪,2004,(8):53-59.
[12][美]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M].王福明,译.杭州: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225.
[13]张静.基层政权:乡村制度诸问题[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
[14]申端锋.二十世纪中国村庄权力研究综述[J].学术界,2006,(4):268-274.
[15]王铭铭.村落视野中的文化与权力[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9-16.
[16]孙立平,郭于华.软硬兼施:正式权力非正式运作的过程分析[G]//清华社会学评论.厦门:鹭江出版社,2000:21-46.
[17][美]理查德·C.博克斯.公民治理:引领21世纪的美国社区[M].孙柏瑛,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20.
[18]张静.国家政权建设与乡村自治单位——问题与回顾[J].开放时代,2001,(9):5-13.
[19]周黎安.行政发包制[J].社会,2014,(6):1-38.
[20]赵树凯.乡镇治理与政府制度化[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8-11.
Public Construction of Grassroots Political Power: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
ZHOU Qing⁃zhi
(Institute of Political Science,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Beijing 100028,China)
Publicity runs through grassroots political power construction,of which includes two meanings.One is the legitimacy of the existence of political power,and the other is the social basis of the nature of politi⁃cal power.Historically speaking,the construction of modern political power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publicity may not have internal consistency.Because when publicity is taken as a means to achieve national strength,grassroots political power construction will be working on resources absorbency,social mobilization and con⁃trol,which will inevitably build a relationship of social dominance and asylum.When publicity is taken as a goal of realizing equal citizen rights,grassroots political power construction can only be working on the public nature of social justice and social welfare.Therefore the construction of grassroots political power involves the change of political logic and the nature of power.In other words,the discussion about the construction of grass⁃roots political power needs to be based on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logic and realistic development of its pub⁃licity construction.
grassroots political power construction;government publicity;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
D630
A
1009-1971(2017)04-0002-06
[责任编辑:张莲英]
2017-04-20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我国县级政府公共产品供给体制机制研究”(11AZZ006)
周庆智(1960—),男,内蒙古赤峰人,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从事中国地方政治、政治社会学、社会转型与社会变迁、历史学、文化人类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