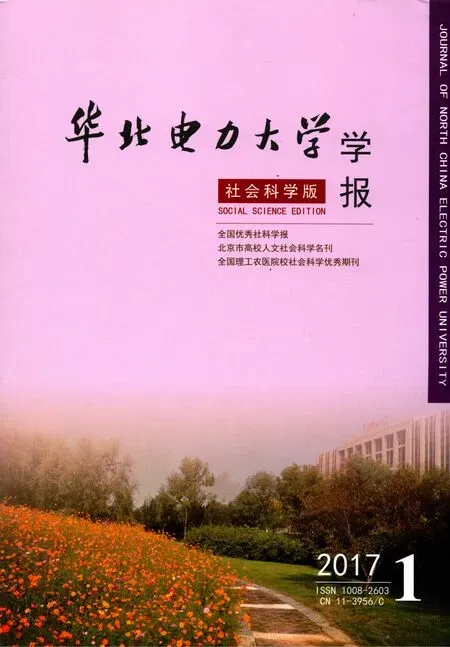唐人所述“艳诗”概念论析
熊 啸
(复旦大学 中文系,上海 200433)
● 人文新论
唐人所述“艳诗”概念论析
熊 啸
(复旦大学 中文系,上海 200433)
艳诗一词最早见于梁代萧绎的《戏作艳诗》,现可见唐人对其论述共有四处,分别是《南史·江总传》、《郡斋读书志》引李康成论《玉台新咏》语、《大唐新语》及元稹《叙诗寄乐天书》。其所述对象各有不同,然对其加以分析整理,则可发现艳诗的内涵在唐人论述的语境中已基本完备,其外延亦趋于清晰,后世与艳诗相关的一些独特现象如戏作、溯源以大其体、赋以教化意义等在此时也已出现,艳诗暧昧的形象遂逐渐形成。唐人的论述对艳诗形象在后代的接受及演变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艳诗;宫体诗;唐代;语境
关于艳诗研究,尚待解决的问题还有不少。就其在概念及性质方面的问题来说,研究者或注意到其与艳曲、艳歌之间的关联性,通过对后者含义的梳理来对前者的含义进行推导;或通过对大量作品的阅读分析从学理的角度为其作出定义,这些当然都是很有必要的。但一些较容易为人所忽视的问题是,艳诗在其产生初期的评述语境中所呈现出的是一个怎样的概念?它具有什么内涵及外延?这与其在后代视野中的形象又有何关联?一些常为研究者所引用的文献多未经过这一视角的研读,因而也就未能充分发挥出其对艳诗研究所可能产生的作用。故本文拟对唐人论述艳诗的资料作一全面系统的梳理分析,以期总结出其在此时语境中所具备的大致含义,并以此作为艳诗概念在后世研究的一个基础。
一、萧绎《戏作艳诗》
在论及唐人的论述之前,有必要对目前可见艳诗最初的出处略作分析,即收录于《玉台新咏》中萧绎的《戏作艳诗》。这首诗就内容来看与《古诗·上山采蘼芜》有较大的关联性,但萧绎并没有采用晋宋时常用的“拟”字,而是用了一个“戏作”,这说明他对这首诗的定性不同于一般的拟作。事实上以“戏”为题的创作在当时已形成了一定的风气,其在不同诗题中的含义也不尽相同,如以“戏赠”为题的诗作多含有对所赠对象的嘲弄或戏谑,而以“戏作某某体”或“戏拟”为题的诗作则可能意味着此体风格并非为作者所熟习,此作带有一种尝试的性质,其“戏”字表明了这一创作的非正式性、随意性。
萧绎这首《戏作艳诗》的情况更近于后者,但又有所不同。他并未将其命名为《戏拟艳诗》,是因为他所拟的原作并非一首艳诗,艳诗的概念在彼时尚未形成,对其诗题的解读应是:他借用了原诗的框架,却对其作了较大程度的改写,使其成为了一首艳诗,且由于其改动幅度较大,因而在某种意义上产生了对原诗的一种颠覆感,是以他采用了当时颇为流行的“戏”字来对其加以定性。两首诗的区别主要在于:原诗写的是女子与故夫相逢的场景,并在大段的对话之中显示出其品行及劳作能力的优秀,对此诗主旨的阐释可以是多样的,但可以肯定的一点是,此诗对女子关注的重点在于其德行,其容貌(也即诗中所说的“颜色”)则被一笔带过。萧绎的诗作则借用了二人重逢这样一个框架,将其内容置换为对女子神态、动作、情感的描绘,塑造了一个满怀愁绪与故情,却又踌躇不已、欲言又止的女子形象。其关注点由“德”向“情”的转移似正可对应于诗歌这一文学体裁的创作主旨由早先的“言志”向魏晋以后“缘情”的转移,此时的诗作明显表现出一种脱离道德政教观念的倾向,对女性形体及情感的审美表现开始成为主流。因而此诗的“戏作”也可以理解为此时宫体诗的创作对儒家诗论的自觉背离,它使得诗歌原本对女性的关注由合于道德观念的“德行”以一种戏谑性的方式转移到了容貌与情感上,这与萧纲所说的“立身先须谨重,文章且须放荡”[1]3010正相吻合。故从这个角度来看,艳诗在其出现的初期就带有一种“叛逆”的色彩,作者们对此或多或少都抱有一种自觉的意识。
二、《南史·江总传》
《南史·江总传》中有这样一句记载:
(总)既当权任宰,不持政务,但日与后主游宴后庭,多为艳诗,好事者相传讽翫,于今不绝。[2]946
这是初唐史书中唯一一处对艳诗这一概念的描述,其所指向的是江总与陈后主“游宴后庭”时的诗歌创作。陈后主《与江总书悼陆瑜》亦云:“吾监抚之暇,事隙之辰,颇用谈笑娱情,琴樽间作,雅篇艳什,迭互锋起。”[1]3423什即诗篇之谓,艳什也即是艳诗。在初唐史臣的批判语境中,梁、陈、隋的诗风乃是一脉相承,其总体上皆是趋向于雕琢浮艳的,这正是宫体诗的特点,试看以下评价:
其(按:指简文帝)序云:“余七岁有诗癖,长而不倦。”然伤于轻艳,当时号曰“宫体”。[3]109
总笃行义,宽和温裕。好学,能属文,于五言七言尤善;然伤于浮艳,故为后主所爱幸。[4]347
炀帝不解音律,略不关怀。后大制艳篇,辞极淫绮。[5]379
其“轻艳”、“浮艳”及“淫绮”固然有程度上的区别,亦带有不同史书作者各自的倾向性,但可以认为其所指向的诗作风格皆是一致的,即宫体诗风。《陈书·后主本纪》亦称:“亡国之主, 多有才艺,考之梁、陈及隋,信非虚论。然则不崇教义之本,偏尚淫丽之文,徒长浇伪之风,无救乱亡之祸矣。”[4]119故在这一语境中,宫体诗与艳诗并无二致。在唐人看来,陈后主及江总的创作是梁代宫体诗风持续发挥影响的结果,其与宫体诗及后来隋炀帝所作的“艳篇”皆可视为艳诗看待。需加以说明的是,学界对于宫体诗是否等同于艳诗这一点存在争议,有学者曾就姚思廉(其论继承自其父姚察)与魏征对宫体诗描述的差异指出当时人与后来人对于宫体诗的认识存在着偏差。但为了解唐人是如何认识“艳诗”这一概念的,则仍应进入到当时对宫体诗的主流批评语境当中去,试看以下评价:
清辞巧制,止乎衽席之间;雕琢蔓藻,思极闺闱之内。后生好事,递相放习,朝野纷纷,号为宫体。[5]1090
其意浅而繁,其文匿而彩,词尚轻险,情多哀思。格以延陵之听,盖亦亡国之音乎![5]1730
可知其所关注的不仅仅是诗风的新变与轻艳,还有“衽席之间”、“闺闱之内”等内容倾向,且后者被强调得更加明确,第二则的“意”、“文”、“词”、“情”则可视为对宫体诗的整体评价,故可以认为,以魏征为代表的初唐史臣对宫体诗特点的描绘主要集中在其内容的香艳、文辞的轻艳、情调的哀艳上,这一评价明显带有一种负面的意味,这是他们对其内涵的基本认识。对于一类以题材命名的诗作(如山水诗、边塞诗、咏物诗)来说,其外延得以确立的依据主要在于其内容,而风格、情调则是相对次要的,但艳诗的微妙之处则在于其究竟是以内容得名,还是以风格得名的?从概念出现的先后来说,艳歌要早于艳诗,而艳歌之“艳”指的是其音乐的性质,但在南朝人对艳歌的批评语境中,其内容显然也被纳入了视野,如《宋书·乐志》“哥(歌)词多淫哇不典正”,[6]552《文心雕龙·乐府》“诗声俱郑”[7]255等,可知其“艳”也逐渐带有了内容上的因素,艳诗这一称谓出现在梁代,其与艳歌之“艳”的连接点应当在内容这一点上。也就是说,内容是判定一首诗是否为艳诗的关键,但同时轻艳、浮艳的风格及哀艳的情调也是其身份的标示,且对于一些论诗家而言,风格、情调的轻艳已足以引起他们的警惕,更不待论其内容的香艳了。
三、《大唐新语》
刘肃在《大唐新语》中对宫体诗曾有过一段著名的论述:
太宗谓侍臣曰:“朕戏作艳诗。”虞世南便谏曰:“圣作虽工,体制非雅。上之所好,下必随之。此文一行,恐致风靡。而今而后,请不奉诏。”……先是,梁简文帝为太子,好作艳诗,境内化之,浸以成俗,谓之宫体。晚年改作,追之不及,乃令徐陵撰《玉台集》,以大其体。[8]234
此语可疑之处不少,是已为一些学者所指出,如沈玉成《宫体诗与〈玉台新咏〉》称“萧纲现存的作品里,丝毫也看不出‘追悔’的迹象。现在考定《玉台新咏》编定时萧纲年仅三十一、二,这就更谈不上‘晚年追悔’了。”[9]徐国荣,梁必彪《宫体诗文献记载之矛盾分析》则提出“先是”以后云云不见于他书记载,乃是“刘肃完全不合逻辑的道德说教”,[10]这是因为当时萧纲及宫体诗已成为反面的典型,人们在需要说教时便将其拿来,而不必考虑其合于逻辑与否。二说颇是,唯后文对“以大其体”也一笔抹倒,则可商榷,要之刘肃此说的问题主要出在“晚年改作,追之不及”上,而编《玉台新咏》“以大其体”的目的则仍合于逻辑情理,沈文对《玉台新咏》在编纂上表现出不少与萧统《文选》的对抗意识这一点作了详细分析,可为之注脚。
刘肃此说中“艳诗”共出现了两次,一指唐太宗所作,一指萧纲所作。关于后者,也即在唐人的观念中宫体诗等同于艳诗,本文已有分析。关于前者,则可参考前文所引《南史·江总传》中的“于今不绝”等语,这说明唐代的鼎革及新诗风的倡导并未使当时的诗风发生立竿见影的转变,相反宫体诗风仍发挥着其持续的影响力,此亦“大其体”的结果之一。事实上不止唐太宗,劝谏的虞世南本人曾受知于徐陵,其诗风亦颇受其影响,此外如长孙无忌、李百药、杨师道等大臣亦多有艳诗创作,也即此时虽已有了新的文学意识,但时人的创作却未必能完全与此种意识保持完全一致。且值得注意的是,唐太宗在这里也用了“戏作”这样种方式或曰说辞为自己创作艳诗的行为加上了一个限定。不同于梁代,此时艳诗的写作已不能获得人们观念上的认同,在初唐史书对宫体诗大加批判的背景下,喜爱艳诗的创作者在写作时所抱有的一种微妙的心态是可以想见的。因而唐太宗的“戏作”便与萧绎等人的“戏作”有了不同,他此举更多是为了消除艳诗创作的道德焦虑感,因为在当时人的观念看来,写作艳诗已属不当之事,身为人君而作艳诗更是会予人以“上之所好,下必随之”的口实,那么唯有在戏作这种带有“偶一为之”意味的暧昧语境中,艳诗创作方不至于使其遭受到太大的道德困境。故在虞世南劝谏以后,唐太宗便止而不作,《新唐书》在这段描述后又加上了一句“朕试卿耳”,[11]3972此言是否有所根据固不可知,但也很好地说明了“戏作”这一独特的创作方式给艳诗作者所留下的余地。“戏作”在后世艳诗的标题中更是成为了一个常见的限定语汇,唐太宗此举或曰刘肃这一描述的意味对于后之作者来说应是很能领会的。
四、李康成《玉台新咏》论
李康成是盛唐中唐间人,曾仿《玉台新咏》一书编有《玉台后集》,其论《玉台新咏》之语见晁公武《郡斋读书志》:
昔陵在梁世,父子俱事东朝,特见优遇。时承平好文,雅尚宫体,故采西汉以来词人所著乐府艳诗,以备讽览。[12]97
此处的“艳诗”与之前所论略有不同,其指的是《玉台新咏》中区别于“宫体”以外的西汉以来诗人的诗作。然而为何不称“乐府艳歌”?这可能是因为《玉台新咏》的编纂目的是为了给宫中女子消闲解闷,以作“讽览”之用,其意故不在歌唱这一点上,关于此徐陵的《玉台新咏序》说得非常明白。崔炼农《〈玉台新咏〉不是歌辞总集》一文通过多方面资料爬梳,提出此集“所录作品以徒诗为主体”,“乐府歌辞作为‘杂诗’之一得以收录,但配乐痕迹全被清除,变成纯粹的‘诗’文本”,[13]其说甚是。然而徐陵《玉台新咏序》又有“撰录艳歌,凡为十卷”[13]序13之语,则又显示出“艳歌”、“艳诗”的使用在当时并未区分得非常清楚,这也反映出这两个概念之间密切的关联性:艳歌之词即可视为艳诗,而艳诗亦有依曲而作者。艳歌在当时大致有两种含义,一是汉乐府中的《艳歌行》诸调,二是南朝乐府中的吴歌西曲,当时语境中的艳歌多指后者,艳诗概念的产生亦与之关联甚大。此外徐陵将书中所收作品概称为艳歌,李康成将书中西汉以来诗作概称为艳诗,则显示出他们对艳歌或艳诗的判定皆采取了一个较为宽泛的标准,正如梁启超所说,“其甄录古人之作,尤不免强彼以就我”,[14]551此亦是“大其体”在操作方式上的具体表现,即为提高宫体诗或艳诗的地位,遂将这一概念出现以前的诗作皆归入其序列之中,以构成其存在合理性的依据。后来袁枚甚至称“夫《关雎》即艳诗也”,[15]1504此亦是他为大“艳诗”一体而采取的策略。
五、元稹《叙诗寄乐天书》
元稹于元和十年作有《叙诗寄乐天书》一文,其中记叙了其学诗作诗的经历,并对自己至元和七年为止所作的八百余首诗作了一个分类,其中一类便是艳诗:
又有以干教化者。近世妇人晕淡眉目,绾约头鬓,衣服修广之度,及匹配色泽,尤剧怪艳,因为艳诗百余首。词有今古,又两体。[16]353
其可注意者有两点。一是他描述这百余首艳诗所描写的内容乃是“近世妇人”妆容、发型、服饰之怪艳,抛开其“怪”的评价,这些内容其实并不出宫体诗描绘女性的范围,而他将艳诗与悼亡诗分开,则表明他对二者的区别有了较为清晰的认识,相反《玉台新咏》则将潘岳的《悼亡诗》收录在内。二是他自称其创作的目的是“以干教化”,这便与宫体诗有了较大的区别,从而回归到儒家诗论的体系中去了。白居易的新乐府中有《时世妆》一诗,其内容及主旨皆非常符合元稹此处的描述,然而《时世妆》是否真的可以称为艳诗?试将其与元稹的艳诗作一对比:
时世妆(白居易)
时世妆,时世妆,出自城中传四方。时世流行无远近,腮不施朱面无粉。乌膏注唇唇似泥,双眉画作八字低。妍媸黑白失本态,妆成尽似含悲啼。圆鬟无鬓椎髻样,斜红不晕赭面状。昔闻被发伊川中,辛有见之知有戎。元和妆梳君记取,髻椎面赭非华风。[17]235
恨妆成(元稹)
晓日穿隙明,开帷理妆点。傅粉贵重重,施朱怜冉冉。柔鬟背额垂,丛鬓随钗敛。凝翠晕蛾眉,轻红拂花脸。满头行小梳,当面施圆靥。最恨落花时,妆成独披掩。[16]682
将文本加以对比,则可发现二者之间的差别非常明显,前者虽对女子的妆容作了详尽的描绘,却并非出于一种审美的目的,相反处处掺杂着作者负面的评价,如“唇似泥”、“八字低”、“失态”、“悲啼”等,皆暗含批评的意旨,“辛有”句更是使用了一个典故来警告世人:这种本非中原妇女妆容的流行并不是一个好现象,它可能昭示着国运的衰微。这种将民众间流行的风气与国家的治乱联系在一起的方式是儒家史观中常见的逻辑,白居易此诗正贯彻了一种史家的记录及批判意识。元稹的《恨妆成》则完全相反,其诗完全不见批评之意,而只有一片欣赏之情,其自“傅粉”至“当面”八句写的全是女子(即其旧日恋人)施妆时的情景,却一气贯注,丝毫不见拖沓堆垛之感,其末句“最恨”二字乃是反写,实则是喜爱到极致的一种表现,此诗何曾有一点“以干教化”的意味?据此观之,元稹的自述恐有不可靠之处。《叙诗寄乐天书》作于元和十年元稹贬往通州的途中,由于仕途屡遭不顺,加之听闻通州自然环境极其恶劣,元稹担心自己可能一去不回,因而将自己的八百余首诗外加前往通州途中所作的五十一首诗托付给白居易,嘱其为之保管,冀有万一之时,自己的诗作也能得以留存下来。因而他的这篇自述实有托付后事的用意,这样他对自己诗作的说明就很可能成为后人认识其人其诗的指南,是以他不得不郑重其事,对自己诗作“寄兴”的因素及有补于世的意图作了明确的强调,甚至为自己并无教化用意的艳诗也安上了这样一个名分。
后人对元稹艳诗的认识多与教化无干,如杜牧《唐故平卢军节度巡官陇西李府君墓志铭》一文便指责元、白艳诗的“淫言媟语”,以至“入人肌骨,不可除去”,[18]744则反成有碍教化了。宋人赵令畤《辨〈传奇〉莺莺事》所录王性之《〈传奇〉辨正》称“仆家有微之作《元氏古艳诗》百余篇,中有《春词》二首,其间皆隐‘莺’字,”其列举篇目如《春词》、《莺莺诗》、《离思》、《杂忆》、《梦游春》等,皆是元稹写其恋情的诗作,后则谓“微之所遇合虽涉于流宕自放,不中礼义,然名辈风流余韵照暎后世,亦人间可喜事。”[19]卷五亦丝毫不及“教化”云云。然而抛开元稹的自叙,他的创作实则为艳诗的题材作出了新的突破,即将诗人自身的恋爱经历写入了诗中。此前的艳诗包括宫体诗中极少此类创作,而吴歌西曲等出自女子声口的作品又非文人创作,文人拟作则为代言体,二者不属于一个系统。继元稹之后,晚唐艳诗中最具特色的一类作品便是此种,这意味着元稹艳诗的创作对后世的影响及后人对其艳诗的接受皆是围绕着这一点展开的,这类艳诗也因含有其“本事”从而多在后世成为关注或争议的焦点。
[1]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M].北京:中华书局,1958.
[2]李延寿.南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5.
[3]姚思廉.梁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3.
[4]姚思廉.陈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2.
[5]魏征,令狐德棻.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3.
[6]沈约.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7]刘勰.文心雕龙义证[M].詹锳,义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8]刘肃.大唐新语[M]//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9]沈玉成.宫体诗与《玉台新咏》[J].文学遗产,1988(6):55-65.
[10]徐国荣,梁必彪.宫体诗文献记载之矛盾分析[J].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12):22-29.
[11]欧阳修,宋祁.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12]晁公武.郡斋读书志校证[M].孙猛,校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13]崔炼农.《玉台新咏》不是歌辞总集[J].云南艺术学院学报,2003(1):31-35.
[14]徐陵.玉台新咏笺注[M].吴兆宜,注.程琰,删补.穆克宏,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5.
[15]袁枚.小仓山房诗文集[M].周本淳,标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16]元稹.元稹集[M].冀勤,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2.
[17]白居易.白居易集笺校[M].朱金城,笺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18]吴在庆.杜牧集系年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8.
[19]赵令畤.侯鲭录[M].清知不足斋丛书本.
[20]中华书局编辑部.全唐诗(增订本)[M].北京:中华书局,1999.
(责任编辑:王 荻)
A Discuss on the Conception of Amorous Poem Described by Tang People
XIONG Xiao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China)
The word “amorous poem” firstly emerged in Liang Dynasty, it’s the workAAmorousPoeminHumorousStyleby Xiao Yi. There are four records of document concerning with this concept in Tang Dynasty, they arelegendofJiangZonginNanShi, a description ofYutaixinyongby Li Kang-cheng recorded inJunzhaidushuzhi,DatangxinyuandALettertoLe-tiantointroducemypoemsby Yuan Zhen. The objects of these descriptions are different, but after analyzing them, we can find that the connotation of amorous poem had been determined in their contexts, its extension had also become distinct, and some special phenomena with amorous poem in later ages such as humorous style, traceability and imposing the significance of education had all appeared in this period, which endowed an ambiguous characteristic on amorous poem. The descriptions by Tang people had caused a conclusive influence to the receptions of amorous poem in later ages.
amorous poem; gong-ti poetry; Tang Dynasty; context
2016-12-20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好色与‘好色’之间:日本江户、明治时期艳诗研究”(项目编号:2016M591587)。
熊啸,男,复旦大学中文系博士后。
I207.22
A
1008-2603(2017)01-0097-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