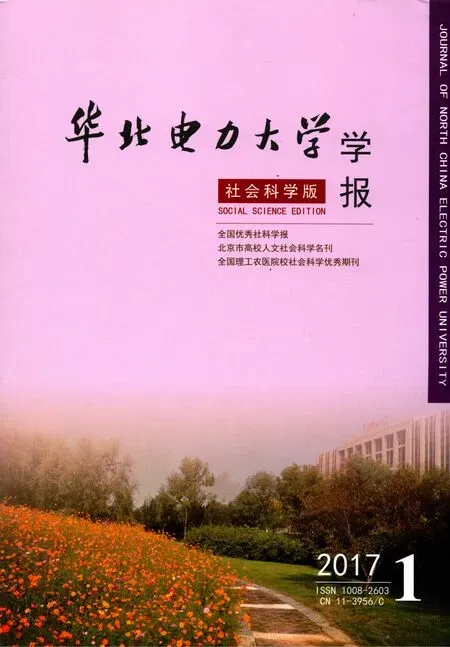社会治理视角下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互构与协调
黎海波
(中南民族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4)
社会治理视角下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互构与协调
黎海波
(中南民族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4)
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存在着二元互构的张力。效率和公平是指导经济和社会政策及其发展战略的两大基本价值原则。效率与公平的增长有时并不同步,甚至还会有较大的落差。效率与公平的对立统一也决定了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对立统一。经济发展和社会基础以及社会福利的协调发展,构成了社会管理或治理的一项基本准则。经济新常态下的社会治理应围绕加强社会建设、倡导社会参与和鼓励社会创新这三个方向来积极构建社会新常态,从而通过理念、主体、体制和机制等的创新来实现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的转型。
社会治理;经济发展;社会发展;社会管理;社会福利
管理起源于人类的共同劳动与社会活动。自从有了人类社会,就有了社会管理。原始社会时期,氏族和部落实行的是一种自主管理。氏族和部落的成员,共同对氏族与部落事务进行管理。其中,由母系氏族到父系氏族的变化,无不与生产力的变化密切相关。总体而言,由于当时的生产力低下,社会关系也相对简单,在原始共产制之下,人们共同劳动,平均分配。
随着生产力水平的进一步提高,产品出现了剩余,私有制逐步发展,社会分化为剥削阶级与被剥削阶级,于是就产生了国家。“国家的本质特征,是和人民大众分离的公共权力”。[1]在国家产生之后及其历史发展的长河之中,社会管理便在国家与社会的辩证张力中演变出不同的形态。[2]
马克思认为,人类社会就是一个“一切关系在其中同时存在而又互相依存”的机体。[3]它是一个包括物质生活、政治生活、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等不同要素和关系的有机整体。宏观社会管理(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社会管理发展为社会治理,治理概念是一个现代化的概念,治理则是一种更有成效、更为成熟的管理)[4],就是把社会当作是一个有机整体,通过运用计划、管控、指导、沟通与协调等手段,对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与社会事务进行统筹管理,使社会系统协调有序、良性运行的过程。[5]11-12它包括了经济子系统的管理、政治子系统的管理、文化子系统的管理和社会子系统的管理。而微观社会管理就是对“社会子系统”进行管理,涉及到对社会生活、社会组织与社会事务的管理,包括社会安全、社会保障和社会服务等。
一、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张力与互构
社会管理在涉及经济因素的作用与影响时,通常关注的是经济基础与政治、意识形态等上层建筑之间的相互关系与影响。[5]11尤其是对于宏观社会管理而言,更是如此。在宏观的社会系统中,经济活动方式制约着人们的社会与政治活动方式。同样,社会管理活动的发展也要受到经济发展水平与活动方式的影响。
无疑,经济建设与发展构成了社会建设与发展的基础,但是二者之间并不是简单的“正相关”关系,而是存在着二元互构的张力。
经济子系统,是人们为满足一定的物质需要从事的物质生产活动而构成的经济关系系统。[6]3人们从事物质生产活动的内容是利用各种经济资源来获取经济收益。其核心原则是追求效率,即通过经济资源的最佳配置来调整投入与产出之间的关系,从而实现利益最大化。
社会子系统,是在一定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政治体制下,社会成员围绕社会性公共资源的供给与配置而构成的社会关系系统。这里所说的社会性公共资源,是指社会成员日常生活所必需(但由于其具有较强的经济外部性和公共物品性),而主要又是通过政府和社会组织等的供给才能够满足的资源,涉及安全、就业、环境、教育、医疗卫生、文化、科技、体育和艺术等方面的资源。[7]人们获取社会性公共资源的核心原则是追求公平。
经济子系统中人们构成关系的 “效率”原则与社会子系统中人们构成关系的 “公平”原则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矛盾与张力。
从抽象的社会层面而言,在一定的社会制度之下,社会基础的发展取决于经济基础的发展,而经济基础的发展又取决于生产力的发展。因此,生产力水平越高,社会基础的水平也就越高,二者呈现出一定的正相关关系。[8]这就是说,生产力水平和经济基础整体上促进了社会基础的发展。
从具体的社会层面而言,经济子系统中人们构成关系的“效率”原则,越是展开其张力,则越容易加剧社会分化,引发社会不公;而社会子系统的“公平”原则,越是展开其张力,则越容易缩小社会分化,促进社会公平。
一方面,经济子系统的运行使得经济主体之间在经济资源和经济利益方面的差距逐渐拉开。而这种经济资源和收益的差距也会对社会性公共资源的供给与配置产生一定的影响。拥有较多经济资源和经济利益的社会主体就希望享有相应的社会资源和公共产品,这似乎是对他们个体的一种“平等”,而这种“平等”却又会导致其他社会成员在获取社会资源上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如果持续发展下去,必然会加剧社会分化,引发社会矛盾和冲突。
另一方面,社会子系统对于经济子系统的效率分化所导致的社会不公,一开始,往往是自发地适应。然而随着经济主体之间在经济资源和收益上的差距越来越大,不同个体和阶层的社会主体获取的社会资源和公共产品也就逐渐地呈现出 一种“不平等”和分化的状况,社会矛盾就会逐步累积。这种矛盾逐步地由个体矛盾发展为一种集体或阶层矛盾时,社会子系统的“公平”原则就对经济子系统产生一种“反构性”,这种反构性就是通过一定的社会冲突体现出来,从而要求和推动经济子系统进行相应的调节,对 “一次分配”和 “二次分配”的状况做出一定的调整与改进,从而促使经济子系统与社会子系统之间形成一定的“适应性”。[6]4-5
在我国当前的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中,存在着较为严重的不协调与反构性问题。新中国成立至20世纪70年代末期,我国主要依靠计划经济体制来实现社会管控,结果造成了大量的决策失误和资源浪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又试图借助于市场经济体制和集中力量进行经济建设来解决社会发展问题,结果却导致了更多的利益分化、冲突和社会危机。[9]一方面,经济社会结构亟待优化,市场过度扩张使得经济与社会发展良性互动的问题不断凸显,由此也揭露出相应的经济与社会管理的不足;另一方面,我国在对待贫富分化等问题上的社会管理成效始终不显著,某些利益集团基于其经济优势勾结和利用权力获得更多的资源配置,这就导致了社会不满情绪日益膨胀,社会失范现象较为严重,[10]社会发展的风险大幅增加。随着这种收入分配和利益问题的积累,不同地区、行业和阶层的社会成员在其维权意识的推动下形成一定的社会反构,即通过一定的社会冲突体现出来,从而对我国的经济与社会管理的有效性提出了较为严峻的挑战。
二、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协调与共进
效率与公平,既是人类社会追求的两大目标,也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争议较大的重要主题。效率和公平也是指导经济和社会政策及其发展战略的两大基本价值原则。效率与公平的增长并不同步,甚至还会有较大的落差。效率与公平的对立统一也决定了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对立统一。
既然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之间是一种对立统一的关系,那么如何才能避免其浅层的对立与矛盾而促成其深层的协调与统一呢?
在我们的现实社会生活中,实际上存在两种社会公平,“一种能够促进经济效率和社会发展,另一种则不能促进经济效率和社会发展。”[11]从效率与公平的角度来看,经济子系统与社会子系统的相互联结和协调的区域正好是效率与公平相统一的区域。[5]15
一方面,经济发展要为社会发展与社会福利奠定基础。这就要求生产力水平的提升和物质财富的增长能够推动社会性公共资源的增长与供给,也就说要求经济主体既有能力也有意愿持续地将经济产出的新增财富的部分转化为社会性公共资源供给;另一方面,社会性公共资源在其配置过程中,政府和社会主体有能力也有意愿将社会性公共资源配置和用于促进经济持续增长的相关社会事业和社会福利。[6]5
位于经济子系统与社会子系统联结区域的社会保障系统,正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了效率与公平的相对统一。一方面,社会保障系统能通过对收入分配格局的再分配,起到调节收入差距的作用,从而改变社会中不同成员和阶层的人们的收入分配状态, 缩小贫富差距,为社会成员创造了一种结果的公平。此外,它也能通过为社会成员提供一定的生活保障,使社会成员不会因先天的弱势、疾病或某些社会风险的侵害而陷入困境,从而为社会成员提供了一种起点和过程的公平;另一方面,社会保障系统对于市场经济的促进作用,就在于它能缓解社会矛盾、解决社会问题、稳定社会秩序、保证社会再生产中劳动力的供给、促进劳动要素的合理配置、刺激需求以及增加积累等,从而为经济的发展创造重要条件。
市场关注和追求经济效率,政府和社会则关注和追求社会公平。只有在国家、市场与社会的三方配合之下,共同为社会性公共资源的供给与配置设置目标、制定规则以及协同推进,社会发展与经济发展之间才可能协调共进。
总之,经济越发展,社会基础和福利水平(广义上的社会福利)也应该相应提高;而社会基础越发展,社会福利越公平,经济发展水平也会相应提高。反之,如果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不能有效地设计社会发展和福利政策,就会导致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社会不和谐因素越来越多,从而引发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这又会进一步阻碍经济的发展,导致经济水平的下降;而经济水平的下降,又会相应地引起社会福利水平的下降。这样一来,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就会处于一种恶性循环之中,甚至还可能导致社会崩溃。当然,我们也不能为了简单地谋求社会福利而超越现实的经济基础和发展水平,那样的社会福利更多的可能只是一种单纯的主观愿望和诉求。基于此,经济发展和社会基础以及社会福利的协调发展,构成了社会管理或社会治理的一项基本准则。[17]
三、经济新常态下的社会治理
2014 年5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首次用“新常态”来描述我国的经济发展态势。基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政策消化期”这三期叠加效应,中国进入经济新常态阶段的主要特征体现为:发展速度的变化(高效率、可持续地中高速增长)、结构优化、创新驱动、多重风险。[13]
从1978 年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到 2008 年,我国的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经济粗放高速增长。这一时期,虽然也有不断凸显的社会矛盾,但对社会领域主要是实行高管政策,社会总体上仍然保持稳定。因此,这一时期处于矛盾社会阶段。而自2009年以来,我国的基尼系数已逼近 0.5,已超过了 0.4 这一警戒线,因此,当前时期已进入不能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的、新旧矛盾交织的、风险剧增的冲突社会阶段。[14]而在2014年,我国的GDP为636463亿元,首次突破10万亿美元,位居世界第二,国民人均GDP也已达到7575美元。[15]由此也标志着我国由一个生存型社会转向一个发展型社会。[16]发展型社会的到来,无疑对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结合基尼系数和GDP指标来看,这一阶段我国既肩负着推动生产力发展与经济增长转型的任务,同时也面临着解决社会矛盾和维护社会公正的挑战。
结合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来看,从粗放型增长向集约型增长的发展与转变,可以说是生产力与经济发展的一般趋势和客观要求。只有适应这一总体的发展趋势和客观要求,才能从根本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17]西方发达国家大都已在20世纪顺利完成了这一转型。
经济新常态既为社会发展和社会治理带来一定的问题与挑战,同时也为社会发展和社会治理提供了一定的机遇和动力。在经济新常态下,我国的社会企业与社会组织不断的发展壮大,如我国当前依法登记的行业协会商会就有将近 7 万个。[18]社会组织被誉为现代社会三大支柱之一,具有政府与企业等不具备的公益性、非政府性和独立性等特征,因此,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中也就能发挥政府和企业所无法发挥的独特作用,从而拓展社会治理主体与渠道,更好地沟通政府与社会,满足民众需求,弥补公共服务的不足。
传统的社会管理,主要是以政府为主体或中心而实行一种单一的的管理或控制。在当前社会多元化、利益诉求复杂化的情况下,单一的政府已无法将不同群体和阶层的利益整合起来进行有效的管理,这就需要个体、群体以及社会组织等多元参与和协同。[19]而治理的主体则包括了政府、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体等,社会治理多元主体通过协商与合作来确立共同的目标,从而实现有效的共治。社会治理正是由传统的社会统治或社会管理等“发展”、“演化”而来的。[20]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治理主体要从政府包揽向政府主导、社会协同转变,既要充分发挥党委的领导作用,又要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也要积极鼓励和支持社会参与,从而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的良性互动。
总体而言,经济新常态下的发展,既要利用好经济的韧性和社会的韧性,又要注意经济韧性和社会韧性的阈限,[21]从而推动经济新常态下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对于社会层面而言,社会治理应围绕着加强社会建设、倡导社会参与和鼓励社会创新这三个方向来积极构建社会新常态,从而通过理念、主体、体制和机制等的创新来实现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的转型。
[1]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中央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14.
[2] 赵雪峰.马克思主义群众观与中国特色社会管理[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5.
[3]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中央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143.
[4] 宋贵伦.中国社会改革评论:第2辑[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313.
[5] 汪大海.社会管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11-12.
[6] 谭明方.社会与经济 “发展协调性”视角的社会管理研究[J].社会科学研究,2012(1):6-15.
[7] 谭明方.社会管理:“性质”与 “内容”研究[J].广东社会科学,2013 (1):225-232.
[8] 殷昭举.社会治理导论[M].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120-121.
[9] 李建军.现代社会治理危机及其化解策略[J].河北学刊,2009(1):47-48+50.
[10] 贾玉娇.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现代国家治理能力提升路径研究[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5(4):99-100.
[11] 徐大建.社会公平、和谐与经济效率[J].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06(1):25-32.
[12] 张云飞.社会管理准则初探[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1(6):142-148.
[13] 刘玉辉.科学把握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J].红旗文稿,2015(15):20-22.
[14] 李瑞昌.经济新常态下的公共治理创新[J].探索与争鸣,2015(7):86-89.
[15] 国家统计局.201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EB/OL].(2015-02-26)[2016-06-06].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502/t20150226_685799.html.
[16] 杨雄.经济“新常态”下中国社会发展面临的挑战及政策涵义[J].社会科学,2015(7):70-78.
[17] 杨伊佳.走向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新常态[J].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5(1):47-61+158.
[18] 康晓强.经济新常态下社会治理的新趋向[J].科学社会主义,2015(4):17-20.
[19] 严仍昱.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 政府与社会关系变革的历史与逻辑[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5(1):167-172.
[20] 乔耀章.从“治理社会”到社会治理的历史新穿越——中国特色社会治理要论:融国家治理政府治理于社会治理之中[J].学术界,2014(10):9-24+313.
[21] 王思斌.试论经济发展新常态下积极的社会政策托底[J].东岳论丛,2015(3):7-11.
(责任编辑:王 荻)
2016-12-21
黎海波,男,中南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博士。
D035
A
1008-2603(2017)01-008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