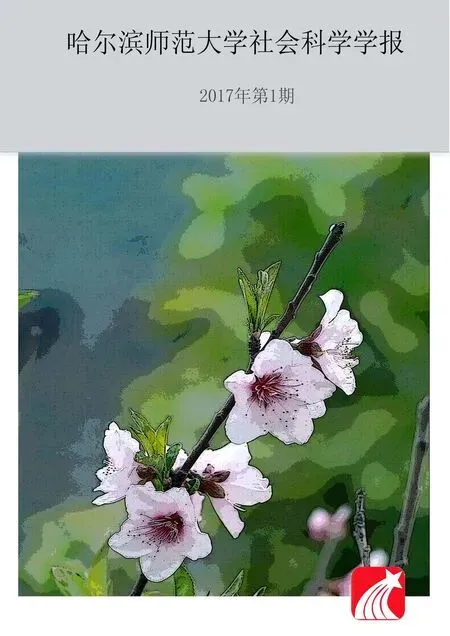现代乡村的结构性变化与乡土文学的嬗变
——《麦河》与《后上塘书》的互文性阅读
宋学清
(东北师范大学 文学院,吉林 长春 130117)
现代乡村的结构性变化与乡土文学的嬗变
——《麦河》与《后上塘书》的互文性阅读
宋学清
(东北师范大学 文学院,吉林 长春 130117)
新世纪以来的中国乡村正在经历政治、经济与文化等方面的结构性变化,乡土文学追踪式描写了这些“新”与“变”,探索现代乡村的发展模式,参与讨论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关仁山的《麦河》与孙惠芬的《后上塘书》都以土地流转作为书写背景,表现新土地制度下乡村的变化与发展。适应新土地制度的“农村新人”形象再次出现在文学作品中,他们带领村民发展经济建设现代乡村,为生态乡村发展做出重要贡献。同时资本的介入也在改变乡村的权力体系与伦理秩序,在冲突与调节的过程中,中国乡村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变化。乡村的变化与乡土文学的嬗变具有一定的同质关系,这也是乡土文学现实主义传统的一种必然结果。
土地流转;“农村新人”;生态乡村;乡村伦理
土地问题一直都是中国乡村的核心问题,只有进入土地,才能真正进入乡村问题的肌理。百年中国对土地问题的探索从未间断,新世纪以来土地制度再次发生变化,2002年国家颁发《土地承包法》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转包、出租、互换和转让)做出明确规定,土地流转成为新世纪中国乡村最重要的土地制度,因此,它也被称为我国第三次地权改革。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土地的转包、转租已经在乡村普及,以政策、法律的形式予以确认、保障。一方面顺应了乡村新景观,另一方面,极大推动了土地改革的进度与力度。作为新生事物,土地流转一直处于试点与推广的探索阶段,中国土地制度在调整过程中一直保持着审慎,“一刀切”式简单粗暴的土地制度不复存在。从目前来看,土地流转还存在很多制度性、操作性问题,前景尚未清晰,因此,需要社会多方面参与谈论,合力探索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与当下乡村发展的土地流转模式。
基于乡村本体性问题与基本现状,新世纪乡土文学再次发扬现实主义精神深入乡村,参与乡村问题大讨论。杨廷玉的《花堡》、千夫长的《白马路线》、赵德发《缱绻与决绝》、谷凯编剧的《马向阳下乡记》都涉及土地流转问题,其中,以关仁山的《麦河》与孙惠芬的《后上塘书》最具代表性。它们都以土地流转作为小说红线,思考承包者、资本、农业现代化、土地情怀、农民选择、乡村伦理与乡村秩序等连带性问题,由于面对同样的土地制度与相近的乡村问题,两部作品表现出一定的互文性关系。正如朱丽叶·克里斯蒂娃认为的那样:“任何作品的文本都像许多行文的镶嵌品那样构成,任何文本都是其他文本的吸收和转化。”[1](P36)在肯定文本间具有一定同质性关系的同时,也承认了具体文本的异质性特征,即所谓的“吸收和转化”。因此,我们在相似性的基础上对《麦河》与《后上塘书》进行互文性阅读的同时,也要注意到二者间的本质性差异。
一、土地流转与“农村新人”的制度性人格
新世纪中国乡土文学伴随乡村在政治、经济、文化与伦理等方面的结构性变化发生巨大的审美嬗变,尤其在“农村新人”形象的塑造方面表现得最为明显。因为不同阶段乡土文学中的“农村新人”往往都与新土地制度有关,土地制度的执行最终要落实到农民身上,不同时期的土地制度对农民素质尤其是执行者的人格结构产生不同的要求,这也是“农村新人”形象能够构成历史序列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我们可以说“农村新人”既是土地制度的“制造”,也是文学作品的塑造。恰如美国学者彼德·布劳所说:“一种社会的制度构成了社会的子宫,个体就在其中成长和社会化,结果,制度的某些方面被反映在他们自己的人格之中。”[2](P29)这一观点强化了制度对于人的养成性与内化性特征,长期在一种制度下生活,不经意间制度已然投射进我们的人格结构,构成我们人格中的一部分。这种制度性人格的承载者将会成为特定制度坚定有效的执行者,从而推动制度的普及与完善。制度性人格的认识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过分强调制度的建构性力量,往往会忽略掉人格的自觉抵制与抗争意识,陷入意识形态的逻辑陷阱。因此,理性认识制度性人格是极为必要的。
新世纪以来,中国土地制度再次发生巨大变化,被称为“第三次地权改革”的土地流转开始在全国范围内试点,这是继土地改革、合作化、家庭联产承包之后中国乡村最为重要的土地制度,必将改变原有的人地关系。学者李兴阳认为:“中国乡土小说中的‘农村新人’形象,大都与土地制度的变革有关。”[3](P80)土地改革、合作化与大包干都曾产生代表性“农村新人”形象,比如,张裕民、程仁(丁玲《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梁生宝(梁斌《创业史》)、刘雨生(周立波《山乡巨变》),孙少安(路遥《平凡的世界》),等等,他们先后参与到中国乡村土地制度的改革,成为制度坚定、有效的执行者。同样在新世纪新土地制度——土地流转制度在乡村试点、铺展的大背景下,乡土文学追踪式表现了农村新变化,塑造出一系列具有代表性的、制度性人格的“农村新人”。
土地流转制度与城镇化进程、农业现代化、农民工进城等问题紧密相连,城镇化与农民工进城致使大量农民脱离乡村,产生大量闲置土地,使土地的集约化生产具备了前提条件。农业的机械化为使土地集中生产具备了可能性,降低农业生产成本实现土地资源的优化。土地流转的最终目的是实现乡村的现代化,帮助农民致富,因为历史早已证明家庭联产承包制解决了农民的生存问题,却无法解决农民的贫困问题。在这一背景下,与土地流转相关联的“农村新人”便具有自己的独特性。作为新世纪的新农民形象,《麦河》塑造出曹双羊,《后上塘书》塑造出刘杰夫,同样作为土地流转制度下的“农村新人”而具有一定的相似性。
在身份上,曹双羊与刘杰夫都有乡村背景,曾经都是农民。他们是乡村能人,离开故乡后没有沦为普通农民工,而是成功获取资本成为企业家和老板,同时都响应国家号召返乡参与土地流转。国务院先后在《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支持农民工等人员返乡创业的意见》(国办发〔2015〕47号)和《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支持返乡下乡人员创业创新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意见》(国办发〔2016〕84号)等政策中提出鼓励支持农民工返乡参与土地流转、创建现代农场。政策的保障是他们返乡创业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在身份上他们不是外来投资者,故乡是他们的“血地”,与他们血脉相连。这种内在关联性使他们与乡村、土地、农民保持着情感关系,情感的维系能够削弱他们对资本的过度追逐,也能制约他们对土地的非农业化使用,保证“失地”农民的利益。
在资本性质上,关仁山与孙慧芬都对恶意资本保持着足够的警惕。恶意资本对乡村的资源掠夺、环境破坏、利益侵占表现得极为明显,关仁山的《日头》即是最好的案例。曹双羊与刘杰夫带入乡村的资本在积累过程中充满了罪恶。曹双羊入伙开矿,利用黑锁杀死合伙人赵蒙,攫取第一桶金。刘杰夫不择手段巴结方永和,做工程、开矿山、夜总会等,他的罪恶在大姐徐凤的三封信里慢慢被剥开。对资本的不信任是两部作品的共同特征,资本积累尤其是资本的快速积累必然伴随着“血和肮脏的东西”。这种偏执性的认识具有一定的历史原因,却也表现出资本的一种性质。但是罪恶资本不等于恶意资本,曹双羊与刘杰夫投资乡村的初衷是为了获利,最终结果却是实现了资本与乡村的共赢,他们没有一味掠夺乡村,而是发展出适合乡村的生态农业。尤为重要的是他们在返乡投资的过程中都历经一个忏悔与转变的过程,他们人格的转变改变了资本性质,将人格与资本性质相结合是《麦河》与《后上塘书》乃至当下中国共同的思维方式。而他们人格的转变又与农民身份有着重要关系,这是乡村能够接受的资本。但是小说对善意资本的期盼与处理方式过于理想化、简单化、情感化,与资本的理智、功利、冷酷相悖逆,不具有普遍性,反而能够引起读者对资本更深刻的戒备。
在人格结构上,曹双羊与刘杰夫都具有一定的缺陷,他们身上不再有赵玉林、郭全海(《暴风骤雨》),张裕民、程仁(《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梁生宝、高增福(《创业史》),孙少安(《平凡的世界》)等人身上的理想主义,他们功利现实充满欲望。在物欲面前,他们都曾迷失,精神陷入虚无,生活淫靡堕落,但是农民出身使土地对他们具有一定的疗治功能。返乡的曹双羊在土地、小麦、“连安”地神、苍鹰虎子的感召下历经三次精神洗礼,终于摆脱精神危机,脱离资本束缚,合理调整了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的关系。返乡的刘杰夫在痛失妻子徐兰之后,在神秘信件的谴责下开始反思忏悔,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自我心灵救赎,这其中“铺垫着一种内在而执着的心灵寄托与精神诉求——只有在他熟悉的这片土地上,从事他最得心应手的事情,与他熟悉的乡民们在一起,得到他们的认同与认可,才能找到一份将自己与乡土和现实社会紧密融合的可能性,也才能够拥有一种踏实的归属感与成就感”[4](P144)。在土地面前他们完成人格的转变,由一位土地的背叛者、贪婪的资本的追逐者转变为乡村现代农业的拯救者,在土地上真正、真切、真实地实现了人生的高峰体验。别尔嘉耶夫认为人经常“悬于‘两极’:既神又兽,既高贵又卑劣,既自由又受奴役,既向上超生又堕落沉沦,既弘扬至爱和牺牲,又彰显万般的残忍和无尽的自我中心主义。对此,人每每莅临自己内心冲突的高峰阶段便时有体悟”[5](P3)。人是一种双重矛盾的产物,依据弗洛伊德的理论,人经常处于超我与本我人格的冲突中,真正人生的高峰体验能够令人确证自己存在的价值,从而实现人格的良性发展。曹双羊与刘杰夫正是在土地面前精神得以升华,从而摆脱资本、物欲对精神的控制,成为土地流转需要的“农村新人”。
二、新世纪生态乡村的文学建构
新世纪以来的科学发展观、生态文明建设已经为乡村发展提供基本方向,2015年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首次将生态文明建设列入“十三五”规划,可以说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变得越来越有理有据。相反,那些消耗资源、污染环境的乡镇企业已经不再是乡村经济的主体,乡村绿色经济、生态环境、农民的精神文明成为生态乡村建设的重点。但是目前对生态乡村的认识还存在一定的局限,“生态乡村建设不仅是一个自然环境保护问题,更是谋划中国经济转型和开辟新的经济增长点的战略问题,确保绿水青山真正成为金山银山的问题”[6](P106)。生态乡村的建设应该是基于乡村环境保护与资源合理化利用的基础上,努力开发适合个体乡村的生态产业,探索适应乡村可持续发展的经济模式,以期成为乡村发展的常态经济,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新的增长点,而不再是简单的城市对乡村的经济援助、政策支持。
曾经的乡镇企业一度成为乡村经济的支柱,但是历史证明工业化发展模式对乡村并不具有普世性,少数地区的成功不具有普遍性。乡村的工业化尝试最终留给乡村的是土地污染、耕地占用、负债累累,关仁山的《天高地厚》、范小青《赤脚医生万泉和》等作品均涉猎这一问题。新世纪以来生态乡村的探索最为成功的应该是第三产业的开发,尤其是生态旅游、度假村之类,比如,周大新的《湖光山色》。但是它们并不适合大多数乡村,而且很难规模化,无法成为乡村发展的主体。于是关于农业的工业化、产业化思考再次提到议事日程,土地流转正是对乡村生态产业发展的一次有效尝试,合理开发农业提高土地生产效率,才是乡村经济的根本。
《麦河》与《后上塘书》积极参与生态乡村建设的思考,以文学的方式参与谈论土地流转背景下乡村生态产业发展的可能性。两部小说同时关注到土地生态开发问题,在土地流转制度下发现了乡村经济发展的新模式,发展绿色环保的生态农业。《麦河》中的曹双羊在鹦鹉村流转到大量土地,种地不挣钱使很多农民进城打工,大量土地荒芜,土地流转首先避免了土地的闲置。家庭联产承包曾经解决了农民吃饭问题,但是土地家庭分散经营生产效率低很难实现农民依靠土地致富,已经开始不适应现代乡村的发展需要,土地流转有效补充了这一制度的现代缺陷。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曾论证:“以资本来代替劳力,就是减低劳力在生产要素中的地位,而增强资本在生产要素中的地位。”“‘以资本代替劳力’,最重要的方式是‘农业机械化’。”[7](P168)土地流转制度下资本进入乡村真正实现了“以资本代替劳力”,曹双羊利用麦河集团雄厚的资本实现了鹦鹉村土地的集约化、机械化与产业化,留用、雇佣职业农民极大提高了生产效率。同时曹双羊的麦河集团主要以生产方便面为主业,流转的土地大面积种植小麦,实现小麦深加工,提升了农作物的利用率,真正实现了农业定向生产、农产品深加工的“农业的工业化”。这种农业开发模式既保证了土地的农用、保护了乡村环境,又提升了农民收入与土地利用率,为当下土地流转提供思路,为乡村生态产业提供了有效的发展模式。
《后上塘书》的刘杰夫同样带着资本回村参与土地流转,集中上塘村大量土地。在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理念、生态乡村与生态产业的开发理念上,刘杰夫与曹双羊保持一致,但是在生态产业开发思路上表现不同。刘杰夫虽然同样拥有资金却没有与乡村相关的产业,无法实现产业对接,但是他能够在上塘村发展生态农业。他将流转土地重新规划,开辟蔬菜园区、葡萄园区、蓝莓园区、温泉区,贫瘠的土地种植树木、果树,林下种植生姜、中草药发展“林下经济”,开发蔬菜大棚承包给农民等,重新将农村劳动力吸引回农村,保证了乡村家庭结构的完整。刘杰夫顺应上塘村土地特点,它没有硬性资源与独特优势的上塘村更能代表中国普通乡村,但是只要集中土地合理规划,同样能够保证农民利益。这也是生态乡村的生态产业开发的一个有效模式。
生态乡村的生态产业开发不是一个孤立的行为,它需要乡村政治的支持甚至是保护,新的乡村经济模式需要新的乡村政治形式与权力体系。而土地流转背景下资本对乡村的介入,首先改变的恰恰是乡村的权力结构。新中国成立前后的土地改革制度改变了传统中国乡村治理方式,地主乡绅被消灭,传统乡贤治乡被取消,村支书取代乡贤成为乡村政治代表。他们在中国乡村发展史上起到重要作用,《暴风骤雨》中的郭全海、《三里湾》中的王金生、《艳阳天》中的肖长春、《平凡的世界》中的孙少安等,他们维护了乡村政治秩序,保证国家政策在乡村的顺利执行,带领村民发展乡村经济。在土改小说与合作化小说里,村支书的主要功能是政治性的,具有很强的意识形态性,发展经济只是附属性功能。在新时期文学之后的家庭联产承包小说中,村支书的功能发生重要变化,职能转向经济发展,带领村民致富,同时村支书的问题开始成为文学关注的重要话题。李佩甫《羊的门》中呼家堡村支书呼天成,蒋子龙《农民帝国》郭家店村支书郭存先,关仁山《日头》中日头村村支书权桑麻等,他们带领农民发展农村工业发家致富,但却无一例外被权力异化成为乡村“土皇帝”,作威作福、欺压乡民成为农村民主的威胁。
但是资本介入后现代乡村权力体系发生很大变化,从《麦河》与《后上塘书》来看乡村权力大体可以划分为三个部分:村支书、资本占有者、乡村民间话事人。《麦河》鹦鹉村的权力划分为村支书陈锁柱、土地流转投资者曹双羊、民间话事人瞎子白立国。《后上塘书》上塘村的权力划分为村支书刘杰夫(刘立功)、土地流转投资者刘杰夫、民间话事人张十四。
《麦河》鹦鹉村的村支书陈锁柱依靠县长哥哥陈元庆的势力把曹双羊请回来参与土地流转,曹双羊带着巨额资本投资乡村,资本的力量即是曹双羊的力量。村支书陈锁柱既想借助曹双羊发展经济又想维护权力,如同很多作品中的村支书一般,陈锁柱贪婪霸道权力欲极强。他先后私留村里的“机动地”“以租代征”试图农地工用、企图强奸堕落的桃儿、指挥流氓弟弟陈玉文强占土地逼疯转香……但是上面依靠县长下面指挥流氓,陈锁柱这位村支书在鹦鹉村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是鹦鹉村的能人,实权派”[8](P16)。曹双羊借助资本的力量在鹦鹉村的权力优势越发明显,他能够解决村支书无法解决的问题,改变了乡村权力体系。曹双羊与陈锁柱的矛盾代表了资本力量与村支书权力的角力,曹双羊试图用弟弟曹小根取代陈锁柱,欲变鹦鹉村由陈家天下变为曹家掌控,好在曹小根追求乡村“公权力”与民主政治。在曹双羊与陈锁柱之外乡村仍然存在另一种话语声音,即以瞎子白立国代表的民间权力。白立国擅长乐亭大鼓,能掐会算,略懂中医,是鹦鹉村民间话事人。在土地流转过程中,白立国起到关键作用,他是曹双羊与陈锁柱以及村民间的润滑剂,居中调节了几方面的矛盾,保证土地流转的顺利进行。白立国身上充满神奇的力量,这是土地、小麦乃至“连安”地神赋予的力量,村民们信任他,在与村支书、资本矛盾冲突之际寻求他的帮助,没有任何政治身份的他不惧怕任何一方,包括县长陈元庆。他站在农民的立场先后与陈锁柱、曹双羊、陈元庆、陈玉文等各方力量发生冲突,保证了农民的利益,成为乡村世界的第三种力量。
《后上塘书》同样存在三种力量的角逐,只是刘杰夫为避免权力冲突直接接管了乡村,使其成为资本与村支书两种权力力量的集合者。刘杰夫曾是《上塘书》中上塘村支书刘立功,下海经商发家后回村参与土地流转,刘杰夫具有双重身份:翁古城中的富商名流;上塘村的村支书。但是在刘杰夫之外上塘存在另一个重要的力量,那就是阴阳先生张十四,他取代了《上塘书》中的鞠文采主持着上塘村的民间政治,他除了肩负阴阳先生的使命,“还得行实着为那些被现实乱麻纠缠不清的人解扣拆锁的使命”[9](P64)。他如同《麦河》里的白立国同为乡村民间话事人,没有他们,资本与权力很难在乡村展开,土地流转很难顺利推行。
生态乡村建设除了自然环境保护、生态产业开发之外,还包括生态文化的建设,这是生态乡村良性循环发展的重要保证。生态文化建设较之于生态乡村其他方面的建设难度更大,面临的挑战更多。但是两部小说对这一问题的思考明显不足,这也是新世纪乡土小说的一大短板。《麦河》试图以“小麦文化”“土地文化”拯救乡村,但是理想主义的处理方式令人难以信服,乡村文化建设的探索仍走在路上。
三、现代乡村伦理秩序的文学重建
土地流转背景下资本的介入,既改变了传统乡村生产方式与权力体系,也改变了农民身份。工业化生产理念开始进入乡村,职业农民开始出现,乡村伦理遭遇冲击,新的伦理秩序正在重建。重建中的乡村伦理与城市伦理形成碰撞,根据学者王露璐的研究成果:在二元化的城乡伦理结构中,乡土伦理是城市伦理的“历史之根”,城市伦理是乡土伦理“现代之源”,“从乡土伦理与城市伦理的内在紧张中实现‘历史之根’与‘现代之源’的成功嫁接”[10](P4)。现代乡村伦理的重建离不开城市伦理,它必将为乡村伦理秩序提供现代资源。现代伦理观念对乡村的渗透方式与途径是多方面的,资本与农民工是其中较为重要的一环。尤其在那些回乡投资者身上,城乡伦理冲突表现得最为明显,恰如学者周景雷所说的那样:“中国乡村社会的最近30多年来,乡村人完成了从不走到出走再到归来的转换,刘杰夫们正是这一流转过程的积极实践者、参与者。在这一进程中,附着于人的身上的文化属性,比如伦理观、道德感、义理秩序等悄然改变。”[11]再次归来的刘杰夫、曹双羊们已经脱离了农民身份,他们携带资本与城市现代气息强势回归,在土地流转中冲击了乡村既定社会秩序,尤其是伦理秩序。
“土地流转”这场土地经济的变革,使曹双羊、刘杰夫重返故乡,带领乡村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他们改变了乡村,带来了财富,但是面对土地、村民他们时常表现出城乡倾轧间进退维谷的两难境地,从而使他们身上表现出乡村伦理的挑战者与守望者的双重困境。人物性格的双重矛盾正是他们在寻找心灵归宿与实现自我救赎时茫然无措的真实写照。
曹双羊与刘杰夫们在城市打拼多年,“成功使他回乡后有了强大的话语权,他可以不再遵循乡村的伦理,相反,他还要把城市的伦理带到乡村”[12](P41)。城市生存与商场拼搏经验使他们身上表现出鲜明的现代文明的表征,重名利,轻人情,省略掉乡村“熟人社会”的交往法则。于是在回村推行土地流转时遭遇到同样困境:郭富九与刘平起拒绝流转土地。曹双羊与刘杰夫在面对同类事件时表现得束手无策,城市经验在乡村失效,因此,在土地流转过程中他们竭力想要斩断自己与他人情感关系的纽带,建立一种城市体制的、公事公办的运转流程。他们通过利益标准来衡量对象,并以十分理性的眼光审视、建立关系网。在其关系网建制中,人情已经被极大程度地淡化,他并不关注身边人的喜怒哀乐,而是通过利益捆绑与他人建立联系。因此,曹双羊与刘杰夫与村民乃至亲人朋友形成一种微妙关系。曹双羊在土地流转过程中先后与县长陈元庆、村支书陈锁柱、父亲曹玉堂、老农民郭富九、情人桃儿、朋友白立国等都曾产生过矛盾冲突。尤其在面对农民与土地问题上,曹双羊表现出资本家嗜血本性,他将农业生产引入工业化管理模式,对待农民同样采用城市伦理方式,利益与伦理的矛盾使曹双羊与农民间的冲突难以调和。同样刘杰夫在土地流转过程中虽然启用了张十四、程有望、于吉堂,努力调和与村民矛盾,但是他仍然与家人甚至妻子徐兰不合,大姐徐凤看透他资本的罪恶,以匿名信件的方式不断揭发谴责他,最后连一向恬然清净的大姐夫也对他发出歇斯底里的控诉……在土地流转过程中与曾经的朋友刘平起关系僵化水火不容。尤其是刘杰夫重回上塘改变了“老祖宗留下的历史”[9](P3),他把城市文明的血液推进乡土社会的脉络中,大兴土木、建公路、修电灯、挖方塘,现代文明让古老的上塘感受到乡土伦理的威胁,从此之后上塘的池塘里开始发愁令人心惊的惨叫,这是上塘渐渐消失的传统伦理的伤口。
贺绍俊认为:“乡村经历了一两千年岁月的经营。在这悠久岁月的经营中,人们为乡村建起了两套沟渠系统,一套是浇灌土地的沟渠系统,一套是约束人们行为规范的伦理系统……但是上塘的这套沟渠虽然古老,上塘人的情感虽然新鲜,但新鲜的情感仍旧奔流在古老的沟渠里……在城市,我们需要拯救情感,在乡村,我们需要疏通渠道,这都是作家们应该努力干好的活。”[13]贺绍俊深刻地认识到传统乡村伦理的规范性力量在乡村的重要性,如果这条伦理的渠道壅塞不通,那么乡村的事情便很难解决。曹双羊、刘杰夫试图以城市伦理的“现代之源”完全取代乡村伦理的“历史之根”,从而阻塞了乡村伦理的沟渠,遭遇来自村民的乡村阻力。于是需要一个能够“疏通渠道”的人,《麦河》中的白立国、《后上塘书》的张十四适时地充当了这一角色。
白立国利用土地、小麦与苍鹰虎子三次拯救了曹双羊的精神危机,在土地流转过程中深谙乡村伦理秩序的他多次调解曹双羊与村民矛盾,既保证了鹦鹉村土地流转的正常有序进行,又维护村民的利益。张十四进入村委会就是为了“维护上塘的秩序和安定”[9](P31),他用桃木在方塘四周布阵应对上塘的惨叫,当着上塘人的面烧了十几墩大纸,放了二十几挂鞭炮,以安抚理顺上塘的人心。他成功调节刘杰夫与刘平起之间的矛盾,保证了徐兰葬礼与土地流转的顺利进行。因此,在某种程度上白立国与张十四更像是处于城乡碰撞间的一个润滑剂——他们以乡土社会为依托,用乡村的方式来柔化城市伦理带来的巨大冲力,肩负着缓和城乡伦理二元矛盾的作用。他们既积极维护着乡村伦理结构,又极力支持土地流转;既不愿放弃老一辈建立的乡村伦理体系,又乐于接受现代文明为乡村带来的积极变化。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性格所具备的张力让他们在乡土城市化过程中既不会成为一味守旧的乡村伦理固守者,又不会彻底沦为现代物欲文明冲击下的殉葬者。
在白立国与张十四的调节过程中,既保证了城市伦理有序有效地进入乡村,又保证了乡土伦理的独立与嬗变,没有被强势的城市文明湮灭。白立国坚持乡村伦理观念多次教育、指导曹双羊,最终使曹双羊认识到乡村伦理的重要性,从根本上认同了乡村伦理,于是有了鹦鹉村小麦图腾与树碑铸魂祭祀仪式。张十四通过徐兰葬礼的安排教育了刘杰夫尊重乡村伦理,让他看到乡村伦理的力量。可以说徐兰的死对于刘杰夫是一个契机,使他“从乡村人的道德思维和心理范畴中寻求可靠自足的力量来实现生命的净化和升华,即在民间报应不爽心理支配下,回归最朴素的人伦良知和人性善恶立场,警惕和反思生存境遇,敬畏生活和生命”[14](P49)。这是一个心灵还乡、自我救赎的过程,使刘杰夫真实实现了精神的还乡,抛弃了以往借土地流转谋利,为家人建造一所后花园的执念,从物欲中清醒过来。于是他开始用温情的目光关注乡村与农民。
可以说在矛盾与冲突中、在内在的紧张关系中,城乡伦理完成一次嫁接,尽管其中还存在很多问题,但毕竟开始走上理性的重建之路。
四、结论
新世纪以来随着土地流转在乡村的展开,土地的集约化、机械化与产业化程度的不断提高,乡村劳动力被极大解放,资本的介入极大推动了乡村的“城镇化”进程。同时随着国家乡村政策的相继出台,2004年党中央通过“一号文件”的形式要求五年内取消农业税,2006年全国范围内全部免除延绵中国数千年的农业税。随着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普及与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确立,乡村福利社会的建构雏形已然出现,中国乡村正在经历着值得期待的新变化。
在乡村转型的过程中,新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正在改变乡村文化与乡土伦理,尤其是职业农民的出现使农民身份发生变化,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农民的思维方式,他们对城镇生活的适应性、对城市文明的认同性正在发生质的变化。可以说乡村“城镇化”进程的一个最大阻力——农民身份与文化认同问题——正在被有效调适。我们既要认同土地流转与乡村转型,也需要肯定乡村伦理与农民需求的合理性。现代化是现代乡村发展的必然趋势,土地的集约化、产业化是现代农业发展的必然趋势,现代农业则是乡村经济重要的发展模式,这是历史的必然趋势。但是同时我们也应该理解曹玉堂、郭富九、韩腰子、刘平起这些普通旧式农民对土地的感情,他们的行为落后于乡村发展,甚至构成乡村现代性的阻力,如何安置他们失落的灵魂也是乡村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
[1]Julia Kristeva,Word Dialogue and Novel,in The Kriste-va Reader,Toril moied[M].Oxford:Blackwell Publisher Ltd,1986.
[2][美]彼德·布劳.社会生活中的交换与权力[M].孙非,张黎勤,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8.
[3]李兴阳.“农村新人”形象的叙事演变与土地制度的变迁——以《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创业史》《平凡的世界》和《麦河》为中心[J].文学评论,2015(4).
[4]韩传喜.多重纠缠中的乡村书写——《后上塘书》论[J].当代作家评论,2016(5).
[5][俄]尼古拉·别尔嘉耶夫.人的奴役与自由——人格主义哲学的体认[M].徐黎明,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
[6]韩秀景.中国生态乡村建设的认知误区与厘清[J].自然辩证法研究,2016(12).
[7]费孝通.乡土中国[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
[8]关仁山.麦河[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0.
[9]孙慧芬.后上塘书[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5.
[10]王露璐.新乡土伦理——社会转型期的中国乡村伦理问题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11]周景雷.孙惠芬长篇小说《后上塘书》:带着疼痛站立起来[N].文艺报,2015-08-12(3).
[12]贺绍俊.孙惠芬的“变”与“不变”——评《后上塘书》[J].当代作家评论,2016(7).
[13]贺绍俊.乡村的伦理和城市的情感[N].文艺报,2004-06-29(2).
[14]张丛皞.《后上塘书》: 致力于人性启蒙的乡村叙事[J].当代作家评论,2016(7).
[责任编辑 孙 葳]
The Structural Change of Modern Villages and the Evolution of Local Literature——Intertextuality Reading of “Mai River” and “Hou Shang Tang Shu”
SONG Xue-qing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117, China)
China’s rural areas in the new century are experiencing structural changes in politics, economy and culture. Local literature traces these “new” and “changes” to explore the development model of modern villages and participate in the discussion of society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socialist countryside. Guan Ren Shan’s “Mai River” and Sun Huifen’s “Shang Shang Tang” are based on the land circulation as a writing background, the performance of the new land system under the village of change and development. The image of “rural newcomer”, which adapts to the new land system, appears again in literary works. They lead villagers to develop economic construction of modern villages and make important contributions to ecological and rural development. At the same time capital intervention is also changing the rural power system and ethical order, in the process of conflict and regulation of Chinese villages are experiencing an unprecedented change. The change of the village has a certain homogeneous relationship with the evolution of the local literature, which is also a natural result of the local literature realism tradition.
land transfer; “rural new”; ecological village; rural ethics
2016-12-06
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新世纪长篇小说叙事的历史意识研究”(14AZW015)
宋学清,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东北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新世纪长篇小说。
I207
A
2095-0292(2017)01-0134-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