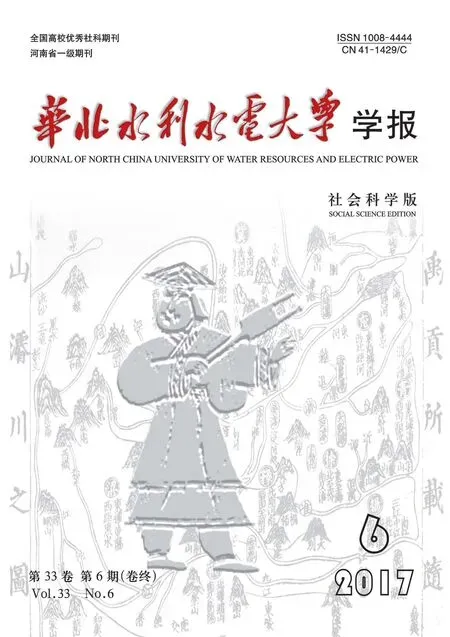“被遮蔽”的空间:贾平凹的语象叙事
王华伟
(西北大学 文学院,陕西 西安 710127)
“被遮蔽”的空间:贾平凹的语象叙事
王华伟
(西北大学 文学院,陕西 西安 710127)
语象叙事是对传统主体线性结构与时间叙事模式的反叛和颠覆,并为视觉书写和意象再现提供更为开阔、更加精准的空间视点。贾平凹的小说蕴含着明显、独特而复杂的语象叙事痕迹,其作品描绘的一幅幅连续性、生活化和语境化的乡土场景,以语赋形于现实的千姿百态,实现被“遮蔽”乡土空间的语象再现与叙事重构。作为当下乡土文学的旗帜型作家,贾平凹个性化的创作实践不仅是对乡土审美观照方式的根本转变,也是对空间记忆基点的深度寻找,更是对文学叙事转向的积极探索。
语象叙事;场景;乡土;空间
作为一种文学修辞与批评术语,语象叙事(ekphrasis)主要用来呈现文学如何通过语言描绘、刻画和再现图像化、视觉化的文本意境,以及阐释文字与图像之间的叙事互文关系。语象本身意在强调文学的空间想象性、意象动态性和视觉冲击性,目的是突出形象化空间在文学作品中的媒介作用与叙事功能,它是语言图像转向与文学空间转向的共同表现。作为呈现文学语言中图像的语象,它是小说呈现画面感的桥梁与路径。苏轼关于“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和古希腊诗人西摩尼得斯关于“画是无声的诗,诗是有声的画”的形象论述均显露出语象的端倪。语象叙事历久而弥新,尤其是在今天的图像时代更受关注、更具价值。正如赫弗南对语象的经典定义——“视觉再现的文字再现”一样,语象叙事是对文学作品中图像意象和视觉形象的空间性阐释与文字性再现。克卢弗在此基础上加以深化,指出语象叙事是“对某个非文字符号系统构成的或真实或虚构的文本的文字再现”[1]26。语象的对象可以是真实存在的,也可以是虚构的。语象描绘的不是现实,而是对现实的空间性感知,这与韦伯所说的“心理感受”有相通之处。托马斯·米切尔把语象叙事界定为“完全隐喻的表达”[2],它是文学叙事与空间意象间的博弈与融通。语象叙事使得文学成为一种可以打破时间线性的共时性空间表达,通过时间淡化、情节弱化、碎片与并置等技巧呈现出同在与共存的意象性想象与空间性印象。
贾平凹坚持将自己的文学脚步行走于乡土或真实或记忆的空间里,所以他被曾经呼吁建立“语象学”的陈晓明称作乡土文学“最后的大师”。无论《高老庄》《秦腔》《带灯》《极花》中的“乡”,还是《废都》《土门》《高兴》中所谓的“城”,均呈现明显的乡土画面感。它们“文如画,一段文字生成一个画面”[3],形成独具特色的语象流。诚如贾平凹在《极花·后记》中所言“以水墨而文学”一样,文学像中国画般散点透视着现实图景。阅读这些作品像是坐过山车一样穿梭于高山、河流与村舍间,更像是在找回记忆中已经消失和正在消失的乡土空间意象。乡土、乡俗、乡风、乡里、乡情、乡亲、乡思、乡愁、乡恋等 “乡”字,呈现出关于“乡”的深刻而持久的记忆画面。贾平凹像其他绝大部分人群一样,“不愿接受所依恋的地方发生这类改变,对美好记忆的珍视使得人们无法忘却曾投入大量情感与精力并和自己的生活联系紧密的地方,旧物于他们而言更可靠、更直观、更感性,因为其存在真实地留住了曾经的记忆与情感”[4]。作为善于把握时代精神和地域文化的高手,贾平凹能够敏锐地捕捉到隐匿于乡土背后的韵味与魅力,并能够通过生动的乡土形象和逼真的乡土意象表达自我对乡土空间的独到眼光、深厚情怀与记忆依恋。从文学地理的角度来看,贾平凹心目中的乡土圣地“商州”不仅与乡村的地理环境相连,更与乡民的空间记忆相通。
文学中语象叙事的对象广泛而复杂,不仅包括诸如绘画、雕塑和建筑等各类文本,而且涵盖各式人物与各种场景。贾平凹对生活细节的极度敏感和对场景再现的精准把握,帮助其绘就出关于文学地理意义上商州的独特语象世界,尤其是其中连续性、生活化与语境化的场景更为符合赵宪章提出的文学图像原型。高尔基认为:“艺术的作品不是叙述,而是用形象、图画来描写现实。”[5]133文学所再现的逼真图像、生动画面与真实场景正是文字极致描绘的结果,语象通过将抽象文字变成形象画面为叙事增添诗情画意。海德格尔在《林中路》中指出,图像在包括文学在内的艺术作品中的再现,更多的是借助语言的暗示、隐喻与引导等功能得以实现。贾平凹笔下的乡土语象呈现较为强大的情节暗示、美学体验、隐喻再现和现实扫描等叙事功能,通过借助作家个性化的语言风格,以语赋形于“被遮蔽”的记忆中的乡土千姿百态,实现最本真、最原生态乡土空间的语象再现与叙事重构。饮食、械斗和权力等场景共同构成贾平凹独特的乡土语象空间,它们成为作家心目中关于乡土的特殊空间记忆基点,正像贾平凹自己曾经亲眼看到的一间间农舍,亲自走过的一条条马路和亲口品尝的一盘盘土菜一样难以忘却、极度依恋。从语象出发,贾平凹真正还原出、反映出“被遮蔽”的乡土生活本来的样子。
一、饮食场的酸甜苦辣
从贾平凹小说创作的文学地理背景看,其作品具有较为原始和传统的秦汉地域性,处处挟裹着淳朴的秦汉民风乡俗,时时流溢着浓厚的秦汉文化气息,形成独特而自然的秦巴山水与意蕴悠长的关中风情书画。“西北,特别是陕西一带有浓郁的民俗、民情、民风,这一带是中国古代文化的发祥地,传统的东西在这里有很厚的积淀,中华民族从历史到哲学在这里扎着很深的根基,从而在民族特色的形态学上这里最纯粹。”[6]1贾平凹言语间流露出强烈的故乡情怀,这里的山水、草木与人物都成为其小说叙事的对象与主体,家乡的历史厚度与文化深度给予作家无穷尽的创作灵感、想象空间与叙事记忆。地处大西北的陕西虽在地理位置上偏居一偶,但在文化定位上却根红苗正。贾平凹摸到地域空间的根,抓住民族精神的魂,自由翱翔于情有独钟的乡土空间,其作品直抵底层社会的最深处,直面地域传统的最深层,直指乡里乡亲的最内心,深察、体悟生活于乡土空间最底层民众的乡风民俗、行为方式、思维习惯和内心情感,唤起、留住最真实、最美好、最感人的乡土记忆。得天独厚的空间环境,造就陕西淳朴憨厚、刚烈粗犷的乡土文化特质,这一点在其作品中众多关于饮食场景细致入微的描绘中得以充分体现。
民以食为天。秦汉之地的饮食文化简单中透着特色,低调中透着张扬,整体上虽不奢华,但却有内涵,凉皮、搅团、锅盔、糍粑、肉夹馍、洋芋糁子、羊肉泡馍和荞面饸饹等代表性小吃,看起来色诱难拒,嗅起来酸甜苦辣,吃起来可口爽心。如若概括起来,陕西饮食有两大乡土特色:不辣不够味道,不喝不够热情。因此,在当地就有离开辣子和白酒不成席之说,这一切无不体现出陕西热诚、真情、敦厚与豪爽的地域性饮食文化。小到朋友聚会、大到红白喜事中的饮食场景,无不得到贾平凹天马行空般的想象与淋漓尽致的抒写。
庄之蝶老婆牛月清在参加完汪希眠老娘的寿宴之后,真心邀请汪老太太和汪希眠老婆到自己家中做客。从她列出的购物单子中,可以想象这必将是一场发生在“废都”之内海吃海喝的私人聚会场景:
猪肉二斤,排骨一斤,鲤鱼一条,王八一个,鱿鱼半斤,海参半斤,莲菜三斤,韭黄二斤,豆荚一斤,豇豆一斤,西红柿二斤,茄子二斤,鲜蘑菇二斤,桂花稠酒三斤,雪碧七桶,豆腐三斤,朝鲜小菜各半斤,羊肉二斤,腊牛肉一斤,变蛋五个,烧鸡一只,烤鸭一只,熟猪肝、毛肚、熏肠成品各半斤……五粮液一瓶,啤酒十瓶……。[7]71
语象叙事是对即将上演的狂欢饮食场景的再现,其中出现的一个个数字、一系列菜品象征着文字本身的图像化,让人浮想联翩起聚会餐桌上丰富的菜肴和醉人的美酒,无不期待一个淋漓酣畅的“大块吃肉、大碗喝酒”的乡土式视觉盛宴。“语象叙事不再只单单被当作一种修辞技巧,而是被当作文本的镜子,它能够呈现无数文本意义,进一步瓦解或延伸叙事信息,在文本叙事中可以起到预示的作用。”[8]语象叙事对故事情节的发展起到暗示、铺陈与预示的作用,为文本的进一步叙事做好铺垫,画面感也因此油然而生,让人不自觉产生一种强烈的前往庄家赴宴的视觉幻象与情感冲动。但是,语象叙事在呈现视觉冲击力与想象力的同时,亦勾画出另一幅完全不同的画面,即通过场景的暗示预示着叙事的某种转向与升华。饮食场景在庄之蝶夫妇各自内心所呈现的不一样期待,让看似热闹的家庭聚会成为庄之蝶别有用心行事和实现个人欲望的手段与工具。“语象叙事的声音常常……承载着道德、警示和教益;语象叙事经常为了有益于虚构的人物,在道德上具有启发性。”[9]文本对菜品和美酒的大肆描写并非叙事的根本目的和主要意图,而是通过渲染饮食场景所呈现的狂欢化场景来预设和启示一个不可知却可感的诱惑,这诱惑正像来自小县城的唐宛儿身上无法抵挡的色诱一样,将庄之蝶一步步拖入丧失道德底线的黑暗、沉迷欲望的深渊和自甘堕落的困境。关于饮食场景的语象叙事预示着主人公潜藏的婚姻危机与错乱的生活现状,揭示出庄之蝶道德的沦丧、内心的迷失和精神的颓废。
类似的饮食场景在《高老庄》《秦腔》《极花》等作品中亦有呈现。《高老庄》中的高子路返乡为已经去世三年的老父亲筹办三周年祭祀以尽孝心,但并不精于世道的大学教授高子路碍于家族的面子和来自乡邻的压力,默许庆来和顺善等人要为其爹大过三周年的提议。大操大办饮食场景的再现,虽为高子路撑足了面子,但同时也预示着已经习惯城市生活的他,不得不在与高老庄乡土传统的斗争与妥协中,毅然选择逃离这片生他养他的故土家园,宁可让这一切消解于城市的繁华与躁动中,尘封于记忆中。《秦腔》中的村干部夏君亭为迎接即将莅临清风街新建市场参观的县商业局局长,不顾两委会欠账过多难以走账的事实,坚持公款宴请县领导大吃大喝以争取市场建设拨款。最终落空的计划预示着夏君亭在乡土空间日益衰败和乡土记忆日趋模糊的残酷现实下,虽有试图挽救乡土命运、改善乡土现实的种种努力,但乡土的颓败之势似乎是已经无法靠其个人的努力和担当可以阻挡得了的。正如秦腔的悄然没落一样,乡土的瓦解与崩塌早晚有一天也会到来。
生活相对宽裕些的黑家准备酒席招待村里人,为儿子兔子办满月宴。与贾平凹其他作品中让人垂涎三尺的“满汉全席”相比,对于《极花》中历尽艰辛“娶”来老婆并喜得贵子的黑亮而言,整个宴席操办得虽充满暖暖的真情却略显寒酸:
开始喝酒吃饭啦,黑亮爹做了三桌菜,当然是凉调土豆丝,热炒土豆片,豆腐炖土豆块,土豆糍粑,土豆粉条,虽然也有红条子肉呀、焖鸡汤呀、烧肠子呀,里面也还是有土豆。但大家都欢喜地说:行,行,有三个柱子菜!如果再舍得,有四个柱子菜就好了!……今儿酒好,二十元一瓶的,黑亮上酒上酒![10]148-149
土豆在胡蝶被拐卖地方的土话中叫洋芋,它是当地人一日三餐必不可少的主食。语象叙事为我们构建一个黑白色调的视觉空间,绘就一幅关于全土豆宴席的简笔画。一方面,土豆受欢迎的程度正如秦腔受到的万般钟爱一样,它已经成为当地饮食习惯的象征,是承载着圪梁村乡土记忆与梦想的最原始文化符号。另一方面,土豆业已成为当地人贫苦落后生活的真实写照与场景再现,其中虽包含着对传统风俗习惯的热爱、继承与坚守,但更多地预示着山民生活的苦辣酸甜与困苦煎熬。他们至今依旧居住在破旧阴暗的窑洞里,日子单调,物质匮乏,饮食单一,香火不旺。土豆配白酒可以是件幸福事儿,那股饮食的憨厚劲儿、喝酒的豪爽劲儿还没有丢,但喜事之中透露的悲凉、辛酸与无奈已经难以掩饰,预示的萧条、衰落与挣扎同样无法阻挡。即便如此,他们依然守护着这片贫瘠的土地,情愿在这“低调的奢华”中享受生活百味,一醉方休。如此这般的语象叙事在其多部作品中反复出现,它在唤起作家乡土记忆、暗示乡土理想的同时,造成的视觉震撼力是直达内心的,预设的乡土没落更是直逼灵魂的。
二、械斗场的爱恨情仇
在深化改革开放的大环境下,农村与城市共同分享着变革带来的红利“蛋糕”,但同时也遭遇各种各样的问题与矛盾。这是乡土空间变化最快的年代,亦是乡土矛盾最集中的时代。“去乡村化”的乡土难以逃脱具有强烈问题意识的作家的法眼,他们用手中之笔书写着当下沉重乡土的爱恨情仇。贾平凹在回望、坚守乡土的同时,不忘批判充斥于乡土空间的劣根性、愚昧性、狭隘性和流氓性,不断诠释农民内心仇恨意识与暴力倾向的民间根基与现实起源。在贾平凹看来,诸如暴力械斗等群体性事件已经成为农民解决问题、消解矛盾和瓦解冲突的重要途径,为了卑微的利益或微不足道的矛盾,邻里乡亲间都极有可能引起一场疯狂甚至致命的群体械斗。农民甚至“已经迷上了野蛮,相信暴力是必须的,而且认为自己永远是对的,所以他们认为自己有权随意运用暴力而不受处罚或制裁”[11]2。原本憨厚朴实的村民变成施暴者和暴力看客,暴力在他们眼中成为保护和坚守自我生存空间的最合理方式。贾平凹看似充满忧郁气质的作品潜藏着暴力冲突的萌芽,哪怕碰撞出丁点儿火花,它随时可能以野蛮而原始的械斗形式爆发出来。
村民为了维护自己及子孙后代的利益,不断向占了地、砍了树的地板厂施压、寻事,以保障自己后半生有的吃、有的喝。菊娃弟弟的意外溺亡成为村民“暴动”的导火索,蔡老黑借机将村民与地板厂之间“不共戴天”的仇恨煽动到极致,一个村民围攻、打砸工厂的群体性械斗场景在《高老庄》血腥上演:
天空中就出现了石头瓦片在飞,工厂的铁皮大门就咚哩咚咣响,有厂院墙上的瓦掉下来的破裂声和窗玻璃很空很脆的粉碎声,随着石头瓦片的越来越密,人群也慢慢向前移动,突然间厂院里又飞过来一阵木棍、石头,人群又哗哗往后退,有人捂了头跑到了房的山墙根,血从手指缝里往下滴……这么拖了十多米,苏红的裙子就拥了一堆,露出白生生的肚皮……便有七只手过去在那肚子上摸,并有人拉住了苏红的裙裤,这一拉,无数的手都去拉,裙裤被拉扯掉了,苏红裸了下身还在地上被拖着……。[12]230-233
语象叙事对群体性冲突的渲染与描写,在呈现血腥画面的同时,更多的是带来别样化的美学观感与动感体验,尽管它是充满暴力和仇恨的,但刚好揭示灰色暴力的乡土根源。“语象叙事描述所产生的画面感,使读者产生语象交会的视力幻觉和认知碰撞,获得更多的想象空间,进而衍生出独特的审美体验,使形象更加深入人心,让人记忆深刻。”[13]整个场景交织着声音与画面,如同电影中的打斗场面般紧张刺激。暴力打、砸、烧地板厂,侮辱副厂长苏红并非高老庄人的必然选择,他们这样做无非是想为自己争取到更大的利益、更多的回报,却选择了非正常的但又具有相当普遍性的乡土式解决途径。代表城市与现代文明的地板厂的侵入,给村民带来改变命运、脱贫致富希望的同时,让生活在变革期的农民更加深刻地感受到现实的残酷、命运的挣扎、信仰的缺失和自我的背叛。已经迷失自己的村民,再也无法忍受自我存在的压抑与狂躁,面对来自地板厂的欺辱与压迫,他们最终在械斗中将蕴藏在骨子里的偏狭、固执与匪气再次激发。群体械斗场景的再现,将叙事从文学中虚幻的描摹带回到真实的现实空间,并把记忆拉回到眼前,产生震撼人心的视觉化美学体验。
难逃乡村城市化命运的西京仁厚村,成为房地产开发商眼中的摇钱树,在震耳又刺耳的机器轰鸣声中,仁厚村在被拆迁的现实威逼下迅速走向衰败,家园轰然倒塌于推土机野蛮的车轮之下。《土门》中充满着传统文化气息的古朴仁厚村,有朝一日也会像其他已经被拆迁和正在被拆迁的村子一样,只剩下曾经美好的空间记忆。
下边的球场上,四面看台上人还是下饺子一样往下跳,有的跳下去就立即往场中跑,有的则摔在那里一时不得起来,起来了一瘸一跛又是跑。场中央就形成了河汊中的一个大漩涡,裁判员被围在中间,对方的球员也被分割了,也是一人一人围住在小漩涡里,甚至本队的球员也被围了,看不清是指责是殴打还是崇拜他们,反正人在那里拥挤,手在空中乱抓,裁判和球员的衣服被撕着,一只球鞋弧形地在空中飞过。[14]39
足球场上因裁判掏红牌处罚严重犯规球员而引起的推搡、混乱与冲突场景十分常见,但贾平凹小说中的语象叙事,其意义已经远远超出足球骚乱的范畴。在仁厚村上演的足球场上的射门比赛与厮杀场面,除了其带来的视觉刺激、身体快感、内心映像与心灵狂欢外,时刻弥漫在足球场上的火药味儿是对仁厚村村民生活空间与生存画面的隐喻性的描写与再现。“文学作品本身即是对生活及其可能形态的隐喻,艺术作品隐喻地表达了艺术家对生活的理想与批判。”[15]作为语象叙事功能的隐喻并不是简单地呈现某一场景的手段,它自身原本就是人类日常生活的根本体验与基本体验。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球迷对足球比赛的不满隐喻地表达着以成义为代表的仁厚村人对现实空间的不满,语象叙事就这样构成对作品主体叙事的隐喻性深化。球员在足球场上的激烈奔跑与精彩射门,形成充满力量与速度感的动感画面,把村民内心压抑的情绪从静态的身体感受转化为动态的空间共鸣,也让村民对生存空间与精神家园丧失理性般的坚守与保护跃然纸上。
相似的械斗场景在《带灯》《极花》等作品中也多有着墨。《带灯》中做沙厂生意的元家兄弟与做钢材生意的薛家兄弟,因生意矛盾而反目,在元家建在河滩的沙厂和薛家位于大土场子的钢材店同时上演着寻仇与复仇的群体斗殴事件,字里行间呈现着令人窒息的血腥画面,极大地暴露出樱镇典型的极端化社会矛盾,揭露了农民在经济利益面前表现出的愚昧行为、变态心理与暴力倾向。这样一个凸显现代性迷失的语象叙事,呈现的必定是一幅被扭曲的画面,无疑会让贾平凹在书写现代文明的过程中陷入无尽的沉思与忧虑。市场经济的洪流不仅淹没了憨厚淳朴的乡风民俗,而且冲塌了曾经美好的乡土空间,冲淡了令人怀念的乡土记忆,一切道德伦理被隐藏于暴力背后的经济伦理无情地撕毁。《极花》中圪梁村村民与前来解救被拐卖的胡蝶的警察、记者和胡蝶娘之间展开一场抢人大战,虽没有血腥的场面和大规模的械斗,但整个抢人场景同样充斥着紧张、刺激与惊险之气氛。在展现底层边缘人物生存空间的语象叙事中,“文学里当然就有太多的揭露、批判、怀疑、追问”[10]210,因为眼前的现实既是混沌而错乱的,也是丑陋而肮脏的。主人公胡蝶渴望通过进城改变自己的生存空间,完成自我的去乡村化进程,而这一切却在梦想即将成真之际被龌龊的现实彻底摧毁。被拐卖后的她再次滑向逆城市化的深渊,直至在这深渊中迫于无奈选择接受现实,并最终完成乡土身份的自我认同。然而,命运无常现实难料,胡蝶的生活又被戏剧性的解救之旅所“改变”,无不暗示着底层小人物悲剧性的现实人生与虚无化的存在空间。“极花”之名之实与胡蝶极具戏剧性的经历形成鲜明对照,它同时彰显贾平凹依然乐观的乡土文学理想。
三、权力场的悲喜迷恋
作为传统观念重要体现的权力崇拜和官本位意识深植于乡土价值的最核心,形成独具特色的中国式乡土权力场。围绕着场内场外的争斗与较量,自古以来未曾式微,甚至在现代性背景下依旧无法超脱传统价值观的影响,相反却有愈演愈烈之势。当下的乡村政治生态日渐扭曲化、利益化,农村现实空间日益异质化、狭隘化,这就造成乡村权力场变得非常复杂,乡土权力文化变得异常沉重。正如费孝通所言:“人们喜欢的是从权力中得到的利益。如果握在手上的权力并不能得到利益,或是可以不必握有权力也能得到的话,权力引诱也就不会太强烈。”[16]61乡村背后隐匿着复杂的人际链条,交织着错综的利害关系,这是权力在中国乡土社会一直以来备受崇拜的真实原因。权力场的磁力虽强大,但却似磁场的正负两级,有吸引也有排斥;也像硬币的两面,有正面也有背面。
贾平凹运用现实主义的描摹手法,深入体察乡土权力现场,近距离倾听权力场的悲喜迷恋与尔虞我诈,通过对乡村权力生态进行全方位的现实扫描,绘就出乡土权力的生态全景。《浮躁》年代的白石寨城为“因公牺牲”的福运举办丧事典礼会,因为县委书记等重要领导要出席,民警们就全力维持会场周边的秩序:
干警们就吼道:“北门外公园开全县大会,这里不准贸易,你听见了没有?!”有卖主再说:“会开它的会,我做我的生意,井水不犯河水嘛!”干警们就说:“你们阻塞交通,破坏气氛,你要不走就收了你的营业执照,到公安局论说去!”于是,百口禁住,慌忙收摊关门,人像逃难一般四下散去,便有清洁工手执扫帚乌烟瘴气地扫起街面了。[17]326
县里要召开全县大会缅怀福运,却要将与福运有着相同艰难遭遇和悲苦命运的小商小贩赶离会场周边,以免破坏气氛、影响心情。面对原本职责是保护自己的民警们的驱赶与威胁,胆小怕事的卖主们无奈逃离现场。小商小贩的慌张狼狈与民警们的威风霸道形成极其鲜明的对照与反差,这一切是权力使然。如此细微的场景描摹,如若没有对现实的细致观察和对权力的深切反思,恐怕是无法表达对一个因受乡镇干部之命为当权者打猎寻找野味而丢掉性命的福运的无尽痛惜和对权力的无限讽刺的。“小说审视的不是现实,而是存在。而存在并非已经发生的,存在属于人类可能性的领域,所有人类可能成为的,所有人类做得出来的。小说家画出存在地图,从而发现这样或那样一种人类可能性。”[18]54语象并非只停留在语言勾画的图像上,它也包含着对未来可能性的预设。作家不仅要对历史怀有深切的关怀之意与批判之情,更要对人类生活中可能的存在有所思考和预知,现实在文学作品中更多地表现为某种未来的存在状态与图景形式。福运的意外死亡与金狗的重返乡土,预示着贾平凹对乡土空间浮躁情绪的批判,以及对乡村权力乱象的嘲讽,也蕴含着作家必须具有的未来眼光与洞见,必须担当的现实责任与使命。
相同的权力场景在《秦腔》《带灯》等作品中亦不时出现。在《秦腔》中,为了迎接亲临清风街考察市场建设情况的县商业局局长,新任村支书夏君亭要求清风街上有头有脸的各色人物必须参加迎接、陪同参观。除了让村干部金莲提前训练几十个小学生列队欢迎局长大驾外,村委会还计划大摆筵席接待领导一行,可谓阵势庞大,仪式隆重,明事理、懂规矩。炎炎烈日之下,夏天智说:“要给清风街撑面子,就要把面子撑圆!”[19]130西装革履的他为了能够亲眼看到、亲自迎接局长的到来,忍饥挨饿中竟犯了低血糖病。如此的场景,让人忍俊不禁的同时,强烈地感受到权力散发出的无限魅力、强大威慑力和难以抗拒的诱惑力,但夏天智的犯病象征着乡土权力的病态化现实。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这是贾平凹对处于社会变革期乡土权力场一次实实在在的现实扫描与场景再现,也是对乡土权力生态的一次隐喻性揭露与讽刺。
市委黄书记将要第一次到访带灯工作的樱镇,当地镇政府在接到县委县政府的指示后,迅速开展迎接市领导的各项准备工作。全员到岗,事无巨细,尽最大可能安排好黄书记一行的全部路线行程与活动计划,但《带灯》描绘的某些细节让人哭笑不得:
黄书记两个小时上一次厕所,这就得把王长计老汉家的厕所收拾干净,三天之内所有人不得再去使用,而视察调研沿途也选择三个干净的厕所收拾干净,并将所有能看到的尿窖子全棚盖上包谷秆和豆秆。还有黄书记要劳动,那就让黄书记拿锨扎地,大石村的田地多石渣,如果黄书记一锨没扎下去多尴尬,这就得提前把那块地翻一遍,疏软才是。随便用一把旧锨不雅观,起码得安个新锨把,但新锨把容易磨手,这就要王长计老汉安一个新锨把了,用瓷片磨光,用手磨蹭发亮才是。[20]248
语象叙事是对乡土权力场最为细致、最为鲜活、最为真实的揭露与嘲讽。语象的突出特点正在于“明晰和生动,这样人们几乎能够看到所叙述的东西”[21]133-134,它使原本抽象的权力生动地呈现在人们面前,变为一种可感可见的真实存在。没有对官场生态的细致观察与体会,贾平凹绝对无法艺术地概括现实权力场。语象叙事的运用比直接的权力叙事更富震撼力和空间感,它是“在隐喻和象征维度上对现实的一个阐释”[22]。权力背后的威严与等级,在给人一种高高在上的视觉差异的同时,让人倍感紧张甚至是恐惧,权力不再是服务群众的工具,而成为权力拥有者身份与地位的象征。厕所和铁锨已经远远超出其原本的日常功能与实用价值,厕所成为特权的符号,铁锨成为作秀的工具,它们像带灯本人一样,只是作为权力场中任人摆布的试验品和牺牲品,也只是贾平凹隐喻地批判乡土权力空间的媒介。厕所和铁锨等隐喻意象成为某种抽象符号的化身,它们使得权力在文学叙事中变得真实而神秘,同时印证贾平凹试图再现乡土权力现场的诗意冲动。如此虚无而裂变的权力场景,必然预示着带灯们将因为无法穿越夜的黑而走向迷失、背叛与疯狂。
四、结语
文学可以借之叙事的媒介很多,而“语”与“象”恰好代表着罗兰·巴特所说的“叙事承载物”,宗白华所言之“读画”,它们共同构成小说中更加具体可感的叙事载体,语象叙事使得文学通过运用时间的暂时性实现意象的恒久性和空间的同在性成为可能。贾平凹的作品是对传统线性叙事结构与模式的反叛和颠覆,它们不再沿袭单一的时间化故事情节推进路径,而是采用将时间融入空间的语象化再现途径。语象叙事为贾平凹寻找和抒写乡土提供了更为开阔、更加精准的空间视点,让乡土记忆顿生画面感与空间感,也让乡土叙事凸显图像性与真实性,它是作家乡土审美的心灵碰撞与自然流露。作为当下乡土文学的旗帜型作家,贾平凹个性化的创作实践不仅是对乡土审美观照方式的根本转变,也是对空间记忆基点的深度寻找,更是对文学叙事转向的积极探索。
[1] CLUVER, CLAUS.Ekphrasis Reconsidered: On Verbal Representations of Non-verbal Texts[M]. Amsterdam: Rodopi, 1997.
[2] 王安,程锡麟.语象叙事[J].外国文学,2016(4):77-87.
[3] 高红樱.艾特玛托夫小说“语言图像”的审美特征[J].天津师范大学学报,2012(3):49-53.
[4] 黄向,吴亚云.空间感知基点影响地方依恋的关键因素[J].人文地理,2013(6):43-48.
[5] 高尔基.文学论文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
[6] 孙见喜.贾平凹前传:卷二[M].广州:花城出版社,2001.
[7] 贾平凹.废都[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9.
[8] 巴奇,埃尔斯纳.导言:审视语象叙事的八种方法[J].古典哲学,2007(1):1-6.
[9] CUNNINGHAM, VALENTINE. Why Ekphrasis?[J]. Classical Philology, 2007(1):57-71.
[10] 贾平凹.极花[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
[11] 基恩.暴力与民主 [M].吴新叶,易承志,荣启涵,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
[12] 贾平凹.高老庄[M].桂林:漓江出版社,2012.
[13] 龙艳霞,唐伟胜.从《秘密金鱼》看“语象叙事”的叙事功能[J].外国语文,2015(3):51-56.
[14] 贾平凹.土门[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10.
[15] 龚道臻.乡村政治生态的隐喻叙事:以《带灯》为视点[J].创作与评论,2014(3):50-55.
[16] 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17] 贾平凹.浮躁[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9.
[18] 昆德拉.小说的艺术[M].董强,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
[19] 贾平凹.秦腔[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10.
[20] 贾平凹.带灯[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
[21] CLARER, MARIO.Ekphrasis[M]. Abington: Routledge,2005.
[22] 段德宁.文学图像学溯源及其中国语境[J].内蒙古社会科学,2015(4):143-149.
SpaceCovered:EkphrasisinJiaPingwa’sNovels
WANG Huawei
(School of Literature, Northwest University, Xi’an 710127, China)
Ekphrasis is a kind of method to rebel and overturn traditional linear structure and time narrative model, and provides a wider and clearer spacial view of visual writing and image reappearance. There exists ekphrasis in the novels of Jia Pingwa, and its novels depict a lot of continuous, lifelike and context-oriented local scene,which makes it possible that real local space is presented by words. As one of the leading writers in local literature, Jia Pingwa’s personalized literary creation changes ways of thinking about home village and looking for the memory basis of local space, and actively explores the turn-around of literary narrative.
Ekphrasis; scenes; home village; space
2017-09-29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一般项目“路遥、陈忠实、贾平凹与新时期现实主义文学研究”(11BZW022);陕西省社科界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研究项目“陕西省图书出版“走出去”中的译介路径研究”(2015Z25);西安市社科基金项目“西安现当代文学作品‘走出去’中的翻译问题研究”(15L127)的阶段性成果
王华伟(1979—),男,河南南阳人,西北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讲师,研究方向为西方文论、文学批评与翻译。
I207.42
A
1008—4444(2017)06—0122—06
王菊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