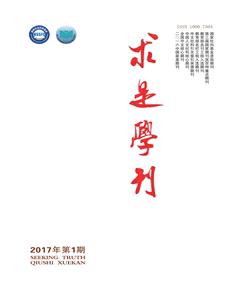挑战与应对:犯罪全球化的主要表现及其研究
摘 要:犯罪全球化表现在不同的维度,其对民族国家政治秩序和刑事司法体制形成了挑战。当代犯罪全球化研究的主要理论范式对于思考如何应对这种挑战具有重要的借鉴和啟示意义,但它们也存在某些缺陷和不足。在应对犯罪全球化的过程中,中国既面临挑战,也面临机遇,只要深化刑事司法制度改革,通过加强犯罪治理制度的创新研究,积极参与全球犯罪治理的制度建设,就能够有效应对挑战,并对人类和平与安全做出贡献。
关键词:犯罪全球化;全球犯罪治理;中国;挑战;应对
作者简介:张文龙,男,法学博士,华东政法大学师资博士后研究人员,从事法律全球化研究。
中图分类号:D9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17)01-0097-08
伴随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全球化,犯罪问题也呈现出全球化的趋势。犯罪全球化对民族国家时代的刑事司法制度构成了挑战。本文尝试提出犯罪全球化的基本问题域,考察犯罪全球化的主要表现,分析犯罪全球化的主要理论范式,进而提出中国应对犯罪全球化的建议。
一、界定犯罪全球化:语境与问题域
全球化的观念和话语已经遍及今天的人文社会科学,早在20世纪末就已经有人谈到“全球化作为一种观念的时代已经到来”[1](P1)。虽然关于“全球化话语”存在很多争论,但是,在21世纪这种话语的影响力已经占据了主导地位,渗透到各个社会领域。如何理解犯罪与全球化的关系是我们思考的中心问题。我们可以从五个方面对这个问题展开追问:(1)全球化如何影响犯罪的发展。(2)犯罪如何影响全球化的演变。(3)犯罪问题离不开社会权力的定义与控制,那么,全球化如何影响社会犯罪控制的发展。(4)社会的犯罪控制如何塑造全球化本身。(5)关于犯罪与全球化的反思性概念如何促进关于犯罪全球化的认知。
首先,全球化是塑造犯罪的重要力量。传统上,我们认为犯罪的社会语境是地方性的,因此,犯罪学家试图通过地方的经济、政治、法律、宗教、文化、教育现状来解释相关的犯罪现象。但是,随着地球村的到来,犯罪的社会语境变得具有全球性。比如犯罪经济越来越成全球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还有全球大众媒体对犯罪新闻的报道,使得犯罪和刑事司法的图像和信息实现全球化的流动和传播;此外宗教的全球复兴现象,尤其是伊斯兰极端分子的恐怖犯罪,也表明了全球化的宗教对于恐怖犯罪的塑造和影响。
其次,犯罪是推动全球化演变不可忽视的力量。犯罪是全球化的黑暗面。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经济犯罪、信息全球化进程中的网络犯罪、文化全球化进程中的犯罪传播、宗教全球化进程中的恐怖犯罪、法律全球化进程中的国家犯罪等等,都是这种黑暗面的例证。可见,犯罪活动本身内嵌于全球社会发展进程中。
再次,全球化推动犯罪控制模式转变。伴随着经济全球化,国家从经济领域撤退,但是社会经济引发的各种犯罪问题,却使得国家不断强化其对犯罪的社会控制。新自由主义的信条开始转换为刑事司法实践的理念,风险控制日益成为刑事司法的运作逻辑。而伴随着“反恐战争”的全球化,以控制文化为特征的英美刑事司法日益渗透到国际刑事司法的实践中。[2](P140-158)
复次,犯罪控制构成全球治理的重要内容。在民族国家时代,犯罪控制是由国家垄断。二战结束之后,由于对国际战犯的审判,国际刑事司法制度开始逐步建立和运作。2002年国际刑事法院的创建,意味着由民族国家刑事司法垄断的犯罪控制逐步发展出适应当代全球治理的国际刑事司法机制。此外,犯罪控制的商品化随着跨国安全企业的发展,逐步渗透到全球治理层面。[3](P148-171)
最后,“犯罪全球化”可能是一个充满争论的概念。这不仅是因为“全球化话语”本身就充满了各种争论,而且由于“犯罪”概念本身也一直充满了历史和现实的争论。尽管如此,概念反思性的争论,却有可能开辟新视野。在这种新视野下,犯罪全球化是指犯罪跨越民族国家的边界在全球范围内流动、传播和游走。作为全球化的黑暗面,犯罪全球化与经济全球化、科技全球化、法律全球化、媒体全球化、宗教全球化等现象相互交织在一起,因此,对于犯罪全球化的研究和应对,离不开对全球化进程各个领域的研究和思考,唯有这样才能对犯罪全球化的现状和趋势形成正确的判断和认识。
二、犯罪全球化研究的主要理论范式
关于犯罪全球化的著述汗牛充栋,其中理论学说不乏精彩之作。相较之下,马克·芬德雷(Mark Findlay)、卡特娅·弗兰科·阿斯(Katja Franko Aas)和安佳·雅各比(Anja P. Jakobi)的犯罪全球化理论,论证系统且影响比较大,所以,下面对他们的理论进行讨论。
首先是澳大利亚学者马克·芬德雷的犯罪全球化(globalization of crime)理论,其核心观点认为犯罪与全球化互为彼此的语境,并主张全球化为犯罪创造了新的和有利的语境。对于犯罪的语境论,芬德雷论证说:“对犯罪的理解不能脱离其社会语境。下述分析的语境包括物理空间、制度过程、关系模式和个体差异。语境是指一种转变状态,在语境中,犯罪影响到许多社会、文化、政治和经济决定因素,并且反过来受其所影响。”[4](PVii)在他看来,全球化作为一个反思性概念,是一个重新理解犯罪选择和犯罪关系的叙事语境,因为犯罪是全球化进程的一个部分。
关于犯罪全球化的分析,芬德雷的观点主要从五个方面展开,具体言之如下:(1)表现(或歪曲)犯罪。这是一个犯罪叙事的建构问题。在社会中,犯罪趋势常常是人们关注的重要问题。那么,在全球层面,犯罪趋势如何?世界犯罪率是增加了还是下降了?芬德雷认为仅从各国犯罪统计来分析世界犯罪趋势是有问题的,因为各国对于犯罪的法律定义和文化理解存在差异。不过,犯罪问题透过大众媒体在全球层面形成的某种共同认知,如对犯罪的道德恐慌,可能是当前全球化的犯罪叙事之特征。(2)犯罪与社会发展。芬德雷认为全球化核心是现代化,所谓现代化就是社会发展,主要是围绕经济发展和消费问题。而犯罪问题很大程度上是社会发展引致的社会问题,比如贫困导致的财产犯罪问题,由此,全球化可能为犯罪提供了新的动力和机会,像跨国的人口贩卖、毒品走私。在芬德雷看来,全球化为犯罪提供了市场条件,正如现代化提供了犯罪的经济动机,因此,犯罪是社会发展的自然产物。(3)犯罪与社会功能紊乱。犯罪通常被视为社会功能紊乱的产物,即一种社会病态的表现,不过,如果犯罪是一种基于利益和机会选择的结果,那么,犯罪就是社会的正常现象。在这个意义上,全球化可能促进了某些犯罪的全球扩散和发展,因为它提供了新的获利机会或条件。(4)犯罪经济。当人们没有获得合法机会,或者处于市场经济的边缘化境地,犯罪经济就可能是人们应对问题的一种解决方法。芬德雷认为经济获利始终是人们实施犯罪的一个主要动因。在这一点上,经济全球化恰恰是犯罪经济繁荣的一个重要语境。(5)犯罪作为选择。当人没有其他的合法机会和条件去生存时,犯罪作为一种选择并非人的社会病态,而可能是一种理性的表现。对此,芬德雷认为全球化为犯罪选择和犯罪关系创造了更多有利的语境,如全球市场。[4](P20-220)
芬德雷对于犯罪全球化的分析和论证,是非常系统而富有魅力的。正如他所说:“语境是关键,比较是框架,悖论是分析工具。”[4](P221)其透过对犯罪与全球化的语境比较分析,揭示出一些重要的悖论关系,比如犯罪是社会现代化的自然结果而不是社会功能紊乱表现,但是,芬德雷的理论存在明显的缺陷就是对于犯罪全球化的解释具有经济主义色彩,而对其他解释维度的关注不够充分。
其次是挪威学者卡特娅·弗兰科·阿斯的全球化与犯罪(globalization & crime)理论,其核心观点认为犯罪学的分析需要超越民族国家的视野,因为犯罪问题已经跨越民族国家的边界而游走全球。在她看来,犯罪问题与全球化之间的关联主要表现为七个方面:(1)全球流动性与人口贩卖。伴随着人口的全球流动,人口贩卖和走私的问题已经日益引起全球关注,全球“性贸易”是这种全球犯罪的重要例证。(2)都市犯罪学与全球都市。全球都市化的膨胀,使得许多城市问题被犯罪化,一方面城市贫民区已经是都市犯罪的策源地,另一方面城市社区日益封闭和监控化,以应对都市犯罪问题。(3)“越轨的移民”。由于移民的文化与所在国家的主流文化之间的差异,移民通常被视为潜在的罪犯,一种“他者的犯罪学”将移民视为“危险的他者”。(4)全球安全与“反恐战争”。9·11事件使得安全变成了一个全球问题,为了应对恐怖主义的全球威胁,英美为首的西方国家发起全球“反恐战争”,由此,使得犯罪与战争的界限被侵蚀。同时,在“反恐战争”的幌子下,可能是各种违反人权的犯罪活动,比如,对“非法战斗人员”实施酷刑。(5)治理全球风险。犯罪被视为一种全球风险,除了恐怖主义之外,还有各种跨国有组织犯罪和国家犯罪问题,应对这些全球犯罪风险需要建立全球治理的体制。(6)控制网络空间。随着互联网的广泛应用,网络犯罪已经成为一个全球问题,网络犯罪既包括“新瓶装旧酒”的现象,如传统犯罪活动对互联网这种新工具的利用,还包括一些新的犯罪现象,如知识产权剽窃、垃圾邮件、网络模拟点击诈骗等。(7)超越国家。犯罪控制通常被认为是国家主权垄断的领域。然而,在新的全球化趋势中,犯罪控制日益被国家分包给企业,私有化的监狱、私有化的社会安保、私有化的边境控制等等,都表明国家对犯罪控制的垄断逐渐被打破,以国家为中心的犯罪控制开始被私人企业或商业模式所控制。[3](P27-230)
阿斯对犯罪(控制)与全球化的叙述和论证具有迷人的话语,充满了启示性的辩证分析,她对传统犯罪学的批判,更是让人看到全球犯罪学所具有的理性魅力。透过她对犯罪全球化的问题分析,我们可以看到犯罪与全球化之间的复杂性和内在张力。同时,她主张的世界主义犯罪学和刑事司法模式,似乎復兴了犯罪学和刑事司法的解放面向。不过,阿斯的理论也存在明显的缺陷:其一,理论分析过于碎片化,她借助各种全球化话语来分析犯罪问题,但是,缺乏足够的理论提炼,使得不同的理论主题过于分散,不同篇章之间缺乏合理的逻辑连贯性;其二,阿斯对于世界主义犯罪学和刑事司法模式的提倡,象征多于功能,口号多于实际,缺乏真正应对方案。
最后是德国安佳·雅各比关于全球犯罪治理(global crime governance)的理论。雅各比认为对错选择因时间、宗教、国家法律或者社会期待而变,同样,犯罪也是相对的,在一个国家合法的,在另一个国家则可能是非法的,过去被认为是允许的行为,今天可能变成是被禁止的行为。不过,在全球化的今天,世界政治越来越关注全球层面或世界范围内定义或重新定义犯罪的规制设置,而且,国家已经在这个领域建立起各种不同的合作,从警务合作到共同的犯罪化。因此,在她看来,全球犯罪化(global criminalization)已经是新兴世界社会的组成部分,并且与一种关于对错被普遍定义的全球文化联系在一起。根据雅各比的分析,全球犯罪治理的重要因素包括:(1)全球标准设置;(2)关于犯罪活动的全球信息传播;(3)对执法行动的监督。在她看来,全球犯罪治理不仅是透过国家规制实现犯罪治理,而且是成功建立起世界范围内关于犯罪化、起诉和惩罚的专门规制活动。
按照雅各比自己的说法,她关于全球犯罪治理的研究是一种刑事政策进路,对此,她建立起了分析全球刑事政策的四种理想类型:国内刑事政策/超领土的刑事政策、国内进路/国际进路,并由此分类出不同的犯罪治理的策略。同时,她还强调全球犯罪治理的理性化,并认为理性化原则是全球犯罪治理兴起的原因。在她看来,世界理性化过程的目的是让这个世界变得透明、可理解和可问责,当然,理性化原则和价值是与西方文化紧密相连的,并体现西方文化独特的规范与价值。此外,在她的分析框架中,社会学的制度主义逻辑是她构建全球犯罪治理模式的基本工具,即不同制度逻辑的差异可能使得全球犯罪治理呈现不同的权力格局,或者说不同的犯罪控制模式。对此,她具体分析了洗钱、反腐败和人口贩卖三种犯罪的全球治理模式。在结论上,雅各比强调全球犯罪治理的碎片化问题,并试图提出替代性的治理范式,比如作为治理性的全球犯罪治理,进一步促进国际刑事政策的理性化。[5](P27-248)
雅各比对全球犯罪治理的系统分析和论证,充满了新的思想洞见。不同于传统的犯罪学理论和刑事政策分析,她透过世界社会的理论视角,揭示出全球犯罪化的复杂性,并刻画出全球犯罪治理模式的差异化制度逻辑。虽然她的理论分析对于我们思考全球犯罪治理很有助益,但不可否认的是,其理论同样存在明显的不足和缺陷:其一,雅各比偏重犯罪政策的研究进路,使得其实证研究有余而理论提炼不足,虽然她借助世界社会的理论视角来解释全球犯罪的治理问题,但是,并未提出一个充分的理论解释框架,正如她自己最后的结论上也试图重拾福柯的治理性概念作为全球犯罪治理的替代性模式;其二,雅各比的研究很大程度上更关注西方国家当前面临的全球犯罪问题,这使得其对全球犯罪治理的分析不自觉地体现出西方中心主义色彩,因此,自然使得她的理论普适性打点折扣。
可以说,上述三种理论范式各有特点,如果说芬德雷和阿斯的理论更偏重犯罪全球化的分析,那么,雅各比的研究则侧重于全球犯罪化的论证。芬德雷的研究比阿斯的研究早,如果说芬德雷力图从犯罪学角度分析全球犯罪问题,那么阿斯则主要从“全球化理论群”寻找解释全球犯罪的话语资源。相对而言,由于芬德雷的理论写得早,像“世界风险社会”这样的理论资源当时还没进入他的研究视野,不过,晚近其写作的新书已经开始将犯罪作为一种全球风险,并提出“全球犯罪风险”概念,试图以此对国际刑事司法制度进行理论重构。[2](P44-47)不过,芬德雷和阿斯关于全球犯罪治理的研究相当薄弱,在这方面,刚进入这个领域的雅各比可谓独领风骚,尽管芬德雷的新书已经弥补前作的不足和缺陷,但是,雅各比毕竟更加详尽实证研究了当前全球犯罪治理模式与实践,对当前全球犯罪及其治理提供了更丰富的政策视野和理论认识。总体而言,上述的理论范式具有前瞻性、创新性和批判性,因此,对推进我国学界关于全球犯罪及其治理的研究,无疑具有很大的启迪和借鉴意义。
三、犯罪全球化的主要表现
在当代世界,犯罪全球化现象错综复杂,但以下方面的表现尤为突出。
第一,恐怖主义成为当前最令人恐惧的全球犯罪问题。恐怖主义在现代演变过程中,一直伴随着民族主义运动,成为反抗殖民统治的一种方式。在以色列与巴勒斯坦、在英国与北爱尔兰等地区常常发生的恐怖袭击案件,反映出恐怖主义被用来当作争取民族独立自治以及引起国际社会关注的一种方式。可以说,这种样式的恐怖主义仍是民族国家时代的产物。
在美国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后,恐怖主义的语义似乎获得了新的维度和演变,恐怖主义开始超越地方语境而变成了全球化现象。虽然“文明冲突论”为这种全球恐怖主义提供了文化解释的语境,但是,更重要的是全球信息媒介使得恐怖主义变成了一个可以直接视觉化的影像。“两架飞机直接撞击世界贸易大厦双子楼”的视觉冲击透过全球化的大众媒体传遍世界,后来“恐怖的媒介化”变成了“媒介的恐怖化”,恐怖分子开始利用大众媒介甚至互联网来进行恐怖主义的宣传、动员和组织实施活动。虽然恐怖袭击可能由不同的宗教信仰者或者具有不同政治信念的人发动,但是,当前世界局势表明极端伊斯兰信仰是全球恐怖主义的策源地。“伊斯兰全球圣战”是这种新恐怖主义的基本理念和精神。[6](P46-48)最近发生在法国的两次恐怖袭击,都表明这种新式恐怖主义继续蔓延全球,并造成全球性的犯罪恐慌。
第二,网络犯罪变成全球化产业。网络犯罪是一种新型全球犯罪现象。伴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全球化,计算机和互联网技术日益成为重要犯罪手段和工具。虚拟的网络空间成为犯罪天堂,因为这个由计算机程序代码构建的社会空间不受现代法律形式的直接规制。Web2.0的运作模式,使得犯罪的空间界面超越领土限制,由此,犯罪活动可以穿透现实物理空间而游走全球。因此,像色情、卖淫、诈骗、诽谤等很多传统的犯罪活动从现实世界漂移到虚拟网络世界,这种现象可谓“新瓶装旧酒”。但从早期的计算机犯罪到现在的网络犯罪,发生的更重要的犯罪变迁现象,就是互联网而不是计算机改变了犯罪的模式,计算机现在只是网络终端而已,而互联网的技术逻辑与行为模式却塑造了犯罪的社会选择模式,像黑客犯罪就是例证。网络犯罪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产业化,很多犯罪集团及组织就利用互联网实施获利性的犯罪活动,尤其是借助黑客的技术手段,实现跨国犯罪,比如,全球点击欺诈产业就是其中的典型例子。
第三,跨国有组织犯罪已经变成突出的全球问题。黑手党或者其他黑社会组织一直是各国政府犯罪打击的重点对象。在现代社会早期,有组织犯罪现象的跨国化是比较少的,因为民族国家的领土限制和交通不便。但是,隨着经济全球化扩散,以及交通运输与通信技术的发展,跨国有组织犯罪越来越被普遍化为一个全球性的治理问题。跨国犯罪组织实施的犯罪或违法活动包括,但不限于走私、贩卖人口、毒品制造与分销、跨国卖淫、核武原料或军事武器交易、洗钱、地下钱庄、偷渡边境、赌博业等等。当今犯罪组织跨国化、全球化的一个重要趋势,就是利用合法企业形式来实现犯罪活动,跨国公司的犯罪活动就是其中突出的例子。与此同时,犯罪组织与互联网技术的结合,也是跨国有组织犯罪演变的一个重要趋势。借助互联网和信息技术,各种犯罪组织相互连接演变成一个全球化的犯罪网络。
第四,全球金融犯罪的崛起对世界经济秩序构成重大威胁。金融犯罪是现代货币经济的产物,并伴随经济全球化而扩散到世界各国。现代金融犯罪已经从早期伪造货币或票据,发展到内幕交易行为、洗钱行为和其他操纵证券市场的行为。现代货币的全球流通,尤其是电子金融工具的出现,使得现代金融犯罪可以跨越民族国家的边界,像黑客对金融网络系统的入侵和攻击就是全球金融犯罪的新趋势。此外,跨国公司也是全球金融犯罪的重要运作架构和媒介,像离岸公司常常被用来实施洗钱等金融犯罪。而且,恐怖组织或其他犯罪组织也会利用公司的合法形式来进行资金的筹集、划拨和投资,从而维系其自身的运作。因此,全球金融犯罪与其他犯罪现象相互交织,在促进其他犯罪活动同时,也被这些犯罪活动所支持。[7](P1-20)
第五,生态全球犯罪已经引起世界关注。环境问题的全球化是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产物,现代西方社会的环境问题与危机,随着现代性的全球扩张而传播到世界各地。环境问题的全球化,一方面是全球经济发展的自然结果,因为世界经济体系的分工,发达国家的一些落后和造成环境污染的产业被转移到发展中国家,自然使得造成西方社会环境危机的产业污染向非西方的国家和社会扩散。另一方面,由于地球生态系统的一体化,在发展中国家制造和产生的污染和环境破坏结果,同时可能对西方国家的环境产生影响,反之亦然。此外,西方环境保护运动,在全球大众媒体的塑造下,强烈影响到全球消费文化对于环境问题的关注。与此同时,全球政治层面对世界发展的环境问题关注,已经促进世界各国对环境保护形成共识,并采取全球行动措施。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西方犯罪学理论最近兴起了绿色犯罪学的思想潮流,并提出生态—全球犯罪的概念和问题,试图从生态正义角度,将危害自然的人类活动犯罪化。在绿色犯罪学看来,跨国生态犯罪主要包括三个重要领域: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废物和污染。在当前全球生态犯罪中,跨国公司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因为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跨国公司利用发展中国家环境保护意识薄弱,对其环境资源进行掠夺和破坏,比如,破坏热带雨林,推广转基因作物,或者进行跨国垃圾贸易,等等。与此同时,全球媒体对这些环境问题聚焦,已经引起全球观众对上述生态—全球犯罪的关注,并引发相应的环保抗议行动。[8](P22-24)
第六,全球犯罪化与国际刑事立法。犯罪全球化离不开全球犯罪化,因为犯罪的定义和标签是社会沟通的产物,即犯罪化的结果。因此,在全球层面形成某种禁止制度,是全球犯罪化的重要表现,比如:《联合国宪章》第七章关于和平之威胁、和平之破坏和侵略行为的禁止规定;《世界人权宣言》中关于奴役、酷刑、歧视等的禁止规定;《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中关于奴隶、奴役、强制或强迫劳动以及关于鼓吹战争宣传,鼓吹民族、种族或宗教仇恨的禁止规定;《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对种族灭绝行为的禁止规定;《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对酷刑、非法拘禁和审讯等行为的禁止规定;《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对海盗行为、海洋环境污染的禁止规定;《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及其补充议定书中关于有组织犯罪、洗钱、腐败、贩卖人口等问题的禁止规定;《联合国禁止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公约》对毒品贩卖行为的禁止规定;《国际法院规约》《国际法庭宪章》《远东国际法庭宪章》《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宪章及其法庭判决书中认可的各种国际法原则》《前南斯拉夫国际刑事法庭规约》《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规约》《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等国际公约对战争罪、危害人类罪、种族灭绝罪和侵略罪的禁止规定。[9](P196-225)
上述的国际刑事立法,反映了国际社会对于某些严重危害全球社会共同体利益的行为进行犯罪化,并透过缔约国家履行国际条约义务的形式,转变为相应的国家刑事法律制度来实现犯罪的预防与控制。此外,一些地区性的犯罪化措施对全球犯罪化也具有促进作用,如欧盟的《网络犯罪公约》对于推动全球层面打击网络犯罪,起到了很好的示范和借鉴作用。
第七,刑事司法与犯罪控制的全球化。在民族国家崛起的过程中,犯罪控制逐渐被国家所垄断形成一整套国家刑事司法制度,即一个民族国家,一部刑法典和一套刑事司法机构,比如,警察、监狱和法院的国家化,使得控制犯罪的合法暴力完全被国家垄断。二战之后,对国际战犯的审判,如纽伦堡审判和东京审判,开启国际刑事司法制度的先河。后来南斯拉夫国际刑事法庭、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的建立和运作,尤其是国际刑事法院的建立与运行,标志着国际刑事司法制度的不断完善。由此,以民族国家制度为基本架构的国家刑事司法体系与国际刑事司法制度就构成了当前世界犯罪控制的“威斯特法利亚双重奏”体系。[10](P80)
不过,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对上述的犯罪控制模式产生很大的冲击和挑战。首先,国家对犯罪控制进行垄断的合法性遭到质疑,大量非国家的行动者开始参与犯罪控制,比如社区、公民个人、商业化的安全企业和跨国安保公司等;其次,面对日益增加的犯罪风险,传统刑事司法运作的有效性也遭到质疑,由此,以保障个人权利为导向的刑事司法模式,向预防犯罪风险的“控制文化”模式转变;最后,面对跨国化、全球化的犯罪问题,以民族国家领土管辖为原则的犯罪规制模式面临着合法化危机,一方面传统民族国家法律难以有效应对全球犯罪,另一方面西方国家借打击全球犯罪的名义,对其他发展中国家实施军事打击和侵略,以维持其全球霸权。正是上述全球化的挑战,使得全球化的犯罪控制变成一种可能选择,但如何有效整合现有的刑事司法制度架构,应对当前犯罪全球化的挑战,仍存在各种争论。
四、犯罪全球化的挑战与中国的应对
对中国来说,犯罪全球化既是挑战,也是机遇,因此,笔者尝试在上述考察和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以下五点看法。
第一,在全球化时代,世界由工业社会进入全球信息社会和世界风险社会。在全球信息社会,“信息没有国界,只有网络;没有中心,只有结点;没有等级,只有界面;沒有历史,只有当下”[11]。在信息化时代,全球时空被信息压缩,人们可以实现远距离的即时互动和沟通,因此,全球信息化秩序赋予人们更多的机会和便利。但是,全球信息社会同时也是一个世界风险社会,因为信息爆炸可能带来风险,风险具有不确定性、反身性和全球性的特征。在当代,恐怖主义、跨国有组织犯罪、生态犯罪、金融犯罪和网络犯罪已经成为威胁人类安全与世界秩序的全球风险。这些全球化的犯罪风险跨越民族国家边界而游走全球,传统民族国家法律已经难以有效应对这些全球犯罪风险,因此,必须在跨国或者全球层面对这些犯罪风险进行新的法律规制。
第二,在应对犯罪全球化的过程中,英美等西方国家对全球犯罪治理的主导作用,包含着霸权主义的逻辑。西方国家在打击全球犯罪方面的主导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层次:(1)在刑事政策和国际刑事立法层面,西方国家拥有更多的话语权和资源;(2)在刑事司法和犯罪控制层面,以风险控制为特征的英美刑事司法模式在全球扩散;(3)在国际刑事司法实践和刑事司法的国际合作层面,西方国家之间形成更加团结的合作模式,而非西方国家通常遭到排斥,甚至是成为西方国家打击全球犯罪的对象。在全球犯罪治理过程中,面对西方国家的霸权主义,非西方国家应当采取反霸权的立场,而非唯西方国家马首是瞻。在学习和借鉴西方犯罪理论和刑事司法制度的过程中,要反对西方法律中心论和优越论,并根据自己国家刑事司法实践和犯罪控制需要自主地决定是否需要移植或借鉴西方的刑事司法理论和制度。虽然西方国家在全球犯罪治理中占据着主导地位,但是,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深入,世界体系格局变化并非绝对有利于西方核心国家。非西方国家完全可以借助世界自由市场和国际法律机制,实现经济增长,推动国内民主政治,增强国家综合实力,从而提升自身参与全球犯罪治理的软、硬实力。
第三,中国作为世界大国和文明古国,必须在继续发展国家硬实力的同时,发挥自身的文化“软实力”,在全球犯罪治理过程中,彰显其道义担当。犯罪全球化危害全人类的利益,打击全球犯罪是每个国家必须承担的国际道德和法律义务。打击全球犯罪,维护人类和平与安全,是人类共同价值的要求和体现,中国作为世界民族的一员,不应当拒斥共同价值的追求。当前人类全球共同体关于道德上的对与错、伦理上的是与非、科学上的真理与谬误、艺术上的美与丑、法律上的合法与非法(罪与非罪)等问题的探讨,离不开共同价值的奠基与支持。可以说,全球犯罪化是与奠基于共同价值的世界文化扣连在一起的,所以,应对犯罪全球化问题的治理,建立在上述共同价值的基础上。为此,中国应当根据现代文化发展需要,从自身文明及其文化传统的丰富思想资源中,提炼出适合现代社会的价值话语,参与全球共同价值的对话与建构,履行自身作为世界文明大国的道义责任,成为全球犯罪治理制度建设的主要担纲者。
第四,犯罪全球化已经对现代民族国家的刑事司法制度和实践产生挑战。现代刑事司法和犯罪学理论是建立在“威斯特伐利亚原则”的基础上的,尽管仍保有其知识有效性,但是,已经不能适应当前犯罪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可以说,现代中国社会的刑事司法制度和理论,完全是对西方国家(包括苏俄)的刑事司法理念与制度的移植和借鉴,从过去向苏俄学习到今天向英美德日等发达国家学习。因此,中国犯罪学和刑事法学目前仍局限于民族国家的理论框架,虽然已经关注到全球犯罪发展趋势,但是,基本的研究范式还没发生真正的转变。这必然制约中国有效应对当前迅猛发展的全球犯罪之制度治理能力。为此,中国有必要从根本上重构现有刑事司法与犯罪控制的理论图式。这种理论图式,应该是既体现中国传统文化“血脉”,又兼具现代文明气质;既体现中国文明思想,又包容共同价值;既切合中国社会发展需要,又能够为人类法律文明和世界和平做出贡献。[11]
第五,应对犯罪全球化问题,为中国深度参与全球治理提供了新的战略空间和机遇。首先,打击全球犯罪将重塑中国刑事司法治理的全球延伸能力。随着中国在全球的影响力和权威的增强,中国应对全球犯罪的国际责任和义务将相应增加,打击恐怖主义、海盗和其他跨国有组织犯罪,将成为中国积极参与全球犯罪治理的重要机遇。其次,积极推动国际刑事司法的全球实践为中国提升自身国家治理能力提供新的实践场域和战略空间。中国目前仍不是国际刑事法院的缔约国,但从应对全球犯罪风险的国际战略来看,未来中国应该积极推动国际刑事司法的全球治理,利用国际刑事司法的多边力量,以此应对英美刑事司法的全球霸权。
总结上述的挑战和机遇,笔者认为中国刑事司法治理及其刑事政策应该具有一种全球化的战略眼光,并需要结合中国刑事司法实践的经验和需要,对这种全球犯罪治理战略进行提炼,从而为未来中国提升国家治理能力及其全球延伸做好准备。[12]
参 考 文 献
[1] 戴维·赫尔德:《全球大变革——全球化时代的政治、经济与文化》,杨雪冬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2] Mark Findlay. Governing through Globalised Crime: Futures for International Criminal Justice. Cullompton: Willan Publishing,2008.
[3] Katja Franko Aas. Globalization and Crime.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Ltd,2013.
[4] Mark Findlay. Globalisation of Crime :Understanding Transitional Relationships in Contex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4.
[5] Anja P. Jakobi. Common Goods and Evils? The Formation of Global Crime Governanc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3.
[6] Assaf Moghadam. The Globalization of Matyrdom: Al Qaeda, Salafi Jihad and the Diffusion of Suicide Attacks. Baltimore: The Joha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2008.
[7] 瑪丽-克里斯蒂娜·迪皮伊-达侬:《金融犯罪——有组织犯罪怎样洗钱》,陈莉译, 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6.
[8] Rob White. Transnational Environmental Crime: Toward an Eco-global Criminology. New York:Routledge,2011.
[9] M. 谢里夫·巴西奥尼:《国际刑法导论》,赵秉志等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
[10] 埃辛·奥赫绪,戴维·奈尔肯:《比较法新论》,马剑银、鲁楠等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2.
[11] 高鸿钧:《法律全球化的理论与实践:挑战与机会》,载《求是学刊》2014年第3期.
[12] 张文龙:《刑事司法的全球治理——读〈通过全球化犯罪的治理:国际刑事司法的未来〉》,载《清华法治论衡》2015年第1期.
[责任编辑 李宏弢]
Abstract: Globalization of Crime manifests in different dimensions, which poses a challenge to political order and judicial system of national states. The main theoretical pattern of the study provides inspiration and revelation to the challenge but with some lacks and flaws. In the process to meet the challenge, China is faced with the challenge and chances. We should deepen the judicial reform, strengthen the innovational study of the management system, participate actively into the global systematic construction, meet effectively the challenge and dedicate to world peace and security.
Key words: globalization of crime, global crime management, China, challenge, to me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