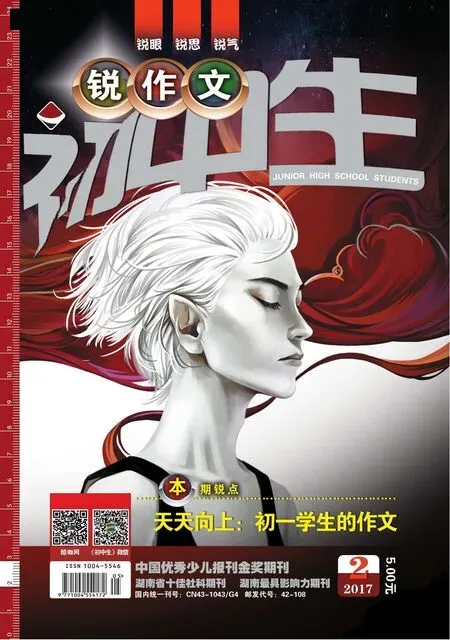对话李登建:好作品讲究匠心独运
文/孙永庆
对话李登建:好作品讲究匠心独运
文/孙永庆

责任编辑:吴新宇
编者按:李登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理事,山东省散文学会副会长,一级作家。有300余篇次散文作品被《散文选刊》《散文·海外版》《青年文摘》《读者》《中华文学选刊》《新中国60年文学大系·散文精选》《百年中国散文经典》《世界美文观止》等选刊、选本收录;《千年乡路》等十余篇散文入选部分省市高中语文必修教材、高考语文摹拟试卷和现代文阅读训练习题;出版散文集《黑蝴蝶》《平原的时间》《礼花为谁开放》、人物传记《乍启典传》《大地为鉴》《最后的乡贤——郭连贻传》等专著;荣获首届齐鲁文学奖、首届奎虚图书奖。下面是教师、作家孙永庆与李登建先生的精彩对谈。
孙永庆:李老师你好!你当年考入师范大学,毕业后当过高校写作教师,能简要谈谈你学语文的体会吗?
李登建:我在大学里读的是中文系,课程有古代汉语、现代汉语,中国古典文学、现代文学、当代文学和外国文学,还有文学理论、美学、写作概论等等,这些都属语文的范畴吧?我很喜欢它们。学好语文为我后来教写作课和从事文学创作打下了基础。如果没有这个基础,很难想象我会胜任自己的工作。
孙永庆:很多散文写的是一些身边的琐事,如朱自清的《背影》、杨绛的《老王》,还有你多次被选为中学语文现代文阅读题的《铁匠铺》。你能结合写作实践谈一下如何写好这类散文吗?
李登建:散文就是写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感、所思,身边琐事自然是重要的题材来源。这要求写作者具有敏锐的观察力,炼就一双善于从平凡的生活中发现美的眼睛。并不是所有的琐事都可入文,那些闪耀着美的光泽、饱含诗意的“琐事”才是我们要撷取的。另外,要写好这类散文,不能停留在琐事本身,必须善于以小见大,从中开掘出深意。比如我写《铁匠铺》,表面看是写一个铁匠世家一天的劳作,旨意却在于揭示底层人的命运,写他们的“苦命”很难改变,一代一代像惯性一般延续着。这样文章就有了深度。
孙永庆:你的散文给我感受最深的是观察细致。你是不假思索一挥而就,还是通过反复酝酿,才下笔如有神?
李登建:写散文,重要的是把内容写充实,把情感写饱满,把思想写深透。要做到这些,不细致观察、反复酝酿怎么能行呢?我不赞成走马观花、浮光掠影、草草下笔、一挥而就的做法,这样是写不出好散文的。
孙永庆:现在网络上有种说法:写文章不需要构思,不需要推敲,想怎么写就怎么写。这些观点也影响到了学生们,你能谈谈这个问题吗?
李登建:我认为这些观点是错误的。文章,特别是文学作品,本质上是一种艺术。而艺术讲究匠心独运,讲究奇妙,这就需要作者精心构思,费力布局。优秀作品思想和艺术含量都很高,作者提炼主题的过程、选择材料的过程、安排结构的过程、运用表现手法的过程,以及打磨文字的过程,都需绞尽脑汁、呕心沥血,没有哪一篇好作品是轻轻松松得来的。古人诗云,“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吟安一个字,捻断数茎须”,都是很好的例证。
孙永庆:作家王剑冰评论你的散文时说:“李登建善于根据内容的需要控制叙述的节奏,行文时疏时密,时快时慢,时张时弛,富有内在韵律。”学者季羡林也说过:“古代散文大家的文章中都有节奏,有韵律。细读中国古代优秀散文,甚至读英国的优秀散文,通篇灵气洋溢,清新俊逸,绝不干瘪,这就叫‘韵味’。”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李登建:叙述节奏是散文创作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美学问题。我们常说“文似看山不喜平”,这从内在形态来看,是说一篇文章从头到尾作者的思想感情要有波澜起伏、发展变化;从外在形态看,是说行文节奏要时疏时密,时快时慢。与主题关系密切的材料,思想感情需要充分表达的地方,要详写,展开写,浓墨重彩,“密不透风”;与主题关系不那么密切的材料,思想感情过渡的地方,则应略写,一笔带过,呈“疏可走马”之貌。详写,叙述速度就慢;略写,叙述速度就快。这样交替进行,行文就有了节奏,就有了起伏,整篇文章就会像一支交响曲,有低有高,有疾有徐,有引曲,有华章,才会产生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反之,如果不分主次,平均用力,像“直头布袋”上下一样“粗”,那文章就没有美感可言了。
孙永庆:你的散文《啊!平原》《站立的平原》,用心观察到植物们拥挤着、嬉闹着,任性地掀起排排绿浪,嗅到它们身上热烘烘的味儿,那种纯正的乡间气息。读你描绘平原的系列散文,我不禁想起钱锺书先生的一段话:“花红得发‘热’,山绿得发‘冷’;广度和音量忽然有了体积——‘瘦’,颜色和香气忽然都有了声息——‘闹’;鸟声竟熏了‘香’,风声竟染了‘绿’;白云‘学’流水声,绿阴‘生’寂静感;日色与风共‘香’,月光有籁可‘听’;燕语和‘剪’一样‘明利’,鸟语如‘丸’可以抛落。五官的感觉简直是有无相通,彼此相生。”这种“通感”的艺术表现手法,在你的散文中随处可见,并且运用得准确、巧妙。你是如何锤炼文章语言的?
李登建:2001年后,我集中笔墨写故乡梁邹平原。梁邹平原是我散文创作的母题,我这一时期的作品都放在梁邹平原的“框架”里,有些评论家把它们概括为“大平原系列”,称我是“大平原散文家”。我写平原上的树、草、庄稼、牛羊、土路、田埂、老河、古桥、荒坟、瓜棚、水车、泥塘,以及各种各样的色彩和声音,在这样的背景下表现农人的勤劳、善良、朴实、敦厚、愚昧、保守、狭隘、自私。我眼里的梁邹平原古老又年轻,博大而浑厚,喧闹又安详,神圣而庄严。我力图对她作全方位、多层次的展现,塑造一个立体的、丰富多彩的平原形象,创造一个属于我自己的艺术世界。我一次次在这块土地上行走,一遍遍轻轻抚摸她肌肤上的伤痕,深深俯下身倾听她的呼吸和脉动。我在文章中力图表现这种深切而复杂的感受,我也力求调动多种艺术手段,正面描写、侧面描写,细描、白描,实写、虚写,化虚为实、烘托反衬,化静为动、以动写静,借景抒情、托物言志,以及拟人、象征等等,其中通感也是我常用的一种。如你说的《啊!平原》一文,开头就写道:“洪亮、悠扬、温暖的钟声的音韵徐徐飘落之后……”再如写树叶“那绿里又添了一份绿,也可说融入了些许墨色,是那种分量很重的绿,那种凝聚了绿之魂的绿”,这里也用了通感。“通感”是把听觉、视觉、嗅觉、味觉和触觉通过联想沟通起来的一种手法,恰当地运用通感,可以拓宽描写的路子,增强表达效果。

锤炼语言必须舍得下功夫。我经常查词典,以确保用词准确。在准确的前提下,再力求生动。这更难,我常常为了寻找一个恰当、生动的词而失眠。
孙永庆:我想起《霏雪录》中一段:“前辈文章大家,为文不惜改窜。今之学力浅浅者反以不改为高。欧公每为文,既成必自窜易,至有不留初本一字者。其为文章,则书而粘之屋壁,出入观省。至尺牍单简亦必立稿,其精审如此。每一篇出,士大夫皆传写讽诵。唯睹其浑然天成,莫究斧凿之痕也。”你写文章也经常修改吗?
李登建:我非常注重文章的修改。有几句话这样说:“文章是改出来的”“文章不厌千回改”“文章越打磨越光亮”,这都是经验之谈。曹雪芹写《红楼梦》,“披阅十载,增删五次”;散文大师杨朔“一边写,一边改,改了又圈,圈了又改,反反复复,切磋琢磨,真比绣花还精细”。我写完初稿后,往往要改很多遍,直到改得一个字也动不得为止。我有的作品改动很大,个别时候几乎重写,多数时候是修改过程中增加内容,特别是补充一些细节,以使文章更饱满结实。有时也调整结构,使之更合理,更具匠心,当然也包括语言方面的加工润色。
修改文章最重要的还是对主题的深入思考,使思想更独到、更深刻。人对客观事物的认识是一步步深入的,要经过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过程。修改文章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这样一个过程,一遍遍地修改,才能一点点地接近、抵达事物的本质。这个过程可能伴随着更易材料,使材料更加典型化。主题在一篇文章中是“灵魂”,所以修改文章首先要重视这个灵魂的塑造,其他方面的修改也都是围绕着这个灵魂来进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