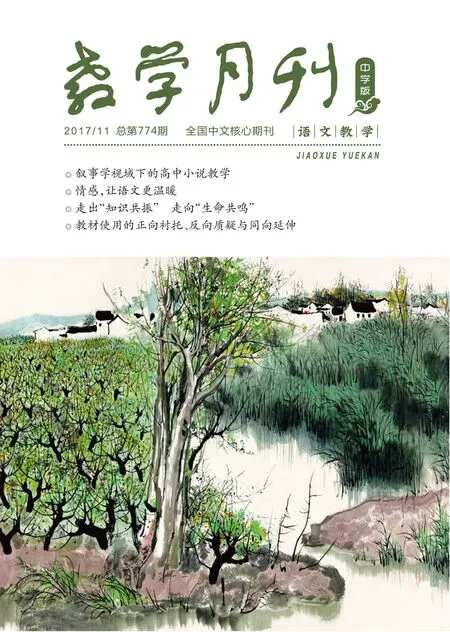《始得西山宴游记》的文化解读
王华琪
(浙江省杭州第二中学,浙江杭州 310053)
《始得西山宴游记》的文化解读
王华琪
(浙江省杭州第二中学,浙江杭州 310053)
《始得西山宴游记》是苏教版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语文(必修一)》“与造物者游”板块里的课文。题目里“始得”二字既可以理解为“开始得到”的实义,强调西山宴游的始发,又可理解为“才得以”的转化语义,凸显宴游来之不易,“始得有惊喜意,得而宴游,且有快足意,此扼题眼法也……”(浦起龙《古文眉诠》)。西山宴游是柳宗元一次极不平凡的经历,西山不仅接纳了柳宗元,抚平了他受伤的心灵,还给了柳宗元精神上的滋养,给了他前行的力量与勇气。在文中,西山是柳宗元的人格符号,身处困顿之中的他依凭西山认知自我、确认自我、升华自我。
一、寻找自我:人找山寄托
文章落笔于西山宴游的背景,一百来字,寥寥数语,概括了“始得”前的游历与感受。
起笔“自余为僇人,居是州,恒惴栗”。柳宗元为何称自己为“僇人”?为何“恒惴栗”?永贞革新失败后,柳宗元被贬永州,“立身一败,万事瓦裂,身残家破,为世大僇……”(《寄许京兆孟容书》),“纵逢恩赦,不在量移之限”(《旧唐书》),他在《答周君巢饵药久寿书》中写道:“宗元以罪大摈废,居小州。与囚徒为朋,行则若带索,处则若关桎梏,彳亍而无所趋,拳拘而不能肆。”虽已被贬谪到荒夷之地,仍随时有可能遭杀身之祸,心灵上荫翳笼罩,惊惧万分,“窜逐宦湘浦,摇心剧悬旌。始惊陷世议,终欲逃天刑”(《游石角过小岭至长乌村》),所以自己画地为牢,上枷囚禁,寡言少语,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以保性命。
焦恐压抑的日子里,柳宗元自我忘却,自我迷失,唯有山水可聊以打发日子,故而“施施而行,漫漫而游”,无目的,无着落,无依凭。“上高山,入深林,穷回溪,幽泉怪石,无远不到”,游山玩水,搜奇览胜,在自然山水中寻找心灵的慰藉,然后,“倾壶而醉”,卧而梦,“意有所极,梦亦同趣”,“觉而起,起而归”。以游山玩水度时日,以酒浇胸中之块垒,唯求麻醉自我,忘却忧郁恐惧。
处于迷茫困厄状态中的柳宗元并未泯灭自我,酒醉心里明,饱览了奇山异水,“以为凡是州之山水有异态者,皆我有也”,寻异态山水,说明内心不屈于常,不拘于俗,只是时者,势也,只能暂时向现实低头,个性被压抑着。
“众山”虽有异态,然终不得我意,这一段文字为西山的出现作了很好的铺垫。“而未始知西山之怪特”,“而”字急转而下,对“异态”尚不认可,别说“常态”,“异态”和“怪特”又不在一个层面,柳宗元寻寻觅觅的西山就在于“怪特”二字,“未始”二字,颇有“众里寻他千百度”之感。
二、发现自我:人与山冥合
北宋王安石在《游褒禅山记》里有言:“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险远,而人之所罕至焉。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柳宗元认为“文者以明道”,“道之者,及乎物而已”(《报崔黯秀才书》),“庄周言天曰自然,吾取之”(《天爵论》),崇法天然的柳宗元当然要到自然山水中取道。一切都是机缘巧合,有了一个特定的位置(法华西亭),有了一个特定的视角(从西望西,从高望高),要注意的是,“始指异之”,又是“始”字,相见恨晚啊,“异”之处就在于其“怪特”。柳宗元的内心突然被触动,然后欣喜若狂,“过湘江,缘染溪,斫榛莽,焚茅茷,穷山之高而止”,一系列的动作,“过”“缘”“斫”“焚”“穷”,攀缘的过程其实很艰辛,却被一笔带过,从短促而跳跃的语句中可读出柳宗元内心的激动,他急不可待地登西山,艰难险阻毫不畏惧。
接下来是具体写西山之美和宴游的感受。山之“怪特”主要在其高,一般写山之高,都是居低处仰视,柳宗元则别出其新,采用居高俯视,“凡数州之土壤,皆在衽席之下”。山峦起伏,地势凹凸,“岈然”之处似蚁垤,“洼然”之处如洞穴,众山渺小卑微,状如蝼蚁,反衬西山之嶙拔;视线放远,千里之地如在尺寸之间,“攒蹙累积”,重叠压缩,尽收眼底,因山高峻,方有视野宽广;视线拉高,“萦青缭白,外与天际,四望如一”,更是直写山之高,视之远,以此烘托西山之嵯峨雄峙。细细品读,有眼见有想象,有实叙有夸饰,目游与神游结合,写实与写意并用。从西山的特立,柳宗元看到了自己的身影,西山唤醒了他的自我意识,让他寻到了理想人格的表征。
“怪特”的西山长期不被人了解,却永葆高耸特立,个性张扬,桀骜不驯。对应自己,虽谪居永州,仍不改初心,不媚权贵,不与世俗为伍。柳宗元寻山识山的过程就是寻找和认识一个真我的过程,山与人的契合,遂产生了惺惺相惜之情,此时,山即人,人即山。那个经历宦海沉浮的柳宗元面对奇崛的西山产生生命顿悟和价值体认。
三、认识自我:人与万物融合
“以我观物,故物皆着我之色彩。”(王国维《人间词话》)柳宗元扩大了眼中的“物”,由西山延展到造化万物,“悠悠乎与颢气俱,而莫得其涯。洋洋乎与造物者游,而不知其所穷”。西山砥砺了他的气节,天地万物充沛了他的“颢气”,所谓“颢气”者,乃“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孟子·公孙丑上》),原来矮化的“小我”吸纳天地之间的正道直行、至大至刚的浩然之气后成了高拔的“大我”,我与天地融合一体,与造化同游,悠悠无际,漫漫无涯,精神高度升华。
人与山冥合,再升华到人与天地融合,使柳宗元“引觞满酌,颓然就醉”,点出标题里的“宴游”二字。一个“就”字值得细细玩味,这是心情释然后的酣然就醉,与之前“倾壶而醉”那样的主动买醉、自我麻痹不一样。“不知日之入”,直到暮色苍然、四合,“无所见而犹不欲归”,这也与之前游众山的“觉而起,起而归”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一个实体的“西山”上升到形而上的“西山”,成为柳宗元精神的化身,让他感到了“心凝形释,与万化冥合”,这既是“以物观物”之境,也是“以我观我”之境,列子曰:“心凝形释,骨肉都融,不觉形之所依,足之所履。犹木叶干壳,意不知风乘我耶?我乘风耶?”(《列子·黄帝第二》)“万化”蕴含了道家委运乘化的思想,“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得意忘言,物我皆忘,俯视凡尘纷扰、纠葛,超越世间的穷达、荣辱,万虑顿释,形骸俱销,成为一个自由的人,之前的不安、恐惧和怨怼自然就消弭了,内心归于平静和安宁。
西山是柳宗元审美主体的对象化,与其说是西山拯救了柳宗元,不如说是柳宗元完成了自我的救赎,这是禅宗里的生命顿悟。柳宗元和一个个杰出的中国文人一样,身处困厄混沌之境时总能在儒释道交融的哲理天空中发现几点星辉、一缕曙光,完成生命的突围。
最后,柳宗元感慨“然后知吾向之未始游,游于是乎始”,再次强调“始”,之前的“施施而行,漫漫而游”只是一种消遣行为,是形在游,此次披荆斩棘登西山,是神在游,故而心旷神怡,如醉如狂。
《始得西山宴游记》位居“永州八记”之首,也是山水游记的典范。章士钊先生有言:“子厚永州山水之游,应分作两个阶段,而以西山之得为枢纽。”(《柳文指要》)游西山成了柳宗元永州十年的一个转折点,他在寻找自我、发现自我、认识自我中完成了精神的升华和生命的蜕变。
(责任编辑:巫作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