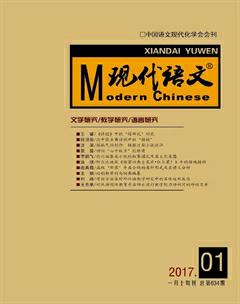从认知范畴谈《诗经》中植物词汇的翻译
董佩芸+李于丹
摘 要:《诗经》中的名物具有博大精深的内容及意义,但是在《诗经》的研究中,名物的内容尚且存在许多未解之处,在《诗经》的翻译研究中,名物的翻译也有不少的困难和疑惑。本文将根据认知范畴的概念,以诗经中的植物词汇的翻译为例,从名物在诗歌中体现的属性和具体性质出发,判断如何在翻译中通过确定词汇的范畴层次,而尽量达到提高翻译质量的目的。
关键词:《诗经》 范畴化 植物
一、引言
《诗经》中的植物词汇意义丰富,它们不仅直接体现了中国先民当时的生活状况,也从各个侧面反映了中国古代时期的宗教,政治和文化现实。这些植物词汇的意义随着时间逝去经历了流变,内容尚且存在不少疑惑之处。而在翻译过程中,意义在汉英语言系统转换中存在不对等性。因此《诗经》中植物的翻译给译者带来了不小的困难,本文從范畴化概念出发,通过确定植物词汇的范畴化层次和属性,使用合适的翻译方法来尽可能的达到对等的效果。
二、《诗经》翻译中认知范畴的概念
认知语言学认为诗歌的意象是一种以人的认知经验为基础的思维方式。人们对各种客观事物进行归类和定位,是一个心理认知过程,事物的客观属性在人的主观认知中获得定位,认知范畴是范畴化的结果。而意义的不确定性,也始于范畴化,在认知范畴化理论中,对于个体范畴化的依据有如下说明:个体范畴化的依据并非其基本特征,而是其属性。属性是事物性质的心理体现,和认知及与现实的互动相关,而前者是指事物固有的本质属性,与认知的主体无关,是独立的客观存在。范畴化是认知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中发挥着巨大作用。
翻译表面上是两种语言之间表层语符的转换,实际上是两套认知范畴之间的移植。认知范畴并不是随意的人为划分。,除了客观事物的自身属性外,影响因素还有人的经验,而经验又受到环境影响两套不同的语言符号系统中,背后的认知范畴必然存在差异。认知范畴具有层级性,可以分为下属范畴,上位范畴和基本范畴,基本范畴兼有完整的感知完形区别特征和内部相似性。
《诗经》中出现的名物种类繁多,出现了大量的草木鸟兽名称,这些动植物,或赋,或比,或兴,有的体现了先民的审美,有的寄托了特定的情感,有的承载了深远的隐喻,名称的意义有多样丰富的层次,只是各有侧重。在《诗经》的中文研究中,名物研究内容博大精深,尚有很多未解之处,这无疑给英文翻译带来了很大困难,本文将根据认知范畴的概念,以诗经中的植物词汇的翻译为例,从名物在诗歌中体现的属性和具体性质出发,判断如何在翻译中通过确定词汇的范畴层次,而尽量达到提高翻译质量的目的。
三、《诗经》中植物词汇翻译的范畴化
诗句精简,却被赋予了深远的含义和丰富的意象,诗句也最容易误译,甚至可能产生与原句相反的含义。尤其在翻译《诗经》这样的文学作品时,更要注意结合全文的意义分析,绝不能孤立的逐字逐句的阐释。了解诗歌的时代背景,掌握诗句的精神实质,简明扼要地力求再现原作,只有这样辩证文字,反复推敲,才能感染读者,达到对等的效果。
既然从认知角度上说,个体范畴化的依据——属性,是事物性质的心理体现。那么在诗歌语言中,同一个词汇在不同的诗篇中受到诗歌情感的影响,具有或强化或弱化的含义,在不同的认知主体心中也会形成不同的折射,体现其多层次的属性。诗人总是把自己的心气衷曲浓缩在典型的生活画卷中,这就是涌溢深微哲理的诗的意境。景与情交融才能成诗,因此本文从语境,意象以及文化三个方面,来分析植物词汇范畴化的过程。
1.语境
认知语境是认知主体对语言使用的有关知识,是与语言使用有关的,已经概念化或图式化了的知识结构状态。在使用语言时,认知语境对语言的不完整进行补足,语言使用者自觉地根据认知语境激活并选择相关信息。在利用认知语境进行推理的过程中,语言使用者获取语言中蕴含的隐形内容,从而达到正确的理解。
《诗经》中出现的一些植物,之所以能够入诗,可能和当时先民的生活息息相关,但现今看来却是一个不能确知的名称。但是根据诗歌语境和注释对植物情态的补足,读者对于该个体有一定的想象。此时,若译者选词时能重现此植物的情态,营造出一样的情境,符合读者的想象,便是可取的译法。下面以“荇菜”译法为例。
《周南·关雎》“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参差荇菜,左右流之。……参差荇菜,左右采之。……参差荇菜,左右芼之。”参差在现代汉语中有长短高低大小不齐的意思,而在古代汉语中蕴含中多姿的含义,多姿的荇菜飘飘摇摇,春意盎然,采荇的姑娘青春活力,引绵长思念。在各个英译版本中,汪榕培译为water grass,杨宪益译为water plants,他们的译法是采用了基本范畴概念“水草”来取代原文的下属范畴概念“荇菜”,却并未体现出荇菜随波逐流在水中招摇的情态。许渊冲译为cresses(水芹),里雅各译为duckweed,意为浮萍,他们都采取了下属范畴概念取代荇菜的译法,可能由于英文中并没有荇菜这个概念,译者以其形态相似的概念代替,在读者心中营造了相似的情境。
2.意象
意象是一般是一种具体的实物情感寄托,诗人用这种物象来抒发情感,寄托其情愫。在《诗经》中也存在一些意象,虽然也被用来抒发诗人的情感,但是更重要的是与诗旨的解读有密切关系,或者烘托氛围,或者与诗歌的主要内容有关键联系。在认知语言学的视角中,诗歌的意象不再仅限于解释为简单的情景交融,而被认为是种思维方式的体现。在这些意象的翻译中,译者必须注意突出它具体体现出的某些功用及属性,从而确定具体词汇选择的范畴层次。
《诗经》中多首诗写到男女交往以植物相赠,比如《邪风.静女》中的彤管,《郑风.溱箱》中的苟药,《陈风.东门之扮》中的握椒。虽然有的植物究竟为何物不确知,但是这些相赠之物多为表达男女之情,比如彤管,"盖相赠以结殷勤之意耳”,《溱洧》之芍药是士与女相与戏谑,“结恩情之厚”的信物。《诗经》中的一些植物,有其特定的隐喻功能,且很多与女性有关,比如“椒”,其果实累累,正是多子的象征,所以用它比喻女子多子,这在《唐风.椒聊》中表现得很明显。多位译者都将椒聊翻译为pepper plant,椒为何物的信息很明确,且《椒聊》全诗都是客观描写椒聊,以达到比兴目的,所以在译法上没什么分歧。而对于握椒的译法,则人各有异,理雅各和汪榕培还是译为pepper plant,而许渊冲并没有译出椒的客观信息,而是译成token of love。很明显,许在此采用的是上位层次的范畴,并不直接译为实物,而是结合椒所代表的男女关系,将此处的画面情态清晰地表达出来。
3.文化
语言和文化相互依存,语言离不开文化,而语言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是文化的表现形式,也是文化的重要部分。两个国家或民族的相互沟通,不仅在于对语言的理解,更重要的是背后文化意蕴的理解。作为中国诗歌的萌芽,《诗经》的一些意象负载着厚重的中国文化,而这种文化内涵很大程度上不是来自其客观特点,而是在历史的使用中人们对其的感受点滴化成的文化心理的凝结,这种属性有鲜明的民族文化特色。在这类词汇的翻译中,更需小心,如果英语中不含此种意象的概念,不可随意置换,即使英语中有客观概念上完全对等的词语,文化意义也难免出现缺省、错误的现象。
《诗经·采薇》描写战后士兵返乡的名句是:“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余冠英的语体译文是:“想起我离家时光,杨柳啊轻轻飘荡。如今我走向家乡,大雪花纷纷扬扬。这是诗经里著名的诗句,它就像一幅画,把出征边塞将士们的心情,描画得淋漓尽致,使读者身临其境。将士们出征的经历,都尽在季节变化,意象倒转中了。“杨柳”一语重点在柳。柳,已成为古人今人某些特定情感的信息载体。汉语语音中“柳”“留”谐音,让人自然联想到柳丝与留思间的内在联系,使折柳赠别之俗带来的。杨柳的名称、形态驻扎在中国的读者心中,而其唤起的送别的意义更直接使读者体会到离别的意境,而这点,西方读者是无法直接理解的。
因此许渊冲将前两句译为When I left here,willow shed tear.译文把抽象的离情化为具体的流泪,这就是把杨柳拟人化了。但杨柳是没有眼泪的,所以英文的眼泪用了单数,表示这不是物质的泪,而是悲哀的象征.。这种将事物深化具体化的方法,未尝不是一个好的译法。
四、结语
综上,《诗经》中一些名物词汇的确切意义难以确定或者难以在英语中找出完全对等的词汇,认知范畴的完全对等移植难以实现。即便以同一层级范畴的词汇翻译,也可能只是处于相近的义域,会存在各自不同的属性,原语读者与译语读者读到原语词汇和译语词汇无法形成完全相同的心理感受。所以在翻译中,译者可以利用认知范畴的理论,在上位范畴词,下位范畴词和基本范畴词中取可取的译法,在翻译的词汇取舍中,考虑诗句的情景再现,旨意传达以及文化蕴含,尽量达到对等的效果。
参考文献:
[1]郭锡良.古代汉语[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2]李玉良.诗经英译研究[M].济南:齐鲁书社,2007.
[3]孙作云.孙作云文集第二卷《诗经》研究[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3.
[4]《外国語言文学》编辑部编.语用学研究:文化、认知与应用[M].福建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
[5]汪榕培,任秀桦.The Book of Poetry[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
[6]王建国.关联理论与翻译研究[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