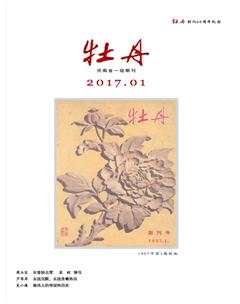萌
辛小龙
几经周折,终于争取到和父亲一同上山砍柴的机会,兴奋的我久久不能入睡。从未走进过大山的我,就是在那次邂逅樱子的。
母亲三更做饭,我们四更启程。幽静的夜,银白色的月光,浸染着广袤无垠的大地,蜿蜒流淌的河流以及山边茂密的杨树林,惬意极了。入秋的夜晚,显得有些清冷,凉意袭身。
五更天,黎明前的黑暗转瞬即逝,十多里的路程很快被我们抛在身后。天蒙蒙发亮,四周的一切清清楚楚地显现出来。隔河的沙岭村,传来牛的叫声和公鸡拉长了的啼鸣,房屋的上空升起了袅袅炊烟。
我跟着父亲到河北岸去借斧子。借给我们斧子的是一个身材高挑四肢颀长的少女,她楚楚动人的身姿像雨后青山般清纯、靓丽。她齐肩的两个短辫上扎着红头绳,轮廓分明的脸盘犹如一轮新月,清澈明净的眼神后显露出些许的忧郁。她上身着一件褪了色的浅蓝上衣,虽然上了补丁,但那几块补丁好像是着意镶嵌的装饰品;下身着一条卡其色裤子,一条红色的薄围巾系在她那长长的脖颈上。
我被这一切惊呆了。
“松伯,这位是……”她打量着我问。
“这是我的老二。”父亲答道。
她指着西山说:“松伯,别远去,清水凹那儿有堆干柴足够您的。”我和她爱怜地打量着对方,似曾相识……
她一走,我连忙问父亲:“她是谁?”
“她呀!叫樱子,早年间我和她父亲在一起放过木筏,后来她的父母因病相继去世,她一直跟爷爷相依为命!”我一度陷入深思。
清水凹那块被新开垦的处女地上,我笨拙地把干柴上的碎枝末叶砍掉,父亲则把它们捆成捆背下山去。在我脑海里一直挥之不去的是樱子的倩影,不知道为什么,我突然爱上了这里的山山水水和这里的一草一木。一直处在这美好的、令人陶醉的梦幻般的遐想里……
啊——啊——该死的两只乌鸦的干嚎,令人毛骨悚然。天哪!听到乌鸦叫是要倒霉的,这该死的东西!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当我试图把一根树杈劈开时,那些个模糊不清的意识,竟驱使我把那一斧子重重地砍在了右脚腰上,这下惨了,鲜血从那大嘴似的伤口里泉涌般地冒了出来,我彻底懵了。事不宜迟,我迅速断了一根葛条,把它紧紧地捆绑在脚腰上。
装好车后,父亲看了看将要西坠如血的残阳,“快!吃了它好赶路!”我接过父亲塞给我的难以下咽的饼馍,我试图掩饰这一切,但还是被发现了。
“你的脚怎么了?”父亲吃惊地问。“没事!”“没事?眼看那血泥都成块了还说没事!”生气的父亲随手摔掉啃过两口的饼馍,“快!把柴禾掀了,拉你回去!”说着要解绳子。
在那个温饱都成问题的年代,我非常清楚这一车柴禾意味着什么,它是我上中学的哥哥一星期的费用啊!我顿感绝望,“你要卸了这车柴禾,我就碰死在这里!”父亲看着两眼模糊的我,无可奈何地顺从了我。
经过沙岭村,父亲去还斧子,致使樱子一路小跑赶了过来,“快给我看看!”我两眼直愣愣地看着她心急火燎的样子。她迅速地解开我捆绑着的右脚,麻利地替我脱掉袜子,果断地擦去伤口周边的血泥,把白药粉撒在伤口上,并用布条把脚包扎得严严实实的。
我俩的目光不时地交织在一起,一种朦朦胧胧的感情已经悄悄地潜入到我们的心田。这种莫名的感情,让人感觉新鲜、激动。我心跳加剧,我悲愁的心也被她柔和的眼神给揉搓得粉碎。
此时,我感到天是那样的湛蓝、云是那样的洁白、阳光也是那样的和煦温柔。我陶醉在无比幸福的漩涡里,难以自拔。
“好了!千万记住,别湿水。”说罢她含情脉脉地盯着我,我不知道她心里泛起的是怎樣的涟漪。
“你——还会来吗?”她悄悄问我。“会的!”我爽快地答应她。
“我——等你!”她的脸红的像个苹果。
“一言为定!”我不假思索地回答。我们走了,我用她带给我的竹子做拐杖,一步三回头地走了!樱子的身影渐渐地模糊起来,她高举着的红围巾,不停地摆动在夕阳西下的余晖里……
岁月蹉跎。那以后,二老再也没有允许我登山半步。在随后的时光里,我上学、参加工作、娶妻生子。我曾跨越过崎岖不平的沟沟坎坎,也曾经历过泥泞难走的羊肠小道,沐浴过春风拂面的和煦阳光。但那条红色的围巾永远隐隐约约地飘动在我的脑海里,那几块精美的补丁和那双清澈深邃的眼睛,永远刀刻斧凿在我心灵碑石的记忆里。时至今日,我羞于面对昔日的激情和承诺。
那年我十五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