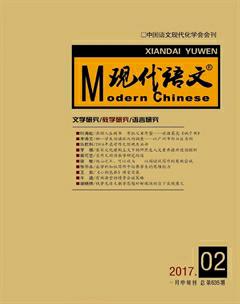大学语文审美教育现状
人文社会科学教学与自然科学教学的最大区别是其带有鲜明的审美教育功能,而只有充分发挥其审美教育作用,才能真正体现人文学科的教育价值。所谓审美教育即美育,王国维在《论教育综旨》中说:“完全之人物不可不备真善美之三德,欲达此理想,于是教育之事起,教育之事亦分三部:智育、德育、美育是也。”美育與德育、智育在塑造“完整的人”方面有不可忽视的作用,三者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可以互相补充,互相促进,却不可以互相代替。审美教育是通过文学艺术和其他审美活动形态净化和升华人的情感意绪,人格襟抱,并与德育、智育、体育结合起来,去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或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大学语文作为高等院校的一个人文学科分支,其审美教育功用是不容忽视的。大学语文教学中之所以要渗透这一理念,是由大学语文学科的根本目的(实现大学生全面发展的需要)决定的,也是大学生语文教育对象、内在特性以及教学过程规律特点的客观要求。
作为审美教育载体的大学语文教材自然成为教学过程的重要一环,如何在教材的编选和使用中充分反映和实现审美教育功能,是一个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国内的大学语文教材近年已出版多部,各有特色和优点,本文选择国内三部教材作为比较的对象,主要就这三部教材所选与审美教学有关的选文来看教材如何反映审美、如何看待审美教育在大语中的作用,并指出当前大语教学中审美教育的相关问题。这三部教材分别是朱万曙主编的、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大学语文》(第二版)、由徐中玉、齐森华主编的、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大学语文》(第九版)和由丁帆、朱晓进、徐兴无主编的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的《大学语文》(第三版)。我们分别称为“朱版”、“徐版”和“丁版”。
一、格局之异:“小美”与“大美”
这三部教材在编写上有各自的特色,就“审美”功能在其中的体现而言,可概括为“小美”与“大美”,即审美的对象是小格局中的美,还是更大格局的美。所谓“小格局”中的美则是把审美设定在某个点,如文学艺术之美等,是“小美”。“大格局”中的美是指各个层面的美,如生活自然之美、人性之美、文学艺术之美、语言之美等等,是“大美”。
“小美”之“朱版”:
朱万曙编的《大学语文》教材专门开辟了“文学审美”版块,主要内容包括古代诗歌、古代词曲、古代辞赋、古代散文、古代戏曲、古代小说、现当代诗歌和现当代散文等八个部分。可见,这一教材中把“审美”专设一章,并定性为“文学审美”,即审美的是“文学”所散发的美。载体是古今文学作品,其鲜明的特色是通过不同文体所展现的文学艺术之美,即诗歌之美、词曲之美、辞赋之美、散文之美等等,让学生接受美的熏陶。
“大美”之“徐版、丁版”:
“徐版、丁版”的大学语文教材在编选时都未专设审美这一栏,而是通过不同的专题渗透审美教育这一功能。徐中玉等主编的《大学语文》在编写时,以人文精神和品德素养的培养为基本基调,在编目安排上并未专设一块审美相关的版块,但在相关的选文上其实暗合了审美素养的培养,如第八单元的“故园情深”版块,选编了《江南的春景、梦回故园》等,第九单元“礼赞爱情”版块中的《蒹葭》等,第十一单元的“亲和自然”版块中的《春江花月夜》、《陶然亭的雪》等,第十二单元“诗意人生”中的《饮酒、慢慢走欣赏啊》等篇目。可见,该教材所展现的审美是多维度的,即涉及到情感之美、自然之美、生命之美和人生之美,丰富而有层次。
丁帆等编著的《大学语文》以“人文性、审美性、工具性、趣味性和新经典”为原则来编写教材,所选篇目涵括“人文情感、人文素养和人文理想”三大部分,该教材在审美教育上除了专门设置单元来引导学生认识美、理解美、发现美和欣赏美等,如通过“美的历程”、“文心诗品”这两个独立单元的篇目进行引导,还把相关呈现美的文理或美的情感文章也作为对审美培养的一部分,如“通古今之变”中的《大同》中孔子对人类社会理想的宏大叙述,“我的信仰”中的《西铭》充满热情的道德自白、《六祖坛经》通白透彻的智慧启示、侯仁之《历史上的北京城》对历史的娓娓叙事、“天工开物”中的《我们宇宙的图像》对科学问题的主动阐发等。虽然丁版也设置了单独的单元来进行审美教育,但与朱版不同的是,其并未按照传统的文体或者文学史的脉络来编选作品,而是通过不同审美功能的版块进行设计,并且进行了分化,如“美的历程”有传统的文学作品如《世说新语》,有关于书法的,如林语堂的《中国书法》,还有关于建筑的,如熊秉明的《佛像和我们》等。而“文心诗品”则主要选编中国古代文学作品,并且以诗歌为主,仅有一篇现代的废名的《竹林的故事》和一篇日本作家东山魁夷的《听泉》。比较三部教材在审美功能上的凸显,可见,朱版是最为突出的,丁版则次之,徐版的则比较隐晦。从审美教育本身来说,“大美”则是应该提倡的,因为美的欣赏和创造是多层次、多维度的,而“小美”则显得相对局促。但从教材编写来说,“小美”也有其突出之处,即在学生接受文学熏陶之时,有意识地从审美角度来学习。同时我们注意到,朱版在审美上虽然注重文学之美,但其实在其他版块的选材上也有“美”可言,如“第一编”的“汉语言文字”版块中其实有语言之美,如王力的《略论语言形式美》即为语言美的重要表现。“第三编”中的中国人生活中的相关作品其实也有生活之美。可见,朱版教材虽凸显“小美”,但也有“大美”隐于其中。
二、格调之别:“沉郁”和“明快”
审美是需要注入情感的,在作品中也往往有不同的情感体现,我们把审美的情感概括为“沉郁”和“明快”。沉郁是指其作品思想内容的博大精深,题材的严肃,感情的深沉、深挚。这本来是对苏轼诗风的一种评价,我们借用这一术语来定性作品本身所体现的审美情愫。明快则是指不含蓄、清晰而畅快,在作品上的表现即感情表达的外露和明晰。从这三个版本中对审美素材的格调上来说,朱版中沉郁为主,徐版则是明快为主,而丁版则是沉郁和明快兼有。朱版在文学审美版块以文学史的视角切入,所选作品按文体进行划分,即古代诗歌、辞赋、散文、小说、现代诗歌、散文等。我们反观整个版块的作品基调,感情深沉之作较多,如诗歌篇中《嫦娥》《圆圆曲》词曲中的《临江仙》《永遇乐》、辞赋中的《长门赋》《别赋》、散文中的《自为墓志铭》《穷鬼传》等等。虽然有的作品本身在文字表达上往往鲜活有趣,但在情感上则偏向于深沉和严肃。以《嫦娥》为例,作者李商隐通过塑造嫦娥这一艺术形象,表现了嫦娥孤独、寂寞的心情,整首诗朦胧而含蓄,有一种凄凉之美,整首诗在表达基本情感的同时,渲染了一种凄美的基调,让读者有种在广寒宫中孤冷而无奈之感。徐版在审美情感上的明快格调从其版块标题上即可感知,如“礼赞爱情”、“关爱生命”、“亲和自然”和“诗意人生”,其中的“礼赞、关爱、亲和与诗意”都反映出作品本身感情明快的基调。当然这几个版块中的所选篇目有的与朱版是相同的,如有《饮酒》等,但这不影响整个版块的基调。以《饮酒》为例,作者陶渊明描摹了诗人弃官归隐田园后的悠然自得的心情,体现出陶渊明决心摈弃浑浊的世俗功名后归真返璞,陶醉在自然界中,乃至步入得意而忘言境界的人生态度和和生命体验。整首诗清新明快,犹如清风扑面,让人微醉而又心神涤荡。丁版所选材料是沉郁与明快兼有。“美的历程”以明快为主,如《丹青引》《慢慢走,欣赏啊!》等,如《慢慢走,欣赏啊!》一文着重讨论人生的艺术化这一主题,但通过一个生活趣例的引导,很自然地把艺术与人生的关系彰显了出来,于无形中潜移默化着读者的感知,牵引着读者的感官慢慢前行,慢慢欣赏和品位。
而“文心诗品”则以沉郁为主,如《秋兴八首》《破阵子》《赤壁赋》等。《秋兴八首》是杜甫的重要代表作,彰显了作者忧国忧民之心,将时代苦难,羁旅之感,故园之思,君国之慨,杂然其中,融铸了夔州萧条的秋色,清凄的秋声,暮年多病的苦况,关心国家命运的深情,悲壮苍凉,意境深闳。这种沉郁风格与社会现实紧密结合的作品,犹能激发学生的思考,让学生在更为深沉的意境中树立其肃穆的历史感和现实感。审美作品的格调在教材编选时可能并不会有意识地考虑到这一点,因为无论是沉郁格调还是明快格调,都是一种审美情感的体验。但从培养学生心态和健全的人格的角度看,沉郁的格调可以让学生沉思、求真,明快的格调则让学生能够更加自由地求善、尚美。因此,在编选审美作品时可以在格调上有意识的进行设置,并与“大美”相结合,相信在大学语文的审美教育上会有新的气象。
三、经典之外:“大家”与“小家”
审美作品的编选当以有着丰富审美能力和体验的大家作品为首选,即为经典之作。尹钟宏(2007)指出,大学语文教学可以借鉴赫钦斯“名著阅读”运动的构思及其践履,以“文学经典教育”为中心,让学生通过学习这门课程,摸索到通向古今中外“文学经典”的一条道路,在那里和人类最优秀的心灵进行对话。诚然,经典或名著对于审美教育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但审美体验往往又不局限于某个大家或者经典作品,往往在不奇之处见奇,所谓经典之外有大家也。因此,大家往往有小作,小家往往也有大作,但这并不影响对美的鉴赏,只要能有美的体验、美的创造即可。而这在三部教材的编选中比较突出的体现。朱版教材的审美作品中,大家中的小作或小家的作品较多,所选作品并不常见,或者说并不入一般文学经典的“法眼”。如屈原的《鬼城》、李白的《长干行》、吴伟业的《圆圆曲》、笵康的《酒》、萧绎的《采莲赋》、食指的《相信未来》等等。但这些作品并不缺乏美感,读起来也令人陶醉或深思。朱版所选作品中从文学史跨度上来说,是选了非突出文学现象时期的经典,比如文学史上诗歌是盛唐的代名词,而清代的诗歌则不大为人注意,而朱版所选清代诗歌作品《圆圆曲》则是清诗中享有最高声誉的七言歌行,因此其作品所选可谓“非经典时代”的经典。而徐版和丁版在编选作品时,经典之作占绝大部分,但也不拒一些别有风味的小作,如丁版“美的历程”版块中所选的陈从周之《说园》,东山魁夷的《听泉》等,都是溢美之作。以陈从周之《说园》为例,作者是中国近现代作家,作品的内容则是关于建筑美学的,对造园理论、立意、组景、动观、静观、叠山理水、建筑栽植等诸方面皆有独到精辟之见解,于小处见大趣。虽其文学地位在正统的文学史上未必是大家,但其关于建筑美学上面的审美情趣等见解则犹可窥其大家风度。当然,并不是说大学语文教材编选时不注重经典,但从审美维度来说,美是“大家”的,也是多元的,所以可以不分大家和小家,只有大美或小美,或者沉郁与明快也。本文对三部教材所选有关审美作品的比较,主要注重其在审美情感层次、内容等方面的不同,并不在說明何者为上,何者为下,而是意在说明三种教材如何侧重,旨趣如何等。当然,如果从教材的好学、好用上来看,则也当各有千秋,这则不在本文的讨论之内,而是有赖于实践教学的反馈和检验。
基金项目:安徽三联学院院级人文社科研究项目“萧子良研究—以文学为中心”(2014S027)
参考文献:
[1]刘晓文、唐振勇.大学语文教学中的审美教育[J].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4).
[2]裴惠云.论大学语文教学中实施审美教育的途径[J].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5,(6).
[3]苏金萍.审美属性:关乎大学语文教学盛衰的一个维度[J].内蒙古电大学刊,2012,(6).
[4]孙文铸.谈《大学语文》的审美教育作用[J].东疆学刊(哲社版),1988,(3).
[5]谢萍.谈大学语文的审美教育[J].成都大学学报,1999,(3).
[6]王国维.论教育之宗旨[J].教育世界,1906,(56).
[7]尹钟宏、王建.论大学语文的审美教育功能[J].当代教育论坛:学科教育研究,2007,(7).
(梁学翠 安徽三联学院 2306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