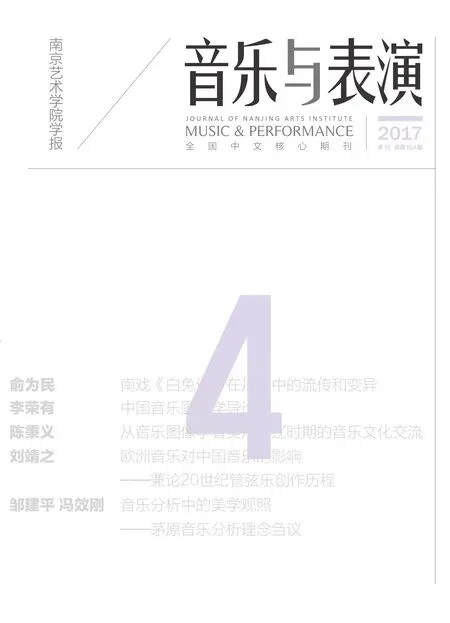土家族图腾与土家族土司音乐互文性阐释①
熊晓辉(湖南科技大学 艺术学院,湖南 湘潭 411201)
土家族至今仍然流传着在远古时期就有的“廪君”传说,他们称“廪君”为自己先祖,死后魂魄化成白虎,祭祀时需要用人来做牺牲。关于“廪君”的传说曲折而神奇,《后汉书·南蛮西南夷传》《世本》《晋书》《水经注》《蛮书》《通典》《长阳县志》等一些史籍都有记载,它艺术地反映了土家族先民巴人的起源、迁徙及所经历的漫长土司统治的历史。我们认为,土家族“廪君”的传说是以灵魂不灭观念为基础,把图腾观念的发生看成是灵魂转移所致。土家族以白虎为图腾,于是保留了白虎与人能够相互转化的神话。从图腾的起源来看,在图腾观念发生的初期,图腾的含义主要还是人的本身,人就是本民族的图腾,它同时也是当事人的另一种存在。其实,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图腾,也就是自己的另一种生存方式,此时,人与图腾可以相互转化,这种转化他们自己在幻梦中也曾看见过。随着图腾文化的演变,图腾的意义开始增加新的内容,开始具有艺术的特质。我们可以看出,土家族的图腾神话慢慢渗透到一些音乐活动中,形成了各种形式的艺术情节。如巴务相化为虎钮錞于,巫师化为梯玛神歌,美丽的土家族姑娘化为杨二姐,狩猎中的猎人都化为毛古斯等,他们都是受到早期图腾幻化神话的影响所致。
早在1966年,法国学者茱莉亚·克利斯蒂娃就提出了“互文性”的概念,他认为,“互文性”就是指文本对话,任何文本都是其他文本的吸收和转化,即一个文本中交叉出现其他文本。[1]947此后,首先是文学的研究,因为文学本身就具有互文特性,它取代了当时流行的“主体间性”概念,所以互文性又被称为“文本间性”或“文本互涉”,也就是所谓的“文本与其他文本发生明显或潜在关系”。[2]64实际上,互文性是混杂了多个文本的内容,但有一个核心意义,同时意味着一个文本利用各种手段去影响其他文本的产生,它是后现代文本的一种重要表征。[3]63土家族以白虎为图腾崇拜,而且较为明显地能够利用本民族的神话传说描绘自己族群起源、繁衍、迁徙与发展,人与图腾的互化观念与灵魂观念的结合,使土家族相信人死后会变为图腾。土司统治时期,土家族人每逢进行音乐活动,都要祭祀祖先,举行图腾崇拜仪式,土家族土司音乐活动与图腾崇拜彼此紧密地联系,而且人们图腾对象往往出现在不同的音乐活动当中。土家族图腾与土司音乐之间互文的构成有其特定的文化根源,因为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喜欢把自己打扮成图腾的模样,土家族以白虎、蛇、牛、洞穴等为图腾,这样,一个氏族、部落的图腾,自然而然成了氏族或部落的标志。随着历史的发展,土家族土司音乐活动中仍然保留着一些神话故事,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土家族图腾神话其实并不是神话,而是一些真实的历史故事。土家族土司音乐文化有着上千年的历史,其中与土家族传统文化互文性表征十分明显。
一、白虎图腾与虎钮錞于
土家族先祖巴人是以白虎为图腾崇拜的,土家族人呼“虎”为“廪”,到处可以听到白虎族祖的神话传说。传说土家族的八部大神是喝虎奶长大的,其先祖是白虎。可以看出,土家族原始图腾与土家族最早的氏族部落首领“廪君”融为一体,使得白虎神话更加趋于完善。土家族传说其巴人鼻祖为“廪君”,他与居住在武落钟离山的赤黑两穴五姓氏族,通过比剑击石独中,乘土船独飘而战胜其他四姓氏族首领,被推为五性氏族联盟酋长。[4]35据《后汉书·巴郡南郡蛮》记载:“廪君死,魂魄世(化)为白虎,巴氏以虎饮血,遂以人祠焉。”[5]134唐代樊绰在其《蛮书》中记载:“巴氏祭其祖,击鼓而祭,白虎之后也。”[6]198汉末史籍《世本》和南朝史籍《后汉书·南蛮西南夷传》曾记载巴人首领“务相”被推为五性氏族联盟首领时,不以名为称号,而是以其图腾白虎为称号,称“廪君”。“廪君”是赤穴与黑穴姓巴氏首领,在成为首领之前,赤黑两穴五姓氏族也应该有其自己的氏族图腾或崇拜先祖,也可能有崇牛者、崇犬者、崇猴者等。“廪君”统治了巴氏以后,其图腾自然转化为“白虎”。时至今日,湘鄂渝黔边邻的土家族地区的“廪君”后裔仍然保留着崇虎的习俗。根据土家族的神话传说,“廪君”是巴氏之子,名务相,所以后来人们又将“廪君”称为向(相)王天子,“廪君”成了土家族图腾崇拜和祖先崇拜结为一体的祖神。千百年来,土家族人一直认为“廪君”是白虎的化身,而“虎饮人血”,所以“廪君”的后裔“遂以人祠”的风俗习惯在土家族地区是很普遍的,这种图腾崇拜显然具有祖先崇拜的色彩,带有“人神合一”的性质。
虎钮錞于是土家族白虎图腾崇拜的有力佐证。錞于原是中原地区的一种军乐器,据《辞海》记载:“錞,古代乐器。亦称‘錞于。’青铜制,形如圆筒,上圜下虚,顶有纽可悬挂,以物击之而鸣。多用于战争中,指挥进退,盛行于东周和汉代。”[7]200錞于传入土家族地区以后,土家族把自己的民族图腾白虎熔铸其中,赋予了錞于一个新的虎钮造型。虎钮錞于作为土家族的出土文物,证明了土家族先民巴人以白虎作为图腾,同时也说明了当时巴人早已存在白虎崇拜的原始宗教观念。早在汉代,土家族地区就有关于虎钮錞于的记载。新中国成立以后,湘鄂渝黔边邻的土家族地区相继出土了50多件汉代虎钮錞于,这些汉代虎钮錞于有高有矮,有大有小,一般高在50厘米以上,矮的在30厘米以下,重量在15至3公斤之间。虎钮錞于都呈椭圆形,鼓肩、收复、直口、平顶,顶上有盘,盘内中间铸有虎钮,虎作昂头张嘴状,列牙翘尾,虎身饰虎皮纹,盘内虎钮两侧饰鱼纹、船纹、虾纹,虎头下饰人面纹。从出土的虎钮錞于来看,土家族先民之所以白虎为图腾与白虎是仁义和勇武的象征有关,土家族的白虎图腾无疑鲜明地体现了土家族的民族精神。
三千多年以前,在我国巴渝地区曾出现过象征民族图腾的舞蹈,人们称之为“巴渝舞。”“巴渝舞”是土家族先民巴人冲锋作战时的一种军前舞蹈,这种舞蹈刚劲有力、虎虎生威,在战争中能起到鼓舞士气和震慑敌人的作用。“巴渝舞”这种图腾舞蹈在汉高祖定三秦时就记载于各类史籍之中。晋代常璩在其《华阳国志·巴志》中曾有这样的记载:“汉兴,亦从高祖定秦有功,高祖因复之,专以射白虎为事,户岁出钱,口四十,放世号白虎复夷,一曰板楯蛮。汉高帝灭秦,为汉王,王巴蜀。阆中人范目有恩信方畧,知帝必定天下,说帝为募发賨民要与共定秦,秦地既定,封目为长安建章乡族,徒封阆中慈乡候,目复除民罗、朴、沓、鄂、度、夕、龚七姓不供租赋。阆中有渝水,賨民多居水左右,天性劲勇,初为汉前锋陷阵,锐气喜舞。武帝善之曰:‘此武王伐纣歌也,’乃令乐人习学之,今所谓巴渝舞也。”[8]56由此可见,史料记载巴渝舞中人们“执杖而舞”的形式很早就存在了,也恰恰印证土家族先民巴人“以射猎为事”的民族特质。至今,在土家族聚居区仍然流行一种叫“摆手舞”的祭祀性舞蹈,根据前人的研究成果得知,土家族摆手舞就是古代巴人巴渝舞的一种衍化形式,摆手舞中的许多动作都与白虎有关,摆手堂神桌上要供奉虎或虎皮,舞者要披虎皮,并且在舞蹈造型上用双爪和上身的姿态生动、形象地表现白虎的形态。笔者认为,作为脱胎于土家族白虎图腾的民间歌舞,从崇拜中的深度信仰到表演形式的选择,从艺术造型作为超越于现实阶段的幻想型心态到民众对祖先的顶礼膜拜,无不和图腾文化、民间音乐等有着紧密的联系。
唐宋以后,尤其是土司统治时期,土家族的族群相对稳定。在湘鄂渝黔边邻的土家族聚居区内,特殊的自然环境使土家族先民具备了勇猛善战的特质。由于土家族聚居区崇山峻岭、沟壑纵横、野兽众多,狩猎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重要内容,所以一些反映土家族先民穴居、渔猎的原始宗教信仰一直流传。改土归流以前,土家族地区比较封闭,原生型的形态遗留较多,许多古老的图腾崇拜习俗一直传承,随处都可以听到白虎族祖的传说故事。土家族人崇拜白虎,每家每户都有一个白虎坐堂,家家都有设坛祭祀白虎。据记载,在很早以前,重庆酉阳、秀山等地的土家族人,在堂屋后墙的中间放一凳子作为白虎坐堂的神位;湖北来凤的土家族是在神龛上供坐堂白虎;长阳、巴东、建始、五峰的土家族人,在跳舞祭祖时,必唱“怀胎歌”,第三唱段唱的白虎是家神。[9]69鄂西长阳土家族地区举行“跳丧”仪式,必须唱丧歌《十梦》,其中有“三梦白虎当堂坐,当堂坐的是家神”;配合唱丧有《虎抱头》等舞蹈。湖北恩施土家族地区,人们在表演“撒尔嗬(一种祭祖的丧事舞蹈)”时,就有“踏歌”“踏蹄”的内容,巫师们“绕尸而歌”,歌词内容主要为“唱白虎”。土家族先民巴人认为其祖“廪君死”而“魂魄世为白虎”。图腾崇拜是民族传统文化传承的载体,同时也是土家族音乐文化本质内核,作为土家族音乐表演的基本元素,图腾崇拜造就了它与土家族土司音乐互文的必然性。很显然,我们可以清晰地观察到土家族音乐中大量存在图腾崇拜的因子,同时在一些歌舞、乐器中发现新的符号与特点,并且赋予它自己的解释。土家族图腾与土家族音乐具有相似性的构成因子,其中包括主题参照、结构引用、模式模仿等方式,这就是它们能够互文的原因之一。
二、蛇图腾与傩愿酬神戏
土家族先民巴人在很早以前就崇拜蛇,并且以蛇为图腾。巴人以蛇为图腾,则可追溯到3000年前的殷商时期,文物工作者在湘鄂渝黔边邻地带的殷商时期遗址中,发现了大批以蛇为主体纹饰的陶瓷。据后汉时期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记载:“巴,蛇也,或曰食象蛇,象形,凡巴之属皆从巴。”[10]309土家族先民巴人在古代常常以民族图腾作为自己部落的族称,可见,巴人是一支崇拜蛇的部落。根据《山海经》记载,巴蛇曾出现在洞庭湖一带。《山海经》中记载:“有巴遂山,渑水出焉。又有朱卷之国,有黑色,青首,食象。”郭璞注:“即巴蛇也”。《海内南经》也曾记载:“巴蛇食象,三岁而出其骨。”由此可以看出,巴蛇其实就是生活在土家族地区的一种大蟒蛇。
蛇对于远古时期土家族先民来说,是一种神物,也是吉祥物,它深刻地影响着土家族的图腾意识、宗教信仰与民俗生活。土家族先民一开始就把蛇当成了图腾对象,在远古时期,他们把蛇当做神仙供奉,认为蛇是神的化身,会给人们带来福气。当今,在土家族聚居区还有“屋基蛇不能打”的习俗。土家族人每当看到室内或房屋四周有蛇,以为是已逝的先人托形回家,于是,赶忙摆上香纸、蜡烛及三牲祭品,诚心供奉,口中叼念着赞美或许愿的话语,引蛇出宅。[11]26本土学者在土家族聚居区也相继搜集了许多有关蛇的传说与风俗,如:“见蛇不打不抓,打蛇其同类会来报仇;七月有蛇、蟾蜍、蛙、虫之类进入堂屋,只能将其赶出,不能有所伤害,因为传说蛇是土家族人的先祖;早饭前忌讳说龙、蛇、虎、豹、神、鬼等,说了整天办事不顺;见蛇交配,不能叫喊别人观看,谁看谁倒霉,若遇此事,应先对树木说,树木枯萎,人方能免灾;传说蛇骨刺入人体内,要用龙骨才能挑出,因而大家不敢吃蛇;若有不懂规矩的年轻人,抓到蛇想吃其肉,也不能将蛇带入家中煮吃。”[12]61在土家族地区,人们经常赞扬蛇,认为蛇能够主宰人的祸福。蛇从来不咬与它无仇无冤的人,如果女人结婚后梦到蛇,则是一件大喜事,意味着将来一定会生贵子;如果男人梦到蛇,则意味着会发财升官。土家族人一般不敢直呼“蛇”名,而是把其称为“金串子”“钱串子”。
根据考证,我们发现,在古代巴人的傩舞演绎中,有许多与蛇图腾相关的动作遗留。一直以来,巴人被称为“蛮”,他们驱鬼酬神,喜爱傩舞,并通过傩舞对蛇进行美化。湘西土家族地区由于敬蛇,忌讳直呼蛇名,蛇被称为“蛮家”,祭蛇就叫“请蛮家”,搬演傩愿戏和祭祀时,都要画一张蛇形象,贴在堂屋的中央。据《山海经·海内经》记载:“有人曰蛮民,有神焉,人首蛇身,长如辕,左右有首,衣紫衣,冠丹冠,名曰延维,人主得而飨食之,伯天下。”[13]253从史料记载来看,“蛮民”应该指的是生活在湘鄂渝黔边区的土著,是一个群体,这一群土家族人具有蛇的形象。“延维”是对这一带“土蛮”的称呼,但又仿佛是称呼一条蛇,按常理解释,我们可以这样认为,“蛮民”以蛇为图腾。据《慈利县志》记载:“又有一惯习,陋习日还傩愿,无论红会白会,群尝演之,法舁木雕半象,垒垒若阵,斩之级坏,陈案上,巫者杖剑踽步,击鼓跳歌,观者乃至入神如木,蜣螂转粪,凡被其尝好,亦与人异酸碱云。”[14]28可见,土家族傩愿戏最大的特点就是表演者装扮成神进行歌舞。资料显示,明清时期,土家族地区的人们还专为蛇修了墓、建了庙,并且巫师在祭祀作法过程中以蛇为动作形象,模仿蛇的动作。曾经认为蛇是自己图腾的土家族人,至今在傩愿戏、打金钱杆等活动中仍然保留着许多蛇图腾崇拜的遗风。巫师在气氛浓烈的傩戏中,扮演着人神角色,喃喃低吟,还往往装扮成“蛇身”,拿着竹筶与司刀,在酬神、娱神的仪式中演绎着土家族的历史。根据地方志记载,清朝初年,土家族部分巫师开始兼做优伶,他们向戏曲艺人学习,各种汉人的戏曲唱腔与戏曲段子在土家族地区迅速传开。当时,土家族傩坛开始分化成两种形式,一种为祭祀性的内坛,另一种为娱乐性的外坛,内坛作法,外坛唱戏,在清同治年间,以沅水九澧一带的土家族傩愿戏登上高台为标志,打破了观演合一与载歌载舞的传统模式。土家族傩愿戏起源于人们的自然崇拜,在表演过程中,全部演绎的是鬼神相关的故事。土家族傩愿戏的唱词,有的是固定化、程式化了的词,具有浓郁的宗教祭祀性;还有的是靠表演者即兴发挥,反映的是现实生活中的一些人和事,娱人色彩浓重。在土家族傩愿戏的一些科目中,如《赶天狗料》《搬土地》《白帝天王科》等,唱词中明显带有对龙(蛇)的崇敬,希望龙(蛇)能给自己带来福气。在民俗生活中,土家族忌讳谈蛇,一方面,巫师身穿法衣长袍,拿朝笏、司刀、金帽等物,根据祭祀内容时而模仿蛇形操演。另一方面,巫师随着锣鼓班子手舞足蹈,口中念念有词,若遇到有“蛇”的唱词,就会更换为“龙”。作为土家族傩愿戏演出的载体,蛇首先是一种图腾崇拜,它的艺术构成主要还是神灵、神话与故事情节等要素,傩愿戏中土家族图腾与音乐文化互文性联系的表现也主要集中在这一点上。土家族人对蛇的形象认识是多层面的,它有着特定的文化涵义,这些涵义千百年来一种传递着土家族图腾崇拜的主题。我们发现,土家族傩愿戏中的蛇崇拜现象具有强烈的叙事性特征,戏曲的叙事有时往往也遵从神话故事的叙事,结构疏松且完整性较弱,善于营造气氛和渲染气氛,它有时还会断断续续地植入多种符号,比如蛇形、龙形、祖先、神灵、阴曹、屋梁、锣鼓等就是话语呈现的一种方式,这些符号不但没有消减叙事的节奏,而且正好参与到叙事之中。不难看出,土家族傩愿戏中的蛇图腾崇拜决定了土家族戏曲音乐文化对民间神话、民间传奇及风俗习惯的吸收,并且普遍运用了引用、模拟、夸张、叙事、转述、参照等互文手法。
土家族人有打金钱杆的习俗,它是流行于土家族地区的一种曲艺形式。金钱杆这种艺术形式是因其道具为“杆”与“钱”组成而得名,“杆”是长约一尺左右的竹竿,竹竿上钻几个小孔,以红线喘上数枚小铜钱。表演时,一手握住没有系铜钱的一端,使系铜钱的一端击出响声,以赴节奏。金钱杆的打法变化较多,每一拍都有一个与蛇有关的响亮名字,如“金蛇过河”“蟒蛇出洞”“懒蛇翻身”“长蛇缠腰”等。作为流行于土家族民间的一种表演艺术,傩愿戏的独特表述方式造就了其互文性创作的必然性。在土家族表演的《金钱杆》中,故事情节影射了人们对蛇的崇拜,一个个与蛇有关的曲牌告诉我们,蛇图腾已经渗透到了土家族音乐文化之中。
三、牛图腾与薅草锣鼓歌
自古以来土家族就有对牛崇拜的习俗,在湘鄂渝黔边邻的土家族地区,至今还能找到一些有关牛图腾的痕迹。春节前后,土家族地区民间流行着送春牛和唱春牛的活动。送春牛活动一般是在春节前就开始了,由送春人将自己画好或剪好的“春牛”送到土家村寨的家家户户,它预示着来年五谷丰登。在湘西、鄂西等土家族地区,居民的房屋屋顶都是用砖、泥或石块砌成牛角形的屋角。有的地方甚至在墓碑上也安上形似牛角的碑罩。据记载:“农历四月十八日,在湖北的来凤、长阳等地为四月初八日,是土家族传统的牛王节。每年的这一天,土家山寨的男女老少都要穿着节日的服装,来到牛王庙举办牛王会。他们供上酒、肉、瓜果等祭拜牛王,演唱牛王戏,为牛王过节。所有的耕牛在这一天都要休息,人们还要用鸡蛋和好酒好肉喂它。每年农历八月十五至下一年交春之前这段时间,土家人都要用好酒好肉来敬‘牛菩萨’,求它保佑全家吉祥平安、生活美满。”[15]71牛在土家族的民俗生活中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同时也是该地区发现最早的古动物之一。新中国成立以前,土家族人一般不杀牛,即便杀了牛,也是用它作为祭品,杀牛人也要念起咒语祈祷它的保佑,祭拜牛时,人们则肃立两旁,不得喧哗。土家族对牛的崇拜由来已久,在湘鄂渝黔边邻的土家族聚居区,人们在新石器时代遗址里,发现两件与牛崇拜有关的兽面图案,这个似人非人、似兽非兽、似鸟非鸟的怪物,就是传说中“饕餮”的形象。史籍《神异经》《述异记》《山海经》等所记载“饕餮”的形象,就是人面、虎齿、牛身,有翅膀,性凶,好吃人。笔者认为,在湘鄂渝黔边邻的土家族聚居区,从新石器时代开始至商周时期,土家族就存在着牛崇拜的现象。
因为与农耕有关,土家族人大多数崇拜的是水牛,人们认为水牛是天赐的“农家宝”,将水牛视为“半边阳春”,在土家族地区至今还一直流传着这样的谚语,如“阳春一把抓,全靠牛当家”“要得庄稼好,三犁两耙不可少”等,他们意识到水牛与生产、生活息息相关。远在数千年前,在湘鄂渝黔边邻的土家族地区就已经出现了原始农业,在农业生产活动中,牛的作用十分重要。由于交通不便、农业生产技术落后,土家族地区只有靠原始农耕才能维持生活,属于典型的山地农耕文化。我们还发现,在民俗生活中,湖南酉水流域的土家族女性喜欢穿戴一种叫“西兰卡普”的刺绣,这种刺绣绘有各种牛与牛角造型图案。在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妇女们将衬布制成牛角形状衬在围腰的上部,显示了独特的个性。显然,这些与牛有关的图案和牛图腾崇拜有着紧密的渊源关系。
土家族人还崇拜犀牛和黄牛。在土家族民间传说和图腾信仰中,犀牛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神物,是吉祥如意的象征,被土家族视为祖先或祖先亲族。湘鄂渝黔边邻地区,历史上曾经存在犀牛及类似的动物,由于后来生态环境的变化,气候的变迁,犀牛类动物迁往别处,但土家族人爱护自然生态,对破坏自然生态环境的现象深恶痛绝,他们认为犀牛有超自然的灵异神力,神圣不可侵犯,犀牛生活的自然环境被视为神地,不可践踏。清代《同治增修酉阳直隶州总志》载:“龙池一名犀牛潭,在州北三十里龙池铺,以此得名,八景内所谓龙池伏脉者也。案此池纵广十余亩,内有三穴,水色澄清,泛涨不盈,旱干不涸,相传犀牛宅其中,嘉庆中或投死犬于池,数日后,池侧居民睹一牛浮池面,水随汤溢,顷之有声如雷,水顿消秏,牛亦随没,阅宿后澄然一泓,始信犀牛之说不谬,近则为潮水淤垫,三穴只存一穴矣,邵志谓泉孔之水出于此池,故以龙池伏脉列州城八景之一。”[16]36可见,土家族人把犀牛看成神灵,有犀牛栖息的地方自然就被染上神异色彩,充分体现了土家族人对自然生态的伦理审美意识。如今,土家族民间传说中有“犀牛望月”的故事,在民间歌舞中有“犀牛望月”的动作,这些都很好地证明了土家族人自然崇拜、犀牛崇拜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内在联系。土家族人崇拜犀牛,认为犀牛相当灵异,能主宰水流,有分水神力,在犀牛崇拜过程中体现了天人感应的神灵感。人们普遍认为土家族土司权威永远存在,是因为土司祖先埋葬在犀牛洞中,犀牛灵感接纳了土司的祖先灵魂而至。[17]126如今,在湘西、鄂西土家族地区,还保留着崇拜犀牛的风尚,湘西北即龙山、永顺、保靖的土家族,还保留着以“犀牛”命名的村寨。鄂西土家族地区一直流传着犀牛助人的故事,又有犀牛给善人报恩的故事,如此可敬、可爱的犀牛,只能出现在湘鄂渝黔边邻的土家族民间传说和民间故事中。在土家族生活的地方,犀牛曾经十分丰富,土家族的《栽秧薅草锣鼓歌》就描述了湘鄂渝黔边邻的聚居区曾经有成群的犀牛存在,并且人们把犀牛皮蒙来做鼓:
说起皮根由,来的有根蔸;
黄连潭中老犀牛,刀枪扎不透。
这头犀牛恶,人人莫奈何;
皮匠祖师把它捉,死牛任现剥。
把它皮子剥,晒了半边坡;
削得不厚又不薄,蒙鼓好家伙。[18]29由于犀牛在土家族地区早已经灭绝,即使土家族曾经有过犀牛图腾,如今也不可能留下更多遗迹,但从部分土家族民歌与传说故事来分析,土家族祖先应该有一个以犀牛为图腾的部落或氏族。
薅草锣鼓歌也称栽秧薅草锣鼓歌、挖土锣鼓歌,它是土家族人在生产劳动中集体创作的民间音乐样式,既起到劳动作息信号的作用,同时也可以惊吓野兽。据清代《龙山县志》记载:“土民自古有薅草锣鼓之习,夏日耘草,数家合趋一家,彼此轮转,以次而周耘之,往往集数十人,其中二人击鼓鸣钲,迭相应和,其余耘者退耕作息,皆视二人为节,闻歌雀跃,劳而忘疲,其功较倍。”[19]15这种击鼓鸣钲、迭相应和以及间夹驱逐野兽的呼喊声,就是土家族薅草锣鼓歌早期的原始形态。从土家族薅草锣鼓歌的歌词中,我们发现,在土家族氏族图腾时期,人们必须遵循图腾规则和禁忌,不能违反图腾规则,不能说一些违反禁忌的话,更不能杀害自己的图腾,但在某一规定的时间内,人们可以集体屠杀图腾,举行图腾圣餐。早期的薅草锣鼓歌内容,绝大多数为图腾崇拜和激励生产劳动,如《请神》《扬歌》《拜神》《送神》《拜牛》《薅草栽秧歌》等;还有一些直接取材于土家族民间故事和民俗生活,如《白果姑娘》《孟姜女寻夫》《七姐下凡》《东山哥哥西山妹》《恶鸡婆》等。因此,用土家族牛图腾的内容和形式来演绎民间音乐,是土家族原始宗教的一个音乐文化交融的特点,具有明显的互文性特征。
土家族薅草锣鼓歌中有关牛图腾的内容,遵从了土家族民间音乐演绎的原则,在唱腔方面沿用了土家族山歌的模式,同时参照了土家族歌舞、曲艺的体裁特征,其旋律具有典型的板腔化倾向。从土家族薅草锣鼓歌唱词内容来看,流行于湘西龙山县的《请神》讲的就是土家族请牛神的故事,这是一则对图腾进行崇拜的祭祀词,其产生年代应不会太久远。如薅草锣鼓歌《请神》歌词唱道:
一请麻田七姊妹,
二请八大金刚神,
三请九牛推车转,
四请南海观世音……[20]265
土家族薅草锣鼓歌中有大量的祀牛章节,几乎都是一些有关牛图腾的神话,这些牛图腾的神话很明显是属于典型的阐释型的图腾神话,它善于营造和渲染气氛,呼唤着人们的体验和崇敬,这类神话的产生是人们图腾观念产生之后的事了,人们对图腾这一现象已产生了疑惑不解,便进行各种猜测与解释。在叙事情节方面,土家族薅草锣鼓歌与牛图腾有着共同的母题,对于表述文本之间关系的创作互文性而言,薅草锣鼓歌对土家族原始宗教母题的接受,不仅明确了土家族民间音乐表述方向及演绎目的,而且通过图腾崇拜的母题所折射出的类型化现象,更能反观土家族薅草锣鼓歌与牛图腾两者之间彼此的文化功能与审美倾向。如果说土家族薅草锣鼓歌更多地受到汉文化的影响,从而呈现出土家族、汉族民间故事、神话交融的特点,那么,在土家族薅草锣鼓歌中,我们几乎看不到儒家文化的痕迹,而是发现它深深地印上了土家族图腾的烙印。
四、洞穴图腾与迁徙歌
史料记载,古代巴人崇拜洞神,他们认为一些山上或岩石群里的岩洞都有洞神,而且认为人若突然生病或身体不舒服时是得罪了某些洞神,于是凡遇有人身体不适或生病,就会带上香纸、蜡烛、粑粑及酒肉去洞门口敬洞神,祈求洞神保佑。我们从《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记录的“廪君”活动可以发现,当时的廪君部落已经形成了许多民俗传统,比如说出自赤穴、崇拜赤色的巴氏,还有出自黑穴的四姓、崇拜黑色。“廪君”虽然是古代巴人神话中的人物,但从有关“廪君”的神话传说中可以了解到土家族部落祖先的起源,同时也反映了古代巴人洞穴生人及洞穴图腾的原始信仰观念和洞穴生育崇拜。从唐朝贞观四年(630年)到元代延祐元年(1314年)的684年里,历代中央王朝在湘鄂渝黔边邻的土家族聚居区推行了“羁縻州”制,唐朝贞观四年中央王朝于“酉溪蛮”地置思州,属黔州治下五十个“蛮州”之一。属黔州治下五十个蛮州,“皆羁縻,寄治山谷”。这种制度无疑加强了土家族人的洞穴崇拜意识。洞穴崇拜与民俗神话在土家族聚居区盛行,为我们解读古代巴人五姓生赤穴、黑穴传说,以及探索巴人洞穴生育崇拜提供佐证依据。
土家族学者们认为,“巴人及其后裔土家族的多种称谓中都曾用到‘洞’或‘峒’这也与赤黑二穴之说及其洞穴生育崇拜有关。‘洞’‘峒’均指洞穴。在典籍中,屡有在巴人后裔的族称前冠以‘洞’或‘峒’的称呼的记载,在土家族土司建制的名称中,也大量出现带‘洞’或‘峒’的名称,‘洞’或‘峒’又常作为土家族各个部落的称谓。这一方面是由于土家族聚居区多为洞溪地貌,这一地区往往被称为‘峒’,有所谓‘蛮不出境,汉不入峒’的说法;另一方面则是由于洞穴生育崇拜在土家族地区有着深广的影响,以致渗透到了有关土家族的各种称谓之中。”[21]64尽管土家族地区在羁縻州制以后实施了土司制度,领地也远远超出了先前部落时期的范围,但在土司建制中,还是保留了大量带有“洞”或“峒”的名称。如属于永顺宣慰司的田家洞、白岩洞、施溶溪洞、馿迟洞、麦着黄洞、腊惹洞,容美土司的石梁下峒、上爱茶峒、下爱茶峒,施南土司的金峒、西关峒、师壁峒等。其实,“洞”或“峒”就是土家族族称的称呼,如酉水流域的八个土家族部落,当地人称“八蛮”,又称“八部大王”,八个部落也被称为“八峒”。《续资治通鉴长编》曾记载:“招抚溪峒夷人,颇著威惠,部民借留,凡五年不得代。”《宋史》记载:“是岁施州溪洞蛮西南夷龙以特来贡。”《元史》记载:“合峒蛮八百余寇施州。”可以看出,以上文献所涉及的“八峒”“溪峒夷”“溪洞蛮”“合峒蛮”等其实就是土家族部落的族称,他们以“洞”或“峒”来划分部落地域单位,“洞”或“峒”应该是土家族先民洞穴崇拜留下的遗迹,同时它也是土家族人存在洞穴图腾的见证。
土家族先民是巴人融合当地土著居民而形成的,他们辗转迁徙于湘鄂渝黔边邻地区,《永顺府志》曾记载了土家族先民这种“渔猎养生,以歌为乐,刻木为契”的生活特征。目前,遗留下来的土家族古代《迁徙歌》是这样记录祖先们崇拜洞神的:
千潭万水走过了千山万岭走过了,
爬岩拉坎的地方走过了鲤鱼标摊的地方走过了,
来到桃源溪洞;
螃蟹爬的地方走过了虾米跑的地方走过了,
麂子走过的地方走过了猴子跳过的地方走过了,
留住桃源溪洞;
彭公爵主上船来田老官人上船来,
八部大王上船来……[22]124
土家族《迁徙歌》巧妙地运用排比的手法,简单地叙述了土家族先民经过千辛万苦来到桃源溪洞,而且将其先祖彭公爵主、田老官人、八部大王等的英灵呼唤上船,来到洞中,渲染了一种强烈的祖先崇拜气氛。土家族人在对洞穴崇拜过程中,采用民歌演唱等形式,抒发了古老的洞穴图腾观念,同时也表达了对民族图腾的认识和感受。在土司统治时期,土家族人利用民歌(主要为《迁徙歌》)并通过隐喻、比拟、比兴、模仿、明引、暗引、改编等互文性手法,对洞穴图腾进行创作接受。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所致,土家族人长期居住在交通不便的山区,属于典型的山地民族,有着区别于其他民族的独特性,他们讲土家话、过土家节、跳土家舞、唱土家歌、做土老司、织土家锦、打土家“溜子”,仍然保留着自己的民族习俗。由于环境的恶劣,土家族人生活十分清苦,在这种背景下,人们更多的是关心自己的生产活动与衣食住行,迷信诸神,希望通过诸神来保佑来年五谷丰登、人畜平安。这样,他们只有通过吟唱民歌来宣泄情感,在演唱民歌中来构建自己的民族图腾意识。如这首流传于湘西龙山境内的山歌:
养女莫嫁洛塔坡,洛塔坡上包谷多;早上吃的包谷饭,夜里睡的包谷壳;养女莫嫁洛塔界,洛塔界上烧岩柴;嫁时是个红花女,回来好像火飘柴;养女莫嫁洛塔坡,只听水响不见河;
哪天若要洗个澡,一直下到洗车河。[23]187这首山歌直接叙述了湘西龙山县洛塔界的恶劣环境,人们都不愿意把女儿嫁到那里,从歌中我们明显感受到了土家族人受环境制约的痛苦心情。我们发现,在土家族大量的民歌中,多多少少具有一些古老的洞穴图腾意思,而且具备了教化、祭祀、娱乐、社交和传播等功能,尤其是迁徙歌,它不仅采用了互文手法,而且运用隐喻方式,增强了土家族民间音乐文化内涵。在土家族迁徙歌中,当歌曲唱到相关洞穴图腾内容时,它会用互文的手法来强调土家族古老的图腾观念,因为土家族迁徙歌寓言性强,常采用互文性手法,通过神灵与群众的对歌,来表达人们崇拜洞神的意愿。在土家族迁徙歌中,一些有关洞穴崇拜的内容往往出现在不同的曲目中,如流行于土家族地区的《田氏根歌》《何氏根歌》《迁徙歌》《来源歌》等,这种图腾崇拜情节互文关系的例子在土家族迁徙歌中举不胜举。可以看出,在土家族洞穴图腾与其民族迁徙歌中,小到祭祀程式,大到歌唱内容,无一不在互文关联当中,而且每一首歌曲都是土家族洞穴图腾内容的一环,每个环节都被图腾崇拜紧紧维系在一起,在演绎这一层面上互涉、互文。
结 语
在民族文化传承过程中,土家族图腾与土家族土司音乐互文、互涉关联是极其普遍现象,它们之间的互文性不仅仅包括了土家族土司音乐文本所指涉的图腾崇拜文本,还包括了音乐的原始材料是宗教祭祀或民俗生活,音乐体裁与风格也可能具有图腾崇拜意识而成为互文性,可以利用音乐演绎制造互文性。所以,土家族图腾崇拜与土司音乐创作的互文成为了必然,土家族图腾的形象、祭祀仪式的场景、人们对神灵的意念等就成了土家族土司音乐的来源。
土家族土司音乐中有许多以民族图腾为题材的内容,有着深刻的历史文化背景和人文精神内涵,土家族图腾崇拜所体现出的维护正义、惩恶扬善、厚生佑民、勤劳勇敢等优秀精神,体现了土家族人的传统美德,其对于土家族土司音乐的传承与创作具有借鉴与纽带作用。在土家族文化、艺术、宗教这一大家族中,文本的性质大同小异,它们在一定的条件下有意识的相互引用、相互影响,特定的主题或场景之间建立了相对稳定的联系,从而形成同一个体裁内部的互文关系。通过对土家族图腾与土家族土司音乐互文性考察,我们认为,土家族土土司音乐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都与土家族图腾崇拜有着紧密的联系。
[1](法)茱莉亚·克利斯蒂娃.符号学:意义分析研究[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947.
[2](法)热厄尔·内奈特.热厄尔·内奈特论文集[M].史忠义,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64.
[3]杨紫轩.近年来中国喜剧电影的互文性表征:阐释与意义[J].社会科学论坛,2015(9):63-72.
[4]吴晓东.苗族图腾与神话[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35.
[5][宋]范晔. 后汉书·巴郡南郡蛮[M].李虎,译.西安:三秦出版社,2004:134.
[6]转引自杨昌鑫.土家族风俗志[M].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198.
[7]周明阜.凝固的文明[M].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2006:200.
[8][晋]常璩.华阳国志·巴志[M].成都:巴蜀书社,1984:56.
[9]刘孝瑜.土家族[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4:69.
[10][汉]许慎.说文解字[M].北京:中华书局,1985:309.
[11]刘文奇.土家族人与蛇文化[J].湖南林业,2003(9):26-27.
[12]龙湘平,陈丽霞.土家族图腾艺术[J].昌吉学院学报,2006(1):60-63.
[13]徐显之.山海经浅注[M].合肥:黄山书社,1995:253.
[14]慈利县志[Z].乾隆刻本.
[15]丁世忠.论土家族的牛崇拜[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5(7):71—73.
[16]同治增修酉阳直隶州总志[Z].同治刻本.
[17]白俊奎.试析土家族的“犀牛”图腾崇拜[J].重庆社会科学,2007(8):125-128.
[18]彭荣德,金述富.土家族仪式歌漫谈[M].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9:29.
[19]龙山县志[Z].乾隆刻本.
[20]龙泽瑞,龙利农.牛角里吹出的古歌—梯玛神歌[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3:265.
[21]向柏松.廪君神话传说与清江流域土家族的原始宗教[J].民族文学研究,2005(2):63-68.
[22]彭勃,彭继宽.摆手歌[M].长沙:岳麓书社,1989:124.
[23]刘黎光.湘西歌谣大观[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0:1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