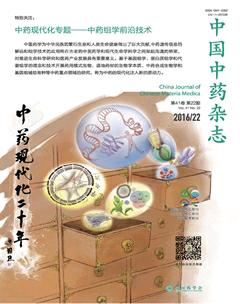中药功效成分合成生物学研究进展
苏新堯薛建平 王彩霞
[摘要] 中药功效成分是中药发挥防病治病等重要作用的主要活性物质,大多数的中药功效成分都来自药用生物次级代谢产物衍生物。目前中药功效成分的获取主要是从源生物中直接提取,提取成本高,收益极低。中药微生物合成生物学,通过在微生物中导入目标产物的合成途径,利用微生物进行发酵生产目标成分,是一项具有发展前景的中药活性物质获取途径。通过异源宿主发酵大规模产中药功效成分,解决了中药功效成分含量低,提取分离困难,未来将极大缓解中药功效成分供需不足的局面。该文从中药功效成分合成生物学实例进展以及中药功效成分合成生物学策略2个方面对中药功效成分合成生物学进行综述。
[关键词] 中药功效成分;合成生物学
Recent advances of synthetic biology for production of functional ingredients in Chinese materia medica
SU Xinyao1,2, XUE Jianping2 , WANG Caixia1*
(1. Institute of Chinese Materia Medica, China Academy of Chinese Medical Sciences, Beijing 100700, China;
2. Huaibei Normal University, Huaibei 235000, China)
[Abstract] The functional ingredients in Chinese materia medica are the main active substance for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nd most of them are secondary metabolites derivatives. Until now,the main method to obtain those functional ingredients is through direct extraction from the Chinese materia medica. However, the income is very low because of the high extraction costs and the decreased medicinal plants. Synthetic biology technology, as a new and microbial approach, can be able to carry out largescale production of functional ingredients and greatly ease the shortag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ngredients. This review mainly focused on the recent advances in synthetic biology for the functional ingredients production.
[Key words] fuctional ingredients; synthetic biology
doi:10.4268/cjcmm20162211
中药功效成分是中药发挥防病治病等功能的物质基础,其大多是来自药用植物的次生代谢产物或其衍生物,具有多种药理学活性,如抗癌,抗氧化,提高免疫力等。根据生物活性的起源这些中药功效成分可分为苯丙烷类(phenylpropanoids)、异戊二烯类(isoprenoids)、多聚酮类(polyketides)、生物碱类(alkaloids)以及黄酮类(flavonoids)[1]。不同种类的中药功效成分在药物开发中均有应用,如抗疟疾药物青蒿素,用于治疗阿兹海默症的石杉碱A,用于治疗感冒的麻黄素、抗癌药物喜树碱以及对埃博拉病毒感染具有治疗效果的粉防己碱,在治疗肥胖中有巨大潜力的南蛇藤醇等[24]。这些例子都展示了中药功效成分在疾病治疗与防御以及其他未解决的疾病方面有很大的应用前景。
目前,中药功效成分的获取途径主要有①直接从药源植物中分离提取;②化学及半化学合成途径;③基于作用机制了解清晰的基础上,寻求替代物;④利用植物细胞或组织培养技术;⑤微生物合成法。
直接从中药中分离提取有效活性成分是目前中药功效成分获取的主要途径。但该方法过度依赖于中药资源,据统计,这些活性成分大约2/3来源于野生资源,而药用功效成分多为次级代谢产物,在植物中的积累量极低,如红参中稀有人参皂苷Rh2的质量分数低于0.001%[5];虽然中药的栽培技术已日渐成熟,但其培养条件要求较高,且耗时耗力,生产成本高;而通过化学合成,无论是化学合成或半化学合成的方法,都会受其特殊的化学结构如手性及不对称中心的限制;利用药用植物细胞或组织培养,能够克服以上多方面问题,目前,以中药功效成分为生产目标的细胞工程数量大约有100多种,研究表明,约40种活性物质经组织培养,其含量甚至高于原植株水平,但大多数中药组培机制研究不甚清楚,而且受基因型以及细胞毒性,生产成本等限制,除了较为典型的例子如人参、紫草外,利用该方法进行工业化生产成功的例子并不多。
中药功效成分的微生物合成生物学法,即在系统生物学基础上,采用工程学的设计思路和方法,通过对相关功能基因的模块化设计及改造,并充分考虑合成过程中适配性的问题,将中药功效成分的合成过程或其前体物质的生物合成途径转移到微生物细胞中,利用微生物的发酵过程完成药用天然活性物质的高效异源的合成。该方法主要是基于目标产物生物合成路径较为清晰的基础上利用微生物易于培养,不受环境影响且生长周期短,生产系统规范化,反应条件温和易于控制,产物成分较为单一,易于分离和提取以及环境友好等特点,解决中药功效成分来源稀缺,化学合成困难,以及造价高的一系列问题,为中药功效成分的工业化生产以及可持续利用提供了一个新的可行的方法。因其在生产中所带来的巨大作用,“合成生物学”被誉为可改变世界的十大新技术之一。本文将介绍中药功效成分合成生物学的应用及研究进展。
1 中药功效成分合成生物学进展
随着本草基因组学[6]、高通量测序结合分子生物学工具等的应用,大大加速了中药功效成分合成生物学的研究进展,在不同的底盘生物如大肠杆菌、酿酒酵母、枯草芽孢杆菌等,多种中药功效成分尤其是来源于药用植物的单体药物等都取得了巨大的研究进展。
1.1 青蒿素
青蒿素的合成,从黄花蒿中提取青蒿素是目前获取青蒿素的主要途径,每年全世界对青蒿素的需求都在增加,而黄花蒿中青蒿素质量分数很低仅为0.01%~0.8%,单一从黄花蒿中提取青蒿素没法满足其巨大的需求。随着参与青蒿素生物合成的各种酶基因不断得到克隆,通过转基因手段在植物体内促进其生物合成、或在微生物中重建其代谢途径的工作取得了较大的进展[717]。
2003年Keasling实验室[7]将优化后的紫槐二烯合成酶基因ADS导入大肠杆菌中,通过结合来自酵母的甲羟戊酸途径(MVA)的相关基因,首次合成了青蒿素的关键前体物质紫穗槐二烯,通过发酵优化,其产量达到了0.5 g·L-1。尽管经过不断的优化研究,大肠杆菌工程菌株产紫槐二烯的量达27.4 g·L-1[8],但是因为P450基因在大肠杆菌体内表达的受限,上下游代谢流的不匹配,使得团队将青蒿酸的合成从大肠杆菌转移到酵母菌株上来。2006年,该团队成功鉴定了催化紫穗槐二烯到青蒿酸的关键基因细胞色素P450氧化酶基因(CYP71AV1),基因功能显示该酶催化紫穗槐4,11二烯的三步氧化,生成青蒿酸。团队将ADS基因连同鉴定的CYP71AV1和与其相关的还原伴侣AaCPR基因同时在酵母中进行表达,成功构建了第一株产青蒿酸的酵母菌株,尽管青蒿酸的产量仍旧比较低,但是这一工作具有创新的意义[910]。2008年Covello研究小组[11]发现青蒿醛Δ11(13)双键还原酶基因(DBR2)在青蒿的腺毛组织组织中表达量很大,克隆该基因其功能催化显示这一基因对于青蒿醛这一底物具有很高的活性。研究团队在酵母中将DBR2基因连同ADS, CYP71AV1和CPR基因一起导入后,在酵母菌株中产生二氢青蒿酸。Donald等[12]将截短了的3羟基3甲基戊二酰辅酶A还原酶(HMGR1)基因(tHMGR)导入酿酒酵母中,增加了HMGR1的表达量从而使角鲨烯的合成量大大提高。由于角鲨烯合酶(ERG9)促使法尼基焦磷酸(FPP)流向角鲨烯, 相对的抑制了青蒿素的合成,因此,Ro等[9]通过抑制鲨烯合酶基因(ERG9)的表达减少FPP流向角鲨烯,使紫穗槐二烯产量提高了2倍。Pitera等[13]研究小组通过增加HMGR和法呢酰二磷酸酯合酶基因(ERG20)的拷贝数,提高了紫穗槐二烯的产量。另研究发现萜类调控因子蛋白UPC2是酵母细胞一个重要转录因子,调控固醇生物合成,对其进行过表达,能够提高紫穗槐的产量。
2013年,Keasling团队研究发现,相比UPC5,细胞色素b5基因(CYB5)能有效促进青蒿醇到青蒿醛的反应,而通过对青蒿腺毛转录组数据的分析,鉴定了乙醇脱氢酶基因(ADH1)和乙醛脱氢酶基因(ALDH1)分别是催化青蒿醇形成青蒿醛,青蒿醛形成青蒿酸的基因,这2个基因在酵母体内的表达,大大降低了青蒿酸中间产物青蒿醇和青蒿醛的产量,大幅度提高了终产物青蒿酸的产量,结合超表达上游MVA的所有基因包括乙酰乙酰辅酶A硫解酶基因(ERG10),HMGCoA合酶基因(ERG13),tHMG,甲羟戊酸激酶基因(ERG12),磷酸甲羟戊酸激酶基因(ERG8),二磷酸甲羟戊酸脱羧酶基因(ERG19),异戊烯基二磷酸异构酶基因(IDI)和ERG20同时通过启动子的替换将ERG9基因表达强度进行弱化以减少碳流走向三萜途径,青蒿酸合成途径的下游基因包括ADS,CYP71AV1,CYB5,ADH1,ALDH1等基因在酵母体内进行表达。这些菌株改造结合优化的发酵策略,酵母产青蒿酸的产量达到了25 g·L-1,初步达到了工业化水平[17]。除了增加通往青蒿素生物合成的代谢流,提高青蒿素的贮存能力也是解决青蒿素产量问题的一个有效途径[1415]。
青蒿素生物合成的工业化必将带来青蒿素生产方式的彻底变革, 也是缓解日益严重的青蒿素短缺局面的根本出路。同时,采用酵母发酵产青蒿素,其最终产物仅有青蒿素,目的产物含量高且单一,大大降低了后期分离纯化的成本。
1.2 紫杉醇
紫杉醇是一种紫杉烷二萜类化合物,基本骨架为三环二萜[18]。1971年首次由Wani等从短叶红豆杉Taxus brevifolia树皮中提取出来一种次级代谢产物,具有低毒、高效的抗癌效果[19],自1992年上市以来,一直是治疗卵巢癌、乳腺癌等癌症的首选药物,是目前最好的抗癌药物之一,市场需求巨大。
目前,紫杉醇的生产方法主要包括源植物提取法[20]、化学合成法以及生物合成法。紫杉醇的半合成法,是工业化生产紫杉醇的主要方法[2123],合成该技术已比较纯熟,但紫杉醇的生产仍受限于有限的红豆杉资源,无法满足市场需要;利用合成生物学技术,通过微生物来合成紫杉醇的前体物质,再运用半合成法合成紫杉醇是目前应用前景最广阔的一种方法,经过多年的研究,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进展[5,7,2426]。
Huang等[24]将脱氧木酮糖5磷酸合酶基因(DXS)基因同IDI异构酶基因、牻牛儿基牻牛儿基二磷酸合酶(GGDPs)基因以及紫杉醇二烯合酶基因在大肠杆菌BL21(DE3)中进行共表达,以异戊二烯焦磷酸为原料进行发酵,合成了紫杉醇合成途径中的重要中间体——紫杉二烯,产量为13 mg·L-1。首次成功的在工程菌株中合成紫杉烯,为紫杉醇的微生物合成提供了基础。Ajikumar等[25]利用代谢工程多元模块法,以异戊烯焦磷酸(IPP)为节点,将紫杉醇生物合成途径分为2个模块,即:产IPP的内源性2甲基D赤藓糖醇4磷酸(MEP)途径的上游模块和合成异源萜类化合物途径的下游模块。上游模块包括MEP途径的4个关键酶基因(dxs,idi,ispD和ispF),由操纵子(dxsidiispDF)控制过表达;下游模块包括2个基因焦磷酸牛龙牛儿基牛龙牛儿酯(GGPP)合酶基因(G)和紫杉二烯合成酶基因(T)。将下游模块导入底盘细胞中并过表达上游模块后,虽然紫杉醇二烯的代谢流有所增加,但其合成量极少(不足10 mg·L-1),因此,该研究小组采用“多元系统搜索”的方法寻找上下游模块平衡的最优组合,并通过改变质粒拷贝数和启动子强度的方法对下游模块的表达进行调节,使其达到最优化,最后紫杉醇二烯合成量最高达1.02 g·L-1,是紫杉醇中间体紫杉醇二烯合成量最高的报道。Zhou等[26]通过大肠酵母共培养技术进行紫杉醇的微生物合成,首先在酿酒酵母BY4700中融合表达5αCYP(P450 taxadiene 5αhydroxylase)基因和其还原酶基因CPR来催化紫杉醇合成过程中的第一个氧化反应,然后将培养基中的碳源由葡萄糖替换为木糖以解决共培养过程中乙醇对菌体及目的产物的抑制作用;增加酵母接种量,将上述构建的酵母菌株中的融合基因5αCYPCPR启动子替换为UASGPDp,在大肠杆菌中过表达葡糖胺磷酸乙酰转移酶(pta),乙酸激酶(ackA),并敲除atpFH和ACS基因以增加含氧紫杉烷类的合成量;最后将更换了强启动子的TAT(taxadien5αol acetyltransferase)基因和融合了一个CYP还原酶的10βCYP(taxane 10βhydroxylase)基因在上述构建好的酵母菌株中进行共表达,最终含氧紫杉烷类合成量为33 mg·L-1,提高了酵母产紫杉醇前体产物的产量并为无法发在单一微生物中进行生物合成的化合物的合成提供了一种新的解决方法。
1.3 人参皂苷
人参皂苷(ginsenoside)是由三萜苷元和糖、糖醛酸以及其他有机酸组成的三萜皂苷类化合物,是人参及西洋参的主要活性成分,具有抗肿瘤、抗炎、抗氧化作用[27]。随着人参皂苷的生物合成路径的解析和相关酶的基因的克隆及鉴定,应用发酵菌株合成人参皂苷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2013年,中国学者戴住波等[2829]将人参来源的达玛二烯合成酶基因(PgDDS),原人参二醇合成酶基因(CYP716A47)和拟南芥(Arabidopsis thaliana)来源的AtCPR1基因,导入酵母菌株中,并对相关基因tHMG1,ERG20,ERG9,ERG1等进行了系统调控,同时对相关密码子进行优化成功构建出了产原人参二醇的工程菌株,原人参二醇的产量1.2 g·L-1,较原始出发菌株产量提高了262倍。这是首次人参皂苷重要前提物质原人参二醇在酵母中实现从葡萄糖的合成。接着该团队构建了同时可以生产原人参二醇、原人参三醇以及齐墩果酸的酵母菌株,其发酵产量可以生产17.2 mg·L-1的原人参二醇,15.9 mg·L-1的人参三醇以及21.4 mg·L-1的齐墩果酸,实现酵母细胞同时生产多种人参功效成分。
2015年,Zhou等[26]成功克隆出了糖基转移酶(UGT)的UGTPg1基因,该基因可以催化原人参二醇合成人参皂苷CK这一物质,CK被证实是人参皂苷进入血液中起功效的活性成分,在鉴定这一基因后,该团队在酵母细胞中组装了人参皂苷CK合成途径的基因,最终利用酵母细胞成功生产人参皂苷CK。接着,基于人参的转录组数据,该团队在进一步的工作中鉴定了UGTPg45和UGTPg29这2个糖基转移酶的基因,UGTPg45在原人参二醇的3号碳位的羟基上加入葡萄糖,形成人参皂苷Rh2, UGTPg29则是进一步催化人参皂苷Rh2形成人参皂苷Rg3,验证此2个基因的催化功能后,在酵母细胞中组装原人参二醇合成基因以及UGTPg45和UGTPg29,最终成功构建了产人参皂苷Rh2和Rg3的酵母菌株,尽管目标产物的生产浓度还比较低,都在μmol·gDCW-1的水平,但是这些工作为昂贵的单一人参皂苷生物合成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1.4 丹参酮
丹参酮是丹参中一类从唇形科植物丹参中提取得到的具有显著药理活性的脂溶性二萜化合物,包括丹参酮I、丹参酮ⅡA、丹参酮ⅡB、隐丹参酮、异隐丹参酮等10余种化合物,具有抑菌,抗炎,抗凝血等作用,是国际上广泛认可的用于治疗心脑血管疾病的天然药物之一[3031]。
二萜类化合物合成来自2个常见的前体物质:IPP和二甲基烯丙基焦磷酸(DMAPP)模块,它们在酵母中通过MEV途径合成。而大部分IPP和DMAPP前体物质进入麦角固醇合成路径。在此基础上,研究者们通过多种合成生物学策略来提高酵母中合成丹参酮的量,例如Dai等[32]研究表明过表达tHMGR基因和突变监控因子基因(upc2.1),可以增加FPP的供给量,但次丹参酮二烯合成量并未增加,反而积累了大量的鲨烯(78 mg·L-1)。与此相反,通过过表达融合基因FPP合酶(ERG20)和内源性的GGPP合酶基因(BTS1)以及来自酸热硫化叶菌的异源性的GGPP合酶基因(SaGGPS),次丹参酮二烯产量增加到了8.8 mg·L-1。过表达ERG20BTS1和SaGGPS基因将次丹参酮二烯产量从5.4 mg·L-1增加到了28.2 mg·L-1。过表达tHMGRupc2.1和ERG20BTS1SaGGPS在产次丹参酮二烯时具有协同作用,次丹参酮二烯产量61.8 mg·L-1,最后经流加培养发酵,次丹参酮二烯产量488 mg·L-1,为丹参酮的生物合成奠定了基础。丹参生物合成路径中的共同前体物质——次丹参酮二烯是由SmCPS和SmKSL催化合成。高伟等[3334]首次克隆了编码丹参柯巴基焦磷酸合酶(SmCPS)、丹参类贝壳衫烯合酶(SmKSL)的全长基因,随后将这2个基因通过模块组合的方式将SmCPS和SmKSL以及BTS1,ERG20,tHMG等5个基因导入酵母底盘细胞中,次丹参酮二烯产量达到365 mg·L-1。Guo 等[3536]鉴定了14个与次丹参二烯生物合成相关的CYP450基因,将CYP76AH1及来自于丹参的细胞色素还原酶基因SmCPR1和SmCPR2基因整合到产次丹参酮二烯的工程菌株中,铁锈醇合成量为10.5 mg·L-1,同时发现铁锈醇的产量和次丹参酮二烯的积累量呈负相关。随后通过进一步的共表达分析,又发现了丹参酮生物合成分支路径上的2个新的P450还原酶基因CYP76AH3和CYP76AK1,并通过生化方法以及RNA干扰技术表明CYP76AH3在2种不同的碳中心使铁锈醇氧化,CYP76AK1羟化产生的2个生成的中间体的C20,最终将铁锈醇氧化为11,20二羟铁锈醇,11,20二羟柳杉芬,进一步实现了对丹参酮中间产物的发现。
1.5 红景天苷
红景天苷(salidroside)是一种多元皂苷,为红景天Rhodiola rosea (也称为“西藏人参”)植物中最为重要的生物活性成分[3738],具有多种生理调节属性,如抗氧化、抗微波辐射、抗疲劳、抗病毒、抗肿瘤以及抗衰老等[3940]。然而红景天生存环境恶劣(一般生长在高海拔寒冷地区),传粉困难且生长缓慢,加之近年来的过多开发,野生红景天的资源正在枯竭的边缘[41],此外,红景天中红景天苷的质量分数相对较低,仅为0.5%~0.8%,远不能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需求。
研究表明,红景天苷属于酪氨酸代谢产物,其合成路径解析已较为清楚:来自于莽草酸途径的L酪氨酸通过酪氨酸脱羧酶(TDC)转化为酪胺;随后酪胺在酪醇氧化酶(TYO)和乙醇脱氢酶(ADH)的连续催化作用下进一步转换成红景天苷的苷元——酪醇[42],随后酪醇和尿苷二磷酸葡萄糖(UDPG)在尿苷二磷酸葡萄糖基转移酶(UDPglucosyltransferase,UGT)催化作用合成红景天苷。Bai等[43]成功运用酵母丙酮酸脱羧酶(ARO10),内源性ADHs, 来自红景天的糖基转移酶UGT73B6,第一次成功地在大肠杆菌中合成了红景天苷。随后经过一系列的基因操作,包括灭火特异性转录调节基因tyrR,删除丙酮酸激酶基因pykA和pykF以及分枝酸变位酶/预苯酸脱水酶基因pheA,过表达编码L络氨酸途径中各种酶的基因,包括分支酸变位酶/预苯酸脱氢酶的反馈抑制突变基因tyrA(tyrA×syn),脱氧阿拉伯糖型庚酮糖磷酸合酶的反馈抑制突变基因,即aroG(aroG×syn),磷酸烯醇丙酮酸合酶基因(ppsA),转酮醇酶(tktA),莽草酸脱氢酶(aroE),3脱氢奎尼酸脱水酶基因(aroD)和优化后的3脱氢奎尼酸合酶基因(aroBop),有效的提升酪醇生产效率,红景天苷最高产量达56.9 mg·L-1,为红景天苷合成提供了一个操作简单,经济效益高的,可用于大规模生产的方法。另外,该研究同时还表明从红景天中提取的糖基转移酶UGT73B6通过将葡萄糖添加到酪醇的酚醛位置来催化淫羊藿次苷D2的形成,这是关于淫羊藿苷的产物生物合成的报道。
2 中药合成生物学策略
合成生物学是一门在基因工程、代谢工程等经典学科上发展起来的整合学科,是一门将生物学工程化的学科,其目的在于将复杂的自然生物代谢系统改造为由简单的可控的模块或零件,经计算机辅助设计对其进行模拟预测,从而构建出由天然或非天然的功能元件或模块组成的生物系统,实现生物系统在各领域的模块化应用。其基本思路是:首先,根据目标产物选择合适的底盘细胞,之后将设计好的目标产物合成途径在底盘细胞中进行重建,对所创建的合成途径进行模块式优化,并根据目标产物的产量调整优化策略,以达到合成途径和底盘生物的最优化适配,最终实现目标产物的大量合成。
2.1 中药功效成分合成路径的创建
目前,中药功效成分的合成途径构建可以分为2种模式,第一种模式是在充分了解目标天然代谢产物代谢途径的基础上,根据研究目的,将目的产物所在基原物种的生物合成途径转移到微生物中,利用底盘细胞中原有的或者重新构建的代谢途径大量生产目标产物;另一种模式是根据目标产物或其合成过程中的中间体的化学结构,利用已挖掘基因元件的功能,实现对目标产物的合成甚至生产自然界中不存在的化学物质。
2.1.1 原代谢途径的直接转移 对原代谢途径的直接转移,重构和工程化这种模式对新代谢途径的构建可分为3种方式[44]。
第一种方式是将来源不同的与目标产物合成有关的基因整合到底盘细胞中,利用底盘生物的主要和次要代谢所提供的前体物质,然后通过异源基因的表达将其转化为目标产物。这种基于基因工程基础上的构建方式是目前最为简单的构建方式,被广泛的应用到了不同的底盘细胞中去,但它的目的主要是对所设计的代谢途径在不同底盘细胞中重构的可行性进行检验。
第二种代谢方式也是基于底盘细胞固有的中间体供应机制,在第一种方式的基础上,还导入了中药功效成分生物合成模块和底物调控模块,通过调节底物合成量来达到提高目标产物的合成量。如Dai等[2829]在构建产原人参二醇的工程菌株时,除了导入PgDDS,CYP716A47以及AtCPR1基因外,同时通过对相关基因tHMG1,ERG20,ERG9,ERG1等进行了系统调控,原人参二醇的产量1.2 g·L-1,较原始出发菌株产量提高了262倍;Donald等[12]将截短了的HMGR1基因(tHMGR)导入酿酒酵母中,增加了HMGR1的表达量从而使青蒿素的前体物质角鲨烯的合成量大大提高。
第三种方式是在前2种方式基础上,同时导入底物合成模块、底物调控模块以及中药功效成分生物合成模块,这种方式可以不依赖于底盘细胞的底物供应,既可以在无底物供应的情况下完成目标产物或其前体物质的合成外,还可以同时利用底盘细胞供应的前体以及新引入的底物供应途径提供的底物进行目标产物及其中间体的合成。最经典的是Keasling实验小组在构建的产紫穗槐4,11二烯的大肠杆菌中,将来自于酿酒酵母的甲羟戊酸合成模块(底物调控模块)、FPP 合成模块(底物合成模块)以及紫穗槐4,11二烯合成模块(中药功效成分生物合成模块)这3个模块同时导入底盘菌株中,成功构建了产青蒿素前体物质紫穗槐4,11二烯的工程菌株,后经优化操作,紫穗槐4,11二烯产量达27.4 g·L-1[10]。Ajikumar等[25]将紫杉醇生物合成途径分为2个模块,即:产IPP的内源性MEP途径的上游模块和合成异源萜类化合物途径的下游模块。将下游模块导入底盘细胞中并过表达上游模块,经最后优化后,紫杉醇二烯合成量最高达1.02 g·L-1。
2.1.2 产目标中药功效成分的新合成路径的创建 这种模式是基于对所需合成的目标产物或其中间体的化学结构了解比较清楚的情况下,在底盘细胞中对中药功效成分或中间体的合成路径进行重新设计,然后根据这条路径从基因数据库中筛选出与目标产物合成有关联的酶基因,将这些酶基因导入受体细胞中,在底盘细胞中进行组装、表达,从而构建出一条全新的、与原植物中的合成路径相差很大的合成路径。采用这种模式构建的代谢途径与原底盘细胞中固有的代谢途径相差比较大,不需要对代谢途径有太深入的了解。上述1.5项中红景天苷和淫羊藿苷的合成都是这一方式的典型案例。
2.2 对中药功效成分合成路径计算机模拟设计
当选定要生产的目标产物时,首先要确定该产物的最优合成途径。伴随着新一代的测序技术以及生物信息学分析技术的发展为合成路径的发现提供了一个新的选择,即参考代谢流分布,设计一些启发式的假设(如菌体最大生长量、产物最大合成量等),进行通量平衡分析(FBA),最小代谢调整分析(MOMA)等in silico分析方法,通过各种各样的依靠大规模的细胞代谢模型其他工作对细胞代谢进行系统的模拟操作,通过计算机模拟出最高的物质产出(流平衡分析),确定最优的合成途径。目前,化学计量的基因组尺度代谢模型是最常用的一种模型,它能够对整体代谢网络进行深入的思考以及对如何将中央路径引入到其他细胞的新陈代谢中[45]。
最早最简单的关于化学计量模型(基因尺度或非基因尺度)是发现产品的最大理论产量和最高产量的中代谢的流量分布。Opt Strain算法可以搜索反应数据库,找到可以添加到网络提高理论产量额外的反应。这些方法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例如二氢青蒿酸的生产[46]。Alper等[47]通过应用MOMA方法,鉴定并通过实验证实了缺失7个基因的E.coli JE660菌株中番茄红素的合成量显著提高(比原菌株高约40%),成功完成了对大肠杆菌中能够改善番茄红素合成量的靶基因位点的预测及鉴定工作;2011年,Song等[48]利用基因组规模代谢网络和流量平衡分析,确定2个氨基酸和4个维生素作为必要化合物补充到培养基中,将改善曼琥珀酸的产量(比原培养基中提高15%)。Sun等 [49]提出了一种基于约束条件,通过计算机模拟生物可达到的最佳反应速率,基于模拟结果,确定能够改善萜类物质潜在的敲除位点,结果表明,相比野生型,大多数单突变体产生紫穗槐二烯的产率增加8~10倍。
2.3 对所创建的代谢途径的优化调控
将基因导入到底盘细胞后,需要对其所产生的一系列不良反应[5055],采取一定的应对措施进行优化调控。第一个要解决的障碍是确保导入基因的协调表达,异源合成途径导入过程往往会打破微生物在长期的自然进化过程中所形成的代谢方式,破坏细胞内基因表达的动态平衡,造成上下游途径的不适配性,引起中间代谢物尤其是有毒中间代谢物的大量积累,造成细胞毒性,严重影响细胞的正常生长,致使目标产物无法高效合成[50],同时也会影响细胞自身的生长繁殖[51]。这可以通过正确选择包括启动子的调节组分和转录终止子,以及核糖体结合位点,分别控制转录和翻译速率;另一方面,由于底盘细胞无法自发的对外源基因的表达进行调控,因此还会诱发一系列的不良反应如严谨反应,热激反应,压力反应等[5254],而这些不良反应又会造成细胞的多种改变如质粒不稳定,细胞裂解以及遗传信息的改变等[55]。为了避免这些因素对产物合成的影响,必须对所构建的工程菌株进行优化。
2.3.1 启动子 一般来讲,协调多基因表达最常用的方法就是采用不同的启动子对不同的基因分别进行调控。目前常用的启动子分为2类:组成型启动子和诱导型启动子。组成型启动子是一类可以在保持下游基因持续表达的启动子,并且不需要任何诱导剂,其表达系统最为经济简便,对于比较低廉的化学品以及药物来说,使用组成型启动子可以节约成本。但是过早的表达产物会对细胞造成毒害作用,影响宿主细胞的生长,甚至会导致宿主细胞的死亡。因而,在利用工程菌生产中药功效成分时,大多用的还是诱导型启动子,这也是协调多基因表达最直接,最简单的方法。Van Dien S J等[56]在大肠杆菌中用Ptac启动子控制大肠杆菌多聚磷酸盐激酶(PPK)的表达,同时用另一诱导型启动子PBAD对聚磷酸酶(PPX)基因的表达进行调控,通过在菌株的不同生长时期添加不同的诱导剂,对两基因在不同的时期进行表达实行了简单的调控。但在实际运用中,诱导型启动子只能对基因的表达起到粗略的调控,即对所控制的基因实行全部开启或全部关闭,而不能实现对基因表达的精细调控;另一方面,诱导型启动子的数量以及诱导剂之间的相互干扰也极大的限制了这一方法的大规模应用。针对这一问题,科学家们首先想到的是对启动子进行改造,即应用启动子工程,构建出能够满足不同表达强度需求的启动子库。ReddingJohanson等在构建产倍半萜烯紫山槐4,11二烯的大肠杆菌工程菌株时,甲羟戊酸激酶(MK)和磷酸甲羟戊酸激酶(PMK)2种蛋白质的表达水平非常低。为了克服这一瓶颈,对MK和PMK基因进行密码子优化以及替换强启动子,这些变化显著提高了紫山槐4,11二烯的产量(4 500 mg·L-1)[57]。另外就是通过筛选得到能够响应同一诱导物的具有不同表达强度的诱导型启动子,从而避免不同诱导剂之间的相互干扰,如Ajikumar等[25]利用代谢工程多元模块法生产紫杉醇二烯实验中,上游模块就是由Trc启动子控制MEP途径的4个关键酶基因(dxs, idi,ispD和ispF)。但该方法所能利用的启动子库非常少。
2.3.2 建立动态平衡 在合成路径的构建往往会增加几个数量级的前体途径的代谢流,即使是细胞本源的代谢路径,也会使酶活性水平的失衡,导致代谢物浓度的巨大波动。例如,在利用酵母中异戊二烯途径产青蒿素过程中,会有2个中间体在这个途径导致细胞生长抑制,一是HMGCoA,它会在脂肪酸生物合成路径中导致反馈抑制,这是由于它和malonylCoA的相似性所导致的;一个是倍半萜的直接前体物质法呢基焦磷酸(FPP)。而FPP代谢流需要很大才能满足萜类物质大量合成的要求,当下游途径的表达模块与FPP供应量不能相协调时,FPP的积累会造成细胞毒性,对细胞生长造成威胁,同时,目标产物的合成也受到影响。针对这一问题,Dahl等[58]将来源于大肠杆菌的对FPP压力起负调控的启动子被用来调控上游乙酰辅酶A硫解酶(atoB),而对其起正调控启动子被用来调控下游ads的表达,通过设计紫槐二烯途径以及甲羟戊酸途径的动态回路,成功促进了紫槐二烯的合成;Yuan等[59]利用实时定量PCR对酿酒酵母中基因的表达进行了探究,发现当细胞中麦角固醇积累时,羊毛甾醇14α去甲基化酶(ERG11)、C8甾醇异构酶(ERG2)、C5 甾醇去饱和酶(ERG3)这3个基因的表达是下调的,并对调控这些基因的启动子进行了鉴定,利用这些响应启动子对ERG9的表达进行调控,萜类合成量提可高2~5倍。
2.3.3 操纵子策略 在原核生物中,多个相关基因在表达是往往会被组合成一个操纵子,而操纵子基因之间的序列能够直接影响mRNA的加工以及稳定性。合成生物学运用这一特性,用一个启动子对多个基因进行表达进行调控。Pfleger等通过改变基因间的区域(tunable intergenic regions,TIGRs)这一方法,成功实现了对同一个操纵子中多个不同基因的精确调控。该方法通过构建包含mRNA二级结构、RNA酶切位点以及核糖体结合位点的TIGRs库,对这些调控元件进行适当的组合,得到最优化的DNA序列,Pfleger等利用该方法,对大肠杆菌中异源的甲羟戊酸途径中的3个基因的表达量进行了平衡调控,最终,甲羟戊酸产量提高了7倍[60]。
2.3.4 支架蛋白 支架蛋白是存在于生物信号转导系统中的一种不具备酶活性的蛋白质,能同时将2个或多个功能相关的蛋白质结合在一起,从而保证了信号传递的特异性和高效性。以该理论为基础,通过人工设计支架蛋白,对代谢途径中相关酶进行优化和改造,把功能相关的酶形成可控的复合体,通过对代谢途径中基因表达的精密调控,在提高底物的有效浓度的同时,解决细胞毒性以及代谢压力的问题,最终达到提高底物转化效率的目标。Keasling实验小组[50]根据大肠杆菌工程菌中所构建的甲羟戊酸途径,设计构建了一个由3个不同配基组成的支架蛋白,同时对该途径中的3个合成酶atoB、羟甲基戊二酰CoA合酶(HMGS)、HMGR添加了相应的配体,通过改变支架蛋白上配基的数量来改变着3个酶的化学计量数,从而达到平衡代谢流、减少细胞负荷的目的,同时甲羟戊酸生产浓度提高了77倍。虽此方法可以对代谢流进行精密高效的控制,但自然界中的支架蛋白只存在于其固有的信号途径中,而对其进行设计及改造十分局限,实施起来难度较高,目前成功的例子很少。
3 展望
中药功效成分的获取,无论是从中药中提取,还是化学合成、半化学合成以及一些其他方法等,这些方法都有很大的局限性,同时无法满足人类对中药功效成分的需求。合成生物学方法利用微生物易于培养等特点生产中药功效成分,为其可持续利用提供了一个新的可行的方法。虽然合成生物学起步较晚,但发展迅猛,各种高效、简便的生物学技术也相继诞生,如高通量测序技术、不同尺度的DNA组装技术以及一些文库,如启动子文库、核糖开关文库等的建立,都极大的推动了该方法的发展。通过合成生物学技术,利用微生物发酵来进行中药功效成分的异源合成已经取得的一系列成果,如青蒿素、人参皂苷、丹参酮等的生物学合成,尤其是青蒿素的生物合成方面更是显示出了其在中药功效成分合成方面的巨大优势和潜力,为中药领域的开发注入了新的活力。
尽管利用合成生物学生产中药功效成分近几年取得了很大进展,但这一领域同样存在很大的困难和问题,最主要的是目标产物的产量达不到工业化的需求,很多中药功效成分的合成还处于实验室合成阶段,在产量比较低的情况,造成目的产物生产成本比较高,因此目前而言,合成生物学技术生产功效成分适用于那些资源短缺、植物中含量低且比较贵重的中药功效成分。另外,中药功效成分生源合成途径的解析限制了利用合成生物学进行生产这些成分,尽管目前已有青蒿素、人参皂苷等成分的合成途径解析,但是中药大部分功效成分的解析依然存在很大的困难,进展缓慢,这严重限制了合成生物学在合成中药功效成分上的利用,因此实现目标产物产量的提高和更多中药功效成分生物合成途径的解析应是未来合成生物学生产中药功效成分的重点研究方向。
[参考文献]
[1] Julsing M K, Koulman A, Woerdenbag H J, et al. Combinatorial biosynthesis of medicinal plant secondary metabolites[J]. Biomol Eng, 2006, 23(6):265.
[2] Qiu J. Traditional medicine:a culture in the balance[J]. Nature, 2007, 448(7150):126.
[3] Sakurai Y, Kolokoltsov A A, Chen C C, et al. Twopore channels control Ebola virus host cell entry and are drug targets for disease treatment[J]. Science, 2015, 347(6225):995.
[4] Liu J, Lee J, Hernandez M A S, et al. Treatment of obesity with celastrol[J]. Cell, 2015, 161(5):999.
[5] Wang P, Wei Y, Fan Y, et al. Production of bioactive ginsenosides Rh2 and Rg3 by metabolically engineered yeasts[J]. Metab Eng, 2015, 29:97.
[6] 陈士林,宋经元.本草基因组学[J].中国中药杂志,2016,41(21):3381.
[7] Martin V J J, Pitera D J, Withers S T, et al. Engineering a mevalonate pathway in Escherichia coli for production of terpenoids[J]. Nat Biotechnol, 2003, 21(7):796.
[8] Tsuruta H, Paddon C J, Eng D, et al. Highlevel production of amorpha4, 11diene, a precursor of the antimalarial agent artemisinin, in Escherichia coli[J]. PLoS ONE, 2009, 4(2):e4489.
[9] Ro D K, Paradise E M, Ouellet M, et al. Production of the antimalarial drug precursor artemisinic acid in engineered yeast[J]. Nature, 2006, 440(7086):940.
[10] Lindahl A L, Olsson M E, Mercke P, et al. Production of the artemisinin precursor amorpha4, 11diene by engineered Saccharomyces cerevisiae[J]. Biotechnol Lett, 2006, 28(8):571.
[11] Zhang Y, Teoh K H, Reed D W, et al. The molecular cloning of artemisinic aldehyde Delta11(13) reductase and its role in glandular trichomedependent biosynthesis of artemisinin in Artemisia annua[J]. J Biol Chem, 2008, 283(31):21501.
[12] Donald K A, Hampton R Y, Fritz I B. Effects of overproduction of the catalytic domain of 3hydroxy3methylglutaryl coenzyme A reductase on squalene synthesis in Saccharomyces cerevisiae[J]. Appl Environ Microbiol, 1997, 63(9):3341.
[13] Pitera D J, Paddon C J, Newman J D, et al. Balancing a heterologous mevalonate pathway for improved isoprenoid production in Escherichia coli [J]. Metab Eng, 2007, 9(2):193.
[14] Graham I A, Besser K, Blumer S, et al. The genetic map of Artemisia annua L. identifies loci affecting yield of the antimalarial drug artemisinin[J]. Science, 2010, 327(5963):328.
[15] Singh N D, Kumar S, Daniell H. Expression of βglucosidase increases trichome density and artemisinin content in transgenic Artemisia annua plants[J]. Plant Biotechnol J, 2015, 14(3):1034.
[16] Zhan Y, Liu H, Wu Y, et al. Biotransformation of artemisinin by Aspergillus niger[J]. Appl Microbiol Biotechnol, 2015, 99(8):3443.
[17] Paddon C J, Westfall P J, Pitera D J, et al. Highlevel semisynthetic production of the potent antimalarial artemisinin[J]. Nature, 2013, 496(7446):528.
[18] Phillipson J D. Phytochemistry and pharmacognosy[J]. Phytochemistry, 2007, 68(22):2960.
[19] Wani M C, Taylor H L, Wall M E, et al. Plant antitumor agents. VI. Isolation and structure of taxol, a novel antileukemic and antitumor agent from Taxus brevifolia[J]. J Am Chem Soc, 1971, 93(9):2325.
[20] Zaiyou J, Li M, Guifang X, et al. Isolation of an endophytic fungus producing baccatin Ⅲ from Taxus wallichiana var. mairei[J]. J Ind Microbiol Biotechnol, 2013, 40(11):1297.
[21] Jennewein S, Croteau R. Taxol:biosynthesis, molecular genetics, and biotechnological applications[J]. Appl Microbiol Biotechnol, 2001, 57(1/2):13.
[22] Altavilla A, Iacovelli R, Procopio G, et al. Medical strategies for treatment of castration resistant prostate cancer (CRPC) docetaxel resistant[J]. Cancer Biol Ther, 2012, 13(11):1001.
[23] Denis J N, Greene A E, Guenard D, et al. Highly efficient, practical approach to natural taxol[J]. J Am Chem Soc, 1988, 110(17):5917.
[24] Huang Q, Roessner C A, Croteau R, et al. Engineering Escherichia coli for the synthesis of taxadiene, a key intermediate in the biosynthesis of taxol[J]. Bioorg Med Chem, 2001, 9(9):2237.
[25] Ajikumar P K, Xiao W H, Tyo K E J, et al. Isoprenoid pathway optimization for taxol precursor overproduction in Escherichia coli[J]. Science, 2010, 330(6000):70.
[26] Zhou K, Qiao K, Edgar S, et al. Distributing a metabolic pathway among a microbial consortium enhances production of natural products[J]. Nat Biotechnol, 2015, 33(4):377.
[27] 何道同,王兵,陈珺明.人参皂苷药理作用研究进展[J].辽宁中医药大学学报,2012,14(7):118.
[28] Dai Z, Yi L, Zhang X, et al. Metabolic engineering of Saccharomyces cerevisiae for production of ginsenosides[J]. Metab Eng, 2013, 20(5):146.
[29] Dai Z, Wang B, Liu Y, et al. Producing aglycons of ginsenosides in bakers′ yeast[J]. Sci Rep, 2014, 4(4):3698.
[30] Robertson A L, Holmes G R, Bojarczuk A N, et al. A zebrafish compound screen reveals modulation of neutrophil reverse migration as an antiinflammatory mechanism[J]. Sci Transl Med, 2014, 6(225):225ra29.
[31] Dong Y, MorrisNatschke S L, Lee K H. Biosynthesis, total syntheses, and antitumor activity of tanshinones and their analogs as potential therapeutic agents[J]. Nat Prod Rep, 2011, 28(3):529.
[32] Dai Z, Liu Y, Huang L, et al. Production of miltiradiene by metabolically engineered Saccharomyces cerevisiae[J]. Biotechnol Bioeng, 2012, 109(11):2845.
[33] 高伟. 丹参酮类化合物生物合成相关酶基因克隆及功能研究 [D]. 北京:中国中医科学院, 2008.
[34] Gao W, Hillwig M L, Huang L, et al. A functional genomics approach to tanshinone biosynthesis provides stereochemical insights[J]. Org Lett, 2009, 11(22):5170.
[35] Guo J, Zhou Y J, Hillwig M L, et al. CYP76AH1 catalyzes turnover of miltiradiene in tanshinones biosynthesis and enables heterologous production of ferruginol in yeasts[J]. Proc Natl Acad Sci USA, 2013, 110(29):12108..
[36] Guo J, Ma X, Cai Y, et al. Cytochrome P450 promiscuity leads to a bifurcating biosynthetic pathway for tanshinones[J]. New Phytologist, 2016, 210(2);525.
[37] Qu Z, Zhou Y, Zeng Y, et al. Protective effects of a Rhodiola crenulata extract and salidroside on hippocampal neurogenesis against streptozotocininduced neural injury in the rat[J]. PLoS ONE, 2012, 7(1):e29641.
[38] Yang Y, Liu Z, Feng Z, et al. Lignans from the root of Rhodiola crenulata[J]. J Agric Food Chem, 2012, 60(4):964.
[39] Mao G X, Deng H B, Yuan L G, et al. Protective role of salidroside against aging in a mouse model induced by Dgalactose[J]. Biomed Environ Sci, 2010, 23(2):161.
[40] Ouyang J F, Lou J, Yan C, et al. Invitro promoted differentiation of mesenchymal stem cells towards hepatocytes induced by salidroside[J]. J Pharm Pharmacol, 2010, 62(4):530.
[41] Yan Z Y T. Ecological analysis on sexual reproductive produce and endangered reason of Rhodiola sachalinensis[J]. Bull Botan Res, 1998,18(3):336.
[42] Satoh Y, Tajima K, Munekata M, et al. Engineering of a tyrosolproducing pathway, utilizing simple sugar and the central metabolic tyrosine, in Escherichia coli[J]. J Agric Food Chem, 2012, 60(4):979.
[43] Bai Y, Bi H, Zhuang Y, et al. Production of salidroside in metabolically engineered Escherichia coli[J]. Sci Rep, 2014, 4:6640.
[44] Kong J Q, Wang W, Cheng K D, et al. Research progresses in synthetic biology of artemisinin[J]. Acta Pharm Sinica, 2013, 48(2):193.
[45] King Z A, Lloyd C J, Feist A M, et al. Nextgeneration genomescale models for metabolic engineering[J]. Curr Opin Biotechnol, 2015, 35:23.
[46] Misra A, Conway M F, Johnnie J, et al. Metabolic analyses elucidate nontrivial gene targets for amplifying dihydroartemisinic acid production in yeast[J]. Front Microbiol, 2013, 4:200.
[47] Alper H, Jin Y S, Moxley J F, et al. Identifying gene targets for the metabolic engineering of lycopene biosynthesis in Escherichia coli[J]. Metab Eng, 2005, 7(3):155.
[48] Song H, Kim T Y, Choi B K, et al. Development of chemically defined medium for Mannheimia succiniciproducens based on its genome sequence[J]. Appl Microbiol Biotechnol, 2008, 79(2):263.
[49] Sun Z, Meng H, Li J, et al. Identification of novel knockout targets for improving terpenoids biosynthesis in Saccharomyces cerevisiae[J]. PLoS ONE, 2014, 9(11):e112615.
[50] Zhu M M, Lawman P D, Cameron D C. Improving 1, 3propanediol production from glycerol in a metabolically engineered Escherichia coli by reducing accumulation of snglycerol3phosphate[J]. Biotechnol Prog, 2002, 18(4):694.
[51] Dueber J E, Wu G C, Malmirchegini G R, et al. Synthetic protein scaffolds provide modular control over metabolic flux[J]. Nat Biotechnol, 2009, 27(8):753.
[52] Wick L M, Egli T. Molecular components of physiological stress responses in Escherichia coli[J]. Adv Biochem Eng Biot, 2004,89:1.
[53] Harcum S W, Bentley W E. Heatshock and stringent responses have overlapping protease activity in Escherichia coli[J]. Appl Biochem Biotechnol, 1999, 80(1):23.
[54] Gill R T, Valdes J J, Bentley W E. A comparative study of global stress gene regulation in response to overexpression of recombinant proteins in Escherichia coli[J]. Metab Eng, 2000, 2(3):178.
[55] Wang J, Qi Q. Synthetic biology for metabolic engineering——a review[J]. Chin J Biotechnol, 2009, 25(9):1296.
[56] Van Dien S J, Keasling J D. Optimization of polyphosphate degradation and phosphate secretion using hybrid metabolic pathways and engineered host strains[J]. Biotechnol Bioeng, 1998, 59(6):754.
[57] ReddingJohanson A M, Batth T S, Chan R, et al. Targeted proteomics for metabolic pathway optimization:application to terpene production[J]. Metab Eng, 2011, 13(2):194.
[58] Dahl R H, Zhang F, AlonsoGutierrez J, et al. Engineering dynamic pathway regulation using stressresponse promoters[J]. Nat Biotechnol, 2013, 31(11):1039.
[59] Yuan J, Ching C B. Dynamic control of ERG9 expression for improved amorpha4, 11diene production in Saccharomyces cerevisiae[J]. Microb Cell Fact, 2015, 14:38.
[60] Pfleger B F, Pitera D J, Smolke C D, et al. Combinatorial engineering of intergenic regions in operons tunes expression of multiple genes[J]. Nat Biotechnol, 2006, 24(8):1027.
[责任编辑 孔晶晶]
——青蒿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