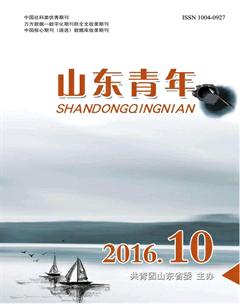WTO协定及DSB裁决在欧盟法律体系中的效力
宋俊荣�オ�
摘要:根据欧洲法院的判例,不论WTO协定还是DSB裁决在欧盟法律体系中均不具有直接效力。这意味着,当个人因欧盟所采取的违背WTO规则的措施而遭受经济损失时,无法直接援引WTO协定及DSB裁决来获取救济。欧洲法院的这一做法顾全了欧盟的整体利益,但牺牲了个人利益。目前较具可行性的建议是适用非过错责任原则来追究欧盟的损害赔偿责任。
关键词:WTO协定、欧盟法、直接效力
WTO协定及DSB(Dispute Settlement Body,即争端解决机构)裁决在WTO成员方法律体系中的地位和效力是一个非常重要和敏感的问题。一方面,它关系到WTO规则的有效性、稳定性和可预见性。另一方面,它还关系到WTO成员方的主权,以及受WTO成员方的贸易措施所影响的个人的切身利益。①本文主要从保护个人利益的角度来考察WTO协定及DSB裁决在欧盟法律体系中的效力。即,个人是否可以直接援引WTO协定及DSB裁决来质疑欧盟相关机构所采取的贸易措施?
一、国际条约在欧盟法律体系中的效力
《欧洲联盟运行条约》中涉及到国际条约与欧盟法之间关系的条款主要有第216条第(2)款和第218条第(11)款。欧洲法院对这两项条款的解读分别是:经签署的国际条约生效后构成欧盟法律体系的一部分;国际条约在欧盟法律体系中的位阶在一级法律和二级法律之间。由此似乎可以推断,欧盟二级法律与已生效国际条约不符的,应属无效。受到该二级法律影响的个人应当可以获得法律上的救济。但事实并没有这么简单。个人是否可以依据国际条约来质疑欧盟二级法律及相关执行措施,还要取决于该国际条约是否具有直接效力。“直接效力”这一概念最早是由欧洲法院在审理van Gend en Loos案时提出的,是指某些欧盟法所具有的无需欧盟成员国进一步立法就可以直接适用的效力。其效果在于,在向欧盟成员国法院提起的诉讼中,个人可以直接援引欧盟法的规定来主张自己依据该法所享有的权利、挑战成员国的国内立法和行政机构的行政行为。②后来,直接效力的概念扩大适用到国际条约与欧盟法之间的关系。根据欧洲法院的审判实践,国际条约是否具有直接效力首先取决于条约自身的规定。如条约自身缺乏这方面的规定,则必须具备以下条件才可以被认定为具有直接效力:综合考虑条约条款的用语、及条约的目的和性质,条约的条款设定了明确而确切的义务,且该义务的履行不依赖于任何后续措施。③ 由于WTO协定及其前身GATT1947(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均未就其自身在成员方国内法中的效力做出规定,因此,它们在欧盟法律体系中的效力就取决于欧洲法院在审判实践中的认定了。
二、欧洲法院有关WTO协定及DSB裁决之效力的判例
(一) Biret案
2002年的Biret案是首例个人援引DSB裁决提起损害赔偿之诉的案件。从20世纪80年代起,欧共体颁布了一系列禁止含荷尔蒙牛肉进口的指令。本案原告Biret International 公司和Etablissements Biret公司因此而蒙受了巨大的损失,并于1995年12月进入破产程序。与此同时,美国和加拿大在WTO框架下对欧共体的进口禁令提起了申诉,1998年2月生效的DSB裁决判定该禁令违反了WTO规则。欧共体随即表示愿意执行裁决,但需要合理执行时间。经裁决,合理执行时间于1999年5月13日截止。2000年6月,本案原告的破产清算人代表原告向欧洲初审法院提起非契约责任之诉,但以败诉收场。随后,两家公司向欧洲法院提起上诉。本案的法律顾问(Advocate General ) Alber表示,当DSB裁决判定欧共体的某项措施不符合WTO规则,且欧共体未能在合理执行时间执行该裁决时,该DSB裁决和相关WTO规则就具有直接效力,应当可以作为个人向欧共体机构提起损害赔偿的法律依据。④遗憾的是,欧洲法院并未采纳Alber的意见。首先,欧洲法院重申了其在葡萄牙诉理事会案中的立场,并排除了Fediol原则和Nakajima原则在本案中的适用。接着,欧洲法院指出,作为上诉方的两家公司已于1995年进入破产程序,而欧共体执行DSB裁决的合理执行时间于1999年才截止。所以,上诉方不可能因为欧共体被DSB裁定为与WTO规则不符的行为而遭受损失。⑤因此,本案最终以上诉方败诉收场。但是,对于个人在合理执行时间届满后援引DSB裁决主张损害赔偿的可能性,人们还是心存期望的。不过,这种期望在Van Parys先行裁决案中彻底破灭了。
(二) Van Parys案
本案原告是一家从事香蕉进口的比利时公司,已连续20多年从厄瓜多尔和巴拿马进口香蕉。1999年1月和3月,即欧共体——香蕉案III的合理执行时间届满之后,本案原告两次向比利时干预和退税局(Belgian Intervention and Refund Bureau)申请从厄瓜多尔和巴拿马进口一定数量香蕉的许可证,但只有其中部分数量得到了许可。1999年2月和5月,原告向比利时最高行政法院两次提起诉讼,主张比利时干预和退税局的决定是非法的,因为其依据的欧共体条例已被DSB裁决判定为与WTO规则不符。由于涉及到欧共体条例的效力,比利时最高行政法院于2002年10月就此问题提请欧洲法院先行裁决。首先,欧洲法院再次申明,WTO协定原则上在欧共体法律体系中不具有直接效力。然后,欧洲法院对于在本案中首次出现的合理执行时间已经届满后DSB裁决的效力问题进行了分析。欧洲法院指出,WTO争端解决机制非常注重鼓励争端当事方之间通过谈判解决争端,即使DSB裁决已经判定某WTO成员方的措施违背了WTO规则。如果败诉方未在合理执行时间内执行DSB裁决,它可与胜诉方就补偿问题进行谈判。如谈判未果,胜诉方还可向DSB申请授权报复。因此,合理执行时间届满并不意味着欧共体就穷尽了与胜诉方共同寻求争端解决的所有办法。如果欧洲法院仅仅因为合理执行时间届满就依据DSB裁决和相关WTO规则来审查欧共体措施的合法性,就会剥夺欧共体与胜诉方寻求共同满意之解决办法的机会。此外,欧共体的大多数重要贸易伙伴均未承认WTO协定和DSB裁决的直接效力。如果欧洲法院单方面认可WTO协定和DSB裁决的直接效力,就会有违互惠性原则,导致WTO规则在成员方之间适用的不对称。因此,欧洲法院最终认定,合理执行时间已经届满后的DSB裁决也不能作为衡量欧共体措施之合法性的依据。⑥
(三) Fiamm & Fedon案
本案的特别之处在于原告首次提出了以非过错责任原则(no-fault liability)为基础追究欧共体非契约责任的主张。它们首先主张,欧共体未在DSB规定的时限内使得欧共体法与WTO规则一致,违背了WTO规则以及欧共体法的一般原则,应被判定为非法。在此基础上,欧共体应承担非契约责任,向两公司进行赔偿。如果上述诉求未能得到支持,两公司主张以非过错责任原则为基础追究欧共体的非契约责任。两公司的上述诉求均遭到欧洲初审法院否决。2006年2月,两公司向欧洲法院提起上诉。欧洲法院强调,DSB裁决的目的无外乎判定被诉方的措施是否符合WTO规则,就是否能作为审查欧共体机构行为之合法性的依据而言,DSB裁决与实体性WTO规则无任何实质性区别。因此,两公司的第一个诉求不应得到支持。接着,欧洲法院转向两公司的第二个诉求,并指出了欧洲初审法院所犯的法律上的错误。欧洲初审法院承认在符合一定条件的情况下,即使不存在非法行为,也可追究欧共体机构的非契约责任。只是本案的相关事实不满足其中的条件,因而不可追究欧共体机构的非契约责任。欧洲法院则认为,以非过错责任原则为基础追究欧共体非契约责任并不是所有成员国法律体系所共有的法律原则。所以,在一般情况下,如果欧共体机构不存在非法行为,那么就无需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当然,例外也是有的。如果欧共体的某项立法以某种不相称、不可容忍的方式从实质上限制了公民的基本权利,诸如财产权、从事贸易或职业的自由等,那么欧共体应该为此承担非契约责任,予以赔偿。不过,欧洲法院指出,经济主体在某一特定时期拥有的市场份额并不能作为财产权的一部分,因为市场份额只是某一时刻经济状况的反映,随时都会随着环境的变化而波动。向欧盟之外的国家出口产品的经济主体应当意识到,其出口业务可能会遭受进口国依据WTO协定采取的贸易限制措施。因此,本案原告所称的市场份额流失的损失不属于对其财产权的侵犯,从而也不适用上述例外规定。⑦也就是说,本案中不能以非过错责任原则为基础追究欧共体非契约责任。至此,欧洲法院彻底断绝了个人直接援引WTO协定或DSB裁决挑战欧盟二级法律或欧盟机构行政行为的可能性。
三、结论与建议
对于欧洲法院否定WTO协定及DSB裁决具有直接效力的做法,肯定者有之,否定者亦有之。总的来说,争论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对欧盟立法机构和行政机构之独立性及其所代表的欧盟整体利益的考量;另一方面,是对相对处于弱势地位的个人之利益的同情。欧洲法院将天平倾向了欧盟机构及其所代表的欧盟整体利益,便有了WTO协定及DSB裁决不具有直接效力的结论。
从当前形势来看,欧洲法院不会轻易改变其有关WTO协定及DSB裁决不具有直接效力的结论。那么,欧洲法院在保护个人利益方面是不是就不能有所作为呢?就这个问题,不少专家学者提出了建议。其中比较具有代表性和可行性的建议是适用非过错责任原则来追究欧盟的损害赔偿责任。如此一来,欧洲法院就无需审查被诉措施的合法性,也就无需对被诉措施是否符合WTO规则做出表态、授人以柄了。可以说,这一建议既能照顾到个人利益,又能顾全欧盟的整体利益。此外,还有学者建议专门就适用非过错责任原则追究欧盟因WTO而产生的损害赔偿问题进行立法,以避免在其他领域可能造成的扩散效应。⑧上述建议是否会得到采纳,我们拭目以待!
[注释]
① 本文中的“个人”是一个广义的概念,包括自然人、法人及其他任何类型的经济组织。本文中的“贸易措施”泛指WTO成员方所采取的与贸易有关的任何措施,包括法律法规、行政管理措施等。
② Case 26/62 NVAlgemene Transporten Expeditie Ondememing van Gend en Loos v. Nederlandse Administratie der Belastingen [1963] ECR 1.
③ Case 12/86 Demirel v. Stadt Schwaebisch Gmund [1987] ECR 3719, para. 14.
④ Opinion of Advocate General Siegbert Alber in Cases C-93/02 P and C-94/02 P, CJE/03/39, 15 May 2003.
⑤ Cases C-94/02 and C-93/02, Biret International SA and Etablissements Biret et Cie. SA v. Council of the European Union, [2003] ECR I-10565.
⑥ Case C-377/02 Van Parys v Belgisch Interventie- en Restitutiebureau (BIRB) [2005] ECR 1-1465.
⑦ Joined cases C-120/06 P and C-121/06 P, Fabbrica italiana accumulatori motocarri Montecchio SpA(FIAMM), Fabbrica italiana accumulatori motocarri Montecchio Technologies Inc. (FIAMM Technologies) enGiorgio Fedon & Figli SpA, Fedon America, Inc. v. Council, [2008] ECR I-06513.
⑧ Marco Bronckers , “Sophie Goelen, Financial Liability of the EU for Violations of WTO Law: A Legislative Proposal Benefiting ‘Innocent Bystanders”, Legal Issues of Economic Integration, 2012(4), p.407.
(作者单位:上海政法学院国际法学院,上海 2017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