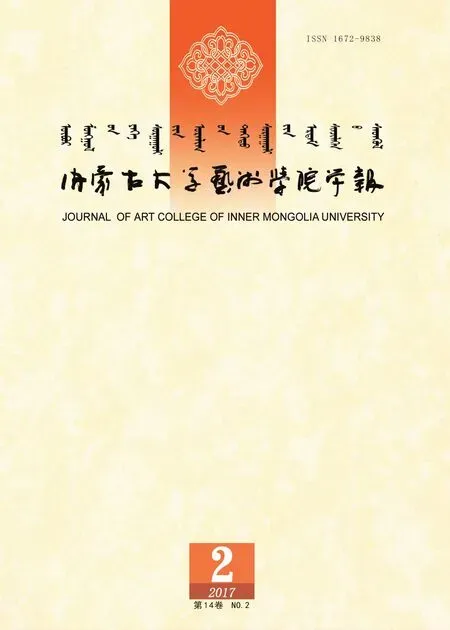浅议蒙古族宗教饰品的形制与审美取向
杨小晖
(内蒙古科技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视觉传达系,内蒙古 包头 014010)
浅议蒙古族宗教饰品的形制与审美取向
杨小晖
(内蒙古科技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视觉传达系,内蒙古 包头 014010)
作为蒙古族传统饰品的组成部分,宗教饰品有其独特的形制特征与内容丰富的民族审美情趣内涵。宗教饰品在仪式场域中通常有着重要的意义,这种意义既与极具象征意味的饰品本身形制有关,又是在民族自身审美文化之上的集中体现。与传统的蒙古族生活饰品对照来看,宗教饰品因其自身的特性使得其形制和材料有所不同,在传承与流变中彰显着民族文化价值。
蒙古族;宗教饰品;形制;审美取向
长期生活在北方草原上的蒙古人,对于宗教的信仰由来已久,蒙古人在历史上信仰的宗教有很多,在成吉思汗建立蒙古汗国之前及建立初期,萨满教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多桑蒙古史》中曾经有提到“自信有一主宰,并崇拜太阳,而遵从珊蛮教……”之后由于统治者采取了兼容并蓄的政策,北方草原上有了多种宗教的并存,如萨满教、道教、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等。在众多的宗教流派里,萨满教和藏传佛教的影响最为深远。因而众多的萨满教、佛教宗教观念渗入于民族习俗中来,如祭天、祭火、法会及其它民俗与宗教仪式等。蒙古族宗教饰品包括的内容丰富,藏传佛教饰品中有法铃、金刚杵、法鼓、法螺、念珠、佛龛等。而萨满教造型饰品中有法冠、神刀、翁衮、面具、铃铛、铜镜等。“北方游牧民族的原始宗教非常发达”[1](299)有着多深崇拜的观念,工艺饰品在宗教活动中的应用也很频繁,在佛教传入草原后,原始宗教的观念没有被彻底取代,反而与新的宗教结合,在宗教饰品上出现新的特点。在宗教仪式中,宗教饰品以其具体的形象、符号直观的让人可以感受到宗教礼仪的文化内涵。
宗教饰品相对于生活饰品来说,从使用的频率上来说必然不像生活饰品那么频繁,再加之使用人群的限定,它们的总量不多,其中有很大一部分为世代流传,而另一部分则为现当代所制造。由于现代文明推进,从事宗教活动的人群的减少,很多宗教饰品进入博物馆成为民俗文化的展示品。蒙古族宗教饰品在蒙古族传统饰品中占有的比重小,也不像生活饰品更容易作为现代工业产品的大量推广,在民族文化商店、旅游等场所随处可见,只有从少数的宗教活动从事者、寺庙、博物馆能够看得到蒙古族宗教饰品的存在。
宗教饰品由于有其自身的庄严性和神秘感,其制作规格有严格的程式。宗教饰品与生活饰品不同,其造型样式一般呈现出相对稳定的形象特征,但是这种稳定性与宗教教义的规范是否完备有关。与藏传佛教饰品相比,萨满教由于没有具体的法理和法典等较为规范性的依据,在近代和当代的传袭中发生了一定的流变。
一
蒙古族作为典型的生态民族,在宗教饰品的材质运用上有着就对材质本身特性的喜好以及就地取材的特点。一类由于蒙古族的对于宗教的信仰,使得他们对于材质选择偏向于使用贵金属,在历史上加之宗教曾经在政治中参与较多而受到统治阶层的尊崇,故金、银、铜等被视作制作宗教法器、礼器等饰品的首要材料。“宗教的价值大过其商品的价值”[2](377)对宗教和宗教内容的敬畏远远大于了物品本身,因此这些器物会选择贵金属来表达对于宗教的虔诚。另外一类则是根据就地取材的方法,选择生活里所比较容易取得的材质如:皮质、动物的骨骼,木质等。这一类材质有着物尽其用的现实意义,也更加贴近生活,从宗教的角度来看,用这些天然的材料所制成的饰品,被赋予了大自然的力量,符合蒙古族的崇拜观念。
对于选择金、银、铜作为传统的宗教饰品或生活饰品的制作材料,是游牧民族对于制作材质的特殊爱好。从色彩的构成来说,金色、银色是金、银、铜的固有色,金色在视觉上通常给人带来神圣、温暖、祥和的视知觉特征。银色被认为是明净、慈爱、纯洁的象征。游牧民族特别钟爱具有闪闪发光属性的金属,并将这些金属材质大量加入到生活中,从盛放事物的器皿,到服饰衣着的配饰,再到宗教祭礼的饰品,到处都有金属材质的出现。《禹贡》一书便记载着“唯金三品”,孔传:“金、银、铜也”。金、银、铜作为贵金属,在古代社会中是社会地位的呈现,而对于宗教的尊崇,使得人们在进行制作宗教饰品中大量的加入金、银、铜以示对于宗教教义的虔诚。
收藏于内蒙古通辽市民族博物馆中的藏传佛教的宗教法器两件骨号和一件金刚杵,是极具典型的佛教饰品,两件骨号通体为铜制,骨状前端为银制,中段为黑线所缠绕,中前端为铜制套筒,上面有银制镶嵌花卉图案,前端还有橙、白、红、蓝彩色布状飘带。金刚杵通体为铜制,三股,每股上面雕有植物纹样与金刚形象,中间连接部分有宝相花图案。三件宗教饰品器形精致,金属的金银色与飘带的彩色色彩搭配和谐,器物上的装饰纹样细致精美。骨号被视作是藏传佛教中的圣物之一,在进行重要的宗教仪式中吹奏使用。早期骨号的形体构造中有使用胫骨,外面包裹各种如金、银、铜的材质。由于金属的特殊的传导性,因此骨号在吹奏时会发出浑厚低沉略带有凄冷的听觉感受,这样的听觉感受在仪式中会增加宗教的庄严感和神秘性。
笔者曾经在科尔沁右翼后旗衙门营子萨满毛敖海家进行田野调查中发现一件世代流传的萨满饰品—铜腰镜,萨满腰镜是萨满在进行跳神时所穿戴的装束,用厚实的牛皮将铜镜排列之上并悬挂穿合,在萨满旋转时铜镜由于碰撞会发出金属碰撞的声响。萨满腰镜共有九面组成,每一面有着不同的图案和内容。和佛教饰品不同,萨满教饰品器物上虽然有一定的固定模式,如数量的规定,但在图案或形态构成中并无特定的要求。萨满腰镜便是如此,在数量上必须为九面,这是与萨满教中灵魂观的层级符合的。在具体的装饰和表现上,可以用素镜,也可以用花镜,素镜是没有图案和装饰的镜子,而花镜则在镜子上雕刻或铸有各式纹样。这些纹样当中有龙、蛇、植物花卉等蒙古族传统吉祥图案,也有一些宗教图案如万字纹、宝相花、回形纹等。
取生活中所接触到的材料作为饰品的制作材质是也是蒙古族传统饰品制作的一大特点,这与长期深居于草原人们所有的生态智慧有关。游牧民族将崇拜自然和利用自然完美结合,并将宗教观念与天地万物相关联,将日月星辰、山川河流、花鸟鱼虫等都视为是神秘力量的存在,然后将这样一种或者多种的自然属性无限的放大,置入于所制作的宗教饰品,以期取得强大的理想功能。
在内蒙古博物院宗教制品的展区中,有一件用动物骨骼所制成的佛珠,共有108颗,造型为骷髅头形状,通体打磨的洁白而富有光泽。此外还有一件清代的驼骨制成的佛教法衣,全部由大小相近的驼骨珠子经打磨后,串在一起,然后经过衣服的版式结构的样子组装而成,整体晶莹剔透,光泽度极好。在宗教和民俗信仰中,骆驼可以长时间穿行于浩瀚的沙漠,忍饥挨饿耐力又强,有着沙漠之神的称号,因此,将驼骨制成佛教饰品也象征着饰品所有的坚韧,顽强,坚持的品格。此外,还有其他动物的骨骼也常被作为佛教饰品,比如蛇骨、狼骨、牛骨等。
笔者曾经在科尔沁萨满毛敖海家看到过一件萨满仪式中必不可少的宗教饰品—萨满鼓,鼓柄为铁质,上面用红色的布条缠绕,鼓柄最下面为三个焊接在以其的铁环,而每个铁环上面还垂挂着三个小的铁环,这样的构造仍然与萨满教崇尚的灵魂观—“三界九重天”有关,而最重要的鼓面是用狗皮做的,取得了疯病的狗的皮所制成,因为据说这样的话萨满鼓这一法器会法力大增,此外用狼皮等其它动物的皮制作,应该也是取动物的凶猛的性格放置于宗教器物中,以渴望取得相应的功能。
蒙古族宗教饰品在图案应用上有几个类型:一为宗教图案,这类图案是宗教精神的物化体现,比如佛教中各类的佛像,依据具体的宗教仪式中功能的不同,大量的雕刻于各种器物之上,如一些佛牌、佛龛等。由于部分萨满教派别在近代接受了佛教教义,且萨满教没有很完备的法典法则,因此萨满教的饰品中所包含的宗教图案内容也多采用佛教的一些图案,如八宝中的盘肠、莲、鱼纹等,此外,象征着吉祥万寿的万字纹饰也常常出现在佛教和萨满教的宗教饰品中。第二类为图腾与祖先崇拜的图案题材,蒙古族在与自我社会生活中向来有着对生命敬仰的生存态度,这种生存态度的统一性就体现为对图腾崇拜和祖先崇拜。有关蒙古族对于图腾崇拜的史料文献并不具体,多为民族内部口口相传的为延续,图腾崇拜是原始文化的典型特征,这种典型特征就体现在蒙古族所信仰的“万物有灵”中来。在“万物有灵”的这一宗教信仰观念之下,其赋予了蒙古族崇拜的各种图腾所具有的生命力,《蒙古秘史》中对于苍狼、白鹿的描述就最为直接,此外,蒙古人崇拜的日月星辰、鹰、蛇、熊、水、火等都作为图腾崇拜的形象被刻画于宗教饰品当中,如佛教的传统法会查玛上,有各种图腾崇拜面具出现,萨满的腰带,鼓面和法器上也经常出现一些图腾的造型。对于祖先崇拜最早源自于萨满教,先为简单的崇拜祖先,继而发展为以翁衮为形式的祖先崇拜,到了元朝之后蒙古族共同的祖先崇拜对象就是成吉思汗了,人们对于祖先的崇拜多是因为先人的功绩,人们将先人当做祖先神来崇拜,将其形象描绘与饰品之上,以期望获取祖先的护佑。具体的形象在佛教的各种佛龛和唐卡中,萨满教的翁衮形象中,和萨满冠饰的饰片当中均有体现。第三类则是蒙古族的传统吉祥纹样,同蒙古族生活饰品一样,宗教饰品中也有着大量的吉祥图案的应用,其寓意着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愿景,如兰萨纹、寿纹、云纹、回形纹、以及植物花卉的吉祥纹样等。这一类图案纹饰主要作为辅助性纹样出现在宗教器物上,如佛教饰品中佛牌、佛珠的具体刻画上以及萨满饰品中裙带和冠帽中都有体现。
二
蒙古族的宗教饰品主要被运用于各种的宗教和民俗仪式上,源于宗教的信仰内容,北方游牧民族长期在草原上,以草原上所有的天地万物为生产资料,依赖大自然并将大自然的一切赋予无上的神力加以崇拜,这就体现了游牧民族朴素的生态观念。费尔巴哈曾经说过:“对自然的依赖感,再加上那种把自然看成是一个任意作为的,有人格的实体的想法,就是献祭这一自然宗教的基本行为的基础。”[2](460)游牧民族正是将自然人格化的观念放置于宗教信仰中,从而进行宗教献祭的行为,宗教饰品的用途由此而生。
蒙古族宗教饰品的审美取向首先是偏向于宗教的仪式功能的,仪式在特定的场域下营造出一种庄重的氛围,在这种氛围下所需要的礼器、乐器、法器是需要有着一定的能代表宗教教义形式的体现。宗教饰品在仪式在所承担的作用即时渲染一种情感,让这样的情感去感染周围的人。哈里森在《古代的艺术与仪式》中曾经说到“仪式想要产生一种情感,…我们稍后看到的仪式只是一种反复举行的行为。”[3](11)宗教饰品在仪式中既要渲染情感,又要反复使用以配合宗教活动的重复进行,这就使得人们在选择其制作材质时会选用经久耐用且又能体现对于宗教崇敬的思想。于是像金、银等贵金属以及一些玉石、宝石作为制作材料。
不同于蒙古族的生活饰品,在生活饰品中尤其是服装配饰上,蒙古族一些首饰、配饰制作材质虽然钟爱于选择贵金属,但形态构造上整体显现出“拙”的审美形态,这是源自于蒙古人传统的审美习惯和价值观念。而同样用金、银、铜等贵金属制成的宗教饰品,则处处体现着制作精良的艺术特色,对于一些礼器的锻造和打磨,镂空与雕刻体现着异常精细的工艺技巧。这种工艺的迥异风格与历史的发展和宗教的变革有很大的关系,蒙古族的原生宗教为萨满教,萨满的生态观要求人与自然和谐一体,萨满教的宗教饰品在早期也曾经与生活用品形制的“拙”较为相近,而后来由于草原上佛教的传入,统治者对于佛教的崇尚,佛教由于其有着较为完备的法理和规范,使得宗教饰品制作工艺开始精细化。加之民族间手工艺方法的交流,越来越先进的工艺使得宗教饰品更加精致华美。这在审美文化中,就是一种文化的变迁和融合。
蒙古族宗教饰品的审美取向另外还有着本民族审美习惯的“根”性,这就体现为游牧民族“天人合一”的朴素的辩证思想,蒙古族世代以“天”为崇拜对象,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充分的利用自然与自然环境相适应,以此来延续草原生存的基本技能,蒙古族视天地为父母,水草为血液和魂灵,视动物为生产资料,这便是“万物有灵”信仰观念的源泉。社会的人依赖于自然界,同时也要实现人与自然适应为一体,这一观念也在宗教饰品的制作和表达中有所体现,用动物皮质、木头、石块、骨骼等制作的饰品,在仪式中通过宗教饰品与仪式的配合达到人与生态环境的和谐相处,这充分体现着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可持续发展生态智慧,也展示着蒙古族追求自然美的精神内涵。
蒙古族宗教饰品作为一种文化符号存在于蒙古族的社会生活中,具体通过其表象的符号体系来对宗教信仰的认识和把握。宗教饰品所呈现出的审美取向物化为一系列的符号体体系,这样的符号体系经过宗教活动的传递模式世代相传,呈现出了文化的沿袭和文化的交往。符号在宗教对于思想的传递上,通过具体的形象,起着一种承接的作用,这样的符号在进行着人与人,人与社会的交流中,将宗教的文化和民族习俗进行发展,符号便有了新的内涵,符号也不再是空洞的代码,而是人的审美经验充实其内的载体。
结合当下社会的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民族文化资源被不断开发,在民族工艺品的这一部分,由于商业取向和旅游经济的原因,一部分传统的民族手工艺品在置入于商业社会中,被进行大力度的推广,而在多民族文化、经济交往中,民族间的涵化现象在手工艺制品的工艺及制作中尤为突显。另外,在追逐经济利益的情境下,有不少的民族文化的样式样态被曲解,甚至出现知之皮毛、牵强附会的元素加之于蒙古族的手工艺制品上,这样一来,既不是对民族文化的传承,也起不到宣传地区文化的效果。而蒙古族宗教饰品由于其具备宗教所固有的传袭模式和教义内容,在一定程度上对于民族文化内涵的正确传达有着积极的作用。时至今日,伴随着生产方式的不断转化,社会生活的现代化推进,不少的文化形态在社会发展中面临着消亡的命运,随着宗教从事者的减少,大量的宗教饰品逐渐丧失了其所具有的祭祀仪式功能,慢慢的走进了博物馆,其本身具备的文化符号和审美价值在弘扬蒙古族文化的领域内意义重大,借助于文物、史学文献和实地调查,还需要进一步来对蒙古族传统手工艺品—宗教饰品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1]张景明.中国北方游牧民族的造型艺术与文化表意[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3.
[2](德国)费尔巴哈.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读•下卷[M].上海:三联书店,1976.
[3](英国)简•爱伦•哈里森.吴晓群 译.古代的仪式与艺术[M].郑州:大象出版社,2011.
【责任编辑 徐犀】
An analysis of form structure and aesthetic orientation of Mongolian religious ornaments
Yang Xiaohui
(School of art and design, Inner Mongolia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aotou, Inner Mongolia, 014010)
Religious ornaments, as a significant component of traditional Mongolian ornaments, have their unique form and structure, as well as rich connotation of national aesthetic. In the ritual field, religious ornaments play a farreaching significance in the symbolic form and structure of the ornaments, and they surpass national aesthetic culture. The form, structure and material of religious ornaments are different from the Mongolian ornaments in daily life, due to specific characteristics. In the process of inheriting and developing, religious ornaments manifest national cultural value.
Mongolian; religious ornaments; form and structure; aesthetic orientation
J529
A
1672-9838(2017)02-097-04
2016-10-10
本文为内蒙古自治区社科基地-内蒙古文化传播力建设研究基地一般课题《内蒙古传统手工制品的现状调查及传承机制的研究——以蒙古族饰品为例》(项目编号:2016ZJD023)阶段性成果。
杨小晖(1987-),男,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人,内蒙古科技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视觉传达系,讲师,硕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