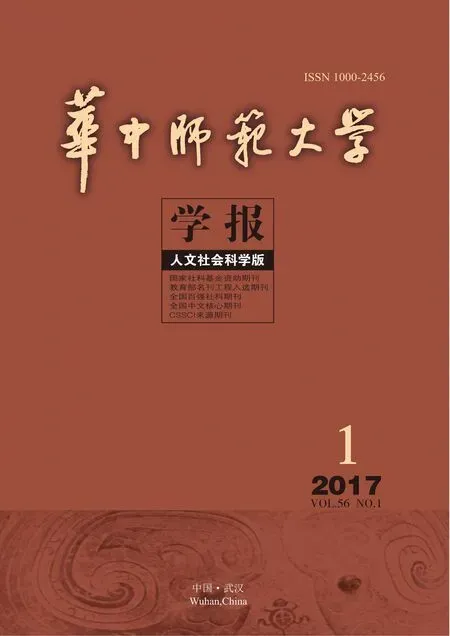也谈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对“二流子”的改造
——与其他政权实体比较的视野
渠桂萍
(山西大学 近代中国研究所, 山西 太原 030006)
也谈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对“二流子”的改造
——与其他政权实体比较的视野
渠桂萍
(山西大学 近代中国研究所, 山西 太原 030006)
乡村游民系不安本分、无产无业、危害乡村社会者的总称。他们往往谋生不以其道,好逸恶劳,绝对有德行的缺陷,对社会有一定危害性。这一群体始终是地方政府治理的目标。除了基层政府,地方社会的习惯法、社区舆论以及乡村正统权威等乡土约制资源对游民的危害行为也发挥着抵制功能。20世纪40年代初,国共摩擦升级,国民党对抗日根据地实行全面经济封锁,中国共产党陷入空前财政危机。根据地政府展开生产自救,大力开荒。囿于劳动力的严重短缺,根据地政府自上而下地掀起了改造“二流子”运动。中国共产党评价体系中的“二流子”与乡村游民有所不同,“二流子”根据抗日政府的标准进行身份识别,注重“有无正当职业”,乡村游民则是乡村民众的社区角色认定,侧重“乡村危害性”与“德行”的品评。相比其他政权实体,根据地政府以国家的角色通过运动模式对乡村脱序者进行“专项治理”,其改造的规模、力度,效果,都有不俗的表现。改造“二流子”则通过对传统约制资源进行创造性地转化予以推进。社区权威角色、村庄舆论与道德评价机制、宗教仪式与象征符号等各种传统约制资源有机结合,交互运用,成为现代政党改造“二流子”的手段,较为成功地实现了对“二流子”的改造。
乡村游民; “二流子”; 乡土约制资源; 抗日战争; 中国共产党
当前,关于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改造“二流子”问题的研究,成果不菲,论者分别对中国共产党改造“二流子”的原因、路径、方法、影响及成功经验进行了讨论,具有一定的说服力与启发性。然而,总体而言,研究者对此问题的探讨多数停留在“就事论事”的层面,缺乏历史长时段的视野与横向比较方法。从历史长时段视野来看,游民问题在中国经年持久的社会变迁中并不罕见,它的社会危害度常常伴随着王朝、政权的兴衰而变动,这一群体在中国社会变迁的洪流中几乎从未消失过。诚如韩丁所说,游民是中国农村司空见惯的现象①。游民的治理也一向系国家治理范畴。本质而言,中国共产党改造“二流子”亦属于国家对“游民”的治理。那么,中国共产党所改造的“二流子”与“乡村游民”有无不同?与其他政权相较,中国共产党对“二流子”的治理与改造目的、路径、效果等有何异同?在治理“游民”的历史长河中,中国共产党取得了哪些不同于以往、值得借鉴的成功经验?以上问题,只有放宽历史的视界,置于比较的视野才能释清,并且也可以小见大,窥视中国共产党革命成功的原因。
一、20世纪前期中国的乡村游民及其治理
(一)乡村游民的定义、成因及危害
乡村游民系不安本分、无产无业、危害乡村社会者的总称。他们往往是谋生不以其道,好逸恶劳,属寄生性与消耗性分子;他们私心较重,绝对有德行的缺陷,对社会有一定危害性。“人类生在社会中,参加社会生产(无论特质的、精神的、直接间接的)是人类的天赋,如其游手好闲,不劳而获,非社会生产阶级,用非法手段敲诈掠夺,冀图幸存,那便是无业游民。游民寄居农村无营固定生活者,叫作地痞;住无定所,往来异地者,叫作流氓。这便是地痞流氓的简单意义”②。
对于游民的形成,论者往往强调外在环境的原因,如天灾、兵祸、经济凋敝、人口压力、社会治理衰微、政治剧烈变动等。如黄宗智认为,人口压力与社会不平等产生一个庞大的“贫农”阶级。在贫农阶级的底端则是没有经济能力结婚的单身汉,其中不少变成由无业者和乞丐组成的“游民”的一部分。自18世纪以来,他们构成了中国社会一个持久的特征③。
在充分考虑社会、政治等外在因素前提下,对于游民的成因,其个人主观因素也值得重视,如个人意志薄弱、生性懒惰,厌恶本业,桀骜不驯,心意躁动,教育水准低下,家庭不管不教等。此类成员在社会环境恶化时,受到外在环境的刺激与各种不良诱惑,更容易失业堕落,混迹乡间,甚至铤而走险。
清末民国年间,战乱频仍、天灾接踵,伴随着畸形都市化的现代变革,农人生活“贫而又贫”,游民群体激增,影响波及面甚广,“近数十年来,乡村游惰之民,日益加多”④。“今合计,每州县为士为农为工为商之人,十仅三四,而不士不农不工不商之人,十将六七,类皆嗜洋烟,结死党,小则鱼肉善良,抢掠财物,大则托名义忿,焚毁教堂,谁为为之?”⑤
乡间游惰之民,劣迹斑斑,因其偷盗、赌嫖、作奸犯科、违法乱纪、甚至出没为匪兵,极大地影响了乡民正常生活,扰乱了乡村秩序,破坏了社会治安:“整个农村社会,被扰乱得江湖海滚,鸡犬不宁……”⑥;“行为嚣张,号称难理”⑦。
在乡土社会,这一群体最为乡民痛恨,有的乡民竟将其视为“剥削者”,“土棍盗贼是乡民最痛恨的群体”⑧。“有些农民,把少数地痞流氓和无业游民的为非作歹认为是第三种剥削形式”⑨。甚至还有学者指出,整个社会从家庭愁苦,到国难日深,均与游民脱不开干系⑩。
正是基于游民的社会危害性,无论是官方政府还是地方社会,在经年的实践中,生成了一系列防范、抵制与治理游民的方式与制度。
(二)乡村游民的治理
1.地方政府对游民的治理




就村落一级而言,村庄内部凭借自身的“自治肌体”,对无赖痞棍有一定免疫功能。
2.村落公共秩序层面对乡村游民的约束


乡村社会公共秩序的维系,对无赖流氓的抵制主要依靠内生的权威——村庄领袖、家族长等头面人物;同时,乡村中自发形成的习惯、社区舆论以及各种仪式与象征符号等软环境,塑造着乡村民众的社会心理,促成乡村对于各种不轨行为形成一定程度的共同防御效应。
(1)村庄领袖、家族长、村落精英凭借其声望、合法权威,对村庄秩序有着一定的控制与约束力。

以下个案是甘布尔于1928年对华北村庄进行的调查,他详述了村庄权威出面惩处盗贼的过程,提供了村庄权威管治乡村游民的典型个案:
1928年8月11日,王妈妈发现“社”里有180穗玉米被盗了,李先生发现他丢了1730穗玉米。第二天他们把这件事报告给了邻村的乡村权威——集体看青中心。村长召集领导成员开会,派遣看青夫出去查找偷青的贼。


(2)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传统村规民约、村民评价等村舆论,一定程度上形成抵制无赖痞棍不轨行为的软环境。

通过甘布尔调查的D村,可以看到村舆论较强的约制效果:

这是一个村民也能够给村庄的领导集团施以足够压力的典型个案,村民的压力是通过村舆论来表达的,从中可见村舆论无形的约制效应。
(3)乡间的仪式与象征符号。



二、比较视野下中国共产党抗日根据地“二流子”的改造
20世纪40年代,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根据地自上而下发动了大规模的改造“二流子”运动,其本质可以视为国家对“二流子”的改造行为。中国共产党改造的“二流子”与乡村游民有何关系?其改造的根本缘由是什么?改造“二流子”的路径与乡村游民治理有何异同?探讨此一系列问题,需从改造“二流子”的原因着手。
(一)中国共产党改造“二流子”的根本原因——巨大的财政压力与劳动力短缺




(二)从乡村游民到“二流子”
如前所论,乡村游民系不安本分、不务正业、危害乡村社会者的总称。他们的行为特征大致归纳为二:一是不务正业,游手好闲;二是危害乡里。此类人群的判别与品评,通常存在于乡村社会内生的舆论空间与层级地位评价中,乡民对这一人群有“无赖”、“土豪”、“土棍”、“痞棍”、“痞子”、“地痞”、“流氓”、 “有嗜好者”、“赌徒”、“泥腿”、“狗腿子”、“光棍仡孑”、“二流子”、“二混子”等称谓。由于其社会危害性,乡村游民是地方政府与民间社会共同抵制、治理与控制的对象。
同为脱序人群,“二流子”与乡村游民有共同行为特征,但并不能等同。“二流子”的身份辨识主体是根据地政府,而非乡村民众,其标准更多地体现了政府意志。抗日政府认为,根据地的“二流子”与旧社会的“流氓”称呼的不同,是因为二者的含义有所区别。旧社会的流氓是不良制度、社会腐朽风气的产物,而根据地“二流子”生活在新的社会秩序中,与社会制度已经没有关联,只是过去寄生意识的残余:

在抗日政府看来,由于政治生态、社会环境发生了根本的变动,“流氓地痞”失去了活动的依托,社会危害性大为降低。因而,他们的主要特征是“好吃懒做”,“游荡无事”社会危害性已退居其次。以下从抗日政府对“二流子”、“半二流子”与非“二流子”的区隔中可看到,与不良嗜好、危害社会相比,“好吃懒作”对“二流子”身份识别更显重要:


以下个案,可具体印证“是否从事生产劳动、有无正当职业”标准对“二流子”身份识别的重要性:

抗日政府认为,赵怀亮虽不做什么坏事,但是游手好闲,不事生产,应当归入“二流子”之内。白三茂虽有不良嗜好,做坏事,但是劳动很好,就不能说是“二流子”,只是说不是好公民。






(三)“二流子”改造的路径——传统乡土约制资源的利用与创造性转化
长期以来,地方政府、社区权威、乡村习惯法、村庄舆论、道德仪式、象征符号等内容,共同构成了约制乡村游民的传统乡土资源,将游民的越轨行为控制在有限空间。抗日根据地改造“二流子”,对传统游民治理的手段与路径有所传承、借鉴,并予以创造性转化,进而形成了一整套既能有效利用乡土资源、又富有革命气息的,行之有效的改造“二流子”路径。
1.政府自上而下的动员、主导模式


与其他权力实体相较,中国共产党对“二流子”的改造,发轫于政府自上而下的动员,政府的意志总是嵌入其中;改造“二流子”的背景是在经济极度困窘的背景之下提出的,根本意向在于激活社会潜在生产要素,并且以“运动”的形式展开;其他政权实体对游民的治理,则是在政治常态之下维持社会秩序、正常行使治权的行为,治理范畴旨在针对游民的社会危害行为。此外,乡村舆论环境、正统权威等乡土约制资源对游民的活动有一定的抵制功能,并且自发地起作用,政府介入社会程度较少;中国共产党抗日根据地改造“二流子”运动,乡土权威、村庄舆论等乡村约束机制虽然不可或缺,但其作用力的有效发挥,与根据地政府的动员往往脱不开干系。在抗日政权的主导下,中国共产党通过对各种传统乡土约制资源借鉴、利用并创造性转化,较为成功地实现了对“二流子”改造的意图。
2.传统乡土约制资源的利用与转化
(1)传统权威与新式精英的“社区长老”角色。

又如下述个案:

俯拾即是的“劳动英雄传记”,翔实记述了新式精英对“二流子”的劝说、监督与改造的经过,他们的身份虽然有别于“传统乡绅”,但在改造“二流子”过程中,则以“传统社区长老”的角色出现,对二流子“劝解”、“批评”、“教育”、“鼓励”。60岁的劳动英雄孙万福自述了劝解、批评、教育“二流子”的生动场景:

新旧精英作为“群众”,以乡民所熟识的“社区长老”身份对“二流子”进行规劝、说服与教育,他们往往通过感化方式营造合乎乡情的情感氛围,使“二流子”在愧疚中得以转变。
(2)村舆论等乡村约制资源的利用与转化。



乡土社区中,孤立、社区隔离是比较严重的非正式舆论约制,这种方式也被用来改造“二流子”,给“二流子”造成较大的心理压力,如下个案:


上述案例中,无论是“懒旦”刘全、赵六十一,还是“女二流子”王桃梅,均是感觉到被熟人社区“孤立”与“隔离”的痛楚与耻辱,最后下决心转变。除了乡村舆论,传统的民间与宗教仪式、象征性符号等,也携带着激励“二流子”的隐形因子。
(3)传统仪式、象征符号的利用与转化。

中国共产党抗日根据地改造“二流子”过程中,各种传统仪式与象征符号被巧妙而纯熟地转化为革命象征仪式,对“二流子”的改造形成了无形却有效的压力空间。

惩罚性的斗争仪式也是改造“二流子”方式,这种仪式给“二流子”带来极大羞辱感,常常迫使“二流子”不得不寻求转变,如下个案:


抗日根据地政府“改造二流子”,不同于其他实体政权,以其特有的现代政党动员方式——自上而下的群众运动展开,但在改造过程中,并未将传统摒弃,而是对各种传统约制资源加以利用,并创造性地转化,从而较为成功地实现了“二流子”的改造。
三、结语



尽管如此,也应注意到,中国共产党对“二流子”的改造,是在根据地严重的财政危机情势下展开的,其根本初衷是为了解决劳动力短缺的问题,因此,与其他政权相比较,对于“二流子”身份的辨识是一个难点,以致出现根据地政府的“改造对象”与乡村民众的“改造诉求”有所背离。社会上一部分行为不端,危害乡里的人群,可能由于其未脱离生产,在“二流子”的辨识当中并未划为改造的行列;而少部分“懒汉”,虽然不愿意从事生产,但社会危害并不显著,可能被划分为“二流子”,受到羞辱。其次,运动式的动员与改造模式固然对改造“二流子”作用明显,但如何使抵制“二流子”的惰性、寄生性与社会危害性成为制度化常态,则值得进一步深思。
注释
①⑨韩丁:《翻身——一个村庄的革命纪实》,韩琼等译,北京:北京出版社,1980年,第322页。


④⑩郑新汉:《乡村游惰份子之研究》,《特教通讯》1941年第3卷第4期,第22页。
⑤《州县稽查患保甲宜先安置游民论》,《申报》第9985号(上海版)1901年1月30日第1版。

⑧《阎伯川先生言论类编》卷三下,太原:太原绥靖公署办公处,1935年,第55页。


















































责任编辑 梅莉
Taking a Second Look at Chinese Communist’s Transformation of “Hoodlum” during the Resistance-against-Japan War——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mparing with Other Political Entities
Qu Guiping
(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 Shanxi University, Taiyuan 030006)
Rural vagrant was used as a collective term to address social members who were likely to break social rules and traditions,had no real estate and fixed occupation,and may jeopardize the rural society. Due to their potential harmfulness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ociety, rural vagrants had long been taken as a principle renovation target by local governments. Customary law, community opinions and rural restrained resources supervised by rural orthodox authorities played a significant role in relieving the harmfulness of vagrants. Under the condition of tremendous financial pressure and lack of labour in 1940s, a movement transforming “hoodlum” was initiated and mobilized thoroughly in Chinese Communist Resistance-Against-Japan bases. In the Chinese Communist evaluating system, “hoodlum” is different from rural vagrants. In dynamic collaboration with Chinese Communist, governments in Resistance-Against-Japan bases employed a variety of rural restrained resources and succeeded in creatively transforming “hoodlum”.
rural vagrant; hoodlum; rural restrained resources; creatively transforming
2016-10-14
2013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民国时期的乡村游民与乡村社会”(13BZS059);2013年教育部新世纪人才支持计划;2013年度山西省高等学校中青年拔尖人才支持计划;太原理工大学“华北社区调查与研究”基地支持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