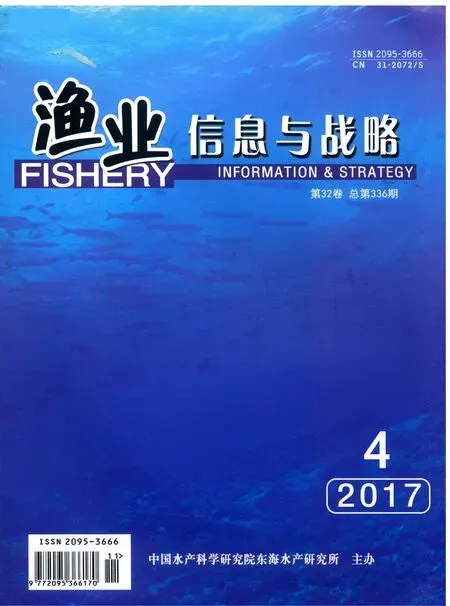转产转业背景下沿海渔村共同体的嬗变与重建
——以福建平潭东美村为例
杨宏云, 景 晶
(1.福州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福州 350116; 2. 电子科技大学中山学院人文社会科学学院,中山 528402)
转产转业背景下沿海渔村共同体的嬗变与重建
——以福建平潭东美村为例
杨宏云1, 景 晶2
(1.福州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福州 350116; 2. 电子科技大学中山学院人文社会科学学院,中山 528402)
为适应专属经济区渔场调整,转移沿海地区过剩的渔业劳动力,促进海洋渔业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农业部自2002年起对海洋捕捞渔民开始实行转产转业政策。该政策的实施立足于海洋资源的保护和渔业可持续发展,但却使渔民失去了世代所依赖的生存资源。相应地,它给渔村共同体带来一系列影响和冲击,出现亲缘疏离、地缘弱化、业缘增强、文化式微等的嬗变。由此引起学界对渔村共同体未来发展趋势的思考和探讨。文章基于“共同体”的理论基础,透过福建平潭沿海渔村——东美村的实地调查和深度观察,梳理了该村所发生的诸多变化,并从重建沿海渔村共同体的视角,提出政府宏观政策支持、文化保护及照顾渔民主体性的对策建议。
转产转业; 沿海渔村共同体; 嬗变和重建
1 共同体与渔村共同体
1.1共同体
“共同体”一词最早由德国社会学家斐迪南·滕尼斯提出。他认为:“共同体是人们基于血缘、感情和伦理纽带自然生长起来的人群组合,是一种有机的社会组合模式”[1]。根据其论述,共同体应包含有几个基本的要素:亲缘或家族关系,包括父子母子关系、夫妻关系、兄弟姐妹关系等亲缘关系;互帮互助的地缘关系;默认一致的习惯传统或是共同的意志;地理承载体,即在共同体之上形成由土地决定的复合体等地理形态,包括农业地区、村庄、行政区或边区等。这种共同体特征是人们之间的关系建立在纯朴的、亲密的自然感情基础上,且互帮互助,是一种有机的联系。
根据滕尼斯的理论,中国传统的乡村社会无疑也是一个“共同体”。一方面,人们在一定区域群居而形成一定的社会关系,随着不断的生息繁衍,社会关系的核心被血缘关系所取代,各种生产、生活方式也在此基础上形成,并加以固定,成为“默认一致”的共同体,这样就形成了各个大同小异的自然村。另一方面,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特别强调“家”的概念,这些基于血缘关系的村庄被视为“大家”,居于其中的村民互帮互助、自给自足,在这个“家”的范围内过着相对封闭的生活[2]。但随着市场化、工业化等现代化的冲击,传统村落共同体正面临着一系列的困境和转型。对其发展趋势,目前学界大致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随着市场经济不断渗透以及城市化进程的影响,村落的边界越来越开放。传统村落的共同体将被纳入到市场与社会的大环境之中,村落将逐渐成为一种渐行渐远的历史传统,村落共同体注定走向终结[3]。另一种观点认为,传统村落共同体的存在仍具有其重要功能与意义。这是因为现代风险不断增加,社会流动速度加快,个人主义不断盛行,现代化过程中蕴藏着各种危机。而“村落共同体作为一种安全和归属感的源泉,将会引起人们的持续的怀旧之情”[4]。因此对于村落共同体传统的保护是应对现代性危机的重要选择之一。此外,还有一些学者主张应超越这两种观点的看法,即“正确的看法应从两面性去把握中国村落的性质,而不是做简单的非此即彼的二元论式判定”[5]。
上述观点皆立足于农耕型村落共同体的分析,缺乏对沿海渔村共同体特性和现状的深入讨论。
1.2渔村共同体
所谓渔村共同体本身是一个相对复杂的概念,目前还没有明确定义。根据作者调研总结,应是指涉海人群在渔村里从事海洋资源开发的生产实践活动,并基于这样的生产活动形成了特定的生活形态,进而建立起有别于农耕型村落共同体的社会组织、社会规范,并形成基于海洋性文化认同的社会聚集体。然而,一直以来,乡土村落、城市社区共同体的功能被人们讨论、研究颇多。但在海边繁衍生息的沿海渔村共同体却未能被人们所认知和重视。众所周知,沿海渔村从古至今存在的根本理由就是对海洋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但随着我国近海水产资源枯竭,工业化、城镇化给沿海渔村带来的一系列冲击,以及自2002年起,农业部在沿海地区逐步推行的渔民转产转业政策等多重因素作用,沿海渔村共同体陷入解体或重构的转折点。然而,学界目前关注较多的却是转产转业政策本身的成效,且多以产业经济学、制度经济学考察,缺乏社会学视角探讨渔民转产转业可能带来的影响。
一般而言,传统的沿海渔村作为一个资源型区域社会,以海洋捕捞业为基础,基于一定的血缘和地缘形成亲密合作,也是典型的“熟人社会”[6]。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渔村的人口、环境和文化形成了相对固定的文化、经济、社会和自然边界,具有明显的“共同体”特征。但这种共同体社会在自然环境改变、资源枯竭、政策形塑下,正面临嬗变和重构,甚至可能瓦解的处境。笔者认为:尽管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共同体的内容和形式不断发生变化,但共同体是人类生活的一种基本需要[7]。在渔村社区,它作为广大渔民生活的主要场域,如同农耕型村落共同体一样,既是保持渔村社会有序治理的基本结构,也是延续和维系中华文明多元性的基本组织载体。它的保存、延续甚至重塑十分必要。
2 研究方法、对象与福建平潭东美渔村概况
本研究基于社会学的共同体理论,采用实地调查和深度观察等质性研究方法,试图以福建平潭流水镇沿海渔村东美村的案例分析,探讨转产转业带来渔村共同体的流变,从而引发学界对渔村共同体建设问题的思考。
本研究对象选择福建平潭流水镇东美渔村,与传统农耕村落相比,东美村属于典型的“沿海渔村”, 即指地处沿海且以海洋资源为主要生存来源的自然村落,是依据历史传承而自然积聚起来的“事实上的群体”[8]。“以海为田,以渔为食[9]”是该地区人们典型的生活方式。渔业资源既是他们食物的主要来源,也是他们进行市场交换的资源。在海边世代生活的村民自然地以“讨海”作为自己的谋生渠道。甚至,民俗信仰也有着明显的海洋特色。村落广泛分布的妈祖庙和各种与海洋有关的神灵存在即是明证。
而且,东美村渔民世代依靠海洋渔业资源为生,以海洋捕捞为业。20世纪90年代,流水镇的海洋捕捞业十分红火。东美村作为流水镇的重点渔业村庄,曾经因年捕鱼超万t而获得平潭县1993年、1994年度“渔业明星村”称号。经年的海洋捕捞特性塑造,渔民家庭成员之间互动紧密,渔民与邻居之间合作关系密切,渔民群体之间享有共同的价值规范和文化习惯。渔村深具滕尼斯所说的“共同体”特征,并蕴含着一定的社会、文化、自然和经济等边界。其中社会边界是村民基于血缘、地缘、业缘关系的社会关系圈子,文化边界是村民共同的价值体系的心理和社会认同,自然边界是基于土地属权的地域范围,经济边界是村民经济活动和财产权利的网络和疆域[10]。由此,渔民彼此之间相互依赖,并与渔村共存、共建与共荣,形成了一些“默认一致”的社会模式和制度性规范。自2002年始,面对日益枯竭的海洋资源,农业部向沿海各省印发了《关于2003~2010年海洋捕捞渔船控制制度实施意见》,开始逐步对沿海渔民实施转产转业政策。作为渔业大省,福建省政府响应农业部号召,积极开展渔业生产结构调整。而平潭作为福建省重点海洋渔业捕捞地区,也陆续开始鼓励渔民转产转业。2009年,福建省政府又正式设立平潭综合实验区,拉开了平潭岛海洋开发的大幕。2013年,国家海洋事业发展“十二五”规划更是提出要把平潭岛建设为面向台湾的旅游海岛。平潭的海洋开发与建设愈益加快,渔民的转产转业进程也进一步提速。传统的渔村村落——东美村渔民转产转业进程也急遽加快。
笔者根据东美渔村的实际调查,发现目前东美村渔民转产转业的方向主要为三类:一是转产转业到海洋运输业, 这是该村渔民最主要的转产转业方向。渔民转向海洋运输业的方式主要是投资运输船,或者成为船员到运输船上工作。一般渔民家庭都有参与投资海洋运输业,且家中男性劳动力通常又选择到运输船上工作,成为运输船管理员或者船员等;二是转向发展渔业休闲旅游产业,包括一部分渔民依靠渔业休闲旅游业的兴起成为个体商户;三是直接到城市打工。与之形成对比的是,该村很少有渔民转型从事水产品加工业。据东美村文书介绍,截至笔者调查的2013年,该村共有450户,总人口1 580人,劳动力有800人左右,其中20岁到60岁的男性劳动力有340人,60岁以上老人有300多人。本村经济产业目前主要为渔业(少量合法捕捞,以及合法捕捞掩护下的非法海洋捕捞业)、海洋运输业以及旅游业。故村民目前的职业类型有三大类:一类是仍然以海洋捕捞为生的渔民,目前本村有18艘73.5 kW马力以上有证作业渔船,渔民以近海捕捞作业为主,从事捕捞业的渔民仍然采取的是家庭联合经营的形式。这些渔民既有本村渔民,也有较大部分是近几年来自平潭岛以外地方(以东庠岛为主)的渔民。二是以海洋运输业为生的渔民。当前本村有1/3的男性劳动力在海洋运输船上工作。三是从事其他职业的人,如渔村旅游休闲产业,进城务工人员等。因而,经过转产转业,东美渔村的经济活动显然出现了多元化,村民的职业也变得多样化,传统的渔村共同体社会有了显著的嬗变。
由此,本研究冀图以东美渔村的案例分析,为中国“三渔”问题的解决提供实践借鉴;并由此审视更大范围内的沿海渔村变迁进程,从而为我国社会主义新渔村建设理论内涵有所贡献。
3 转产转业背景下东美渔村社会共同体的嬗变
渔民的转产转业深刻改变了渔村的经济基础,进而动摇了渔村的社会结构。因而,参照滕尼斯等人有关共同体的论述,根据笔者考察,东美渔村共同体有了若干嬗变。
3.1亲缘关系的疏离
亲缘关系是渔民社会关系中最为原始的一种社会关系,“是人类社会关系中相对于地缘关系、业缘关系而独立存在的亲属关系”[11]。在社会结构中,亲缘关系属于传统的先赋关系范畴。笔者本文所说的亲缘关系疏离化是指,渔民家庭成员及亲属之间因互动空间隔离、交往频率减少,以及互助社会关系弱化而导致的关系演变。
历史上,东美村渔民多以海洋捕捞为生,渔民通常每天都能出海回来,最多的出海日期也不到半月。一般说来,家中男性劳动力负责出海捕鱼,女性及家中长辈则帮忙做些附属的工作,如收渔、分拣、补网、扫网等。在这样的生产、生活模式下,渔民家庭成员以及亲属之间都保持着紧密的互动关系。自2002年以来,东美村大部分渔民陆续转产到海洋运输业等其他行业,职业的转变削弱了渔民的互助需求,增强了渔民群体空间地域上的流动性。这种人口的流动对渔民家庭的亲缘关系带来深刻影响。譬如,笔者的采访对象C1(男,退休渔民,65岁)有两个孩子,儿子在山东工作,女儿也嫁到外地,不到过年不回来。对象C2(女,43岁,县城打工,丈夫为船员)自2006年没有捕鱼后,丈夫就去做船员,一年在家的时间不到一个月。对象C3(男,35岁,船员)虽然已婚,但和老婆孩子见不了多少面,回家一次,发现孩子变化一次,感觉父子之间关系越来越生疏了。
据村干部介绍,渔民的转产转业通常会产生“一人转产、全家流动”的情况。因海洋运输业的工作性质,船员需要常年在海上,通常到节假日才能回家。这种工作特性,使得船员与家庭成员之间的互动频率减少。尤其是新生代渔村居民,选择脱离渔业的过程也是逐渐远离渔村、远离家庭的过程。由此,亲缘关系淡化势难避免。有学者指出,传统的乡村共同体体系内,“人们基于共同的劳动和生活,家庭成员间的凝聚力很强。但随着家庭成员的不断外迁,家庭的凝聚力也逐渐下降”[2]。因而,转产转业不仅改变了渔民的职业,同时也加速了渔民的空间流动,亦造成了渔民亲缘关系的疏离化。
3.2地缘关系的弱化
地缘关系是指成员间基于空间或地理关系位置而形成的社会关系,包括邻里、老乡、民族社区等具体形式。
一般来说,在农村,村民长期生活在一起,彼此熟悉对方的家庭背景,各种社会活动也都是以家庭或家族为基本单位展开。这种因地缘而形成的邻里关系在日常生活中具有重要地位。按照费孝通对“邻里”的界定,它“就是一组户的联合,他们日常有着很亲密的接触并且互相帮助。这种互相帮助的关系,并不严格地限制在几户人家之中,它更多地取决于个人之间的亲密关系,而不是按照正式规定 ”[12]。他认为邻里之间的互帮互助,是我国农村社会中最重要的支持系统之一。
在传统的渔村社会,渔民的生活方式比较单一,渔民之间交往最多的都是在经济生产领域。学者曹锦清认为,中国小农经济的特点,造成了中国农民的“善分不善合”的合作困境[13]。然而,在渔村共同体社会,渔民却天然地需要集体合作,且渔民群体之间这种因地缘结合而形成的合作关系比农耕型村落更趋紧密。无论是海洋捕捞业或者“赶靠”,抑或“放针良船” ,都需要渔民之间的密切合作,否则无法开展作业。这与传统认知中的陆地生产型农民劳作完全不一样。海洋渔民不仅在同一海域中共同生产,上岸后的多数生产形式也需要数人或者数十人通力合作才能完成。这种集体作业的特性,使得渔民家庭与邻里之间彼此熟悉,并保持着较为紧密的人际互动。正如笔者访谈对象C4(男,68岁,退休渔民)所指出的,“我们这些老人年轻时一直跟海打交道,一辈子最熟悉的人都是一起捕鱼的人。搞合作社的时候,大家是共同生产的。后来虽然改革了,也必须得家庭合作才行。”
而且,渔民不仅依靠邻里关系进行生产,并在不断的互动过程中将地缘关系注入了更多的情感。如同老渔民C4所说:“我们渔民之间都像是患难兄弟,感情很深”。然而,随着转产转业,渔民群体之间的地缘关系发生了改变,感情逐渐为利益所取代。用访谈对象C5(男,46岁,曾经是渔民,目前是运输船船员)的话讲,“在以前,家家户户捕鱼时,平时的补网、扫网的事都是一起做的,为了生活,大家是你帮我,我帮你的关系。现在村里捕鱼的越来越少,找人补网、扫网或者其他一些小忙,都得计算时间,计算劳动量,付工钱。”对此,访谈对象C6(男,48岁,曾经是渔民,后从事船员,目前无业)也提到:“以前我们都是一起捕鱼的,现在人家有钱了,交往的和我们不是一个圈子的人。现在不敢太信熟人了,有些人为了钱心都黑了呢!谁还给你讲熟人啊!” 访谈对象C2也表达了“不一起做工,邻里关系自然就没以前好”的看法。
转产转业之前的渔村,因海洋捕捞的特性,渔民流动性较低,渔民群体之间形成了较为紧密的地缘关系。然而,随着渔民生产方式和职业的改变,越来越多的渔民开始向城镇流动。笔者前往东美渔村的数次调研中,所见除仍在捕鱼的渔民以及村中的老人和小孩以外,青壮年村民的身影十分稀少。渔村最热闹的地方是老人会。生产、生活方式的改变,使得渔民之间互帮互助需求减少,村民之间团结协作关系亦减弱,地缘关系也随之弱化。乡村日常生活中的“熟人社会”特征也随地缘关系弱化而逐渐消失,呈现出帕森斯“社会系统”理论中所指的因缺乏足够数量的行动者而无法维持系统均衡的“病态”[14]。
3.3业缘关系的增强
业缘关系是指人们基于职业或行业活动之间的联系而形成的人际交往关系。在我国的传统农村社会,农民交往方式和价值观都是与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即强调集体,依附于土地,注重地缘和血缘关系,情感亲密,交往类型单一等。在传统的渔村共同体中,渔民群体的人际交往也是以血缘和地缘关系为主,业缘关系通常是与地缘关系相重合的。但2002年以来,东美村渔民在政策和环境影响下,陆续脱离渔业生产,转向海洋运输业,或者直接去城里寻找工作机会。海洋捕捞这种生产方式,已不再是渔民之间交往的重要纽带。因而,村民的职业空间、活动范围逐步扩大,人际关系的交往边界也突破了血缘、地域限制。
根据笔者采访对象C5描述,“现在做了船员,一年到头都在海上,平时认识交往的都是船上的人。船上好多都是外地人,山东的、河南的,自然与他们交往得多了。现在和村里的人只有过年过节回去才有接触。”访谈对象C7(女,34岁,县城打工)也提到:“我在县城一家专卖店卖衣服,平时交往的肯定都是店里的人,和她们都熟悉了,还一起去广场学舞,所以我都很少回村里了。在村里没意思,都是老人孩子,没什么交往”。渔民因职业空间改变,人际交往对象自然而然有所变化。有学者曾指出,现代社会中,“由于流动性加大和社会需求扩大,人们越来越注重‘后致性’朋友关系的建立,基于学缘、业缘和趣缘建构的非传统关系在上升,原有的先赋性亲属关系逐渐弱化 ”[15]。而渔民因转产转业进程,改变了传统渔村共同体较为单一的生产方式,从事非渔行业工作而结成的业缘关系迅速增强,渔民社会传统地缘网络关系趋向瓦解,传统渔民身份特质不断弱化,原先的紧密型联系日趋消解。
3.4渔村传统民俗信仰文化的式微
渔民“寄命波涛”,一直以来对传统海洋信俗十分尊崇。渔村共同体社会惯有的祭神和祭祀仪式,不仅增强了渔村中渔家与渔家之间的凝聚力,而且也增强了渔民个体之间的团结,从而增添了彼此征服海洋的信心和力量。一般说来,海洋渔业生产必须集体协作。渔民群体性的祭神和祭祀仪式举行,就某种意义来说,本身就是海上渔业生产群体协作精神的体现。这种活动也形塑了渔民群体之间的文化边界,使得渔民对集体有很高的认同感,并强化着渔民之间的互利合作关系。然而,随着渔村共同体的消解,笔者调研时发现渔村中这种共同的祭神和祭祀仪式变得日益淡化。
据渔村文书C8(男,50岁,曾投资运输船,妻子在风景区做小商贩)描述:“出海捕鱼的人大多会祈求妈祖保佑风调雨顺。过去,每年农历三月廿三是妈祖的诞辰日,也是我们村里比较热闹的节日,从装饰福船,到准备祭祀的喜面、喜包、红蛋,再身着祭祀的盛装,每一件事情渔民都积极参与。但渔民转产以来,村里这种公共祭祀活动就没有之前那么热闹了。”访谈对象C9(女,40岁,景区个体户)也强调道:“我们家都不靠捕鱼生活了,只是在节日里去烧个香,求一下平安健康。现在这种大的祭祀活动没多少人举办,也没多少人参与。”而访谈对象C10(男,70岁,退休渔民)则提到:“因祭祀仪式需要投入很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以前捕鱼的人多,每家凑些钱就可以解决。现在就剩十几条船,组织这种活动会让捕鱼家庭费钱,所以也就变简单了”。
在传统的渔村社会,海洋捕捞是渔民的主要谋生方式,渔民对组织和参与共同的祭祀、祭神很容易达成共识。而且,这种活动也是加强群体凝聚的推动力,并形成了清晰的文化边界。转产转业之后,渔民很少涉入海洋捕捞,在行为选择上也就更加注重个人利益,难以为公共的祭神和祭祀活动达成共识。由此导致渔民曾经神圣对待、齐心协力合作开展的祭祀和祭神等公共生活逐渐淡化。仪式的简化以及渔民参与积极性的下降,使得传统渔村的海洋信俗文化式微,凝聚力下降,传统渔村的文化边界也渐趋消亡。
3.5渔民村落认同的下降
村落认同主要体现在渔民对渔村的心理归属之上。这种归属既体现在渔民对自身村民身份的认同上,也体现在渔民对村集体的认同上。
依据访谈观察,当前村民对渔村的认同态度主要有两种:一是对村庄仍然怀有很深的感情,这主要存在于已退休的渔村老人身上。对他们而言,渔村是其“生于斯,死于斯”的最后归宿。尽管儿女都远在外地工作,他们仍然不愿意离开早已熟悉的渔村。城市的高楼大厦不是他们向往的生活,因为“对村庄有感情”,他们才一直坚守着自己的家园。如访谈对象C4就说:“我们一辈子生活在渔村,肯定有感情啊。城里有什么好,高楼大厦不方便,乡下条件是不好,但是能吃好喝好,靠着海,还能天天吃海鲜呢。留下来的老人又都很熟悉,没事就闲聊,打麻将” 。
另一种认同态度则是对村庄的感情趋向淡化,向往城里的生活。这主要体现在村庄的中年人和年轻人身上。他们也不再对自己的渔民身份保持认同。如访谈对象C9谈到:“都不捕鱼了,算什么渔民呢”。另外,因职业的转变,渔民的思想观念也受外在环境影响,生活态度更趋理性化和功利化。访谈对象C7言道:“守着村子的人让人家觉得你没本事”。这种功利取向驱使村民走出渔村,减弱了渔民对渔村共同体的认同感,导致渔村愈益衰落。与此同时,渔民群体对公共事务参与意愿也逐渐降低。访谈对象C11(男,48岁,渔村书记)谈到:“转产之后,渔业不行了,渔民都到处谋生了。以前我们维护渔港,大部分都是村民集资,共同参与修缮。现在渔港越来越旧,政府不拨钱,我们也没多少资金和人力去修了。不捕鱼的村民不会参与维修,都不是他们的事情了嘛;渔村一些捕鱼的也是外地来的人,他们才不会管这些!”由此透射出渔民村落共同体认同的弱化窘况。
4 重建沿海渔村共同体的思考
自滕尼斯提出“共同体”的概念以来,共同体的研究越来越受到重视,并成为人们思考社会转型的一个重要维度。而在资源枯竭、转产转业政策驱动下,传统的沿海渔村共同体也成为转型研究者不得不正视的一个问题。
因海洋渔业的特性使然,渔民转产转业导致的渔村共同体社会面临的就是终结或者新生问题。这种困境既是传统与现代、发展与保护如何调适的矛盾,亦是全球化与地方化二元悖论的局部体现。其实质是一种现代性的危机。由此,我们透过东美村渔民转产转业对渔村共同体社会影响的分析认为:传统渔村,作为人口、环境和文化等有着明确边界的共同体社会,是渔民在自然感情一致基础上紧密联系起来的社会有机体,给渔民提供了稳定的社会秩序和确定的生活意义以及安全保障和亲密情感,是一种和谐共生的生活形态。它对渔民有着超强的附着性,是缓解基层社会矛盾演化、维护社会大局稳定的基础。若是陷入解体,无论直接冲击抑或间接影响,程度俱巨。
因而,面对渔民转产转业的实际需要,政府若能以此为契机,加大引导,重塑渔村社会共同体,将会对渔村治理体系巩固,凝聚民心,提升渔村文化自信乃至建设美好渔村有着重要帮助。
4.1注重渔民的主体性,激发渔民的共同情感,合力打造渔村共同体建设
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16]。不管是新农村建设还是新渔村建设,都需要对农民或渔民的主体性需求进行尊重和满足。学者李强教授曾指出中国的城市化可以分为主动和被动两种类型,而且在中国更多的是农民没有主动参与的,“仅仅是被拆迁、被上楼、被搬走的被动城市化”[17]。因而,我国在目前的沿海渔村、海岛开发和建设中,应该吸取新农村建设的经验和教训,不仅仅要注重对渔村基础设施等的建设,更需要对渔民群体进行整合,尊重渔民的主体性需求。由此,才能集思广益,充分调动渔民的积极性,激发渔村村民的共同情感和传统互助精神及主人翁意识,促使渔民投入到对自身家园的生态化、可持续化建设之中。
4.2实行“一村一策”的渔村转产转业政策,促使渔民就地转产,原地就业,从而保留渔村共同体的根基
作为渔民群体来说,既要面对转产后的失海问题,又需要面对市场经济对他们所从事行业和心理的冲击。多重夹击之下,渔民往往无所适从,因此而致贫、致乱现象凸显,渔村的衰落也显而易见,产生的社会问题已有所显现。如作者所调查的东美村,在渔业不断衰落的情况下,发展旅游业、休闲渔业并未能够解决渔村不断衰落的困境。但因缺乏政府政策具体指导和资金支持,旅游业、休闲渔业等陷入负循环。社会凝聚力耗散,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亦面临挑战。合法或非法途径重回渔业捕捞遂又成为部分渔民各种试错后的无奈选择。政府政策执行亦陷入两难境地:若严格依法执行捕捞政策,许多重回渔业的渔民将会生计无存;若不取缔非法捕捞,海洋环境受到影响,政府权威亦受损。因而,笔者建议政府应充分调研,立足实际,加大政策扶持,实行“一村一策”,指导渔民转产转业。其次,政府应加大社会保障机制,对转产转业渔民进行合理的生态补偿和救济,以确保渔民的生活有基本保障。第三,针对上岸后渔民,要采取就地转产,提倡原地就业,并采取精细化的财政扶持措施,鼓励渔民围绕海洋资源开发可持续性发展的产业,使渔民转产转业无需离乡离土,不会因此而致贫。最后,政府在财政方面加大对渔村公共基础设施的投入,以“新渔村”或“特色渔业小镇”建设模式重塑渔村面貌,加强渔民对渔村共同体的附着性和认同感。
4.3应尊重地方特色,加强对渔村村落文化的保护
村落作为地方性共同体,其生态环境、生活方式、文化传统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不能简单地用经济指标来考量。而传统的沿海渔村作为一个资源型区域社会,是海洋渔民基于血缘、地缘和业缘等基础上形成的统一体。渔村的存在,不仅仅为渔民提供生存所必须的物质资源,更是渔民获得自我认同及社会认同的精神家园。而这又离不开长久以来渔村海洋文化传统的型构。但随着渔民转产转业进程加快,以及城镇化和市场化的影响,渔村的海洋文化传统正在逐渐弱化,甚至泯灭。这不仅仅对渔村共同体的维系有所损害。间接地,它对我国当前“海洋强国”战略的潜在影响也不可忽视。因此,在海洋开发和新渔村建设过程中,我们不仅要搞建设,更要注重对渔村村落传统和村落文化的保护,重建渔村发展生态;在巩固传统渔村文化同时,大力提升渔民生活环境质量,并激发渔民基于共同文化记忆的社区参与意识,促进渔民关怀本地渔村共同体建设的氛围,从而重塑渔村新型、生态的海洋文化。这将使渔民生活传统与渔村发展同步,避免现代化、市场化冲击造成渔民的心理失衡和文化危机,以致渔村共同体的消失。
5 结语
渔民转产转业,是实现海洋捕捞业健康发展、人类面向海洋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2002年以来,作为福建平潭流水镇重点渔业村庄的东美村,渔民也面临转产转业的现实选择。渔民陆续放弃或者转让了生产工具以及渔船证明,其逐渐丧失了对海洋资源的合法使用权。相应地,渔民基于地缘、神缘及渔业劳作等形成的渔村共同体,亦面临着一系列前所未有的冲击和嬗变,处于走向衰落乃至终结,抑或重建的转折点。它引起我们的关注和思考,并带来我们对传统保护与可持续发展如何均衡的遐想。笔者认为,人类实现海洋的健康、生态与可持续发展,并不必然与传统海洋捕捞二元对立,渔村共同体也未必会完全瓦解。若能顶层设计,合理谋划,海洋捕捞承载的传统与现代应能在未来社会和谐共存,渔村共同体焕发生机也未必不可能。当然,如何留住传统,又能守住蓝天碧海,同时还能适应现代化而与时俱进,仍需要继续探索。
[1] 费迪南·滕尼斯,林荣远译. 共同体与社会[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2] 刘明德,胡珂.乡村共同体的变迁与发展[J].成都大学学报(社科版),2014(3):20-27.
[3] 李培林.巨变:村落的终结——都市里的村庄研究[J].中国社会科学,2002(1):168-179.
[4] 陆宝良.村落共同体的边界变迁与村落转型——基于一个城郊村的观察和思考[D].杭州:浙江大学,2012.
[5] 蔡磊.中国传统村落共同体研究[J].学术界(月刊),2016,218(7):168-175.
[6] 费孝通.乡土中国与生育制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7] 许远旺,卢璐.中国乡村共同体的历史变迁与现实走向[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15(2):127-134.
[8] 唐国建.沿海渔村的终结——海洋开发、资源再配置与渔村的变迁[M].北京:海洋出版社,2012.
[9] 朱晓芳.明清以来福建沿海渔民研究[D].福州:福建师范大学,2007.
[10] 李培林.村落的终结——羊城村的故事[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11] 郭于华.农村现代化过程中的传统亲缘关系[J].社会学研究,1994(4):49-58.
[12] 费孝通.江村经济[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13] 曹锦清.黄河边的中国[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
[14] 吴重庆.农村“空心化”状态下的公共产品供给[EB/OL].(2015-09-02)[2017-06-15].http://www.cntheory.com/zydx/2015-09/ccps150902ZAC9.html.
[15] 赵泉民,井世洁.“后乡土”时代人际关系理性化与农民合作的困境与出路[J].江西社会科学,2013(8):203-208.
[16] 中央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7] 李强.主动城镇化与被动城镇化[J].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20(6):1-8.
Transmutationandreconstructionofcoastalfishingvillagecommunityunderthebackgroundofproductionandoccupationtransfer:AcasestudyofPingtanDongmeiVillageinFujianProvince
YANG Hong-yun1, JING Jing2
(1.CollegeofEconomicsandManagement,FuzhouUniversity,Fuzhou350116,China; 2.CollegeofHumanitiesandSocialSciences,ZhongshanInstitute,UniversityofElectronicScienceandTechnologyofChina,Zhongshan528402,China)
In order to adapt to the fishery adjustment in the exclusive economic zone and to transfer the surplus fishery labor force in the coastal areas and promote the sustainable use of marine fishery resources, since 2002, the policy of Production and Occupation Transfer for the Coastal fishermen from the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has started to be implemented. This is based on the protection of marine resources and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fisheries, but it makes the fishermen lose the survival resources on which generations depend. Correspondingly, it brings a series of influences and impacts on the fishing village community which is facing the relational alienation of affinity, geographical weakening, professional relationship enhancement, cultural decline and so on. This has led to the thinking and discussion on the future development trend of the fishing village community. Based on the theoretical basis of the "community", this paper combs the changes through field investigation and in-depth observation in the Dongmei village of the coastal fishing village of Pingtan, Fujian Province, and puts forward the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building the community, including macro-policy support from the government, cultural protection and consideration of the subjective core of fishermen.
production and occupation transfer; coastal fishing village community; transmutation and reconstruction
2095-3666(2017)04-0241-08
10.13233/j.cnki.fishis.2017.04.001
2017-07-17
2017-08-22
杨宏云(1975-),博士,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华商创业、文化产业发展、海洋文化与旅游等。E-mail:fz2014yhy@163.com
C 912.82
A
——基于山东省5个地级市的渔户调查数据*
- 渔业信息与战略的其它文章
- 小型聚乙烯材料渔业船舶应用分析
- 渔业科技前沿
- 渔业信息与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