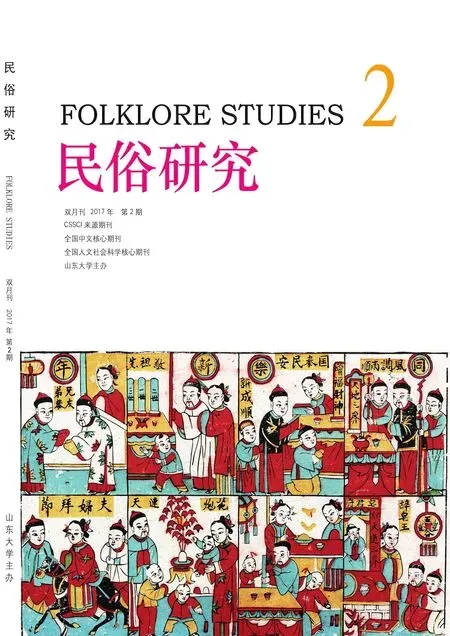“走百病”民俗的渊源与流变
陈恩维
“走百病”民俗的渊源与流变
陈恩维
走百病是中华民族的一项古老而又分布极为广泛的传统习俗,起源于南北朝时期的耗磨日习俗,约在唐代与驱鬼逐疫、元宵节俗、少数民族放偷习俗、偷瓜祈子习俗相混合,汇合了照耗、逐疫、过桥、采青、赏灯、摸钉等多种习俗,形成了度厄、逐疫、求子等多种内涵,是一种兼具累积沉淀型和合流变形型类型特点的民俗。
走百病;过桥;采青
走百病,北方多称作度百厄、游百病,散百病,南方多称为走桥、走三桥,岭南地区则多称为“采青”、“偷青”等。此俗起源于南北朝时期的耗磨日习俗,约在唐代与其他多种习俗相混合,形成了度厄、逐疫、祛病、求子等多种内涵,是一种兼具累积沉淀型和合流变形型类型特点的民俗。由于其来源混杂,变化多歧,地方性差异较大,所以学界对其渊源流变的综合性的梳理甚少。本文不揣浅陋,对“走百病”民俗颇为复杂的渊源流变情况作一梳理,以期加深我们对于这项传统民俗活动的认知与理解。
一、走百病之缘起
走百病习俗的直接渊源,为“耗磨日”。光绪《东光县志》卷二指出:“正月十六日,古谓之耗磨日。……此乃走百病之缘起。”*光绪《东光县志》卷二,光绪十四年刻本。按,“耗磨日”,又称“耗磨辰”或“耗日”,忌磨茶、磨麦和一切事务,官私不开仓库,皆停业饮酒。这一风俗形起源于何时?南朝彭城人刘敬叔《异苑》卷八记载了两则故事,隐约透露了一些信息。其一曰:“余姚县仓封印完全,既而开之,觉大损耗,后伺之,乃是富阳县桓王陵上双石龟所食,即密令毁龟口,于是不复损耗。”其二曰:“琅琊费县民家,恒患失物,谓是偷者,每以扃钥为意,常周行宅内。后果见篱一穿穴,可容人臂,甚滑泽,有踪迹,乃作绳驱,放穿穴口,夜中忽闻有摆扑声,往掩,得一髻,长三尺许,从此无复所失。”*(南朝宋)刘敬叔撰,范宁校点:《异苑》卷八,中华书局,1996年,第79页。这两则传说都说明南朝刘宋时已有虚耗鬼怪损耗、偷盗财物的传说。鬼怪善盗,使公家和私人的财物损耗,所以大家不开仓库,不事劳作,以减少损耗,这实际上是后世所说“耗磨日”习俗的滥觞,其起源时间当在南北朝,分布地域则包括北方的黄河流域和南方长江流域。
到了唐代,“耗磨日”已经相沿成俗,唐诗中相关描写颇多。张说《耗磨日饮》其一云:“耗磨传兹日,纵横道未宜。但令不忘醉,翻是乐无为。”其二云:“上月今朝减,流传耗磨辰。还将不事事,同醉俗中人。”赵冬曦《和张燕公耗磨日饮》曰:“春来半月度,俗忌一朝闲。不酌他乡酒,无堪对楚山。”*(唐)张说:《张燕公集》卷九,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61页。上述三首诗,说明了耗磨日至迟在唐玄宗时期已经流行。正月十六这一天,因为虚耗鬼要偷盗财物和欢乐,所以唐人都不磨麦,甚至什么事也不干,只是饮酒取乐。此俗历代相传至今。宋代袁文《瓮牖闲评》云:“正月十六日大耗,京师局务如都商税务亦休务一日,其令如此。”*(宋)袁文:《瓮牖闲评》卷三引《嘉祐杂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25页。南宋戴复古《闻严坦叔入朝再用前韵》:“凄凉风雨日,强把瓮头春。独守空虚室,那逢耗磨辰。”*(宋)戴复古:《石屏诗集》卷四,《四部丛刊》本,第17页。王世贞《正月十六日于鳞会于齐河挟一生为姑布术者》:“小酌可成烧尾宴,壮心俱付耗磨辰。”*(明)王世贞:《弇州四部稿》卷四十,《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279册,第501页。乾隆《上元后一日小宴廷臣用重华宫赐宴韵》:“岂是耗磨沿俗例,要因昭鬯遇昌年”。*《乾隆御制诗集》卷三十八,《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352册,第696页。上述对于耗磨日的记载,也反映了当日人们守财避耗、休闲求乐的民俗心理。现今甘肃河西走廊的武威、张掖、酒泉等地的民间还留存此俗:“正月十六不干活,牛啊马啊歇一天”。也就是说正月十六人们还不用开工干活。这是“耗磨日”的遗留。
盛唐时期,耗磨日习俗还与钟馗信仰混合,“虚耗”成为鬼名,形成禳除习俗。*有关“虚耗鬼”的由来与禳除习俗,详参常建华《岁时节日里的中国》,中华书局2006年,第250-265页。唐代卢肇《唐逸史》记载过钟馗捉住“虚耗”吃掉的故事:唐玄宗梦到一个小鬼偷盗了自己的玉笛和杨贵妃的香袋,玄宗叫住小鬼,鬼自称叫“虚耗”、喜欢偷盗他人的财物,也能偷去他人的欢乐、使人变得忧郁。玄宗大怒,立即唤人,于是有一个大鬼出现将虚耗撕成两半吃掉了。*(元)陈元靓编:《岁时广记》卷四十,《丛书集成初编》本,第181册,第435-436页。后来唐玄宗让吴道子画钟馗捉鬼图,并批示说:“灵祗应梦,厥疾全瘳。烈士除妖,实须称奖。因图异状,颁显有司。岁暮驱除,可宜遍知。以祛邪魅,兼静妖氛。仍告天下,悉令知委。”*(宋)沈括著,胡道静校证:《梦溪笔谈校证·补笔谈》卷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987页。上述故事的流行,说明了耗磨日与盛唐、中唐广泛流传的钟馗信仰*高国藩:《敦煌古俗与民俗流变》,河海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332页。融合,新出现了驱鬼、驱邪等文化内涵。
与此同时,由于虚耗成鬼,唐代又形成了耗磨日的禳除习俗——“照虚耗”。照耗日点灯,与古人认为灯火可以驱鬼的观念有关。南朝宗懔《荆楚岁时记》说:“正月末日夜,芦苣火照井厕中,则百鬼走。”*(南朝·梁)宗懔撰,宋金龙校注:《荆楚岁时记》,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8页。即在正月第一个末日晚上,点燃用芦苇捆扎的火把,照亮井厕里,那么众鬼就会逃跑。灯火驱鬼的观念在六朝十分流行,到了唐代则为照虚耗习俗所借用,形成了“照虚耗”的习俗,一直流传到清代。北宋吕原明《岁时杂记》:“交年之夜,门及床下以至圊溷,皆燃灯,除夜亦然,谓之照虚耗。”*(元)陈元靓编:《岁时广记》卷三十九,《丛书集成初编》本,第181册,第431页。南宋周密《武林旧事》卷三《岁晚节物》:“明灯床下,谓之‘照虚耗’。”*(宋)孟元老等:《东京梦华录(外四种)》之《武林旧事》,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第384页。不过,各地照虚耗的时间并不一致,主要有除夕、祈灶日(腊月二十四)、元宵节、天仓节(正月二十日至二十五日是其节期)。宋代以来“虚耗”被理解为老鼠,因此照耗又衍生出照耗和老鼠嫁女习俗。《古今图书集成·历象汇编·岁功典》卷九一“季冬部”引《琐碎录》:“二十四日床底点灯,谓之照虚耗也。二十四日取鼠一头烧在于子地上埋之,永无鼠耗。”*《古今图书集成·历象汇编·岁功典》卷九一。老鼠,也称耗子。腊月祀灶日照虚耗时举行烧老鼠的仪式以祈求“永无鼠耗”。唐代照虚耗是在灶里,宋代扩大在为厨、厕、门及床下,清代的范围更广及浴室、井以及楼上、鸡埘等阴暗、潮湿之处,这是把虚耗作为鼠耗理解的缘故。道光《佛山忠义乡志》卷五:除夕点灯于房,曰“照耗”。*(道光)《佛山忠义乡志》卷五《乡俗志》,《中国地方志集成:乡镇志专辑30》,江苏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62页。如今,不少地方都有老鼠嫁女的故事和年画,其实就是照耗习俗的一个反映。给老鼠嫁女点灯,其意义在驱除“虚耗”,一种认为老鼠为害人间,使老鼠嫁女也有“送”和“出”之意,“以礼相送,化灾害为吉祥”,是一种求平安的传统思想。另一种认为“以鼠嫁女喻人丁兴旺,多子多孙”,是来源于鼠的生物特征。老鼠快而多的惊人繁殖力,实在令渴望多子多孙的人家所向往。*宋兆麟:《灭鼠还是求子?——老鼠嫁女年画剖析》,《西北民族研究》2007年第4期。因此,老鼠嫁女便成了如鼠一般多子多孙的象征,因此有了求子的内涵。
“耗磨日”的禳除习俗,还与古代驱鬼逐疫仪式——傩祭混合。逐瘟驱鬼的习俗,最早可追溯到周代以来逐除疫鬼的驱傩仪式。《荆楚岁时记》载:“十二月八日为腊日,……谚云:‘腊鼓鸣,春草生。’村人并击细腰鼓,戴胡公头,及作金刚力士以逐疫。”*(南朝·梁)宗懔撰,宋金龙校注:《荆楚岁时记》,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64页。古人认为十二月厉鬼“随强阴出害人”*(唐)孔颖达:《礼记正义》,(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本,中华书局,1980年,第1383页。,所以要行大傩以逐除之。因此形成了腊月击鼓驱疫之俗。宋以后,击鼓驱除鬼祟,时间为岁暮至来年的元宵节。宋程大昌《演繁露》卷六:“湖州土风,岁十二月,人家多设鼓而乱挝之,昼夜不停,至来年正月半乃止。问其所本,无能知者。但相传云,此名打耗。打耗云者,言警去鬼祟也。”*(宋)程大昌:《演繁露》卷六《腊鼓》,《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18页。由于时间的接近,一些地方的虚耗日与逐疫之傩礼出现了混合。如光绪《寿阳县志》载:“士女游观街陌,并入官署不禁,谓之‘走百病’。十六日,撞钲击鼓,挨户作殴逐状,略如古人之傩,谓之‘逐虚耗’,亦曰‘逐瘟’。夜燃灯、燔柴如元旦,谓之‘照虚耗’。”*丁世良、赵放:《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华北卷》,书目文献出版社,1991年,第589页。
综上所述,脱胎于“耗磨日”的走百病习俗,是在民间虚耗传说的基础上不断衍生,唐代以来与钟馗信仰、点灯驱鬼习俗融合形成“照虚耗”习俗,宋代以来又进而与驱鬼逐疫习俗混合,从发展形成了度厄、逐疫、求子等多种文化内涵。
二、走百病与过桥
明清时期,黑龙江、吉林、陕西、北京、河北、山东、江苏、浙江、广东、福建、四川、贵州、云南、广西、海南、台湾等省的地方志书,多见“走百病”的记载和描述,各地“走百病”习俗仪式与内涵并不完全一致,其最为引人注目的是“过桥求子”。
早期唐宋文献中有关“虚耗日”、“照虚耗”的记载,鲜少有走桥的记载,其求子的内涵也并不明显。但是,明代以来“走百病”的相关文献中关于“过桥”的记载就比比皆是了。明刘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卷二:“(正月)八日至十八日,集东华门外,曰灯市。贵贱相遝,贫富相易贸,人物齐矣。妇女着白绫衫,队而宵行,谓无腰腿诸疾,曰走桥。”*(明)刘侗、于奕正著,孙小力校注:《帝京景物略》卷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101页。明沈榜《宛署杂记》记载:“正月十六夜,妇女群游,祈免灾咎。前令人持一香辟人,名曰走百病。凡有桥之所,三五相率一过,取度厄之意。”*(明)沈榜:《宛署杂记》卷十七《民风一·土俗》,北京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190页。这里只是说,走百病时凡是有桥的地方则需要过桥,过桥并没有成为“走百病”的必须仪式。南方多桥,走桥开始成为南方地区走百病的必要内容。明范景文《文忠集》卷十有诗:“火树明时夜色骄,蝶飞照见上吴绡。纱笼引向皇城下,女伴相邀共走桥。”*(明)范景文:《文忠集》卷十,《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295册,第597页。江南多桥,甚至还出现“走三桥”的习俗。明人陆伸《走三桥词》云:“细娘分付后庭鸡,不到天明莫浪啼。走遍三桥灯已落,却嫌罗袜污春泥。”清顾禄《清嘉录·正月·走三桥》中说:“元夕,妇女相率宵行,以却疾病。必历三桥而止,谓之‘走三桥’。”*(清)顾禄撰,来新夏点校:《清嘉录》卷一,中华书局,2008年,第58页。“三”不一定是实指,有时也可以表示“多”的意思。如宁波必须“走过七桥,可得福寿”。*(清)吴友如等绘:《点石斋画报》(大可堂版)第9册之2《走桥韵事》,上海画报出版社,2001年。但是,北方多平原旷野,并不是每个地方都有桥,因此一些地方甚至临时架桥以走百病。民国《中牟县志》载:“城内于四达巷口,架木为桥,纵游三日,曰‘过天桥、走百病’。”*丁世良、赵放:《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中南卷》,书目文献出版社,1991年,第38页。架木为桥的习俗,主要出现在桥梁较少的北方都市,称“百子桥”、“星桥”、“天桥”等,用以代替,且又可求子。清乾隆《新乡县志》云:“(上元)于旷地叠木为星桥,曰‘天桥’,结草成闉,方十丈许,曲折通径,男女绕行,昼夜不疲,谓之‘走百病’。”*丁世良、赵放:《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中南卷》,书目文献出版社,1991年,第47页。清嘉庆河南《洛阳县志》云:“元宵……衢首结彩桥,妇女行其上,曰‘百子桥’。”*丁世良、赵放:《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中南卷》,书目文献出版社,1991年,第261页。又民国《洛宁县志》云:“元宵……街衢或结彩桥,谓之‘百子桥’,妇女行其上,谓宜男。”*丁世良、赵放:《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中南卷》,书目文献出版社,1991年,第297页。还有地方,则出现了桥的“替代物”。比如,南京人正月十六喜欢登城头、并且有“爬城头,踏太平,走百病”的说法。*(民国)潘宗鼎:《金陵岁时记·走百病》,南京出版社,2006年,第20页。
走百病与“过桥”习俗的融合,这与桥的象征性有关。桥梁以各种姿态架设于河流、沟壑、峡谷之上,它使两岸得以沟通,是人们日常生活中司空见惯又不可或缺的事物。桥可以说是通往某地的必经之路,起到联系沟通的作用,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通往某地的关卡,通则过,不通则难过。以此种实际功能为依据,人们便对桥赋予了许多重要的象征意义。这种象征意义“深切地关系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与人生历程:从生老病死到婚丧嫁娶,从起居行旅到互通有无,从爱情到事业,从理想到信仰”,其中与生育婚恋相关的习俗为大宗,在构成或表达男女两性之间的交涉及其相关事象的象征或隐喻方面最为突出。因此走桥不仅关乎健康,在相当程度上还涉及到祈嗣。*周星:《汉民族的桥俗文化》,载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编《中国社会发展与文化研究的探索》,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142-170页。桥作为一种生育崇拜的象征巫物,而‘桥’俗则为这种生育崇拜的假想模拟,具体功能集中表现在祈求和招魂上。由于人们对种种神灵感到敬畏和惧怕,但又无能为力,于是用架桥方式积累阴功,取悦神灵。一方面希望神灵能保佑自己,镇鬼驱邪;另一方面,求神赐子,保佑平安。然而,桥这种生育象征巫物本身没有任何生育魔力,它还需要一种媒体——人的参与活动。这正是桥产生生育力的源泉。由于桥大多修在过往行人密集的交通要道上,无数路人经过、休息一下,甚至触摸栏杆,都有可能使桥产生这种生殖力来。*覃绍山:《中国南方少数民族桥俗浅探》,《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92年第5期。有学者指出:“广大汉族地区整个春节期间的节俗活动,一般都以正月十五为界限。十五以前多以家庭、家族、宗族的活动为主,十五以后则转而为群体的、集团的活动,多采取‘走会’的形式;而桥、城门等交通要衙大都是走会的必经之路,人们认为只要从此处经过,必然会感染节日中的集团的生殖魔力。”*张铭远:《生殖崇拜与死亡抗拒》,中国华侨出版公司,1991年,第75页。这实际上源于古代人们对于集团活动生殖力的一种信仰崇拜观念,也是民间巫术思维中相似律、接触律和交感律的反映。
三、走百病与采青
明清以来,南方不少地方的“走百病”习俗中出现了“偷青”的细节,这其实是走百病习俗混合放偷求子习俗、偷瓜祈子习俗后的一种变形。
放偷的习俗,最早形成于南北朝时期北方各少数民族。据《魏书·孝静纪》载:东魏孝静帝天平四年(公元537)春正月“禁十五日相偷戏。”*(北齐)魏收:《魏书》卷十二,中华书局,1974年,第301页。正月“十五相偷”,既然有禁止的必要,说明当时已相沿成俗。不过,禁止的效果差强人意。如宋叶隆礼《契丹国志》卷二十七:“正月十三日,放国人做贼三日。”*(宋)叶隆礼撰,李西宁点校:《契丹国志》卷二十七,齐鲁书社,2000年,第254页。女真族则于十六日夜进行相偷戏。《帝京景物略》卷二曰:“妇女相率宵行,以消疾病,曰走百病,又曰走桥。金元时,三日放偷,偷至,笑遣之,虽窃至妻女不加罪,夷俗哉。”*(明)刘侗、于奕正著,孙小力校注:《帝京景物略》,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89页。洪皓《松漠纪闻》也记载,女真人“正月十六日则纵偷一日以为戏。妻女、宝货、车马为人所窃,皆不加刑”。有情人“先与室女私约,至期而窃去者,女愿留则听之。自契丹以来皆然,今燕亦如此。”*(宋)洪皓撰,翟立伟标注:《松漠纪闻》,见李澍田主编《长白丛书(初集)》,吉林文史出版,1986年,第30页。其实,这是一种古老的求爱求子的方式,反映了尚处于辽王朝统治下的早期女真族由对偶婚制向个体婚制转变的诸多细节。*刘肃勇:《从“放偷日”习俗看女真族早期婚制与经济生活》,《满族研究》2009年第1期。这种风俗后来又被女真族的后人——满族人所吸收,并将放偷与汉族的照耗混合,谓之“照贼”。
唐代,由于长安一带胡汉交流频繁,北方少数民俗的放偷习俗为汉族吸收,并与元宵节习俗合流。这种混合首先表现在“金吾弛禁”和放偷的合流。唐代起正月十五夜前后各一日暂时驰禁,准许百姓夜行,称为“放夜”。韦述《西都杂记》载:“西都京城街衢,有金吾晓暝传呼,以禁夜行;惟正月十五日夜敕许金吾弛村,前后各一日,谓之放夜。”*曹元忠辑本:《两京新记》卷一,《南菁札记》本卷一,清光绪二十一年刻本。宋高承《事物叙原·岁时风俗》:“唐睿宗先天二年正月望,初驰门禁”。*转引自夏本戎主编:《五华民俗史话》,云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8页。金吾,古官名,掌管京城的戒备。金吾禁夜,实际是为了防止夜晚出行,而“放夜”一则是为元宵夜灯节人们的外出游玩服务,一则也是吸收了“放偷”习俗。明陆启浤《北京岁华纪》载:“正月十六日夜,归女俱出门走桥。不过桥者,云不得长寿。手携钱贿门军摸门锁,云即生男。”*(清)于敏中等编纂:《日下旧闻考》卷一百六十《风俗》,北京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2349页。“门军”,即唐代的“金吾”,贿赂他们的目的,让他们提供方便“放偷”,而放偷则是为了仪式性的“求子”。清初查嗣瑮在《燕京杂咏》中言:“六街灯月影鳞鳞,踏遍长桥摸锁频。略遣金吾弛夜禁,九门犹有放偷人”。*(清)查嗣瑮:《查浦诗钞》卷五,《四库未收书辑刊》第8辑20册,北京出版社,1997年,第64页。此诗前两句描写走百病,后两句写放偷,显示了二者的融合。如清代褚人获《坚瓠续集·耗磨放偷》云:“正月十六日,古谓之耗磨日。官私不开仓库……是日各家皆严备。遇偷至,则笑而遣之,虽妻女车马宝货为人所窃,即获得,亦不加罪。闻今扬州及黔中尚然。而燕地正月十六夜之走街,恐亦遗俗也。”*(清)褚人获:《坚瓠续集》卷二,《笔记小说大观》(七),广陵古籍刻印社,1984年,第356页。这反映了扬州地区正月十六“耗磨日”与“放偷”、“走百病”出现合流。
北方的放偷习俗,到了南方则演变为走百病时的“偷青”,或者说“采青”。地方史志记载显示,元宵期间有“偷青”习俗的地区主要在我国东南、华南和西南地区,分布在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如江苏、浙江,湖北、福建、江西、湖南、台湾、广东、广西、云南、贵州、四川等地,即中国秦岭-淮河一线以南地区,是为自然地理意义上的华南地区,而其他地方则比较少见。“偷青”的目的在于祈子。《清稗类钞·迷信类》说:“广州元夕,妇女偷摘人家蔬菜,谓可宜男,名曰采青。花县曾晓山照有诗云:‘篱头雨歇湿游尘,弱柳绯桃解媚人。最爱蔬中冬芥好,年年生子及青春。’”又说:“广东妇女之艰嗣续者,往往于夜中窃人家莴苣食之,云能生子。盖粤人呼莴苣为生菜也。”*(清)徐珂:《清稗类钞》,中华书局,1984年,第4661页。各地出现的走百病偷青习俗,又与我国南方曾普遍曾在的“偷瓜祈子”习俗有关。这一习俗在各地发生的时间有所不同,有的发生在中秋,有的发生在元宵(或正月十六)。广东东莞旧俗,逢中秋月夜,有些久婚不孕的妇女便走出家门,沐浴月光,希望早生贵子,谓之“照月”。在少数民族地区,偷瓜祈子习俗也分布普遍。如侗族的中秋节流传“偷月亮菜”,传说这天晚上天宫仙女下凡,将甘露洒遍人间,人们在月光下偷了这种洒有甘露的瓜果蔬菜,就能获得幸福。所以青年男女便到意中人的园子里去“偷”,“偷”时嬉笑打闹,引出自己的情侣。*巫瑞书:《南方传统节日与楚文化》,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91页。更多的则是发生在元宵节或者正月十六走百病之时。如江苏无锡旧时女子在“走三桥”时,通常在路旁任拔一菜,左右拂其肩背,说是可拔除不祥。在江西南康的妇女则三五为群,窃摘别人园蔬中之芥菜和白菜,然后中间插以烛火,沿街擎照,谓之“拉青”。广西龙州县“十五日,偷青。每年是晚,老少男女联群结队,俟更深人静,越园度圃偷取蔬菜,名曰‘偷青’。”凤山县“十五日元宵,偷青,相传以禳不祥。”来宾县“上元夜间,士女有偷青之戏。”贵县“上元夜,俗例妇女入人园圃摘蔬菜,名曰‘采青’,盖取一年清洁之兆,园丁亦不禁。”*丁世良、赵放:《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中南卷》,书目文献出版社,1991年,第921、943、979、1068页。广东、福建等地则主要是偷摘人家的园蔬或是春帖,若能遭到他人诟骂,以为将来必得佳婿。流行于贵州省黄平一带苗族的偷菜节也是在每年农历正月十五日举行。节日这天,姑娘们便成群结队去偷别人家的菜,严禁偷本家族的,也不能偷同性朋友家的。在台湾,有未婚女性在元宵夜偷菜摘葱,将来会嫁好老公的传统习俗,俗称:“偷得葱,嫁好公”、“偷得菜,嫁好婿”。
在偷青的习俗中,偷盗是一种必需的“仪式”。偷青得子的仪式,实际是一个求子巫术,符合巫术的接触律与相似律原理。在中国的民间信仰中,福气是一种很实在的东西,它可以通过仪式保留或传递。在某些流行此俗的地区,人们会特别注意被偷的人家是否是多子多孙的吉祥之家,因而“偷青”、“偷瓜”就不是简单地偷一个瓜,而是通过青菜或者瓜果传递福气。向人家要青菜或者瓜果是可以的,向人家要子孙或福气,则是不被欢迎的,所以“偷”就成了必需的手段。被偷的人家在这个习俗中,一般都表现出配合而不加指责。而偷青的人们则相信被骂得越凶越应验,用听到人家叫骂证明偷的成功。这种偷青者以受詈为祥,失者以不詈为吉的习俗,似乎是藉着民俗的论述来“合理化”非法行为本身的正当性,但这种在特别的节庆里,反常的,非礼的,甚至违法的行为,不论是“偷”,“骂”,或“放”,毋宁只是象征性的仪式表演。*陈熙远:《中国夜未眠——明清时期的元宵,夜禁与狂欢》,《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2006年第4期。
然而,近代以来,随着近代观念和商品经济的发展,这种仪式性的偷取开始受挫。《吴友如画宝》之《风俗志图说》“采青受挫”记载:“芳郊草绿,紫陌风和,闺中小儿女联襼嬉游,为拾翠寻芳之举,亦一韵事也。而粤中风俗,乃不卜昼而卜夜。每当金吾不禁,玉漏停催,鬓影衣香与火树银花相掩映,迨至更阑人静,潜入人家菜圃中,窃取菜蔬,谓之‘采青’。虽老圃见之,亦不之禁,惟索取利市钱。所取菜蔬,以生菜为上,盖取生育之意。回至家,即于露天烹煮,聚家人而共食之。咏皮日休‘紫甲采从泉脉畔,翠牙搜自石根旁’之句,觉菜根滋味,真有趣而弥长者。今届元夜,肇城一带,适值考试,菜值较昂。有采青妇至东门外菜圃中,正拟薄言采之,讵菜佣妇坐于暗陬,呵阻之,不听,乃以挑菜竿击之,致伤其额,微有血痕。夫采青所以取吉利也,而反致受辱,彼菜佣妇亦可谓大煞风景矣。”*(清)吴友如绘:《吴友如画宝》第十集下《风俗志图说上·采青受挫》,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第十集下之二十一页背面。这则图文并茂的记载,生动记录了广东“采青”习俗及其信仰内涵,也反映了其逐渐消失的原因。如佛山古镇的“行通济”习俗中,原本的偷青,民国时期已经变成了摆卖生菜。*《犹言旧习“行通济”,郑掷肥鹅取兆头》,《越华报》1936年2月9日星期日特刊。
四、走百病与元宵
由于时间上的接近,也由于求子仪式的接近,“走百病”与元宵节开灯习俗也出现了融合。这种混同,在唐代“照耗”习俗形成时期,就已经出现。明刘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卷二云:“张灯之始上元,初唐也,……上元三夜灯之始,盛唐也,玄宗正月十五前后二夜,金吾弛禁,开市燃灯,永为式。”*(明)刘侗、于奕正著,孙小力校注:《帝京景物略》卷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88页。如前所述,唐代正月十六日为“耗磨日”,灯照是禳除虚耗的主要形式,而唐代又有“上元三夜灯”的习俗,二者时间相连,仪式相似,因而出现了混合。另一方面,因为“灯”与“丁”谐音,所以赏灯求子的文化内涵十分突出。如浙江省的金华、兰溪、衢州、浦江等地,每年正月都有盛大的“迎桥灯”活动,有接灯(丁)、分子息等与祈嗣深切相关的仪式细节的设计与表演。闽粤部分地区谓女子元宵观灯有繁衍子孙的神力,盖“灯”与“丁”谐音,因男称“丁”,女称“口”,更引申为生男的吉兆。故而尚未生育与未生男孩的妇女,元宵节观灯尤为踊跃,而且专看有生子好口彩的灯,如贵子麒麟灯、送子娘娘灯、五子登科灯、观音送子灯。
在北京、河北、山东、福建等地,在元宵节走桥观灯的同时,则有摸门钉以为祈嗣吉兆的民俗。明刘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卷二记载妇女“走桥”之后,又“至城各门,手暗触钉,谓男人祥,曰‘摸钉儿’。”*(明)刘侗、于奕正著,孙小力校注《帝京景物略》卷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101页。又《长安客话》云:“京都元夕,游人火树沿路竞发,而妇女多集玄武门(前门)抹金铺。俚俗以为抹则却病产子。”*(明)蒋一葵:《长安客话》卷二《皇都杂记》之《金铜钉》,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32页。清窦光鼐、朱筠《日下旧闻考》引《陈检讨集》云:“燕京风俗,元夜妇女竞往前门摸钉为戏,相传谶宜男也。”古城门门钉为九行九列计八十一枚,九为最大阳数;又,门钉形像阳具,俗或以为摸之宜男。《日下旧闻考》引《北京岁华记》云:正月十六日妇女出门走桥,并“手携钱贿门军摸门锁,云即生男。”*(清)于敏中等编纂:《日下旧闻考》卷一百六十《风俗》,北京古籍出版社,1985,第2349页。徐釚《词苑丛谈》卷九:“京师旧俗,妇人多以元宵一夜出游,名‘走桥’。摸正阳门钉,以袚除不祥,亦名‘走百病’。予向欲填一词记之,近见《青城集》中《木兰花令》正咏此也。句颇雅丽,词云:‘元宵昨夜嬉游路,今夕还从桥下去。名香新暖绣罗襦,翠带低垂金线缕。回头姊妹多私语,鱼钥沈沈纤手拄。钗横鬂軃影参差,一片花光无处所。”又录女词人徐灿《燕京元夜词》云:“华灯看罢移香屧,正御陌,游尘绝,素裳粉袂玉为容,人月都无分别。丹楼云淡,金门霜冷,纎手摩娑怯。三桥宛转凌波蹑,敛翠黛,低回说。年年长向凤城游,曾望蕊珠宫阙。星桥云烂,火城日近,踏遍天街月。”*(清)徐釚著,王百里校:《词苑丛谈校笺》,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第532页。“钉”与“丁”同音,而“丁”又象征男子,所以妇女特别是未有身孕的妇女必须诚心“摸钉”,以求子嗣,使家业兴旺,有传宗接代之人。妇女们热衷于去正阳门“摸钉”,因正阳门秉“正阳之气”,摸了正阳门的门钉,宜生男丁,消灾祛病。《清稗类钞·迷信类》甚至记载了摸秀才的“宜男”民俗:“科举时代,江苏之常州各属院试,必于江阴。凡赁庑者,一衿既青,门前屋角,必有妇女于暗中牵襟弄裾,名曰摸秀,谓可得佳壻,兆宜男。又或于院试奖赏之日,小家新妇联袂出游,故与新秀才摩肩而过,则曰轧秀。”*(清)徐珂:《清稗类钞》,中华书局,1984年,第4659页。
摸丁习俗,还有其他变形,如摩狮子、摸乌龟等,与摸门钉同出一意。清同治《保靖志稿辑要》云:“(正月)十三夜,乡间老少妇女入城,在各寺庙观灯,谓之‘走百病’。参府署前狮子系明宣慰司遗制,乡俗每于元霄(宵)各备香烛,群相祷祝,头痛摸头,腹痛摸腹,耳目手足亦然,俗谓之‘摩狮子’,盖祈以治病也。”*丁世良、赵放:《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中南卷》,书目文献出版社,1988年,第643页。仔细推究这项民俗活动的原初意义,它最初应该与过桥时摸桥栏一样,源于古代人们对于集团活动生殖力的一种信仰崇拜观念。潘光旦先生曾在为蔼理斯《性心理学》所作的译者注中指出:“性与触觉的关系,方面甚多,……一个女子,要她在日常环境之下,和男子的生殖器官发生触觉的关系,当然有种种的顾忌,但若和它的象征发生接触,就没有顾忌了。不但没有顾忌,并且往往是一件公认为吉利的事;至于吉利何在,就得看当时当地社会的说词了。……徐灿所作的词里有句说,‘丹楼云淡,金门霜冷,纤手摩娑怯’,指的就是摸钉这回事。说‘宜男兆’,说‘走百病’,都是所谓说词了,要紧的还是那黝摸。”*(英)霭理士著,潘光旦译注:《性心理学》第二章《性的生物学》注48,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97页。换言之,摸钉,其实是在摸男性生殖器的象征物,其实是民间巫术思维相似律和接触律的反映。
由于与元宵节俗的合流,各地走百病还出现了狂欢的趋向。前面提到唐代虚耗日有“不事事”和“饮酒”作乐的习俗,已包含狂欢的意味在内。成书于五代时期的《开元天宝遗事》记载:“都人士女每至正月半后,各乘车跨马,供帐于园囿或郊野中,为探春之宴。”*(五代)王仁裕《开元天宝遗文》“探春”条,中华书局,2006年,第58页。光绪《抚宁县志》载“‘上元’张灯,放烟火,戏秋千,妇女走百病,时则有春宴。”*《抚宁县志》,清光绪三年刻本,引自丁世良、赵放《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华北卷》,书目文献出版社,1991年,第255页。上述材料都明确记载走百病和探春宴习俗出现合流。
在“走百病”民俗中,求子群体以妇女为主体,但对于祛病和春宴来说,则可以是男女同欢、老少皆宜了。之所以对女子出游大开绿灯,首先是为了祛病。封建社会里的女性,特别是年轻女子,受妇德的束缚,终年禁锢家中;大户人家的女儿更是深居闺阁,连楼都不得轻易下。元宵节却是例外,能得放飞出门且是夜游,踏街观灯走百病。年轻妇女梳妆打扮后,三五成群,健步行走,其信仰基础是因为相传这一天夜晚鬼穴空,百病都归尘土,所以此夜外出可以避疫,可避百病,否则的话就会终年手臂疼痛、头昏眼花。其次,元宵节赏花灯正好是一个交谊的机会,未婚男女借着赏花灯也顺便可以为自己物色对象。欧阳修《生查子》云:“去年元夜时,花市灯如书;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就是描述元宵夜男女青年与情人相会的情境。传统戏曲陈三和五娘是在元宵节赏花灯进相遇而一见钟情,《春灯谜》中宇文彦和影娘在元宵定情,都反映了这一民俗。有学者指出:“‘走桥’其实不过是个形式,‘盛妆出游’才是正经。”*陈熙远:《中国夜未眠——明清时期的元宵,夜禁与狂欢》,《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2006年第4期。宋代以来,在宋明理学的影响下,开始讲究男女授受不亲,所以出现男女不同游的讲究。如正德《江宁县志》载:“箫鼓声闻,灯火迷望,士女以类夜行。”*(正德)《江宁县志》卷二,《金陵全书》本,南京出版社2012年,第718页。意思是男女分别结伴而行。但是也有一些地方,仍是男女俱出。如安徽全椒、山东邹城等地都是这样。还有一些地方“走百病”时则出现了身份阶层的分别。如民国《翼城县志》卷十六载:“(元宵)士女夜游不禁,至十六日亦然。此二日间乡村男女观剧、观灯,恣意游玩。亦多来城,周历街巷,名曰‘走百病’,谓此一走而百病可除也。然亦庶民小户如此,绅士之家则否矣。”*《翼城县志》,民国十八年铅印本,引自丁世良、赵放《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华北卷》,书目文献出版社,1991年,第656页。士绅之家不参与,其实因为封建礼教认为女子应该足不出户,男女更不应同游。但是,作为一种风俗论述与实践,“走百病”为妇女元夕出游以及男女同游提供了暂时越界的正当性。走百病以日夜接续、城乡交通、男女杂处、官民同乐、以及雅俗并陈的方式,颠覆“礼典”与“法度”所调控定位的日常(everydayness)——从日夜之差、城乡之隔、贵贱之别到男女之防。而这种暂时性的越界与乌托邦里的狂欢,可以解释成盛世太平中民间活力的展现,也可以功能性地视为岁时生活的调节,或是积郁力量的抒解,但也可能被判定为对礼教规范与法律秩序的扭曲与破坏。因此尽管历代不乏士人从统治阶层的立场衡量,尝试祛除、禁绝所有非礼不经的行为。但衡诸历史,尽管民间狂欢的活动内容因时因地而演进分化,但究其基调,显然从未在元宵嘉年华会里褪色消失。*陈熙远:《中国夜未眠——明清时期的元宵,夜禁与狂欢》,《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2006年第4期。
不过,由于医疗卫生水平的提高、妇女解放和妇女地位的提升、生育观念的转变以及狂欢娱乐手段的多样化以及一些偶发事件,晚清民国以来,不少地方的“走百病”的驱鬼度厄和求子生育内涵逐渐弱化,或者隐没于元宵节俗之中,甚至而渐渐消失了。如据张江裁《北平岁时志》载,走桥摸锁的习俗至庚子(公元1900)年正阳门被灾后才完全消失。*张江裁:《北平岁时志》卷一,见国立北京大学中国民俗学会编《民俗丛书》第87册,1976年,第22页。《津门杂谈》指出:“原来在津卫里一般老根旧底大宅门的妇女们,一向是讲究大门不过,二门不出,规规矩矩的深藏在在家里。就是有时候到亲友家里‘出门’,也是车来轿去,轻易不肯随便的出现在街上。当年一般妇女,尤其是青年的妇女们,受了多年沿传下来的旧礼教所束缚,是处处不能像男子般那样自由行动。所谓正月十六这天,要巧立一个名目,叫做‘走百病’的日子,是一般妇女借题发挥的一个公开解放日子而已。时至今日,民智大开,潮流日趋摩登。一般时髦妇女,无论是千金小姐,或者小家碧玉们日夜可以出入各娱乐场所,或是在马路上游逛。早已是打破“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旧俗,冲开礼教束缚圈,不像从前那样受拘束了。所以这妇女界一年一度的正月十六‘走百病’日子,在今日津卫里已不像从前那样为一般妇女所重视了,当做一种习俗罢了。”*刘炎臣:《津门杂谈》,三友美术社1943年版,第63页。
综上所述,走百病习俗其实是一个多民族、多源流的,兼具累积沉淀型和合流变形型类型特点的民俗,具有展现中华民族文化创造力的杰出价值的民间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具有促进中华民族文化认同、增强社会凝聚力、增进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的作用;在历史学、民族学、民俗学、社会学、人类学及文学等方面均具有重要价值,值得深入研究。
[责任编辑 李 浩]
陈恩维,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中文学院教授(广东广州 510420)。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传统手工艺类非遗的生产性保护及其绩效研究——以佛山为例”(10YGCZH008)的阶段性成果。